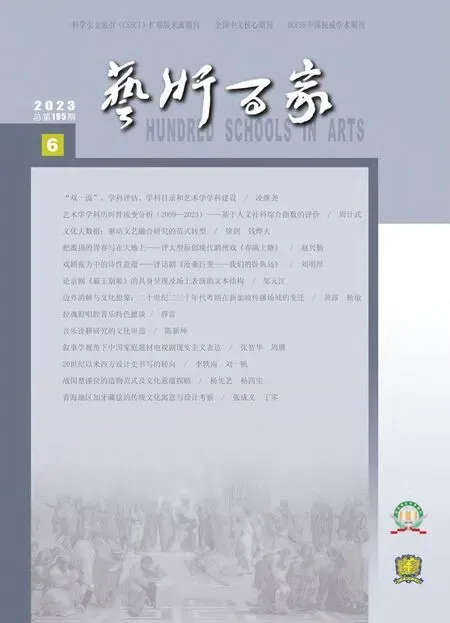音乐诠释研究的文化审思*
陈新坤
(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音乐诠释研究是西方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向度,与客观的实证主义研究和封闭的形式主义研究相比,诠释研究相对主观和开放,它把音乐作品看作一个鲜活而有意味的世界,主张通过感同身受的理解而非客观实证的认知来发掘音乐作品的意义。西方音乐诠释研究肇始于德国,之后在美国蓬勃发展,并进一步影响中国。不同地域的音乐诠释既有相通的一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这三个地域的音乐诠释研究的文化根据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何共性与差异?文章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从自发到自觉的德国音乐诠释
德国的音乐诠释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世纪至20世纪前20年的自发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的自觉时期。①尽管“音乐诠释学”这一术语由赫尔曼·克雷奇马尔于1902年正式提出,但19世纪时已经存在大量音乐诠释现象。卡尔·达尔豪斯指出,19世纪除音乐的手工艺学说与音响学外,属于理论范畴的还有释义学。[1]298
音乐诠释研究肇始于19世纪的德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器乐地位的凸显与浪漫主义美学对器乐的推崇是音乐诠释研究出现的基础。巴洛克时期之前,器乐在西方音乐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巴洛克时期的器乐与声乐并驾齐驱,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的器乐则开始超越声乐,并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尤其体现在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等德国作曲家的创作中。交响曲、奏鸣曲、协奏曲、室内乐、器乐小品等成为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音乐创作的重心,在声乐领域,只有歌剧和艺术歌曲能够与之抗衡。与以往相比,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的很多器乐作品不仅摆脱了外在服务性功能和歌词的束缚,而且进一步摆脱了体裁规范的制约,展示出独特而自足的一面。浪漫主义美学家不再像18世纪的研究者那样把器乐看作低于声乐的空洞音响,而把它看作一种崇高的语言,并开始认为器乐的不确定性优于声乐的确定性。达尔豪斯直言:“器乐的美学在19世纪与以前时代的声乐颠倒过来,带有一种篡位者的特征。”[1]236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路德维希·蒂克、E.T.A.霍夫曼、叔本华等人的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把纯粹的器乐表述为“器乐的形而上学”“作为独立艺术的音乐”“所有艺术中最浪漫的”。[1]81浪漫时期器乐的地位由此得到空前提升,它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让一些研究者产生了对其进行解释的冲动。浪漫主义音乐美学尤其重视器乐的诗化解释,让人们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感觉到“超凡脱俗的存在”和“无穷的渴望”。[1]81之所以出现这种重精神、轻技术的诗化诠释,是因为浪漫主义美学家认为精神是本、形式是末,对音乐技术进行类似解剖学的分析是一种下等行为,他们主张“不是以解剖者的冷静而是以爱好者的热情去谈论一些伟大的作品”[1]263。
另一方面,商业社会的受众需求也是19世纪音乐诠释研究的驱动力。由于社会结构的转变,音乐的受众群体逐渐由贵族转为中产阶级,这些相对缺乏音乐素养的听众与浪漫主义美学家眼中高深莫测的器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音乐诠释则可以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达尔豪斯曾称美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所反对的“陈腐的情感美学”为“音乐大众美学”,并指出当时的音乐诠释与这种情感美学紧密相连,所谓“分析的使用与形式主义的美学、释义学的使用与内容美学是相互联系的”[1]258。这里的“内容美学”指的就是为大众服务的情感美学。而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音乐诠释,标题音乐的解释性文字由作曲家本人撰写,这同样是出于引导听众的目的,即“指导听众按照作曲家的意思来理解作品”[2]134。新德意志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瓦格纳认为,标题音乐具有大众音乐美学的特点,音乐的情感是模糊而抽象的,而标题音乐可以让情感具有某种确定性。正因为主要为音乐会听众写作,早期的音乐诠释往往独立于专业性的作曲理论,寻求“基于内容而非声音本身”的音乐诠释。[3]14当时埃克托尔·柏辽兹、瓦格纳、威廉·冯·伦茨、尤利乌斯·奥古斯特·菲利普·施皮塔、汉斯·冯·沃尔措根等人写了大量基于内容的诠释文字,霍夫曼、舒曼等人的音乐诠释中尽管加入了一些客观的技术分析,但最终目的是导向音乐的诗意内容。克雷奇马尔被认为是早期音乐诠释的集大成者,他为音乐会听众写了大量音乐解说文字。他宣称音乐诠释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理论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所有音乐理论最后的、最珍贵的收获,他还公然承认对音乐作品进行文学性诠释的合法性,指出浪漫主义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首次把音乐诠释学带到公众面前。②
早期音乐诠释在特定时代对公众的音乐理解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随着自律论音乐美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的发展,它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伊恩·本特指出,克雷奇马尔把诠释学建立于巴洛克情感教义基础上的做法,表明了克雷奇马尔对一般诠释学的理解充其量只停留在表面,这把我们带入一个悬而未决的困境。[3]25达尔豪斯则认为早期音乐诠释的衰落是由于“内容的优先权观念损害了结构形式”[1]158。这种主观而缺乏根据的诠释方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被实证主义研究取代,基本处于中断状态。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以达尔豪斯为首的学者们的倡导下,音乐诠释研究才逐渐复兴。
与自发时期音乐诠释的大众性和文学化取向相比,20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的达尔豪斯、汉斯·海因里希·埃格布雷希特等人的音乐诠释更严谨和学理化。一方面,与音乐诠释很少与哲学诠释学发生关联的自发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音乐诠释与马丁·海德格尔和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着根本的联系。在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看来,诠释不是方法问题,而是此在对存在的追问,人只有通过存在物的诠释才能体会存在,诠释学由此发生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重大转向。之前被启蒙主义者所批判的“前见”(Vorurteile)在加达默尔这里成了理解的前提和基础,无须克服而应加以利用,诠释学由此实现了作者中心向读者中心的转移。达尔豪斯、埃格布雷希特等人的音乐诠释就是在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另一方面,以达尔豪斯为首的学者们还对汉斯立克的形式主义美学进行了批判和吸收。针对当时泛滥的情感论,汉斯立克提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4]50这一著名论断,提醒人们要返回音乐本身,注重音乐内在的形式构造。汉斯立克的形式主义美学带有明显的科学实证主义思维,他在《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一书中多次提到“科学”“客观”等词,并声称:“假如美学不致全部成为幻觉的话,那么至少必须采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至少要试图接触事物本身,在千变万化的印象后面,探求事物不变的客观真实。”[4]15究其原因,主要是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让一些学者在人文科学研究中尝试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音乐学(Musikwissenschaft)这门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科学而存在的。1863年,弗里德里希·克里赞德尔指出,音乐学应该与其他学科一样被视为科学,当时的代表人物赫尔曼·冯·黑尔姆霍尔茨和卡尔·施通普夫分别从声学和听觉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科学研究,他们试图对很多不确切的感性事项给予确切的解释。[5]489达尔豪斯指出汉斯立克局限于把音乐看作声音事实的观点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它违背了西方音乐历来与歌词、标题、情感相结合的历史,而把情感看作一种外在于音乐的东西同样是有问题的。达尔豪斯借鉴了汉斯立克的形式主义美学观,但否定了汉斯立克把情感排除在音乐之外的做法。他从现象学角度把情感与形式进行整合,宣称音乐并不是反映了“忧郁”这种具体情感,而是这种情感所具有的效果。[6]7可见,达尔豪斯的音乐诠释对汉斯立克的形式主义美学与克雷奇马尔等人的早期音乐诠释进行了批判和继承,指出形式与情感并不是二分的,而是一体两面、主客合一的关系。有人因此认为达尔豪斯所追求的是一种以音乐形式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诠释学”(Formalist Hermeneutics)。[5]494达尔豪斯还进一步把形式与历史相关联,指出“审美和历史之间的调解只能产生于这种诠释——它通过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个别作品在历史中的位置”[7]49。埃格布雷希特也是这一时期音乐诠释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与达尔豪斯一样受到加达默尔诠释学的影响,主张美学理解是一切理解的基础,并借用加达默尔的“游戏说”对音乐作品进行诠释,声称真正的理解就是对作品游戏规则的理解,这同样体现了以形式为基础的音乐诠释路向。
二、多元并举的美国音乐诠释
如果说德国是音乐诠释研究的发源地,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则是音乐诠释研究的重镇,它与德国音乐诠释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很大不同。美国的音乐诠释既吸收了德国以审美为基础的诠释方式,又对其进行了拓展。相对于德国,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更容易受到新事物和新观念的影响,在音乐诠释中借鉴了当时盛行的文化、政治、性别等研究取向。因此,与保守的德国音乐诠释相比③,美国的音乐诠释更加开放、多元与包容,它在传统音乐诠释的基础上尝试更多可能,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
一方面,美国的音乐诠释与德国的音乐诠释有内在的关联,美国音乐诠释是德国音乐诠释的进一步发展。受战争、政治等因素影响,一些德国音乐学家如西奥多·阿多尔诺、列奥·特雷特勒等移民美国,促进了美国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并使其成为欧陆之外的第二个音乐学研究中心,一些德语研究文献也陆续被翻译成英文,促进了英语界对德国音乐学术资源的吸收。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音乐诠释基本以它为基础进行展开。以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为基础的达尔豪斯、埃格布雷希特等人的音乐诠释研究,同样对美国音乐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直言加达默尔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德国音乐学家达尔豪斯,而达尔豪斯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美国音乐学施加了强烈影响。[5]494与德国的音乐诠释研究相比,美国的音乐诠释研究同样经历了对科学实证主义思维的批判过程。约瑟夫·克尔曼发现了实证研究的弊端,他在文章《美国音乐学概览》和《我们如何走进分析,又如何走出》及著作《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中对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主张批评式的音乐研究,由此拉开了美国音乐诠释研究的序幕。爱德华·T.科恩、劳伦斯·克雷默、苏珊·麦克拉蕊等美国音乐学家在克尔曼的基础上不断把音乐诠释研究推向高潮。无怪乎本特声称:“在英语界,探索音乐诠释学的驱动力量无疑是约瑟夫·克尔曼为批评而进行的论战。”[8]1另一方面,美国的音乐诠释在吸收德国音乐诠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很大拓展。克尔曼在音乐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吸收了英美的新批评思想,主张对音乐进行文本细读,同时强调研究应该注重“音乐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的互动”[9]30。随着意识形态批判、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性别研究等思潮的不断涌现,美国的音乐诠释变得越来越激进与多元,与德国保守的形式与审美诠释形成鲜明对比。
阿多尔诺的音乐社会学和音乐批评对美国的音乐诠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阿多尔诺的成果在国外比在他自己的国家更受欢迎。[5]494当然,美国音乐学家对阿多尔诺的音乐思想并非照单全收,查尔斯·罗森、特雷特勒等人也像达尔豪斯一样,批判地看待阿多尔诺的音乐社会学和批评,罗森戏称阿多尔诺眼中的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为一种轻率的隐喻。[10]25但是,阿多尔诺有关音乐的社会政治批判为美国音乐诠释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与达尔豪斯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合一不同,阿多尔诺认为艺术具有两重性,即它是自律的,又是社会性的。[11]8阿多尔诺的音乐辩证法就是一个从社会视角看音乐的经典案例,他声称奏鸣曲中代表大众的和声与代表个体的旋律之间的冲突就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与个人利益之间冲突的反映。阿多尔诺认为贝多芬音乐作品的形式是由社会转化而来的,它主要体现了社会冲突,个人感情表现相对比较节制,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音乐则非常个人化,它陷入一种自我满足的荣耀。[10]256-257如果说达尔豪斯有保留地吸收了阿多尔诺的音乐诠释观,主要在形式和审美层面对音乐进行诠释,那么一些美国的音乐诠释者则大胆吸收了阿多尔诺从社会、政治等方面诠释音乐的策略。美国音乐学家罗斯·罗森高·苏博特尼克不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把阿多尔诺的成果陆续介绍给英语界,而且还用阿多尔诺的音乐社会学思想进行音乐诠释。她在著作《发展中的变奏:西方音乐的风格和意识形态》中批判性地吸收了康德、阿多尔诺等人的思想,挑战了音乐的意义只来自内部结构形式的看法,试图建立音乐与社会和哲学的联系,指出风格是社会交流的模式,而意识形态是音乐产生的社会背景。[12]3-14麦克拉蕊把音乐的意义与社会和政治进行关联,声称音乐就是一种社会交谈,“作曲家在谈话中面对既有的范式可以有多种选择,或遵照、或颠覆范式的传统意指,或强调、或轻视范式中固有的矛盾冲突,而意义借助特定的选择而产生”[13]139。理查德·塔鲁斯金宣称音乐与政治密不可分,指出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明显刻上了他所信奉的斯大林主义。[14]60
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为代表,之后逐渐掀起了席卷全球的文化研究热潮,渗透到包括音乐诠释研究在内的各个领域。同时,民族音乐学的文化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西方音乐的文化诠释研究。传统的西方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本体,通过音符之间的关系和整体结构而展开,文化研究则试图发现音乐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克雷默是主张对音乐进行文化诠释的重要代表,他把音乐看作一种文化实践,特别注重文化在诠释中的参与性和能动性,认为“音乐也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的能动性,即作为具体话语实践的参与者,而非它们的一面镜子”[15]270。加里·汤姆林森同样十分重视音乐的文化诠释,但与克莱默将音乐作为文化实践的主张不同,汤姆林森更强调文化语境在诠释中的作用。他受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观的影响,指出音乐作品就是人类创造性行动的编码和反映,因此应该通过文化语境的诠释而被理解。文化就是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网,一个人通过它与周围的另一个人乃至世界发生联系,“意义源于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在语境中的关联,没有文化语境就没有意义”[16]350。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对美国音乐诠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麦克拉蕊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学家的音乐诠释中,这里的性别主要体现在社会层面而非生理层面。麦克拉蕊认为贝多芬的许多交响曲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胜利,《第九交响曲》最鲜明地表现了启蒙运动以来父权制的残暴性。[17]129而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则带有男性同性恋倾向。[17]79卡罗琳·阿巴特通过研究施特劳斯的歌剧《莎乐美》,指出作曲家试图通过消除男性的权威声音,诱骗人们的耳朵从女性角度进行倾听。[18]247
质言之,美国的音乐诠释带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如果说德国的音乐诠释体现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固守,那么美国的音乐诠释则体现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它试图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种终极的理性,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既定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打破这一旧有模式,通过去中心、解构、颠倒等方式对既定的法则、秩序和封闭式结构进行颠覆和破坏,走向多元文化和相对价值。有人坦言“后现代主义音乐学的建构将解除音乐内部和外部本质的边界”[19]144,克尔曼对传统音乐学封闭的、进化论式的研究方式的批判,实质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而他提到的政治和社会的视角就是在寻找封闭结构的突破点,寻求“学术音乐批评中的新跨度和灵活性”[20]313。克雷默的“诠释学之窗”(Hermeneutic Windows)④更是如此。本特指出,音乐诠释透过这些窗口就可以进入文化领域,发现该作品与其他音乐作品、文学作品、视觉艺术、哲学与其他文化的联系,这一观念来自话语理论、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3]27
三、中西结合的中国音乐诠释
与德国和美国这两个音乐诠释研究比较活跃的地域相比,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音乐诠释方面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目前,国内音乐诠释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于润洋的文章《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1993)和著作《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杨燕迪的文章《音乐理解的途径:论“立意”及其实现》(2004)和《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作品29的个案研究》(2009),姚亚平的著作《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2015)等。中国音乐诠释勃兴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我国自古就具有朴素的音乐诠释传统。有人声称孔子对《周易》的读解在中国诠释传统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并指出孔子的诠释观因以“立德”为宗旨而带有教化色彩。[21]158就音乐而言,在“文以载道”思想的支配下,我国形式主义色彩的纯音乐相对较少,乐曲常常带有类似西方标题音乐的文字暗示,如琴曲《酒狂》《潇湘水云》《梅花三弄》,琵琶曲《十面埋伏》《海青拿天鹅》等,近现代依托西方音乐体裁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钢琴协奏曲《黄河》等也带有一定的标题暗示。由于受“文人音乐”思维的影响,人们在听音乐时总希望能从音乐中感受到一些人文内涵。钟子期对俞伯牙琴曲《高山流水》的读解就是一个经典例子,白居易《琵琶行》的经典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则通过象征的手法对音乐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陶渊明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更达到了注重音乐内容的极致。当然,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诠释,但无疑具有音乐诠释的冲动。这种朴素的音乐诠释传统或多或少潜藏在中国音乐学者的思维中,成为音乐诠释研究的内在驱动力量。其二,欧美音乐诠释理论和实践的传入,激发了中国音乐学者的音乐诠释研究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音乐学者开始赴欧美求学,西方的诠释学和音乐诠释思潮也不断涌入中国,我国的一些从事音乐诠释研究的学者对西方哲学诠释学和音乐诠释理论较为了解,对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有比较强的认同感,如于润洋的文章《从海德格尔阐释梵·高的〈农鞋〉所想到的》(2002)。中国音乐学者还译介了一些西方音乐诠释研究方面的论著,扩大了西方音乐诠释研究对我国的影响,如于润洋翻译的《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2003),张馨涛翻译麦克拉蕊的《阴性终止》(2003),刘经树翻译埃格布雷希特的《西方音乐》(2005),杨燕迪翻译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原理》(2006),朱丹丹与汤亚汀翻译克尔曼的《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2008),何弦翻译科恩的《作曲家的人格声音》(2011)等。其三,中国的西方音乐诠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音乐学者的文化自觉和主动选择。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局外人,如果仿照西方音乐的手稿研究、资料考据的实证主义研究的路数,很难企及西方音乐学者所取得的成就,毕竟这种研究依靠的是占有一手资料,而选择诠释研究路数则可以避开这一研究劣势,与西方学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正如有人所言,“正是由于学术重心转向了阐释,它支持了个性化的创造,西方传统的优势——实证的、客观的、以探索规律为己任的学术势力被削弱了”[22]23。
具体来看,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诠释研究既没有德国那样保守,也没有美国那样开放和多元,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体现了中庸之道。中国的音乐诠释同样建立在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础上,与达尔豪斯、埃格布雷希特等人的音乐诠释研究一样,试图弥合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裂隙。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试图借助审美描述来使音乐本体和社会历史之间实现沟通和融合。如他指出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的第一主题为整部作品奠定了“阴沉、抑郁的气氛基调”,而第二主题“透着温情、又隐含着痛苦的感情”。[23]43这种情感性的审美描述把客观的技法分析与主观的审美体验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为“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分析”[23]39作铺垫。姚亚平指出:“真正的音乐学分析应该关涉这两个部分,或者说应该努力化解和突破这两个部分的二元分离关系,使之互相说明、互相支持,合力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24]55可见,于润洋的“音乐学分析”既借鉴了审美诠释,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传统。姚亚平在音乐诠释研究方面也是一位较为活跃的学者,他除了对润洋的“音乐学分析”进行学术探讨,还亲自进行音乐诠释实践,其专著《性别焦虑与冲突:男性表达与呈现的音乐阐释》尝试从男性视角进行音乐诠释,接续了麦克拉蕊《阴性终止》以女性为视角的诠释方式,是性别研究的一次突破。他指出,麦克拉蕊提出调性是男性话语和父权制象征的观点很有想象力,但作者并没有对此进行充分论证,因而给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大空间。姚亚平在这本书中以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为对象,通过多方面考察得出结论:相对于贝多芬音乐的绝对男性化,柏辽兹的这部作品带有较强的阴性特质。该书进一步指出19世纪音乐语言的种种变化,如“调性概念的松动,奏鸣曲及奏鸣曲式的危机等,都是父权制危机的征兆”[25]37。杨燕迪提出的“立意”说同样是为了弥合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割裂状态,所谓“避免有关音乐的文字表述中常见的内容/意义诠释和形式/结构分析的彼此分离”[26]57,这里的“立意”并不是回到作曲家的主观意图,而是“超越了创作家自己所能意识到的创作意图范围”[26]56。可见,中国学者的音乐诠释既与德国、美国的音乐诠释有内在的联系,又具有自己的诉求意义。
四、结语
我们由上面论述可知,受地域文化的制约,不同地域的音乐诠释研究既具有相通的一面,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德国之所以成为音乐诠释的发源地,是因为它与德国音乐,尤其是器乐在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的崛起有着根本的关系,亚伯拉罕直接称这一时期为德国中心。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成为音乐的主要受众群体,他们无法理解浪漫主义美学家眼中的诗意的音乐,音乐诠释研究的出现则拉近了他们与音乐之间的距离。自发时期的德国音乐诠释主要面对大众进行写作,以激发公众对音乐的兴趣为导向,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和文学性。自觉时期的德国音乐诠释则通过对早期音乐诠释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批判与吸收,以及与哲学诠释学的勾连,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和学理性。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音乐诠释在德国音乐诠释的基础上进行拓展,社会、文化、政治、性别等诠释视角的引入为音乐诠释研究带来了更多可能。当然,这种诠释不同于把音乐与外部世界做机械对应的德国早期音乐诠释,而试图从音乐的内在进程中寻找证据,也不同于主要限制在形式和审美层面的德国自觉时期的音乐诠释,而寻找音乐诠释的各种可能。中国音乐学者之所以对音乐诠释这种研究方式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国自古就具有朴素的音乐诠释传统,而西方音乐诠释理论和实践的传入,则激发中国音乐学者从学理上对音乐诠释进行思考和建构的积极性。当下,音乐诠释和批评研究已经成为音乐研究的趋势,音乐诠释对象也由西方音乐拓展到非西方音乐,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音乐诠释体系,为世界贡献中国的音乐诠释智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可以相互激发彼此音乐诠释探究的潜能,正如有人所言,“文化的旅行是学者对于制度的一种反叛的策略,通过连接社会关系和文化网络作出理性的思辨,揭示其中的复杂矛盾,以某种激情来憧憬未来的文化”[27]215。
① 由于德国1871年才建立统一的国家,这里的德国并非指政治上的德国,而是指文化上的德国。
② 赫尔曼·克雷奇马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为当时的听众写了一些音乐评论。
③ 有人指出,卡尔·达尔豪斯曾着迷于西奥多·阿多尔诺的思想,但反对他的社会学方法,而把诠释集中在音乐形式本身。参见:Stanley Sadie,TheNewGroveDictionaryofMusicandMusicians,Macmillam Publishers Limited,2001。
④ “诠释学之窗”主要指作品中的不同寻常之处,通常表现为一些不连续或过度表达的地方。参见:Lawrence Kramer,MusicasCulturalPractice,1800—190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