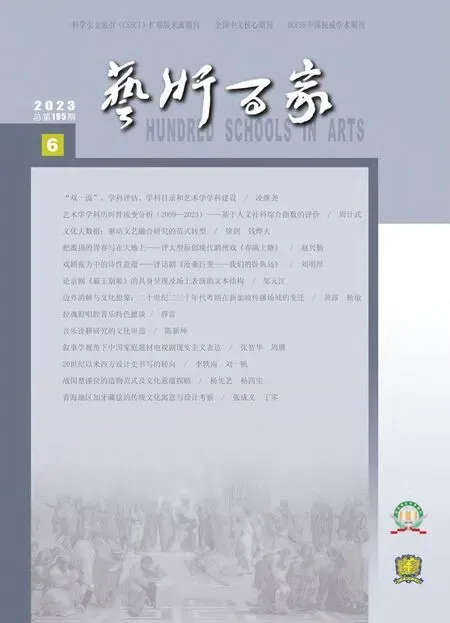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症候反思与文化建构*
王思源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6)
自2004年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被改编为电视剧以来,言情剧、穿越剧、宫斗剧占据了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的主流市场。2015年,改编自同名网络仙侠小说的电视剧《花千骨》热播,自此掀起了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热潮,涌现出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香蜜沉沉烬如霜》(2018)、《琉璃》(2020)、《沉香如屑》(2022)、《苍兰诀》(2022)等一系列剧作,它们呈现出了恢宏的想象力与绮丽的东方美学色彩,以奇幻的世界观架构和古今互通的叙事策略吸引了观众。近些年来,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热度虽未冷却,但极端相似的情节桥段与视觉呈现未免使观众兴致不高,长此以往,并不利于仙侠小说IP资源的可持续转换。因此,在竞争愈发激烈的创作环境之下,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不应以快速获利为导向而过度依赖“粉丝经济”,而要深度挖掘仙侠题材特有的叙事魅力,走精品化之路。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强调“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1]无疑,仙侠剧擅长将浪漫爱情、个人成长、英雄救世等经典母题联结在一起,用古神话外衣与数字时代的技术奇观包装它们,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了传统文化现代意义,是具备中国特色的想象力资源。而网络仙侠小说又为影视呈现提供了丰厚的故事素材,在仙侠空间的表征之下,是现代个体的所思所想与精神困境。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提高独特的“中国式浪漫”的文化影响力,是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实现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媒介融合与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本文旨在厘清“仙侠”概念及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发展历程,并反思现有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创作症候,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网络仙侠小说建构文化载体,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
一、发展历程:从百花竞放到门前冷落
关于“仙侠”概念,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暂无定论。《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指出,“仙侠”一词是“修仙”和“修真”的混称,是“从传统武侠和神魔小说中生长出来的、对内容和结构有较强规定性的中国风格的网络幻想小说类型”。按照故事发生的世界背景,修仙可分为“古典仙侠”“幻想修仙”“现代修仙”“洪荒封神”四个类型,被大众称为“仙侠”的是“以中国古代社会为背景的修仙小说”,即古典修仙,其核心是“由人修炼成仙的过程”。[2]253-254戴清认为:“‘仙侠奇幻’题材影视剧以表现神、仙、妖、魔的情感故事和正邪较量为主要内容,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自然能力,在艺术风格上充满非写实的瑰奇浪漫色彩。”[3]47也有学者倾向于将“仙侠”和“玄幻”融为一体来谈——“仙侠玄幻剧是仙侠剧和玄幻剧的统称,通常改编自网络游戏和网络小说,主要以修仙成侠、斩妖降魔为故事主线,讲述仙、神、魔、妖界的神话故事和情仇异事”[4]47。但玄幻题材小说的世界观架构糅合了较多的西方奇幻元素,与倚重东方气质的仙侠题材小说略有不同。综上来看,本文所述的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主要是指改编自网络作家发表在网络平台上的,以中国神话世界或古代“架空”社会为背景,以仙、神、魔、妖、鬼、怪等脱胎于中国神话、民间传说的超自然能力者为主要人物,以个人成长及侠义行为、各族间的爱恨情仇为主要情节的小说的电视剧,其特点是画面效果精美、颇具东方意境。
最早的仙侠剧可追溯至1991年的《蜀山奇侠》(包括《蜀山奇侠之紫青双剑》和《蜀山奇侠之仙侣奇缘》两部),但真正令仙侠题材在电视荧屏上崭露头角,使仙侠剧成为类型剧并获得口碑与收视率双丰收的电视剧是改编自同名网络游戏的《仙剑奇侠传》(2005),同样改编自游戏的《仙剑奇侠传三》(2009)、《轩辕剑之天之痕》(2012)、《古剑奇谭》(2014)等电视剧也是战绩斐然。此时,市场上尚未出现优秀的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这一时期的仙侠剧作品虽然不多,但是精品率较高,不仅有荡气回肠的爱情,也有并肩作战的友情,更有赤胆忠心的家国之情,其叙事结构、人物设定与仙侠意蕴大致符合观众的预期。直到2015年,改编自Fresh果果创作的同名网络仙侠小说的电视剧《花千骨》一鸣惊人,自此掀起了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热潮。在网络小说丰富的资源加持下,仙侠剧如虎添翼,进入发展期,这一时期同时也是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萌芽期。2017—2019年是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的繁荣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香蜜沉沉烬如霜》(2018)、《扶摇》(2018)、《陈情令》(2019)等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接踵而至。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相比早期的仙侠剧,行侠仗义的叙事比重减少,情节的设置多为男女主人公的旷世虐恋服务,“侠”的内核愈发空洞,“情”与“恋”开始喧宾夺主。2019年“限古令”发布后,在卫视综合频道播出的仙侠剧受到限制。但从2020年开始,仙侠剧多以网络剧的形式出现,数量未减反增,《琉璃》(2020)、《三千鸦杀》(2020)、《三生三世枕上书》(2020)、《且听凤鸣》(2020)、《千古玦尘》(2021)等均为在此时期播出的作品。2022年至今,仙侠剧发展已经白热化,涌现出《镜·双城》(2022)、《与君初相识》(2022)、《沉香如屑》(2022)、《苍兰诀》(2022)、《月歌行》(2022)、《玉骨遥》(2023)、《长相思》(2023)、《七时吉祥》(2023)、《尘缘》(2023)、《护心》(2023)、《重紫》(2023)等作品,但除却《琉璃》《苍兰诀》和《长相思》的观众接受度与评价尚可之外,其余的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虽然保持着较高的受众关注度,但是口碑评价却陷入低迷,甚至差评如潮。例如观众认为《千古玦尘》“空有高价特效,内里华而不实”,《镜·双城》“本末倒置,轻家国之情,重CP虐恋”,《重紫》“是‘低配版’的《花千骨》”,等等。即便有流量明星为这些剧作的曝光量“保驾护航”,但千篇一律的故事套路却再难打动人心。
从百花竞放到门前冷落,仙侠剧被视作类型剧已有十八年,而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也已有八年的发展历程。仙侠剧少有原创剧本,早期的仙侠剧多改编自网络游戏,在仙侠剧百花竞放的井喷时期,大多数作品改编自网络小说。“限古令”颁布之后,仙侠剧以网络剧的形式大量上线,但作品质量却断崖式下跌。可见在流量时代,激烈“内卷”的作品并未带来创意与创新,反倒深陷流水线式的机械复制。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观众群体的大量流失,更会使观众对仙侠题材产生反感情绪。通过探析仙侠剧的发展脉络、分析其热度及公众评价,我们或能找出其症候所在,以突破困境重续新神话主义的辉煌,建构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故事。
二、症候反思:泛情叙事与艺术惰性
伴随后现代语境中个人主义的高涨,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活跃于荧屏之上,侠义与成长叙事逐步让位于情爱叙事。电视剧沿用了网络仙侠小说的“现代消费主义精神”[5]1,即人物面对困境的自主挣扎逐渐隐匿,转变为一种自身携带的“主角光环”和“爱情之力”,人物在自恋与他恋中反复横跳,这也可引申为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的交织。在弗洛伊德看来,“理想自我属于对自我的里比多灌注,而自我理想属于对客体的里比多灌注,客体里比多对象是自己之外的对象。尽管自我理想的里比多能量向外投射,但是本质依然是自恋的,因为爱别人其实就等于爱自己”[6]17。即言之,过往的行侠仗义在“现代消费主义精神”之下,天下大义让位于个人私情,而私情被承载于泛情的叙事样态中。
在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中,主角都不再是纯粹的肉体凡胎,即便他们开场时以凡人或灵力低微的形象出现,但他们各个拥有非凡的宿命,以满足理想自我的期许。如《花千骨》中的花千骨是女娲后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浅有上神身份的庇佑、《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锦觅是花神的后代、《琉璃》中的褚璇玑是战神转世……她们天赋异禀,遇到磨难时,“主角光环”和“爱情之力”必会有其一在场。譬如花千骨遭遇埋伏,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她身上隐藏的洪荒之力被激活,惊退众人——“主角光环”助其脱困;在修仙之旅中,花千骨同时获得异朽阁阁主东方彧卿、魔君杀阡陌、西蜀皇帝孟玄朗的好感,更有“官配”长留上仙白子画护其周全——危难之际“爱情之力”轮番登场拯救花千骨。而花千骨自身的冒险之旅也并非为了苍生大义,而是为了一己之情。剧情高潮是花千骨为救了白子画,迫不得已集齐神器,引发了洪荒之灾。而这一切的缘由是夏紫薰因对白子画爱而不得而堕入魔道,她得知花千骨是白子画的生死劫,便设计幻境毒害花千骨,千钧一发之际白子画救了花千骨,他自己却身中卜元鼎之毒。一切因果似乎都基于个人私情,白子画一次又一次弃花千骨于不顾的自我感动是制造旷世虐恋的不二法门,苍生大义与悲悯之心仅为人物口中虚妄的言辞和与情对立的矛盾设置,而非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而与主角“自恋与他恋”相对应的是配角的“单恋和卑恋”,典型表现为爱而不得与为爱疯魔,如上文提到的《花千骨》中的夏紫薰,若非夏紫薰对白子画爱得太深,白子画中卜元鼎之毒的情节也就无从推动;若非东方彧卿深爱花千骨,宁可自己承受“五官尽失,不得好死”的代价,花千骨也难逃蛮荒之劫。无独有偶,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孤女素锦痴恋夜华,于是她处处针对素素,离间素素与夜华,致使素素伤心欲绝,这才有了素素跳下诛仙台并飞升成为上神的情节。配角的爱恨情仇一方面推动了剧情主线的发展,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主角人格魅力之强大及男女主人公爱情之伟大。而这种充满悲剧感的、扭曲的情感,在剧作中,美其名曰“爱之深切”,实际上将自我异化为了爱情的附属品,是虚假的自我感动。由此可见,从第一部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花千骨》开始,泛情化叙事便已初见端倪。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又强化了世代相恋的爱情宿命感。青丘女君白浅与九重天太子夜华为爱纠缠三生三世,并在一世又一世的相遇中相恋。尽管《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借用中国传统神话,建构出了天族、九尾狐族、翼族等族群共存的仙界秩序,并设计了由人到仙、由仙到神的修仙顺序,但在这一具备宏大世界观空间之中发生的矛盾纠葛皆以“情爱”为叙事动力,例如墨渊在封印擎苍一战中牺牲,是因为在此之前他为了守护爱徒司音而遭受了飞升之劫,功力受损;夜华为了封印擎苍牺牲,表面是为维护四海八荒的太平,但更重要的动因是守护爱妻白浅。在仙侠世界宏大的世界观下,故事非但没有拓展出多维度的叙事,反而局限在情爱视域中并将爱情提纯,仙侠沦为爱情的保护伞,成为突破时空,突破禁忌,可以容纳师徒之间、同性之间禁忌之恋的空间。
而《花千骨》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火爆,也为投资人选择剧本提供了范例,大量“女频”(女生频道)网络仙侠小说被选中改编,剧方挪用原作中女性向情感模式,建构浪漫的温柔乡,打造无关现实的乌托邦,爱情成为毋庸置疑的神圣信仰,所有人都可以为了爱情前仆后继而不必觉得羞愧或遭受道德审判。如《香蜜沉沉烬如霜》虽然有一定创新,但是通篇还是围绕“情”展开,故事主线为锦觅、旭凤、润玉三人之间的情感牵缠,而这一切皆源于他们父辈之间的情爱纠葛。从小被种下“陨丹”(让人断情绝爱的丹药)的锦觅对男女之情毫无认知,这为锦觅性格的转变和感情的转折埋下伏笔,观众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锦觅的天真与坦率,“陨丹”作为重要的线索从一开始便推动着情感线的发展。《琉璃》女主人公褚璇玑沿用了锦觅“六识残缺”(心智未开,不懂情爱)这一设定。剧作重点刻画褚璇玑与禹司凤的情感纠纷,并大胆地把轮回情缘化作十生十世——男女主人公历经多次轮回,具有超越人性般矢志不渝的情感。网络仙侠小说乐此不疲地借用仙侠的背景,无限想象神、仙、妖、鬼等各式角色,上演痴情缠绵的情感故事,而改编剧则直接挪用这些经过市场检验的IP,让这些文字的幻想成为真实可见的视觉形象,酣畅淋漓地表达着充满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色彩、跨过种族与时空的障碍以达成永恒的相守的爱情,仙侠的存在似乎沦为了情之多样化的保护伞。在前人作品成功的基础上,此后的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几乎沿用了这些叙事元素,不仅如此,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甚至衍生出“样板服化道”,后续的大量剧作都沿用经市场检验的“爆款”剧的服化道美学与场景特效。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成为“爆款”剧之后,其“披散长发+素色纱裙”的角色造型被大量的仙侠剧沿用至今,甚至不同剧作中的角色放在同一个剧作中都不违和,如《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锦觅和《沉香如屑》中的颜淡,她们的造型均为简单的发髻配以披散的长发、身着素淡的长裙,角色辨识度几乎为零。而《千古玦尘》全剧中的人物,不论身份地位,服装颜色都统一为白色,这种同质化的造型被网友嘲弄为“丧葬风”。尽管仙侠剧中的人物身着白衣颇有仙风道骨的气韵,符合观众对仙界尊者的想象,无可厚非,但投机取巧、模式化的复制与重组却难消观众的审美倦怠感。仙侠剧的艺术创新手段愈加匮乏,充斥着复制“爆款”的惰性症候。
此类倚重情爱、挪用“爆款”剧成功经验的改编方式,或许是为了还原原作的基本情节与故事内核,却也携带了方便拍摄、节省经费的功利性动机,毕竟“热门网络小说+流量明星+嗑cp+仙气满满的服化道”可保证剧作在商业竞争中立足,是较为稳妥且省力的一种投资。但是这种改编方式会让剧作陷入一种“后情感”模式,即梅斯特罗维奇所述的“一种新的被智能化(Intellectualized)、机械化(Mechanical)、批量生产(Mass-Produced)的情感样式”[7]26的创作窠臼,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将自发的情感粉饰为大众热衷于看到的“后情感”。而更加立体的人物形象、更为合理的剧情框架对编剧创作来说有一定难度,对长期沉溺于碎片化信息的“网生代”受众来说终归有一定的欣赏门槛。然而,当观众被套路喂饱了,看够了千篇一律的人物形象和满屏白衣,一味追求“爽”和“肤浅爱”的批量复制作品势必自作自受,面临淘汰。
三、文化建构:侠义精神与海外传播
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要突破创作瓶颈,实现更广泛的文化传播,绝非执着于在男女主人公“几生几世”的情缘轮回、主角身世或爱情阻力方面下功夫,或雕琢视效奇观,而应聚焦故事本身,在剧作的文化格局上做文章。“仙侠”,顾名思义由“仙”文化和“侠”文化组成,脱胎于中国上古神话、具备虚拟性和奇幻色彩的仙文化打开了文化的想象空间,是一件浪漫华美的形式外衣,为现世的哲思披上一层神秘的纱,而作为内核的侠文化才是故事落地的关键。相较于仙文化,侠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侠文化的核心要义为侠义精神,它强调的是维护正义、惩恶扬善、不畏权贵、锄强扶弱等正直品格。侠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墨家文化,如“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8]126。当时社会动荡,诸侯争霸,游侠、门客等人物应运而生,他们通常武艺高强,重信守诺,具备侠义的原始品质,毕生游走于各国之间,为人排忧解难,逐渐形成了侠文化的雏形。秦汉时期,侠文化得到了正式的传播和发展。唐宋时期是侠义精神真正的繁荣时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侠义故事,如唐传奇小说《红线传》《聂隐娘》,宋代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歌颂了侠士们的英勇事迹,使侠义精神深入人心。到了明清时期,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与通俗小说《水浒传》等作品兴起,侠义精神开始从传统的游侠向武侠与江湖世界转型。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侠文化多代表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替天行道”和“为民除害”等言辞都是众人锄强扶弱的信条,因此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反抗权贵、劫富济贫的侠义品格颇受称赞。到了法制健全、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以武犯禁的侠义精神不再被推崇,取而代之的是儒侠互补的现代侠义精神,行侠者无须以“天”的名义化为神仙惩戒恶人,身为凡人也亦可怀揣侠义与仁爱之心,心系民众,与黑暗和不公做对抗,是普通人的英雄。“英雄崇拜,是存在的,正如它以前永远存在、到处都存在一样,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它就不会停止。”[9]12真正的英雄侠肝义胆,心系天下,而不是沉溺于个人私情,追求表面的自我感动式的舍生取义。
早期仙侠剧《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在神秘力量的驱使下来到仙灵岛冒险,尽管他也曾陷入与赵灵儿和林月如之间的情感纠葛,但是他与反派斗智斗勇,最终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再如《仙剑奇侠传三》中的群像叙事,普通人历经磨难、修炼成仙的过程纵然大快人心,但令观众为之震颤的却是龙葵为了消灭邪剑仙舍身跳下铸剑炉与镇妖剑合体、茂茂割肉为百姓换取粮食、景天以献祭阳寿为代价换得众生重生的那些大义凛然的瞬间,并非花千骨胁迫白子画“选天下还是选我”的浅薄试探。在仙侠剧中融入爱情叙事的本意是赋予神仙以人的情感,以微观叙事承载宏大的侠义主题,但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却将“情”化作主体,侠义精神被置若罔闻,这正是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每况愈下的症结所在,重拾侠义精神,才能使仙侠剧平稳落地,不再是悬浮在情欲世界的空中楼阁。脱胎于后现代主义、遵循快乐原则的网络小说与传统主流娱乐形式有截然不同的使命,所以仙侠剧很难依循“忠实原作”的原则去进行改编,但在狂欢的世界中解构出一个个侠骨柔情的血肉之躯,并不意味着要背离原著;消解泛情叙事,也并非完全摈弃私情的存在——否则又会回落到宏大叙事与英雄主义的窠臼中,并不利于“网生代”受众的接受。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中,故事的精彩程度才是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是否优秀的标准。如《苍兰诀》便平衡了情爱书写与侠义精神表达,剧作遵循原作立意,但对原作的人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原作中的东方青苍生性自私、狂傲不羁、痴迷变强,对月族子民并无怜悯之意,而电视剧将东方青苍冷酷狂傲的性格归咎于他要修炼业火、守护月族子民,不得已才断情绝爱。与小兰花的相遇相知逐渐唤醒了东方青苍封存已久的爱人的能力,从绝情灭性到情根深种,这样的改动丰富了东方青苍的人格特性。因为参悟了“爱一人”,东方青苍也学会了“爱苍生”,拥有了比业火更为纯净慈悲的琉璃火。而在取材于《山海经》的《长相思》中,女主人公小夭历经磨难却仍心怀善良,在清水镇悬壶济世,当她恢复王姬身份之后,又一心辅佐神族帝王玱玹继位。玱玹目睹亲人逝世,孤苦无依,明白掌握权力成为明君才能守护亲人和百姓的安宁,为此不得不克制情感,拉拢各方势力,将儿女情长升华为家国大爱。而相柳为了回报恩人情义,成为辰荣义军的军师,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将个人私情抛却脑后。剧中的人物心怀大义,各有抱负,他们都不是圣人,但也正是性格上的瑕疵使其更为真实。侠义精神让人物找回丢失的“侠骨”,此刻的“柔情”才令人动容。
相比历史、现实、悬疑、科幻等题材,仙侠小说携带的中国文化特性最为显著,它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自由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受到国内“网生代”群体的青睐,其海外传播也获得了阶段性成功。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2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000余部……海外用户超过1.5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10]。但据相关学者观察,“由于文化折扣的影响,一些在国内受到追捧的作品在海外却传播效果不佳,而故事性强、具有典型东方神话色彩的玄幻仙侠题材作品构成了海外读者的基本盘”[11]39。而影视作品作为融合视听元素的综合艺术,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的文化载体。优酷发布的《古装剧出海报告》显示,“优酷出品或播出的影视剧出海题材多样,海外播放量近140亿次,覆盖全球超200个国家及地区”,其中YouTube频道口碑评论近30万条,评论热词集中在“侠义精神”“家国情怀”等。[12]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在海外传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自其诞生起,海外传播便随之兴起,《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均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国家播出;《琉璃》在国内首播结束后仅半月,英文字幕版《琉璃》就在美国第二大流媒体平台Prime Video上线,并在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流媒体平台陆续上线,该剧在美国视频网站Rakuten Viki上的评分高达9.6分;《苍兰诀》在国内仅播出一小时,韩国便买下了版权,该剧在全球范围内火速“出圈”,登上了多个国家和地区视频网站热度前十榜单;《长月烬明》(2023)因在服化道和视效上融入了敦煌元素,激发了海外观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等等。由此可见,仙侠题材是中国式想象力消费、传播中国文化、建构中国形象的极佳载体。综合国际评价来看,海外观众热衷于观看仙侠剧的原因大多在于被中国仙文化的形式外衣吸引,对东方异域神话感到好奇以及神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如若能对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加以主流化和精品化的引导,将侠义精神熔铸其中,保持东方想象力的创新意识,消解浪漫爱的悬浮感,那么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将成为中国文化精神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中华文化在国际间的传播前景将不可限量。
四、结语
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从中华传统文化走来,受网络小说“爽感”的加持,又融合多种媒介,利用特效技术打造出颇具东方美学魅力的影像奇观,在互联网上得到飞速传播,本应更具创新性与包容性,但受困于泛情叙事,逐步偏离侠义的内核。几千年来,侠文化在时代的更迭中不断发扬光大,生生不息,侠义精神在我国文化自信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3],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我国文化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要求不断深化。侠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可巩固民族精神,对外可彰显中国形象,是网络仙侠小说改编剧应持续注入的精神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