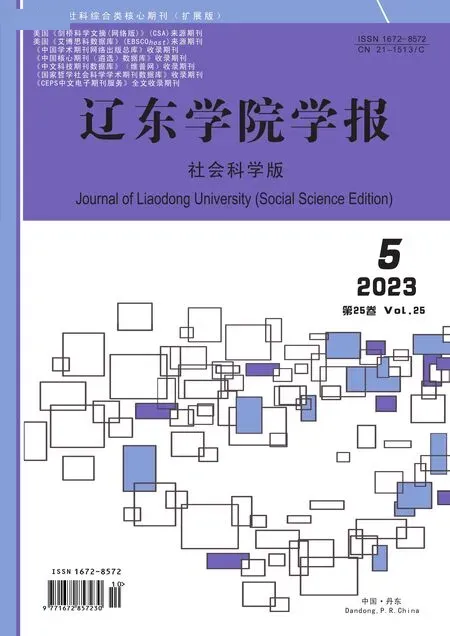《春柳堂诗稿》的难解之疑
谢德俊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33200)
“张宜泉”其人仍隐于历史帷幕之后,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有这么一位先生走进了曹雪芹的晚年生活,为后人留下了四首有关曹雪芹的诗歌,这位先生姓甚名谁却无法肯定地知道,我们称他为“张宜泉”,是因为这四首诗出现在署名为“宜泉先生”的一部诗稿里,而这部诗稿却在曹雪芹去世100多年后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被“宜泉先生”的嫡孙“张子介卿”付刻刊行,是为《春柳堂诗稿》。《春柳堂诗稿》也因录有四首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诗而成为《红楼梦》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春柳堂诗稿》被发现、公布以来,学界曾有多次论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诗稿作者和诗稿本身的真伪问题[1]。基于对《春柳堂诗稿》所涉内容的不同理解,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总体来看还是说服力不足,即便是一些“诗作中反映‘历史唯一性’的内容”[2],实际上也非常难以作为说明问题的确切证据。
除去这些对《诗稿》材料不同解读而产生的争论,另有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疑难问题,兹列如下,以俟方家考辨。
一、未被《熙朝雅颂集》等诗文集收录
清人铁保等编纂、嘉庆帝赐书名的《熙朝雅颂集》,辑录了八旗入关以来至清中期嘉庆时期旗人的诗歌作品,共134卷,收录八旗诗人585位,选诗7 743首,是一部较为全面地记录八旗诗史的诗歌总集。
《熙朝雅颂集》选诗的来源,首先是铁保收集的诗钞。铁保选诗以“兼收并蓄”为标准,注重人品与诗品,两者居其一,即“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也有乾嘉时期的八旗诗人未见诗集传世者也能在《熙朝雅颂集》留下诗作,据《批本随园诗话》记,“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则竟当作卖买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3]。这一说法可能言过其实,却也透露了《熙朝雅颂集》除收集来的诗集刻本及写本外,选诗的另一个来源是自荐,而自荐便难免会有些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现象。
受乾隆时期严苛的文字狱影响,《熙朝雅颂集》作为一部呈达御览的旗人诗歌总集,在选录作品时有许多忌讳,例如有怨怼情绪的作品不选,直接反映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作品也几乎没有(而在一些旗人诗别集中这类作品往往随处可见),这是《熙朝雅颂集》在选录诗歌方面的局限性[4]。胡适曾在日记中表达了《熙朝雅颂集》不选曹雪芹诗“殊不可解”。不过按照铁保的选诗标准,曹雪芹既无诗集传世,诗风奇诡而近李贺,《熙朝雅颂集》不录也正常,但同是汉军旗人张宜泉所作的《春柳堂诗稿》未录入其中,确实令人不解。
《春柳堂诗稿》虽然刊印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但从内容来看,五言排律多是“鼓吹休明,和声以鸣”,称颂“国家之盛”[5]9-10的试帖诗,五言近体和七言近体主要记录作者丰富的生平经历和个人感悟,其交游广泛,留下与友人唱和及怀人诗作60余首,所涉人物有30多位。该书未刊印之前,为之作序的贵贤在20年前(1869年),还能从“友人箧中偶得其诗数首”[5]5,说明张宜泉诗作在外流传甚广;济澂在作跋前12年的丁丑(1877年)夏,也有机会读到《春柳堂诗稿》,说明诗稿在此次刊印前还在一定范围内传阅。那么,《春柳堂诗稿》里的诗质量如何呢?贵贤在序中说:“所作诗古文,学者久奉为圭臬。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尝于友人箧中偶得其诗数首,骨力苍切,意味深厚,得汉唐作者神理而不袭其貌,其体物之细,赋物之工,其待以天为之而神有余者乎?”[5]5延茂在序中说:“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5]7济澂在跋中说:“丁丑夏,获睹宜泉先生斯集,叹曰:此正始之音也。”[5]125评者都是进士出身,有较高的诗文鉴赏水平,诗作能获得他们的一致赞赏,诗歌水准显然可以。
此外,成书于1929年,由近代徐世昌携门人幕客编撰的清代诗歌总集《清诗汇》(又名《晚晴簃诗汇》)200卷,收录了6 159位清代诗人的27 420首诗,该集凡例称:“自大名家外,要皆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二例并用,而搜逸阐幽,尤所加意。”[6]这部总集中不乏流传不广的作品和一些不知名诗人的资料,可惜也不见张宜泉及《春柳堂诗稿》的诗。直到1935年,八旗蒙古人恩华在《八旗艺文编目·集部》中才记录了《春柳堂诗稿》书名及作者兴廉。
《春柳堂诗稿》在1935年以前的史料中不被提及,与其序跋诸人对该作及作者张宜泉的高度评价相矛盾。如果说《熙朝雅颂集》成书时《春柳堂诗稿》未刊刻有沧海遗珠之可能,那么《清诗汇》的编者徐世昌与贵贤、延茂等人属同时代,《春柳堂诗稿》刻本已经流传甚广(1)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查询,现存《春柳堂诗稿》藏本至少有四本,加上未录入数据库的三本,已知现存刻本共有七本。那么,清末民初流传的《春柳堂诗稿》刻本应不在少数。,正常情况下不可能遗漏,除非徐世昌等人知道一些关于《春柳堂诗稿》不为人知的内情而有意不录。
近年来,随着《春柳堂诗稿》相关研究的深入,发现其内容上存在着诸多互相矛盾的情况。例如,张宜泉世居北京或京郊,《冬暮二首·其一》却出现具有洛阳地方年节习俗特色的“丝鸡”“粉荔”等事物。又有两首以“长安”为背景写作的诗--《万户捣衣声》和《长安城阻风》,其中《长安城阻风》有句“斑衣土点红”,可见长安并非指代京城北京,而是实写西安府,因为在西安东郊有丹霞地貌形成的红土坡,风暴袭来时吹起的红土沾染在衣服上,就会出现诗中描述的这种现象,而北京地区却没有红土。这几首诗穿插在写京郊或北京附近的诗之间,如《冬暮二首》前有《登东安县城楼》(东安县即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后有《答良乡县酒家》(良乡县在今北京西南房山区),不像是宜泉旅居在外所作,令人怀疑这几首诗的作者另有其人。又如,《春柳堂诗稿》中有大量诗作表现作者功名不就、家业不兴,甚至生活困顿,境况堪忧,如《自嘲》:“蛛丝牵幕细,鼠迹印床疏。零落囊中句,纵横架上书。”[5]54再如《感遇二首·其一》:“牢落何时了,年来意未安。不知新病瘦,只讶旧衣宽。况味浑尝胆,流光易跳丸。诗裁两眼泪,滴滴血成团。”[5]57诗集中又有部分风格完全相反的诗作,表现作者能文能武、勤于王事的积极形象,如《雨雪载途》的“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5]19句,表明作者曾为国征战沙场;《殉节诗十二韵》表现作者在任地方官时,为殉夫的黄门次女“具疏上闻,表彰乡间”[5]41。作者的朋友里不但有“龙二府”“穆县令”这类现任官员,甚至与宗室也有交往。他在经济上也一扫困顿之态,在《新居志喜》中豪言“买断东邻宅,得房有六间”[5]77。很难想象,这两类诗会出自同一人之手。
因此,《春柳堂诗稿》的成书过程可能比较复杂,而《清诗汇》录诗以“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为要务,如果其编者无法确定诗作者为谁,就有可能弃之不录,这可能是《清诗汇》未收录《春柳堂诗稿》的主要原因。
二、《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不明
1955年7月,王利器首次公布《春柳堂诗稿》的发现情况,他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文中引用恩华《八旗艺文编目》的记载,认为《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兴廉字宜泉者,并推测“兴廉当是年十五六岁左右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7]1955年8月,文学古籍刊行社编辑部在影印出版《春柳堂诗稿》的说明中提出:“春柳堂诗稿,张宜泉撰。”否定了兴廉宜泉的著作权,明确了“宜泉先生”姓张。此后,尽管在作者问题上还存在争议,但按原署名“宜泉先生”,把著作权交给张宜泉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个张宜泉除了这本《春柳堂诗稿》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包括与他有过交往的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宗室朋友敦敏、敦诚,在他们的诗文中完全找不到任何与张宜泉有关的只言片语。因此,这位张宜泉先生更像是一个符号,仅有的研究资料就是《春柳堂诗稿》里的序、跋和诗、注,可能还包括1977年发现的曹雪芹书箱[8],从这些有限的资料中还原张宜泉的生平,非常困难,至少从研究现状来看,分歧远大于共识。
例如,在班级当中,我们要时刻严格要求幼儿遵守班级中的规章制度,使幼儿懂得制度的不可破坏性和必要性。如对于班级的值日制度,我们要对幼儿进行明确的分工,将每一件事情的责任分配到位,让幼儿在进行简单的值日过程中,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等,这种制度化的管理使教师和幼儿都能够轻松完成自己在班级中的责任,从而使幼儿园的班级管理更有秩序,更加简单,使幼儿园的管理质量和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和增强。
《春柳堂诗稿》的首要价值在于其中四首涉曹诗,这些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丰富了曹雪芹的生平,因此,自《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红学研究者引用其诗及注,“基本上也都是不论不证,以自明性视之而直接采用的”[9]。20世纪90年代初,欧阳健发表《〈春柳堂诗稿〉曹雪芹史料辨疑》一文,全面否定该书的红学研究史料价值,基本观点是张宜泉“决(绝)不可能与曹雪芹同一时代”[10],他通过“序跋推定”“张介卿的年龄推定”和“张行的年龄推定”三种测算方法,推测张宜泉的出生时间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之间,与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没有交集,这一观点的推论过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曹雪芹书箱的收藏者张行的年龄来推定张宜泉的年龄,显得有些随意,因为当时没有证据表明张行就是张宜泉的后人(2)2014年,张家提供了一份书面证明,澄清张行并非张宜泉后人,书箱系清末任职户部的二品资政大夫陈宗妫所赠,因此,张行和张宜泉毫无关系。。
欧阳健的文章在红学界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关于《春柳堂诗稿》的大争论,其中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其写作年代。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以欧阳健、魏子云、刘广定、胡铁岩为代表,或认为张宜泉即兴廉,生活和写作年代在嘉庆以后,或认为张宜泉出生在曹雪芹去世以后,生活与写作年代跨乾隆朝、嘉庆朝甚至道光朝;另一方以刘世德、贾穗、蔡义江、严云受、黄一农等为代表,认为张宜泉出生于雍正末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之间,生活与写作年代不超过乾隆朝。应该说,后一个观点是自《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为红学界所默认的,因此,当欧阳健最早提出不同观点的时候,较早回应的贾穗和刘世德在反驳文章中,对此显得不以为然。如刘文开篇就说“有些红学的文章往往还免不了需要从ABC做起”,“我万万没有想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还要来撰写文章,公开为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辩护”[11]。贾文则表示:“长期以来,红学界对张宜泉及其《诗稿》的研究虽很有限,但对《诗稿》和其中记载的曹雪芹史料的真实性问题看法一致,从未表示过怀疑。”[12]
对比关于张宜泉生活和写作年代的几种观点,论据都不够充分,比如认为张宜泉生活在乾隆时期,与曹雪芹有交集的观点,主要依据《春柳堂诗稿》的自序中的“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试五言排律八韵”[5]9这句话。此句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丁丑”,这一年,在乡、会试中增加五言排律八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上谕要求在丁丑科会试第二场开始“以诗易表”。另一个可能表明时间的词是“我皇上”,大多数学者认同“我皇上”指当朝皇帝,即乾隆皇帝,则张宜泉给《春柳堂诗稿》作自序的时间不得超过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2月8日。几乎所有认为张宜泉与曹雪芹有交集的研究者,都基于这个资料来推测张宜泉的生活和写作年代,但胡铁岩却指出“我皇上”一词在非官方使用场合,也存在用来称谓前朝皇帝的情况。他还举出共11例“我皇上”用来称谓前朝皇帝的例子[13-14]。胡铁岩的考证动摇了“张宜泉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立论基础,进而威胁到《春柳堂诗稿》涉曹诗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遗憾的是此观点自2015年提出后,至今只见到张志给予回应和反驳[15-16]。台湾学者刘广定则认为即使“我皇上”一词是指乾隆帝,“也不能由此确认《诗稿》中各诗皆作于乾隆朝”,因为《春柳堂诗稿》“自序并无日期,有未结集时所写之可能”,并举了18例清代诗文集中序文在前、集成在后的案例,如敦诚的《四松堂诗集》未刊前已有永忠之序。因此,“《春柳堂诗稿》里不一定都是乾隆朝的作品,也可能有嘉庆,甚至更迟之作”[17]。
欧阳健提出张宜泉与曹雪芹无交集,很可能是在《春柳堂诗稿》的序跋中发现端倪,所以,他推定张宜泉生活年代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从《春柳堂诗稿》的序跋推定”[10]。贵贤在序中道:“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尝于友人箧中偶得其诗数首……”“命余为序,余见之如晤故人,如获珍宝”“回忆廿载前所深嗜者,即先生诗也”[5]5-6。延茂在序中道:“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而耳熟能详,心仪已久。”[5]7济澂在跋中道:“丁丑夏,获睹宜泉先生斯集……至于先生学养之邃,性情之纯,家庭孝友之乐,往来酬答之殷,具见于诗……先生往矣,而读是诗者,犹相遇于几席梦寐之间也。”[5]125-126三篇序跋在记述张宜泉的字里行间,未见因年代变迁而产生的沧桑感,流露的只是相见恨晚的遗憾,特别是济澂跋中所述张宜泉生平,包括学养、性情等“具见于诗”[5]125,可见济澂是先认识张宜泉,再在诗稿中看到他所认识的张宜泉,才会这么说。而且,他在跋中提到“宜泉”“先生”时必另起一行,对张宜泉的态度比贵贤和延茂更加恭敬,所以,他与张宜泉可能是有过交往的。很难想象,张宜泉如果只生活在乾隆时期,而序跋写于他死后已历五朝近百年后的光绪十五年(1889年),即便是客套话,用“所恨未获亲炙”“余见之如晤故人”“不获亲其杖履”等语,贵贤和延茂就不觉得虚伪吗?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句“客套话”就能解释的。
对《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和写作年代的研究,如果仅停留在对诗稿内证资料的各自解读上,则难有突破,近年研究逐渐转向“更多地使用历史文献,对《春柳堂诗稿》某些诗中提及的事件或地名进行考证,以确定某诗确切的写作时间。”[9]这方面的研究,胡铁岩和黄一农两位贡献较大。如胡铁岩对《春柳堂诗稿》五言近体诗第26首《陪吴三兄钓鱼台访友》中“轮班有苑丞”句,引用《燕京岁时记》《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和王践和《钓鱼台行宫修建始末》文中关于钓鱼台宫苑设置苑丞和全部竣工时间,确定该诗写作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四十四年”;对《春柳堂诗稿》五言排律最后一首《四时殊气得阳字》,引用《清秘述闻三种》《乾隆御制诗五集》,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和清人方浚师《蕉轩随录》等资料,确定该诗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8]。黄一农检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春柳堂诗稿》刊本后,排除了有关曹霑的小注乃钤帖的假说;检索“中国方志库”,发现“霑”字有多种俗写,证明“上雨下沽”之字亦是“霑”字的俗字之一[19]。这些考证结果证据确凿、推理严谨,逐渐被各方接受。但这些成果仍无法确切地锚定《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
此外,七言近体诗《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记载了特定的事件,学人多有探讨,如顾斌主张“哪怕张宜泉恭纪的是乾隆五十八年这次‘驾幸’,那张宜泉也应该生活于乾隆时期”[20]。樊志斌认为该诗“当作于乾隆五十年前后”[2]。也有认为该诗“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嘉庆二年”[18]或诗纪“咸丰二年”事[21]。可见,对这首诗的理解存在较大争议。即使按照顾斌主张的,诗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驾幸”事,又不知如何推断出张宜泉只能生活在乾隆时期?假如张宜泉在乾隆五十八年那年20岁,那么他可以继续生活至道光时期,而该诗位列《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第一首,极可能就是张宜泉年轻时所作。樊志斌把这首既存在较大争议又无法确定《春柳堂诗稿》写作时间的诗列为“能够确定《诗稿》写作时间的‘历史唯一性’的硬性证据”[2],实在是缺乏说服力。
三、张宜泉与其“嫡孙张子介卿”的年龄问题
张介卿的年龄可依据与《春柳堂诗稿》序跋诸人的关系加以合理推测。据黄一农考证,贵贤生于咸丰三年(1853年),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为《诗稿》作序时37岁;延茂生年不详,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济澂可能生于1852年(3)网上有资料显示济澂生于1852年,但未提供证据。待考。,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序跋中,贵贤有“命余为序,余见之如晤故人”[5]6句,其中两个“余”字小一号书写,以表敬意;济澂跋有“命列名卷末”[5]126句,且提到介卿则空格阙字,因此,贵贤和济澂的年龄应该比张介卿小,张介卿生于1853年以前;延茂序中有“问序于余,余既喜……”[5]8句,此处两个“余”字书写正常,提到介卿时不用平阙,可见,延茂的年龄要大于张介卿,假设他30岁考中进士,则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前后,作序时约57岁。这样推算,张介卿应该生于1833-1852年之间,光绪十五年刊刻《诗稿》时年龄约在38岁至57岁之间。
如果以张宜泉出生年龄下限乾隆十一年及张介卿出生年龄上限道光十三年(1883年)计算,两人的年龄差有87岁,如果以张宜泉出生于雍正末乾隆初算,而张介卿出生年龄以下限咸丰三年计算,两人的年龄差可达117岁,折中一下是百岁左右,祖孙之间这样的年龄差即使放在现代也很少见,何况清代的人均寿命远低于现代。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学界,蔡义江认为“张宜泉作为将《诗稿》交付刊印的张介卿的祖父,确实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年代上的矛盾”。“(祖孙间的年代差距)是《春柳堂诗稿》疑案的症结所在”,他把这一矛盾归结为“张介卿自己先弄错了张宜泉的辈份”,认为张宜泉可能是张介卿的曾祖父甚或高祖父[22],这一观点因为主观性太强,信者几无。黄一农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极端情形下,如果张介卿60岁时刻书(生于1830年),而其父70岁时生他(其父生于1760年),那么,张宜泉的生年可能早到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甚至可以比曹雪芹年长3岁。当然,黄一农认为张宜泉生年的绝对下限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以张介卿及其父的生年仍有共34年的“上下调整的空间”[19]。其他学者推测的结果也大致不出此范围,如贾穗认为张宜泉45岁左右生子,其子50岁左右生张介卿,介卿60岁刻书,则张宜泉可生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左右[12];严云受认为张宜泉37岁左右生子,其子在50岁左右生张介卿,张介卿刻书时73岁[23]。这些解释看似合理,实际上缺乏确定性资料的支持,之所以如此强行解释,是因为不管怎么推算张宜泉祖孙三代的年龄,有一个大前提必须肯定,就是张宜泉与曹雪芹必须有交集,如樊志斌就认为:“《诗稿》作者宜泉生活于乾隆时代,作为张介卿的祖父,宜泉能够与曹雪芹产生交集……在这样的前提下,宜泉与张介卿之间的年龄差距过大虽然还是一个问题,但也只是一个疑问而已,丝毫不能动摇宜泉生活于乾隆时代、《诗稿》成书于乾隆时代这一事实。”[2]可见,以现在的研究思路,张宜泉与其嫡孙张介卿之间的年龄疑案永远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此疑问的症结在于4首涉曹诗限定了张宜泉的生活年代。如前所述,《春柳堂诗稿》的成书过程并不简单,对于这4首涉曹诗,与其在证据不充分的前提下质疑此曹芹溪非彼曹雪芹,不如转变思路,探讨创作这4首诗的作者有没有可能不是张宜泉。毕竟4首涉曹诗其中两首的题下注异于全书体例,显得非常突兀,虽然蔡义江对此作出了解释,但也完全是主观推测,理由较为牵强[22]。张宜泉的生活年代较晚,他与曹雪芹没有交集,《诗稿》中涉曹诗的作者另有其人。当然,具体到是谁与曹雪芹交往并写下这4首诗,已不可知矣,可能是宜泉的父亲或祖父,也可能是从他处得来,这已不重要。
以上三个难解之疑牵涉《春柳堂诗稿》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纵观《春柳堂诗稿》被发现以来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许多研究缺乏客观性和全局性,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研究者不得不在有限的资料上进行各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解读,比如《春柳堂诗稿》七言近体诗《和龙二府〈在滇游螳螂川赠空谷先生〉原韵》,因龙姓较特殊且有具体官职,学人多有研究,如欧阳健主张龙二府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科大挑二等后留云南补用道(候补知府)的龙瑞图[24],黄一农主张是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在云南担任威远同知的龙廷栋[19],胡铁岩认为是道光十年(1830年)任顺天府西路同知的龙载恬[18],考证的结果都与自己的预设观点相关,孰是孰非,难以论断。二是因为《春柳堂诗稿》对于曹雪芹的研究非常重要,其中的涉曹诗经过各方深入研究,印证和完善了曹雪芹的生平资料,已经成为曹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因此,长期以来,任何对《春柳堂诗稿》有所质疑的观点,最终都会落实到对涉曹诗真实性、可靠性的否定上面,这是绝大多数红学研究者无法接受的。比如贾穗在反驳欧阳健质疑文章时就指出:“假如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4)指欧阳健文提出的“张宜泉和曹雪芹不可能相交”和“涉曹诗作伪”两个观点。,确如其言,则《诗稿》红学资料上的价值就即刻等于零。”[12]所以,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任何结论如果危及涉曹诗的真实性、可靠性,就很难获得普遍认同,这无形中降低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三是因为《春柳堂诗稿》本身除涉曹诗外并没有太大的艺术或史料价值,因此至今没有见到一部系统性、全局性的研究专著,说到底,还是重视不够。
蔡义江对张介卿的描述为:“其人学问有限,文字水平不高,对其祖上的事情几乎不了解,且已无处可问了;但他人情练达,能与在官场混的有身份的人拉上关系。”[22]此语总结下来就是“没文化但人脉好”,这样的人来张罗已故祖父留下的诗稿,有没有可能把其他人的诗掺杂进来呢?比如曾祖的、高祖的、宜泉友人的(互赠),甚至介卿友人把兴廉宜泉写的诗,误以为是其祖父流传在外的诗而收集起来一并刊刻,这些情况不但不能排除,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循此思路,《春柳堂诗稿》中的诗歌非一人所作,则诗作内容反映的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大等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许多难解之疑也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