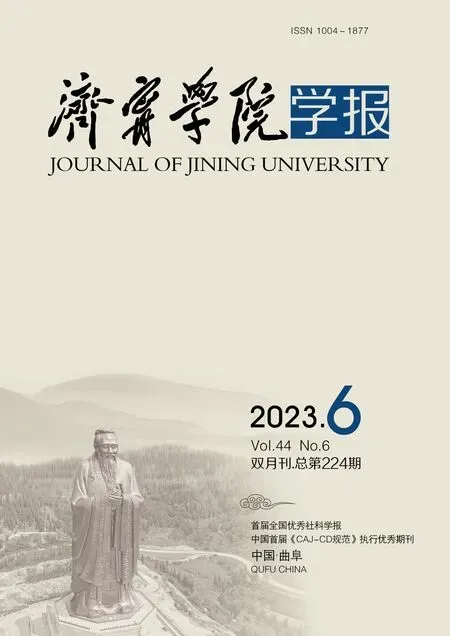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悲剧美学阐释
张英伟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趣,对于悲剧和喜剧的认识也有异于西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言:“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98-99的确,中国经典戏曲悲剧很多出于元代,但王国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所言不确。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将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纪君祥《赵氏孤儿》、高则诚《琵琶记》、冯梦龙《精忠旗》、孟称舜《娇红记》、李玉《清忠谱》、洪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方成培《雷峰塔》列为“中国十大古典悲剧”,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其中《精忠旗》《娇红记》便是两部较为经典的明代传奇悲剧。除了王季思所列,明代亦有其他悲剧戏曲作品,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便是一部优秀的悲剧传奇之作,情节曲折跌宕,蕴含中国古典悲剧美学思想,亦体现出中国人以“中和”为美的独特审美意趣。
一、悲剧发生的原因
传奇《何文秀玉钗记》是一部优秀的古典戏曲悲剧,共两卷三十八出,今存稿本,藏上海图书馆。作者陈则清,字泰宇,新安祁阊(今安徽祁门)人,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另有同名传奇,署名“心一山人”,有明万历间富春堂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全剧四十四出。学界有将署名“心一山人”归为陈则清者,如齐森华等编《中国曲学大辞典》言:“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此剧稿本,题‘新安祁昌泰宇陈则清甫编著’,可知此心一山人,应为陈则清。”[2]377但通过对二者内容等进行比较分析,更多说法倾向于两种同名传奇并非同一剧本。例如陈志勇《孤本明传奇〈剑丹记〉〈玉钗记〉的作者问题--兼论古代剧本著作权与署名不对称现象》[3]29一文从二者结构安排、关目处理、曲牌组合方式等方面进行辨析,认为稿本和刊本是不同的两个剧目,之所以作者错署,则源于版本信息不对称。廖可斌主编《稀见明代戏曲丛刊》著录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提及同名传奇,即署名“心一山人”之作,“内容与此本有异,此本无‘心一山人’剧中何文秀出游南京与妓女刘月金相好情节,此本何文秀妻名兰英,‘心一山人’剧中作琼珍,两剧显非同一剧本。”[4]731
根据陈则清剧前序云:“山人曰:寡和之音,不谐里耳,警世之言,归于谕俗。故予之谱《玉钗》,稍委宛其事,成人美也;必直致其辞,醒人心也。”[4]733以及《玉钗记》引之“《玉钗记》者,盖桃源陈山人则清氏之所谱也”[4]734等言,可知《何文秀玉钗记》或为陈则清独立创作,非改编其他文本。而《曲海总目提要补编》则言“心一山人”剧作“本小说、弹词而作”[5]40。且“心一山人”剧相较陈则清剧不仅人物增多,故事情节亦更加丰满,故“心一山人”之剧或改编自陈则清剧。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以文人视角勾勒故事,与偏向民间趣味的“心一山人”之作大相径庭,陈剧作为该传奇的最初版本亦体现出与后世改编之作的不同审美意趣,更能展现该传奇原本的悲剧美学韵味。
对于大多数悲剧而言,“故事中的悲剧情节本质上是一个或一系列继发的巧合事件。也就是说,悲剧是由于某种后起的原因而从无到有地发生,悲剧主人公因此而由顺境转入逆境的”[6]71。陈则清传奇《何文秀玉钗记》亦不例外。虽然传奇第一出《梨园开演》便奠定了悲剧基调,但故事真正悲剧的转折则发生在第五出《仇计焚廪》,直隶监察御史程练因昔日何文秀父何君达任提学时黜退其二子而伺机报复,设计谋害何氏一家。从此,何文秀一家陷入悲境,何文秀开始接连遭遇重重巧合性的陷害,痛苦和灾难便成为何文秀始终无法挣脱的梦魇。
导致何文秀悲剧发生的背景便是当时贪官污吏横行、腐败滋生、钱权交易泛滥的社会现状。明代官吏贪赃枉法之风盛行,朱元璋便叹息道:“自开国以来,惟两浙、江西、两广、福建所设有司官,未曾任满一人,往往未及终考,自不免乎赃贪。”[7]1可见当时官场腐败现象之普遍。该剧作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相较明初,此时段贪污腐败的官场案例不减反增,对于当时的种种黑暗现象,海瑞《治安疏》言:
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8]218
当时的社会犹如黑漆皮灯笼,决疣溃痈,而官吏的贪污腐败必然会导致冤案的发生,《何文秀玉钗记》便是此时代下的产物。
在传奇《何文秀玉钗记》之中,贪官污吏可谓处处可见,有致使何文秀悲剧开始的官吏程练,借用公职报其私仇,千方百计地迫使何文秀家破人亡。如剧中第五出:
里正算我伶俐,颇能撑持门第。一乡左右任施为,果然是当年太岁。奉官府十分奉承,骗乡民百般巧计。只晓得孔方老兄,管甚么朋友亲戚。这都是吃了黄河浊水,便惹起夜叉心肺。奉上司点报富民,上粮米广施赈济。有钱见我,虽石崇改作贫民;无钱见我,虽范丹报为发积。上司倘若闻知,拼了三十五十,医得棒疮全愈,依旧还要作弊。自家因按院行文书下来点报富民,小子在乡间乘此机会,也骗得一些钱钞。[4]745-746
直隶监察御史程练滥用职权,没有任何公平可言,宁可被上司发现问责杖罚,也要冒险骗得钱财,这段宾白生动形象地揭露出当时官吏贪污腐败成风的社会现状。为迫害何文秀一家,程练更是利用职权,公报私仇,剧中程练直言:“思想昔日何君达曾为我本省提学,我二子在学,被他黜退,如今在我治下,若报此仇,真犹反掌。”[4]746逼迫清贫落魄的何家上粮赈济,程氏犹不满足,还要设计将何家抄没,“要报何家仇,上粮赈济,还好了他。怎么设个计较,把他一家害了,方称吾意。有个计了,今晚夜静,使人悄地焚了官仓,大声喊叫,说何文秀嗔察院叫他上粮,故意焚了,那时把他抄没,有何难处?”[4]747于是,程练设计陷害何家,害得何母离家逃难,义兄何九思拔剑自刎,何家的悲剧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此后何文秀的每一次遇难都避免不了有贪官污吏从中作梗。张堂觊觎何妻王兰英的美色,设下计谋,杀害婢女图害何文秀,致使其被捆至官司。而审讯何文秀的杭州周太守亦是一位贪污受贿之人,第十八出《刺史拷鞫》开篇唱词道:“【西地锦】(外上)铜虎符分外郡,玉麟宠自皇恩。黄堂皂盖人钦逊,政令任我纵横。”[4]777可见其玩弄职权,横行霸道之势。其宾白更是狂言妄语:
一方宣化领专城,五马驰骋耀紫轮。听讼犹人何足羡,片言折狱岂夸能。下官杭州府周太守是也,直隶常州武进人氏。莅一郡之政令,擅灭门之权威。今早张堂有书来,其中说那何文秀杀死人命之事。思想起来,先年我与何君达曾有宿怨,况承张堂厚爱,亦当存些分上。今日放告之期,谅他必有进状。[4]778
作为一郡之官,周太守借着职权徇私偏向,执法不公,无视何文秀的冤情,对其施以严刑,逼其“招供”,手段残暴至极。充满戏剧性的是,在该剧中不仅官吏耀武扬威,腐败昏庸,就连看守犯人的禁子亦是如此。传奇第二十一出《监中相会》唱词道:“【三棒鼓】(丑上)我做禁子管囚人,检点牢中须费心。天堂不肯登,偏入地狱门,若是无钱受我刑。”[4]784下更有宾白:“自家杭州府禁子便是。轻重囚犯,由我掌控,百般刑禁,任我施为。昨日那何文秀收在监中,他苦苦只告艰难,没有送我一些常例,不免叫他出拷打一番,弄些钱去买酒吃。那何文秀出来!”[4]785将禁子贪财好利,滥用职权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描写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何文秀的命运是与明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传奇中的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悲剧色彩,他们始终面临的都是一个官官相护,贪墨之风盛行,黑暗腐败的社会,冤案的发生是社会现实驱使下的必然现象。因而,在《何文秀玉钗记》中,人物的苦楚及悲剧性命运势必无可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不再是单纯的巧合或偶然,而是整个社会悲剧的必然。
二、悲剧人物的塑造
中国古典戏曲悲剧,尤其是清之前的作品,普遍遵循的仍然是非黑即白、非忠即奸的创作原则。这种人物塑造原则下的戏剧冲突,实质上呈现出二元对立模式的两种具有相反伦理道德守则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这种二元对立形式中,正面人物往往是道德品行几近完美之人,反面人物则是刁钻刻薄、虚伪狡诈者,二者处于极端对立的二分状态。诚然,《何文秀玉钗记》中的人物塑造仍大体不脱此模式,但作者陈则清有意识地赋予人物形象丰富的一面,使剧中角色更加鲜活,人物性格开始趋向复杂多元化。
明清之际,才子佳人戏曲作品的创作达到巅峰,素有“十部传奇九相思”之说。《何文秀玉钗记》的产生便与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创作风气有关。明朝在政治上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制加强封建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亦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特别是王阳明学派“知行合一”以及“致良知”等观点的盛行更是为封建礼教的统治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基于此背景下的明朝,为了控制社会舆论,更是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明律法明确规定: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9]18
明代统治者希望通过杂剧戏文等来达到教化的作用,由于所设标准严苛,唯有才子佳人剧既不触犯律法,又能通过才子佳人故事来宣扬义夫节妇等道德楷模形象,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因此,以才子佳人为题材的戏曲成为当时文人创作的热点,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土壤。该传奇是典型的教化剧,卷前序、引等多次直言该剧主旨,如笑鹏生庄持本所撰《陈山人〈玉钗记〉序》言:
山人曰:寡和之音,不谐里耳,警世之言,归于谕俗。故予之谱《玉钗》,稍委宛其事,成人美也;必直致其辞,醒人心也。一以警下石者,报施不爽,而出尔入尔,事正相当。一以儆行露者,沾濡可畏,而沦胥及溺,自完良苦。一以警吠庞者,凛乎大防之难犯,而反中自驱,适以藉仁人之资,而作戮民之首,恩怨明矣,美刺互矣,劝惩备矣。虽编缉所裁,有惭绣虎,而义旨所合,无取雕虫。杂雅俗而并陈,合愚智而同谕,冀移人于耳目之外,斯立教于声伎之中。此自关风化之纪,何暇论文墨之际乎?余闻之而怃然曰:嗟乎!此三百篇无邪之教也。[4]733
庄持本序言记有其与陈则清的对话,陈氏直言要通过该剧警醒人心,为了更好地起到教化作用,便“立教于声伎之中”。庄持本听了陈则清之言,大为惊愕,并将陈氏之剧以《诗经》相比。通过庄氏序言,可以明晰《何文秀玉钗记》的主旨思想即为“教化”。倪道贤撰《〈玉钗记〉引》亦言:“余未识山人,而喜其以风教也,为之卒业焉。已而叹曰:嗟乎!以余观于山人之谱也,其有忧世悯俗之心乎!”[4]734倪道贤与陈则清虽不相识,但对于陈氏的风教之作尤为喜爱,并感叹陈氏有一颗忧世悯俗之心。不仅如此,陈氏剧中亦有多处提及该剧有教化之旨。如第一出《梨园开演》:“芳名劲节两兼全,风化攸关非浅”[4]737,卷尾亦云:“忠贞节孝振纲常,间气争腾日月光。为托传奇垂竹帛,高风千载永流芳。”[4]828诸如此类文辞尚有很多,均直言此剧“教化”之旨,在此不予多论。
基于此创作主旨,剧中主角必定多为“全忠全孝”的道德楷模形象。何文秀便是一个标准的道德完人。首先,何文秀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十分尊崇“孝道”,剧中多处均可体现。第二出《北堂家庆》之【尾声】:“(贴云)孩儿孤陋寡闻,终难上达。即当遍访高朋,讲明经术,倘得成名,不负老娘之望。(生云)老母在堂,无人承奉甘旨。孩儿怎敢远游。”[4]740父亲早逝的何文秀,虽有考取功名、振兴家门之志,但念及其老母在堂,亦不敢远游,后因母亲鼓励,且有义兄何九思在家侍奉,方敢出门讲学。第九出《荷亭奇覯》中,何文秀为王兰英及王母献唱的词名便是《忠孝词》。第十四出《异域思亲》更是表达了何文秀对老母的思念之情:
【踏莎行】泪渍红班,眉峰翠撵,只因骨肉轻拆散。天涯游子几时归,慈帷何处添凄惨。萍梗鸳鸯,寂寥无雁,白云无定空目断。人生聚散总难凭,蹉跎暗把时光换。文秀自逃难而来,虽偶谐伉俪之欢,但老母流落他乡,竟未获团圆之会,对景追思,好闷人也。[4]766
【江头金桂】(生云)夫和妇虽琴瑟谐欢,子与母痛参商两地。老娘,况你桑榆暮景,一似风中之烛了。只虑慈帏远遁,存亡未审。娘,你当初养育孩儿,受了多少苦楚,岂知今日不能报答。是呵,自念劬劳罔极,鞠我情深,乌鸟难酬反哺恩。叹云山万里,叹云山万里,飘零无准泪淋淋。寿昌哀苦应无限,何日同城慰子情。[4]767
逃难在外的何文秀对景思亲,字字句句将其对老母的惦念以及无能尽孝的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孝”字当头。其次,何文秀亦是一个“忠贞”之士。何文秀立志考取功名,振兴家门,却命途多舛,屡次遭受贪官污吏的迫害,终登甲科之魁,擢御史之职。剧中第三十五出《柏府剪豪》云:“【菊花新】(生)法星耿耿列光芒,柏府森森凛雪霜。铁面剪豪强,泻拔一方冤枉。专制江南域,丹心日月明。威行山岳撼,节按鬼神惊。”[4]818何文秀考取功名,被授予官职后,刚正不阿、廉洁清明,一心为百姓伸冤,是一个极为忠贞亮节之人。最后,何文秀亦是一位知恩图报的良善者。剧中第二十二出《狱子代命》中,狱官王鼎之子不幸染病早逝,王鼎夫妇得知何文秀遭此大冤,在饱受丧子悲痛之余,决定以其子之躯代狱中何文秀,认何文秀为子,将其带回家中,易名王察。何文秀感激涕零,直称王鼎夫妇为重生父母。在王氏夫妇的帮助下,何文秀最终荣擢兰台。授官后的何文秀一心想要报仇雪恨,与母妻团圆,终得冤屈平复,尘埃落地。心愿已了的何文秀一心辞官归养,但并未忘记王氏夫妇的救命之恩,如第三十七出《奏旨雪冤》言:“喜得圣上准了表章,不免转到行馆,修书一封,就差人马迎接恩父母到我家,同享荣华,多少是好。”[4]826再如第三十八出《衣锦团圆》中:“(生云)孩儿奏过朝廷,恩父封为尚义大夫,恩母封为尚义夫人,安奉圣旨,一宅分为两院而居,意下如何?”[4]827可见何文秀并未忘却王氏夫妇之恩,是个知恩报德之士。总之,何文秀是个忠孝两全、知恩图报的道德完人形象。
诚然,该剧的确符合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写作模式,正面人物多是道德品行几近完美之人,反面人物则多为刁钻刻薄、虚伪狡诈者,但作者试图赋予剧中人物真实鲜活的一面,使人物性格开始朝向多元化发展。剧中旦角王兰英总体是一个知书达理、严守妇道的贞节女子。兰英是苏郡王太师之女,自幼接受传统礼教,如第三出《宦庭训女》言:“(外云)我儿虽闺秀未字,年已及笈,今日是我的孩儿,异日做他人的媳妇,当遵守女妇之道,庶无忝阃范之仪。(旦云)孩儿独居闺阃,昏昧无知,望爹爹垂懿训,豁愚蒙,俾孩儿知所衿式,庶女道无亏”[4]741“【降黄龙】(外)阃阈规箴,须当效玉洁冰清,兰心蕙性。但看烈女传籍,尽都是淑德幽贞,竹帛声垂耿耿。其慎,阀阅家声,须重千钧名分。(合)细评论,但把四德三从,晨昏思省”[4]741“【前腔】(旦)承颜垂训,永作终身标准”[4]742。王兰英严守妇道,将父母训导之言,作为终身标准,这并非纸上谈言,在王兰英的言行举止之中亦有体现。在剧中第九出《荷亭奇觏》中,王兰英见何文秀丰姿俊伟,貌比潘安,且得知自己与何文秀尚有婚约在身,便动了春心,丫鬟唆使其与何秀才花园一会,然而王兰英言:“贱人,那等淫奔之事,岂是我所为的么?”[4]757另外,王兰英于荷亭见过何文秀之后,不忍其流落在外,便让丫鬟送金子给何文秀,助其读书,以求上达。谁料被父亲得知,大为震怒,欲将兰英与何文秀捆了沉入湖心,幸得王母暗中相救,两人方能逃出,对此王兰英表示:“奴家初怜秀才流落穷途,馈金之意,既不白于严君,而玷璧之冤,尚可诉于冥府。岂今日渔翁搭救,死而复生,自思欲待回归,则母庇难隐。若从秀才而去,则淫奔难明,不如还是一死。”[4]762可见,王兰英的内心深处早已被传统妇道礼教所缚,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大小姐形象。但是剧中王兰英亦有与其身份不符的举止,例如第三出《宦庭训女》中,王兰英一面对父母的训教俯首听命,但转头便对丫鬟又打又骂,“(丑云)我小姐心性极难伏侍,倘有不周,便是打骂,受此禁持,枉为人在世。(旦云)贱丫头,你在旁边唧唧哝哝,讲甚的?(旦打丑科)”[4]742,此处王兰英的言行举止显然不符合其淑女形象,作者于此有意赋予兰英性格多元的一面,并未拘于一格,使得王兰英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真实。
剧中王父亦是如此。王兰英的父亲在得知女儿私下馈金于何文秀,直言:“你把何文秀与我那畜生一齐捆着,沉在湖心,不得有违!倘若容情,一并重究。总把污泥沉浊浪,休教粪土玷朱门。”[4]760王父认为女儿行为有违妇道,为家门蒙羞,便狠心将其二人沉入湖中。但在第三十六出《忆女得会》中,王父又开始思念女儿,后悔当初一时冲动害得女儿毙命,王父言:“腾空鸾鹤舞翩翩,随处裹玉种丘园。西山景暗,空悲玉树凋残。袁门僵偃,安能有骨肉同欢忭。忆昔一时之暴,误把我女孩儿沉在湖心。想当初癖性多愆,到今日追悔徒然。”[4]821此处王父十分悲痛,追悔莫及,相较之前欲将女儿沉入湖心的残暴之举,又体现了父亲对女儿的骨肉之情,这便使得王父形象更加立体。还有剧中禁子,虽为小人物,但作者亦为其增添了人物性格多元化的一面。何文秀被冤枉入狱,王兰英前去看望,起初禁子态度恶劣,利用职权谋取财物,没有任何公平可言。但后来听闻何文秀的冤情,又为之动容,禁子言:“何文秀,你可写张状词与你娘子,我今日撵得二钱银子,与你做盘费,但遇清廉上司,即便伸冤,不可羁迟。”[4]787一向只为钱服务的禁子竟主动自掏腰包,希望何文秀能有机会伸冤,体现出人性的复杂多面。可见,该剧虽大体不脱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但作者已有意识地赋予人物形象多元复杂的一面,使得人物性格开始趋向真实、立体。
三、悲剧结局的“中和”之美
悲、喜剧概念于中国古典曲论中原是没有的,实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而引入中国。王国维最早将西方悲剧、喜剧理论应用到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中,王国维言:“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10]11王国维根据西方悲剧理论,将悲剧分为三种,并以此来探究中国戏曲。《窦娥冤》《赵氏孤儿》等确为难得的中华优秀戏曲悲剧作品,但其“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之言,甚不足取。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曾云:“由于我国古代文学论著中没有出现悲剧的概念,也没有系统地探讨过悲剧和喜剧的不同艺术特征,而欧洲从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以来流传了大量这方面的论著,当时熟悉欧洲文化的学者就往往拿欧洲文学史上出现的悲剧名著以及从这些名著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著作衡量中国悲剧。而另外有的学者--他们多数是专攻中国文学的,则认为中国戏剧的发展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能拿欧洲的悲剧理论来衡量。”[11]前言1-2由于中、西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纯以西方悲剧美学标准来看中国戏曲,不甚客观,难以令人信服。
亚里士多德《诗学》曾对西方悲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2]19,该定义较为经典,一直广为流传。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言,西方悲剧永远是严肃的。而中国戏曲里面的悲剧和喜剧明显不同于西方,未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古典戏曲创作有自己的特色,悲、喜剧的界限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正如安葵所言:“在西方,滑稽与崇高是对立的,崇高与悲剧相联系,英雄人物之死是悲剧,体现崇高;滑稽与喜剧相联系,是卑微、渺小的。而在中国,滑稽也常常能体现崇高。”[13]219中国戏曲悲剧往往是寓哭于笑的,纯粹的“严肃”悲剧十分稀少。李渔曾言:“‘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14]24古典戏曲重“机趣”,注重戏曲作品的“趣味性”和“喜剧性”,即使是悲剧,也并非完全“崇高”、不近地气,而是常常融“趣言”“趣行”于其中。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亦是如此,如第三十四出《妻诉明冤》,何文秀此时已登甲科之魁,擢御史之职,值其妻子前来上诉明冤,对话如下:
(生)叫巡捕官,那张堂谋杀人命,就差你去,火速拿来,不可延迟。(丑)领钧旨。(生、众下)(丑)我今日这等造化低,被那妇人喊叫,到责了十板,不知那妇人有甚来历,路上就准了他的状,且不在话下。左右的,今日是那个值日看座子?待我点名同去。按院所委,不可轻易。(净)是小的值日。(丑)你叫甚么名字?轮该是你值日,怎么不备座子?(净)小的姓高,叫高一佐,路上那得有座子。(丑)你既叫高一佐,饶你打,就把你当高椅坐坐着。叫都来揖。(末、小生齐作揖介)(丑)这狗才欺我,怎么大胆和我作揖?(小生)是老爷叫小的都来揖。(丑)我是叫你名字。(小生)小的姓都,叫都来楫,舟楫之楫。(丑)到是我眼花了,叫莫做声。(末不应介)(丑)这狗才一发欺我,怎么不答应?(末)是老爷叫小的莫做声。(丑)我是叫你名字。(末)小的姓莫是实,叫莫佑馨,保佑之佑,馨香之馨。[4]817-818
剧中巡捕官等人的对话十分有趣,滑稽至极,在如此“机趣”的言语中可窥得这几位“小人物”的形象特点,而又不影响主角的悲惨命运和全剧的悲剧性,这是中国古典戏曲与西方悲剧的不同之处。如同李渔之言:“所谓无道学气者,非但风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当以板腐为戒,即谈忠孝节义与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如王阳明之讲道学,则得词中三昧矣。”[14]25
另外,古典戏曲悲剧往往崇尚“团圆之趣”,与西方悲剧的绝对“崇高”不同,戏曲悲剧常常百感交集、悲喜交替。郭汉城言:
中国传统戏曲剧目中,悲剧和喜剧融合在一道的优秀剧目很多,悲剧中有喜剧人物、喜剧纠葛的穿插;喜剧中有某些悲剧性的情节,自不必说。比如《梁祝》前半场是抒情喜剧,后半场是悲剧,喜和悲之间构成了对比和反衬,前面的喜给后面的悲渲染了气氛;《薛刚反朝》则是一悲一喜交递发展,像两根缠绞在一起的藤子,迂回曲折却又各自向自己的方向伸展,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有悲剧的悲壮激烈,又有喜剧的轻松愉快,两者起着交相辉映的作用。[15]4
王季思亦云:
就《还魂》全剧看,上半部是杜丽娘由生而死的悲剧,而下半部则不仅是杜丽娘由死而复生的喜剧,而且还以比较多的篇幅演柳生由失意而得意、由逆境转顺境的喜剧。合而观之,《还魂记》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传奇戏中较为典型的悲喜剧,即正剧。
正因为悲喜相乘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我们大可不必为中国戏曲中悲、喜剧的这种“不纯”而妄自菲薄。[16]76
《何文秀玉钗记》亦是如此,该剧上卷是何文秀连遭迫害、流落在外的悲剧,而下卷则是何文秀慢慢自困境转入顺境,最终功成名就、沉冤得雪、衣锦团圆的喜剧。全剧悲喜交加,但于整体上又是基于当时社会背景,以“教化”为依托的戏曲悲剧。
与西方悲剧不同,中国古典戏曲悲剧更多地展现出悲喜交替、苦乐相错的审美意趣,这种创作及审美意蕴的产生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我国古代,儒家美学思想影响深远,《礼记·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7]175儒家讲究“中和之美”,孔子在评论《关雎》时,认为它可作为中正平和的典范,达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程度,并以此标准来要求诗歌和音乐。这种“中和”思想成为中国古典戏曲流传千古的美学意趣。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便是这种审美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该剧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颇深,无论是其中的忠孝节义道德准则,还是饱含“中和”审美意趣的团圆之旨,均不脱儒家思想的影响。
总之,陈则清《何文秀玉钗记》与西方悲剧不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其中言语颇具“机趣”,虽未脱符合中国古典审美倾向的“团圆之趣”,但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逐渐趋向立体、多元,亦体现了我国传统以“中和”为美的审美意趣,确为一部少见的优秀悲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