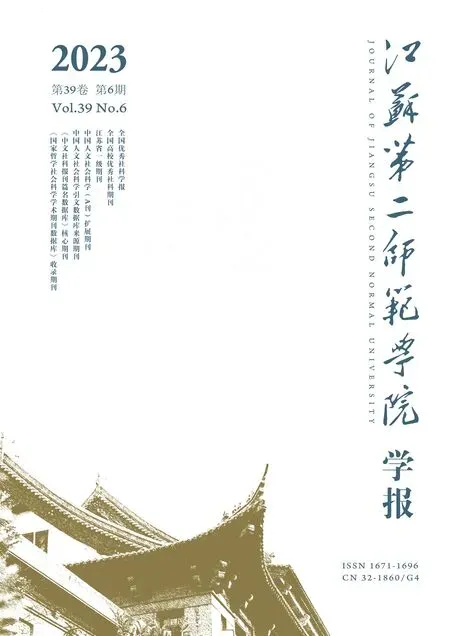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视域下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关系的三维审视
王 铁 柱
(1.天津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171;2.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李泽厚先生在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这篇文章中,李泽厚先生对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关系进行了归纳解读。文章以五四运动蕴含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两个性质相反的运动为论证逻辑起点,提出五四运动开启了启蒙与救亡相互促进的历史演进行程,但在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遭受个体反抗的失败及群体理想的困境后,思想启蒙为政治革命让步,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谋求对社会的激进式改造成为时代的路径选择,与此同时,启蒙让位于救亡成为近代中国的显性问题。李泽厚先生进而认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体的关系在五四后未得到合理解决,也未予以真正探讨和重视[1]1-46。自李泽厚先生文章发表以来,针对李泽厚先生本文中的核心学术观点,学界已展开了许多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启蒙与救亡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范式框架,李泽厚先生的这一思想理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贡献。综合考察对李泽厚先生进行批判的学术思想观点不难发现,多集中在对李泽厚先生所论述的方法论思维的批判即启蒙与救亡不是割裂独立而是对立统一的。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何以成为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如何从这一关系框架下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推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价值?这一分析思维框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何种历史启示?都是需要在李泽厚先生和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接着研”的学术任务。本文简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对这一关系问题进行尝试性思考,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维度:启蒙与救亡关系的纵向审视
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拯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寻找救亡之路,在经过器物革命、制度变革失败后,救亡的探索进程逐步指向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中也开启了思想启蒙。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相互交织,成为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场景。
对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关系的审视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背景场域进行审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尤其是以生产工具变革为肇始的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民族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嬗变。因而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审视,需要在世界历史的大变革视野中释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启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社会意识依存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变革。从这一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看,对思想启蒙的审视同样离不开对世界社会存在变化的论述。西方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方式,这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思想启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西方思想启蒙源于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又促进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发生,思想启蒙、政治革命又与西方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紧密联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阐释理路审视,西方思想启蒙为内源式启蒙,其外部没有救亡的使命包袱,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曾发挥过重要的推动功能。
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和社会形态上审视,鸦片战争前后,近代中国在生产方式上已落后于西方社会发展进程。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侵略。背负着救亡图存使命的各个阶级的仁人志士,探寻着民族国家的救亡之路。从中国近代史的视野审视,新文化运动前的救亡探寻之路隐蕴着思想启蒙的叙事,魏源、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精英群体,皆在救亡探寻之路触及了思想启蒙的时代问题。鸦片战争以降,近代知识精英群体在对中国救亡道路的探寻和对西方现代化的探求进程中内在地含蕴了思想启蒙的学习与传播。故而在早期阶段,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表现为救亡对启蒙的开启。
在探索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思想学说、主义道路纷纷登场,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历史证明:没有科学先进理论的思想指引,没有科学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进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探索,没有找寻到社会历史变革的主体力量,旧中国的面貌还将存续。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与认识是辩证统一的,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认识的前进,而认识的前进也推动了社会实践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一理路审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总是以一种波浪式、螺旋式的轨迹行进。魏源的《海国图志》宣介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也独辟一章引介西方政治制度、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同样介绍了美国政治制度。社会实践的发展会引发思想的进一步变革,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一批思想家对中国内部社会制度的反思,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对比了中西政治制度,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富国强兵之术”[2]211。后来的郑观应、马建忠、王韬等同样对中西社会政治制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这使思想精英们逐步认识到传统的器物革命已无法挽回摇摇欲坠的将倾大厦,只有通过制度效仿才能力挽狂澜。由此观之,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思考认识遵循着一条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因应近代中国救亡之路中的历史,知识精英群体的思想也发生着嬗变。因而,对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关系的审视,离不开对历史的观照,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下审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交融谱写着复调叙事,新文化运动前,这种复调叙事又是以救亡为主旋律而行进,思想启蒙的隐蕴叙事逻辑也会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逐步突显。
改良派直接与封建制度体系承续着“剪不断”的联系,他们的改良思想从本质上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固有框架下的时代回应。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统治阶级总是试图依靠其政治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通过国家政权,将社会经济关系规制在利益和秩序范围内。从这种理论逻辑视野下审视,改良派是带着旧有制度的镣铐推进社会的改革,他们的改革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而一旦涉及最根本的土地制度,他们采取了折中含糊的改革路径,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从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到康有为、严复等改良派思想家继承着龚自珍、魏源等开明地主阶级的思想路线,一直坚持反对农民革命,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1]71。李泽厚先生认为,整个改良派思潮是中国近代最先反映近代意图具有进步性质的早期自由主义,它的时代和民族特征与反帝救亡相联系[1]70。李泽厚先生看到了近代中国改良派的思想启蒙作用,然而囿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种思想启蒙窒息于阶级利益,马克思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286囿于旧有统治阶级利益藩篱的束缚,改良派在探寻救亡之路中也逐步压制了思想启蒙。这种阶级的局限性也使得救亡与启蒙无法实现真正的双重变奏。
制度效仿的失败,也迫使知识精英群体审视以往救亡之路。先进知识精英从辛亥革命中发现,要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民群众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时期承担着思想启蒙作用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社会进化论与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等,通过对传统糟粕思想的批判,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根基,开启了遏制启蒙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大地上掀起思想启蒙的时代大潮流。虽然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前进发展的思想先导,然而仍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救亡方案,仍未跳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圭臬。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矛盾业已相当尖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这一社会制度矛盾暴露于世人,梁启超先生《欧游心影录》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全面审思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重要思想力作。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在资本逻辑主导下,抢夺市场、资源等就成为资本主义逐利性的外在表现。梁启超先生通过所见所闻,反思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进化论、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国家主义等现代性,这位曾搬引西式文明的引介者,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大战中反思了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膨胀所导致的物欲主义、信仰危机等。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审视,新文化派推进的思想启蒙运动,无疑发挥了社会催化剂的功能。这一救亡范式的转换,使救亡之路从政治上层建筑转向思想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对政治上层建筑乃至经济基础又会发生能动反作用。然而,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打开了国人的思想阀门,另一方面,由于新文化派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所推进的思想变革启蒙又使得“效法欧美”成为标尺,最终又成为马克思批判法国启蒙学派的“意见支配世界”的悖论那样,成为一种抽象思辨层面的循环。此时,新文化知识精英群体由于在推进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中,未从根本上触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因而在思想领域的启蒙教育也就限于资产阶级启蒙学说的藩篱之内。
中国知识精英再次面临“路”向何处去的时代苦恼之问,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且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这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和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自觉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作为政党使命,科学协同好救亡与启蒙的辩证关系,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要求,科学协调救亡与启蒙的内在关联,在领导民族救亡中不断推进民众的思想启蒙,而民众思想启蒙又汇聚了民族救亡的主体力量,实现了救亡与启蒙的互动叙事逻辑。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领导民众进行社会革命。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变革,此时,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进程中,创建新型民主政权,不断获得政治民主意识,推进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对民众的启蒙。在根据地,面临民众识字率低、文盲率高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采用军队宣传队、识字班、教唱歌等多元化、平民化方式,对民众实施文化教育,在识字文化教育中灌输民族国家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文化教育的开展,极大地实现了女性解放,这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文明的发展,而且为近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主体力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中国共产党正是科学处理了救亡与启蒙的辩证关系,故而科学解答了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主题。
二、理论维度:启蒙与救亡关系的学理阐释
从历史的纵向审视,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需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方能得到科学解答,因而思考近代中国这一关系问题需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论下予以观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思想启蒙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救亡属于革命实践范畴,从历史辩证法看,启蒙与救亡又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
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并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化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两对矛盾同样是相互交织,近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为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必须推翻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旧政权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之一。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英勇不屈的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发展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4]421。从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述中,可见真正的救亡革命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两大领域进行。对于近代中国各阶级在救亡与启蒙过程的审视,也需要在这两大领域的有机联系中释析。人类社会发展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在探索救亡道路进程中,客观上实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正如刘景泉教授指出的:“近代中国将救亡图存与向西方文化学习联系起来思考的第一步,对以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具有启蒙作用。”[5]24也就意味着在探求近代中国救亡之路进程中,客观上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一论证理路审视,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在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中,由于对旧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维护,使他们的救亡之路始终束缚于旧有社会制度的藩篱规制。因此,这些群体阶层的救亡探索不可能实现民众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根本的约束,也使得他们在推进思想启蒙进程中,是不愿甚至不敢真正对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因为他们的救亡主体力量往往只局限于上层主体,这就使得他们不敢发动民众。洋务派希望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派试图通过开明皇帝力挽狂澜,革命派希冀通过“先知先觉”实现革命,他们在探索民族救亡进程中,忽略了对民众的政治动员,进而无法激发起广大民众的救亡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这一理论下观照,以往救亡与启蒙的范围只是局限于上层精英,对于民众是一种排斥和否定性态度,因而在探求救亡与启蒙的进程中,两者皆未彻底成功实现。缘何以往阶级对这一关系问题的探求始终未成功突破,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正是阶级的利益局限性使然。
思考启蒙与救亡的关系,需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审视。而要从这一理论进行学理阐释,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分析切入口,阐述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扎根,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启蒙与救亡的辩证关系。吴玉章回忆道:“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要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6]509由此发现,以吴玉章为代表的原资产阶级革命派成员在面对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军阀混战的现实情形下,迫切需要一种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科学理论。
李泽厚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以前,中国近代先后出现过三种主要反帝反封建的社会思潮: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大同”空想和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1]104。李泽厚先生指出的三种启蒙社会思潮,皆未实现救亡之目的,亦未真正实现彻底之启蒙。且在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进程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都是在一种被动式的范式框架内探求,找不到何以科学处理救亡与启蒙内在关联的媒介。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7]1516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一以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政党的产生真正实现了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互为推进为特征的主动性探求。
中国共产党对救亡与启蒙关系的主动性探求解答内蕴了三层含义: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救亡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征,也是能指导中国共产党科学处理好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的重要方法论指南。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源于对人类思想文明成果的批判与扬弃。法国启蒙思想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法国启蒙学派的抽象人性论,将实践置于思想启蒙之中,将思想启蒙置入现实的实践场境。中国共产党在科学解答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时,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社会出发。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救亡与启蒙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现实的个人”,充分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阶级构成,将农民阶级的生存问题置于革命救亡的重要位置,将土地革命作为救亡的重要现实路径。同时,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不拘泥于救亡与启蒙的思辨争论,而是在打碎旧有政治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不断推进思想上层建筑的变革,进而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来指导如何探寻救亡路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进行民族救亡道路的探寻,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革命道路的探索,使民族救亡拥有了崭新面貌。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多元化方式对民众进行文化思想启蒙,在促进民众文化思想觉醒过程中,激发了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不断汇聚和壮大了民族救亡的主体力量,实现了救亡与启蒙的有效互动。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救亡之路是主动出击探求救亡之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有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所武装的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才会使这一主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5-6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一条新型革命救亡路径,且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这条救亡之路进程中不断推进主体思维领域的丰富与发展,实现了救亡与启蒙有机统一的新型革命范式。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工人力量从萌芽到发展,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在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形态变化过程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近代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同盟关系,使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进程中,也不断对农民阶级的思想进行矫正规训,使两大阶级同盟在民族救亡中实现思想启蒙。以往阶级的探寻,由于未曾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在处理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中,皆以形而上学的范式推进,因而无法彻底实现民族救亡与民众启蒙。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同时以这个思想武器对民众进行文化思想启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推进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叙事逻辑的展开。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近代中国在更高位置、更深层次、更大领域实现救亡与启蒙相互推进、互为发展的重要媒介。
三、现实维度:启蒙与救亡关系的实践探求
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救亡与启蒙实践主体的范式转换。在探索救亡与启蒙的历史进程中,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基本忽略民众的社会实践主体作用。李怀印先生指出:“改革者无论身为朝廷官员还是知名学者,均为社会精英而非普通民众,而后者在革命叙事中是推进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9]86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洋务派的效法欧美军事技术进程,客观上也发挥了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效法欧美军事技术,必然涉及现代工业、翻译出版、新式学堂等,陈旭麓先生认为,“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0]106。洋务派在推进器物变革的实践中,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生成了社会变化发展的思想酵母。维新派的变法自强希冀通过开明皇帝实现救亡,同样也忽略了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然而在进行革命进程中同样只是注重上层精英的作用,将民众当成要被拯救、被启蒙的群体。从社会纵向发展看,这些派别的探索推进了近代历史的前进,然而他们未曾根本上将民众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故而在处理救亡与启蒙关系问题上,常处于一种内在的张力势态,造成以往阶级在探寻启蒙与救亡的进程中只注重上层人士的作用,忽略人民群众的作用。阶级利益的固有藩篱,造成他们在探寻民族救亡中,不敢对广大民众实现真正的思想启蒙。
传统的救亡道路,由于忽略了民众的作用,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参与,展现了民众在救亡中的巨大力量,极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逐步实现了救亡与启蒙关系式实践路径中的主体范式转换,即由原来的精英式实践路径向大众化路径的转换。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引,在实践中广泛发动工农民众运动,在领导民众参加革命实践中,形塑民众的革命观念和民族国家意识,推进革命救亡与民众启蒙的复调行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行人民群众革命实践路线,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1031中国共产党人在乡村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民众由传统“血缘”关系向现代“政治”关系的递嬗,对乡村民众通过识字教育、妇女解放、参与民主政权建设等方式,极大激活了民众现代启蒙意识,逐步形塑了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充分调动民众积极参与中华民族救亡进程中,实现救亡与启蒙在人民逻辑下的更高层次的相互推进。李怀印指出:“现代化的前提则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有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经济起飞、政治参与扩大和社会整合才有可能。”[12]371中国共产党救亡之路遵循人民逻辑,积极通过多元化方式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救亡行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还积极通过文艺工作激发民众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国民意识。党领导和影响下的爱国进步文艺作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于民族国家意识、现代国民意识等,同样具有重要宣传效能。中国共产党摒弃了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忽略民众的革命救亡旧道路,而注重通过启蒙广大民众一起参与民族救亡行动中。张静如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即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可以理解为“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13]64。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华民族救亡新道路的思想武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广大民众也不断获得了现代启蒙意识,从而真正使中国人民的精神由被动变主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参与民族救亡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对民众进行文化思想启蒙教育,使这一时期的民众以一种主动性精神姿态投入民族救亡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救亡与思想启蒙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化”革命救亡实践进程中,不断地激活了民众的救亡意识、政治民主观念等,进而实现了革命化与现代化的双重螺旋推进。这种“化”实践后的理论逐步形成为“中国化”和“实践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为中国革命救亡实践和思想文化启蒙,提供了更为具有民族风格和特征的思想指南。
审视以往阶级的救亡与启蒙实践路径轨迹,不难发现,维新派和革命派、文化派等在探索救亡与启蒙的实践探索中,有两方面缺陷:一是在将西方思想运用于近代中国时,却未意识到西方思想启蒙学说所生成的社会实践背景。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家只是空喊词句,使以往阶级在处理救亡与启蒙关系中,表现出形而上学性。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救亡与启蒙是辩证统一的,两者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意味着,救亡与启蒙是无法割裂的,不是简单的孰先孰后,亦非是彼此独立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救亡与启蒙’不是应当孰先孰后的问题,它们是同一主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同一过程。”[14]34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民族在面对内外交困的时代场境,从器物革命—体制改革—政治革命—文化救国这样一条救亡探求之路中,救亡作为重要的历史时代任务,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在这一逻辑进路中,为救亡而向西方所学习的各种现代器物、政治体制、思想学说等,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近代中国救亡的深化拓展。二是他们未曾找寻到实现救亡与启蒙沿着正确行进路径的科学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和时代条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开启了新型革命救亡实践道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狭隘性。由于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对传统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维护与固守,造成他们在推进救亡和启蒙的进程中,始终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行进,无法从根本上呼唤和激发民众的社会变革主体力量。他们也无法从根本上找到实现民族救亡和民众启蒙的科学道路,洋务派对现代器物的学习、维新派对现代政体的效仿等,都由于传统制度的藩篱和自身阶级利益的狭隘性,造成“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与此相反,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精神由主动变被动的同时,积极唤醒民众的现代意识,使原处于“马铃薯”状态下的个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动员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农民进行文化思想启蒙,不断赋予广大农民以救亡观念,激发他们的救亡意识,逐步突破传统农民血缘关系的藩篱,使广大农民在参与民族救亡实践和新政权建设中,不断建构新型政治人际关系。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在民族救亡的实践历程中,不断实现解构与建构的辩证统一,谱写救亡与启蒙的互动逻辑叙事。正是在民族救亡实践中,对农民的文化思想启蒙,使得农民不再是“马铃薯”状态,而不断生成为孕育新社会的重要主体力量。“唯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与中国的历时性实践建立起本质的关联。”[15]13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救亡与现代启蒙的双重实践探索,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更重要的是自觉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立足革命实践,直面各种现实问题,科学解决好革命救亡与现代启蒙的对立统一关系,带领民众推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政党与民众共同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新兴政权,民众的社会关系实现了由传统血缘关系到现代政治关系的形塑,实现了民众革命救亡与现代启蒙的双重实践推进。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16]2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解决现实问题,带领民众进行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推进的革命救亡实践,内蕴了政治现代化的元素,实现了革命化与现代化双向推进、救亡与启蒙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结果。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内蕴的“启蒙”,不是社会思想文化形态的突进式嬗变,而是思想文化现代化元素的不断积累。中国共产党正是科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民众在进行土地变革和救亡的革命实践中,激活了民众的思想启蒙,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救亡力量,从而使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实践探索有了正确的行进路径。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代性,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众最广范围、最深层次的现代思想启蒙,使其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新革命道路中形成救亡的民众“合力”,彻底解决了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