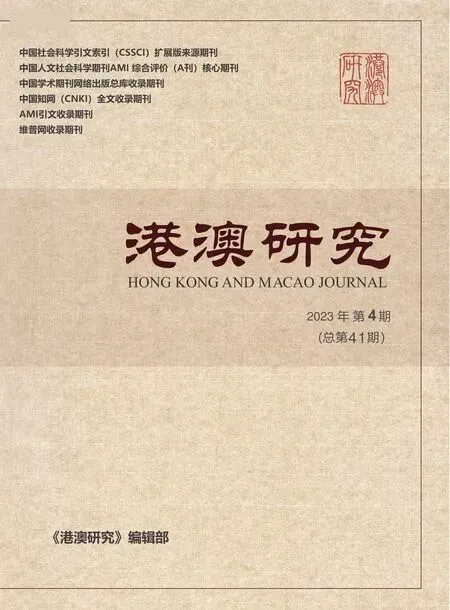析澳门新国安法中实体法修订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
赵国强
2023 年5 月18 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以下简称“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了关于《修改第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案;5 月25 日,经行政长官签署并命令公布,第8/2023 号关于《修改第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律正式生效;6 月12 日,经行政长官批示,《政府公报》重新公布了经第8/2023 号法律修改后的《维护国家安全法》文本(为表述方便,经修改并重新公布的《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为新国安法,原未经修改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则简称为原国安法)。新国安法的公布与实施对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特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立法理念上落实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要求,反映了新国安法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二是在立法内涵上不仅严格遵循刑事实体法立法的基本规则,而且始终坚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需要出发,借鉴香港特区的立法经验,体现了新国安法直面现实的特征。三是在立法结构上一改原国安法以刑事实体法为主的局面,使新国安法实现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有机结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从立法理念、立法内涵,还是从立法结构上看,新国安法都堪称一部“接地气”的国安法。
新国安法第2 章“刑法规定”属刑事实体法的范畴。这一章共规定了七个具体罪名,即“叛国罪”(第7 条)、“分裂国家罪”(第8 条)、“颠覆国家政权罪”(第9 条)、“教唆或支持叛乱罪”(第10 条)、“煽动叛乱罪”(第11 条)、“侵犯国家秘密罪”(第12 条)和“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第13 条)①根据该条文,罪名实应表述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罪”,但考虑到这样设置罪名过于繁琐,故笔者将该罪名表述为“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第15 条因仅涉及法人性质的犯罪,故并非独立的罪名。②具体解释可参阅本文“3(1):调整‘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主体和地点要件”。本文拟结合新国安法第2 章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从立法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角度,浅谈个人学习体会。
一、厘清宪制性法律与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
宪制性法律与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这关系到新国安法究竟应当如何规定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问题。众所周知,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规定的都是事关国家基本运作的“大事”,如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而其他部门法则都是就特定的范围事务加以规定,如刑事实体法的根本任务就是规定犯罪与刑罚。所以,宪法不会规定具体犯罪,即使宪法中个别条款可能会涉及到刑事实体法方面的内容,那也只是一种与法治社会密切相关的原则性规定,如有的国家宪法会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厘清了宪法与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规定具体犯罪乃是刑事实体法的专属立法权限。而刑事实体法究竟应当如何去规定具体犯罪,自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宪法的规定可以指导刑事实体法的立法,但宪法的规定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刑事实体法。比如,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立法上,宪法会规定公民应当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但危害国家安全具体有哪些犯罪,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应当如何处罚,这都要由刑事实体法按照自身的立法规则和实际情况作出详细的规定,不会由宪法来作出规定,这是最基本的立法理论和立法通例。
在澳门特区的法律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虽然不是宪法,但它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制性法律,其所规定的事项类似于宪法,都是关系到特区基本运作的“大事”,如中央和特区的关系、特区的政治制度及特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因此,澳门基本法同样不会也不可能就具体犯罪作出规定。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澳门基本法第23 条所包含的三种禁止性规定呢?③根据澳门基本法第23 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澳门基本法第23 条本身的属性进行解读,即该条文是宪制性法律的条文,不是刑事实体法,作为一种政治性宣示,其立法宗旨就是作出两个方面的宣示:一是依据“一国”原则,宣示澳门特区“应当立法”维护国家安全,以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性责任;二是从“两制”精神出发,宣示考虑到澳门特区实行高度自治的实际情况,授权澳门特区通过“自行立法”来维护国家安全。这两点宣示才真正体现澳门基本法第23 条对刑事实体法立法最直接的指导作用。至于澳门基本法第23 条规定的三种禁止,其性质仍然属于一种宣示性的规定,它对刑事实体法立法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仅具有引导性,不可能取代刑事实体法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比如,对第一种禁止所列举的五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行为来说,明显是一种建立在传统国家安全观基础上的“常规式”列举,既不代表具体罪名的表述,也没有穷尽所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行为。至于后二种禁止,则属于为捍卫国家主权而作出的一种政治性宣示。由此可见,刑事实体法在规定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时,可以参考澳门基本法第23 条所作出的三种禁止性规定,但也必须从刑事实体法自身的立法规则和实际情况出发,去设置、规定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刑事实体法为维护国家安全法益,无论规定什么样的具体犯罪,只要这些犯罪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安全法益,只要这些犯罪行为对国家安全法益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程度,那么,将其规定为具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就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根本不存在违反澳门基本法第23 条规定的问题。
遗憾的是,原国安法在其立法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宪制性法律与刑事实体法之间的关系,认识上比较模糊,致使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几乎是照搬澳门基本法第23 条规定,不敢有丝毫的“僭越”。①比如,原国安法第1 条至第5 条规定的五个独立罪名即“叛国罪”、“分裂国家罪”、“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煽动叛乱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无疑来自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中的第一种禁止性规定列举的五种不法行为,而第6 条和第7 条关于法人性质的犯罪虽非独立的罪名,但明显也是源自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中的后二种禁止性规定。新国安法则不然,它在充分把握宪制性法律与刑事实体法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既切实尊重澳门基本法第23 条的指导作用,同时又严格遵循刑事实体法立法的一般规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求实的态度设置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犯罪。比如,新国安法将澳门基本法第23 条所列举的“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和“窃取国家机密”的表述分别修订为“颠覆国家政权”和“侵犯国家秘密”,将“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修订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组织或团体”,并且还新增了“教唆或支持叛乱罪”和“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新国安法在规定具体犯罪时,并没有机械地受制于澳门基本法第23 条的禁止性规定,而是以国家安全法益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突显了刑事实体法本身的立法使命。这是新国安法不同于原国安法的一大立法特征。
二、遵循法益内涵和行为性质合理置换罪名
罪名的设置应该合理揭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内涵,也必须符合行为的性质,这是刑事实体法立法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从新国安法设置的罪名来看,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和“侵犯国家秘密罪”的罪名置换,就充分体现了这样的立法规则。
(一)关于“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置换
在原国安法中,立法者使用的是“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的罪名,这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澳门基本法第23 条列举的“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结果。但如上所述,澳门基本法第23 条所列举的不法行为只是一种宪制性法律的宣示,并非刑事实体法上的具体犯罪和罪名。从“一国两制”的角度考察,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之所以作出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列举,主要还是就中央和澳门特区的关系而言的。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具有上下级关系,澳门特区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无论如何高度自治,其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并不会改变。所以,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言,作为“一国两制”政策法律化的基本法用禁止“颠覆中央人民政府”来维护“一国”的权威,以此来突出建立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基础上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并将其同国家安全直接联系起来,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作为刑事实体法在规定通过颠覆性的行为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时,就必须考虑到国家安全法益的基本内涵,此情况下再将颠覆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表述为“中央人民政府”,就无法准确地揭示颠覆行为所侵犯的国家安全法益的具体内涵,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虽然也代表国家,但毕竟与“国家政权”的概念有所区别,如国家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显然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所能包括。“国家政权”则不然,它与国家的政治安全息息相关。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政治安全是根本,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根据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可见,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基于颠覆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内涵在于“国家政权”,强调政治安全,故新国安法第9 条将原国安法规定的“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修订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不仅突出了政治安全的本义,而且必将更有效地预防及遏止那些企图推翻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犯罪行为。
(二)关于“侵犯国家秘密罪”的罪名置换
原国安法之所以设置“窃取国家机密罪”,显然也与“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一样,照搬了澳门基本法第23 条列举的关于“窃取国家机密”不法行为的表述。但从原国安法对“窃取国家机密罪”所规定的罪状来看,这样设置罪名显然有悖于犯罪行为的性质。
在刑法理论中,以主观罪过为标准,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分为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设置罪名时,如果一个罪名会包括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两种行为时,立法者都会用一个“中性”的罪名来包含两种性质的行为。比如,澳门特区《刑法典》分则第264 条规定的罪名叫“造成火警、爆炸及其他特别危险行为罪”,这就是一个“中立”的罪名,因为这个罪的行为性质既可以是故意行为,也可以是过失行为,故意放火、爆炸可以叫作“造成火警、爆炸罪”,过失造成火灾或爆炸,也可以叫作“造成火警、爆炸罪”。但是,我们从原国安法规定的“窃取国家机密罪”的罪状来看,此罪不仅包括了故意行为,如窃取、刺探或收买国家机密的行为,同时也包括了过失行为,如因过失导致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既然如此,用“窃取”来设置罪名,当然是不合适的。道理很简单,“窃取”在中文中只能是指故意的行为,不能包括过失的行为。澳门基本法第23 条用“窃取国家机密”的表述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作为一种宣示,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宣示禁止通过故意窃取国家机密来危害国家安全,至于存在因过失泄密而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那就是由刑事实体法通过立法来解决的问题了。这也间接地说明,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作为一种宣示性条款,它不可能对刑事实体法要规定的犯罪作面面俱到的列举。正因为如此,新国安法第12 条将“窃取国家机密罪”修订为“侵犯国家秘密罪”①根据修改第2/2009 号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法》的理由陈述,关于“侵犯国家秘密罪”的设置还涉及到从结果犯转为危险犯以及将“国家机密”改为“国家秘密”的问题。因这两点修正不像将“窃取”修订为“侵犯”那样关系到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故本文不作赘述。就具有了合理性,因为故意窃取秘密可以说是一种侵犯,过失造成泄密也可以说是一种侵犯,这样就是用一个“中立”的罪名取代了只能由故意行为构成的窃取型罪名,因而充分体现了刑事实体法的严谨性。
三、从实际出发调整或扩充构成要件
在刑法理论中,构成要件都必须是法定的,这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为此,新国安法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保护国家安全法益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相关的法人性质的犯罪以及其他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调整或扩充。
(一)调整“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主体和地点要件
根据原国安法第6 条规定,“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机关或其人员以该组织或团体的名义并为其利益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作出本法第1 条、第2 条、第3 条、第4 条或第5 条所指的行为,除行为人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外,对该组织或团体科处以下主刑和附加刑”。这一规定的依据来自澳门基本法第23 条关于“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的规定。很显然,这是一条关于法人性质犯罪的规定,不涉及独立的罪名。有人认为,原国安法第6 条规定也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其实这种理解是一种误解。因为对法人性质的犯罪,理论通说和立法通例都是采取“双罚制”,即既处罚责任人员即行为人,也处罚相关的法人性质的组织或团体。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组织或团体构成什么罪必须依据责任人员的罪名而定,两者不会分离。举例来说,外国的A 组织中的甲以A 组织的名义并为A 组织的利益在澳门特区作出了分裂国家的行为,甲作为责任人员即行为人,需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要按“分裂国家罪”来定罪量刑,而A 组织所触犯的罪名必然会依据甲的罪名而定从而构成“分裂国家罪”,只不过处罚时要按照原国安法第6 条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处罚,事实上这种主刑和附加刑本来也是为犯了罪的组织或团体设置的,因此不存在独立罪名的问题。
但是,原国安法第6 条关于法人性质的犯罪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组织或团体的性质限定为“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不符合实际情况。例如,从香港特区发生“修例风波”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少幕后的外国“推手”组织或团体并非是什么“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他们往往打着所谓的“民主”“自由”旗号,公然煽动、教唆香港年轻人“逢中必反”,鼓动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实施暴乱。如果我们将组织或团体的性质限定为“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就无法有效惩治此类“挂羊头卖狗肉”的外国组织或团体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二是将实施犯罪的地点限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境内,同样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外国的组织或团体所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在澳门特区实施,当然也可以在澳门特区以外实施,如输送资金、培训“暴徒”,如果在澳门特区以外实施,按照保护管辖原则,澳门特区一样享有刑事管辖权,这样就有利于构筑起一道维护国家安全的域外保护网。基于此,新国安法第15 条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保留原国安法第6 条关于法人性质犯罪的基础上,在主体方面将“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机关或其人员”修订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组织或团体或其人员”,在实施犯罪的地点方面则删除了原国安法第6 条关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限制性规定。这一修订不仅扩大了对此类法人性质犯罪的惩治范围,而且也证明了澳门基本法第23 条规定与刑事实体法规定是不能相互取代的。因为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作为宪制性法律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这是一种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性宣示,但刑事实体法在规定具体犯罪和刑事责任时,都必须遵循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必须符合实际情况。
(二)调整“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犯罪手段
根据原国安法规定,构成“分裂国家罪”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不仅主观上要有分裂国家或者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故意,而且客观上必须要求使用“暴力”或者“其他严重非法手段”。然而,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立法上,对此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客观上是否一定要求使用“暴力”手段,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从发生在香港特区的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来看,有些行为当然具有暴力性质,如冲击立法会、机场和占领校园等行为,但有些行为不一定使用暴力,如通过煽动、鼓吹“港独”以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或组织、策划打着“港独”的标语或港英时期的旗帜游行、招摇过市。基于此,香港国安法第20 条和第22 条在规定“分裂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时,排除了使用“暴力”行为的必要性,明确规定只要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和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即构成犯罪。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以后,“港独”分子之所以不敢再狂妄、嚣张,与这一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为此,新国安法第8 条和第9 条借鉴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经验,明确废除了原国安法关于构成“分裂国家罪”或“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客观上必须使用“暴力或其他严重非法手段”的限制,在客观方面,只要“藉任何非法手段”,试图作出分裂国家行为或颠覆国家政权行为的,即构成犯罪。这对于那些企图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不法分子,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威慑力。
(三)扩充“分裂国家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原国安法第2 条规定,“分裂国家罪”主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就是实施了“试图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国家主权分离出去或使之从属于外国主权者”。应该说,这一分裂国家的定义具有普遍性,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考察,国家安全是不能仅用传统国家安全概念强调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所能概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国家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一体化,强调国家根本制度和社会内部的稳定性,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稳定性。根据我国宪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由宪法明确加以规定的,蓄意破坏宪法所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无疑是在破坏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破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因而也是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尤其是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区因享有高度自治权,其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的稳定关系,是通过我国宪法和基本法明确加以规定的,而这种稳定关系又是建立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基础之上的,不管如何高度自治,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在法律地位上都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因此,依照我国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维护中央与特区之间的这种稳定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内部安全,当然也属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任何企图改变特区法律地位的行为,都应视为分裂国家的行为。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新国安法第8 条参考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经验,扩充了“分裂国家罪”的构成要件,将原来的构成要件行为细分为三种行为:一是试图将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国家主权分离出去的行为,二是试图改变澳门特区或国家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的行为,三是使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从属于外国主权的行为。其中第二种行为就是对“分裂国家罪”构成要件的扩充。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行为和第二种行为有所不同,前者涉及使某部分国家领土脱离国家主权,而后者是在不脱离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违反宪法及澳门基本法的规定,非法改变澳门特区或国家其他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以此来破坏国家的内部稳定,并企图以此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举例来说,“港独”分子试图将香港特区从国家主权中分离出去,这是符合第一种使香港特区脱离国家主权的分裂国家的行为。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改变由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下中央与香港特区之间的关系,这就符合第二种非法改变香港特区法律地位的分裂国家的行为。对澳门特区来说,同样如此。可见,新国安法对分裂国家罪构成要件的修订,实际上深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四)扩充“煽动叛乱罪”的构成要件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煽动也是一种教唆行为,但由于煽动的对象通常是不特定的人群,如在集会、游行中煽动,煽动的方法包括利用语言、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各种方式,煽动的目的往往是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鼓动他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希望造成社会动荡、暴力冲突、恐怖袭击等严重后果,以至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在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立法中,立法者考虑到煽动型行为的危害很大,通常会将其与一般的教唆行为区别开来,使其独立成罪。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3 条第2 款规定的“煽动分裂国家罪”和第105 条第2 款规定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属于此类煽动型犯罪。原国安法第4 条规定的“煽动叛乱罪”就是一例。
原国安法规定的“煽动叛乱罪”主客观构成要件,仅限于煽动他人实施“叛国罪”、“分裂国家罪”或“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三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煽动驻澳部队成员弃职或叛变。但是,从香港特区发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某些煽动者的煽动行为并非直接煽动他人叛国、分裂国家或颠覆国家政权,而是煽动他人参与各种骚乱,意图通过各种骚乱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内部稳定,乞求外部敌对势力的干预等,以此达到使政府的管治瘫痪和搞乱香港的目的。对这种肆意危害国家总体安全的行为,必须加以惩治。为此,新国安法第11 条本着居安思危的立法理念,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扩充了“煽动叛乱罪”的构成要件,除了规定公然和直接煽动他人实施“叛国罪”、“分裂国家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三种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公然和直接煽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的成员放弃职责或叛变会构成“煽动叛乱罪”外,同时还规定,凡属“公然和直接煽动他人参与旨在危及或损害国家的内部或对外安全利益的骚乱”,只要“按其他法例规定不科处更重刑罚”的,同样会构成“煽动叛乱罪”。无庸置疑,这一修订同样深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四、参考香港国安法增设新罪名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极力阻挠下,香港基本法第23 条被严重污名化、妖魔化,难以实现立法,而香港特区原有的本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却长期形同虚设,以至在涉港国安事务方面,法律制度处于空白状态。二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以致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勾连合流,明目张胆地使用各种非法手段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挑战“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②关于这一历史背景,请参阅2020 年5 月22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王晨副委员长所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的说明。面对香港特区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中央政府果断出手,制定实施了香港国安法,迅速扭转了局面,充分展示了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强大的治国能力。
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究其根源,就是因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接地气”的国安法。香港国安法充分考虑了反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内外勾结的行为,反中乱港分子公然煽动、教唆他人走上街头实施骚乱,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正因如此,规定了针对性很强的具体罪名,可以说个个都有“打蛇打七寸”的功效。香港和澳门是近邻,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发生的事情澳门并非没有苗头,因此澳门必须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新国安法应当借鉴“香港国安法”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
新国安法参考香港国安法立法经验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增设了“教唆或支持叛乱罪”和“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
(一)关于“教唆或支持叛乱罪”
根据新国安法第10 条规定,“教唆或支持叛乱罪”实际上可拆分成两个独立的罪名,即“教唆叛乱罪”和“支持叛乱罪”。
“教唆叛乱罪”是指用公开或私下劝说、怂恿、利诱或威胁等方法,唆使并引起他人实施“叛国罪”、“分裂国家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且按此三罪的规定不会被科处更重刑罚的行为。对“教唆叛乱罪”的理解,要注意与“煽动叛乱罪”区别开来,因为“煽动叛乱罪”中煽动行为指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而“教唆叛乱罪”中的教唆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的,一旦教唆行为指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群,行为具有公然和直接的特征,那就会构成“煽动叛乱罪”。
“支持叛乱罪”在构成要件上可包括两类行为:一类行为是指意图帮助或协助他人实施“叛国罪”、“分裂国家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对其给予支持,尤其是通过提供物质、情报或其他支援给予支持;另一类行为就是指意图资助他人实施“叛国罪”、“分裂国家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提供或收集资金、经济资源或任何类型的财产,以及可转化为资金的产品或权利从而给予支持。只要这两类支持行为按上述三罪规定不会被科处更重刑罚的,可独立构成“支持叛乱罪”。
从主观要素来看,此类教唆或支持行为的目的非常明确,其犯罪故意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应当指出,在大陆法系的共同犯罪理论中,直接参与犯罪或在幕后指挥、策划的人叫“正犯”,而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教唆者或帮助者叫“教唆犯”或“帮助犯”。对“教唆犯”或“帮助犯”本来理应作为共同犯罪人按照“正犯”构成的罪名依法进行处罚,但是,立法者为了更有效地惩治某类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往往会将相关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正犯化”,使其独立成罪,并为其配置独立的法定刑。这样一来,实施了该类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的人就会与共同犯罪中的“正犯”行为分开处理,并被当成一种新罪名的“正犯”而独立定罪。在现代刑事立法中,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且也被各国和各地区的刑事立法广泛采用。
以上分析表明,在新国安法中增设“教唆或支持叛乱罪”,不仅有着充足的刑法理论依据,符合关于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理论与立法实践;而且也是在充分考虑到香港特区发生的幕后策动暴乱及幕后提供资金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借鉴“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经验,以此来加大对国家安全法益的保护力度,体现新国安法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形势需要的特征。此外,还必须指出,基于一定的立法目的而在刑事立法中采用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技术,这在澳门刑法中也是早有先例的,因而符合澳门刑事立法的惯例。①比如,澳门《禁止不法生产、贩卖和吸食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17/2009 号法律)规定的“怂恿他人不法使用麻醉药品及精神药物罪”,就属于教唆行为的“正犯化”。而澳门《预防及遏止恐怖主义犯罪》(3/2006 号法律)规定的“资助恐怖主义罪”则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
(二)关于“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
根据原国安法第7 条规定,“澳门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机关或其人员以该本地组织或团体的名义并为其利益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作出本法第1 条、第2 条、第3 条、第4 条或第5 条所指的行为,除行为人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外,对该组织或团体科处以下主刑和附加刑”。这一规定的依据当然也是来自澳门基本法第23 条关于“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的规定。如前所述,这一条规定因涉及法人性质的犯罪,所以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新罪名。
值得注意的是,原国安法第6 条和第7 条虽然都是关于法人性质犯罪的规定,但新国安法对这两个条文采用了不同的修订方式。对原国安法第6 条,新国安法采用的是继续保留其法人性质犯罪的修订方式,只是在犯罪主体和犯罪实施地点上作了修正。但对原国安法第7 条,新国安法则采用了明文废除的修订方式,并增设了“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新罪名。新国安法作出这样的修订,主要原因在于原国安法第7 条规定就其性质而言,无外乎是一种内外勾结型的犯罪,它与法人性质的犯罪没有直接关系,将这种内外勾结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视为法人性质的犯罪,既不妥当,也没有必要,而且极不利于有效打击内外勾结型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澳门基本法第23 条之所以明文禁止澳门特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是一种政治性宣示,与具体的刑事罪名没有直接关系。而作为刑事实体法在规定内外勾结型犯罪时,除了要考虑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外,更应当考虑的是如何从实际出发有效维护国家安全法益,惩治内外勾结型的犯罪活动,以适应形势需要。
香港特区发生的骚乱告诉我们,在香港特区,对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国的武装侵略,也不是来自外部的制裁,而是来自内外勾结的“颜色革命”的威胁。尤其是来自内部的“仇中”政客和“港独”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勾结外部敌对势力,用非法“占中”、操纵选举、发动骚乱、乞求外部敌对势力制裁等手段来危害特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其危害之大,不严惩不足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香港国安法之所以明确规定“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是要从根本上斩断此类内外勾结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分子的魔爪。因此,在澳门特区国安法的立法中,设置内外勾结型的具体罪名,反映了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
正是通过香港特区那些“反面教员”的各种丑行,新国安法第13 条参考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经验,在废止原国安法第7 条规定之后,明确规定了“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根据该条规定,凡“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外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就会构成“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该罪在犯罪主体方面是“开放性”的一般主体,不管什么样的组织、团体或个人,只要符合法定的构成要件,都可以构成此罪。为此,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新国安法不仅对内外勾结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如非法扰乱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操控、破坏选举,乞求外部势力对国家或澳门特区进行制裁、封锁或采取其他敌对行动,引发澳门特区居民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仇恨,而且就“联系”的外部表现形式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如向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提出请求,与其串通,接受这些组织、团体或个人的指使、控制、资助或其他形式的支援,协助该等组织、团体或个人作出法律所规定的各种不法行为。
可以说,新国安法增设“教唆或支持叛乱罪”和“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乃新国安法最“接地气”的表现,因为它们是中央人民政府、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政府以及广大爱国爱港爱澳同胞与形形色色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斗争的智慧结晶和法治产物,在特区构筑起严密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网”。
五、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
在刑法理论中,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是两种不能混同的行为。对犯罪预备行为,澳门《刑法典》总则采取的是不处罚主义,即“预备行为不予处罚,但另有规定者除外”。这就意味着,在规定具体犯罪的条文中,只要没有处罚预备行为的特别规定,就表明对该等犯罪的预备行为不予处罚,不构成犯罪。那么,在澳门刑法中,有没有处罚具体犯罪预备行为的特别规定呢?若有,其处罚的标准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澳门《刑法典》分则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特别规定稍加审视,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在澳门《刑法典》分则中,经立法者特别规定,有三类重罪的预备行为是要处罚的,而这三类重罪并非是侵犯个人法益的重罪,它们都属于侵犯社会公共法益的重罪。第一类是危害社会金融安全的犯罪(第261 条),包括“假造货币罪”在内的五种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类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第266 条),包括“造成火警、爆炸及其他特别危险行为罪”和“核能罪”两种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三类是危害澳门本地区安全的犯罪(第305 条),包括“暴力变更已确立之制度罪”、“煽动以暴力变更已确立之制度罪”和“破坏罪”三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很显然,在修订原国安法过程中,立法者已经充分考虑到澳门《刑法典》分则处罚犯罪预备行为的立法标准,并认为国家安全法益乃是社会公共法益的重中之重。既然危害澳门本地区安全罪的预备行为都要处罚,那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预备行为,则更应当处罚其预备行为。为此,新国安法第14 条特别规定,对“叛国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叛乱罪”、故意的“侵犯国家秘密罪”以及“与境外组织、团体或个人建立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预备行为,以犯罪论处,最高可处三年徒刑。这一规定完全符合澳门《刑法典》分则对犯罪预备行为所采取的处罚立场,有充足的合理性。
处罚犯罪的预备行为,会直接涉及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问题。在刑法理论中,所谓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是指通过立法将某种犯罪的预备行为升格为实行行为,从立法技术上考察,这种升格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一体化的立法模式,即直接将预备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如对“贩卖人口罪”(第153 条)来说,绑架本属于贩卖的一种预备行为,但被立法者直接规定为“贩卖人口罪”的实行行为。第二种是独立成罪的立法模式,即将预备行为规定为另外一种新的罪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2 条之二规定的“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第三种是不规定新的罪名,但规定独立的法定刑的立法模式,如澳门《刑法典》分则对三类侵犯社会公共法益的重罪处罚预备行为的规定虽无改变罪名,但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新国安法对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显然是采取了第三种立法模式。由于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有助于对重大法益的提前保护,故得到了学者和立法者的青睐。新国安法关于处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预备行为的规定,不仅符合犯罪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立法理论,而且必将大大强化对国家安全法益的保护力度。
必须指出,新国安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预备行为予以实行行为化,还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
一是完善了澳门《刑法典》分则与新国安法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上所述,根据澳门《刑法典》分则第305 条规定,“煽动以暴力变更已确立之制度罪”(第298 条)的预备行为是要被处罚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徒刑。但根据原国安法规定,除对“叛国罪”、“分裂国家罪”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罪”要处罚预备行为外,对“煽动叛乱罪”却不处罚预备行为。这就出现了澳门《刑法典》分则和原国安法之间在处罚犯罪预备行为方面产生了明显的不协调现象:同样是煽动型的犯罪,为什么煽动危害本地区安全的犯罪要处罚预备行为,而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则不处罚预备行为?难道本地区安全的法益要高于国家安全的法益?这当然是荒谬的。因此,新国安法将“煽动叛乱罪”纳入处罚预备行为的范畴,就克服了澳门《刑法典》分则与原国安法在处罚犯罪预备行为方面的不协调现象。
二是克服了“教唆犯从属性”带来的解释上的困境。因为根据澳门《刑法典》总则第25 条规定,在教唆犯的属性方面,立法者采用的是“教唆犯从属性”的观点,即只有当被教唆的人已实行或开始实行被教唆的罪时,教唆犯才能作为正犯成立,否则,教唆犯不能成立,也就是不构成犯罪。举例来说,甲教唆乙杀人,乙准备去杀人并开始磨刀,在磨刀过程中被发现制止。像这种情况,因磨刀只是杀人的预备行为,并非杀人的实行行为,所以表明乙还没有开始实行杀人行为,如此一来,不仅乙的杀人预备行为不构成犯罪,甲的教唆犯也不能成立,其教唆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如果某种犯罪的预备行为被实行行为化了,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举例来说,甲教唆乙去实施爆炸行为,乙在制造炸弹的过程中被发现抓获。像这种情况,由于爆炸罪的预备行为已被立法者升格为实行行为,因此,乙的制造炸弹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爆炸罪的实行行为,也就是表明乙已开始实行爆炸罪,在此情况下,不仅乙构成爆炸罪(预备)的正犯,①在刑法理论中,正犯的行为就是实行行为,所以,犯罪预备行为的实行行为化也被学者称之为预备行为的正犯化。甲也会构成爆炸罪(预备)的教唆犯,二人属共同犯罪,都会按正犯受到处罚。②根据澳门《刑法典》总则关于共同犯罪人的规定,对教唆犯须按正犯处罚。由此可见,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之后,凡教唆他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即使被教唆的人在犯罪预备阶段即被抓获,也应视为被教唆的犯罪已“开始实行”,故教唆犯成立,并会与被教唆的人一起构成共同犯罪而受到应有的处罚。
综上所述,新国安法作为澳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中的基础、主干和核心法律,是一部充分体现时代性与合理性的法律,其公布实施必将为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性责任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也必将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成功实践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