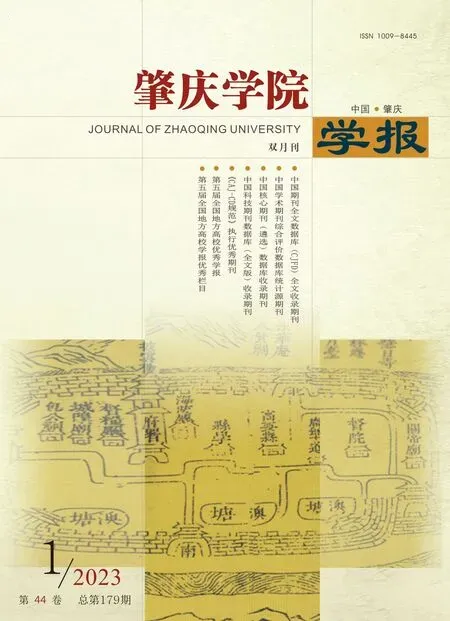谢文洊《中庸切己录》思想内涵析论
黎雅真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一、前言
谢文洊(1616-1682)字秋水,号约斋,江西省南丰县人,先后在果育斋、新城、梅源等处设馆授学。顺治十一年(1654)于南丰县城西建立的“程山学舍”,时称“程山学派”,卒后门人私谥为“明学先生”①谢鸣谦《程山谢明学先生年谱》载:「弟子议,私谥曰:明学夫子,议曰:孔孟之学,至宋程朱学派而益明,近代薛胡数君子继之,然而二氏之说功利之习中于,人心为世道之害,终不熄也,吾师程山谢先生,生于僻壤蚤,厌举子业,参究佛书有所得,頼天诱其衷,返悟圣学,一宗程朱学派三十余年,潜心肆力体认,则极其深沈践履,则极其笃实辨异端,则毫厘毕析辟俗学与诲人也。」收录于《年谱丛刊》73册,页305。。谢文洊处于明末清初之际,主张中兴儒学以挽救世道人心,其为学严谨,践履笃实,本着以诚意为本,以识仁为体,提倡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令当时许多学者因其才华而愿列门下。可惜谢文洊的著作不是至今毫无存本流传,就是仅有序文存世,很少有内文完整的作品留存,《中庸切己录》即是其著作中,序文、内文皆完整的作品之一,乃其阐发儒家《中庸》思想的重要著作,主要说解谢文洊对《中庸》义理思想的观点,主张以率性为根本,以切己为工夫,以慎独为准则,以程朱之脉为依归的思想内容。可惜综观目前学界对于谢文洊的研究成果,多是集中在“江西三山”的学派比较,或者围绕其“畏天命”思想衍申的西方宗教观点,而聚焦《中庸切己录》义理思想的研究尚待开拓。
《中庸》是精微而实践的人生哲学,主要阐述天人之学,说明自然与人的关系,以“性”“道”“教”为总纲,以“诚”为内发的原动力,期望达到天人合一、成己成物的终极目标。自古《中庸》一直是中国哲学界探究义理之课题,亦是儒家论及修身养性、进德达善的著作,不仅继承先秦儒家的道德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儒家的经世实学。笔者研究发现谢文洊《中庸切己录》亦对《中庸》的天人关系、人伦实践,以及慎独思想的内容多有发挥。其内文首要阐明着书动机:
千古学术之不明,以致世道人心之陷溺者,皆由于本原之不正耳。本原不正,则工夫不切,工夫不切,则功用成就适足为祸害之案耳。是以子思子忧道心切,必先挈出本原,推其义之所由来,正其名之所由在,使学者志之所向,途之所趋,昭然知所归往,不至彷徨歧惑,然后下手中其肻綮,循循而进,生机娓娓,及其成功,巍巍荡荡,可与古帝比隆,方见头正尾正,体用一贯,内外一脉,然后知吾儒学术。[1]595
谢文洊表示学术昏明,以致人心陷溺萎靡,是因心之本原不正之故,本原不正则修养工夫无法笃行,工夫不切即使功成名就,皆沦为祸害无益,最后终将流于功利俗学而不自知。谢文洊提出学者明学须先明道,了解道德本性的来源,才能确立志向循序而进,深知明道为世道人心之所仰赖,彰明学者求学的本原在于道德本性,应导正被世俗蒙蔽的本心,以躬行实践的工夫去除恶习,同时融入程朱理学的体用、内外关系,最终回复本来之善性、良知,达到成己成物的境界。笔者由此推断谢文洊意图将程朱的理学观点与儒家的修养方法结合,故本文以《中庸切己录》内容为主轴,分为“天道率性”、“切己工夫”和“慎独达德”三点,析论谢文洊《中庸切己录》之思想内涵。
二、《中庸切己录》思想析论
(一)天道率性
《中庸》一书出自《礼记》第三十一篇,内容阐述不偏不倚、至中至正的常理,是讲求发展本性至善的尽性之书,不仅有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并展现“天人关系”的一贯之道。谢文洊认为天地万物皆有其循常不变的道理,此道出自于天,所以遵守此道而行,不违背此理而驰,即是依循天道天理而行。正如《中庸》开宗明义言: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2]
《中庸》说明天命是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它是一种存在的根源、存在的道理,与存在的规律,所以天时变化的趋势,称为本性。率性是自然而然依道而行,正因上天赋予人本质之性,依此本性而行称之道,故遵循着本性而运行活动,即为人道,即是人所遵循的正路。修养自身的过程,以礼乐教于天下,无非是遵循人性,修明人道的教育教化,而教化就是将此道为依归,不断修养自身品德,以达尽性至善的境界。谢文洊《中庸切己录》主张“道者率性”:
所谓道者,率性而已,性无不有,故道无不在,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动静食息,不假人力之为,而莫不各有,当然不易之理;所谓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贯彻古今。[1]598
谢文洊赞同朱熹之说,主张“率人性以明天道”,此道无所不在,大则涉及君臣父子;小则牵动饮食休息,充塞于天地,贯通于古今,同于《中庸》所言“率性之谓道”之意,循之则治、失之则乱,绝不可须臾离开,违背此正道而行,强调若有例外,离道而行却无所损益者,即是后天人力所为,并非率性循道而行。谢文洊《中庸切己录》再言“道本于性”:
道本于性,只率性便是道,率性二字孟子指点得最亲切,如爱亲、敬长,出于孩提之童怵惕恻隐,出于乍见,嘑蹴之食宁死不屑,如此等处皆是本性。[1]597
谢文洊说明天道本于人性,正因人性与天道能相应相通,故“率人性”则可“明天道”,此“性”同孟子所言天生本有的善性,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面对嘑蹴无礼污辱的施舍,人宁可忍饥受饿,此良知之性皆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本性,依本性而行,率本性而为,正是依循天道自然法则的作为。关于阐释“率性而知性”,《中庸切己录》有言:
率性二字真切,于日用动静,才有个本领,一毫不由人力私智矫揉造作,即造到圣人地位,存神过化,出奇不测,皆是性分所固有,非有一毫增减于其间,然后知圣人之道,一日不容昧,千古所必由,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与夫百家众技、支离偏曲,天渊不侔,皆根于所性故耳,故学者贵在于知性。[1]597-598
谢文洊说明率性体现于日常生活中,正因“性”为人本固有,依循天道而行,不可经人为矫揉造作,须后天存养本性本质,方可迈向圣人的境界,如同儒家所言“圣人观”,如何成圣成贤之道。所以修养道德贵在“知性”,“知性”即可循道而行、率性而为,不可片刻离开或违悖此道,生命本就是率性修道的过程,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又同杨祖汉先生表示:“儒者所体证之天理是即于伦常日用之活动而显的,不能离伦常日用而别有超然独立之最高实体。”[3]我们遵行天道、天理,就是依循人道、人理,故“知性”才能掌握此理,所以学者不可忽视“知性”的重要。
《中庸》提出“诚”为天道本体运行的彰显,并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与原则,人既然受天命之性所生,自然不能违背天道而行,必须依循本性向天学习真实无妄的修养之道,达到成己成物的“圣人”境界,可知“诚”不仅贯通天人之道,亦是修养工夫的完成。谢文洊《中庸切己录》又言:
凡事豫则立,泛泛言来归重在道,先立乎诚,即道前定则不穷也。[1]629
谢文洊认为行事预先做好准备才更能成功,说明《中庸》提出“诚”贯通天道与人道,阐释“诚”字之义有二,“诚者,天之道”阐述形而上的本体即“诚体”;“诚之者,人之道”说明人依循本性来涵养道德而不失其道,所以注重“道”当先立“诚”,儒家所言“诚”,即是天道、天德,人依天道努力做到“诚”,就是人道、人德,故“至诚能尽性”能将天道、人道展现于至诚者,才是真正实践人无穷尽的至善之性。
(二)切己工夫
《中庸》内容阐发“诚”是天生万物的道理,是身为人天生自然的禀性。由哲理的观点来看,《中庸》把空泛、抽象的形上之学道德化,并融入于日常生活中,根据孔子“践仁以知天”的智慧,开展出形上的道德思想,由形上的天道至形下的人道,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故实践内心之“诚”即是印证做人的原则、反求切己的工夫,便落实在“诚”字上。谢文洊《中庸切己录》云:
至圣即至诚,诚则明,明者诚之用,聪明睿知正指至诚之明耳,乃天性中所发之良知,不由学问而得者也。……细分明中之条理,乃仁义礼智之用。[1]644
“诚”是天人合一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亦是进德修业的不二法门,谢文洊强调“诚”是人性本有之良知,虽不经外力学习求得,但须持续自我修养实践,所以不断地实践“诚”,则可达圣人崇高的智慧。“明”为“诚”之德行展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实践“仁”“义”“礼”“智”,亦是“诚”各个面向的体现。徐复观先生认为:“诚是以仁为内容,故《中庸》全篇所言之诚,实际皆说的是仁。”所以如何做好“仁”“义”“礼”“智”等诸德行,正是考验个人切己工夫的实践。谢文洊《中庸切己录》有云:
人人在五伦之中,然而能尽其道者,盖寡其故何在,只是缺却智、仁、勇耳,不知则不知此道之何以尽,不仁则虽知之而不能尽,不勇则遇艰难处便生阻隔,亦归于不能尽究而言之,只是此心不诚耳,心果诚则智、仁、勇,无有不到而达道尽矣。[1]627
谢文洊结合五达道与三达德,说明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彼此间的伦理关系,当围绕三德:“智、仁、勇”三种体现“诚”的道德行为来实践,而“智、仁、勇”三者关系相连相扣、缺一不可。是由人道的道德实践,反映天道的真诚本性,正因人之心性本诚,透过存养到扩充,反省至实行的切己功夫,才能达“智、仁、勇”至诚的境界。
谢文洊认为人性有许多私心、惰性,如不加以适当的节制,长年累积的成见弊端将无所遁形,所以不断修养自身的工夫显得格外重要,而修养工夫首重“切己”为要,“切己”就是不断反省自身的去私过程。《中庸切己录》内文亦云:
学者须是极力去私,求复此至大至深,体段自然,当宽裕温柔,即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即发强刚毅;当斋庄中正,即斋庄中正;当文理密察,即文理密察,丝毫不爽矣。[1]645
谢文洊认为人之心性如眼目,本身自带光明,但经后天外在欲望的浸染,则满眼逐渐浑沌不清,导致不明事理,故学者应当努力去除私欲,追求回复原本至大至深的德性,正是切己实践的修养工夫,当宽裕温柔,即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即发强刚毅;当斋庄中正,即斋庄中正;当文理密察,即文理密察,丝毫不可矫揉造作,强调该从心性上袪除私欲才算达成。相对来说若私欲不除,所作所为则遭障蔽,想宽裕温柔,因私欲而阻碍;想发强刚毅,因私欲而困馁;想斋庄中正,因私欲而放荡;想文理密察,因私欲而昏散,即使竭尽一切努力,终将徒劳无功。至于切己工夫当如何实践?《中庸切己录》再云:
做慎独工夫,其初立心处,便只是切实为己,故首节先序,立心为己处,做个冒头,人心无不贪外好名,若非切实为己,怎肯收拾向里面来,闇然正是极力敛藏,不使些子渗泄,一切外炫尽情刊落,专精毕力,只向内地究觅,久之,一念天理,几希微妙,渐见昭著日章,只是内地日渐盛大昌明,且莫遽说向外来日亡,亦是内地日渐销亡。[1]647
谢文洊表示道德修养的工夫当从具体着手,尤其当注意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因人心无不贪外好名,所以更应加强自身去私欲的切己工夫,慎小慎微、笃实为己、躬行践履,袪除外在名利欲望的渲染,着重内在切实反省的实践。谢文洊后文再指出“淡、简、温”,属于观照切己的外在工夫,“不厌、文、理”属于体察切己的内在修养,如此内、外两者同时进行,才是做到切己工夫之极致,可惜现今贪外好名之人甚多,导致外在何等浓热,内在却只消沮;外在何等繁缛,内在却只枯槁,如此反差,即便浑厚朴实的气质,也容易流于放荡恶习,所以学者必须立定心志,淡习、简事、温行,并着力体察切己实践,才能自持处之得宜。
(三)慎独达德
《中庸》言:“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谢文洊认为在细微和隐蔽的情境下,对道德原则的把持遵守格外重要,“慎独”要求人须存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遵循天道赋予的纯然本性,并且扩充此善心良知,最终则能成圣达德、止于至善。所以学者当毕生践行“慎独”,提升高尚的人格与博大的胸怀,体现中庸思想之道的内涵。《中庸切己录》有载:
君子只一念之间,时时戒谨恐惧,便尽了中庸之道。小人所反中庸者,只一念颓然自放,便到无忌惮的境界,人品有天渊之别,只在一敬怠之间而已矣,所以中庸道理说得如是深、如是大,其实下手只在此处。[1]605
谢文洊表示中庸之道体现于“戒谨恐惧”,强调“一念之间”意识的发动,为于“人虽不知而己独知”的念头刚刚萌动之初,便加以谨慎克制,使心所体认与天理须臾不离,是对一念萌发的欲望觉知,具有强烈道德省察的心理活动,因此就其作用的时段来说,“戒谨恐惧”其实就是“慎独”贯通动静的工夫,此同朱熹之说“静养动察,敬贯动静”的工夫,故“慎独”的核心即是“主敬”,“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5]185“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5]186故人欲的克制,最终要消融到粲然的地步,才可达“持敬”纯熟的境界。谢文洊认为小人无法戒谨后沉于颓废委靡,无法慎独终流于自我放逐,正因“敬怠之间”产生的善恶差异所致,故朱熹言:“就其中于独处更加谨也。是无所不谨,而慎上更加谨也。”[5]1342-1343所以“慎独”需要格外地醒觉、克制、省察,避免流于自欺。《中庸切己录》亦载:
慎独则省察、存养俱在内,不可专以慎独属省察也,首章末章都说慎独,可见慎独是工夫本领。[1]648
谢文洊说明慎独的工夫包含省察、存养两部分,因当今人们往往着重省察容易忽略存养,所以省察自身是否克制去私,存养本心是否扩充持敬,如此才能达到慎独的目的,《中庸》首章与末章皆有特别言明,足见慎独之重要性。《中庸切己录》亦探究由慎独工夫,达无善无臭的境界:
《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终言无声无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惧,曰谨独,曰笃恭,则皆示人以用力之方。盖必戒慎、谨独,而后能全天性之善;必笃恭而后能造无声无臭之境,未学使人驰心窈冥,而不践其实也。……可见《中庸》为道虽博,而其入手亦甚约矣。[1]596
谢文洊说明《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终言“无声无臭”,上天化育万物,没有声音和气味,正因天地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与变化,万物则在大自然中找到适合生存的地位,彼此形成和谐共融的关系,故世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形容如此高妙的境界。谢文洊建立一套以天命人性为旨趣;以中和之道为核心;以修身养性为重点;以切己务实为根本,即是言戒慎、言恐惧、言谨慎、言笃躬,可见《中庸》为道虽博,但身为学者只要努力实践,以“慎独”时时警惕自己,则可达到“无声无臭”成德的终极目标。《中庸切己录》阐释“慎独”之终极目标则有载:
《中庸》一书首言慎独,便推其效,至于位天地,育万物,终言慎独,便推其效,至于笃恭而天下平,复赞其德,至于幽深元远,至于无声无臭,慎独工夫之切要如此,慎独功效之神奇如此。[1]649
谢文洊表示《中庸》一书本着“慎独”二字,平时推行其德,以至化育天地,实践本性方能体悟自性,才可让万物各遵循其天性挥发,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生,推行其功,以至太平天下,有天德便可语王道,通过不断切己践履,培养回复自性,终达天人合一的成德之道,正因“道”无时无刻不在,所以“修道”必须由当前日常生活切己做起,即便四下无人,更须道德自觉,力行道德视作自己内在而神圣的义务,即慎独达德的真正精髓在此,达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境界。
三、结语
总结《中庸切己录》阐发思想内涵有三:其一,天道率性。天地万物有其循常不变的道理,此道出自于天,遵守天道率性而行,体现知性于日常生活中,而生命率性、知性的过程,展现“至诚尽性”,实践至善本性,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二,切己工夫。实践“诚”可由“仁”“义”“礼”“智”各个面向的体现,由人道的道德实践,反映天道的真诚本性,透过存养到扩充,反省至实行的切己功夫,才可达“智、仁、勇”的道德实践,而人性有许多私心惰性,故袪除私欲惰性、体察切己实践的工夫显得格外重要。其三,慎独达德。要求人须“慎独”,慎独包含省察和存养,遵循天道赋予的纯然本性,扩充此善心良知,提升高尚的人格与博大的胸怀,体现中庸思想之道的内涵,即可达到“无声无臭”成圣达德的终极目标。自从孔、孟子以来,直至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之后,世风逐渐衰微已持续漫长的时间,谢文洊生于数百年之后,正处明末清初学术复杂的过渡时期,谢文洊《中庸切己录》内容主张将程朱的理学观点与儒家的修养方法融合,使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得以实践传承,后人称其为清代江西理学正宗,俨然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