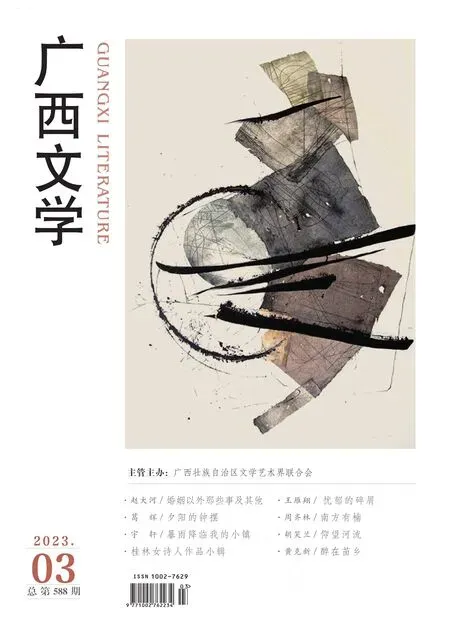诗歌圆桌
主持人语
谈论广西诗歌,桂林是一座无法轻易绕开的重镇,无须过多罗列理由,仅举一例即可见一斑——新千年以来,广西有五个诗人入选《诗刊》青春诗会,桂林市就占了三个。而这三个诗人中,女诗人占了两个(黄芳、王冬),这为桂林女诗人此次能够在《广西文学》集中展示奠定了作品基础。
参与此次展示的,是桂林市创作活跃的部分女诗人代表,她们当中有黄芳、唐女这样具有二三十年诗龄的实力诗人,也有诗一、劳明萍这样在语言感觉上颇具新意的新人,还有王冬、许桂林这样在近几年创作发表势头可观的新锐,以及像蒋淑玉、韦香媛、玉兔莎这样一直坚持创作,但较少为诗界所知的隐逸者。而作为组稿人,我尤为惊喜的是收到了刘永娟的诗歌。在广西作家中,刘永娟以小说和散文见长,诗歌只是偶尔为之,但这些作品从容而纯正,令人刮目相看。
由此深感《广西文学》开辟“女诗人小辑”的重要意义。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广西文学》第三次推出本土女诗人小辑,地方诗人作品小辑和广西诗歌双年展等策划的陆续推出,于广西诗歌的整体发展和诗人的个体写作都有大幅推动——如果没有省刊一次又一次的助推,可能我们会错过身边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可能我们会继续沉浸在自我的小圈子中,守着一方窄地自得其乐,而不知远方的同行们早已展翅高飞。
——刘 春
春台诗话
刘 频
她们的诗歌向生活敞开,亦是生活向诗歌敞开
在诗歌写作和阅读经验里,我特别看重诗歌里人文关怀的深刻背景和超越性的审美创造。十位桂林女诗人的近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诗歌的期待,她们的诗歌向生活敞开,亦是生活向诗歌敞开。
在这里,命运和人性是关键词。在人性的裂缝里,诗歌涌出命运的凛冽和光亮。黄芳无疑是很出色的,作品有四两拨千斤的把控能力,时代中司空见惯的命运和忧伤,被处理得隐忍、节制、低回,这不仅得益于技术的娴熟,更重要的是心灵能入能出,始终给诗歌留出一个通道。刘永娟从日常农事和凡俗亲情中,看到了命运在温情中不易察觉的锋刃,以纯良的心灵缓释了生命的残酷。无独有偶,唐女善于从普通事物中发现人生的本相,将理想主义与灰色现实的割裂、人生的冷峻与灵魂的慰藉交融一体。蒋淑玉的作品设置一种命运寓言的氛围,有灵魂的戕害和被戕害之后的思索,更多的是走出命运隐喻后的人生淡然、豁达。韦香媛、许桂林的作品潜溢出悲悯与哀伤,一种人生的隐痛向空茫岁月延伸而找不到伤口。王冬极有耐心地分享她的童年生活经验,从文字返回与当下浮世迥异的简朴、宁馨的诗意生活。劳明萍的诗歌是基于现代意义的爱的探寻,在被遮蔽的精神世界的幽秘通道里举着孤独的烛光。诗一的口语诗,以个人化的方式对世界进行修剪、砍削,体现出执拗的解构、反叛意识;玉兔莎的作品,则试图在传统文化的疏离与融入的两难中获得一种新的平衡,两人的文本都呈现出诗歌的现代性价值。
迈向宏阔天地
石才夫
诗“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更能反映诗人的情怀和境界
桂林这个地方,就应该出诗人,尤其是女诗人。桂林果然有一批优秀的女诗人。这是读完这期“小辑”后,我的第一个感想。
文无定法,诗更如此。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十个。几十首诗,显然不能代表十位作者的全部,只能是某时某刻,她们恰好写下这些,或者选中这些。整体上看,内容是充实的,技巧是娴熟的,风格和个性也是鲜明的。
她们当中,黄芳和唐女,是比较成熟的两位。黄芳出过作品集,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了。唐女写诗数量不多,但质量不低。她给人的印象还是小说、散文比较多些。其他的作者,大部分很年轻,堪称新锐。
黄芳这几首,写了“你”“她”“他”和“一场大火”。一段情感、一个场面、一个人去世、一场远处的山火,日常而普通。她一如既往地在这些日常里表达关爱、温暖和决绝。唐女《水凼里的天空》和《狗娃花》,第一首让我想到刚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地上的天空》,都是在倒影和镜像里,追问某种终极意义。她写的都不是大题材,但描述的对象,总能让人过目难忘。
诗一的作品如同她的名字,简单利索,绝不拖泥带水。文字干净,指向明确,“无招胜有招”。王冬写了两种童年小吃,她写得耐心但不拖沓,仿佛童年的绿皮火车,缓慢却有固定的节奏,咣当咣当,抵达每一个站点。她的腔调是独特的。
其他诸位,亦各有特点。刘永娟“关心身边的小事”,蒋淑玉在伤害和忽略中反思,劳明萍沉迷“虚无”,韦香媛关注生命和苦难,许桂林传达个体命运浮沉,玉兔莎追求古典韵味。她们共同营造了桂林女诗人杜鹃花一般的绚烂风华。
最后想说一点,诗“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什么”更能反映诗人的情怀和境界。尤其是相对成熟的诗人,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要求,比如黄芳,她不能一直在相似的情境里逗留、徘徊,更不能止步,她需要迈向更宏阔的天地。
如果把她们的作品比作人
大 雁
桂林女诗人的作品,各有态度又人性十足,很好地切片了自我的心灵
桂林女诗人的作品,各有态度又人性十足,很好地切片了自我的心灵。
黄芳的诗,特点是命运追问和痛感呈现,命运线上她会三两笔牵出一个共通性好的故事,然后去抓取人的行为细节深入绘写,以高压痛感引导读者“悟”,使弱者真正成为自尊的人。其诗整体质感犹如严厉、独立又温厚的母亲。
刘永娟的诗歌多为亲情题材,表达得放松自如,生活现场感十足,甚至有了消解性,消解了生活的苦涩,以生动和趣味做调和,有跳脱的豁达。整体质感像个懂事心细的孩子。
蒋淑玉的诗擅长以开朗、知性、辩证的视角来观照情感关系。质感像是一个亲和力强的老师。
劳明萍的诗有经典的异化感,语言力度、意象密度都大,属于哲思化表达的耐读作品。质感犹如忏悔自身也替众生忏悔的布道者。
诗一坚持口语表达,诗歌的反思性突出,也不乏具有直接冲击力的喻体设置。质感像会议或课堂上突然发难的诘问者。
唐女的诗具有丰富的画面感和奇异的想象力,意象之间的串联、照应能力好,是变形日常事物的好手。质感如同一个熟练而又能随性发挥的魔术师。
王冬的诗有小说或散文的质地,靠细节描绘突出人对旧物、时空的情感,非诗性但有可取之处。整体质感像一位认真、动作细慢的木匠。
韦香媛的诗没有老道诗人对文本的约束感,表达似乎有些随性,但又含着可咀嚼的日常性和突然一击的力度。质感像个漫不经心又机敏的猎人。
许桂林的诗,切片小、角度妙,是以巧力撬动绵长之思的作品。质感像利索又轻盈的采茶人。
玉兔莎的作品,交杂着意象作品的奇异和当下智性表达的灵气,同时具有浸入和看透感。质感似一个同时练习哭笑的演员。
从个人角度,我对她们的作品有如下期待:黄芳削减人物弱势预设,增加作品的亮度和妙趣;刘永娟拓展亲情之外的题材,在表达厚度和精辟度上加强;蒋淑玉减少铺垫性、新意不足的喻体,快速刺入内核并拓展其指向宽度;劳明萍的意象再日常化一些,表达节奏的变化再多些、松弛些;诗一寻找多层次的意和思置入口语,避免单一性;唐女的形和意的结合去向虚实相间,弥漫性再好一些;王冬的对象解剖能刹住,能跳跃,概括性再增强些;韦香媛的铺垫再精辟利落些,整诗的均匀度再好些;许桂林的文本宽度再拓展些,细节再饱满些;玉兔莎的意象新颖度再加强些,个人生活细节再突出些。
总的来说,桂林女诗人的作品,能加强的是精辟的日常发现和穿透了技巧的自在性,枝条清晰、韵味无穷、厚而不老是她们仍需要进一步做好的,这样的作品就不只是心灵切片,而是笼罩所有受困、疑惑的心灵。
于日常细部凝视生活的“灰色调”
陈爱中
女性诗人梳理出了另一种凡俗众生相,逼真、形象而又真实
在自我身体呈现和性别隐秘的诉说中,女性诗人轰毁了性别大词或者社会圣词的天宇,回到大地,在及物的鲜活肉体气息和不断重述的日常景象中,女性诗人梳理出了另一种凡俗众生相,逼真、形象而又真实。来自现实和想象的压抑气息,广场气息和恢宏主题相对远离女性诗人的创作,性别生活的场域决定了对日常细节的凝视成为女诗人反复冲杀之后的开阔地,种下诗歌的“淮山药”,关注日常生活的灰色调,深深地扎根到日常生活的深层,生老病死,洞见细节诗意的锐利,这是这辑桂林女诗人较为鲜明的特质。黄芳依然善于让记忆复活,以禅意的心态写熟悉人的死亡,写足危及生命的“大火”,不疾不徐,在琐碎细节的描摹中让对人世的悲悯不停映现,在“剥洋葱”中摩挲生活的震荡不安,描画其中的隐忧。王冬让童年以纪录片的方式映现在“血豆腐”和“酸辣子”中,简洁、素朴而浸染亲情的吃食让略显寒碜的记忆有了温暖的样子。刘永娟以蜻蜓点水的意象结构关联起生活中的抽象哲理,关注日常边角的疼痛,韭菜的伤口,父亲母亲买药、沏茶等“小事”,一粒纽扣或者一个轮子的缺失泛起的思想波纹,于忧伤中荡漾起豁达的生命之思,“要学会拥抱所有的悲伤、痛苦,直至,死亡”。蒋淑玉用“桃花剑”和“石榴”讲述生命中得与失的辩证伦理,吞噬与反噬的对立统一,诗人似乎已经洞彻生活的某一种真实,互文性的原罪意识。劳明萍则在“无意义”的叙述中寻找自然生命的顺意,以反弹琵琶的技法强调存在的正向价值,写夜晚的归乡,在想象中寻找“漂泊的灵魂”,在词语的“灰色调”中凸显自我的倔强。执意要修剪树枝的诗一,从被修剪得“光秃秃的树干”上“便完成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在情爱忧伤的夜晚,以极致的笔调书写“我的书里有只鸟/它一页一页地飞/后来它就死在了书里”这样孤寂的境界。许桂林则用淡然而简洁的语言叙述人间至为悲恸的身边人,无论是寄托父亲对母亲哀思的黄叶还是自己资助的没有名字,失去丈夫的大凉山女人,她都能从容不迫地娓娓道来,如此的不幸多少令人瞠目结舌但又是如此寻常。唐女的处理显得很老练,她写被水凼里逮住的天空,以先抑后扬的方式处理逆境,“不知道黑暗的牛肚子里会不会因此拥有一片铺满霞光的天空”,想象力丰沛,语言聚焦能力强。相比较来说,韦香媛、玉兔莎的诗语言尤擅抒情,两者诗风相近,叙述格调缓慢而悠长,意象的选择偏传统情指,有落霞孤鹜的意境。
情感,生活,与事物的秘密
非 亚
有几个关键词大致可以解析她们作品的特质,这就是情感、生活、与事物的秘密
本期十位桂林女诗人的诗歌通读下来,有几个关键词大致可以解析她们作品的特质,这就是情感、生活与事物的秘密。
黄芳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女诗人,其作品在近年已日趋成熟。和以往一样,黄芳仍然是从自己的情感出发,将情感与生活之间的关卡打通,其诗歌大都呈现出一种深度、大气与厚度。比如《东去吧,像流水一样》和《他走了》,无论是对岁月的流逝,还是对逝者的缅怀和追忆,都能将细腻、饱满的情感编织于长长短短的诗行之中,在情感的克制和诗句的推进中,寻找着一个冲出阀门的缺口。《剥洋葱》和《大火》来自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观察,无论是剥洋葱的具体与细腻,还是《大火》中对现实的直觉与发现,都体现了黄芳诗歌写作中超越生活和挖掘事物秘密的能力。
劳明萍和蒋淑玉与黄芳类似,也是从日常生活和情感的展开入手,情感锚定于某个具体的事物,以想象的不断展开代替事物的行走,在逐步深入的挖掘中,最终呈现诗人想要表达的诗眼。蒋淑玉在《祭奠一个石榴》和《桃花剑》最后的几句——“这是个通俗而深奥的问题/正比如,有时候别人辜负了你/有时候,你又辜负了别人”,以及“那把剑已锈迹斑斑,它成了一个道具/不再伤害自己,也不再指向别人”,既呈现了诗人对事物的关注,又体现了诗人的深度思辨。相比之下,劳明萍的诗歌更为开放,她不锚定具体的事物,但诗写却和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场景的跳跃与内外观照的思考不断串联成风格飘逸、想象力奇异的诗句。年轻的劳明萍如果能将飘逸的诗句更为紧密地和具体细致的生活和事物绑定,将更有助于其作品质感的提升。
王冬、韦香媛、唐女的诗歌,同样更为具体地表现各自所熟悉的生活。这一类诗歌要写好,确实有赖于诗人对生活的发现。唐女和蒋淑玉一样,将诗歌锚定于特定的事物,并展开自己的想象,“不知道黑暗的牛肚子里会不会因此/拥有一片铺满霞光的天空/那颗沉重的头颅会不会因此/抬起来,看一眼天地交接的地方”。王冬将书写的题材集中在与日常生活关联的食材之上,在层层推进中展开自己的书写和想象。韦香媛则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诗歌,延伸向自己熟悉的生活,从身边琐碎的小事发现平凡生活之美与刻骨铭心的痛楚。
刘永娟和许桂林的作品更偏向于事物、亲情和具体人物的呈现,题材虽然不新鲜,但努力让情感饱满、浓烈,依然是她们写作的第一原则。刘永娟的诗歌有一种复杂的质地,在开放的结构和对日常事物的呈现中,难能可贵地呈现她对生活的挖掘和思考。比如《等待》中的“它们等待着尖刀划出浆液/它们等待重生,已经太久”,以及《一个灰色念头包裹着我》的哲学思辨——“死神肯定会先钻进一个人的身体/那么留下的另外一个人怎么办?”都体现出她诗歌的复杂底色。许桂林则以冷静的白描,不动声色地呈现她笔下的人物,这样冷静与克制的呈现,也正是其诗歌写作的秘密所在。
另外两个新人,诗一偏向于口语与诗歌形式的干净,其诗歌更喜欢突出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意义的阐释。这一类口语诗歌要引发惊奇,想象力、张力和爆发力无疑是最重要的。此外,语言作为一种方式和形式,更需要诗人不断地打磨与修炼。而玉兔莎的诗,我第一次读到,其诗有其独到的发现。作为新人,她需要做的,是不断将心灵贴近事物,贴近自己的生活,在具体细致、真实的书写中,展开自己想象力的飞翔。
凝视现实的诸多面相
唐 允
她们无意纠缠于风花雪月,而是逼近现实,叩击内心,且有各不相同的呈现向度与诗写个性
作为桂北重镇,桂林以明丽山水驰名天下,我原以为桂林女诗人的作品,会有诸多笔墨落于此处,读下来,发现她们无意纠缠于风花雪月,而是逼近现实,叩击内心,且有各不相同的呈现向度与诗写个性。
黄芳的抒情追问性灵,审视个人处境与命运,切入尘世的荒芜、压抑和卑微。因为直视根源,她的诗句朴素、直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刘永娟立足生活,凝视其中的痛苦和秘密,隐忍而耐心。其句式舒展,气息稳健,走在通往透彻和广阔视域的途中。蒋淑玉写物,反观内心的嬗变与醒悟,从平凡的细节发现日常的牺牲,自有其深意。劳明萍在意象的联想和辨析中,让形而上的思考进入具体,成为感受。她的诗取意颇高,落点扎实,诗意从繁复中穿透至眼前。诗一直觉式的呈现,有敏锐的思考和痛感,给人鲜明的印象。唐女用充满勇气的视角演绎生死,奇特、真诚,有深沉的感染力。王冬回忆制作食物的诸多细节,朴素亲切中透出生活的质感。韦香媛着力描绘女性形象,传递对生活、生命的思考和容纳。许桂林的诗克制,把情感和现象放回原处,反而获得明晰的呈现。玉兔莎从想象摄取人世印象,却未失去个人温度。
她们的诗大多有物有据有心,“写什么”的问题,在她们那里各有回应,且多摆脱了陈旧主题表达和情绪惯性的牵扯,具有相对自主的视角和建构。这让我相信,诗歌于个人而言,首先是倾诉自我与事物、世界的联系,这联系首先是热爱,然后是因热爱而起的所有。怀抱着热爱,诗人们会走向哪里,能走到哪里?谁都无法得知答案。但知道同一片大地上有人各自孤单前行,是一种默默的呼应,是种慰藉。
领悟生命的具体与抽象
陈振波
桂林诗人……善于从生命的具体物像切入,由表及里,逐渐升华,形成抽象的诗意想象空间
我们生活在具体的世界之中,同时存在于抽象的思维里。具体与抽象,作为生命的两种模式,相互转化,彼此相融。由具体而抽象,关乎一种哲学意识,也体现着一种诗性智慧。桂林诗人基于其地域与环境、阅读与互鉴,乃至共同的女性心智,善于从生命的具体物像切入,由表及里,逐渐升华,形成抽象的诗意想象空间。
黄芳成名较早,持续创作且成绩不俗,善于从日常生活中的人、事、物中提取诗意,勘测生死、命运,或存在的某种命定的悲剧性状态。《剥洋葱》一诗即是此类诗歌中的精品,该诗从剥洋葱这个日常生活的场景入手,随之因傍晚乃至黑夜降临,引发出某种感悟:“想到生活中努力抱团的一个个日子/一颗颗被包裹庇护的心/打散往往就在一瞬间,往往/不费力气。”此情此景,因剥洋葱引发的泪眼婆娑,形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思虑及其应对。
刘永娟则试图借助诗歌,把某种经历,如路过狮子山所产生的言语冲动一一释放:“我要学会在数不清的疼痛中说话,用精确的语词/我要学会以同样的感情拥有所有的田野、山脉;所有的玉米、黄豆、红薯藤/我要学会拥抱所有的悲伤、痛苦,直至,死亡。”这几乎是她内心宇宙的显现,或许,“还有无数数不清的宇宙。”
蒋淑玉和王冬的诗极具画面感,蒋淑玉《桃花剑》一如电影的情节,描摹记忆深处的某种追悔与感伤。王冬《酸辣子》《血豆腐》皆是具象描绘,透露着生活的记忆和感悟。
劳明萍《榃美冲》一诗,为孤独寻找栖所,也是为生命寻找栖息地。榃美冲拥有无限可能,放飞想象的翅膀,安抚内心,让灵魂舞蹈,在孤寂中流露愉悦,使人感受到某种不可言传的温暖。
诗一和玉兔莎的文字带着某种寓言性,简单明了,却蕴含深意。诗一《标本》一诗,短短三行,形象生动,充满想象。玉兔莎《听雨》一诗流露出某种禅悟,回味无穷。
唐女是写作的多面手,诗、散文、小说,各体皆擅,且具较高水准。《水凼里的天空》以小见大,通过小水凼倒映着天空,被各种外物搅扰,乃至被水牛吸入腹中的历程,在相互的观照中,凸显某种形上诗意,简直是一花一世界的美学构造。
韦香媛和许桂林善于勾勒人物及其命运。韦香媛《春雨,终于落下》《子鼠之春》既是对他人的描画,同时也以他人存在形成对自我的观照。许桂林《阿珍》一诗,通过对主人公的速写式勾画,寥寥数笔,映现芸芸众生。
总体而言,桂林诗人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具体物象入手,通过特有的诗性感悟和想象联结,形成抽象诗思,或感悟人生与命运,或透露禅机与顿悟,为当代诗歌写作注入了鲜活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