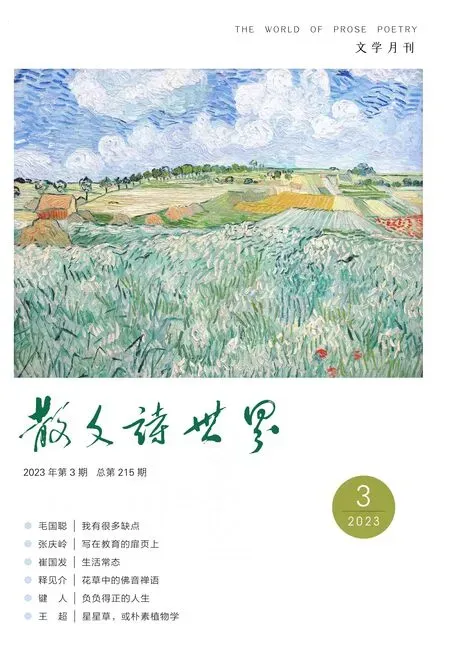光雾山,允许想象泛滥三章
刘景智(四川)
北纬,三十二度
北纬,三十二度,中国米仓山南麓。
五十万亩云雾,五十万亩阳光,五十万亩雄性的山。
即使捅破亿万年前的心事,北来的风也无法将其全部翻阅。
光雾山,已在最美丽的词语中就座。无法复制的时光:从不怀疑秋天的疆土和骏马,从不无视群山的神奇和伟大。
一万次离去,又一万次返回。栈道戳穿时间的诅咒,便与秋风伴行南北。溪水漂洗了最初的语言,却无法收紧蝴蝶和蜜蜂的翅膀
谁操纵了山月的圆与缺,云雾骏马般的征程?谁撕裂久积的压抑,替代无数次追寻、无数次叙述?谁的鼓点敲开神门洞的心扉?谁的眼眸被小巫峡的神女点亮?谁人仗剑煮酒,一去无回还,只留蜂蜜香?谁高举红旗,在冰雪中射出真理的子弹?
雾和云演绎着遍布的历史、奇观、奥秘、脚踪、幽密和时间。博大的红叶时代,就是光芒万丈的千万个太阳。
走笔光雾山,来一次雄性的荷尔蒙的挥发,古典的斜阳成全了虚掩的年轮和高昂的头颅。而蓦然回首的女子,热烈、华丽、丰富,敞胸露怀的气韵暗含了无法说出的期待。
我寻找自己的山川河流,却忌惮于云雾把卑微的念想带回另一个世界。只想微微闭上眼睛,让最初的回音渐渐地悬浮起来。
然后,看见五彩斑斓,不死的存在。
云雾之光
是为雾,是为云。
光雾山,亿万年出发的露水,停留在这里。
白色的雾,抱着昨夜的星辰,或是就要发芽的种子,沿着山脊向上爬行,像是缥缈的梦,流浪的梦,不舍怀抱的梦。
不管天空的屋檐有多高,雾总是要努力成为结伴太阳的云。
雾是云的根,山是云的父亲。云雾搬弄着是非,便是光雾山的风景;阳光裹着云雾,便是众山的云裳雾纱了。
雾里说话是漂浮的,云端飞翔是有风的。敞开又关闭,或是一瞬间,阳光就会把遗落的幸福提拎到眼前。
即使云雾是灰色的,也很纯净。
那么,云雾之痕,是谁的足迹?
高悬于群山之巅的,云雾之上的,是不朽的太阳啊。
大起大落、龙蛇狂草,雾海云帆替代了一万次泪流,一万次呼唤,都不曾搁浅远行的意念。待云鬓撒落,便是金辇浩浩。云雾破坏了所有足迹的方位,却又把所有的壮丽还给了阳光。
雨说下就下,是云的自由,太阳说走就走,是天空的诗意。
思念有鳍,只在云雾之光里。
没有天上地下。
光雾山,允许想象泛滥
想象是什么?
是比喻,是形容,是漫无边际的遐想?
在光雾山,似乎什么都不是,又似乎什么都是。
那么,天空的路怎么走,大地的路怎么走?我一直没问清楚。
指点迷津的时间太多了。站上香炉山或者燕子岩,分不清天际和地平线,不知哪是尽头哪是遥远。光和雾的海洋上,年轻的虚幻和梦想,像一匹奔驰的骏马,鬃毛飞扬地溅起无数浪花;又像一叶张开的云帆,始终志向远方的彼岸。
感谢太阳赠予秦蜀大地享用的箴言。一条穿过北纬三十二度的长路,早已将流血流汗的正确方式刻印在了山崖上。即便荒草掩埋风雨剥蚀,也能应和千里瞩望,万亩虔诚。
群山也是天空的孩子。秋风踩乱了一窝甜蜜羞涩的笑,笑声的背后沾满露珠。我双手接满忧伤,一尾木叶鱼儿再度从心底游窜。
发炎的关节只接收阳光,但我仍要学习怎样把红叶移植到胸中,或者为自己添置一枚心形的书签。低微地活着,也有高挂心里的明灯。
扶正山水的意志,伸出去的手掌就拥有了握紧梦想的力量。踩着光和雾去散步,我就内心安详,想着自己是幸福的。
但不要被好口感诱惑,蜂蜜酒烧下喉咙,燃着的是天堂醉语。
醉了,心就有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