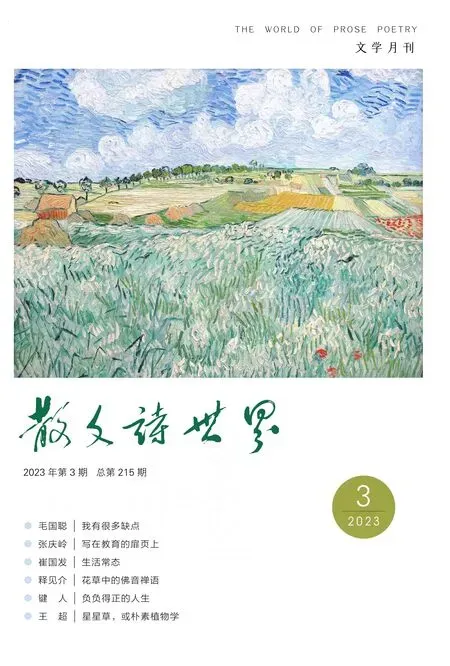浩特
2023-04-15 17:12:36许淇
散文诗世界 2023年3期
许 淇
月牙形的沙丘下面,尚月光明朗,能听到马嘶驼鸣。
据说,很久以前,一支马帮驼队遭遇沙尘暴不见了踪影。
时光流沙一样游走。我们父辈栽种的串地杨、加拿大杨、大叶榆、青榆和黄榆,围绕着我们的沙巴拉浩特(地名)。在小树林里,瞬息的雨,将绿草寸长的绒毛湿透,满身水珠,挂着无数小铃铛、小灯笼。我们的驼队,经沙地长时间烤灼之后回到绿荫的宿营地,小公驼的眼仁点亮了蒙着雾气的暮春的欲念。篝火的青烟刺激它们的胃囊。
它们呼吸急促起来,涎水像反刍的呕吐物,需要一种爱抚的挤压,喷涌彻骨的痛苦或者无比的快乐。
树林尽头的沙丘,吞噬刚升上来的月亮。月亮为什么怪模怪样?又听到马嘶驼鸣了吗?
蓝紫色的马蹄花香得令人昏厥。
用柳芭、沙篙、黄泥糊成的“崩崩房”里,你用奶瓶喂黑羔了,那粉嫩的小嘴巴啃着你的袍沿儿。
月光照着浩特附近的沙湖。湖边的沙蒿丛里,有羽毛花褐色的沙斑鸭在睡梦中呓语。
喂过羊羔以后,你到湖畔放骆驼,额古(蒙语:阿妈),你一面捻线锤,一面旋转着日子。
多年以后,我们也将成为这黑塔拉大沙丘底下的一缕午夜的呜咽。
猜你喜欢
连云港文学(2023年4期)2023-12-11 01:02:57
艺术大观(2023年24期)2023-09-19 12:18:16
少年博览·小学低年级(2022年9期)2022-05-30 16:10:56
作文小学中年级(2022年1期)2022-03-03 08:30:44
新世纪智能(英语备考)(2019年12期)2020-01-13 06:07:04
牡丹(2018年31期)2018-01-03 12:33:26
新高考(英语进阶)(2017年3期)2017-05-04 04:15:45
创新作文(小学版)(2016年23期)2016-12-01 05:51:00
发明与创新(2016年5期)2016-08-21 13:42:44
河南科技(2014年1期)2014-02-27 14: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