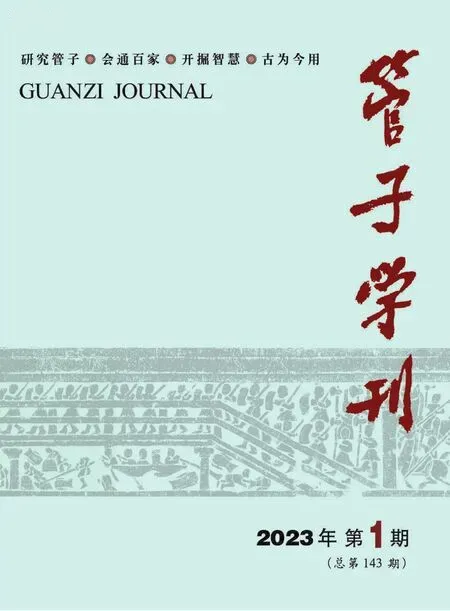论黄宗羲的“治法”思想
——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为中心
崔 罡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人类全部的政制(politeia)(1)政制不同于政治,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形式化的制度设计”,也被译为“统治形态”。参见[美]史蒂芬著,贺晴川译:《政治哲学》,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88页。既可能是善政,也可能是恶政,究竟是善是恶,取决于其是否合“法”(2)这个重要区分最早见于希罗多德《历史》,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有详细讨论。需要事先指明的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law与中国哲学中的“法”大不相同,前者大约只相当于后者中的“科条”部分。事实上,单纯的law并不一定带来良性的政治生活,因为“科条”本身即可能是恶法。具体分疏详见本文第二节。。“法治”的实质是如何处理“法”与“权力”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就是如何将统治者(无论它是个体、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私意与良序政治生活中的公共理性断然分开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法治”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资源,但历史表明,西方国家的制度与理论也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洛克在《政府论》中担忧行政权膨胀及其对立法权的侵占,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揭示了精英主义问题,蔡爱眉在《起火的世界》中讨论了立法权失控与暴民统治问题,等等(3)洛克在《政府论》中已涉及此问题,他称之为“特权”。在20世纪,比较典型地体现在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与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之间的争论。暴民制如今在许多亚非拉国家频繁出现,亦与立法权的失控有关。参见[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美]C.赖特·米尔斯著,尹宏毅、法磊译:《权力精英》,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美]蔡爱眉著,刘怀昭译:《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传统。而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文本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极具代表性的。本文认为,黄宗羲的思考从“无法”的政治乱象开始,继而进行了“原法”,即分析了“法”之为“法”的本质,并最终提出以“学校与政府良性互动”为核心的“治法”思想。
一、无法:“三权钳制”的政治乱象
黄宗羲思考的出发点是“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而导致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代以下无法”(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6页。。以“法”作为治乱的标准,与西方学者可谓不谋而合。
具体而言,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中存在着某种“三权钳制”格局,分别是君权、相权和吏权。参照孟德斯鸠式的定义方式,三者分别对应君主掌控的立法权、以宰相为首的官僚体系运作的行政权和基层胥吏把持的执法权(6)黄宗羲的框架中没有司法权,同样,洛克或孟德斯鸠的思想中也并未涉及行政系统最底层实际运作着的执法权。西方哲学通常将此问题放在政治学或行政管理等领域探讨,并未将其视为政治哲学问题,但此环节必不可少。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补充说明,能否用“三权”来勾勒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运作方式,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最广义的“法”是“天”或“天理”的发用流行,其文本载体即是“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圣人立法”“天子代天巡狩”,也可以理解为精英群体公共立法,即文彦博所说“与士大夫共天下”。但本文的意图仅在于勾勒一种“权力现象”,也就是公共生活中“如何集体行动”,那么君主、官僚和胥吏就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这个视角下讨论的“法”更切近于law,这些科条自然是非经君主宸断不得制定、非经官僚运作不得贯彻、非经胥吏执行不得落实。具体讨论见本文相关章节。。之所以将其称为“钳制”,是因为它并非有目的的政治设计,而是权力运作中博弈的结果,本质上是私意争斗的产物。由此,伴随着上层的君相之争和下层的官吏之争,天下遂成为各级蠹虫侵蚀的对象,其结果自然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君相之争的表现是,君主为实现其“保此产业”(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的目的,不断追求把立法权与行政权集于一身。一方面,“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另一方面,君主要求“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0、8页。。其结果却是“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6-7页。,最终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10)高一涵:《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2页。的官制系统。
但不容否定的是,“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于是“大权不能无所寄”(1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4、9页。。这意味着,君主必须或不得不依托官僚系统治理天下,行政权天然属于后者。君主的诉求是通过控制行政权而将自身的意志彻底现实化,但这必然会与官僚体系的意志发生冲突。反过来,官僚系统又总会不断力争把自身的意志施于君主,也就是争夺立法权。双方之间的斗争自然永无休止。如此一来,源于“君权之孳生”的相权,本身是君主控制官僚的手段,却必然而又吊诡地摇身一变,成为反抗君权的领袖。早有学者将其称为“波纹式的循环发生”现象,意即“天子个人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了政府的大臣,终于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其中又别有私臣变成实权者,再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后浪推前浪式的往复不已”(12)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55页。还应注意到的是,这是一切帝国统治的共有形态。例如,英国的财政大臣(exchequer)和首相(chancellor)同样是由国王的私人幕僚转而成为官僚领袖的。。必须清楚的是,双方真正的关注点都只是“私意”。
官吏之争涉及执法权,是另一种形态。执法权不同于司法权,根据孟德斯鸠,后者是“惩治罪行,裁决私人争执”(13)[法]孟德斯鸠著,许明龙译:《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6页。,而执法权源于行政权,是后者的具体落实,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虽然如此,它是全部社会管理系统与被管理者即民众直接发生关系的领域,也就必然成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
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把持了执法权的即是胥吏。胥吏的职能大致分为“守簿书、定期会”和“奔走服役”(1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41页。两种,前者承担文书、行政类的工作,后者办理具体的事务。后者原先由百姓临时承担,王安石变法之后,由差役改为雇役。黄宗羲认为雇役之害源自胥吏之害,其害有四:“其一,……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目为异途,羞与为伍。……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遍,况其人之贤不肖乎!……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1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43页。中国古代有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等民谚。在政治运作中,官员由科举而来,自上而下任命;胥吏却是自相授受,在本地服务。“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1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3页。由此亦可见,胥吏之害的本质在于以“吏法”代替“国法”,其目的是满足胥吏的私欲。
当然不能否认封建专制时代存在着“科条”式的“法”,但科条的制定,归根结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只是“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1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6页。的私意而已。在黄宗羲看来,“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1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如果君主拥有将天下视为私产的权利,那么同理,所有的人也可将天下视为私产。“私法”内在的逻辑冲突表明:私法非法。君相之争和官吏之争的本质都是“无法”。
如此一来,黄宗羲的主张已然呼之欲出了。既然天下必须由官僚系统来治理,那么,就必须保证行政权的独立性,在上要摆脱君权,在下要控制吏权。但这又何以可能呢?那就必须要“依法治国”。
这就涉及黄宗羲理解的“法”。
二、原法:治天下之具
黄宗羲在《题辞》中明言“条具为治大法”(1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页。,这表明《明夷待访录》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治法”,也表明《原法》方为本书核心(20)历来研究将《原君》视为《明夷待访录》的核心,相关判断参见谭嗣同《仁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名篇。钱穆先生亦以为,“《原君》、《原臣》诸篇,发明民主精义,已为近人传诵”,其他诸篇“皆与《原君》、《原臣》两篇用意相足”。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38页。。《原法》篇有“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之论(2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7页。,足见黄宗羲认为“法治”高于“人治”。之所以将《原君》置于篇首,是因为在黄宗羲看来,先秦儒家强调的“君臣之义”被遮蔽已久,必须重新申明,而君臣论正是“法治”的前提。
黄宗羲的君臣观集中体现于曾被后人多次征引的一段文字:
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2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5页。
这段话显然包含了两层意味。第一,君臣关系是以“治天下”为前提才得以可能,“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2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5页。。这是逻辑在先的。第二,在前述基础上,君为主(唱邪),臣为辅(唱许)。小儒的流俗之见以为“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2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4页。,是只见其末而不知其本的迂腐之论。
虽然黄宗羲的观点在当时属“真极大胆之创论”(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但这其实是对先秦君臣观的还原与复归。先秦儒家的君臣观是“君臣有义”(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9页。。《论语》中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的说法。“使”“事”“吏”“史”四字的字义相近,都是“治理”“治人”之义。“使”与“事”区别仅仅在于,“使”有“令”之义,有主导性;而“事”有“职”之义,有从属性。但主导和从属唯有在“事”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这首先表明,无“事”的时候,君臣关系并不存在,“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2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5页。。同时表明,在一般意义上,当完“事”之后,君臣关系应随之解体。其关系的本质是临时性合作,实现其维系的是正义原则。这才是黄宗羲通过《原君》《原臣》两篇试图展示的基本立场。
就“治天下”这件具有持续性的大事而言,君臣之义在于“公”,其目的是“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公”就是天下。“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5页。万民就是天下所有人,无论其职分为何,都在万民之列。这个区分非常关键。黄宗羲讨论了遭遇“离散子女”的民众之苦,也讨论了承受“臣妾之心”的官吏之苦,同时更讨论了“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3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的君主之苦。天下最苦的不是别人,正是君主。他们时时处于“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3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7页。的状态之中,即便如此,“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3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的下场终究不可避免,其“废然摧沮”(3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是命中注定。根本原因在于“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3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3页。,任何为“一己而立”的私法均会被天下之人无可阻挡地摧垮。“天下为主,君为客”不是立场,而是事实陈述。在这个意义上,“公”强调的是权力应由万民全体拥有(35)《明夷待访录》的定位有“民主说”和“民本说”二论。清末学者大多以黄宗羲为“民主主义”,梁启超即说黄宗羲“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大约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逐渐倾向于将其定位为“民本”或“新民本”。参见徐进:《黄宗羲的民本思想及其对限制专制君主的构想》,《文史哲》1992年第1期,第36-40页。《浙江学刊》于2005年发起了一次“黄宗羲民本思想笔谈”,参与者有沈善洪、陈来、秦晖、李存山、吴光等著名学者,“民本说”遂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参见《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的相关论文。其中的关键区别当然在于黄宗羲的思想是传统儒家式的还是近代资本主义式的。笔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不能在西方政制的框架下讨论,“民主”“民本”二说均难成立。。“公”自然就是“法”的原则,要“藏天下于天下”。天下当然应由天下人共治。要实现共治,就要有共治之法。
不过,黄宗羲所说的“法”与西方使用的law大不相同。law指的是规则,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是指明文颁布的、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条文条款。康德将其称为“体系知识”(36)[德]康德著,沈叔平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8页。。作为立法权根据的是自然法(习俗)以及更高的上帝的法条(37)[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85页。。现代契约论认为,“法”的功能在于保障“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来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38)[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59页。。立法权所立的就是这样的law,其核心功能是“防止作恶”,也就是惩罚。
但在中国传统中则不然。荀子即指责法家“尚法而无法”,因为“终日言成文典,反纟川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3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law大约只对应“文典”或黄宗羲所说的“科条”。中国哲学讨论的“法”含义极为丰富,而其本义是“模板”“模具”,引申为动词性的“模仿”“效仿”,方才有规范意义上的条文、条款之义。其功能涵摄了正义原则、人格养成、社会管理、政治运作、规训惩罚等方方面面(40)相关讨论参见崔罡:《论法的精神——荀子法思想管窥》,涂可国、刘廷善主编:《荀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版,第254-264页。。有学者正确地指出:“黄宗羲所谓的‘法’总指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并非单指今天所说的法律。”(41)张永忠:《黄宗羲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与西方相比,不仅三权分立的内容,就连构架本身乃至于作为其前提的习俗、宗教等内容都应当被纳入“法”的范围之内。
用黄宗羲的话来说,“法”指的是“治天下之具”,追求的是“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4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6页。的状态,也就是一整套天下人治天下的模式。此法要限制的是一切私意,不仅针对君主,亦针对官僚、胥吏。
那么,他的具体构想是什么呢?
三、治法:行政权与立法权的良性互动
黄宗羲条具的治天下之法的主要内容是:把立法权交给学校,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把行政权交给官僚系统,并通过去除君主、裁并胥吏、专业分工来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
(一)立法权: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在黄宗羲的构想中,学校才是重中之重。这是以往研究中未曾充分强调的(43)笔者认为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彭国翔,不过,他并未充分强调学校的“立法”地位,而是讨论学校“公议”功能的民主价值。参见彭国翔:《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求是学刊》2006年第4期,第44-49页。。他提出: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4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0页。
如前所述,“法”是“治天下之具”,而此法“出于”学校,也就是学校立法。如何能够出于学校?在于“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其公议的职能。如何能够实现公议?在于养士。如何养士?又在于公议。此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互为前提。
黄宗羲所养之士,不是宋明两朝所谓“夫士,牧民者也”(王安石语),而是全体民众。在理想状态中,学校要推行全民教育,追求“郡邑无无师之士”。上至天子,下至平民,“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45)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1-12页。。而“公议”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养士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各级学校应定期集会(太学每月一次、郡县每月二次)。集会有两件事。一则“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即切磋学问;一则“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4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2页。,即议论政事。因此,学校既有才能的培养,更有公议的熏陶。由于全民都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因此,全民都参与或曾经参与到议政之中(47)《学校》篇指出“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似乎议政的群体只是学校精英,但根据“郡邑无无师之士”“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的表述,黄宗羲诉求的是人人都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那么,议政的就是全民。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那么,如何保证学校所持的是公议?或者说,如何控制学校的立法权呢?黄宗羲提出了两条原则。
其一,学校始终是独立的民间组织。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校负责人的产生是独立的,而非由行政系统任命。“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4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1页。虽然接受“名儒提督学政”,但“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4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2页。。第二,学校负责人必须是“布衣”。“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5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1页。无论其是否曾经出仕,就任学官之时必须“谢事”。第三,学官由公议产生,也随时可能被公议罢免。“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5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1页。“稍有”一词表明其是非常严格和苛刻的设想。
其二,学校与行政系统的非对抗性。黄宗羲特别批判了书院与朝廷争权的现象,“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5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1页。。双方为了对抗而对抗,如此一来,学校表达的就不是公议而是私意了,明末党争是此种争斗的极致。而黄宗羲的理想是“未必是、未必非”,关键在“未必”二字,一切以公心为旨,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学校与行政系统的互动。一方面,学校有推举权,但考核权在吏部。意即,士子以“待诏者”的身份参与政事,途径包括了“太学之法”“郡县佐之法”和“辟召之法”等,但是,“其后选除出自吏部”,学校无权干预。另一方面,官吏全部出自学校,且其谢事后可再次返回学校,当然,返校任职需要经过“公议”的表决。
所谓人性化服务:是以网格为基础,动态掌握各类特殊重点人群的不同情况、不同需求,逐一匹配相应工作力量,逐一落实针对性的服务管理措施。将一些特殊群体如重病、特困、重点人也设置于党支部、党小组、党员的下一级相对应的网格中,掌握详细情况,对重病、特困的离退休职工进行亲情化服务,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对于重点人密切关注,必要时要特别走访,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维护离退休队伍的稳定。
与西方的“人民”(people)概念相比,黄宗羲的构想显得更有具体性。麦金太尔曾批评西方政治体制说,人民只是主权者的面具而已(53)“诉诸于人类普遍的裁决实际上就是诉诸于那些在生理与社会问题上与休谟有着相同的态度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人,前者无非是后者所戴的面具而已。”参见[美]麦金太尔(Maclntyre,A.)著,宋继杰译:《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3-294页。。洛克也曾提出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谁来判断君主或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辜负他们所受的委托?”他的答案是“人民的集体”(54)[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155、156页。。但是,“人民的集体”又在何处呢?“人民的集体”又如何且在何处成为裁决者呢?他们的代表及其执行委托的场所不正是现在已然辜负了他们的立法机关吗?于是,“如果使用强力的双方在世间缺乏公认的尊长或情况不容许诉诸世间的裁判者,这种强力正是一种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诉诸上天”(55)[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156页。。显而易见,除非有一个人民出于其中又复归于其中的组织,且其始终保持着公议的能力和活力,权力方能得到从始至终的监管。黄宗羲设想的学校就有这种意味。由于“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大狱讼”“大祭祀”都要在学校举行(5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0页。,在理想状态下,也就是一切重大的决策、仪式都在学校公议监督下开展。考虑到行政系统中的所有官吏都出于学校并可能复归于学校,他们在公议中被培养,同时必然养成在其监督下行事的习惯。学校遂成为公共意愿得以充分表达的场所。
(二)行政权:善政当自置相始
由于立法机构在理论上是人民授权的最高权力机构,对立法权的限制就必然是分权思想的重点。而在黄宗羲的构想中,学校虽有立法权,但其对政事的干预仅限于“清议”,行政权得以被完全掌控在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手中。由此产生的首要问题是,在黄宗羲的分权模式中,究竟有没有君主?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虽然《明夷待访录》多次使用了“天子”“君”等语词,但黄宗羲的基本立场是无君,或退一步说,是可以无君的。我们能够从三个层次发现这点。
首先,从君的本质来看,由于“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5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8页。,君是治天下所需的手段。因为“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的现状,要求“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5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2页。。三代之后非但是坏君,甚至就是伪君,不过是一个个“独夫”(孟子语)而已。同时,“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59)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8页。,这表明,君其实只是官,而官也是君。若“以天下为事”,君臣实乃“师友也”。君仍然在官僚系统之内。这就决定了君的地位。
其次,从君的地位来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6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8页。。黄宗羲以为“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6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8页。。这意味着,天子或者君固然是官僚系统的最高等级,但仍然在等级之内。他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更遑论什么君权神授了。这又影响到君的权力。
第三,从君的权力来看,其只拥有有限的行政权。专制时代君主的核心权力是立法权,但此权力现在由学校所有。而在朝廷议事之时,“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6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9页。。虽然天子“南面”,但在“同议可否”的过程中,参与决策的是天子、宰相、六卿和谏官,天子只有部分权力或形式上的权力。更值得玩味的是,“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天子与宰相的分工并非大事、小事,而是将“不能尽”者交付宰相。如果这里没有定性的原则,即表明,在天子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宰相和六科给事中仍然能够执行全部的行政权。
由此可见,天子实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宰相才是实质上的官僚系统首领。既然天子可有可无,皇权就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也唯有如此,方能理解黄宗羲的《方镇》《兵制》《田制》《财计》《奄宦》等方案。以方镇为例,黄宗羲以为“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征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6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22页。。这已然就是某种形态的封建。黄宗羲的封建设想,非常类似于某种邦联制。
需要补充的是,黄宗羲讨论的行政权力,不同于洛克的执行权(executive power)或孟德斯鸠所说的行政权(executive power)。从理论上来说,后两者只是执行机构,并且执行的是立法机构所立的law。但在实际运作中,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洛克用特权(prerogative)来化解实践中可能产生的困难。其一,“立法者既然不能预见并以法律规定一切有利于社会的事情,那么拥有执行权的法律执行者,在国内法没有作出规定的许多场合,便根据一般的自然法享有利用自然法为社会谋福利的权利,直至立法机关能够方便地集会来加以规定为止”(65)[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102页。,也就是行政权拥有了暂时的立法权;其二,“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66)[英]洛克(Locke,J.)著,叶启芳、瞿菊农译:《政府论》(下),第102页。,也就是行政权拥有了部分司法权。美国确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如二战时期,感受到了政府“特权”带来的好处,但这也意味着,正如美国政治现实所示,行政权的扩张不可避免。
而在黄宗羲的构想中,虽然治天下之具均出于学校,但类似于law的科条,其实是由官僚系统自身掌握的,因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置上,行政权有绝对的独立性。学校所立之法与官僚系统所制之科条不在同一个层面,因而双方不会发生冲突。
官僚系统的独立性还体现在其专业性,“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6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9-10页。。黄宗羲对官僚系统的分工当然谈不上缜密,不过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专业治理的思路。专业性的另一层保障是取士。各种绝学,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同样“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6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第19页。,也能够进入官僚系统。因此,黄宗羲的设想更类似于韦伯主义的科层制度(bureaucratic),也就是一种专业化、高度组织化的官僚行政系统。
余论
总体来看,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仍然是前现代的。特别是学校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位高权重,兼具意见领袖和学术领袖双重身份,颇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教会首脑。在现代生活中,这种取向当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如果我们抽离了黄宗羲认可的儒教意识形态,他的“治法”模式本身依然能够正常地运作。权力(power),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共同行动的能力。“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良序政治当然需要这种能力。这也就是说,权力的获得方式应当是人民的同意,同时,人民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本身也必须是“法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黄宗羲“法治”思想的基本立场在于,应当将全部的权力都置于公共意见的管控之内,从而彻底切断权力与私意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