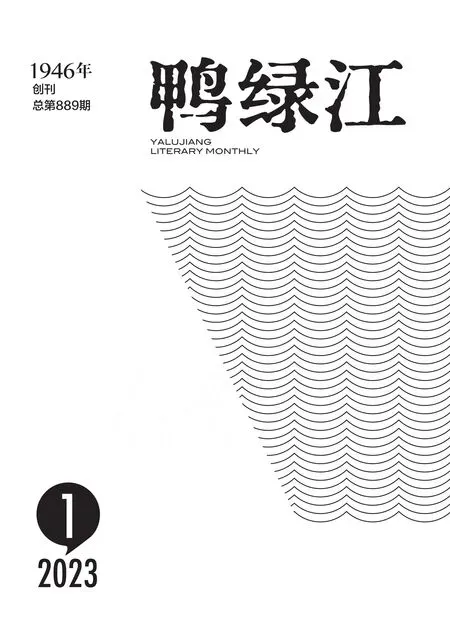付久江的故事法(评论)
牛寒婷
付久江似乎格外着迷于故事,无论是自身的际遇,还是道听途说的轶事传言,都可能成为刺激到他写作神经的开关按键。然而,键子按下后,随叙事逶迤而来的后续的一切,与故事的关系,则肯定复杂而又微妙。于是,如何剪裁和编织它们,如何稀释或浓缩它们,尤其是,如何通过文学的魔法使它们突破原生态的个别真实而演化为艺术世界的普遍真实,把故事最终发育为小说,便成了更需要他严肃面对的结构性难题。是的,故事想要成为小说,就必得经过虚构的重铸,因为“不借助虚构的冒进不可能走近认知”(迪伦马特语),而不能有效实现认知的小说,必然意义阙如,价值低微。
为了让自己拣选的故事所攀爬的阶梯能更切近地朝向美和真实,付久江不乏智性又颇具勇气地,尽量在自己与故事间,建立起一种既亲密无间又对抗疏离的复杂关系,时而与它们互诉衷肠,时而与它们抢白争辩,通过绝不轻松的一轮轮博弈,将其俘获上自己思想与艺术的战车。借助叙述的层层深入,他找到了不断逼近小说内核的方法:通过某种偶然与必然的交叉换位,促使故事不断地起飞和降落,从而编织出主人公曲里拐弯的跌宕人生。在他的《千分尺》《甜磨粥》《神牛神牛》《伙墙开门》等小说里,这种实践都很成功,他的主人公也都能合情合理地去接受那种西绪弗斯式的命运考验。可显而易见的是,付久江又隐约并且坚定地知道,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那过于流畅的情节让他自我怀疑,那过于明晰的人性让他无法满足,恐怕,要真正逼近小说内核,他就必须伺机制造“事故”以“斩断”故事。
可以想象,在所谓欧·亨利笔法的运用上,付久江曾下过功夫,他小说中戏剧性的时刻,常常发生在意外之处,这对于刺激读者的阅读情绪特别奏效:历经种种情节上的辗转腾挪翻云覆雨后,疾速奔向终点的故事在接近目标时,却敢于突然刹车乃至掉头——故事中的故事或者故事外的故事,便这样令人惊讶地面世现身了。某种意义上,不言而喻的“事故”让行进中的故事全然断裂,那断裂之处的触目惊心,犹如斑斑血迹鲜亮耀眼。小说的魂魄像个新生儿一样,在与故事的对决中脱颖而出,而故事也由此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和方向。正是在浴火重生的这一时刻,而不是在大起大落又中规中矩的起承转合中,故事才真正开始起飞,尽管之前,并不曾有预先滑行的丝毫暗示。起飞或爆裂后的故事,从此会拖曳出一条无形的断尾——它不仅包含着全部过往,还启示了未来,它既是终局也是开始。
短篇小说《千分尺》的故事并不复杂。上高一的叔叔不小心弄坏了学校的千分尺,面对家里无力承担的130元赔偿款,他选择了中断学业去打工赚钱。不承想,勇于担当的人生选择,却成了改变他命运的推手,原本学校里那个人人称羡的好苗子,居然远走他乡早早结婚生子,“沦落”为一个普通农民。在经历了一生的贫苦和磨难后,因身患癌症而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叔叔,为完成年少时的心愿,网购了一把千分尺。直到此时,那个神秘的、几乎被整篇小说一直“雪藏”着的核心道具,才呈现出呼之欲出的“撩人”姿态。读者的胃口被彻底吊起来,故事谜底即将揭晓的紧张激动和生怕真相再次溜走的小心翼翼,让小说接下来的每个字每句话,都充满了玄妙的意味。
“给你看个东西。叔叔冲我诡秘地一笑,回身打开衣柜,慢慢蹲下去,拉开下面的抽屉……盒子里,躺着个奇形怪状的小东西。我一眼就认出,那是一把千分尺。”有意思的是,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叔叔的命运因它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它的价格,却匪夷所思地还是当初的130元。在如愿以偿地完成实验,也就是用千分尺量了自己的头发丝儿后,叔叔让“我”也试一试,但“我”却像躲避瘟疫似的不想碰它。多年来,千分尺事件不仅是叔叔的噩梦,更是全家人的禁忌。可尽管如此,迫于叔叔的命令,“我”还是犹疑着伸出了手:
在叔叔的指点下,我将头发置于测砧上,小心翼翼地拧着微调旋钮,驱动着测微螺杆缓缓前行。头发夹住了,开始改用测力装置,旋转尺柄尾部的棘轮盘。随着越夹越紧,叔叔猛然喊了一声:“停!”
几乎同时,我听到棘轮发出“咔咔”的警报声……
千钧一发之际爆发的喊声和警报声停滞了时间,如同开启了一个时空隧道,径直抵达几十年前那个相同的时刻:当年,叔叔就是这样把千分尺弄坏的吗?当时他手中的尺子也发出了类似的警报声吗?面对响了或者压根儿没响警报的、坏了的千分尺,他该多么气馁和沮丧呀,也许那一瞬他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他还没操作到这一步尺子就坏了?毕竟那时的他无法像现在这样提前阅读说明书,又或者,他还压根儿没来得及操作,尺子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毛病,好似它出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他的人生……戛然而止的小说,留下的无尽疑问挥散不去,只有叔叔行家里手般的精准所复活的他身上全部的活力和激情,让人依稀看到当年那个天才少年的朦胧身影。与千分尺的再次“亲密接触”,能让他对过往的一切释然吗?那几乎绵延了整整一生的怅惘、懊悔和挫败感,能被眼前这把已不再构成难题的小小尺子给治愈吗?虽然《千分尺》讲述的故事逃不脱既定的终局,其人物也走不出残酷的命运,可这一灵光乍现般的结尾所烘托出来的主人公——也是整篇小说——的高光时刻,却以开放的姿态通向自由的飞地。在那里,梦想与现实、偶然与宿命、希冀与悔悟、欢乐与痛楚、慰藉与恐惧、丰盈与贫瘠,终将握手言和、彼此谅解。
《千分尺》里叔叔的形象,能让我想起付久江另一个短篇《神牛神牛》的主人公古克力,因为这两个人物身上,都具备那种专注型人格的醒目特质。古克力是位三轮车(被称为“神牛”)车夫,为躲避警察追赶,他的骑车技术几乎练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小说对他惊人的车速和精湛的车技的描写煞是好看,甚至还上演了一出“独轮飞车”的戏码。在付久江丝丝入扣的叙述下,一个专注、执着、颇有些天分的骑车能手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古克力以炼钢厂工人的身份,参加了一场全市瞩目的自行车比赛。让人没想到的是,原本优势明显的他关键时刻摔了一跤,结果输掉了比赛,而更加让人没想到的是,一时之间“假摔”的说法沸沸扬扬,炼钢厂那群赔了赌资的年轻人为泄愤对他穷追猛打,结果导致他坠桥死亡。故事的谜底同样在小说结尾被揭开:赛场上,就在古克力即将赶超专业对手的那一瞬间,看台上突然爆发出“神牛,加油”的呼喊之声,这导致他下意识地做出了刹车的动作。听到有人喊“神牛”立马刹车,这是所有车夫的本能和本分,毕竟,古克力不是赛车选手或者说只是看起来像个赛车选手。
天赋异禀有时是诅咒,平凡的人,大约无法承受神额外的赠予。无论是叔叔还是古克力,在他们对事与物近乎执拗与疯狂的专注里,都潜藏着厄运甚至是死神的重重阴影。当诡异的命运突然翻转,当不知所以的错愕取代专注和投入的愉悦与欢欣时,他们才突然发现,唯有苦难与荒诞,才是始终如一的世间律法。他们遵从本心的选择,毋宁说是在履行某种契约。他们必须成为神手中的牵线木偶,被从不出错的命运女神时刻照拂。人生的苦厄因而有了些许神圣和悲悯的意味,这就仿佛缺少了苦难和荒诞的衬托,那属于他们的闪耀着人性和技艺之光的美妙瞬间就无法达成。
比起姊妹篇《千分尺》和《神牛神牛》的沉重,《伙墙开门》倒像一出黑色喜剧。小丑般的男主人公与两个女性的婚恋故事,让我想起了福楼拜小说那触目的名字“情感教育”。在小说中,李有归受到两个“不同款”女人“同款”的爱的教育,或者说,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身上,李有归将殊途同归地发现爱情的同一真相。“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小说蓄意矮化李有归,塑造其不无荒诞的形象,似乎只为了给歌德这句因太过著名而被滥用了的话做出注脚。爱情是一种教育,这或许是一条尽人皆知的爱情秘密,早在2500年前,柏拉图就提出了“爱的阶梯”的理论图式:从肉体之爱到精神之爱,再到知识之爱,最后抵达爱和美本身;而爱欲不断攀升阶梯的过程,也即爱的教育的过程,是爱与被爱的个体精神成长的过程。
丧偶多年的乡村教师李有归,一直期待和自己年轻时的恋人、现在的情人林雨凌步入婚姻殿堂。借着学校搬到县城的契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在县城置备了房产,一心等着和林雨凌双宿双飞。可楼盘项目意外出事、开发商卷钱跑路的现实,不仅打碎了他的如意算盘,还让他成了无家可归之人,而买了他房子的老邻居田美兰则借机展开了对他的追求。一个是在县城当教师的文化女性,一个是村子里开超市的乡下妇人,在李有归眼中,二者有着天壤之别。可是,二者的观念,也会有别如同天壤吗?
楼盘生变,绝望的李有归告诉林雨凌,自己在县城买房是为了与她结婚,这却让后者大吃一惊:“结婚?我啥时候说过要和你结婚了?”“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都是过来人了,何苦还要往婚姻的套子里钻。傻不傻。”林雨凌一语点醒梦中人的回答,让人到中年的李有归成了个一厢情愿的花痴少年。而接下来,从青春幼稚病的迷雾中坠落到清醒大地上的李有归,虽然终究选择了与一心一意想与他共同生活的田美兰结婚,可是,田美兰却在与他温柔缱绻耳鬓厮磨之际,说出了与林雨凌的意思异曲同工的话:“咱俩活着一起过,死了还是两家人。你有朱老师,我有吴大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想了,往后你一天三顿在这边吃。住呢,还回你那边住。我这边守着超市,整天人来人往,没黑没白的,也打扰你看书休息……你想我了就过来,我想你了就过去。”
质朴中有心机和伶俐、谋算中有宽厚和周全、执拗中不乏豁达和通透的田美兰,在这一刻,俨然是一个让人另眼相看的现代女性,其独立、清醒和聪慧的一面,可与着墨不多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林雨凌媲美。通过文化的熏染或人生的阅历,她们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认知,早已完成了现代式的升级换代。林雨凌安于并享受与李有归的情人关系,而田美兰即便与后者结了婚,依然渴望保持生活的自主、人格的独立。与二人相比,李有归反倒像个现代社会里墨守成规的老夫子,只会单一地、简单化地去用婚姻挟持和定义爱情:婚姻大于爱情;爱情受制于婚姻;爱情是婚姻的附属品,婚姻是爱情的驱动力。
极具反讽意义的情感故事背后,是观念上的鲜明反差与强劲对垒。显而易见的是,人设上感情用事、心态低幼、思想保守的李有归彻底输给了与其过招的两位女性。而小说在有意无意间所凸显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文化人与下里巴人的身份界定,在此遭到一一消解,甚至出现了黑色幽默式的融合交汇。意味深长的是,小说的题眼也即田美兰与李有归家之间伙墙上被开启的那道门,看上去是一道情感关系之门,实则是一扇“情感教育”之门。正是田美兰隐藏于弱势下的强势,才让李有归的心理感受从沾沾自喜的“入侵”变成了不尴不尬的“入赘”。林雨凌没能完成的情感教育的接力棒,现在交到了田美兰手上。
阅读付久江小说时,我如同兴之所至的涂鸦孩童,在脑子里不时地勾画着他笔下那些引我入胜的人物的模样:痴迷千分尺的天才少年、擅长“独轮飞车”的古克力、不再将爱情与婚姻混为一谈的林雨凌、生活生意爱情三不误的农村现代女性田美兰……我想象中的他们的样子,也许与小说中的他们相去甚远。尽管如此,对于他们被刻画和创造的过程,甚至对于他们在故事素材里原初的样子,我依然充满好奇。为此,我特意向付久江打探了一番。结果,原本关于小说人物的“闲聊”,竟演变成了一次极为严肃的文学对话:从主人公的塑造到故事情节的编织,再到叙述手法的运用,付久江一股脑儿地倾诉了让他感到困惑困扰的各种问题。比如,对于他驾轻就熟的欧·亨利式小说结尾,对于他不断复制的某些叙事策略,对于他多数小说的线性时间发展模式,对于他调度小说时过度看重外在情节的路径依赖……他已越来越不满意。我急忙把话头岔开,因为对于一个为愉悦而阅读的读者来说,这些问题实在是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