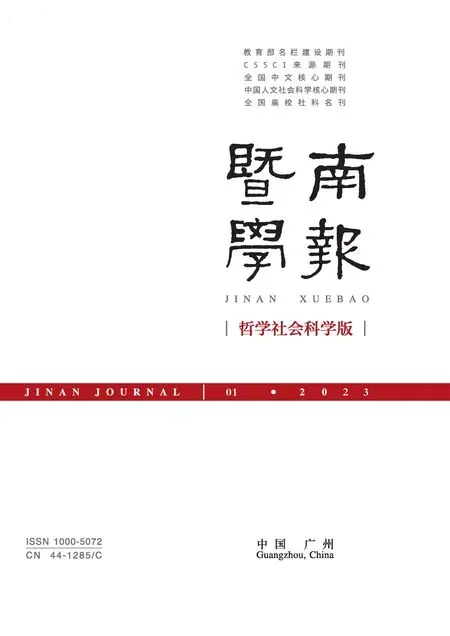基于“阅读”的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研究述论
金 琼
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创作逐渐进入一个兴盛期,大批女性小说家登上了文坛,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有玛丽亚·埃奇沃思、范妮·伯尼、简·奥斯丁、玛丽·雪莱、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三姐妹和乔治·艾略特等。她们的小说风格多样,共同构建了19世纪英国文坛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两百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已做了大量研究,似乎已无继续言说的空间。不过,也有部分学者另辟蹊径,从“阅读”角度来观照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之于小说兴起、小说批评以及小说创作的影响,取得了一些较有新意和启迪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对这些成果进行简要的梳理与述论,以期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国外有关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
(一)传记、日记与书信等披露的女性小说家阅读信息
从“阅读”入手研究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首先离不开对女性小说家阅读情况的调查与分析。这本来是一件难以措手的事。好在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传记、日记与书信的出版,或多或少地给提供了她们阅读的书目信息。在传记方面,盖斯凯尔夫人《夏洛蒂·勃朗特传》(1857)、詹姆斯·爱德华·奥斯丁《简·奥斯丁传》(1870)、约翰·休伊什《艾米莉·勃朗特传》(1969)、伊丽莎白·郎格伦《另一个安妮·勃朗特》(1989)与凯丽·麦克思威尼《乔治·艾略特的文学生活》(1991)等,均对传主的阅读经历有所揭示。以奥斯丁、勃朗特姐妹与乔治·艾略特几位作家为例,《简·奥斯丁传》中提及奥斯丁阅读过《英国史》《旁观者》《西班牙游记》《女主人公》与《滑铁卢》等书目。《夏洛蒂·勃朗特传》中提及勃朗特姐妹对司格特、约翰·洛克哈特、迈克尔·萨德勒、约翰·威尔逊、伊索等人的文学作品均有涉猎;除文学外,三姐妹的阅读范围还延伸到了绘画与政治领域,诸如文艺复兴时期基多·瑞尼、裘利奥·罗曼诺、拉斐尔等人的作品,党政报刊《利兹通讯员》、《利兹信使》与《约翰·布尔》等,这些信息皆在传记中有所披露。(1)[英]盖斯凯尔夫人著,祝庆英等译:《夏洛蒂·勃朗特传》,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0—73页。《艾米莉·勃朗特传》认为,并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艾米莉的阅读情况,只能通过勃朗特姐妹的共同阅读情况与《呼啸山庄》中表现的艺术特征推断艾米莉阅读过莎士比亚、司格特、华兹华斯与拜伦等人的作品。(2)John Hewish,Emily Bront⊇,London:Macmillan Press,1969,pp.34-36.《另一个安妮·勃朗特》特别提到安妮的阅读与姐姐的不同,她更倾向于阅读考珀、摩尔和韦斯利等诗人具有强烈宗教性质的作品。(3)Elizabeth Langland,Anne Bront⊇:The Other One,London:Macmillan Press,1989,pp.31-32.《乔治·艾略特的文学生活》则提到乔治·艾略特在早年的学习生活中已开始接触历史、科学书籍以及大量的诗歌作品,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其中又以华兹华斯对其影响最为深远,在阅读莫克森出版的六卷本华兹华斯诗集后,她情不自禁地感慨,“我从未有过如此多的感受,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4)Kerry McSweeney,George Eliot:A Literary Life,London:Macmillan Press,1991,p.10.,暗示自己的宗教观与生活观与华兹华斯的契合。
在日记书信方面,目前已有《奥利芬特夫人的自传与书信》(1861)、《乔治·艾略特书信》(1878)、《简·奥斯丁书信集》(1884)、《盖斯凯尔夫人书信》(1966)与《夏洛蒂·勃朗特书信》(1984)等出版。这些女性小说家在日记书信中往往会提及自己当时的阅读情况。《简·奥斯丁书信集》中,奥斯丁曾几次在信件里提及自己阅读弥尔顿、理查森、考珀、克拉克、司格特等人作品的感受,特别是约翰逊博士,奥斯丁热情地称其为“亲爱的约翰逊博士”,并以其作品来观照自己的创作理念:“我认为我处理的更多的是概念而不是事实。”(5)Edward Hugessen,Letters of Jane Austen Volume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328.《夏洛蒂·勃朗特书信》提到了自己阅读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盖斯凯尔夫人和哈丽特等人小说的情况,亦提及与萨克雷、出版商威廉斯、史密斯谈论小说创作、出版事宜以及阅读文学杂志等相当丰富的信息。
可以说,现已出版的英国女性作家的传记、日记、书信中提及的阅读书目信息,是学者考察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状况与知识结构的重要参考资料与可靠依据。
(二)基于“阅读”的女性小说家研究与文学史梳理
从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情况入手,自然不难揭示女性小说家所受到的文学传统的影响,沟通女性小说与此前文学史之间的关联。早在1848年,夏洛蒂就在刘易斯的推荐下阅读了奥斯丁的小说,但对奥斯丁的创作持否定态度,认为奥斯丁的小说毫无激情可言,“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惟妙惟肖的银版照相!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精心侍弄的花园,整齐的花坛镶边,娇嫩的花朵;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没有开阔的田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6)朱虹:《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1页。;而对法国女性小说家乔治·桑的创作,夏洛蒂则给予肯定。同年,伊丽莎白·里格比的评论《〈名利场〉、〈简·爱〉和女家庭教师联合会》,从《简·爱》第二版的题赠中推测夏洛蒂·勃朗特曾阅读过萨克雷的作品。(7)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其实夏洛蒂对萨克雷的阅读情况,在她写给出版商威·史·威廉斯的信件中早已提及:
你提到萨克雷和最近一期连载的《名利场》。我越读萨克雷的作品,就越发认定他是独一无二的——论智慧,论真实,论情感(他的情感虽不事宣扬,却属文学中最真挚的情感),论气势,论质朴,论节制,他都是独一无二的。萨克雷是一位泰坦天神,他那么强有力,以致他能够不动声色地完成大力神似的丰功伟绩;他的最伟大的作品里有一种泰然自若的魅力和壮丽;他从不借助于狂热,他的力不是狂乱的力——他的力是清醒的力,从容的力,深思熟虑的力。最近一期的《名利场》特别证明了这一点。(8)[英]夏洛蒂·勃朗特著,杨静远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4—145页。
由此可见,同时期作家之间的相互阅读与批评活动较为活跃。事实也证明,夏洛蒂不仅阅读过萨克雷小说,还在给其出版人乔治·史密斯以及好友艾伦·纳西的信件中多次提到其阅读萨克雷小说的体验与看法。爱弥儿·蒙泰居在1857年发行的《两世界杂志》上认为“《简·爱》和拉德克里夫夫人的小说接壤”(9)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这是最早注意到《简·爱》中哥特元素运用的评论,阐述了夏洛蒂对哥特小说的阅读和吸收。乔治·艾略特的书评《女作家写的蠢故事》(1856),既展示了她丰富的阅读经验,也涉及她对当时一众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与创作的看法。艾略特分析了女帽小说、神谕体小说、白色圣领体小说和现代仿古类小说这类流行的蠢故事小说,在她看来,“女作家写的蠢故事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浅薄空洞、迂腐卖弄”(10)[英]乔治·艾略特著,孙平华、石伟东译:《女作家写的蠢故事》,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这类小说如《补偿》《劳拉·盖伊》与《阶级与美女》等的流行,对女性创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随着一些著名女性小说家的离世,该时期的英国女性创作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困境,针对女性创作的评论也相对减少。直到20世纪,随着学界对19世纪英国女性创作的重新挖掘和深入探析,涉及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也在不断拓展与深化,而其中不少探索是与文学史的梳理与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牛津版《奥斯丁文集》的出版人查普曼在《答加洛德先生》(1929)中就提到奥斯丁十分熟悉莎士比亚与约翰逊的作品,还阅读了大量的小说、诗歌、传记、游记等。除此之外,卡尔的《游记》、亨利的《英国史》、帕雷斯上尉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军事政策和机构论文》等也是她阅读书目的一部分。(11)朱虹:《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这份材料多少揭示了奥斯丁阅读范围的广泛。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中则着重分析了奥斯丁对前人如菲尔丁、理查逊、伯尼作品的阅读,承继了他们在创作中对现实生活的强烈道德关怀,由此形成了英国文学史上一条重大的脉络——“理查逊—范尼·伯尼—简·奥斯丁”(12)[英]利维斯著,袁伟译:《伟大的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而对奥斯丁作品推崇备至的乔治·艾略特紧随其后,继承了她在创作中的道德关怀。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1992)中进一步论述了奥斯丁对理查逊、菲尔丁和伯尼作品的阅读与继承:在小说艺术上,奥斯丁继承了理查逊与菲尔丁细微入至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同时将叙述视角转移至固定角色上,展示叙述者的精神状态;在小说内容上,奥斯丁继承了理查逊对婚姻和女性地位、菲尔丁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关注,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13)[英]伊恩·P.瓦特著,高原等译:《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1—343页。正是由于奥斯丁对菲尔丁、理查逊、伯尼,艾略特对奥斯丁的阅读与接受,构建起了英国小说的“伟大的传统”。此外,文学传统的确立离不开国别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与此消彼长,奥斯丁的国际视野亦得到一定佐证。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者辛迪·康格《阅读〈情人的誓言〉:奥斯丁对英国式理性和德国式感性的反思》(1988),从奥斯丁对《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设置的戏剧《情人的誓言》的阅读出发,认为奥斯丁对当时英国文学中的亲德倾向进行了反思,将这视为对英国文学传统的暂时威胁,但最终又是检验英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手段,从演剧活动的狼狈终场到托马斯爵士的严词批判,我们不难从奥斯丁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照与历史选择,明晰其对英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认同。(14)Syndy McMillen Conger,“Reading Lovers’Vows:Jane Austen’s Reflections on English Sense and German Sensibility”,Study in Philology,Vol.85,No.1,1988,pp.92-113.众多的阅读研究,都试图将奥斯丁的小说创作纳入英国文学传统进行考察,《剑桥文学奥斯丁指南》(1997)却指出,奥斯丁的阅读和写作并没有刻意考虑英国的文学传统,她所阅读过的书籍自然地成为其小说中人物的阅读内容,并进一步成为作者理念的延伸。(15)Edward Copeland and Juliet McMast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189-190.《奥斯丁的阅读》(2015)一文就为考察文学传统之外奥斯丁的阅读提供了新的佐证,文章显示,奥斯丁阅读过考珀、克拉布、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摩尔、拜伦、伯尼、拉德克里夫夫人、伦诺克斯夫人、埃奇沃思的作品以及当时市面流行的通俗小说。除了文学类书籍之外,奥斯丁还对历史与政治领域的书籍深感兴趣,包括布坎南的《亚洲基督教研究》、克拉克森的《呼吁废除奴隶贸易》、格兰特夫人的《美国夫人回忆录》、卡尔的《西班牙游记》、巴迪莱的《意大利礼仪与习俗》等,以上论著涉及宗教、政治与地理文化等领域,其中对奥斯丁创作产生明显影响的当属克拉克森,读者显然可以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发现有关奴隶制的隐晦讨论。(16)Laura,M.Ragg,“What Jane Austen Read”,Mount Allison University,Vol.2,No.1,2015,pp.167-174.
勃朗特姐妹的研究在该时期也在不断拓展,但涉及阅读研究的成果则较为少见,也比较零散。英国作家玛丽·沃德在1900年版《呼啸山庄》导言中,从艾米莉接受文学思潮影响的角度对她的阅读做出推测:“如果没有三四十年代的德意志风格,没有《布莱克伍德杂志》和《弗雷德杂志》中的德国文学翻译作品,没有艾米莉在布鲁塞尔和回家后显然读过的霍夫曼的故事或其它德国童话,是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的。”(17)转引自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这显然是试图揭示艾米莉小说所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剑桥文学勃朗特姐妹指南》(2002)特别提到勃朗特家庭订阅的报纸《水星报》《利兹情报报》《约翰·布尔》等都是姐妹三人的重要阅读来源。利物浦大学的日裔学者小田缘《〈呼啸山庄〉与威弗利系列小说:司格特对艾米莉的影响》(2007)指出,司格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对《呼啸山庄》影响最大,如《黑侏儒》中莫雷爵士与《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有着相似的恶魔般性格;《罗伯·罗伊》与《呼啸山庄》有着相似的荒原设定;司格特笔下的艾米·罗萨特、麦格雷夫人与戴安娜·弗农等女性人物性格对《呼啸山庄》中凯瑟琳角色塑造所起的作用等。此外,艾米莉还继承了司格特在小说创作中通过采用不可靠的叙述方式,表达其对历史和政治保持中立与模糊态度之技巧,在《呼啸山庄》中引入了丁耐莉与洛克伍德两人作为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达到一种模棱共存的境界。(18)Yukari Oda,“Wuthering Heights and the Waverley Novels:Sir Walter Scott’s Influence on Emily Bront⊇”,Bront⊇ studies,Vol.32,No.1,2007,pp.216-218.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米莉亚姆·伯斯坦《夏洛蒂何时阅读〈名利场〉》(2012),认为夏洛蒂有可能在她创作《简·爱》之前就阅读过《名利场》的部分内容,至少阅读过1847年4月号报纸连载《名利场》的部分,因为两部小说在部分情节和人物对话上存在某种相似之处,而不是夏洛蒂所声称的在创作《简·爱》时并未阅读过《名利场》。(19)Mirian,E. Burstein,“When Did Charlotte Bront⊇ Read Vanity Fair”,Bront⊇ Studies,Vol.37,No.2,2012,pp.159-162.《轰动的维多利亚时代:玛丽·伊丽莎白·布莱顿的生活与小说》(1979)一书突破了前人仅仅专注于著名女性小说家研究的局限,注意到维多利亚时代通俗小说作家玛丽·伊丽莎白·布莱顿的《死海果实》对巴尔扎克的借鉴,《一个医生的妻子》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改编。(20)参见Robert Lee Wolff,Sensational Victorian:The Life and Fiction of Mary Elizabeth Braddon,NewYork:Garland Publishing,1979,p.141.由此可知,对前辈或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之阅读,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小说家本人的创作。
进入20世纪后,学界对乔治·艾略特的关注较维多利亚时代有所下降,对她的阅读研究,除了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将其纳入英国小说发展脉络中考察外,《剑桥文学乔治·艾略特指南》(2001)开创性地认为,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的“道德现实主义”手法是“华兹华斯式”的,即在真实平凡的叙事中表现人物情感的丰富性。(21)George Levine,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George Elio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7.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女性主义研究者不再关注个别女性作家的阅读情况,而是更加留意整个女性作家群体的阅读,她们希冀凭此重建失落的女性文学史。伍尔夫在《女性与小说》(1929)中首次提及性别因素对女性小说家阅读与创作的影响。伍尔夫从女性阅读经验出发,强调了19世纪一批女性小说家对前辈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与接受:“如果没有那些先驱者,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作。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孤立地产生的,它们是人们多年共同思索的产物,是群体思维的产物,因此在个人声音的背后,是群体的经验。简·奥斯丁应该给范尼·伯尼的坟墓献上一个花圈,乔治·艾略特应该向伊丽莎白·卡特强有力的荫庇表示敬意。”(22)[英]维吉尼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2012)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强调在英国女性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女性小说家除了阅读男性批评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外,还习惯阅读女性前辈与同辈的作品,并从中获取女性经验。肖瓦尔特认为评论家们对于女性文学的传统进行了两极化处理,使之成为可称作奥斯丁与乔治·桑的两个支系,非此即彼地把她俩之后的女作家分别看做简或者乔治的女儿们。前者沉静,更加注重道德言说,后者激情,更富女性叛逆色彩,而两人的继承者分别是乔治·艾略特与夏洛蒂。围绕着这两支传统,在女性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不少追随者,在小说情节、人物设置上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肖瓦尔特不无揶揄地说“当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对她们所处的时期越来越起决定性的影响,并越来越代表用以衡量其他女小说家的范型时,她们也就成了女性奉承和怨恨的对象了”(23)[美]伊莱恩·肖瓦尔特著,韩敏中译:《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肖瓦尔特就以林顿夫人与奥利芬特夫人的经历为例,前者认定自己被出版社拒绝的小说不比《简·爱》与《亚当·比德》差,而后者在创作小说时要避免与乔治·艾略特的选题接近,因为她的《塞勒姆小教堂》就曾因与《亚当·比德》内容相近而常被拿来进行比较。这种现象就为考察19世纪英国的女性阅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观察视角。
(三)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之于其创作的影响研究
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在创作时,往往会受到先前阅读经历的影响,这些会在风格、题材、人物、情节的选择与安排上显示出来。
奥斯丁的阅读对于其创作方式的影响研究,集中在小说的风格、情节与主题上。利维斯夫人所著《〈傲慢与偏见〉:简·奥斯丁早年的读书与写作》(1942),从奥斯丁早年作品判定她明显受到了哥特小说和范尼·伯尼小说的影响,既借鉴其小说结构,也对其思想情感、语言艺术进行讽刺与改写。(24)朱虹:《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简·奥斯丁的小说》(1963)一书中同样提到奥斯丁对伯尼作品的接受与改造,在结构和主题上,《傲慢与偏见》与《理智与情感》类似,都是对伯尼式传统写法的模仿和改进,伊丽莎白·班内特的塑造是为了超越西西莉亚。(25)Robert Liddel,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London:Longmans,1963,p.20.奥斯丁小说的校订者索瑟姆《简·奥斯丁的文学手稿》(1964)也通过对奥斯丁早期作品《少年习作》《爱情与友谊》与《英格兰史》的研究,指出她对当时感伤流行小说的戏拟(26)转引自龚龑、黄梅:《奥斯丁学术史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6页。。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员罗伯特·福普《简·奥斯丁与女性阅读》(1987)将奥斯丁在小说中的女性阅读情节设置归结为托马斯·吉恩伯斯《对女性职责的调查》中提出的女性每天都需要分配一部分时间进行阅读的行为准则的影响,但奥斯丁显然反对吉恩伯斯认为女性不应该阅读小说的观点。(27)Robert,W.Uphaus,“Jane Austen and Female Reading”,Study in the Novel,Vol.19,No.3,1987,pp.334-345.玛格特·比尔德《浪漫的幻象,普通生活的焦虑——解读奥斯丁的哥特小说〈诺桑觉寺〉》(1998)认为,奥斯丁的小说《诺桑觉寺》的情节是对拉德克里夫夫人的哥特小说《奥多芙的秘密》的模仿,但又采取现实化的描写手法发展了新的小说创作模式,无疑是对传统哥特小说创作的突破。(28)Margot Beard,“Visions of Romance—Anxieties of Common Life,—Jane Austen’s Gothic Novel: A Reading of Northanger Abbey”,Southern Afric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5,No.1,1998,pp.130-138.
勃朗特姐妹的阅读对其创作的影响,也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美国当代评论家罗伯特·海尔曼《夏洛蒂·勃朗特的“新”哥特体小说》(1958)详细论述了夏洛蒂对传统哥特小说的改造:“夏洛蒂以干巴巴的写实与幽默,部分地消除了旧式的哥特体裁,此外,她还进一步对这种形式做了更重要的修正:我们将看到,那种激情之发现,超理性之重视,这些原本在哥特体裁中起过历史作用的东西,在《简·爱》和她的其它小说里,不再置于惊险的环境之中,而是深入到人生较冷僻的领域中去。”(29)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6页。苏联译者格拉日丹斯卡娅在为夏洛蒂的1963年苏联译本《雪莉》所作的前言中指出,夏洛蒂·勃朗特受到了罗伯特·欧文的某些社会乌托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在《雪莉》的结尾才会出现一幅工业田园牧歌的图景。(30)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的荣誉研究员艾莉森·霍丁科《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的阅读与看图》(2007)认为,夏洛蒂小说中的阅读书目显示了她广泛的阅读经历和所受的浪漫主义影响,对其塑造角色性格与阐明主题起到了重要作用。(31)Alison Hoddinott,“Reading Books and Looking at Pictures in the Novels of Charlotte Bront⊇”,Bront⊇ Studies,Vol.32,No.1,2007,pp.1-10.玛吉·艾伦《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对艾米莉·勃朗特的影响》(2005)指出,以歌德、席勒与诺瓦利斯等为中心的德国诗人创作的诗歌与散文,对艾米莉诗歌的主题与意象有所启发,同时音乐家贝多芬对艾米莉也颇有影响。(32)Maggie Allen,“Emily Bron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Romantic Poets”,Bront⊇ Studies,Vol.30,No.1,2005,pp.7-10.
因乔治·艾略特的知识场丰富与多样,其阅读对小说创作影响的研究并不局限在文学领域内。以色列学者威廉·贝克《乔治·艾略特对19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的解读——以〈丹尼尔·德隆达〉为背景的注解》(1972)关注到乔治·艾略特阅读的许多历史著作,都集中在犹太文化历史上最丰富复杂的时期。其小说《丹尼尔·德隆达》的历史背景是她对八位19世纪犹太历史学家(聪茨、盖格、约斯特、萨克斯、德利茨、芒克、斯坦施耐德和格雷茨)研究性阅读的虚构转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小说中人物的观点表达提供了基础的知识框架,小说中吉迪恩和帕什表达的同化主义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学家聪茨和盖格;莉莉关于后圣经时代犹太文化空洞和堕落的观点在约斯特的作品中得到了支持;莫迪凯关于犹太民族主义复兴的论点,部分源自聪茨、萨克斯、德利茨、芒克和斯坦施耐德。(33)William Backer,“George Eliot’s Readings in Nineteenth-Century Jewish Historians: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of Daniel Deronda”,Victorian Studies,Vol.15,No.4,1972,p.463.美国圣欧拉夫学院的维多利亚文学研究员戴安娜·波斯尔斯特维《当乔治·艾略特阅读弥尔顿时》(1990)一文指出,弥尔顿《失乐园》的史诗世界观对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起了创造性的推动作用,《米德尔马契》和《失乐园》分享了一个基本类似的主题:对知识、婚姻和自由的追求,但《米德尔马契》对《失乐园》进行了一次滑稽模仿,发展了女性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批判。(34)Diana Postlethwaite,“When George Eliot Reads Milton:The Muse in a Difference Voic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Vol.57,No.1,1990,pp.197-221.《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就是一个不仅追求智性水平提升,更冀图通过婚姻来献身丈夫的伟大书写计划——编撰《世界神话大全》——从而实现自身的知识追求梦想的女性。与此同时,作品的另一条线索则描摹了利吉盖特在米德尔马契普及医疗科技思想与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道路上历经艰辛却最终幻灭的结局。难能可贵的是,在小说中,艾略特还书写了多萝西娅的农舍改建计划及其实施,对社区命运共同体的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加拿大特伦特大学研究员苏珊·贝利《阅读的关键:乔治·艾略特与高层次批评》(1996)提出,《米德尔马契》在形式和认识论上的复杂性与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著作有哲学相似性,即对历史或文本证据进行怀疑性批评,使曾经被认为是稳定与统一的文本产生分层与破碎,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解释,艾略特在小说中所做的形式选择就印证了这一批评思想——例如多情节叙事,通过“二手”证词、同一事件多视角的分层叙事、人物的结构配对等手段,使《米德尔马契》的小说意义获得了多层次的解释。(35)Suzanne Bailey,“Reading the ‘Key’: George Eliot and the higher criticism”,Women’s Writing,Vol.3,No.2,1996,p.132.《剑桥文学乔治·艾略特指南》则更是从哲学、科学、宗教、政治与性别五个维度对艾略特的阅读与创作之间的联系展开了讨论。(36)参见George Levine,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George Elio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此外,艾略特的阅读广度与阅读深度,还可以从其1854—1857年发表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与《领袖》上的文章目录中管窥全豹。这些充满辩证思维与历史眼光的文章,涉及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威斯敏斯特评论》的主要论文有《法国妇女:萨布莱夫人》(37)George Eliot, “Woman in France: Madame de Sablé”, Westminster Review,Vol.LXII,1854,pp.448-473.《西行漫记》和《康斯坦丝·赫伯特》(38)George Eliot, “Belles Lettres (Westward Ho! and Constance Herbert)”,Westminster Review,Vol.LXIV,1855,pp.288-296.《福音教义:卡明博士》(39)George Eliot, “Evangelical Teaching: Dr. Cumming”,Westminster Review,Vol.LXIV,pp.436-462.《德国人的智慧:亨利·海涅》(40)George Eliot, “German Wit: Heinrich Heine”,Westminster Review,Vol.LXV,pp.1-18.《德国生活的自然史》(41)George Eliot, “The Natural History of German Life”,Westminster Review,Vol.LXVI,pp.51-79.《女作家写的蠢故事》(42)George Eliot, “Silly Novels by Lady Novelists”,Westminster Review,Vol.LXV,pp.442-461.;《领袖》上的主要论文有《创世纪览略》(43)George Eliot, “Introduction to Genesis”,Leader,Vol.VI,pp.41-42.《弥尔顿的生活与观点》(44)George Eliot, “Life and Opinions of Milton”,Leader,Vol.VI,p.750.《玛格丽特·富勒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45)George Eliot, “Margaret Fuller and Mary Wollstonecraft”,Leader,Vol.VI,pp.988-989.《德国哲学的未来》(46)George Eliot, “The Future of German Philosophy”,Leader,Vol.VI,pp.723-724.《安提戈涅及其道德》(47)George Eliot, “The Antigone and Its Moral”,Leader,Vol.VII,p.306.《威廉·迈斯特的道德》(48)George Eliot, “The Morality of Wilhelm Meister”,Leader,Vol.VI,p.703.《托马斯·卡莱尔》(49)George Eliot, “Thomas Carlyle”,Leader,Vol.VI,pp.1034-1035.,等等。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这一时期艾略特写作的文章罗列出来,是因为这充分显示了作家阅读的国际性、前沿性、专业性与综合性,艾略特的阅读视域委实是所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小说家中最丰赡、开阔的,甚至远远超过当时的许多男性智慧大脑,包括《威斯敏斯特评论》的著名主编查普曼,此人不仅仰仗艾略特组稿赐稿,更是谦恭地将艾略特当作自己论文的指导老师。艾略特曾对其论文进行审读并提出严厉的修正意见,使得这位大名鼎鼎的办报人心怀惴惴、言语讷讷,令人读后不禁莞尔:
但每当你从叙述过渡到论文时,某些老毛病就会重现——表达不准确,动词和形容词的叠加组合,混合的隐喻,以及一种需要通过蒸发来减少的水一样的体积。(50)Gray Beryl,“George Eliot and the Westminster Review”,Victorian Periodicals Review,Vol.33,No.3,p.219.
这里所说的“通过蒸发来减少的水一样的体积”无疑就是指查普曼的论文臃肿膨胀、枝枝蔓蔓,需要大刀阔斧地删减清理了。这些阅读批评意涵丰富且睿智,是研究艾略特丰厚思想与创作理念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在20世纪后期,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到女性小说家的跨文学阅读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这是该领域研究的新突破。阿利斯泰尔·达克沃斯教授在《改良庄园》(1971)一书中就指出,奥斯丁深受雷普顿《园林景观简编》《论园林景观之理论与实践》与伯克《法国大革命反思》的影响,并体现在《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创作之中,以“庄园改良”隐喻“国家改革”,并以此批判无序的政治改革。(51)参见Duckworth Alistai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1,pp.38-54.伊丽莎白·艾略特《奥斯丁小说中对教育的强调》(2014)认为奥斯丁接触过同时代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并在她的小说创作中通过对女性教育的讨论显现出来,谴责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社会现象。(52)Elizabeth McElligot,“Jane Austen:Shaping the Standard of Women’s Education”,The Midwest Journa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Vol.1,No.1,2014,p.98.《乔治·艾略特与音乐》(1989)与《乔治·艾略特与医药》(2000)两本专著则别出心裁地发掘艾略特所具有的音乐和医学知识及其在小说中的呈现,前者关注作为听觉艺术的音乐在其小说中对人物情感的激发和对作品结构的凝聚作用(53)Beryl Gary,George Eliot and Music,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89,pp.10-11.,后者关注其小说中医药对社会、身体、政治与艺术等层面的隐喻(54)Kathleen McCormack,George Eliot and Intoxicati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0,p.9.。关于医药与医疗知识在小说中的嵌入,艾略特不仅得益于孜孜不倦的学习与研究,也与其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她曾服侍重病在身的父亲,自己也一直被头痛这个顽疾所困扰。在容受病人的各种情绪状况以及由于宗教观念的不相容所带来的精神折磨之下,作家在《米德尔马契》中成功地塑造了费瑟斯通这个久病在床、性格乖戾的老人形象,亦对利吉盖特这个热衷普及医疗知识并矢志医疗改革的小镇知识精英的精神心理进行了深度刻画,彰显了19世纪中后期社会改革洪流中金钱至上观念与科技伦理意识、宗教精神与利己主义思想的激烈交锋。
此外,20世纪后期以布鲁姆与伊瑟尔两人为代表的解构传统阅读理论浪潮的兴起,为女性阅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国外学界已出现运用新的阅读理论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问题进行探究的成果。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的理论》(1973)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针对传统的阅读理论提出了批判与修正。作者认为,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保持与前辈诗人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认为“诗人中的诗人”的灵感是通过阅读另一位诗人的诗歌来进行写作,并倾向于创作有可能成为现有诗歌衍生品的作品,所以前辈诗人影响激发了现在诗人的焦虑感。(5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15页。有鉴于此,由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1979)就借用了布鲁姆“影响的焦虑”概念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创作进行研究。布鲁姆的有关研究是十分具有男性色彩的,而且毫无疑问是具有父权中心意识的,因此作者认为:“女性诗人身上并不同样存在男性诗人所有的那种影响的焦虑,原因很简单,她所必须面对的前辈,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男性作家,而他们和她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前辈不仅体现出父权意识的权威,甚至还试图将她拘禁在有关她人格和潜能的界定之中,方法便是通过对她进行极端化的删削。”因此“一位男性诗人所感受到的影响的焦虑,到一位女性诗人那里,就会更多地为作者身份的焦虑所取代——这种身份的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即女性诗人担心自己无法进行创作”。(56)[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韩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女性小说家在阅读男性前辈的作品时是心存恐惧的,这种阅读恐惧在她们的创作中往往会导致两种倾向:一是模仿顺从,二是叛逆反抗。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在考察了简·奥斯丁、玛丽·雪莱、艾米莉·勃朗特和艾米莉·狄金森等大量女性创作后指出:“女性作家都创作过某种意义上算是重写手稿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表面上的设计隐藏,或者说模糊了更为深层,也难以把握的(同时,还有更不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意义层面。”这些女性作者“需要在争取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权威时,做到对父权中心的文学标准既妥协,又加以颠覆”。(57)[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著,韩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13页。这种关于性别“影响的焦虑”在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开篇也有相关论述,但与吉尔伯特与古芭的观点不同,肖瓦尔特更注重从历时性的女性群体经验进行考察,将女性创作的顺从与颠覆分隔为两个历史阶段,英国早期女性创作受男性文学标准的限制,导致女性创作过分地模仿男性创作,成为“过分模仿的文学”,她将从夏洛蒂到乔治·艾略特之间的女性创作称为“女性的”文学阶段,直至女性惊悚小说的出现“大范围地表达了被压制的女性情感,激发并满足了抗议和逃逸的白日梦”(58)[美]伊莱恩·肖瓦尔特著,韩敏中译:《她们自己的文学 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女性创作才进入颠覆进程当中。
总之,国外基于“阅读”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女性小说家们可资借鉴的重要阅读信息,还从阅读信息出发考察了女性小说家创作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明晰了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之于其创作的影响,并借助20世纪新的阅读理论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问题进行深度探究,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女性小说创作进程的认知与领悟。
二、国内有关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
较之于国外研究,21世纪之前,国内学界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相对冷落。20世纪80、90年代,杨静远选编《勃朗特姐妹研究》(1984)、朱虹选编《奥斯丁研究》(1985)与《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1997),其中已涉及国外学者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研究,对国内学者无疑有开启之功。
进入21世纪后,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关注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之于其创作的影响。如罗杰鹦《布鲁姆的“互文性”和〈曼斯菲尔德庄园〉》(2000),从互文性的角度解读奥斯丁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对前人的借鉴,指出“奥斯丁从塞缪尔·理查逊那里学到最多,从《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女主人公芬尼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查逊的创作原型——帕米拉和克拉丽莎”,“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在叙事结构身上与《帕米拉》似有异曲同工之处,即爱情故事所包含的欲望实现的延异性”。(59)罗杰鹦:《布鲁姆的“互文性”和〈曼斯菲尔德公园〉》,《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刘文荣编著的《19世纪英国小说史》(2002)涉及除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几名大家之外的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如简·波特、玛利亚·埃奇沃思、苏珊·费里尔、夏洛蒂·扬等的阅读情况,指出她们均熟读并崇拜司格特的小说,在其影响下,简·波特创作了《苏格兰大盗》,玛利亚·埃奇沃思创作了《拉克伦特城堡》,苏珊·费里尔创作了《结婚》《遗产》和《命运》,夏洛蒂·扬创作了《小公爵》《林恩伍德的长矛骑士》《王子与侍从》和《笼中的狮子》;萝达·布劳顿深受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的影响;汉弗莱·伍德夫人则追随了乔治·艾略特的创作道路。(60)参见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潘忆燕《女性阅读和女性小说之兴起》(2006)也阐述了19世纪英国女性阅读对女性小说创作的促进作用,其中涉及《天路历程》、说教小说、《女人义务之探讨》《父亲给女儿们的遗产》这些当时英国女性可能阅读到的书籍。(61)潘忆燕:《女性阅读与女性小说之兴起》,《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第4期。
马建军《乔治·艾略特研究》(2007)是国内首部对乔治·艾略特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论著,作者认为,“她(乔治·艾略特)本人翻译过斯宾塞、斯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先后拜读过黑格尔、康德、卢梭、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等,对查尔斯·布雷关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因果说与历史延续性、斯宾罗莎的认识论、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孔德的实证主义等理论颇有心得,对其它分析哲学的门类,如认识论、伦理学、玄学、语言学、美学等也有非常独到的研究”(62)马建军:《乔治·艾略特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0页。,作者据此指出,艾略特作品中的社会改良思想与有机社会观正是分别源于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与孔德的实证主义。毛亮《历史与伦理:乔治·艾略特的〈罗慕拉〉》(2008)直指孔德实证主义对艾略特小说创作的影响:“艾略特对文艺复兴社会与思想的理解则更多地来源于另一个不同的思想传统: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63)毛亮:《历史与伦理:乔治·艾略特的〈罗慕拉〉》,《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孔德实证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伴随着人类道德伦理意识不断完善的连续的发展过程,他肯定早期基督教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然而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将道德伦理与世俗政治的结合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中人们呼唤科学与理性的需求。《罗慕拉》就涉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邦统治集团与罗马教廷间的政治冲突、新思维与艺术方式与传统基督教宗教创作间的观念冲突,表达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宗教观念已无法与现代生活适配的观点,以此实践孔德实证主义中的社会发展观。朱桃香《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2009)涉及了大量乔治·艾略特的阅读情况,指出乔治·艾略特的阅读内化到了她的小说叙事中,如小说题记的使用“在文本和过去传统之间建立了联系,或阐述、复述、示范题记中的真知灼见,或反讽、质疑题记中的真实”(64)朱桃香:《叙事理论视野中的迷宫文本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04页。。
陈礼珍《〈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2011)中认为盖斯凯尔夫人对政治经济学十分熟悉,作者至少看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在小说《玛丽·巴顿》中有所体现。(65)陈礼珍:《〈克兰福德镇〉的“雅致经济”》,《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何畅《“风景”的阶级编码——奥斯丁与“如画”美学》(2011)指出奥斯丁早期创作对吉尔平的如画美学观念的接受:“吉尔平的如画准则赋予了奥斯丁一种观察自然的方式,并且为其构建主人公阶级趣味和阶级特征的叙事手段。”(66)何畅:《“风景”的阶级编码——奥斯丁与“如画”美学》,《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李维屏与宋建福合著的《英国女性小说史》(2011)对19世纪几位著名的英国女性小说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涉及的阅读研究也较前人有更多的发现,如在对勃朗特姐妹早年的阅读经历述评中就提到:“她们自由涉猎文学经典和流行读物,从圣经、《伊索寓言》、《天方夜谭》、《天路历程》、《失乐园》,到当时流行的各种杂志,包括姨妈订阅的妇女杂志,她们都读得有滋有味。拜伦是她们最喜欢的作者,《布莱科沃德杂志》对她们影响巨大。”(67)李维屏、宋建福等:《英国女性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乔治·艾略特的阅读范围甚广,从班扬、弥尔顿、歌德、席勒、华兹华斯、雪莱、施特劳斯、费尔巴哈、斯宾诺莎、斯托夫人、斯宾塞的作品到查尔斯·布雷的自由思想以及查尔斯·汉纳尔的宗教怀疑主义、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的“人本宗教”观点均有涉猎。张鑫《奥斯丁小说中的图书馆空间话语与女性阅读主题》(2016)则从奥斯丁小说中女性角色的阅读情况入手,推测作者本人的阅读情况和对女性阅读所持的态度:“奥斯丁意欲借此展示阅读对女性教育和权利争取的启迪。在阅读空间的运用、阅读类型的选择上,女性必须分清重要与琐屑、尊重与唾弃。而对女性阅读意义不大、女读者类型千篇一律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68)张鑫:《奥斯丁小说中的图书馆空间话语与女性阅读主题》,《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张秋子《夏洛蒂·勃朗特晚期小说中的鬼魂、幻觉与互文》(2017)采用了互文理论对夏洛蒂·勃朗特晚期小说中出现的鬼魂与幻觉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作者创作不但受到卢梭的教育观影响,后期小说中大量的心理学叙事与颅相学叙事则与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的心理学与颅相学密切相关。(69)张秋子:《夏洛蒂·勃朗特晚期小说中的鬼魂、幻觉与互文》,《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6期。张秋子的另一篇论文《皮·骨·心——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颅相学叙事》(2020)同样提及颅相学这一学说对同时期其他女作家所产生的影响,如盖斯凯尔夫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即提到,“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读施普茨海姆关于颅相学的书,还准备在之后的讲座中向各位介绍这种学说”(70)J,Uglow,Elizabeth Gaskell: A Habit of Stories,New York:Farrar Straus & Giroux,1993,p.45.,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隆达》开篇对葛温德林的形象描写就表现出对人物颅相的特别关注。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2018)探讨了简·奥斯丁、夏洛蒂·勃朗特与乔治·艾略特三人之间阅读与承继的文学艺术流变关系,认为“奥斯丁、勃朗特和艾略特三人的创作生涯,不仅没有重叠,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艺术上的连续统一体。1816年勃朗特出生,次年奥斯丁去世。而当勃朗特去世时,艾略特刚刚开始写作。不言而喻,她们每人都读过前人的作品,并受过其影响,而每人都曾试图凭借自己的独创性写出与前人不同的小说。不仅如此,她们三人的小说在生动反映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气息的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19世纪小说艺术的时代烙印”(71)李维屏:《英国小说艺术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2页。。事实上,李维屏所作的推论是完全成立的,夏洛蒂·勃朗特对奥斯丁毫无激情书写的批评早已为读者所熟悉,而乔治·艾略特在其早年的编辑生涯中,对丈夫刘易斯肯定奥斯丁创作的精妙与批评《简·爱》情节剧式的夸张格调与不可能的情节等内容,也肯定早有耳闻。
总的看来,国内涉及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多从影响角度出发探究女性小说家的阅读对创作的影响,这为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一些较有启发性的思路与见解。
综上所述,迄今国内外学界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问题已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取得不少成果。在国外,不少女性小说家的传记、日记与书信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女性作家的阅读信息。20世纪后期,新的阅读理论以及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女性小说家阅读与创作之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不过,目前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阅读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或薄弱环节:第一,大部分研究只着眼于女性小说家某一方面的阅读,全面反映女性小说家阅读情况的论著与论文都还比较欠缺;第二,研究成果尚显零散、不成系统,难以全面、有效地反映女性小说家阅读与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第三,掌握的第一手文献有限,加之无论是日记、传记、书信等的研习与梳理,还是文本细读工作,不少工作还停留在比较粗疏的层次,对作家阅读之于创作的具体影响还停留在经验主义和推测假想的基础之上,有待进一步辨析与考证。鉴于此,对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阅读的研究,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开拓与系统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