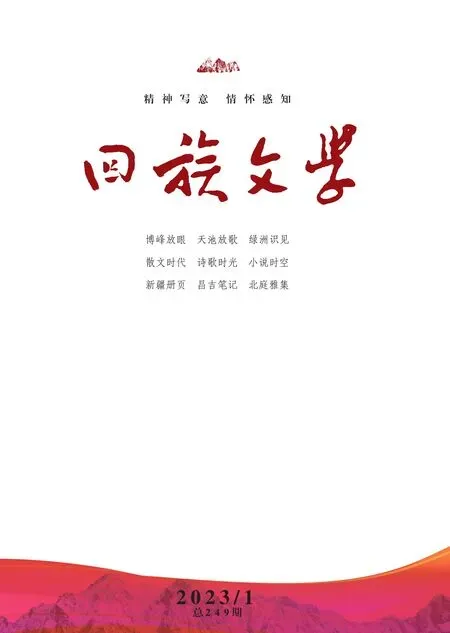一场大雨的因果
提云积
这场雨下在了汉武帝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操纵了这场雨的人也想象不到会有这种结果,他以为一场雨只能是解除干旱,救黎民百姓于热火之中,但不能浇灭他心中的旺火。这把火在他的心里已经燃烧了很久,从他还没有坐在这个位置上时就开始燃烧了。他会隐藏,极力将这把火压在心里最隐秘的地方,只有那些宫廷术士和江湖异人才知道他的这把火该如何疏导。他循着术士的指引到了这里,他没有看到点燃了自己隐藏心里那把火的人。这个人是仙人,不是凡夫俗子能看到的,即便他贵为天子也不能。在此刻,他却看到了正在被烈阳炙烤的大地。
那一日从清早开始便晴空万里,天上没有一丝一缕的云彩,烈阳初起,地面的温度持续上升,虽说是早晨,世间一如蒸笼般溽热,村庄在烈阳下无有任何的声息。河岸上密匝匝排列的树木全部耷拉着灰突突的叶子,叶子之间传出知了枯燥的叫声,也是极为鲜闻。没有鸟儿,鸟儿都循着天空的指引,追随着无常的云朵逃到远方寻找水源去了。
如果现在有一场雨于这世间落下,你会想到这场雨会带来何种“果”。作为最本真的思维反应,雨落下,大地之上,小溪径流,注入江河,江河满;植物青翠,生机复苏,继续喂养生活。
如果时间跨度再久远一些呢,一场雨会有怎样的“果”,不但我们想不到,作为总结了因果关系的前人也不会知道,只有在“果”显现出来,成定论才能知晓。而这个“果”,有的需要经过几日、几月、几年,有的甚或是几个世纪才能见分晓。现在有一场雨的结果已经知道,它决定了一个村庄的诞生。然而,它的出现并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在那个文本里,它是一个附属事件,只有几个字的记录。现代的人如果想求得事件的原本,只能是依靠一些传说来加以描述。然而,这样的描述如同一张残破的渔网,不敢祈盼这样的渔网能网住多少真相,毕竟,作为“果”的前世,“因”的出现太早太早了。
世间因果纷纭,作为世人永远不知道那些最初的因与最终的果是如何发生隐秘联系的,及至果显现出因的本意,世人才恍然,原来如此。因与果之间的过程,人们反而漠视了。
这个人站在大河的北岸,也可能是大河的南岸,他有没有想过如果现在有一场雨于这世间落下会造成何种因果,作为现代的我们无法揣测。他站立在这里,是为一场雨而来,这场雨在他刚站定在河岸上时还是未知的。如同他根本不能预想到下一刻会有何种机缘发生,何况是两千余年后的今天,这一点我们与他相同,也就是说,我们也无法猜测他的想法。
现在,不仅是他站定在河岸上,他的身后也站定了一众随从,旌旗被太阳晒得没有精神,全部耷拉在旗杆上。汗水顺着那个人的脸颊一路滚落到下巴,在下巴汇聚到一起,然后滴落到皇袍的前襟上,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他毫无所觉,一直固执地站在河岸上。随从颇有眼力,将伞盖伸过他的头顶,努力给他制造一个阴影,让他在伞盖的阴影里得到短暂的阴凉。他并不接受随从的好意,也无指责随从的意思,只是向前迈了几步,已经彻底站在了河岸的边缘上,不消半步,便会踏空,跌落到河道里。
面前的河道早已干涸,河底的淤泥被太阳晒成了鱼鳞状,之前河道里繁茂的芦苇已经干枯,若干年在河床的淤泥上生长的苔藓早已归为尘土,空旷的河道没有丝毫的生机。大河两岸上的田野里一片白突突的黄,阳光像明晃晃的大刀片子,铺满田野。
他站在河岸上一动不动,他的皇袍已被汗水浸透,慵懒地贴在身上。术士在他的身后做着法术,肢体像莫名其妙的一股风,只吹拂他一人。河岸上跪满了乡民,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面前的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他,一个是术士。此刻,术士承受的目光应该多于他,毕竟,一场雨与他相比较,乡民们更关注一场雨的来临。
其实,乡民们不知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对于术士能否将未知的雨召唤来,他的心里没有底。治理一个国家,他是专家,求雨,他是门外汉,只能是假托这些术士,或者是江湖异人。他明白这些术士或江湖异人,看透了他们隐于内心的动机。他与这些术士或者是江湖异人之间一直在做一桩交易,他有足够的财富,全国之财力;术士们有异能,可以通晓天地之间最隐秘的物象,比如长生不老、飞升成仙。他虽贵为天子,但不能以肉身抵达天上,只能是借助这些术士来加以成全。在那个时代,许多未知的物象,都被世人看作神,这些神化的物象须有像神一样的人加以操控,这些像神一样的人,被世人称作神仙。何况,这些被神化的物象与神仙都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他深信不疑,虽然吃过苦头,并没有抵消他对成仙的渴望。
元鼎五年春天,也就是他站在这里的两年前,公元前112年,他亲自下令腰斩了自己的女婿,女婿的尸身就埋葬在当利城南侧,当利城距离他现在站立的地方大约七十华里。女婿叫啥名字?世人只是以栾大相称,生年不详,他葬身的坟墓后世人叫作栾大墓。对于此人,《汉书》《史记》《资治通鉴》多有记载。摘录《汉书·郊祀志》如下,《史记》《资治通鉴》的文本与此无太多出入。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王死,它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入,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为亲属,以客礼侍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得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河,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飞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弟,使者存问共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视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掔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他给予了栾大最高的荣耀——财富与名誉。然而,栾大并不能给予他任何的升仙契机,在一次次的失望过后,他始悔悟,他的信任最终换来的是对方的欺骗,还因此耽误了女儿的人生,他一怒之下将栾大腰斩。这是栾大的因果,谁也不能代替。现在还能寻得栾大墓的具体所在。我曾在那个地域工作过十年的时间,每次下乡向北出镇区东行,便会经过栾大墓。栾大墓在东西路的南侧,封土早已与大地同平,栾大借由他追求长生不老所谋求的财富与名誉,都湮灭于时空深处,只有一些传说被时时提起,常说常新。
太阳继续攀升,眼见着日上三竿,温度持续升高,隐藏于枝叶间的知了也不再鸣叫,空气也仿佛忘记了流动,他一个人就这么站在河岸上,在他的身后,术士一会儿手舞足蹈,一会儿念念有词。这些举动他看过太多太多,今日他不想再看,他只是想看到一场大雨的样子,从天上直达人间。有一刻他曾想过,他与前朝的秦皇相比还是幸运的,秦皇急于成仙,吞下了仙人假托术士之手交给他的不死草,结果因为这株不死草死在求仙的路上,这给他一个警醒,他要亲眼见到仙人才为准,不是仙人亲自交给他的,任何灵丹妙药都不足为信。求仙的路与治国的路是一样的,其中的甘苦况味只有他自己知道,术士与众位大臣只是看到了一个表象,最真实的内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分寸,这是一条漫长的不知终点的旅途,他不着急,他耐得住性子。
术士看不到他的脸色,一双微睁的眼睛一直盯在他的后背上,有时候也会看一眼没有丝毫云彩的高天。此刻,术士多想头顶上的那方高天会和他的后背一样,有像汗水漫漶一样的云朵从不知的方向被狂风吹拂过来。他早已湿透衣衫,没有一角是干爽的。其实,他的衣衫已被汗水湿过几遍,脚下的泥土里有点点的痕迹,像一场轻洒的雨水,水滴清晰可数。他的汗水除了太阳的炙烤,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术士不想如前辈那样惹怒皇颜,与栾大一样的下场。术士就这样一边做着祈雨仪式,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如果事情败露会有何种结局,该如何面对他的质问,在心里思虑了几套说辞,感觉每一套说辞都不能洗清自己对他的欺骗,冷汗瞬间奔涌而出,与热汗交织在一起,浑身冒出的汗就比别人更多。
燥热难耐,时间过得也感觉到了缓慢。日中午时,跪伏的百姓相互之间用眼神作着交流,他们素来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暴晒的天气,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曾单纯地想,如果深跪、长跪能使高天洒下甘霖,他们可以跪一辈子。从上年就鲜见雨水,他们就在这河边跪拜过,一直难见水迹。今日今时的阵仗是第一次见。他们把一切的期望都寄托在面前的这两个人身上,祈得雨水救万民。在术士的一次次号令下,他们一次次地对着面前的黄土地磕下头去,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个凹槽,正好是额头的样子。
术士又举起了手里的三角令旗,一直在嘴角默念的咒语此刻变得大声,一碗水酒泼于河道,随着水酒落地,术士手里的三角令旗挥向高天。乡民们看出了异样,术士的面色凝重,好像是成败在此一举的样子。那个一直独自站立的人在听到术士大声的咒语时,明显地看到他的后背震颤了一下,迅疾就恢复了原初的样子。没有人能看到他此刻脸上的神色,即便是面对面,相信那些人也不会看出他面色的变化。
一滴汗珠流了下来,改变了直线的运动轨迹。又一滴汗水滚落下来,依旧改变了直线的运动轨迹。不知是谁先喊出了第一声:有风了!是的,有风了。他也感觉到了,那丝风好像是从广袤的河道上游吹过来的,但感觉又不像。他想再次确认一下,却感觉这风比起初有了更加明显的痕迹,有一刻,他感觉这风是从天上来的。
风持续,越来越强,高天上开始有了云朵,起初是白色,眨眼的时间变成了灰白色,继而是黑灰色。随着云朵颜色的改变,风势逐渐增强,河岸上的柳树被风摇动了枝叶,沉寂很久的知了又开始鸣叫,有的甚至飞出藏身的枝叶,在河道的上空打一个盘旋飞向了河道对面的柳树上栖落。在他背后的旌旗舞动起来,发出猎猎的声响,就像他要出征一样,显示他的雄心。术士像是掏空了全身的气力,手里的三角令旗还是保持着指向高天的样子。
浓黑的云朵继续堆积,越来越多,像是吸满了大江大河的水一样,不堪重负,越来越低,甚至擦着河岸两边的树梢一样。此刻,狂风劲吹,黄土飞扬,午时的天地间一片混沌,如尚未开启天地一般。眨眼间,一道异常明亮的闪电从河道里直冲天际,而后,脆烈的炸响落在每个人的心上。雨跟随着落了下来,人们匍匐在地,头颅紧紧地贴在面前的土地上,他们佝偻跪拜的样子像极了大海上奔腾的波涛一般。
雨不是如往日一般从天上飘下来的,今日是砸下来的,在人们的眼前晃着白亮的光,从高天上直直地砸落下来,带着燥热的气息砸在河道里,砸在河道两岸,砸在河岸上祈雨的人群里,爆泛起土腥气息。他依旧不动。那些雨瓢泼起来,这样描述好像不能真实还原那场雨降落的状态,应该是决堤的天河水倾倒下来。很快地,河道里有了积水,积水形成水流沿着河道向西而去。上游的水也奔涌过来,发出轰轰的声响,隆隆的雷声,明晃晃的闪电在河道里交汇,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情感迸发。乡民们在他的身后再次跪拜下去,这次跪拜没有令旗的指挥,乡民们是从内心里跪拜下去,异口同声地山呼:万岁!万岁!
他在乡民山呼万岁的呼喊声中走了,大雨落在他前行的路上,雨幕清洗了世间的一切。河岸上的杨柳洗去凡尘再次泛起了绿意,落过雨的田野有了明亮的气息,那些生机开始冒出地面,甚至是村庄的上空也冒出了炊烟。炊烟与雨幕交织缠绵,所有生的欲望都得到完美的诠释,令人想到这是大雨于这世间最真实的意义,也是这场大雨在当下最直观的因果关系。
雨继续下,这场雨有多大呢?后世人不知道,只是民间口传这场雨很大,有几天几夜的持续落雨,似乎将干旱时期积攒的雨水都在这几日下完了。自他来此求雨后,这条河就再也没有干涸过。
这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一段令人遐想无限的故事,那遥远而又清晰的故事情节,因为一座村庄,被重新结构还原。他走后,乡民们将这条河的名字作了更改。早年这条河的官方名字称为“万岁河”,俗称“旺河”,因为他是那个时代的王,就改为王河。古书记载,掖邑境内以万岁河最巨,支流众多,成其为大。河流广袤,积沙深厚,称谓万里沙。《汉书》注:“沙径三百余里。”《明一统志》载:“万岁河在府城东北三十里。两岸皆沙。秦始皇、汉武帝皆祷于此。”《方舆纪要》载:“万岁河,府东北三十里。其两岸即万里沙也。秦始皇、汉武帝皆祷于此。”
其实,在这场雨之前,还有一个故事需要讲述。因为他不是刻意到此求雨的,而是想成仙长生不老,求雨只是在求仙不成后作为补遗的一件事情。《汉书·郊祀志》载:“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人、采药以千数。是岁旱。天子既出亡名,乃祷万里沙……”因为求仙师出无名,只能以为天下苍生祈雨为名,博得天下民众归心,这是政客的把戏。
这个人是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汉武帝与莱州颇有渊源,在他做皇帝期间,随着年纪增长,他对长生不老的渴望愈加强烈。根据史料记载,他至少有九次莅临莱州。他多选择春日出行,由长安至莱州,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抵达。其时,莱州已初夏,正是四季中最好的时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多有记载。其于莱州,多为求仙而来。明初朝鲜使臣李詹路过莱州时,作《莱州路上》,有一句话“齐桓图霸业,汉武望神人”。由此可见,莱州自古以来便是物阜民丰安居乐业之所在,应不乏高龄长寿之人,为历代朝廷所追逐之地。
对于汉武帝,后人是这样评价他的: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就是在他执政天下时开辟的。
那时,所有的文本记载都以万里沙为名,并无有关于村庄的任何一个文字的记录。前面说到的那个“因”已经有了——一场大雨,“果”还没有显现,需要时间继续沉潜前行。根据传说与文本记载,在万里沙旁,有万岁亭,是汉武帝所筑。《三齐记》曰:“水北有万岁亭,汉武所筑。”莱人先贤毛贽曾作《万岁河》诗:“万岁河中万里沙,汉家祷雨驻仙车。莱王祠已归荒草,两岸秋林映晚霞。”帝王、荣华富贵,甚至是神仙都已归去,荒草萋萋,秋林向晚,只有霞光追随着太阳日日升起,日日没落,这才是宇宙的永恒。
寒暑易节,春种秋收,大地依旧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行,时光也在跌宕起伏的岁月里伸展。我来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后了,夏天已经过半。一棵古槐树立于此世间时,与我产生了因果关系,因为它的存在,几百年后,我循着我们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指引来到了这里。这里已经不是早年的万里沙了,它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罗台。
罗台村在王河的北岸,也就是万岁河的北岸。不大的一座村庄分了东西两个行政村,根据一些文本记录和乡人传说,汉武帝祷雨的地方就在东罗台村。对于村庄的来历,我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外的墙壁上看到一块黑色的花岗岩刊板,刊板上记录了村庄的来历:“东罗台,莱州市地名志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刘彻曾在此筑‘行乐台’,建‘万岁亭’于其上,亭内修有罗汉像,故又称罗汉台。明朝洪武年间由四川移民迁此立村,取名罗台。明末村庄发展扩大,以村中排水沟为界,分为两村,居东者称东罗台。”
文字极简,一百一十七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如果没有错漏,应该也是直白易懂。凡事需要推敲,不能人云亦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地官方机构地名办拟对辖区所有村庄的来历作一个深入的调查,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却以“想当然”的态度,将大部分的村庄史进行了重新架构,致使错漏百出,变作了一个贻笑大方的工程。
汉武帝在位期间,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以儒家的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的学说。何况,佛教是在西汉末年才传入华夏,以汉武帝的手段,断不能在万岁亭内修立罗汉像。我们都知道,罗汉为佛家的形象代表,在一个独尊儒术的时代怎么会有佛教的影子,这说辞是村志的硬伤。
我曾根据“罗”的发音作过两个推测。一是“乐”,在此地的方言读音为luo,因为这个读音,早年的“罗台”文本应该是“乐台”二字。乐台也就是“行乐台”,人们为了交流的简捷,只说后两个字。岁月变迁,“乐”的读音未变,字却被“罗”取而代之;二是以“罗”为准,因为王河水系庞大,鱼种多杂甚丰,两岸乡民有以打鱼为业者。“罗”本身就是网的意思,渔后需要将网进行晾晒,在万岁河的北岸晒网,日久天长,将晒网的地方称为罗台,延续下来至今世。两个推测,我更倾信于第一个。
对于移民的说辞,不再作更多的表述,此地官方没有洪武年间有外迁于此的移民记载,反而是有从此地移民至外乡的记载。至于万岁河的称谓也有明显的错讹,并不是因为汉武帝祷雨成功后,乡民呼喊万岁而得名。《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有这样的描述:“曲城侯刘万岁,中山靖王子。”汉时,万岁河地域属于曲城管辖,这条河的源头出自曲城诸山,汇流至此,然后继续西行,直到入于渤海。由此可见,万岁河名称的来历,应该是曲城侯刘万岁在向世人宣示他对受封领地的权力。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该地域曾出土一残瓦,上有篆书“万岁万岁”四字,字约一寸二分厚。前一个“万岁”应为名词,单指刘万岁;后一个“万岁”,应该是形容词,是对刘万岁的祝福。后人据此推测,此瓦为万岁亭之瓦无疑。
由文字可以明确一件事情,万岁亭是真实存在的,自汉以降的史料并无罗汉像的记载,在现代却凭空出世,想来是当代的官方机构听闻了道听途说信手拈来的说辞,或者是根据字义进行的强加推论,从而影响了此地百姓的口传历史,造成了传统历史的差错,贻害后世。
对于村庄的来历,我还想通过走访民间的说辞来加以印证,这些说辞以村庄各姓氏的族谱为凭,或者是以村庄早年传世的风物作为佐证。在村民李振山家我看到了李姓家族于2004年修订的《李氏族谱》,其时,李氏一族于此已有十七代传人。现在是2021年,于李氏修订族谱已过近二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有两代人已是成人。按照现在的时间推算,李氏族人于此已有近六百余年的时光。
李振山还告诉我一个现象,村子里耕种的地块有许多是以姓氏命名,诸如孙家茔、赵家石头等。令人疑惑的是,村里并没有孙姓与赵姓的后人,周边散落的村庄也无有这些姓氏。他曾问过老人,老人也只是说这些地名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自古以来就有的。他曾想过,这些姓氏是早年的住民,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流离他乡,或者是无有后嗣从而绝户。也或许是曾有过以这些姓氏命名的村庄,因为居王河边上,适逢洪水泛滥,裹挟了泥沙将村庄淹没也未可知。前面说到的万岁瓦,现代曾有人为储藏大姜深挖地窖时,在地表以下四米处又发现了一块完整的万岁瓦,该瓦长约一米,宽未知,现已不知被何人收藏。
宇宙宏阔,世间万物都各有来处与归处,并不是想求得真相便能遂人所愿,罗台村亦如此,它的来历成谜。村庄不大,一百七十户人家,不足五百口人。村子里树木纷杂,树种多样。在村子里行走的时候,住宅的房前屋后都会有三三两两的树木耸立着,看到几株上百年的香椿树,穗状的花序正开着淡黄细碎的花。在一户人家的屋后还发现一棵异树,问过周边居住的老人也叫不上名字。树叶相似了榆树的叶子,主干却像松树,树皮皲裂,灰黑里透着隐隐的红,老人说也有过百年的历史了。这棵树给我留下了遗憾,回程后会时时想起,如心中有一块垒,总不能消解。只能再等机缘,有人帮我消除。
与村庄相衡比较古老的风物,除了一座一百余年的四合院外,尚有一古槐树。古槐树在村子南部的主路上,村庄硬化了水泥路面,古槐树在路的南侧,偏安于一户人家屋后,留给它的泥土地就极为有限。古树的生存空间过于局促,在我走访其他村庄古树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多见,有隐于内心的着急,苦于不能为它们向世人争辩一些存世的道理,颇自惭。
到罗台村,主要还是因为古树。因为是先知道了古树,到了罗台村后,才想到探究罗台村的来历,进一步了解村庄与古槐树之间的因果关系。村庄与树,共生于此,它们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我想这是肯定的。不管是先有树,还是先有村庄,或者是树与村庄一起于此,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由此产生的隐秘联系在此地走到了明处。它们与两千余年前的那场大雨有因果关系吗?我想这也是肯定的。大雨落下,万物勃发生机,吸引了与此地有因果关系的人,或者是其他的物种奔行到此,了却这一段机缘。
上午九点钟左右的阳光照射下来,笼盖了村庄与古树。古树的长势极为茂盛,树冠被浓密的枝叶营造得庞大,在路面上投下黝黯的阴影。古树起初给我的印象是两棵树,及至近前才发现,这是一棵树裂为两半,在树干与树冠交界处,还余有一段树干将两半的树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圆形拱门。阳光穿过碎裂的树干,拉出长长的影子照在地面的绿草上。树干中空的地面上生长着几棵弱小的香椿树苗,不难想象,这些香椿在长成大树的时候,会形成树抱椿的景象。这些香椿的幼苗应该是来自古槐树西侧的那株香椿树,香椿树颇高,枝干挺拔,已超过南邻的屋脊,约有五米的高度,叶片对生墨绿,看得出它正处壮年。
槐树干极粗,一个成年人的合围也不能对接。树的中空部分比较宽敞,能容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我蹲在里面向上看去的时候,发现树干的内里木质部分有碳化的痕迹。树干上部的空洞被绿色的树冠掩盖,看不到天空的样子。树腔中那些木质的纹理像悬崖上跌落的水流,有的直泻而下如瀑布,有的兜转回旋形过险滩,无一不呈现出岁月奔突流逝的样子。
其实,在说到岁月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迅疾晃过一个念头。从汉武帝于此祷雨开始,岁月一路颠沛流离,如奔逃而去的逝水,一路有浅滩,有深沟,它总能一如既往地前行。及至世间有了罗台村庄与古树,它们是否就是构成岁月滔滔逝水的支流?或许村庄与古树就是岁月旅途上的一个驿站,需要承前,需要启后,后来人于此休憩时分,便会觅得它们的前世今生,继续流传而下。
古槐树有多少年了,村民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根据《李氏族谱》推测,如果是与村庄同时代出现,也不过六百余年的光阴。然而,通过古树的外观推测,应该要早于村庄的历史。围着古树转了几圈,我竟然发现古树的一个秘密。分裂成两半的树干,在破裂处,伤口在逐渐愈合,渐合的树皮将残存的树干包裹成一棵完整树木的样子,或许有一日,一棵古树真的会生成两棵树。这是古树强大的再生能力的呈现,如此,非一日一时之工,须百年以上的修为才可,由此可以看出古树占据岁月的久长。
作为后来者,村庄与古树都在坚守着汉武帝于此的遗迹。汉武帝的行乐台早已无踪,赖以存身的万岁亭也已经沉没于时光深处,唯有王河或者是万岁河还在岁月里兀自存身。顺着村路向南,路过一片成熟将要收割的麦子地,便站在了王河的堤坝上。面前的王河河道开阔,目测有三百余米的宽度,岸边长满荒草,早已不见古时沙径三百里的景象。河床有三个梯次下降,第一个梯次有的地方被乡民开垦了农田,与堤坝比较也有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再下一个梯次,芦苇与荒草间杂,这里离岸边大约百余米;第三个梯次便是王河河道的中分地带。
我没有下到河道中分地带去,第二梯次的河床如同河岸一般,从我站立的地方向东,河道中分地带还有蓄积的河水,河水映照着高天,映射出墨蓝的颜色。河道里长满青翠的芦苇,现在是仲夏,正是万物勃发与收获的时节,那些生长于河道里的知名与不知名的绿色植物都含着欲滴的绿或者是深邃的青,这是王河在当下养育万物最直观的体现。
燕子从河道的上游划着黑色的羽翅游弋穿梭,它们时而低伏于芦苇的叶梢,时而飞上我站立的河岸,我孤身于此,于它们是谜一般的存在。它们飞过我身侧时,啁啾有声,似在探问此刻我于此的动机,如同我想求得汉武帝于此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一致的。可惜的是,燕子不能求得我的动机,和我也不能求得汉武帝的动机是一样的。风从空旷的河道里急促地攀上河岸,迅疾穿过我的身体,连带着我在此时的一些想法,跑得无影无踪。风声粗犷,感觉它们如流水一般充斥了整个河道。有一刻,我想俯下身去,像掬一捧河水般去抚摸它们,却只有一些暖意夹裹着丝滑的时光从我的手指间流过。
回到堤坝上,沿着堤坝向西,我想以罗台村的长度为基准,寻觅汉武帝曾经走过的身影。现在的堤坝,汉武帝是否曾经伫立过,不得而知,但我面前的王河,汉武帝曾长久地审视过;不知我踏在堤坝上的哪一个脚印会与汉武帝遗留的脚印重叠;我伸出手抚摸过的风,也曾抚摸过汉武帝。我在罗台村南的堤坝上来来去去,堤坝北侧一丛成熟蒲公英的果实已经膨出,圆润的球形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一阵强盛的风吹了过来,碾压了那些白色种子,它们纷纷四散开来,随风而走。它们飞翔的姿态,如同时光深处一场大雨的样子,只是不知,这场大雨会落于何处。
风继续吹过,于河岸听风,风里是遥远的呐喊。阳光落于风里,被风载着四处流浪。面对午时太阳照耀下的王河,恍然间,我感觉它们再次被流水充盈。流水无声无息,静默如当下午时的大地。它们一路奔行,带走当下及曾经的一切,只有那些坚强到不为所动的事物才得以留下,包括身后的村庄,虬结的古槐,一些在传说里生存的人与事。已经虚无的,曾经真实存在过;现在真实存在的,必会走向虚无。它们于这世间不管是昙花一现,还是恒久如金石,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万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愿这世间的一切因果,都在岁月里觅得自己本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