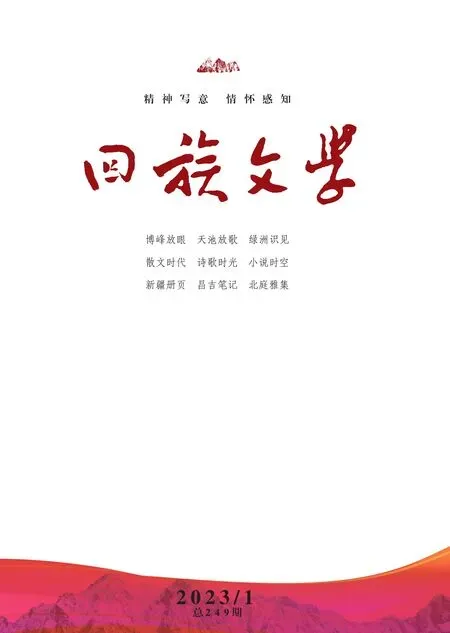场圃集
昌吉,元代准噶尔语,主要释义,意为场圃。可以想见,准噶尔盆地之场圃,沃野宽阔,四境田畴,足资耕牧,是名副其实的场圃。场圃意味着生机盎然,养育冀望。《回族文学》作为昌吉地区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自2022年第一期始,以“场圃集”为长期固定专栏,就是用心良苦为本土各族青年作者尽培育之力,知责于心,相扶相携,奋发有为,跋涉于文学漫漫路。
牵我的灵魂飘回家乡
孙童翌
2019年的时候,我和朋友瓜在木垒书院住了三个月,跟老师朝夕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才19岁,每天傍晚都爬到后山上去,看夕阳落下去又升起来,夕阳看我一天天长大。大多数时候我看不到她升起来,那时候我都躲懒,在睡大觉。在漫天晚霞里,老师掐了麦穗给我们看,一粒一粒、鼓鼓囊囊的,我犹豫了几次,想把麦穗带回去夹在书里,但最后还是撒在了土里。可能它在土里会比在书里长得好些,不像我要多读书才能长得好些。
书院里有许多书,书房里是书,画室里是书,每一间屋子里都有书,不同的房间里有不同的书。2019年的时候我在画室门口上午12点的太阳底下读了《捎话》;2020年的时候在国学讲堂和树屋的阴凉坡里读了《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2021年的时候只过年回了趟书院,其余时间一直被疫情烦扰着;今年在书院读了《本巴》,那天下大雪,我拿了老师新签名的《本巴》在院子里的水缸边,一屁股坐进书里去了,冰溜掉到脖颈里才跺着脚跑到屋里去。
书院的冬天总是很冷清,房檐上坠满了冰溜,雪把孔子像都盖住了,院子里只有动物们的脚印,人都待在屋子里。老师也常躲在楼上书房里不出来,书房里暖乎乎的,老师就光着脚在电脑跟前写作。惊蛰刚过的时候,新爬出来的蚂蚱没想到天气还是这么冷,也躲到书房去取暖。过年的时候倒是不冷清,老师和师娘一般元宵节就会从沙湾回来,师娘会煮热腾腾、好吃的饭邀请村里的好朋友来吃,我连着蹭了两年的年饭。师娘最疼我们,常常做好吃的给我们吃。有一次两个姐姐来做志愿者,和师娘做了好多杏子酱和草莓酱,我最喜欢蘸着草莓酱吃食堂阿姨刚馏热的馍馍,能吃好多。我有天贪凉感冒,师娘大晚上给我煮了姜水端过来,喝了第二天就全好了,师娘跟妈妈一样,都有包治百病的妙招。
冬天老师不写作的时候,总是站在窗户边看院子,我有时去了,也会跟老师扒在窗户上往外看,看雪,看天,看月亮。雪下得很厚,连秋天留下来一截没砍干净的苞米秆都埋在雪里了,老狗月亮不管多冷都在雪地里溜达,几只猫咪却怕冷地在房门口叫唤。月亮很乖,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也不爱动,等人主动凑过去,也不理睬,只偶尔摇一摇尾巴,略表心意。我最近两年冬天回书院,老师都把小黑和星星拴起来,夏天会放开。它们俩冬天总是闯祸,去偷人家的羊吃。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偷羊吃,可能和我在家嘴馋偷偷点外卖一样,喜欢吃点刺激的。
三只狗里我最喜欢小黑,虽然憨憨的,但是眼神里总有一种清澈的愚蠢。2019年我和瓜在画室里住着,带了许多零食来吃。小黑就每天在我们房门口贼着,看到我们吃东西就过来献殷勤,四脚朝天地躺着撒娇。小黑干过许多坏事,有天我和瓜在草丛中看到它在啃玩着什么东西,看它玩得起劲我们也没在意,不一会儿就听见师娘在找老师的布鞋。我们俩猛想起小黑嘴里叼着的东西,都瞬间反应过来。我俩从小黑嘴巴里抢过那只布鞋,趁师娘不注意,偷偷给老师放回去,才替小黑躲掉一顿骂。星星倒是不像小黑那样顽劣,但嫉妒心极重的。我捧着小黑的脑袋夸小黑可爱时,星星就会生气地过来咬小黑的尾巴。但我还是很少捧着星星的脑袋夸它,星星看起来就是狗中的优雅美人,捧着它的脑袋这动作一点也不优雅。我只夸过它毛长得漂亮,摸起来跟狗尾巴草的尖尖一样。
常常有慕名而来的客人在书院里耕读几天或者吃顿晚饭,老师就会带着客人们在院子里走一走,书院里有很多植物,老师就讲花花草草,讲山山树树。国学讲堂门口有好几棵沙枣树,春天的时候花开得很好闻,黄色的小花一串一串的,能吸引许多小飞虫在上面安家。我和瓜十分“狗腿”地折了许多沙枣树枝插在各个房里,想让大家都闻到香味。当晚吃晚饭的时候,我俩冲老师邀功。老师说,花开得好好的,折下来就死了。谁折的?吓得我俩再也没去折过沙枣枝,后来我好几次路过那棵沙枣树都觉得抱歉,连在它树荫底下乘凉都有些不好意思。
院子里千奇百怪的草中,我最喜欢苍耳,小小的刺球,不扎人,粘在裤脚上要用力给它扯下来。但月亮可能不喜欢这种草,苍耳总是粘在它毛茸茸的尾巴上,都撕下来的话,就要撕掉好多毛,尾巴也不好看了。但有一种叫荨麻的草,我讨厌极了。草莓长出来的季节,书院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草莓,我吃过午饭就会随手摘几个吃。草莓地里还长着些野薄荷,泡茶喝很提神。老师要招待客人,喊我去摘两棵野薄荷,我不认得野薄荷,方经理就指给我看,叫我摘。我明明看着那是一棵荨麻,但方经理的笃定让我瞬间怀疑自己的判断,伸手挨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方经理又不靠谱了。那棵荨麻蜇得我手痒了好几天,后来我在那块地摘草莓都一直小心翼翼的。
方经理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一天要搬床,一天要修路。2019年的时候我跟院子里的方经理、王姨、汪姨、杨姨他们还不太熟,一有活要干,就颠颠地跑去。现在倒是变懒惰了,看到有别的人跑去帮忙,我就缩在书房里看书躲懒。方经理带我们干的大多是书院建设的大活,搬床、打扫院子之类的。老师带我们干的大多是些农活,种蘑菇,种土豆。师娘带我们在厨房帮忙,帮厨房阿姨蒸馍馍。奶奶带我们在院子里拔草,赶鸡。每天都有事做,从来也不会觉得无聊。老师有一天要搭葫芦架,我们跟着给树道歉后,总共砍了几十根木头,从后山上搬下来,搭成高高的架子。我那时候在书院长得很好,吃得多身体壮,扛一根小树轻轻松松。今年那个葫芦架上结了好大的葫芦,都快比小知知大了。
小知知是老师的小孙女,我见过小知知好几次,第一年见她的时候还是个小娃娃,见到人会害羞地往后躲。老师好几次叫我回书院陪知知一起玩,近两年的疫情总是反复,我也没能在书院多住几天。今年夏天回书院我和小知知玩得最开心,老师和师娘在屋里忙,知知拿了一根草和我拔河,要把我拽过去,我假装拽不动,再一点一点挪到她跟前,好像她真把一百多斤的我给拽过去了。虽然这次只见了半个下午,但她笑着扑过来到我怀里的时候,我真高兴得不得了。我和朋友千程同年,知知却叫他刘叔叔,叫我姐姐,还是我显得年轻些,刘叔叔太显老了。千程是我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他每次回书院,老师的心就偏到他那里去了,拉着他在书房聊上许多文学上的事。千程学习好,知识广,比起他,我应该就属于那种家里调皮捣蛋不爱学习的小孩,不得大人喜欢。其实我和千程也常有话聊,老凑在一起吹牛皮。奶奶还以为我在跟千程恋爱,偷偷问了我两次,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蹭了千程的热度。
沙湾的土话和木垒的土话像极了,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木垒人,会说方言,所以每次跟奶奶聊天的时候都跟奶奶说方言。奶奶是刘老师的母亲,我是在老师的文字里认识了这位奶奶,老师笔下的奶奶很不容易,辛苦将几个孩子带大。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觉得奶奶很熟悉,就像曾经见过的那么亲切。奶奶好像是院子里的主心骨,每天早上都坐着电动车在院子里完整地绕一圈,将院子的一花一木都记在心里,顾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我每次回书院,奶奶都坐着电动车远远地迎过来,拉着我的手问我最近好不好。奶奶常拿了好吃的出来给我吃,尤其是草莓,夏天奶奶让我一盆一盆摘着吃,冬天还有冰柜里冻着的草莓解馋,哪年回书院没吃到草莓,还觉得遗憾呢。
吃过饭太阳就要落下去了,借着夕阳的光,我坐在门口还能再看一会儿书,傍晚的风说不上温柔,吹过来凉丝丝的,还要披一件夹克。2019年的时候我背了吉他到书院,等到书上的字看不清的时候,我就坐在门口和瓜唱歌。那时候老师和师娘住在上面,离我们很近,每天傍晚,老师和师娘都听着我们的琴声,坐在一起说话。我们唱歌的声音招来小黑和星星,方经理有时候也和我们混在一起玩,跟我们一起唱歌。天总是唰的一下就黑了,从一弦扫到六弦就看到星星一颗两颗地冒出来了,在天上编成谱子给我弹。等黑透了,院子里就没人了,大家都钻到屋里去。我们晚上不开灯,开了灯小飞虫就要钻进屋子里来,绕着灯转,扰得人心烦。晚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就和瓜缩在被子里聊天,有时候聊着聊着我就失去意识睡着了。有一年夏天,那段时间书院没什么客人,晚上我一个人住在画室,倒是有些害怕,小黑在外面一叫,我就更害怕了。老师说狗晚上是保护院子的护卫,我偷偷掀开窗帘一角想看小黑和妖魔鬼怪大战的英姿,可它和夜早就融在一起,只有尾巴尖儿上的白毛没有参与战斗。
我和老师聊过鬼魂,聊过我小时候的梦。第一次跟老师聊《捎话》的内容时,我觉得《捎话》就像我梦里的故事,飘在我梦里的鬼魂和老师书里的鬼魂是一家的,他们在我的梦里聊天,不知道会不会飘去老师的梦里聊天。《捎话》里有头小母驴,今年7月份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一起跟《文学的日常》摄制组去了驴场,驴场里有许多驴,每头驴都与众不同,每头驴都急着在镜头前展现自己最美的模样、最动听的声音。我小时候很喜欢学驴叫,外公家前面那户人家的门口一直拴着一头驴,每天都昂叽昂叽地叫。我可能是耳濡目染了,学驴叫学得很像,连驴听了都要怀疑的那种。可惜我只学会了驴叫的声调,不懂驴语的语法规律,没办法跟驴交流沟通。但老师好像能听得懂驴说话,和许多驴都成了朋友。
我有时觉得老师像朋友,会跟我聊些不着边际的梦话,跟我讲梦里的故事;有时又觉得老师像父亲,唠叨我许多事,叫我早点找男朋友,早点留长头发;有时又觉得老师就是老师,问我有没有好好学习,教我多读书;或更多的可能是灵魂的引领者,我常常在老师的文字里看到我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家乡、熟悉的梦。在梦里,老师牵着我的灵魂,一路摇摇晃晃回到家乡。《一个人的村庄》里写“文学是做梦的艺术”,我觉得许多事都是做梦的,文学也是,生活也是。
认识老师,做老师学生,也是一场梦。真实的梦。
纸牌情理
王 帅
父母亲20世纪70年代初从四川宜宾不远千里来到新疆,这一来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姊妹四人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四川宜宾成了我们记忆深处的故乡。虽说没在那里生活,却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温度:景美,人勤劳好客,爱好打牌。自然我的父母也不例外。
初到新疆,父母亲扎根在红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那时穷,农活重,父亲生病无钱医治,落下病根“气管炎”,无法下地干活。家里农活全靠母亲和两个姐姐,生活勉强可以维持。那时父母打牌是苦中作乐吧。劳累了一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打打牌,输了就刮鼻子、贴纸条。我和弟弟年龄最小,老是输,又输不起,总要捣乱耍赖皮,还是逃不过贴一脸的纸条,纸条随着我俩的呼吸一起一落,他们却笑得前仰后合,一天的疲惫在这笑声中也就消散了,打牌成了那段艰难岁月不可或缺的佐料。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姊妹四人都搬进县城,成家立业,为人父母。二老年纪也大了,是时候该享享清福了。我们做儿女的一合计,在县城买了电梯房,将二老接到城里生活。凭自己的能力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我们做儿女的甚是欣慰。
初到县城,父母显得格格不入。陌生的邻居,紧闭的房门,远离亲朋好友,没有牌友,二老整天郁郁寡欢。只盼望着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围坐一起,打打牌,拉拉家常。以城里人自居的我们,打牌早已淡出了我们的生活圈,我们宁可抱着手机刷抖音,聊微信,看朋友圈,听歌看电影,也不愿再打牌。人是回家了,打牌的事从未有人响应,自然父母的牌局也从未组成过。
一次我回父母家撞见父母打牌,一发三沓,一人选一沓,只不过,有一沓牌始终没有翻起来过,他俩就这样一直玩着。我们回家探望,十有八九都会撞见父母两人打牌,永远有一沓牌不曾翻起过。看到此情此景,我不免生了怨气,同事的父母退休了去健身、写书法、跳广场舞,自己的父母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只会打牌。我唠叨得多了,父母赶紧把牌收了,从此不在我眼前打牌。我一走,他俩照旧玩起来,我的唠叨从未停止过,父母打牌也不曾停止过,只不过牌局从家里搬到家外的小广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他俩打牌变成了四个空巢老人一起打牌,打牌时父母好像变了个人,有说有笑,精神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回家,父母又不在,不用想,一定去打牌了。我气冲冲跑到小广场,打断他们的牌局,硬是把父母拽回了家。一路上我边走边唠叨个没完。回到家,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一脸的严肃,倒出憋在心里的话:“我们老了,不中用了,碍你们眼了!你们都有自己的小家,工作也忙,我们不好叨扰你们,就这点乐趣,你们也要干涉。我们打打牌,拉拉家常,动动脑子,活动活动手指,有什么不好,不至于老了得老年痴呆,拖累你们。孝顺孝顺,先顺才有孝。”我哑口无言,父亲积存已久的心里话,字字像针尖扎在我的心上,隐隐作痛。
父亲说的没错,平日里我们姊妹四人总是各自忙着工作、家庭、应酬,确实很少回家探望,更别说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了。逢年过节钱一给,东西一买,实在忙了就干脆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从未真正想过父母需要什么。细看父母,他们脸上不知何时已布满岁月的印痕,两鬓斑白,满脸堆积着皱纹,腰弯了,背也驼了,二老苍老许多,我们却不曾察觉。我不禁眼眶湿润。
从那过后,我不再反对父母打牌,顺着二老的心意,碰到他们与牌友打牌时,我会送去一些糕点和水果。父母嘴上说不要乱花钱了,但我知道他们心里美滋滋的。闲暇时,我跟他们一起打牌,听他们话家常。说也奇怪,不反对父母打牌,他们反而不那么热衷打牌了。父母也“洋气”了起来,与时俱进了,淘汰了老年机,用起了智能手机,和牌友们一起健身、散步、K歌,学习如何养生……他们的变化着实让我惊喜又意外。
如今回家,总是我在张罗着打牌的事。父母一人一沓,我拿起之前那沓未翻起的牌,我们边打边聊,我饶有兴趣地听着,听父母聊哪个牌友的孩子如何孝顺,聊小区里最近发生了哪些新鲜事,聊我儿时的趣事……
后来,不止我,只要我们姊妹四人同时回家,便与父母围坐一圈打牌。虽然牌在手上,心思却不在牌局上,没打几圈,一家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有说有笑聊着家常,父母总是忆苦思甜,我总是自曝儿时糗事。有时聊得起劲,竟然忘记了打牌,该谁出牌。屋里笑声不断,回忆也就不断,纸牌让一家人的心贴得更近了。
我终于明白,父母的牌局其实不是什么牌局,他们爱打牌,爱的是牌桌上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热线电话
董应范
时针已经指向11时,夜晚柔和的灯光漂白了四周的墙壁。窗外春雨一根根线似的打落下来,清脆入耳。
灯下,我拿起手机,刚打开微信,视频铃声骤然而起,扫了一眼屏幕,没错,是爱妻的电话,又到视频时间了。恍惚间,我又看到了爱妻的身影,又听到了爱妻清脆的笑声。
上世纪末,经过一年的相识、相知、相恋,我和红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然而,另一件让人头痛的事又摆在面前:我和爱妻分属两个团场,也就是说,结婚意味着聚少离多。好在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两地分居,更多的是对对方的牵挂与思念。自此,通话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宛若“红娘”,一解我们相思之情。我们约定每晚11时通话。
我们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对方打电话,总感觉这样可以超越时空,和对方的距离更近一些。每个夜晚,我与妻都会拨通那串倒背如流的号码,倾听对方的欢乐、苦闷与忧愁。电话这头,是我的思念和牵挂;电话那边,是爱妻的叮咛和希望。电话一拨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电话中,我们只是把千般的情,一句一句传进了对方的耳朵;将万般的爱,一丝一缕倾注在对方的身上,滋润着对方的心田。不知有多少个寒来暑往的夜晚,通过热线电话,找到了自己向往的归宿。电话中,面对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我们尽情地体味着家庭的温馨。
每个夜晚按时倾听对方的声音,根本不理会电话费的高昂。电话情思伴随着我的生活,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也给了我巨大力量。
那时,我在某企业从事政工工作,或许是经常写写画画的缘故,每天都感觉弦绷得太紧,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每每此时,有多少情思多少感受要倾吐,而爱妻是我最好的听众;当我感到高兴时,又有多少欢乐多少激动要与她共享啊。生活中不仅仅有阳光,也有眼泪。在我最痛苦、最迷惘无助的时候,是爱妻安慰我,鼓励我。2005年,我因工作调整不如意,陷入苦闷。为了鼓励我早日振作起来,爱妻早、中、晚都会通过电话鼓励我:“任何时候都要坚强。只要振作起来,迈过这个坎前面就是艳阳天。”尤其是夜里通话结束时,爱妻都要重复一句话:“祝我的夫君天天时时开心快乐,夜夜好梦连连!”这种亲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在爱妻的鼓励下,我很快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一晃就是7年,终于,组织上把爱妻调回同地工作。望着妻子脸上留下的岁月痕迹,我本以为持续了整整7年的牛郎织女的问题解决了,热线电话的日子也该结束了,然而,2021年3月16日,爱妻来到我办公室,告知我因工作需要,她要去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五十团“访惠聚”工作队工作两年,我的脑袋瞬间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蒙了。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就这样,热线电话再次在我们之间上演了,只不过这时的热线电话改为热线视频了。每次视频时,爱妻的笑容是那么灿烂,当初就是她那纯洁无邪的笑容打动了我的心,决定用一生的耐心和爱心呵护她。
遥遥相望,思念绵绵。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爱妻。我知道这就是牵挂。牵挂是一种美丽,它需要凭借无尘的心灵才能感应,就像清风吹皱了一池的微澜,让人心儿颤颤的,且时间愈长愈珍贵愈不可舍弃。我也深知,爱妻也有着和我同样的感悟。我们都为彼此心灵的驿站留下一份牵挂。我和爱妻的爱情是一种朴素的爱,是我在平平淡淡真真实实的人生旅途中收获到的美丽。爱妻是上天馈赠给我的最好的一份礼物,我将永远珍惜,永远永远!
做了20多年夫妻,我们感激这世上还有电话,让我们可以随时听见彼此的声音,视频让我们天天可以“看到”日思夜想的对方。
我与爱妻的热线电话,就是“鹊桥会”。满屏微笑的爱妻又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