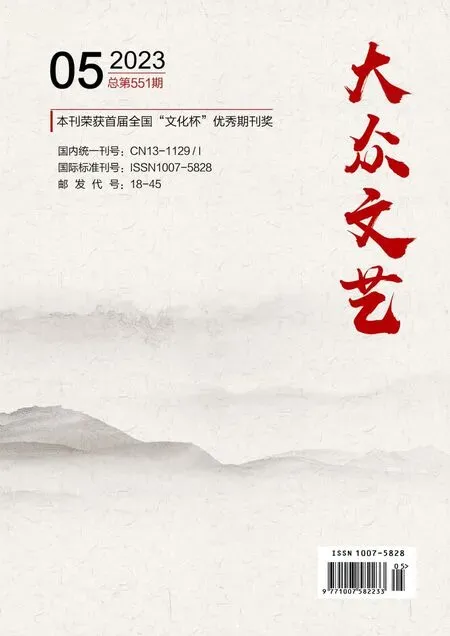音乐修辞视野下的中国钢琴音乐分析
孙庆瑜
(信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修辞”一词来源于文学,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期。音乐修辞和文学中的修辞在含义和作用上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比如说在作用方面,和文学修辞一样,音乐修辞也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内容的色彩浓度。而要想区分这两者,我们可以先对修辞一词进行解构:修,乃修饰、修正;词,意为词语、字词。合在一起理解修辞的含义便指:对词语的修饰或对文辞所表达内涵的修正。因此,音乐修辞也就可以解读为“一种用于装饰音乐文字的手段”。
文字是“人类用符号记录表达信息的方式和工具”。文字与口耳相传比起来,能够很大程度提高一门学问或技术传播范围的横纵向距离。可以说,文字是文明发展的基础。音乐能够和语言、文学等艺术形式一样传播、继承、发展,正因为它也是有文字的。声音由物体的振动产生,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谱、音符、节奏、和声、体裁等,这些便成为音乐的文字。最早的音乐只有简单的记谱法和音符组成,因此所有在它基础上的变化尝试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音乐“装饰”。[1]作曲家出于自身的表达欲望加上社会环境的变革,不满足于单一的旋律,于是大量与其不同的节奏型、体裁、和声产生了,符合作曲家表达情绪、情感需要和时代审美的留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成熟的风格体系,那些曾带有“装饰”意味的风格和作曲法则成了常规手段,不再是与众不同的,也就无法起到特殊效果,最终成为音乐文字的一部分。这些音乐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再度发展,产生新的表达手法。不难看出,音乐的文字相比于文学的文字具有特殊性、抽象性、时代性,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同一时期内作曲家们普遍使用的作曲法则就是音乐的文字,而文字中与此截然不同的特殊处理就是“装饰”,也就是所谓音乐修辞了。
音乐中的修辞现象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第一是作曲家创新的作曲技术、和声连接、音乐色彩,这些修辞手法能够带来音乐风格和音响效果的全新变化;第二是作曲家对曲目的特殊处理,某些音乐片段或整体风格和他本人或同时期普遍的作法明显不同,这种特殊化的音乐是有原因的,作曲家为何故意创作出具有“分裂感”的音乐?作曲家的意图和音乐具有的全新意义,需要诠释者进行分辨和解读。
阐释者有没有必要从修辞的角度解读音乐,还是忽视这些特殊的处理将它们视为音乐整体的一部分?[2]当我们发现,那些具有修辞意义的音乐实际上要么几乎等同于发展前沿上的音乐,要么便蕴藏着作者本人独特的个人表达时,答案其实不言而喻:已经发展成为一般规则的作曲法则不能体现音乐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作曲家的个人烙印,创新的探索和与众不同的处理才能。
一、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第一阶段
五线谱和现代钢琴在19世纪时传入中国,随着传教士的礼拜活动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而后教会学校逐渐增多,它们是中西文化重要的交流场所,钢琴音乐艺术随之逐渐兴起,19世纪末在年轻一代中得到高度重视。20世纪初,中国作曲家开始尝试创作钢琴音乐,这便是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开始。
钢琴音乐文化相比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记谱法、发音方式、音乐体系、用途都有着鲜明的差异和“对比”。如钢琴是一种基于五线谱的键盘乐器,而中国传统记谱法的基本旋律单位是“谱字”,在正确的乐句划分下没有固定的节奏,每个乐师解读传统乐谱不同演奏的效果便存在不同,演奏过程基本等于乐师的二度创作;钢琴以及西方的乐谱基本旋律单位是音符,节奏固定,演奏家需要严格按照乐谱进行演奏等。中国音乐历史悠久,有强烈的民族性和独特性。民间音乐广泛运用五声音阶,地方民歌和戏曲众多,风格多样,还有大量“音乐图像化”作品,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特点在于“意境”和“腔韵”,“韵味”是中国传统音乐作曲家和欣赏者共同追求的首要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对音乐的精准性和系统化记录退居二线。
中国作曲家对钢琴音乐探索初期的特征表现为以西方现代作曲技术为基础,加入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如地方民歌的旋律、某种民族器乐的音色、使用五声调式等手法试图“组合”出归属于本土的钢琴音乐文化。这种思维使钢琴音乐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意义——它诉说着中华民族赋予其的精神内涵。这是钢琴音乐的根本创新。因此,具有这种“组合”思维的中国钢琴音乐便带有强烈的修辞意味。这种尝试属于起步阶段,它可以直接使钢琴音乐带有明显的中国音乐特征,但“组合”阶段同时意味着音乐民族化手段比较单一,缺乏作曲家对中国钢琴音乐的个性表达,作品数量比其他两个阶段少等特点,它是简单的“合并”,不是灵活的“交融”。从这一角度分析,以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为起点,到艺术歌曲的伴奏,如青主的《大江东去》黄自的《玫瑰三愿》,以及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等拥有“组合”特点的钢琴作品都可划分进此阶段。
二、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第二阶段
走过尝试阶段,中国钢琴创作迎来了繁荣时期,全新的钢琴音乐产生了。这一时期大量钢琴作品延续了中国传统音乐追求“韵味”的创作理念,讲求情景交融,数十首由中国民间音乐的曲调或传统器乐曲运用西方作曲技术如复调、变奏改编产生。如贺绿汀《牧童短笛》陈培勋《思春》李英海《夕阳箫鼓》王建中《浏阳河》储望华《二泉映月》[3]。此外还有一类钢琴曲创作理念与中国20世纪社会背景“危机、战争和革命”息息相关,如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钢琴独奏组曲《娘子军操练》《奋勇前进》,钢琴协奏曲《黄河》。
这一阶段的核心是“交融”:钢琴音乐的作用渗透进了社会中,传统器乐声乐的特点与钢琴弹奏技法交织使音乐的艺术性更加丰富。在简朴的“组合”基础上创作理念和作曲技术双双更进了一步,和声织体更加复杂,体裁更加多元,作品数量也比第一阶段更多。这一阶段作曲家所思考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创作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上,从作品中明显的大量民族性和声、对传统器乐声乐戏曲演出音色直接的模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作曲家普遍认为,中国的钢琴音乐就是融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钢琴音乐。这是对“中国风格”表层的理解,如果说谱例是一部钢琴作品的外衣,作曲家的精神是作品的内在,那么第二阶段设计的重中之重,便在这件外衣和其款式、剪裁上。这也是二三阶段区分的依据。从此开始,钢琴音乐实际运用到宣传民族精神、影视配乐、音乐会中。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例,这一阶段的创作无论在风格、结构、和声连接还是在对整体钢琴音乐的意义上都有巨大的特殊性和创新性,但作曲家在这一阶段还是在用中国传统音乐开发中国钢琴,没有用自我内心主导创作,因此这种做法虽然因其民族性和声使中国钢琴音乐与西方钢琴音乐区分开来,并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但形式、体裁沿用西方缺乏突破,创作理念方面很难看出作曲家对庞大中国多角度的个人探索和态度。
以《牧童短笛》为例。《牧童短笛》是一首典型中西思维交融成功的钢琴作品。成功之处体现在这首作品拥有跨时代的生命力。从谱例分析,首先其使用了五声G徵民族调式[4],并且从标题表面看来所描绘画面事物总共有三:显性的是牧童和笛子;隐性的和联想的是乡下田野里放牧的场景。并且可以说我们看着这个标题非常容易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大约是在一个微风吹起第一支柳条的季节,村里一个小男孩骑在牛背上吹起放牧的笛声,伴随着悠扬的笛声,牛儿闲闲地吃着草,踱着步。这是因为标题由微见著,虽然惜字如金,却直接联系到我们血脉的深处,几乎能使每个中国人都能产生文化认同感: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牧童和牛的组合是农耕文明的一枚代表标签,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的一个剪影,也是每个中国人最熟悉的事物,童年温馨的记忆。这些浓厚的独特本土性设计是作品的灵魂,它们根植于西方规整的单三部曲式结构之内,赋予钢琴音乐全新的意义。
因重意而不重技,主调音乐是我国音乐创作的主阵地,而西方音乐由于记谱法和和声体系的发展,十分推崇复调音乐。《牧童短笛》借鉴西方复调作曲技法,使中西音乐文化特点在《牧童短笛》中相融,这种“融合”使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横向拓宽,也是钢琴音乐风格上的修辞。
三、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第三阶段
由表及里,由质变到量变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外表”中国化的钢琴音乐也是如此,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第三阶段的标志便是作曲家个人精神世界由隐性到外显的明显转变。中国素材和表现形式不再作为作曲家的关注点,而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点缀”在作品中。这一时期中国风格不仅表现在作曲手法上对民族元素的运用,更体现在作曲家本人高度个性化的创作角度、思路、目的,可能在结构、节奏、和声、风格方面都是全新的,个人的,带有修辞性的。如作曲家梁雷和他的作品《反钢琴》《我的窗》《千山万水》《潇湘》等。
比如说《反钢琴》,梁雷创作灵感来源的自述如下:“……一天傍晚,他在山林里散步的途中忽然遇到了突来的一场暴雨,雨势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眼前的所有景象都被大雨所遮挡。‘我的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雨雾,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把我团团围住,风声、雨声、青蛙的叫声……我完全沉浸在其中,这就是交响乐。’他富有感染力的表述打开了我想象的空间,激发了这首《反钢琴》的创作灵感。”[5]由此可见作曲家的创作动机的出发点来自自我表达的需要,有着特殊的目的。这个表达的表现形式和作曲技法便完全为更好地突出表达目的而服务。《反钢琴》水平线式的乐谱、包含声音和静音时间的音符值、时间流,还有利用塑料泡沫敲琴弦、用塑料棒或细长的玻璃瓶拉琴弦、手掌敲击低音琴弦等特殊演奏技法即为作曲家“音响世界”理念的表达方式。梁雷将钢琴“世界化”,钢琴的意义本来是演奏乐器,在这里改变了,作者将人们每日所处的周遭的环境比作钢琴,使用17种不同物体在钢琴不同部位制造出不同节奏、音色、音量的声音比作生活中由于自然环境或人们使用各种物体所导致的细微声音,这种类比修辞使作品的音乐性被无限压缩,突出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和启迪性。其目的在于给作曲家们传达生活中看似普通、普遍声音的多元与美,让听众从对音乐审美的刻板印象中跳脱出来,“逼迫”听众注意到被忽视的声音,扩大了音乐美含义的范围,使作曲家们发现一种获得灵感的新的途径。
可以说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与武学的发展规律有很多相似之处,武学境界第一层为“手中有剑,心中也有剑”,第二层为“手中无剑,而心中有剑”,第三层为“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这其实就是指对武学的熟练程度,剑法的形式和技术真正熟练了,运用中是不会一板一眼和刻意使用的,倒会随机应变或者新招频出。实际上音乐也是如此,那么达到“心中无剑”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便是新旧交替的契机,这个“新”将体现在音乐的技术、形式、意义、作用上,是全面的革新。
结语
作为外来文化的钢琴音乐自传入中国后的演变历程,笔者从作品本土化的开始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根据所创作曲目不同的创新之处将其分为“组合-融合-个性化”三个层次,每一层次都代表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质变。其与上一个区分的判断标准为作曲家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中所蕴藏的创新点。三个阶段共同以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为动机。其中第一阶段是“尝试时期”,其特殊之处首先在于,钢琴音乐首次由中国人编写出来,这是根本的变化,它直接扩展了钢琴音乐的内容和含义并从中产生了一些全新的问题:钢琴音乐该不该在中国发展?或: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钢琴音乐?围绕这些问题,作曲家们一边了解西方作曲技术,一边在钢琴音乐的创作中加入了一些民族调式、模仿弦乐的旋律等。这些尝试和模仿的修饰明显具有局限性,无法说是审美成熟的中国钢琴音乐,但它们开启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先河,是前所未有的音乐处理,具有特殊的修辞意义。
从音乐修辞的角度看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层次就是从“新”看其发展。在第一层次“新”体现在成熟的西方作曲技法、和声体系与片面的中国音乐元素首次结合,回答了钢琴音乐该不该进入中国的问题。这一层次的标志为作曲家尝试加入本民族的音乐元素进行创作,但加入的元素因时代背景和钢琴文化传入中国时间还尚短的原因较少,曲风、结构、节奏、和声连接等安排都比较保守。
第二层次的“新”体现在中西融合技术上的成功,此阶段中国钢琴音乐包含传统声乐器乐改编曲、受西方无标题无调性等现代技法影响产生的钢琴曲。这一层次的音乐作品回答了和中国钢琴音乐如何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现代化的问题。划分进这一层次的钢琴音乐在技术上是成熟的,和声安排上具有民族性、复杂性。众多中国标志性元素被作曲家刻意构入乐谱中,在旋律、节奏、结构、标题等音乐的各个方面悉数融合。换句话说,第二层次的中国钢琴音乐就是民族风格的成熟了的中国钢琴音乐。
第三个层次代表在技术成熟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作曲家独特的个人风格作品,中国钢琴音乐完成了由符合大众审美的创作跃升至记载自我探索的质变。这一层次的音乐作品回答了中国钢琴音乐该不该遵守西方和声学,遵守到什么地步这两个复杂问题,代表了个人意志的觉醒。无论是在音乐作品的意义或是手法上,拥有强烈个人风格的钢琴音乐便可以划分进这一层次。如果说第二层次代表中国钢琴音乐在技术上的成熟,那么第三层次即是精神上的成熟,这是根本的创新,目前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正处于第三阶段,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个体分析,众多具有修辞意味的作品不断产生,相信会极大丰富现有的作曲法则,在音乐意义、对社会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角度方面更加多元化,为下一个发展的循环积累优质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