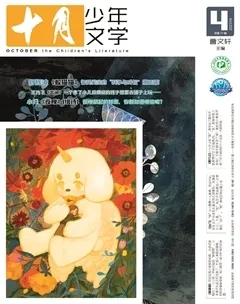儿童游戏视域下的战争书写
《躲猫猫》是舒辉波继《老狼老狼几点钟》之后又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儿童小说,在历史书写与儿童经验的呈现之间,作者延续了《老狼老狼几点钟》的处理方式——以儿童游戏为载体,来书写宏大的战争主题。具体说来,躲猫猫承担了双重的叙事功能。先来看作为游戏的躲猫猫,在秋水河村,心安躲在麦秸垛的洞穴中等待伙伴们和奶奶的寻觅,与田野间麦子躲在雪被子下面睡觉过冬形成了某种呼应,躲猫猫在“序幕”中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形态出场的,它承载的是一种古典形态的乡村经验,麦子的生长,四季的轮回,躲猫猫在时间的流逝中平添了些许童趣。躲猫猫的游戏传递出心安内心深处的孤独感,这种与生俱来的孤独在奶奶的关爱与理解下多了一丝温情。耐人寻味的是,在小说的第一部中,作者饶有兴致地记录了心安、保庆、子聪在打谷场上的躲猫猫经历,“攻占”“攻击”“佯攻”“掩护”“迂回”“敌人”“袭击”等词语令这场游戏具有某种战争冲突的意味,军事术语的修辞和运用预示着作为宠物狗的“躲猫猫”与战争之间的隐秘关联。
在小说中,作为宠物狗的躲猫猫充满了传奇性。与它的母亲白灵一样,这只来自叔叔徐佩玉家的小狗天生会捕鱼,实属狗中翘楚。对于心安而言,躲猫猫拯救了被马蜂蜇伤的心安,即使它的嘴巴被马蜂蜇后肿得老高,也毫无怨言。躲猫猫与心安之间的友谊因马蜂事件而变得更加牢靠,心安对躲猫猫的喜爱与感激是不言而喻的。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躲猫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机智地帮助大家侦察敌情,在紧要关头克服重重困难精准地传递了庆余叔一行人平安的消息。毫无疑问,躲猫猫身上聚集了勇敢、忠诚、机智等品格,经过战争的磨炼,它从一只被心安父亲嫌弃的小狗,成长为众人得力的助手。
同时,躲猫猫还是审视心安与父亲徐先生之间代际冲突的绝佳窗口。心安从叔叔徐佩玉家领养了躲猫猫,招致了父亲强烈的反对。在躲猫猫拯救心安于危难之后,父亲的态度才有所缓和,“约法三章”(不许进祖屋、不许与家禽抢食物、在院子里守家)严格地限制了躲猫猫的生存空间—牲口棚。表面上看,父亲极度排斥躲猫猫,是因为他对之前那只名叫玳瑁的猫打翻祖宗牌位的行为十分不满。从深层的心理动因来分析,实则是作为私塾先生的父亲的文化性格使然,儒家的礼教早已刻入这个中年男人的骨子里:他从始至终竭力维护宗族祖先的至高地位,他应兄弟徐佩玉之邀做“村民自救会”的会长,在心安母亲下山连摔两跤时他甚至发出了“这双小脚啊”的感慨……大男子主义与爱国精神有机地统一于徐先生身上,他的性格是一种复杂、矛盾、多样的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游戏的躲猫猫再现的是一种缓慢的、充满诗意的乡村生活,作为宠物狗的躲猫猫则代表了一种暴力的、血腥的、反人性的战争状态。如果说小说的前两部重在呈现战争来临前人们的心理嬗变的话,那么小说的第三部则是聚焦战争状态下人们的生存处境,那是一部包含着家破人亡、生离死别、家仇国恨的血泪史。在小说中,既有如“蝌蚪”般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土匪,也有与日本人积极战斗的张队长、年轻人“兔子”等英雄,还有徐先生、庆余叔等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躲猫猫》的人物画廊。同样,我们更不能忘记惨死日军刀枪火炮下的九香婶、保庆奶奶、庵生娘、庵生爹……这些底层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揭示出战争的残酷与无情,促使我们不断地反思战争,并以此来唤醒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