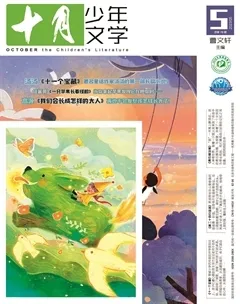我们会长成怎样的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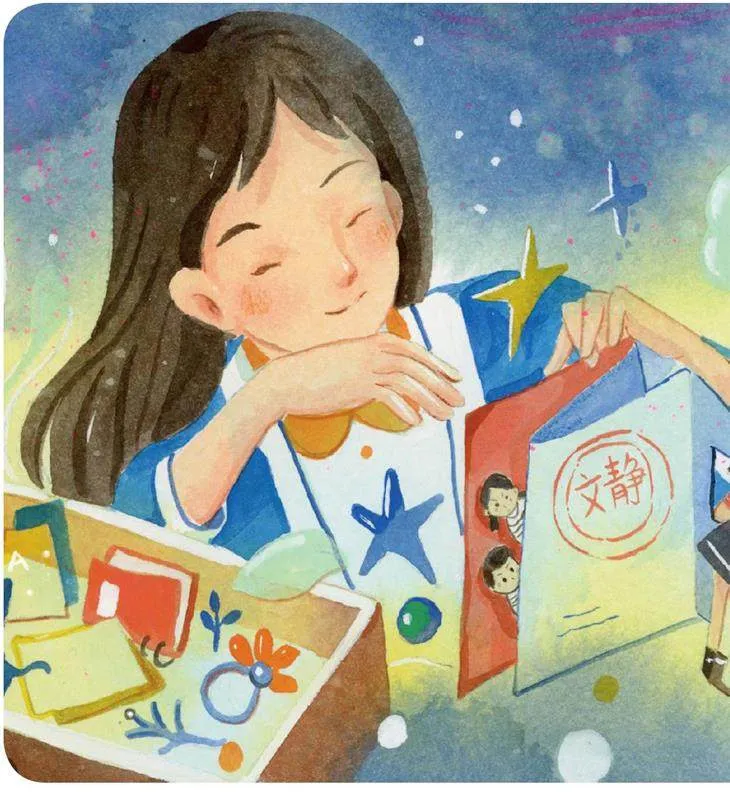
1
小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怎样的孩子,也没想过以后会长成怎样的大人。所有对自己的认识,都源于家长和老师的评价。
他们说我内向,我便更加不爱说话;他们夸我听话,我便越发服服帖帖;他们批评我不爱运动,我便理直气壮地体测不及格;他们预言我有绘画天赋,我便在心里种下一个画家梦想。大人说什么我都深信不疑,并下意识地将其当作行为参考——我没有独属于自己的鲜明性格和人生目标,因为一切都尚未成型,模糊不清。
每个同学都有一本红皮的评估手册,里面有小学生守则、成绩栏和教师评语。学期结束时,班主任会在手册里登记期末成绩,并根据每个人的日常表现写下有针对性的话,比如“活泼开朗、乐于助人”,或者“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每年得到的评语大同小异,基本都是“踏实好学”" “内向、胆子小”“班级小画家”之类。
“这就是我。”看着老师的字迹,我对自己说。
2
表弟乐乐没有评估手册,他才上幼儿园。有一次我们偶然在书里看到对血型的解析——不同血型的人会有怎样的性格,适合什么职业,对应什么幸运数字和花卉。那种东西当然是纯属娱乐,但我和乐乐都当真了。我们郑重其事,紧张兮兮,兴奋得两眼放光,以为可以借此解开自己的命运之谜。
我们谁都没验过血,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便只好从性格来逆推:书里说A型血的人性格比较文静、稳重、执着。没错,那正是我!大人们不都说我文静吗?就这样,我高高兴兴、顺顺利利地敲定了自己的血型,从而得知自己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教师、秘书、护士,或者艺术家。
对此结论我相当满意,这几个职业都喜欢得不得了,特别是教师。我还曾像模像样地扮作老师,给表弟和邻居家小妹上过一节美术课呢。郁闷的是,他们连一只猫都还没画完,就东张西望扭来扭去,一刻也坐不住了,任我敲黑板扔粉笔也无济于事。唉,当老师真难。
“太准了!”我使劲儿戳着书感叹道。
乐乐很是着急,他也想赶紧弄清自己究竟是什么血型,未来会做什么职业。
我一条一条给他念:“O型血的人比较慷慨大方,热情活泼;AB型血的人比较神经质,偏激易怒,有点儿吝啬……”
“吝啬是什么意思?”
“就是小气,抠门。”
乐乐眨眨眼,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有些难为情:“那,我应该是AB型血。我很抠门。”
嘿哟!他还蛮有自知之明嘛!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要知道,以前妈妈和小姨带我们去公园玩,要是我掰了他一块面包,他必须咬一口我的火腿肠心里才能平衡。而且就在几天前,我们还刚刚因他的抠门而打了一架。
说来好笑,那天小姨给他新买了一盒带青苹果香气的油画棒。我闻了闻,突发奇想,把画纸塞进油画棒盒子里。他十分警觉,问我要干吗,我说想让画纸沾上一点儿香气。
“不行!”他赶紧把画纸抽出来,“你不能偷我的香气,香气会变少的!”
我瞪大了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又没用他的油画棒,只是借点儿香气而已啊!
就这样我们扭成一团打了起来。小姨闻声赶来,把我们扯开,问怎么回事。我解释之后,她也觉得不可思议:“不会吧……他肯定是怕你抢他的油画棒,不可能因为什么香气。”
我和乐乐都气得够呛,并扬言再也不跟对方说话了。然而——总是这样——不出半小时,我们又亲亲热热地挤在一起玩了。
总之,我们稀里糊涂连蒙带猜,自以为搞清了血型,还为此扬扬得意了好几天。
A型血的我,幸运数字是3和6,幸运花卉是满天星。从此之后我每次设置密码都会用到这两个数字,还特意跑去花店,看了看满天星长什么样子。
妈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根据我和你爸的血型,你不可能是A型血。如果真是,那只有一种可能: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可能是当年在医院抱错了。”
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起来。照照镜子,再看看照片,千真万确,我跟爸妈长得都挺像,应该是亲生的。那,血型又该怎么解释呢?A型血的性格和职业,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啊。
亲生父母和A型血,我都无法割舍,真够纠结的。直到几年后,我和乐乐因为疫苗的事而去医院抽血,顺便验了一下血型,谜底才真正解开。
化验结果令我们大跌眼镜:我并不是“文静稳重”的A型血,而是“活泼热情、浪漫稚气”的B型血;乐乐也压根儿不是“抠门”的AB型血,恰恰相反,他是“慷慨”的O型血!
我俩傻了眼,大脑一片空白,感觉三观尽毁,天翻地覆,一片狼藉。这,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
妈妈在一旁偷着乐:“我早跟你说了,你不可能是A型血嘛!”
3
大约在小学四年级前后,我的身高像失控的火箭,一个劲儿猛长,长到我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买新裤子。
我倒也不介意买裤子这件事,反正用的也不是我的零花钱。我所苦恼的,是班里座位按个头排,我个头高,就得往后坐,可那时偏偏又有些近视,坐在后排看不清黑板。跟妈妈说吧,实在害怕挨骂——她一提起近视就原地爆炸,好像我害的是什么不治之症,要把全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走投无路之际,我只好在深夜跪在小床上,虔诚地向苍天祈祷别再让我长高了。很遗憾,不知是苍天没接收到还是接收到了懒得搭理,我仍旧静悄悄地长,像一株植物。
表弟乐乐上小学了,小脸圆鼓鼓、红扑扑的,特别受老师喜爱。他也在长,可惜不是纵向,而是横向。邻居们叫他“小胖墩”,哥哥叫他“胖墩儿”,弟弟叫他“胖哥哥”,总之少不了一个“胖”字。当然也有人觉得矮矮胖胖挺可爱,但更多的时候,他受到的是冷嘲热讽,其中不乏大人们的故意刺激,为的是督促他减肥。
乐乐想没想过减肥我不清楚,但他做梦都想长高这是真的。他疯狂地爱上打篮球,还每天喝牛奶、拉伸腿上的韧带,据说有助于长个子。
有一天,他挥舞着一张刚刚冲洗出来的合影,连蹦带跳地冲过来,脸上洋溢着梦想成真的狂喜:“快看快看!我已经和姐姐一般高了!”
小姨拿去瞄了一眼:“不可能,只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他不服气,非要站过来跟我比一比。果然,还是差了一大截。看他心灰意冷怪可怜的,小姨安慰道:“你比姐姐小三岁半呢,急什么!再说,男孩子本来就比女孩子发育晚……”
还有一次我们吃东西,馒头掉在了地上。他捡起来看见上面沾了灰尘,正要扔,我随口道:“听说,吃灰尘能长个子。”
“真的?”
我用力点点头。千真万确,我没有胡说八道,也不是搞恶作剧逗他,我是听家里大人说的。或许大人只是开玩笑,但当时幼稚的我对此毫不怀疑,并牢牢地记住了。乐乐也当真了。他盯着雪白馒头上那层若有若无的土灰色,略作迟疑,一口咬了下去。我惊得眼都要裂开了——知道他想长高,但没料到竟能到这程度。我笃信吃灰能长个子,但无论如何也不会冒着拉肚子的危险去吃灰的。幸好当时没有大人在场,不然他免不了一顿揍,我恐怕也在劫难逃。
真遗憾,那时我们做的所有天真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我依然那么高,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使劲儿眯着眼也看不清黑板;乐乐依然那么矮,也不知他有没有背着别人再吃几次沾了灰的馒头。我们都认命了,以为这就是我们长大后的样子了。
大人们都说命运爱开玩笑。几年之后,玩笑开到了我和乐乐头上。先是我变得越来越矮——当然不是个头缩了,而是身边晚发育的同学开始奋起直追,个头噌噌噌往上蹿,而我却像冻住了似的,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初中入学时按个头排座位,我坐倒数第二排;然而毕业时,我已经不知不觉坐到了正数第二排……直到今天长成了生理年龄层面标标准准的大人,我也没再长高哪怕一毫米。
大概是苍天被我的虔诚打动,最终应允了我的心愿吧。我为十几年前愚蠢的祈祷痛心疾首、捶胸顿足。
再说表弟乐乐:他如愿以偿地长高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令全家人都感到恐慌——他进家门不低头就会碰到门框!这……这不是正常的植物,而是吃了强效化肥的农作物吧!高二的时候他就已经超过一米九了,那年暑假我们坐卧铺去西藏旅行,我不得不跟陌生乘客请求,能不能给我们换个下铺,因为乐乐个子实在太高,睡上铺的话腿都伸不开……
不知不觉,长高的狂喜变成了烦恼的起源。他发愁,大家也都跟着愁:“才十七岁就这么高了,再这么长下去可怎么办啊!生活处处不方便啊。”还有人说:“不如参加篮球队,做职业篮球运动员吧!”
说来也气人,他小时候整天抱着篮球玩,现在好容易有了完美身高可以随便灌篮,却又对篮球无感了。
小姨说:“哎呀,你可别再长高了,我之前期望的是一米七,顶多一米八就可以了。把你多出来的十厘米分给别人该多好。”
我在一旁大叫:“对啊!分给我多好!”
不知他们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乐乐挥舞着照片着急跟我比身高的日子。忘了吧忘了吧,怪尴尬的。
事实上,尴尬的不只是我。前阵子在外婆家,妈妈透过厨房门上的玻璃看到一个人的腰部——正常情况下应该看到人的肩背才对——脱口问道:“奇怪,是谁站在凳子上做饭?”
乐乐探出头,抹了把汗:“是我……我没站在凳子上……”
4
如今想来,长大真是不可思议。它不是在某一刻发生的,也不是延续几年的过程,而是长达一生又短如一瞬的奇幻之旅。
长大后的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教师资格证,却不再像小时候那么想做教师了,也没有如大人们预言的那样成为什么画家。乐乐又高又瘦,而且一点儿也不吝啬,出门旅行回来,大包小包全都是带给我们的礼物。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复杂而深邃,我们的性格很难用“内向”或是“外向”几个词简单划分,也不可能由大人们的评语或杂志上的血型分析来判定;我们的内在和外在特征,如风中水面颤动的波光,一刻不停地变化,我们对他人的固有印象,也迟早有一天会像纸船一样被水浪打翻。
我曾是什么样的孩子,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大人——谁知道呢?谁说得清呢?我就是我。这样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