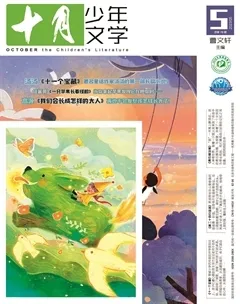[评论]天真的和“有邪”的童年书写
2020年夏天,我和汤汤一起去沂蒙山区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在旅游大巴上,我们天南海北地闲聊。汤汤讲了很多她当老师时的故事,她的语气很平静,却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在那之前,我曾经有一次问过汤汤,当老师会给你的写作带来灵感吗?我记得她当时给出的是否定回答。但是沂蒙山区采风那次,在汤汤的讲述过程中,我三番五次地怂恿她:“你把这些写下来吧,简直太精彩啦。”
大约一年之后,汤汤拿出了初稿。
这个作品最打动我的,是那个带点儿自传色彩的“方豆豆”形象。这也是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最具价值的地方。故事里的方豆豆处在20岁左右的年纪。显然,方豆豆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她的身上仍然保留着孩童时代的几分天真,所以在成人社会里,她的言行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有一种奇崛的效果。
当方豆豆面对教育局局长直白地发问,仿佛已经不是一个如孩子般的老师在向教育管理者发问,而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灵魂在向这个社会发问。当考了第三名的豆豆老师最终如愿被录取,小说这样写道:“她就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公平的事情比较多。”读这样的作品,会帮助我们重新清点、审视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恒常价值观:公平、正义、诚实、守信、善良、勇敢,等等。
作家汤汤用了很多笔墨来塑造“儿童本位”的豆豆老师形象:奖励孩子们放假一天、带头和孩子们一起淋雨等;她还用了很大篇幅去交代豆豆老师和包结实、李锦、叶小灵、张丛之间的情感互动。以上这些,如果换作另外一个有经验的作家,或许也是可以虚构出来的,但是豆豆老师身上那股子天真劲儿在成人社会里的左冲右突,很多人是写不出来的,或者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包括我自己)。
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汤汤的“传说”,不少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但是当我亲自听到她讲的那些故事,我突然发现,我眼前的这个汤汤跟她笔下的童话角色或者说那些“传说”中的汤汤合二为一了——这让我无比相信她写下的那些文字,关于善良,关于信念,关于理想,关于浪漫。
当然,《十一个宝藏》没有停留在对天真心性的单纯刻画上,而是更进一步,给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抛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携带这份天真行走多久?或许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并不是说,当一个人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人之后,就一定要走向天真无邪的反面。实际上,豆豆老师凭着趋利避害的本性,已经在分配工作时,表现出对更好生活的向往了。豆豆老师从农村走向城市,就是进一步被社会异化的过程:她要去更好的学校,获取更好的教学资源;她要跟男朋友在一起,最终会组建家庭。
当她产生这样的念头,并为之付诸行动时,豆豆老师已不再是全然天真的理想化人物,而是逐渐变成一个符合社会期待的成人。小说妙就妙在,豆豆老师仍然是相信公平公正的,比起“走关系”,她更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小说复杂也复杂在,豆豆老师其实是懂人情世故的,虽然她认为自己的男朋友小林“虚伪得很”,但她终究还是拎着沙瓤西瓜去登门拜访老校长了。只不过,她会坦荡地接住老校长的目光,自信地说出:“现在他(邵峰老师)肯定比我优秀,以后说不定。”
从这意义上来说,豆豆老师不是无邪的天真,而是“有邪”的天真,但只要她仍在心底为天真保留一个小小的角落,就足以迸发出动人的力量。当谜底揭晓,汤汤虚构了十一个宝藏:九个分别装着玻璃珠、小石头、螺蛳壳、花糖纸、纽扣、羽毛等珍贵宝贝的玻璃瓶,还有两个玻璃瓶则装着来自不同时空的童年的字条。这样的情节设计难度不太大,找到第十个玻璃瓶的过程也“纯属巧合”,但作家的兴奋点并不在于要写一个考验读者智商的推理故事,而是通过编织一个富有游戏精神的主干情节,把读者逐步引向审美的境地和深度思考的空间。
这是我们熟悉的童话作家汤汤为读者奉上的首部长篇小说,而且是现实题材的童年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