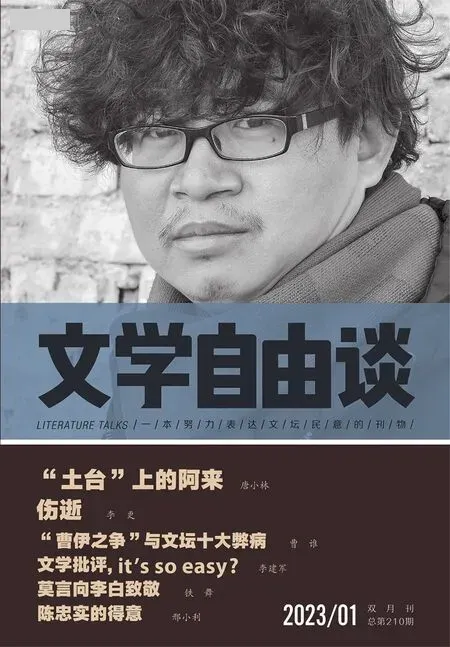李更的胡言乱语
□古远清
李更说,好久没有人“骂”他了(见《琐碎文章》,《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6期)。为解除他的寂寞,也证明他是值得别人骂的,特写这篇小文。
《文学自由谈》是我长期自费订阅的少数刊物之一。这个刊物所登的文章既不是“学报体”“学位体”,更不是“项目体”。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份刊物,文前没有什么“关键词”和“内容提要”这类劳什子,文后也没有长长的注释,更很少发表如钱锺书所说的“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的文章。所发文章,微言甚多,套话极少,不是云淡风轻的随笔体、携电挟雷的锐评体,就是“入木三分骂亦精”的板桥体。
这份刊物广纳贤才,继前些年的北京李国文、河北陈冲之后,又来了广东“二虎”:唐小林和李更。他们忠实地执行了韩石山所教唆的“谁红,跟谁急”的写作方针,急用先学,成绩显著,这几年竟成了该刊未挂牌的“专栏作家”,我几乎每期必读。他们风格各异:唐小林锋芒毕露,李更更老成持重。唐小林过于尖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路数,且屡屡重复,有不是就事论事之嫌,少了一份商榷的诚意,不利于营造“宽松、宽容、宽厚”的学术氛围,会引发被批评者本能的反感,“杀伤力”就有可能大打折扣。比如他对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批评,我读后感觉他是在糟蹋自己——把自己装扮成“法官”,把文学评论写成“判决书”。
而处于“更”年期的李更,大概是人到花甲,活到写回忆录的年龄了吧,他比唐小林更狡黠世故:很少使用语言暴力,但字里行间仍可以看出他的锋芒指向。他善用春秋笔法,有时候又像和他的同姓“兄弟”李逵那样“排头砍去”,可他“砍”的人实在太多了,故弄得灰头土脸,虽然还没有成为孤家寡人,但朋友毕竟越来越少。不过,我还算是他目前为数不多可以对话的朋友之一吧。
李更说我与他互赠著作,还相互欣赏对方的文章,确有其事。比如我读了他的《琐碎文章》后,感到他时有洞见,还有耐人寻味的警句。他用《世说新语》的手法描绘当前文坛动态,有浓烈的现场感。
我除了爱看李更的文章,还爱看《文学自由谈》封三任大戈文、王凤桐画的《画谈文事》。可惜的是,这两位作者捕捉的文坛怪象过于表面化,尤其老是把“现象”当“文事”,其实也可以让“人物”当“文事”,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评论家在那里一一登场亮相。这里不妨开个“文坛脸谱”名单:“文坛杀手”唐小林,“学术警察”王彬彬,“文坛恶棍”韩石山,“不受待见”的古某人,还有“文坛黑马”李建军,等等。这个版面的图画也应改进,因为它深刻比不上华君武,生动不如廖冰兄,读者可能早已产生了审美疲劳。我有个大胆的建议:为换换口味,把封三“地盘”让给一位水平有可能“更”高,还能文画合一的李更如何?我虽没有看过李更的漫画,只看到他在封二经常发表的“作家的画”,但我深信他改行作漫画绝不会比别人画得差,尤其是他提供的“文事”,肯定生猛,有看头。
不过,《文学自由谈》如“起用”并不年轻的新人李更,一定要注意他那些“琐碎文章”中,暗藏着不少废话。比如他说“陌生感就是新鲜感”,这就好比说感冒就是身体不舒服。更使我恼火的是,李更的“只言片语”中,还有不少脑壳灌水后所产生的胡说八道的歪论。
证据之一是,他从未涉足过海外华文文学,可对他自己不熟悉的这个领域竟敢品头论足。他在《琐碎文章》中,说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水平低,有如“武钢的车间黑板报”。这里要对“武钢”二字略作笺注:“武钢”是“武汉钢铁公司”的简称。这是李更的出生地,也是他成长的地方,其父李建纲曾担任过武钢文联主席。李更的每篇文章经常提到武钢,提到他的老爸,提到他就读过的湖北大学。可这次他所批评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恐怕很难知晓“武钢”是什么意思,甚至有可能会误认为“武钢”不同于“文钢”,是可用来打仗的武器。马来西亚作家更不可能知道“武钢车间黑板报”是什么玩意,但中国的读者是读得懂的,那就是“损”马华文学作品只不过相当于中小学生水平而已。
李更对马华文学的“贬词”以前也有人用过,比如广州中山大学已故的《香港文学史》著者王剑丛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老师就告诫他:香港文学是中学生的作文,研究台港文学的人属“弱智”一类。有道是:“一流学者搞古典,二流学者搞现代,三流学者搞当代,四流学者搞台港。”华文文学学界本身也有个顺口溜:“海外华文文学属于高中水平,中国香港文学属于大专水平,中国台湾文学属于本科水平,中国大陆文学属于研究生水平。”可自从香港有了金庸、刘以鬯、董桥、西西、葛亮,谁还敢说香港文学属于“大专水平”?但无知者无畏的“文化晃晃”李更,竟敢说马华文学相当于黑板报上的文章!据说他到马来西亚槟城做过不止一次实地考察,可他不太晓得槟城还有个原名林月丝、笔名朵拉的作家,她的散文像一朵云哗哗拉拉地盛开在中国大陆报刊,如《羊城晚报》和《读者》等,她还长期在《香港文学》写“专栏”。或曰“晚报”和《读者》属于消闲类媒体,那里的文章不可能有惊世之作,但能在中国的报刊走红,她的作品就绝非高中水平。
不妨再说说槟城另一位小说家陈政欣,他的《文集》中的小说分量极重,达到了“研究生水平”。华中师范大学黄曼君教授1997年和雷达一起第一次出国,参加“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就是以陈政欣的作品为研讨对象。记得前几年李更到槟城探亲,要我推荐当地作家时,我就首先推荐过这位陈政欣,并告诉了他的电话;可能李更没有联系上他。
槟城虽然是马来西亚华人最多的地方,但毕竟太小,不妨再说说美女作家如云的吉隆坡文坛——柏一的小说确是百里挑一的精品;李忆莙的长篇读后,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空姐出身的戴小华的作品,小国中有浓郁的大中华情结,受到王蒙、雷达、李建军等人的高度赞扬,笔者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论》和《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中,也有她的专节……这些女作家的佳作,就不是什么工厂车间的宣传品了,而是她们以优异的创作实绩在抢摊中国大陆文坛,有的还上了中国的大学教科书。更值得一提的是原名陈树英、来自江苏常熟的左翼作家金枝芒。这个名字,不但李更不知道,就是中国的华文文学研究界也鲜有人知道。陈树英用过很多笔名,如果说起他的常用笔名“乳婴”或“周力”,那可能就有人知道了。他是近年来才被“打捞”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型作家,是马华文坛从“侨民文艺”转型为“马华文艺”的标杆性人物。他的长篇小说《饥饿》,不仅是马华文学经典,同时也是世界华文文学中描写饥饿的经典。作为战地力作,这部长篇小说系金枝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反殖民的斗争中,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创作而成,写的是某游击小分队十四位战士在饥饿线上坚持斗争的惨烈事迹。对比柏杨、张爱玲、朱西宁、潘垒、姜贵、司马桑敦、杜鹏程等人的作品,金枝芒不仅选材独特,而且写饥饿更为生动和深刻。他写饿饭时,着重写了游击战士饿盐的情况,这里面带有作者的生命体验色彩,背后折射出的是对底层人民悲天悯人的生命意识。像这种深刻动人的小说,你能说是“黑板报”水平吗?
李更还对个人写文学史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著作颇有“个人排行榜”的意思,“他们没有时间对以往文学界进行必要、严肃的梳理,多半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甚至近水楼台,谁跟他接近,他就写谁”。这种情况的确是有的,但不可以一概而论,像洪子诚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从不与被研究对象套近乎,与作家们保持着高度的距离。唐小林曾经批判过洪子诚,但他不太了解从不求人写序、也极少为别人写序的洪子诚的批评风格和写作方法,故未能打中要害,这有如重拳击在棉花上。
李更的胡言乱语自然不止这些,如认为阎纲属被淘汰的评论家。他大概没有读过我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1949—1989)大陆部分》,那里有阎纲的专节。李更总是认为评论家是靠作家的作品养活自己,或者如上海杂文家江曾培所概括的“作家是大树,评论家是木耳”。这是典型的偏见。不见钱眼开,不与作家靠近,不随风起舞,不像“峨眉山上的轿夫,靠抬举别人赚点辛苦钱”的评论家,还真不少,不在学府围墙中的李更更不可能知晓。
不仅是李更,第一线的作者写的文章也时有胡言乱语,如韩石山发表的三流文章《越陷越深:我的传记写作》(《文学自由谈》2021年第1期),竟沾沾自喜于考证出徐志摩与陆小曼第一次上床的时间系对学界的一大贡献。如此自吹,真够恶俗。另一位“恶俗”并不一定“恶毒”的李更,我明明送过他由我编注、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21年度二十五本最佳文学类图书之一的《当代作家书简》,他竟说没有收到。后来我拿出微信记录证明他的确收到过这本书,他还狡辩说:“你这本作家书简没有收我的书信,其价值掉半!”这真是一个有李敖的傲气却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的“呸评家”(李更自称)。他自我感觉太良好,这是导致他有时胡言乱语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议李更下次发表文章时,不妨“剽窃”我这篇文章的题目,用“胡言乱语”做标题,想必自由谈文学的编者,仍然会允许这位从广东中山来的“微言”中掺杂不少废话、胡话的文友,“自由”地胡言乱语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