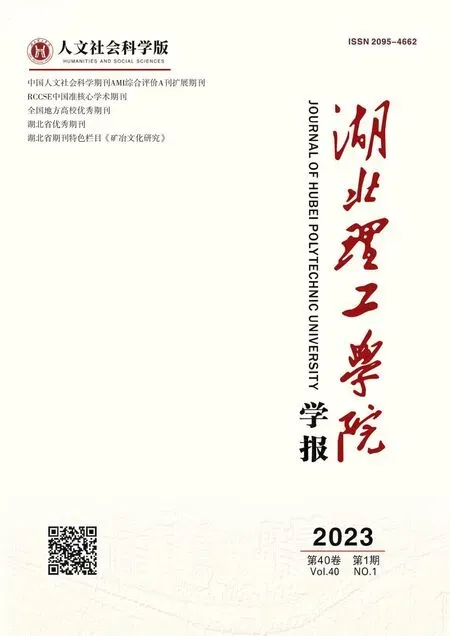从生命伦理到存在美学*
——论海德格尔思想的隐秘书写
张 培 刘秀莲
(1.湖北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2.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在《神圣人》的开篇处,阿甘本便引用了圣保罗的名言,“本是颁布给生命的律令,我发现却是颁布给死亡的”[1]1。死亡与和其相对的生命伦理价值构成了这本书的写作方向。在书中,阿甘本对由福柯和阿伦特所开启的生命伦理政治研究进行了更具历史性的追溯,通过对希腊人关于生命内涵的揭示,他力图在生命伦理政治之中塑造一种例外的个体生命——神圣人。
神圣人可能吗?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神圣人的存在成为了保证政治可能的前提?在这些疑问中,我们似乎总能看见海德格尔思想那漂浮的阴影,正是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存在样式的分析,才敞开了关于生命存在问题的第一次最为深刻的伦理思考。也正是在这一思考的促逼下,他思想的方向和道路才隐秘地发生了变化,并最终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关于生命伦理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在生命伦理政治的分析中,福柯是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生命伦理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部分,它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福柯将这一事件视为一次典型的谱系学意义上的历史断裂,作为宗教人和政治人的伦理学开始让位给作为生物人的伦理学,我们开始将生物性的基本价值付诸于人。新的治理技术正是基于这一伦理价值而产生的,生物性的生命价值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目标,生命的长度、生命的健康、生命的安全、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等等基于生命伦理的社会衡量标准才真正开始出现。按福柯的分析,一种让人活、不让人死的伦理价值成为了整个社会治理技术的基本政治导向。
阿甘本的思考从福柯开始,在他看来,生命伦理政治必然存在着更古老的起源,通过回溯希腊人关于生命的理解,阿甘本发现希腊人将现代人的生命一词更换成了两个词语,“‘zoe’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而“‘bios’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和方式”[1]4。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zoe”和“bios”之间的区别,正是其他生命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差别,人不仅活着,同时还必须首先作为政治动物而存在,生命的(生物的)伦理学不能成为人类伦理生活的根本指向,因为人是城邦的一份子,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动物的个体,他不仅仅作为一种生物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他还必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而存在,城邦所承担的价值和生命(生物)价值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原始的对抗。
该如何进行抉择,是将个体的生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还是将城邦的利益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虽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但这一回答却是不坚定的,其不坚定的原因恰恰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方向,正如他在其思想中不断表明的一样,那就是——一种关于存在者形而上学的真理是不可能促使这一问题获得解答的。
我们可以说,贯穿于海德格尔思想的隐秘线索正是由这一问题主导的,从“此在”的时间性到存在历史的诠释,正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主导方向。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回溯中,海德格尔不仅回应了福柯与阿甘本,甚至也回应了亚里士多德,他向我们表明,被遗忘的存在之思必将把我们带向生命伦理的道路,这是基于存在者真理的唯一方向。而冲破这一方向的唯一可能,只能借助于一次全新的开启,那就是以存在自身的真理为道路,来展示关于生命“此在”的新的可能。
一、“此在”时间性中的生命伦理预设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所有思想隐秘的起源,海德格尔一开始就对存在者和存在进行了区分,认为以往的哲学家研究的是关于存在者的真理,而从未将那个使存在者得以现身的“存在”作为思的方向。为了展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便专门提出了“此在”,那个置身于存在之中并唯一能够展现存在意义的特殊存在者。
“此在”是人,但又不能用人或是主体来加以表示,因为,人这一词语已经在关于存在者真理的诠释中,具备了过于强烈的主体主义色彩。在这一传统中,主体成为了一种单子式的、纯粹自足化的意识实体。海德格尔认识到,这种与生命的具体经验世界相剥离的主体,一开始就预设了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因此这一思想首先就是朝向存在者的,而不是关于存在的。
因为要展示生命具体的经验世界的真实景象,海德格尔在狄尔泰思想中获得了新的启发,“‘事实生命的具体经验’这个表达式本身就透入了狄尔泰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2]327,因此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之前,海德格尔就开始摒弃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而用接近于身体含义的生命(Leben)来意指所谓的人,他说,“‘生命’(Leben)=‘此在’(Dasein),在生命中并通过生命存在”[3]14。
生命总是首先无意识地投身于他存在的世界之中,正是他投身于其中的那个世界,让他拥有存在的空间,给予了他解释的位置和方向。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生命的使用减少了,他意识到,生命太过于经验化了,他需要一个古老的新词来展示他的思考,这就是“此在”。
将生命更换为“此在”,通过展示“此在”的存在结构,来揭示“存在”本身的含义,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基本写作思路。海德格尔首先就对“此在”的存在结构进行了展示,“此在”总是首先存在于它的“此”之中,而“此在”的“此”,就是它的世界。“此”指的是Dasein前面的那个“Da”,它意味着“此在”这种存在者总是存在于一种可能性之中。
在德语中,Da既可以指向这儿,也可以指向那儿;既可以指向此,也可以指向彼,这一前缀的含义表明了“此在”这种存在者特殊的存在形式,即他总是首先存在于某个地方、某种关系、某个位置。他存在的位置、关系,那个赋予他存在“意蕴”(Bedeutsmkeit)的东西,便是他的世界。因此,此在存在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在世存在”。
同时,海德格尔还分析了“此在”存在的第二种方式,那就是“去存在”,“此在”总是通过这种去存在的冲动与世界勾连在一起的,世界作为“此在”存在的前提给予“此在”存在的可能性,而去存在的冲动使得“此在”能够置身于世界之中,按其存在样式存在下去。
在关于“此在”存在方式的两个维度的展示中,海德格尔其实已经预设了“此在”的“此”——也即它存在的世界的优先性。“此在”存在的世界是“此在”得以去存在的前提,是“此在”存在的基础。因此,对“此在”存在方式的分析,无疑首先得回到“此在”的“此”,也就是它的世界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作为那个首先在世存在的存在者,世界是其一切理性和意识发生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可能对“此在”进行任何形式的预设,将之当成一个理性主体或是意识主体,要揭开“此在”存在的秘密,我们只能回到与“此在”勾连在一起的世界中去。
“此在”存在的世界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首先是与其最切近的周遭世界——一个关于物的世界,其次是“此在”存在的公众世界——一个关于他人的世界。“此在”只要存在着,就必然同时存在于这二重世界之中。
在物的世界中,只有与我们切近之物才会与“此在”的存在相关联,并构成“此在”的世界。而这一切近之物,正是用具,海德格尔说,“我们把这种在操劳活动中照面的存在者称为用具”[4]80。在这一和“此在”最切近的周遭世界中,他分析到,操劳或者说是制作(Herstellen)行为是使得“此在”和周遭世界得以照面的方式。海德格尔做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说,器具并非对象,作为应手之物,我们使用用具使用得越自然、越顺手,用具越不会成为我们意识的对象。在“此在”使用器具来劳作的过程中,作为对象的器具实际上被“此在”遗忘了,“制作(poiesis)的世界使得此在不能个体化,它消灭了此在最本己的存在可能性,它的去存在性。简单地说,日常世界遮蔽了生存”[5]117,因为这种遮蔽和遗忘,“此在”也同时遗忘了他自身,而将自己投身在这一用具世界中,这导致“此在”潜移默化地将之应手之物——用具,视为其自身的本质规定,而将“此在”的存在方式用具化。
公众世界,是“此在”必然同时存在的第二重世界。海德格尔分析道:在公众世界中,言语构成了“此在”和世界相照面的方式,交谈得越热烈,交谈者越是兴奋,在这种热烈与兴奋中,此在“以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来传达自身”[4]196,反而遗忘了他的自我。通过话语勾连起来的公众世界,其结果是,每个人都陷在闲言碎语之中,每个人都变成了他人,没有人能够成为他自己。
不论是沦为用具,还是沦为他人,无疑都是一种典型的沉沦状态。但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此在”首先必须在其世界中存在,世界的优先性似乎决定了“此在”只能沉沦下去,正是在这一危机下,海德格尔利用他的存在论分析,敞开了“此在”存在的第三重世界。
海德格尔分析道:“此在”首先是情绪化的,这是“此在”存在的本质规定性,这一情绪本身源于“此在”存在的世界。情绪相对于理性具有优先性,我们常说,不要情绪化,要理性一点。这句话中已经隐含着情绪是先于理性的,是“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海德格尔分析了多种情绪,每一种情绪都展示了“此在”存在的某种样式。而在这些情绪中,海德格尔最为看重的情绪则是畏惧。
什么是畏惧?或者说“此在”在畏惧什么?海德格尔说,畏惧其实是缺乏对象的,我们很难表明“此在”在畏惧什么,因为“此在”总是生存在畏惧之中,畏惧这一情绪正是“此在”存在的世界所赋予的。无论是用具世界还是公众世界,都无法让人感到畏惧,畏惧所要揭示的是“此在”存在的最根本的世界,这就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此在”是必然会死亡的。
死亡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此在”存在之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可能。它每时每刻都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着,畏惧则打开了这种可能,它似乎警告着我们,我们随时可能死去。因此,钟表上均匀流动的时间在这一刹那间失去了意义,生命就是每一个瞬间,在每一个被畏惧所打开的瞬间里,死亡像深渊一样凝视着“此在”,在每一个瞬间逼迫着“此在”作出抉择,是沉沦下去,还是从死亡的可能性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瞬间,“此在”获得了他的自我,并能够抉择他自己的存在样式。海德格尔将这一由畏惧所开启的时间性,称为“此在”的自身世界。
毫无疑问,“此在”正是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而存在的,畏惧让他明白,他是会死的,而且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海德格尔试图要利用这一“此在”自身的存在界限,来赋予“此在”存在的自我规定性。但处在死亡威胁中的“此在”,畏惧同样也让他明白,或者说让他最明白的一点,是不要死,要尽可能地活下去。在海德格尔对“此在”存在样式的展示中,已经明确地指向了一种关于生命伦理的前提性预设。作为要死的存在者,“此在”必然要将——活下去,活得更长更健康——作为其存在的基本伦理价值方向。
作为残篇,《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始终没有完成,这或许是因为海德格尔发现了自己为自己布下的圈套——一种关于生命的虚无主义,正是在这个被形而上学的隐秘倾向所创造的陷阱面前,他重新踏上了思的道路,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二、“此在”的隐匿和真理的发生
存在必须借由“此在”来讲述自己的历史和意义,而“此在”又首先是作为在其世界中的存在者而存在着的,而“此在”存在的世界——因为其自身的有限性特征——它总是不得不返回到预先存在的死亡可能中去规划生命,在这个海德格尔自己创造的循环里,活下去——似乎成了“此在”最紧迫的任务。
在这一思想的隐秘冲动里,海德格尔发现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倾向。在他后期的著作《哲学论稿》中,他将这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隐秘的现代性冲动的起源,最终追溯到了希腊思想那里。
应该说,海德格尔思想的方向在《存在与时间》中就埋下了几乎所有的伏笔,按照海德格尔的论述,“此在”作为唯一能够领会存在意义的存在者,他恰恰只能在其活着的时候来讲述存在。而一个活着的“此在”本就是一个存在者,海德格尔意识到,用死亡来界定“此在”的存在界限,其实已经是用存在者的方式来解释存在了,那这种解释的最终结果,仍是一种关于存在者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要超越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无疑必须找到一种比“此在”的时间性更为根本的东西,存在者哲学的“基本问题:存在自身是如何显现的”[6]151,正是在这一关于存在真理的更隐秘的溯源里,“此在”于存在论中的优先地位被剥夺了,而那可能将“此在”导向沉沦状态的世界——用具世界——反而成为了开启其思想的新的方向。
海德格尔首先感兴趣的便是用具,在《存在与时间》中,使得用具世界和“此在”照面的行为是制作(herstellen)。海德格尔运用对德语词根的分析,将制作的前缀her和stell分开进行诠释。前缀her是过来,让什么进入的意思,海德格尔解释道,“生—产制作(Her-stellen)同时意味着:带入可通达者的或窄或宽的圈子里,过来(her),来到这里(hierher),进入这个‘此’(Da),以至于被制作者就其自身自为而持立,并且作为自为而持立者保持为可现身的而现前而有(vorliegt)”[7]142。也就是说,制作是使得用具世界在“此在”面前展开的方式,这一行为使得“此在”进入了它的世界。海德格尔认为,这一行为的结果是,作为在场者的“此在”遗忘了他的自身规定性,而将自己潜在地规定为用具。
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变,正是首先从这一问题开始的。作为在世存在者的“此在”,会根据他存在的世界的规定性来规定自己,但是,用具到底是由什么力量被带入这一场所,这一世界之中的呢?
按照通常的观点,用具当然是被人制作出来的,但海德格尔却更进一步的提出疑问,“此在”为什么能够制作用具?是什么将这一能力赋予“此在”,并使得“此在”成为这一用具世界的在场者?
为了诠释这一问题,海德格尔利用了一种最特别的器具,一种既可以被称为用具但又不仅仅是用具的东西来敞开这一思考的方向,这种器具就是艺术作品。
艺术作品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揭示了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这个存在的真理被彻底遮蔽的时代,唯有艺术作品作为独一无二的用具,仍承担着敞开存在真理的任务。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在这个被现代技术所促逼的时代里,仍保持着用具之为用具的基本属性,也就是说,这种用具缺乏现代意义的主体性特征。所以我们常说艺术作品虽然出自艺术家之手,却仿佛是由上帝所真正创造。
海德格尔说,艺术作品是被制作出来的,它体现了制作一词的根本含义,所谓的制作,就是将什么带入世界,让它成为存在者。而艺术作品却展示了比一般的存在者更为复杂的含义,他首先从艺术作品的本质规定性出发,认为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8]21。艺术作品敞开了一个被存在者真理所遮蔽的特殊的存在视域,海德格尔将这一存在称为大地。他说:“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大地是大地。”[8]21
大地成为了海德格尔的新的思想维度,成为了诠释“此在”存在状态的新的方向。在海德格尔那里,大地是一种自身隐匿的存在,它不能简单地作为存在者而存在,但是,正是大地的存在,才使得艺术作品,这种特殊的用具成为在场者,被艺术家创造出来。
正是艺术作品,使得被隐匿的大地展现了出来,但这种展现绝不是一种现成存在者的展现,它所展现的是一种争执、一种原始的冲突。我们根本不可能站在存在者的角度去认识它,因为它就是一种隐藏,按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一种遮蔽。但是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总是超越了它自身的界限,超越了它作为存在者的意义和诠释维度。简单来说,一件艺术作品似乎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揭开了一种隐藏着的、与这个世界冲突着的力量。这种力量并没有成为一种存在者,但正是它的存在使得作品本身获得了真正的意义。
在此海德格尔利用了希腊的自然(phusis)一词来展示艺术作品被制作的原因,他说,自然就是“最高意义上的ποτησιζ(制作)”[9]9,因此,艺术作品所设置的存在的真理,在这种最高意义的制作中,被展现了出来。它所展现的就是冲突,艺术作品揭开了一道裂隙。海德格尔认为,透过这道由艺术作品所开启的裂隙,我们能够发现那个和存在者的世界发生着原始的冲突着的“隐匿”,那个存在者界限间的空白——大地。
大地与自然概念的出现,使得“此在”获得了新的存在样式,是自然在创造,它隐而不显的规定了“此在”的存在,并给予“此在”方向和界限。因此,要定义“此在”的存在方式,我们就不能再从“此在”自身的存在界限——时间出发,而必须从赋予它存在的可能——那存在自身的真理中,去寻找“此在”存在的道路。
三、“有”“无”之间的存在美学
海德格尔一生都走在反形而上学的道路上,他认为,正是形而上学主导了欧洲历史的真正方向。如果我们问:什么是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必定会回答,那就是关于存在者,也即关于“有”的真理,海德格尔指出,“形而上学最本己的问题意义,存在本思考为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了”[10]976。
在存在者的真理中,“无”永远是被驱逐的,我们关注的一切都是以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也就是以“有”为其价值导向的。这也正是在《形而上学导论》的开篇海德格尔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11]4
在关于“有”的真理中,死亡也即代表着“此在”的无。所以,存在者的真理只可能考虑“有”,而将“无”视为无价值,所有的意义和价值都隐含在“有”之中,而“无”也就代表着价值意义的彻底崩溃和消亡。
为了对抗“无”,从苏格拉底开始,一切真理都是关于“有”的。死亡是被这种关于“有”的真理所驱逐的东西,因为在存在者的真理中,“此在”无法面对作为“无”的死亡。为了对抗这种死亡和“无”,宗教提供了第一条道路,它创造出了灵魂和天国,将“无”变成“有”。在海德格尔看来,基督教的这一思想倾向早在希腊思想那儿就埋下了种子。
现代科学去除了宗教创造的迷雾,但生命本身是不可能赋予生命以意义的,将生命本身作为“此在”价值的根据,其结果就是把人变成了工具,最终必然导向虚无主义。
尼采发现了这一事实,他说,“上帝死了”,海德格尔赞赏尼采,他认为“尼采这句话说的是两千年来的西方历史的命运”[8]227。为了逃避这一命运,尼采创造出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一尼采所谓的“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12]428。通过轮回的思想,尼采其实仍在表明一点,那就是,存在者永恒地在轮回中存在着,死亡和出生之间的界限弥合了,“此在”将永恒地在其轮回中度过相同的生活,他必须将自身的每一次行为放在永恒的天平上加以度量,并时刻告诫自己是那个被钉在轮回十字架上的人。
正是尼采的思想激发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有关存在的历史观念就是在研究尼采过程中形成的”[13]113,但海德格尔指出,永恒轮回仍是走在存在者存在,而“无”不存在的道路上,仍然是一种关于存在者,也就是关于“有”的哲学,他把尼采的这一尝试称为最后一次形而上学。而海德格尔,则开启了第三条道路。对艺术作品的重新诠释,使得海德格尔发现了一个新的方向,自然本身作为最高意义的创制,将存在的真理设置入了艺术作品之中,因此,在艺术作品里,隐含着整个从存在的真理过渡到存在者的真理的秘密。
海德格尔要询问的是,存在的真理是如何被遮蔽,最终成为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关于存在的真理的开端处就隐藏着它最终的结局,《存在与时间》是对整个存在者的真理开端的最精确的一次描述,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无法真正在政治伦理和生命伦理之间作出抉择一样,海德格尔的思想仍然是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回应了亚里士多德的提问,那就是,唯有选择生命!这一隐秘的生命伦理促逼着存在的世界为“此在”的生命服务,当那个主宰着生命价值的上帝死了之后,生命本身成为了一切价值的最终目标。
正是在这一价值目标的促逼下,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才不断地强迫整个自然为人服务,它不仅以算计的方式规制着自然,也规制着人的生命与价值。海德格尔用“集置”(das Ge-stell)一词来描述现代技术的本质,所谓集置,就是“此在”逼迫存在者作为对象为“此在”存在服务的方式,通过这种强迫,海德格尔描述道:它不仅逼迫着存在者在摆置中,作为技术的对象为“此在”服务,它同样“也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9]19。
技术所敞开的世界里,人也一并成为了技术的对象和产品,人类开始以技术的标准来规定人的价值,这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命运。但我们仍不能否定一点,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确实使得人生命的长度更长了,活得更久了,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医疗技术无疑发展了,人的寿命也更长了,但海德格尔却提问到,‘寿命越长就越健康吗?’”[14]89。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命的长度和生命的健康是两回事,所谓生命的健康,更根本地指向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人类以现代技术来制造自己,“人就把他自己炸毁了”[15]297,“此在”存在的意义被彻底地遮蔽,人因此失去了它存在的根基,成为了被技术制造出的产品。
而这一切的根源,都隐藏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开端处,在苏格拉底慷慨赴死之时,他以灵魂的世界征服现实的世界,从那一刻开始,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似乎就已经被规定了。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总是把思想的起源回溯到这一开端上,这正是存在真理被遮蔽的原因,而基于形而上学的价值体系所建立的解释体系,又进一步遮蔽了那个真正的开端。
通过创造比生命更高的存在者来规定生命的意义,这是形而上学的第一条道路,它源于苏格拉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条道路已经终结了。
通过永恒的轮回,将“此在”有限的生命无限化,来逼迫“此在”作为价值的创造者来创造自己,是尼采开启的第二条道路,这条道路最终导向了虚无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仍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变形,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真理。
而海德格尔,则将起源回溯到了比苏格拉底还要早的人类文明时期,他称为前苏格拉底的那个希腊时期。在这个回溯里,既存在着海德格尔对希腊精神的理解,也存在着他对存在真理的自身领会。他认为,在那一开端处,存在的真理还未被存在者的真理所取代(正是这一替代导向了形而上学),这一真理处在永恒的冲突和争执之中,它是隐匿和显现,“有”与“无”之间的抗争与展示,这一真理的“绽出”规定着存在者的存在,也同样规定着“此在”的生存。
在这一开端处,技术和艺术,诗与话语,这一切都在真理的开启和封闭中,规定着自己的方向。它们存在着,但却不仅仅将自己定义为一种现成存在者,因为在所有的存在者之中,那隐匿着的大地,那个作为“无”的视域,都涌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都在造作,在毁灭和创造。
正如“自然”一词在希腊文中本真地就含有涌现和创制之义,那处在开端处的时代,变化、流动与生成是所有存在物存在的基本样式,而“此在”正是在这种变动与生成之中创制着世界,规定着自己的存在方式。晚期海德格尔提出的天、地、神、人四方域的思想,正是要展示“此在”的本真性的存在方式,以此来对抗被现代技术所彻底遮蔽的存在真理,海德格尔把这一对抗称为“存在历史的第二次开端”。
而这一开端,只能由艺术和诗来承担它开启的重任,因为唯有诗和艺术还原始地隐含着存在真理自身的冲突和争执,海德格尔喜欢引用荷尔德林的诗“但那里有危险,那里也生救赎”来描述这一新的可能性的来临。
在海德格尔看来,唯有通过艺术,才能在这个被生命伦理所规定着的虚无主义的时代里,将“此在”导向那条充满了曲径的大道(Ereignis),而只有在诗的语句中,“此在”才能真正听见存在之真理发出的声音。
艺术和诗,展示了那个被存在者所驱逐的“无”的时域,它撑开了“此在”对于生存和存在意义的根本理解。在这个一切都被“有用”“有意义”“有价值”所规定的时代里,唯有真正的诗与艺术还将“有”与“无”的原始争执展示在我们面前,将我们带到那永恒的变化和发生着的存在真理之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被形而上学所驱逐的“无”,总是借由某种可见物在“此在”的生命中显现着,这种显现在某种程度上又总是遮蔽着自身,诚如希腊箴言所述,“自然喜欢隐藏自己”[16]45,海德格尔则在其晚期的思想中不断地讲述着,真理同样喜欢隐藏自己,因为真理本身总是居留于“有”与“无”之间的奇特位置,真理总是关乎于存在的而非存在者的,正是在这一思想道路上,海德格尔开启了自己的“存在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