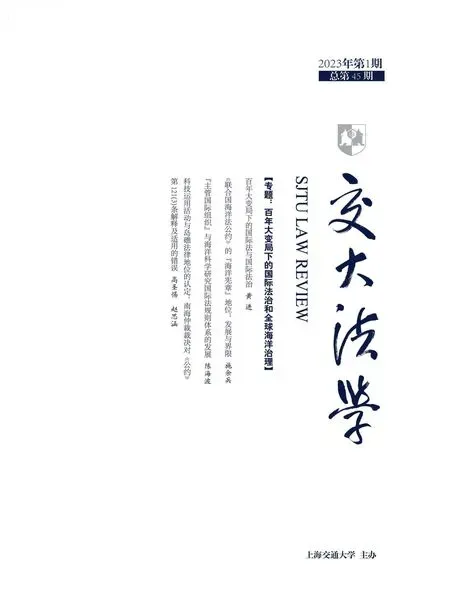洛克纳案、实体性正当程序与“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
杨洪斌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均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一、 导 论
1893年,詹姆斯·B. 塞耶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美国宪法理论的起源与范围》。(1)James B. Thayer, The Origin and Scope of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Constitutional Law, 7 Harvard Law Review 129 (1893). 中译本参见[美] 詹姆斯·B. 塞耶: 《美国宪政理论的渊源与范围》,张千帆译,收入张千帆组织编译: 《哈佛法律评论: 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1页。译文有修订。在这篇论文中,塞耶提出了司法审查的“明显违宪”标准:“只有当有权立法的机关不仅是犯了错误,而且是犯了极为明显的错误时——如此明显,以至于不存在任何理性的怀疑——法院才能拒绝适用法案。”(2)见前注〔1〕,塞耶文,第19页。
平心而论,“明显违宪”标准其实只是对大量先例(尤其是州法上的先例)的总结,(3)塞耶引用了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先例,并认为“明显违宪”的原则早在1811年就“已经完全确立了”。见前注〔1〕,塞耶文,第15—18页。本身并没有什么新鲜。塞耶这篇论文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作者通过重申“明显违宪”这个历史悠久的原则和标准,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司法审查的一种忧虑。塞耶提醒道:“[司法审查]应该被严格界定为司法性质的权力。……[法院必须]避免剥夺另一个部门的任何适当权力,或限制属于该部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行动。……立法者必须被给予自由的空间。……立法机关在决定应该做什么以及做什么才合理的时候,并没有和法官们分享这种职责,它也不需要服从法官们关于‘什么是明智的或合理的立法’的观念。”(4)见前注〔1〕,塞耶文,第9—11、24页。对“明显违宪”标准的强调其实是在捍卫立法和司法的区分和界限。显然,这样的关切和后世所谓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司法克制主义之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塞耶敏锐地预感到了司法审查在20世纪将会面临的争议,而“明显违宪”标准也因此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5)Wallace Mendelson, The Influence of James B. Thayer upon the Work of Holmes, Brandeis, and Frankfurter, 31 Vanderbilt Law Review 71 (1978). 根据Heinonline数据库上的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26日,塞耶这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是1 767次。
塞耶的忧虑是由联邦最高法院对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以下简称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和适用而引起的。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涉及正当程序条款的案件大量涌入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开始试图严守“司法与立法之间的界限”,不愿对立法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但至迟到1894年的里根诉农场主信贷公司案时,最高法院已经相当明确地根据正当程序条款审查立法的合理性和恰当性并推翻州法了:“法院的管辖范围以及司法调查的界限并不会因为现在是由立法机关(而不是承运人)来规定价格而发生改变。……法院有权力和责任去查究某个立法机关或委员会规定的价格是否不公正、不合理,以至于实际上是否摧毁了财产权利,并且如果发现确实如此,那就要[根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制止其实施。”(6)Reagan v. Farmers’ Loan and Trust Co., 154 U.S. 362, 397 (1894);see also Covington & Lexington Tpk. Road Co. v. Sandford, 164 U.S. 578 (1896); Smyth v. Ames, 169 U.S. 466 (1898).此即后来所谓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而当法院可以审查立法的合理性和恰当性时,司法和立法的界限也就开始模糊了。正是在此背景下,塞耶才从19世纪的司法实践中提炼出了“明显违宪”标准作为对此局面的回应。然而事实证明,当明显违宪标准能够良好实施时,它无需特别强调;而当它被明确提出来作为一项司法标准时,则恰恰是它衰落的开始。塞耶的论文表面上是个警钟,其实只是一曲挽歌。
关于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学界通常把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作为一个分界点。(7)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1905).该案是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之一,据说它完全违背了“明显违宪”标准,乃是典型的司法越权甚至“篡权”,并从此打开了司法能动主义的魔盒。由于直接关系到对正当程序条款这个“当代美国宪法的心脏”的解释,(8)“心脏”一说出自V. Earle, ed., Federalism, Peacock Publishers, 1968, p.10,转引自余军: 《正当程序: 作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基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史的考察》,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第160页。洛克纳案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它却无法像其他那些“错案”那样“入土为安”。用孙斯坦的话来说,洛克纳案的幽灵“在大多数重要的宪法裁决中一直徘徊不去”。(9)[美] 凯斯·孙斯坦: 《洛克纳的遗产》,田雷译,载《北大法律评论》2004年第1辑,第167—206页。如何定位洛克纳案,对于理解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当代实践和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不过,和前述的主流观点不同,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讲述一个不同的洛克纳案。依托于这些研究,本文认为,并不是洛克纳案突然“发明”了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并失心疯了似的背离了一直以来的明显违宪标准。相反,该案的多数意见很可能恰恰认为自己是完全符合明显违宪标准的。
“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和“司法能动主义”的兴起乃是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只不过,当最高法院在19世纪90年代根据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来推翻州法时,九位大法官的意见尚能达成相当高的一致(甚至经常是全体一致),因此并未引起太多的争议和批评,“明显违宪”标准看起来也好像仍然十分强有力。然而,由于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要求对立法的合理性和恰当性进行审查,而关于合理性和恰当性的判断是有着相当大主观性的,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将来势必会出现大法官们的意见不那么一致的判决,甚至是严重分裂的5∶4判决。洛克纳案便是如此,它是明显违宪标准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大厦将倾,无可挽回。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司法学说上的断裂。假如不曾有洛克纳案,那么也会有另一个什么案来填充它的位置。
二、 还原洛克纳案
纽约州1895年的《面包店法》规定:“任何在点心店、面包店、蛋糕店或糖果店工作的雇员,不得被要求或允许一周之内工作超过六十个小时,或者在任何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1902年2月12日,由于允许一个雇员每周工作超过六十小时,洛克纳被当地县法院判定有罪,被处以50美元罚金。这是他第二次因同样的行为被定罪。(10)Paul Kens, Judicial Power and Reform Politics: The Anatomy of Lochner v.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0, p.79.这一次,洛克纳踏上了漫长的上诉之路。在先后被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部第四区和纽约州上诉法院以3∶2和4∶3的判决驳回之后,洛克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是为洛克纳诉纽约州案。
1905年4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定纽约州的《面包店法》违宪。由佩卡姆大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指出,“对于雇员在雇主的面包店工作的时间,双方都享有[自愿签订]契约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受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纽约州《面包店法》设定的最高工时“限制了成熟的、具有完备智力的人在通过劳动赚取生计时可工作的时长”,但是该规定却“和雇员的健康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它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不能认为是州治安权力的正当行使,而“纯粹是一种对个人权利多此一举的干涉”,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11)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7〕, at 53, 61, 64.
在本案中,站在多数一边的其余四位大法官是首席大法官富勒以及布鲁尔、布朗和麦克纳大法官。持反对意见的四位大法官是哈兰、怀特、戴和霍姆斯。哈兰撰写了一份异议,并得到了怀特和戴两位大法官的赞同。霍姆斯也撰写了一份异议,不过并未得到其他大法官的赞同。不过今时今日,就洛克纳案的三份意见书来说,反倒是霍姆斯这份只代表他自己的异议成为美国司法审查和法理学历史上的一份经典文献,至今仍旧散发着夺目的光彩。让我们从这份异议说起。
(一) 从霍姆斯的异议说起
1. 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
霍姆斯的异议十分简短。在他看来,多数意见的背后,依靠的是一种特定的经济理论,亦即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后来的学者一般将其概括为“自由放任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第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写入宪法”。(12)这份异议的全文,可参见田雷: 《短意见的长历史——重读霍姆斯大法官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的反对意见》,载《师大法学》2017年第2辑,第388—403页。显然,霍姆斯提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指责”,(13)[美] 理查德·A. 波斯纳: 《法律与文学》(增订版),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如果能够成立的话,可谓釜底抽薪,因为司法裁判的依据毫无疑问应该是法律本身,而不是任何学术理论。但问题在于,洛克纳案的多数意见没有引用任何理论学说,更加找不到任何《社会静力学》的痕迹。更何况,即便判决中的确引用了某些经济学说,我们也不可能直接断定那就是在运用某种学说(而不是宪法)来判案。须知,论辩的基本规则之一就是不揣测对方的动机,因此我们不知道霍姆斯大法官的这番批评是从何说起。
在普通法法系下,判决的论证和推理方式是很灵活的。就当时的最高法院来说,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经济学、穆勒的自由论等理论学说都曾在判决意见中出现过,但从未曾见过哪位大法官发出霍姆斯那样的“诛心之论”式的批评。或许,霍姆斯是为了增加其语言的力度而刻意如此——用学者的话说,通过引用五十年前一个英国人撰写的一部“异域的著名自由主义文献”,他试图使多数意见“看上去深奥难懂,并且冥顽不灵”。(14)Jeffrey Rosen, The Supreme Court: The Personalities and Rivalries that Defined America, Times Books, 2007, p.113.但是,从普通法的论理方法和特点来说,这很难说是一份合格的意见。
2. 一般命题决定具体案件?
霍姆斯在他的异议中还提醒说“一般命题不能决定具体案件”。从法理学上说,这当然是精辟的见解。但就洛克纳案本身来说,这个指责也同样是不知所云。
佩卡姆撰写的多数意见引用了大量的先例,推理步步为营,是一份典型的普通法判决,说理非常周密详备,完全不存在“运用一般命题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反倒是霍姆斯自己似乎是在这么做。比如他说“第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将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社会静力学》写入宪法”,这显然就可以视为一个“一般命题”,而霍姆斯却用它来处理洛克纳案中的问题。第十四修正案确实没有规定《社会静力学》,可问题仍然在于,契约自由到底受不受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呢?纽约州《面包店法》中的最高工时规定是否超出了州治安权力的正当范围呢?霍姆斯似乎完全不关心这些问题。如果他的意思是说,由于第十四修正案没有将《社会静力学》写入宪法,因此洛克纳及其雇员的契约自由并不属于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范围,那这不恰恰就是用一般命题来解决具体案件吗?更何况这个一般命题和最终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并不清楚。
普通法的精髓在于不同案件之间的类比,无论是佩卡姆的多数意见还是哈兰的异议,都分析、比较了大量的案例(前者18个,后者17个),都运用普通法的方法仔细考量这部《面包店法》是否侵犯了洛克纳的契约自由。相比之下,霍姆斯的异议中则充斥着大量毫无论证的断言。在两页的异议中,只有一个段落引用了四个案例——按波斯纳的说法,其中只有两个是切题的——而且都是一笔带过。“他本可以再多引用几个,”波斯纳说,“但相反,他返回到了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面,说宪法‘就是为观点根本不同的人们制定的,并且,我们偶然地发现一定的观点很自然、很熟悉或者很新奇,甚至令人吃惊,但这不应该就此终结我们对表现这些观点的制定法是否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冲突作出判断’。多数意见从来没有说过应该终结。它所说的是,这部制定法是对契约自由的一种不合理干涉。”(15)见前注〔13〕,波斯纳书,第359页。托马斯·格雷也同样指出,在洛克纳案的语境中,霍姆斯所谓的“一般命题”指的就是“他刚刚陈述的并且他本人所信奉的命题:‘宪法并没有意图写入任一特定的经济理论。’”诚然,“法官不可能通过演绎推理由法律原则而决定洛克纳案”,但是在格雷看来,我们完全可能既接受这一原则,同时又认定纽约州的最高工时立法违宪——如果我们把契约自由视为“一种根本的个人自由”,而不是像霍姆斯那样把它“定位于一种备受争议且在历史上短暂存在的经济理论”的话。(16)[美] 托马斯·格雷: 《美国法的形式主义与实用主义》,[美] 黄宗智、田雷选编,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遗憾的是,霍姆斯大法官止步于他那简短的异议,不愿多置一词,他拒绝(像一位严谨的普通法法官那样)对案件中微妙的细节与差异加以分析和权衡,只是紧紧地抓住“明显违宪”标准以及“多数人有权将他们的意见写进法律”这样的一般命题来决定这部法律的命运。
当然,霍姆斯是语言和修辞的大师,后人对他这份异议的赞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的简洁凝练,韵味无穷。但法院需要的是慎思明辨、摆事实讲道理的法官,而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或者神秘莫测的祭司。回到历史语境中来说,在1905年的当时,霍姆斯这份异议中的法律论证,不得不说是相当薄弱的,其中提出的上述两方面的指责即便不是捕风捉影,至少也是相当不充分的。它更像是一个哲人的冥想和喃喃自语——“看上去像是[与佩卡姆和哈兰的意见处于]不同次序的法学文件。[其语气和文风]与洛克纳案的其他意见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17)[美] G. 爱德华·怀特: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法律与本我》,孟纯才、陈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作为霍姆斯的崇拜者,波斯纳也直言不讳地对这份异议提出了批评:“它的结构没有逻辑,没有同多数意见进行尖锐的争论,在处理多数意见或判例时不够细心,没有做细致的法律研究,没有利用事实记录。”(18)见前注〔13〕,波斯纳书,第359页。或许正是因为论证过于薄弱,所以在洛克纳案判决做出之时,霍姆斯的异议才未能获得其他持异议的同事的赞同。在判决做出后的十余年间,它也仍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19)关于这份异议和霍姆斯本人走上神坛的过程,怀特做出了很好的分析,见前注〔17〕,怀特书,第447—458页。
(二) 洛克纳案真正的法理逻辑
要想真正理解洛克纳案,哈兰的异议比霍姆斯的重要得多。因为据说《面包店法》本来是得到了多数大法官支持的,并且已经决定由哈兰大法官来撰写多数意见。但在哈兰开始起草判决意见之后,结果却发生了逆转。(20)David E. Bernstein, Rehabilitating Lochn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33.由于哈兰的异议本来可能是多数意见,因此它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通过比较这份异议和多数意见之间的异同,我们就可以锁定本案多数意见的法理逻辑以及它和哈兰等其他三位大法官之间的真正分歧,因为正是这些分歧导致了判决结果的逆转。
在仔细阅读哈兰的异议之后,我们发现,他和佩卡姆的观点之间存在许多关键的共性。首先,和佩卡姆一样,哈兰也完全承认契约自由属于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范围。(21)众所周知,将契约自由纳入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之下这一做法,最早出现在1897年的阿尔盖耶案,并非洛克纳案的首创。See Allgeyer v. Louisiana, 165 U.S. 578 (1897).这就意味着,九位大法官之中,只有霍姆斯大法官是个例外,他似乎完全不赞同对“契约自由”的宪法保护。(22)见前注〔17〕,怀特书,第404、406页。其次,他们也都认为契约自由并不绝对,州治安权力可以基于“公共健康、公共道德或公共安全”或其他“普遍福利”的理由加以规制。(23)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7〕, at 53, 67.再次,双方也都不否认,州治安权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受到正当程序条款的约束。最后,当州治安权力和契约自由发生冲突时,如何判定立法是否合宪?双方的判定标准也是一致的。哈兰指出,法院要审查“在州[立法中]所设计的手段和某种可以合法达成的目的之间是否存在紧密的关联,以及这种手段和保护与在面包店或糖果店工作的那些人的健康之间是否有着真实或实质性的联系”?(24)Ibid., at 69.而佩卡姆大法官也同样指出:“仅仅声称这一主题和公共健康有关,并不必然能够使这一立法正当、有效。……它作为[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必须[和目的]具有更直接的联系,而且目的本身也必须是恰当的、正当的,这样才能被认定为有效。”(25)Ibid., at 57.很明显,双方运用的是完全一样的审查标准。
哈兰和佩卡姆的根本分歧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哈兰认为面包师傅行业的确不够健康,而这项《面包店法》“显然是为了保护那些在面包店或者糖果店工作的人的身体健康”。因此,纽约州可以为了面包师傅的健康而对最高工时做出限制,这一制定法并未明显违反正当程序条款,应该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不然就是司法机关对专属于州立法机关的权力的侵犯。(26)Ibid., at 69, 72, 73.
而在佩卡姆看来,首先,这项立法和公众的健康没什么关系,因为面包的干净和卫生显然并不“取决于面包师傅是否每天只工作十个小时或者每周只工作六十个小时”。其次,它和面包师傅们的个人健康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如果对所有行业的统计数据都做一番考察,[就会发现,]面包师傅或许确实不如有些职业健康,[但它]同时却也比别的许多职业要健康得多。就常识来说,面包师傅行业从未被视为是不健康的”。如果允许州治安权力以健康的名义对面包师傅的工时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印刷工、锡匠、修锁的、木匠、细工木匠、纺织品售货员、银行职员、律师或者医生的秘书或者几乎所有行业中的文员就都将处于立法机关的权力[规制]之下了”。(27)Ibid., at 57, 59.佩卡姆之所以能够断定面包师傅行业并非特别不健康,或许是受到了洛克纳的律师们所作的案情摘要附录的影响——这份附录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这在当时是很新奇的一种做法,显然极大地加强了他们论辩的说服力。See Philip B. Kurland & Gerhard Casper, eds., Landmark Briefs and Argument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 vol. 14,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78, p.700-714.佩卡姆最后总结说,就面包师傅行业而言,“工时限制与雇员的健康显然没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目的和手段之间缺乏足够的关联性,所以,不能认为最高工时的设定是为了保护雇员的健康。再加上这一行业“是一种私人的业务”,与公共利益无涉,所以此时对雇主和雇员契约自由的限制“就不可能不违反联邦宪法”。(28)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7〕, at 64.
这就是洛克纳案的全部真相。纽约州的《面包店法》被判违宪,是除霍姆斯大法官之外的八位大法官关于以下这个问题的不同判断导致的——最高工时的规定究竟是为了保护公众或者面包店雇员的健康而正当行使州治安权力的结果,抑或只是在缺乏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将面包师傅单列出来予以区别对待,因此未能满足正当程序条款对立法的合理性和一般性要求,并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侵犯?后一种判断取得了五位大法官的支持,前一种则符合另外三位大法官的判断。但是双方对正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和运用却是高度一致的。
对洛克纳案的评价需要回到1905年的场域之中。虽然洛克纳案在当代臭名昭著,但在判决做出之后较早的八篇法律评论中,却有七篇都对其表示了支持,有些支持还很热烈,(29)See John Rogers Commons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p.690.报刊评论也大都持肯定的态度。(30)《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国家》杂志等主流媒体都是如此。See Bernstein, supra note 〔20〕, at 38-39.可以说,传统上对洛克纳案的定性——即它是一个脱离了大众意见、极度不得人心的判决——是严重错误的。
三、 正当程序司法学说与“明显违宪”标准的覆没
以上大体还原了洛克纳案的法理逻辑。我们认为,霍姆斯的指责——即多数意见将斯宾塞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注入了正当程序条款——是站不住脚的。不过,霍姆斯发出这样的指责是有其目的的,即服务于他在后面着重强调的“明显违宪”标准。
在霍姆斯看来,既然“宪法的意旨并不是为了体现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那么代表着多数人民的立法机关,就“有权利”将他们认同的经济理论和观念体现在法律之中,可以“以一些如果我们是立法者,我们可能认为有害的(如果你喜欢的话,称之为暴政般的亦无不可)方式”对[公民的]生活加以规制。他认为,本案多数意见扭曲了正当程序条款中“自由”一词的含义,并将之用于阻止“多数意见的自然结果”(即《面包店法》),实乃大错特错。那么,正当程序条款什么时候才能被用于推翻州法呢?霍姆斯给出的条件是: 当“一个理性而公正的人必定会认为,某项制定法将会侵犯我们的人民和法律传统中的某些根本原则”时。(31)Lochner v. New York,supra note 〔7〕, at 75-76 (Holmes, J., dissenting).那么,什么是“我们的人民和法律传统中的某些根本原则”?显然霍姆斯并不是要用一种自然法的路径来解释正当程序条款中的“自由”二字,(32)用学者的话说,到1905年洛克纳案判决之时,“霍姆斯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者,一个美利坚宪法共和国立法至上论的信徒”。G. Edward White, Revisiting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and Holmes’s Lochner Dissent, 63 Brooklyn Law Review 110 (1997).他的重点在前半句,即除非任何一个“理性而公正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认定某一立法违宪,否则就不能推翻它。毫无疑问,这是在重述塞耶的“明显违宪”标准。而就本案来说,霍姆斯认为,“不需要研究就可以断定,对于眼前的这部法律,并不会引致如此强烈的谴责和非难”。(33)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31〕.
纽约州的这部《面包店法》是否明显地、确定无疑地违反了宪法?四位持异议的大法官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是洛克纳案的又一个核心争议。在1905年的场域下,洛克纳案面临的最大质疑并不是什么运用特定的经济理论来断案,也不是什么发明了“实体性正当程序”的错误学说,而是说它违反了“明显违宪”的标准,以一种“司法能动主义”的姿态侵犯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严格界限。但我们认为这个指责也是不成立的。正如本文开头已经提到的,洛克纳案是“明显违宪”标准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以下将详论之。
(一) 明显违宪标准自身的困境: 基于法理学说的内部视角
如上所述,“明显违宪”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司法标准。早在塞耶对之做出全面论证和总结之前,类似的话语就已充斥在19世纪的司法意见和学术研究之中。在洛克纳案判决做出后不久,州治安权力领域的权威学者恩斯特·弗洛因德对该案的批评也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34)Ernst Freund, Limitation of Hours of Labor and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17 Green Bag 411, 413-414 (1905).而且在洛克纳案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案件面临着同样的批评和质疑。(35)See Chicago, Milwaukee and St. Paul Railway Company v. Minnesota, 134 U.S. 418, 462-466 (1890) (Bradley, J., dissenting); Loan Association v. Topeka, 87 U.S. (20 Wall.) 655, 668 (1874) (Clifford, J., dissenting).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良好运转了一个世纪的“明显违宪”标准,好像突然之间行不通了,以至于只能由持反对意见的大法官以异议的形式加以重申?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的确背叛了这个标准。这是一直以来的主流观点,即认为洛克纳案是错误的,体现了司法能动主义,是一种司法篡权;第二,这些案件并没有背叛这个标准,批评者的指责站不住脚;第三,这个时期的司法审查已经不再能够用这个标准来加以评判,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是遵从还是违反了它。
1. 洛克纳案违反“明显违宪”标准了吗?
我们还是回到洛克纳案。佩卡姆的多数意见指出:“面包师傅这种职业的不健康还没有达到可以授权立法机关对个人——无论是雇员还是雇主——的劳动权利以及契约自由的权利加以干涉的程度。公平人士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因此,最高工时的规定就“纯粹是一种对个人权利多此一举的干涉”了。(36)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7〕, at 59, 61.在判决意见的收尾处,佩卡姆说道:“[面包店法的]工时限制与雇员的健康没有直接的关系,对它也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十分明显的。”此外,他还指出:“[面包店行业]是一种私人的业务,无论如何都对道德没有什么危险,对于雇员的健康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质性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禁止雇主和雇员之间签订雇佣合同,或者对其自由加以干涉,那就不可能不违反联邦宪法。”在别的地方,佩卡姆还提到,“我们不可能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 许多这类性质的法律,虽然宣称是基于治安权力、为了公共健康或公共福利而制定的,但实际上却是出于其他动机”。(37)Ibid., at 64.
这些语气强烈的措辞中传递出的是一种确信,即多数意见确实认为该法案已经明显地违反了宪法。多数意见的五位大法官中,佩卡姆和布鲁尔一贯都对州治安权力类立法持敌对的态度,他们判定面包店法违宪并不意外。这就意味着,是另外三位大法官(富勒、布朗和麦克纳)的态度转变在本案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席大法官富勒的态度转变是有些预兆的,因为在最近的一起主要涉及劳工规制类立法的案件中,他就站在了布鲁尔和佩卡姆一边。(38)Atkin v. Kansas, 191 U.S. 207 (1903).但布朗和麦克纳这两位大法官之前一直都对劳工规制立法持支持态度,因此他们在洛克纳案中的立场转变就决不能说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或教条。相反,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确认为这项立法违宪了。(39)本段对多数派的五位大法官的立场的分析,主要参考了伯恩斯坦的研究。See Bernstein, supra note 〔20〕, at 33, 34.
简而言之,如果仅仅从5∶4的表决结果本身考虑——须知,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裁判极少出现5∶4的结果(甚至6∶3都相当少见)——那确实可以说《面包店法》并非“明显地”“确定无疑地”违宪。既然九位大法官中有四位都认为它并不违宪,那就表明,这项立法的合宪性存在重大的疑问。但是换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即便哈兰和霍姆斯的异议都着重强调了明显违宪标准,(40)哈兰对明显违宪标准的强调,see Lochner v. New York, supra note 〔7〕, at 68 (Harlan, J., dissenting).但富勒、布朗和麦克纳这三位中间派大法官最终还是把票投给了佩卡姆和布鲁尔这一方。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一定是认为纽约州的《面包店法》的确“明显地”违反了宪法,他们肯定不认为自己违反了这个标准或者是在侵犯或篡夺立法机关的权力。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佩卡姆的多数意见强调说:“这里不存在什么以法院的判断来代替立法机关判断的问题。如果法案在州的权力范围之内,那么即使法院可能对制定这一法律持一种完全反对的态度,它也仍然是有效的。可问题仍然在于,它是否在州治安权力的范围之内?这一问题必须由法院来回答。”(41)Ibid., at 56-57.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多数意见仍然还是在坚持明显违宪标准。当然,这样一来,这个所谓“标准”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同样的结果,既可以说它违反也可以说它符合这个标准。易言之,明显违宪标准此时已经变成个不相关的东西了(irrelevant)。
从根本上说,“明确违宪”标准由于其模糊性,操作性比较弱,甚至都不能说是一种“标准”。是不是说只有当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以上都认为某项立法违宪时,才算是足够“明显”?或者是七位,甚至八位或者全体一致?(42)在20世纪初期,的确曾有人提议限制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试图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可以召回法院的判决的规则,或者要求法院只有达到一定多数之后,才可推翻立法,但这一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关于这方面的提议,参见Fred A. Maynard, Five to Four Decis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54 American Law Review 481 (1920); Robert Eugene Cushman,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 by a Bare Majority of the Court, 19 Michigan Law Review 771 (1920); William G. Ross, A Muted Fury: Populists, Progressives, and Labor Unions Confront the Courts, 1890-193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Chapter 5, “The Judicial Recall Movement”.进一步言之,从单个大法官的角度来说,“明显违宪”标准也是说不通的。比如,在洛克纳案中,关于纽约州的《面包店法》是否违宪,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着一个递进关系——佩卡姆和布鲁尔认为它非常明显、100%地违宪;富勒认为它比较明显、80%地违宪了;布朗、麦克纳认为是65%违宪;哈兰等三位大法官认为它是否合宪存在重大疑问,他们或许在比如30%的程度上认为它违宪了;至于霍姆斯,态度不明,或许他认为100%不违宪。难道说大法官们在审查立法时,内心必须达到80%以上的确信才能判定立法违宪,否则就违反了明显违宪标准?这当然是荒唐的,因为违宪的程度是不可能量化的。
2. “明显违宪”标准何以在19世纪末陷入困境?
那么,一直都运转良好的“明显违宪”标准,为什么会在19世纪末遇到上述困境呢?答案在于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它要求对立法的一般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不合理、专断的立法将被认定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即所谓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43)Supra note 〔6〕.
实体性正当程序并非洛克纳案的发明。上文提到,至迟到1894年的里根诉农场主信贷公司案时,最高法院已经开始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来推翻州法了。不过事实上,早在1887年的马格勒诉堪萨斯案中,正当程序条款中隐含的这种巨大的威力就已经有所显现了。(44)Mugler v. Kansas, 123 U.S. 623 (1887).该案虽然支持了一项酒类规制立法的合宪性,但哈兰大法官——正是在洛克纳案中持异议的那位哈兰大法官——在他撰写的判决意见中也着重指出:“当法院开始探究立法机关是否超越了其权力界限时,法院可以自由地考虑事物的本质。……如果一项宣称是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公共道德或公共安全而制定的立法,[实际上]却和这些目标没有真实的或实质性的关联,或者明显侵犯了受到根本法保障的一些权利”,那么法院就应该判定它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只不过,由于此前的司法学说一向都十分强调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区分,对立法权予以高度尊重,因此哈兰又强调说:“纯粹属于立法恰当性的问题,与法院没有任何关系。政府的某个独立分支不应篡夺宪法赋予另一个分支的权力。”此时,“法院会尽一切可能,从肯定某一制定法有效性的角度,来作出假定[和解释]。”(45)Ibid., at 661-662.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两难。既然正当程序条款要求审查立法的合理性、恰当性,那么法院就势必要考察立法目的与公共福利以及立法目的与手段之间是否存在正当、合理的关联等等。用布朗大法官在1894年的劳顿诉斯蒂尔案中的话来说,立法所采取的手段必须“对于某种[立法]目的的实现是合理而必要的,对于个人[权利]不能具有过分的压迫性”。(46)Lawton v. Steele, 152 U.S. 133, 137 (1894).如此一来,那个法院不能介入的所谓“纯粹属于立法恰当性的问题”的标准就岌岌可危了,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严格界限就被打破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样的立法会被认为构成了不合理、不恰当的手段,从而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呢?直到1920年代,最高法院都未能形成一种明确可操作的标准。正如学者所说:“专断的、不合理的、压迫性的,这样的形容词在成文法中根本就没有任何界定,该标准只能通过法官自己的脑力活动来加以应用。……[法院]说州治安权力是有界限的,但是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指导方针是什么?却从未有过清晰的阐释。”(47)Ray A. Brown, Due Process of Law, Police Power, and the Supreme Court, 40 Harvard Law Review 956, 966 (1927).比如就洛克纳案来说,之所以引发争议,就是因为佩卡姆的多数意见和哈兰的异议都可以找到相当充分的学说依据和先例支持(甚至双方引用的先例本身就多有重合),这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是很少见的。正如当时的一位学者所说:“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中的用语非常宽泛,在一方看来,这是认可了司法机关日益增长的在决定政府政策走向方面的权力。但在另一方面,合格的法学家也可以找到足够的先例和理性上强有力的论证来支持如下主张:‘立法公正与否、恰当与否’不应由法院来决定,当法院开始决定政策问题,并且由于某一法案违背了一些含糊、不确定的宪法条款,就判定它不明智或者不公正并因此而认定其无效,那法院就超出了其正当的职能。”(48)Charles Grove Haines, The American Doctrine of Judicial Supremac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p.303.
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州治安类立法是否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将完全取决于法官们在每个个案中依靠其自由裁量而形成的判断。(49)当时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另可参见Robert Eugene Cushman,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20 Michigan Law Review 738, 758 (1921).如果法官认为个案中所涉及的立法不是专断的、不合理的,那么他就会祭出明显违宪标准,坚持严格区分司法权与立法权,宣称司法不得干预立法是否恰当、是否明智等问题,否则就是篡权等等;而当他在个案中认定某项立法是专断的、不合理的时候,又会选择另一套相反的话语,即立法不得专断,手段与目的必须具有恰当的关联性等等,否则就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明显违宪标准也就被抛在脑后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段时期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即大多数法官在不同的案件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立场。比如哈兰、富勒、布朗、麦克纳等大法官都是如此。明显违宪标准遭遇的这种困境和当代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之争的处境简直毫无二致——当自由派大法官确认新型权利时,保守派反对者会指责他们违背了宪法原意,乃是一种司法能动主义;而当保守派大法官基于宪法原意推翻先例时,自由派反对者也可以指责他们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同样是一种司法能动主义。明显违宪标准/司法克制主义实际上成了一个永远的少数派——它总是、也只能是被少数派拿来批评多数派推翻立法的判决是犯下了司法能动主义错误的工具。这样的明显违宪标准/司法克制主义不但无助于澄清问题、解决纠纷,反倒成了一个可以很方便地用来对多数意见进行污名化的标签。
3. 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与司法审查权的扩张
在批评者看来,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意味着司法过程失去了客观性,失去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九位大法官的主观臆断,因此是不可接受的。不过,且不说由此导致的司法上的主观性是否真的有那么严重(甚至于达到了一种司法专制的程度),仅就正当程序条款在司法审查中的应用来说,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法官要审查立法的合理性、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等问题,那他就一定需要某种自由裁量权。
当时的许多学者其实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弗洛因德在洛克纳案判决之后不久的一篇论文中就指出,虽然“法院一直都宣称自己没有权利或权力以不够便宜、不明智或者甚至不公平为由推翻立法政策”,但是现在人们已经渐渐发现,“在[州]治安权力领域,要想在法律与政策之间、某项措施的恰当与否和它是否有效之间、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力之间维持一种严格的界限是极端困难的”。(50)Freund, supra note 〔34〕, at 413.1908年,在一篇以各州的八小时工作制立法为例来探讨正当程序条款司法学说的论文中,年轻的莱恩德·汉德也同样指出:“[司法机关]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像英雄那样,迎难而上,宣告说法院可以而且的确有权力对[立法]采取的措施是否恰当进行审查,并进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这种措施]是否真的和它意图实现的目的之间存在关联性。……法院现在已经相当坦率地这么做了,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在宪法案件的判决中,[法官们彼此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以及在决定这些案件时,[法院]明显缺乏可行的原则。”(51)Learned Hand, Due Process of Law and the Eight-Hour Day, 21 Harvard Law Review 495, 499 (1908).
在洛克纳案判决之后不久,霍姆斯的好友弗里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为该案写了一个简单的注释。波洛克也同样认为除非明显违宪,否则法院不得以不明智、不够便宜而推翻立法,因为“从来没有人认为任何法院(包括州或联邦的)在一般意义上有权审查立法中的利益优劣”。这当然是英国人的观念,波洛克在结尾处也强调了这一点:“英国的法律人可能天然地带有一种偏见,会倾向于相信、支持立法机关的判断能力与结论。”(52)Frederick Pollock, Note: The New York Labour Law and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21 Law Quarterly Review 211, 211-213 (1905).但是,英美宪制毕竟不同,两者最大的区别便是美国拒绝了英式议会主权模式,并且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司法审查制度。而由于正当程序条款对立法的合理性和恰当性提出了要求,美国宪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恰恰就在于通过司法审查来对立法中的利益优劣进行审查,亦即通常所谓的“利益衡量”法。(53)利益衡量法已发展成为当代美国司法审查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现代[宪法]解释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探究宪法用语的含义,而是注重将那些比较概括的含义适用于具体案件,然后根据案件所涉及的问题给以确切的内容。这个过程主要是一种‘平衡’的过程。……这个平衡过程的内容清楚地揭示了法官的新责任与通常的立法程序之间的某些相似之处。”[美] 克里斯托弗·沃尔夫: 《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最迟到1927年,学者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目前来看,第十四修正案实际上是赋予了最高法院这样一种职责——即权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和州[立法机关]的诉求彼此间相对的权重,前者处于‘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个非常一般性用语的保护之下,后者则属于州的治安权力,其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一般性的用语。”(54)See Brown, supra note 〔47〕, at 966-967.
正当程序条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模糊性。就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来说,在正当程序条款崛起之前,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问题上,能够适用的宪法条款都是非常具体而有所限定的,从未有像正当程序条款这样既内涵重大又措辞宽泛的条款。(55)根据一项统计,截至1888年,共有128项州制定法被联邦法院推翻,其中有50件被判违反了宪法中的合同义务条款,另有50件被判干涉州际贸易,还有16件是干涉联邦的征税权力。See Haines, supra note 〔48〕, at 292, note 4.由于正当程序条款对立法的一般性和合理性提出了要求,明显违宪标准的衰落实在是不可避免的。明显违宪标准是建立在立法权与司法权以及政治与法律的严格划分之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正当程序条款逐渐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过程中,它们都遭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并最终渐次崩塌,而司法审查权则极大地扩张了。(56)学界通常都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视为现代司法至上的起点,这不是偶然的。参见[美] 基斯·威廷顿: 《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 美国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美] 小詹姆斯·R.斯托纳: 《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二) 正当程序条款与纵向司法审查: 明显违宪标准衰落的外部因素
以上主要从法理学说的层面上对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与“明显违宪”标准衰落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就会出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第五修正案中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正当程序条款,为什么它在通过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发展成如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那样重要呢?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在这段时间里为什么没有运用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对国会立法进行类似审查并带来类似的效果?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从学说的内部变迁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外部的视角。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众所周知,第十四修正案针对的是各州的立法,而第五修正案针对的则是国会的立法。实际上,塞耶在那篇论文中对“明显违宪”标准进行总结时,他主要强调的就是在对国会立法进行审查时,应该遵守这个标准——此时联邦最高法院面对的是一个与它并列、平行的部门,因此必须尽可能慎重。只是在文章最后结束时,塞耶才捎带提及了审查州法的问题,而在这里他还明确声明审查州法和国会立法乃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如果问题是州的行为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国家的最高法律——那我们所处理的就是不同的事情了。……不错,法院此时仍然是在对立法机构是否侵越其界限而进行辩论,但这里的部门不是并列的,而界限的性质也不一样。法院现在是最高宪法和政府的代言人,其职责是使这部宪法获得恰如其分的解释,并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保护它不受任何外部侵蚀。”(57)见前注〔1〕,塞耶文,第30页。译文略有修订。塞耶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在审查州法时,最高法院不需要严格遵守明显违宪标准。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霍姆斯也同样毫不含糊。在1913年的一次演讲中,霍姆斯谈到,“我并不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宣布国会法案无效的权力,美国就完了。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对各州的法律作出那样的判决的话,联邦可就危险了。”(58)Oliver W. Holmes, Jr., Law and the Court, 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20, p.295-296.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审查州法时就可以完全排除“明显违宪”标准的适用。相反,在这类案件中,大法官们也还是强调要遵守“明显违宪”标准,但此时该标准的遵守理由已经和在审查国会立法时强调这个标准的理由有所不同了。在审查州法时,之所以要奉行这个标准,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恪守立法与司法的界限,而是出于联邦主义的关切。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对洛克纳案提出批评的学者们除了指责法院篡夺了立法权之外,还指责它推翻了纽约州法院的判决。(59)See Freund, supra note 〔34〕, at 413-414.这个指责实际上是在呼应哈兰大法官在洛克纳案的异议中的如下主张:“让纽约州自己去处理它的那些纯粹内部性的事务吧。……州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主要是由州来护卫和保护的。”(60)See supra note 〔7〕, at 73 (Harlan, J., dissenting).这里的重点是“各州事务应由各州自主”这一联邦主义思维——既然,纽约州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治安规制类措施是本州所需,而作为该州政府的另一个分支的州司法系统再次确认了这种措施的正当性,这就说明这种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在该州之内被认为是正当的,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便不应草率地推翻之。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内战和第十四修正案已经决定性地改变了建国时期的二元联邦主义结构。抛开围绕着第十四修正案第1款三个组成部分的原意而展开的种种争议不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第十四修正案的制定是为了对州权做出进一步的限定,并由包括联邦司法机关在内的联邦政府为公民权利提供更多的保障。这是美国人民在经历内战的惨痛教训之后,对建国时期未完成任务的延续。内战前那样的州主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联邦的权威也已经稳固地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也大大地增加了。因此我们看到,当最高法院在内战后运用正当程序条款来审查州法时,无论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推翻州法,还是仅仅声明其具有审查权(与此同时支持州法),都没有再遭到像内战前那样的抵抗。(61)比如马歇尔法院的许多判决都遭到了州政府的强烈抵制甚至废止,而且也无法得到总统和国会的有力支持。诚如阿克曼所说,“马歇尔法院是在作一次殊死搏斗”。[美] 布鲁斯·阿克曼: 《我们人民: 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在美国的联邦主义下,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的。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联邦法院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向来都是冲在最前面的,而自建国以来运用宪法对州法进行审查就是联邦最高法院最重要的任务。(62)参见杨洪斌: 《制宪、建国与司法审查——美国1787年〈宪法〉的结构与司法审查在其中的位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129—140页。前引霍姆斯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作为内战老兵,霍姆斯显然深知此间问题的重要性。只不过在内战前,最高法院在这方面的作为毕竟还是有限的,而有了第十四修正案之后,则可谓如虎添翼,它终于可以承担起它在建国时被期望完成的“驯服各州”的任务。(63)Calvin H. Johnson, Righteous Anger at the Wicked States: The Meaning of the Founders’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与此同时,总统和国会也大力支持联邦法院的权力扩张,允许甚至鼓励它在审查州治安类立法上更加积极地作为。这种政治上的支持,从重建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了镀金时代。(64)重建时期,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诸多法案来扩大联邦法院的管辖权。See Justin Crowe, Building the Judiciary: Law, Courts,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63, 19; Felix Frankfurter & James M. Landis, The Business of the Supreme Court: A Study in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8, p.65.还可见前注〔56〕,威廷顿书,第五章。因此,和对国会立法的审查不同,当联邦最高法院是以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之一、基于联邦宪法的权威来审查各州的立法时,它就可以彻底放开手脚,这样就把正当程序条款的潜力毫无保留地发挥了出来。这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既然最高法院已经享有了,那就一定要使用它。正如当时一位学者观察到的,“法院(包括联邦的和各州的)一旦感受到了自己的权力,那么,在正当程序条款对法院提出的职责上的要求方面,它一定会采取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看法”。(65)Arthur N. Holcombe, State Govern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9, p.361-362.
而就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来说,按照主流的说法,它的原意的确只是提供一种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涉及立法内容的一般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虽然有同样的正当程序条款,但含义却是不同的,前者仅限于程序性问题,后者则可以用来进行实体性审查。(66)See Ryan C. Williams, The One and Only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Clause, 120 Yale Law Journal 408 (2010).不过虽说如此,但由于正当程序条款的一般性用语中蕴含着突破程序性问题的可能性,因此第五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在内战前还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来对立法进行实体性审查,此即斯科特诉桑福德案,而该案也因此往往被视为“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的最早起源。(67)参见张千帆: 《西方宪政体系》(上册·美国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0页以下。但是问题在于,当联邦最高法院从实体性的角度来解释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时,它针对的对象是国会立法。而在面对一个与自己并列、平行的部门时,法院一定是相当审慎克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即便不发生内战,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恐怕也很难顺着斯科特案中的解释思路,发展出像第十四修正案中这个条款后来所发展出的那种“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并产生那么大的威力。内战前各州法院对本州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或类似条款)的适用,也是同样道理。
总而言之,由于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处理的是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内战后州权衰落、国家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联邦最高法院运用实体性正当程序学说来对州法进行纵向的审查时,自然也就更加自信和积极,这是明显违宪标准衰落的外部因素。
四、 结 论
本文试图为洛克纳案正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正确”或者毫无争议的。洛克纳案无疑是个疑难案件,这从以下事实中即可看出——整个上诉过程中的三个法院(包括联邦最高法院在内)的判决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而且,正如上文所说,最高法院据说原本也是要维持《面包店法》的合宪性的,只是后来由于布朗和麦克纳两位大法官临时转变立场,结果才发生了逆转。因此,洛克纳案的判决结果对于许多人来说确实有些意外。毕竟,当洛克纳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时,形势并不乐观。(68)弗洛因德写道:“对于那些熟悉之前一些案件的人来说,洛克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惊讶。”Ernst Freund, Hours of Labor and the Supreme Court, 1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7, 598 (1905).不过,虽说有些意外,但还远不至于说是匪夷所思或者没有合理的根据。整体而言,洛克纳案乃是此前正当程序学说的延续。佩卡姆和哈兰的两种意见,都可以从哈兰在马格勒案中的矛盾立场中找到痕迹。
由于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应用要求对立法内容的合理性和恰当性进行审查,那就意味着问题的核心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见分歧的问题,即就看哪一方能搞定五票。就洛克纳案来说,多数意见和哈兰的异议——也就是说,除霍姆斯之外的八位大法官——其实分享着同样的“实体性正当程序”司法学说,只不过在本案中是佩卡姆一方最后获胜了而已。至于该案随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先例效果,那就不是它所能控制的了,而是要取决于下一个案件中双方的论辩以及哪种意见能够获得五位以上大法官的支持——用法兰克福特的话说,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高度依赖于个案之间的类比,因此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69)See Felix Frankfurter, Hours of Labor and Realism in Constitutional Law, 29 Harvard Law Review 353, 369-370 (1916).对于这样的结果,批评者当然可以提出批评,而赞同者当然也可以表示支持。(70)洛克纳案判决做出之后,与《面包店法》有关的一些工会组织和利益团体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工会威胁要举行罢工,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与此同时,纽约的面包店主则普天同庆。See Bernstein, supra note 〔20〕, at 37.这是个疑难案件,仅此而已。
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必然导致“明显违宪”标准的失效。当法院根据正当程序条款来审查立法时,由于该条款措辞之概括、抽象、模糊,法院就势必要进行某种权衡工作。正如昂格尔所说:“开放性条款和一般标准迫使法院和行政机关从事临时性的利益权衡,并抵制向一般规则的简化。”由此带来的便是对法律确定性的削弱:“结果的不稳定性随着公认政策的摇摆、随着它要解决的特殊问题之可变性而增加了。”(71)转引自[美] 布雷恩·Z.塔玛纳哈: 《论法治》,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换句话说,法官将不得不像立法者一样工作,详细考察立法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恰当性等等,而司法和立法的界限也就模糊了。
在此情况下,“明显违宪”标准显然已经不敷所用。塞耶、霍姆斯、卡多佐等人都强调这个标准,强调要寻求共同体的意见、明智之士的意见,而不是法官的个人意见,然而这两者如何区分呢?法官如何跳出其自身,从而确定自己的确信和共同体或明智之人的意见是否一致呢?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十分困难的。在谈到法官如何确定某项习惯法是否存在时,雷磊教授指出,关键在于民众对其存在是否有“必要的确信”,但“在实际的运作上,这相当于委托法官去决定何谓‘必要的确信’,或者说用法院的确信去取代了民众的确信,因为前者的可识别性更强”。而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所谓习惯法的空心化。(72)雷磊: 《习惯作为法源——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为出发点》,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4期,第62页。“明显违宪”标准遇到的困境也是如此,它同样是空洞的。抛出共同体或者明智之士的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并不能解决问题,反倒可能是一种逃避,极端情形下甚至等于是彻底放弃了法官做出判断的职责,像霍姆斯那样陷入犬儒主义而不自知:“如果我的公民同胞们想要下地狱,我的工作便是为他们提供帮助。”(73)转引自前注〔12〕,田雷文,第397页。译文有修订。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中,司法分支一向都被认为是最不应该屈服于大众一时之激情的一个。大法官的职责是维护宪法,如果公民同胞们下地狱的决定违宪了的话,大法官便应判定该决定无效,而不是为他们提供帮助;即便不违宪,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好公民,大法官亦应利用其身份地位尽力阻止。洛克纳案中的其他八位大法官便是这么做的(当然,我并不是说《面包店法》就相当于下地狱)——虽然他们对于《面包店法》是否违宪的判断不同,但他们都在履行身为大法官的职责。
洛克纳案中采取的审查标准或许不够清晰、确定,但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是所谓现代美国的“艰难开端”。(74)Owen M. Fiss, Troubled Beginnings of the Modern State, 1888-191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正当程序条款的司法适用也处于刚开始的摸索期,出现一些模糊纠结之处在所难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对于洛克纳案中采用的那种“中间审查标准”(即对立法目的和所采取手段之间关联性的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无法一贯胜任,就把它变成一种无效且错误的标准,如果这种审查能够把滥用立法权的程度降低到若无该审查时可能达到的那种程度以下,至少要降到能够证明该审查所引发的成本(如果有的话)属于可以接受的限度,那么,这种审查就是值得的。也不应该因为中间手段审查引发了立法机关和法院之间持久而剧烈的斗争,就反对这种审查标准”。(75)[美] 理查德·A.艾珀斯坦: 《征收——私人财产和征用权》,李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洛克纳案中的八位大法官尽到了他们的职责,他们无愧于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