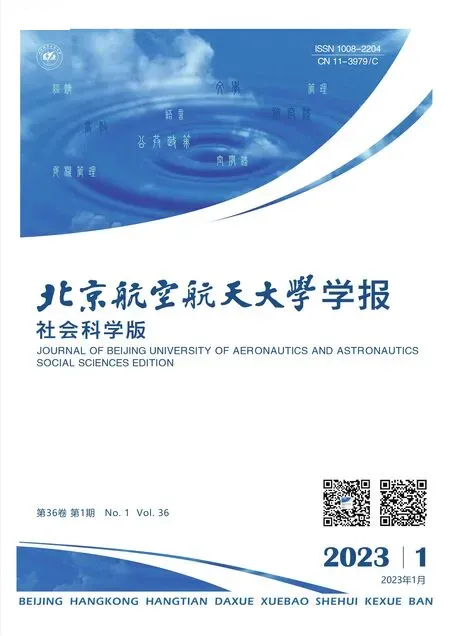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推定规则之检讨
高 通
(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
2022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2022年《意见》”)。其中,第21条对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立了新的犯罪数额推定规则。依据该规则,控方只需证明“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法院即可“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①。虽然推定规则可以从实质上降低控方的证明难度,但也可能会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置于过分不利的境地,故刑事推定规则的设定需要综合考虑人权保障、刑事政策等多种价值。若依此审视2022年《意见》中的犯罪数额推定规则,那么,该规则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司法实践中在适用该规则时又该注意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笔者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设定犯罪数额推定规则的正当性不足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渐确立了以综合认定为主的犯罪数额认定方法。相较于严格的印证证明规则,综合认定已经不再要求严格的印证证明,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证明标准[1]。为犯罪数额的认定设定推定规则,无疑会进一步降低控方的证明责任。对于推定的设定奉行必要性原则,笔者认为,当前并无必要专门设定推定规则,现有的简化证明方法已经能基本解决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的认定难题。
第一,依据涉案账户金额来认定犯罪数额的推定规则,可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过分不利的法律后果。推定体现了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2],在当前信息网络犯罪高发、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更是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背景下,通过设定推定来强化对信息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有其现实正当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解释依据涉案账户金额来认定犯罪数额规则时也明确指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因被害人人数众多而难以逐一取证和认证的问题[3]。但是,推定的设定应当综合考虑多种价值目标,尤其是不能过度违反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如无罪推定、罪疑唯利被告等。从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数额推定规则的内容来看,该推定规则可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过度不利的法律后果,从而带来实质性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风险。例如,推定规则总体上要符合经验法则的要求,推定中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应当存在比较稳定的相关性。但从该推定规则的表述来看,基础事实中的“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依此作出的推定也就缺乏准确性。其实,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曾明确规定,不能仅依据“犯罪嫌疑人无法说明款项合法来源”而将账户内款项全部推定为“犯罪数额”。
第二,综合认定方法可以基本解决被害人人数众多以及难以确定等问题。不可否认,被害人人数众多、逐一取证困难的确给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处理带来了极大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采取推定规则。虽然2022年《意见》中将推定限定在“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的案件中,但该条件本身就是进行综合认定的条件。而且,刑事推定作为一种非证据证明方法,只有在证据证明非常困难或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刑事推定才具有设定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综合认定方法已经能够基本满足司法证明的要求。例如,综合认定依据的证据材料范围非常广,除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勘验检查笔录等常见证据外,工资表、业绩表、银行交易明细、记账本数据、微信转账记录等材料亦可用于对犯罪数额的认定②。这些证据已经脱离了被害人而存在,对其进行收集并不是特别困难。而且,综合认定方法其实已经放宽了对控方的证明要求,不再要求严格的印证证明、容忍更大的事实认定错误概率等。所以,综合认定方法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信息网络犯罪中司法证明困难而出现的一种简化证明方法。
二、犯罪数额推定规则的限制适用
虽然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犯罪数额推定规则在正当性上存在疑问,但对司法实践来说,既然该推定规则已经确立,在未来司法实践中必然会被适用。从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角度来看,应当慎重并严格限定该推定规则的适用。
第一,坚持适用推定的补充性与最后性原则。刑事推定作为一种非证据证明方法,与其他证据证明方法之间是一种补充关系,只有在其他证据证明方法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刑事推定规则。对于这一点,2022年《意见》中亦有表述,其规定只有在“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时才可适用该条款。而且,该条中的“确因客观条件限制”应作严格解释,其内涵应当比综合认定方法中的“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更为严格。通过对其作严格解释,也可建立起证明方法的次序性,只有当穷尽其他证据证明方法都无法证明时,才可适用推定规则。这一思路在2022年《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中已有体现。依据该纪要,“全力查证具体诈骗数额”“查证发送诈骗信息条数和拨打诈骗电话次数”“依据出境时间和次数认定诈骗情节”三种证明方法之间存在顺序安排,只有前一种证明方法无法实现证明目的时才可适用后一种证明方法。
第二,降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理说明”的标准。刑事推定会带来证明责任的转移,如依据2022年《意见》中确立的犯罪数额推定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就“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账户中接收资金不属于犯罪所得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对于转移的是何种证明责任,学界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只转移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不转移说服责任[4];也有观点认为,两种责任均会转移[5]。笔者认同推定同时转移提出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的观点,因为推定规则的目的在于建立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直接联系,在基础事实得到证明的前提下,只要相对方未提出有效的反驳,该推定事实就会被直接予以确认。若允许相对方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那样,当辩方提出线索或材料时即会引发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适用,无疑会架空刑事推定规则,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何种程度的说服责任?犯罪数额的证明困难不仅存在于控方,同样也存在于辩方。要求辩方去逐一证明、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并将反驳事实证明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是不现实的。依据控方就定罪量刑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的要求,辩方的反驳并非要建立新的事实,其主要目的在于否定控方推定的可信性。当辩方否定控方推定的可信性之后,控方显然应当就推定事实承担新的证明责任。所以,辩方就反驳事实的证明只需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第三,建立依据涉案账户认定犯罪金额时的量刑减免制度。推定的实质是对日常经验的确认,是对客观详情的归纳总结,故而推定中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逻辑关系也并非确定无疑。从应然意义上来讲,刑事推定不能被推翻并不必然意味着推定事实的成立,此时仍然存在推定事实在客观上错误的可能性。而且从实践上来看,虽然推定通过设定反驳规则保留了其被推翻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辩方存在举证能力弱、记忆偏差等问题,且因辩方反驳而使推定被推翻的可能性总体上较低,所以,旨在减轻控方证明责任的刑事推定可能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其本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这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公平的。此时,司法机关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适度量刑减免,以缓和减轻控方证明责任与增加被告人不利后果可能性之间的矛盾。其实,通过量刑来补偿程序违法或证明瑕疵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如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对于“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的被告人,在量刑时应当从轻处罚。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在运用综合认定或推定规则来认定涉众型信息网络犯罪案件中的犯罪数额时,也有通过适当减少犯罪数额认定来实现对被告人量刑减免的做法③。因此,为平衡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建立适用推定规则时的量刑减免制度。
注释:
①2022年《意见》21条规定:“对于涉案人数特别众多的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收集证据逐一证明、逐人核实涉案账户的资金来源,但根据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交易记录和其他证据材料,足以认定有关账户主要用于接收、流转涉案资金的,可以按照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案外人提出异议的,应当依法审查。”
②参见:(2019)浙 0483刑初 24号、(2019)浙 1023刑初 359号、(2020)陕04刑初53号等裁判文书。
③例如,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法院在一起电信诈骗案判决书中指出,关于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公诉机关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电子证物检查工作笔录、售后手机截图、业绩表、工资表等电子数据综合认定,已属就低。参见:(2020)浙0483刑初373号裁判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