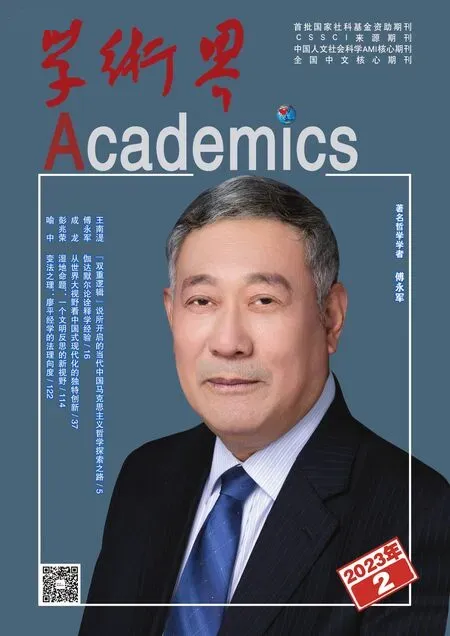湿地命题:一个文明反思的新视野
彭兆荣
(1.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401331;2.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 言
湿地主题近来夺人眼球。《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Ramsar COP14)于2022年11月13日在中国武汉和瑞士日内瓦圆满落下帷幕。我国成了世界上“国际湿地城市最多的国家”。〔1〕实际上,湿地的重要性并非近期才受到重视,联合国的《湿地公约》(1971年2月2日通过并颁布)比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11月16日通过并颁布)还更早。湿地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人类与环境的共生关系,包括湿地的调节水分循环的基本生态功能、湿地的生物链形态、湿地是季节性迁徙动物的栖息地、湿地动植物的原生关系、湿地的生物生存的食物链功能等。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球上的湿地越来越少,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为破坏,并与世界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互为说明。因此,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已越来越成为人类共识。
似乎是不经意的巧合,近来人类学对这一主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与生态保护主题同中有异。人类学讨论湿地,除了对生物—生命的关注之外,更将眼光集中到传统的主流观点——栽培—驯化、水利灌溉导致的农业革命的反思性探讨上。其中,尤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亦译为《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2〕中的所谓湿地命题为代表性观点,〔3〕进而以此对传统的历史范式提出了挑战。他甚至认为,原始湿地才是农业产生的基本依据。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我国第一部人文地理学说《禹贡》大致反映了相似的主流线索,中华农耕文明更是世界典范。然而,灌溉∕湿地是否成为中式农耕文明产生的原始依据,抑或有另一种形态?值得重新探讨。笔者以为,“汭形态”为“灌溉∕湿地”之外的另一种解释。
二、汭:一个中式农耕文明的解读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以水开篇:
人类文化的最先开始,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于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里的居民,一则易于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于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围敌人之侵扰。在此环境下,人类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进展到恒河流域,较为扩大,但仍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的地理背景,显然与上述诸国不同。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4〕
钱先生以水开说中国古代文明之滥觞委实把握住了文化的脉理。但他否定了一般的“黄河造化农耕”的笼统说法,提出了“汭”的农耕文明生成说;给出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阐释。只可惜他没能将这一话题提升到文明形态的高度,即中华文明作为东方农耕文明的代表,既非直接源自于黄河,亦非来自于自然湿地,而是河流的另一种形态:汭形态。
“汭”,指河流弯曲之地。在河流弯曲的地带,水中泥沙流速不均匀,土地肥沃,造成平原面积越来越大。我国先民首先在居住的安全上选择了“汭”地带,以利于交通、耕种、渔猎。“汭”还嵌入了中式风水观念。从“汭”字的结构看,指水入内。《说文解字》释:“汭,水相入也。”〔5〕也引申为“水滨”,即客居河畔处所。我国史籍最著名的记录为《尚书·尧典》帝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说的是天子为了考察舜,下嫁二女到妫水的湾处,也就是舜的居处。〔6〕按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大意是说,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让他在河畔耕种;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让他居住;在河滨制陶,那里的陶器没有不好的。一年后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形成聚落,两年后成了一个小镇,三年后就成了一个都市。)有学者认为记载中所述“历山”乃河东之历山。〔7〕此非孤例,我国古代的曾侯墓與钟铭也有“营宅汭土”之说,即周王命曾国祖南公括至江水与夏水之汇流处营宅建设,夏水即汉水之别名,即江汉。〔8〕由是可知,“汭”既非河流直接灌溉,亦非原始生态湿地,却成了我国先民的一种生计方式、居住选择和城邑形态。
重要的是,汭的形态是否表示我国古代曾经不是完全以农耕为本,而是存在以渔猎农牧混合为主的食物来源的可能性?西安的半坡遗址中彩陶上的鱼纹,特别是著名的人面鱼纹,包括大量与鱼氏部族有关的记录、图案,以及以鱼为符号的文字的出现等,似可说明“鱼生人”“寓人于鱼”的意象,这些都证明以鱼作为图腾的氏族和部族徽号的存在。〔9〕这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人类学命题:如果国家的生成与人工灌溉(农业革命的关键要素)有关,湿地作为自然形态,它可以导致人群的聚集和定居,却不直接导致国家的生成。那么,主流观点的“链条”就此断裂。这是斯科特的观点。但我国的“汭”既不是灌溉,又不是湿地;重要的是,它不必与农业的生成构成唯一说明性理由,却可能同样具备国家的生成条件。这些问题颇为值得深入探讨。换言之,汭可能、可以促使人群聚集、定居,甚至导致早期国家原型的生成,却不完全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前提。
水利灌溉式的农业与国家生成的历史关联,——具体地说,以人力工程控制水作为国家生成的原理和观点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特别是德国人卡尔·A.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水利灌溉—东方专制”之说,成为相关讨论绕不过的一个话题。〔10〕这种将国家生成和治理的关键因素置于水利对农业灌溉的观点今天受到了人类学、历史学的质疑:“我们以前认为,古代的苏美尔文明创造了奇迹,在一处干旱区域,由国家组织起伟大的灌溉工事,现在证明,这一经典立论是完全错误的。”〔11〕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对这一观点是否认可,“农业灌溉”这一历史性命题已经从现实功能上升到了哲理、伦理、义理的层面,并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存在逻辑和解释关系。对这一判断的反思,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为当今人类学一个重要的代表性观点,与生态湿地保护话题不谋而合。
从历史表述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似乎并没有摆脱“主流观点”的基本线索。《尚书》中的“禹贡”“洪范”两个篇章为我们描绘了治水—水利—中邦—九州—五服—贡献国家形制的历史线索: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确立“中邦”,创建“王治”,圈定“五服”,禾兑“贡献”。具体地说,就是疏通河道,确立帝都(“王畿”——都城以及周边的田地)为中邦,划了一个两千五百里的大圆圈,每五百里为一“服”,共“五服”,根据远近为王国提供贡品。所谓“贡”就是提供粮食,“服”就是提供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以“谷物”作为贡献、提供服务以兑换国家赋役。其认知和表述模型与中式特殊的宇宙观“天圆地方”存在关联。
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1.疏通河道,修建城郭,建立中邦(城邦王国),昭告天下。这在《周礼》第一章(“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第一句就说明白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12〕治水疏通、建立王城成了中式国家伦理的滥觞。2.所谓甸服,其实就是充实国家粮仓。“甸”的本义为王田。《说文解字》释:“甸,天子五百里地。”〔13〕说明王者不仅有田地,而且亲自务农,古称“耤田”,后演化成了“耤田礼”。〔14〕3.所谓贡献就是纳税,其实就是上交粮食(“税”即以“禾”“兑”国家的课税,此字今天仍在沿用)。4.根据“一点地方”(也称为“五方”)原理,以“五服”的远近交纳各种形态的粮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农为本社稷国家—家国天下的原型。
有意思的是,我国古代国家的治理以“洪范”为法则,也成为最早的法典。建立“大法”的原委因水而起,故两字皆从水。“洪范九畴”讲述的是从国家生成到国家治理的九种大法。〔15〕其中包含着水利—灌溉与国家权力的隐性话语叙事。看来德国人魏氏将水利—灌溉作为国家专制主义的解释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对历史过程出现了一个误判,即将农业革命视为一个像工业革命那样的历史事件。而事实上以水为命题的农耕存在着一个适应自然的漫长过程,更是一个以栽培和驯化为特征的“长时段历史”。〔16〕而且,无论是栽培还是驯化,历史形态极为复杂、多样,显然不是一次“农业革命”足以说明的。
回眸中华文明,我们溯源中华文明时通常习惯上称之为黄河文明—黄土文明。之所以如此表述,是因为黄河冲积出的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使得农耕文明得以实现。然而,我国考古发掘的大量相关遗址和考古材料似乎又不足以完全、完整地支持这样的表述。以兰州附近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为例:
兰州市位于黄河上游,黄河自西向东流。自西柳沟大坪至东岗镇30余公里的河谷间,山坡地带统为发育极佳的黄土台地,有高出河岸20—30米的第一台地,第二、第三台地则高出河岸40—80米左右。遗址所在地多在第二台地上。土门墩大坪到崔家崖5公里的第二台地,在一条水平上,面积相当平坦宽广,现为肥沃的农耕地。〔17〕
这证明了古代人们生活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以免受洪水的威胁,却也无法利用河水从事原始的农业灌溉。〔18〕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河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夹带5%的泥沙已经相当多,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46%的记录。其中有一条支流在夏天达到了难以置信的含沙量63%。〔19〕如果早期的人们筑高台而居不便于进行水利灌溉,那么,“汭”便可能成为中国漫长农耕文明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形态,——而且是介乎于人工灌溉和自然湿地之间的特殊形态。
概而言之,水与农业革命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没有疑义。但是言及至此不够,因为二者之间的多样性更表明文明的差异性和文化的复杂性。中华文明总体上说属于农耕文明,“汭说”却不重蹈传统“灌溉说”的覆辙,也与“湿地说”不完全契合;与世界其他一些古代文明迥异,属于中式农耕文明的特殊范式。
三、“栽培—驯化”的新界说
众所周知,除了水利灌溉,与农业革命关系较为密切的无疑是栽培—驯化。英文agriculture(农业)的本义就是指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牲畜,后来衍义为农学、农艺。在农业产生之前,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以野生动植物为食。人类远古祖先以20—40人组成的小部落为基本规模,他们根据一年一度的猎物迁徙时间以及野生的坚果、种子、水果和蔬菜的成熟时间安排自己的生计方式。所以他们被称为狩猎—采集者。大约在5000年至1.2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培育”食物。逐渐地,他们除了捕捉野生猎物,还开始“驯化”野山羊、野猪和野绵羊;开始建立最早的一批园子,采集野生植物的种子和插条,将它们种在一处进行照料和收获。人们逐渐在一些永久性定居点稳定地生活。人类从此完成了从狩猎者和采集者到放牧者和耕作者的重大转变。农业革命从此开始了。〔20〕
从知识考古的角度看,英文中domestication(栽培、驯化)这个术语源自domus原义,与“农庄”“居住”有关,也就是人类祖先根据他们当时的生计需求改造了相应的动物和植物的结果。〔21〕有意思的是,domestica 既可以指家畜,特别是家猪,也指家庭、家里。这与中文“家”的释义无意之间竟相吻合。《说文解字》释:“家,居也,从宀,豭省声。”〔22〕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信息相互关联,即居住方式与栽培驯化同构。一直以来,以栽培驯化为主导的农业形态被认为是对采集狩猎原始形态的进化和进步,理由包括定居比游动更稳定,农耕比采集狩猎收获更丰裕、生计更有保障、生活更有安全感。可是这些在学术界具有相当共识性的观点却受到了人类学家们的质疑,萨林斯认为采集狩猎时代属于“原始丰裕社会”;〔23〕斯科特则关注到“栽培”与“驯化”并非绝对关联性的事件,二者相差“长达四千年”,认为把二者放在一起是个“天方夜谭”。〔24〕按照斯科特的观点,湿地命题似乎可以解释前农业时代的人类生存方式。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虽然农业在历史上的演化线索大致可以成立,但并不因此成为世界文明演进的规律和通则,即使在中国也不是如此。至于二者之间的“时间差距”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存在质疑。另外,在表述上也存在问题,比如将农业当作一个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时间上还是性质上既不吻合、也不严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25〕贯穿着多种文明,特别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并置、交替与融合。文明形态的交替并不是简单的、绝然的“进化程序”和“阶段替代”。诚如人类学家李济先生所说,采集狩猎阶段与农耕文明阶段的交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二者存在历史性的交错。比如在商代,狩猎成风,却已进入到农业阶段。〔26〕因此,所谓农业不存在事件性的新旧替代关系,更不是以“革命”足以概括的。
根据主流线索,当我们在探讨“黄河文明—黄土文明”时,也很自然地将其与农业起源联系在一起:
在大家熟知的中国地形图上,除了高耸的青藏高原外,巨大的中国版图基本上是由西北的棕黄(第二阶梯)和东南的青绿(第三阶梯)两大板块组成的。在黄河即将冲出黄土高原的地方,嵩山像一座灯塔,引导着她奔向华北大平原,其西边是山脉,……东边则是河道和若干大泽形成的断续的隔离带,形成了一个“地理王国”……中国古代四渎中的河、济、淮三水及其支流呈放射状外流。这些河流以及支流组成了密集的水路系统,连通中原腹地内部及周边区域,形成交通枢纽。〔27〕
事实上,刻板地将黄河(灌溉)与黄土(农业)并置以概括华夏文明确有简单之嫌。从自然生态的情形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东西横跨60多个经度,距离约5200公里;南北跨越50个纬度,距离约5500公里,气候跨亚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土壤情况也不一样,水资源南北分布很不均衡,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农业生态文化。〔28〕通常我们都将中华文化定位于“农耕文明”,并将黄河认定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滥觞,这固然不错,然而却忽略了“游牧—农耕”在历史上的生成和互动关系。拉铁摩尔曾经比较过蒙古的游牧族群与汉人的农耕者,虽然游牧与农耕可以同时在一个地区生成,可是,游牧民在与农民的竞争中占得优势。〔29〕像拉铁摩尔这样的学者拒绝在狩猎采集、放牧和农耕之间作出任何界限分明的区别。原因是:为了安全起见,多数先民会“做好两手准备”。〔30〕这也是我国北方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实情。即使是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也可以看作是农耕与游牧融合的范例。
地理的历史演化同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地理学上的“胡焕庸线”就是一条“游牧—农耕”互动线,它东起东北的瑷珲,西至西南的腾冲,全长1万多公里,农耕和游牧的历史关系(包括冲突、友好、平行、互动、融合等)在这条线上演绎了上万年,构成了中国历史重要的部分。这是一条由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也是一条降水分布比例的划分线。它在中国人口地理研究上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学者定名为“胡焕庸线”(也称“瑷珲—腾冲一线”)。〔31〕
这样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复杂性与包容性,特别是封建朝代延伸到元、明、清,更将“黄土文明”中的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形态融合在一起。换言之,中华文明属于多重、多种文明因素的融合性文明,栽培与驯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表述中完全可能自圆其说;即便是农耕文明也因南北地理上的差异而形成“麦作文明”与“稻作文明”,同样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有山海之势所形成海洋文明、山地文化等多种文明交织的自然历史景观。而如果我们将这一条线路看成“旱地”对“湿地”的历史性挤压似乎也可以成立。
概而言之,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这样概括虽不错,但不够,过于笼统;要加上“多种文明之综合”。除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基因外,还有山地耕作、海洋渔业等文明基因。因此,即使是栽培与驯化,在中华文明中也是独特的。我国的农业从来就是大农产业——农桑畜牧多种经营的综合产业。〔32〕古代的所有农书都如是说。而湿地对“大农产业”的生成更具说服力。
四、湿地与生命共同体的关系链
人类在今天讨论湿地命题有何意义?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它与“人类是什么”关系密切,即人类是生命自然界中生命共同体的一个“类别”(Man-kind)。然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人类最难认识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正如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七句名言,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只有一句:“人啊,认识你自己。”对于人类如何成为“人类”,达尔文给出了一个宽泛的解释:人类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产物。而特殊的自然条件是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湿地正是生物进化凭借的重要原始依存与依据。
如果说进化反映了物种起源与进化规律的话,那必然离不开农业与驯化的特殊关系。人是进化的产物,是表示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普遍性(自然)。驯化则表示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独特性(人为)。“驯化”指人类有目的地对物种进行改造以适合人类的需要。人类也在这一过程中达到自我驯化。黑猩猩与众不同地体现出成熟和合作的社会气质是通过“自我驯化”进化而来的。自我驯化是基于生态学的自然选择过程。〔33〕进化论为人类开启了一个自我解释的阀门:承认我们是灵长类动物的后代,但这决不是说我们本身是灵长类动物。在这里,“进化”有两个基本条件:1.任何生物物种的进化是有生态条件的,以强调进化的自然条件。也可以这么说,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物种。海洋有海洋生物物种,这已经不是道理而是常识。2.进化是对环境的关系重构,以强调进化的人为选择。湿地则可能、可以成为各种物种生命共生的自然场所;人类借助湿地条件也助力了人类“自我驯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环境生态与生物的基本关系由食物所建立。“我们相信:自从我们的祖先从曾经生活过的热带树上爬下来以后,我们就永远摆脱了林栖生活,我们在自然之外建立了独立的文化王国。”〔34〕其中食物成为最为重要的满足生物基本需求(basic needs)的生存枢纽。复杂的人类社会行为是通过男性间竞争和对觅食生态学(即在环境中对食物进行更高效的利用)的自然选择之间相互作用进化来的。在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到农业革命之间的重要环节是栽培驯化,根本动因却是食物。而湿地之所以被人类学家认定为前农业时态的一种重要范式,正是因为湿地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为人类提供最适用、最完整的食物链,其中包含着人类在博物关系中生命驯化的重要过程。
今天,保护湿地已经成为保护生态的一种人类社会行动。这不错,却有失公允。众所周知,生态学是一门探讨生命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人类生态学则是一门描述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在人类生态学中,环境被视为一种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所指定的范围有:空气、土壤、水、生物体,也包括所有人类创造的物质结构。其中生态系统的生物部分——微生物、植物、动物(包括人类)都是其生物群落。而人类活动的“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最为基本的人类生态学的关系结构。〔35〕也就是说,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与其他生物一样曾经与湿地是一体性的,至少是“部分一体”;只是到了后来才被 “主体∕客体”地逐渐分离,进而人类又自封为保护湿地的“英雄”。从博物学的视角,我们要提醒的是:人类与湿地曾经是生命的整体,而全球湿地出现危机,人类是逃脱不了干系的。
今天,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着眼于当下的需求,又要照顾到子孙后代的需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就是保持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允许他们保持功能的充分完整性,以便继续提供给人类和该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以食物、水、衣物和其他所需的资源。〔36〕人类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具有共同进化和相互适应的关系。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社会系统存在两种途径:1.生态系统通过改变自身来应对人类的行为;2.人类改变生态系统,使其适应社会系统。〔37〕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系统也要适应生态系统。如果只让生态系统适应人类社会系统,其后果一定是生态危机。人类在过去和现在都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做恢复和补救工作,以保证可持续的人类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湿地保护与生态学相兼相融,湿地生物性研究又以博物学为学科依据。事实上,博物学与生态学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生态学(Ecology)是认识与揭示自然现象和规律的一门科学,主要研究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博物学与生态学的联系首先就体现在生态学是建立在博物学基础上的学科。“生态学是一门古老学科的新名词”。〔38〕生态学是从生物学延伸而来的。〔39〕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由不得人类因自己的行为不当而伤害到生物多样性。事实上,从生物学本身来看,人类正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样本。“人类遗传就有无限的多样性,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包括肉体和心理的性状,又包括身材和智力。”而除了人类遗传方面的多样性以外,还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40〕换言之,人类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产物,无论是针对大自然的生物种类而言,还是指人类作为一种类型——“人类”性状的差异而言,都表现为无限的多样性。所以,差异成了一种生存的性状和识别,不尊重生物多样性其实也是不尊重人类自己。
逻辑性地,博物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科学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博物性”,主要包括:1.“物种”(包括人类在内)的演化过程;2.在博物学范畴,人类只是生物中的一种,在物种分类上并无特别;3.人类的独特性与生物的普遍性都是相对的;4.自然的生物界是一个共生关系,食物链与生物链相辅相成。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与其他生物伙伴保持着合作关系,属于合作的物种。“人类具有合作性。而我们的基因却是自私的,那么,自私的基因是否造就利他的人类?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41〕所谓“合作”是指人们同别人一起从事互利活动的行为。互惠交换具有现实的普遍性。〔42〕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大量证据表明,人类社会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重要的合作原理正是缘于互惠性,其实也包含着共生关系。反过来说,互惠是人类社会藉以维护社会关系的纽带。同理,“自然的互惠性”是生物的生存条件。这也是人类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理由。
概而言之,湿地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共生的自然条件。从生命进化的角度看,生命是变化的,又是不变的。前者指在不同的条件下的生命形态,后者指生命的共同体离不开与生态的关涉。湿地命题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生命共同体”的奥秘。
五、结 语
就人类历史的进化而言,农业的出现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次历史事件可以替代的重大历史变革,——无论是此前的采集狩猎,还是后来的工业革命,乃至当今各式各样的所谓“革命”“变革”,皆无法与农业相比。人们可以不用电脑,不开汽车,不用微信,却不可以不吃饭。从表象上看,世界上现行的国家体制、社会形制、城市形态也都与农业有关。如果人类没有别的行业至多是活不好,没有农业则活不了,因为农业解决温饱问题。
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业以水为本。从历史的角度看,对水的掌控成了人类定居、城邑形成,乃至国家诞生的重要缘由。人类学的反思性观点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而斯科特新出版的著作《反谷》,对农业灌溉以及栽培驯化两个“农业革命”的历史理由进行抨击,其中湿地命题虽发人深省,但置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语境中,却难免力不从心。
毫无疑问,湿地是自然界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舞台,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共生的重要场所。2020年9月30日,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治理”;〔43〕后来又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44〕这些重要的理念也为湿地保护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注释:
〔1〕“14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https://www.ramsar.org/event/14th-meeting-of-the-conference-of-the-contracting-parties.
〔2〕James C.Scott,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其中Against the Grain是作者有意而设定的双关语,具有“事与愿违”的意思。该书2019年由翁德明译,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反谷》;2022年由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意译为《作茧自缚》。笔者在引用时兼顾三者,择而引之。
〔3〕〔11〕〔16〕〔29〕〔30〕〔美〕詹姆斯·C.斯科特:《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田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8、51、40、299、66页。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2页。
〔5〕〔13〕〔22〕〔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9、290、150页。
〔6〕〔15〕王云五主编:“古籍今注今译系列”之《尚书今注今译》,屈万里注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7、63-70页。
〔7〕任振河:《舜居妫汭与妫汭舜都所在地名考》,《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8〕杨一波:《浅析曾侯與钟铭“营宅汭土”之地理原因》,《齐鲁学刊》2018年第4期。
〔9〕郭小武:《汉字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0-32页。
〔10〕〔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4〕彭兆荣:《乡土社会的人类学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11-222页。
〔17〕陈惠:《兰州市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第7期。
〔18〕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1页。
〔19〕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4页。
〔20〕〔美〕乔·罗宾逊:《食之养:果蔬的博物学》,王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21〕〔24〕〔美〕詹姆斯·斯科特:《反谷》,翁德明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19年,第99、80页。
〔23〕〔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张经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
〔25〕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7、28页。
〔27〕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39-41页。
〔28〕〔32〕惠富平:《中国传统农业生态文化》,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3、16页。
〔31〕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45度的一条直线。在我国的地理人口分布上,线东南方占全国36%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占全国64%的国土,居住着全国4%的人口,是以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为主的环境,自古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胡焕庸线”以西是游牧民族风情,以东则是农耕文明景象。从人口密度与民众生活水平看,“胡焕庸线”的东南各省区,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地说,对比全国人口平均密度,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为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这张人口密度图被附在其于1935年发表在《地理学报》上的论文《中国之人口分布》之后。另外,“胡焕庸线”也是气候变化的产物。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因此西北部呈现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因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变化,今天,“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密度已经有所变化,但总体格局不变。
〔33〕〔美〕理查德·O.普鲁姆:《美的进化:被遗忘的达尔文配偶选择理论如何塑造了动物世界以及我们》,任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74页。
〔34〕〔法〕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5〕〔36〕〔37〕〔英〕杰拉尔德·G.马尔腾:《人类生态学》,顾朝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2、11、120页。
〔38〕〔39〕刘华杰主编:《西方博物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2、393页。
〔40〕〔法〕让·费雷扎尔:《人类遗传》,陆象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4页。
〔41〕〔42〕〔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5、29页。
〔43〕《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全文)》,《人民日报》2020年9月30日。
〔44〕参见马俊杰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人民日报》202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