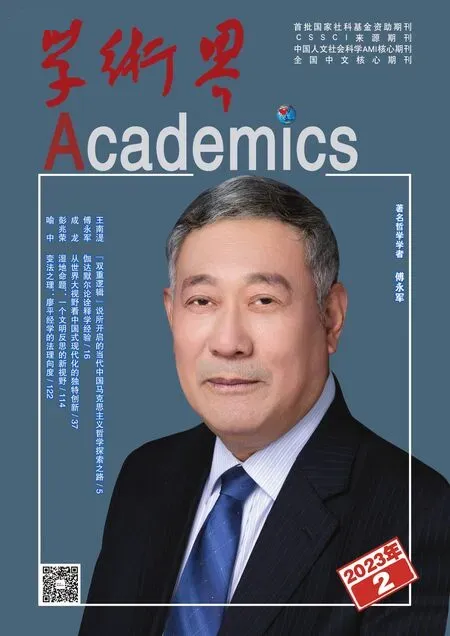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区域国别学语境下的考察
汪诗明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0062)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将区域国别学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这是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必将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注入活力。
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一个新事物,但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是一个新事物。这自然引起学界广泛且高密度的关注,相关论坛应接不暇,相关成果不断涌现。稍加梳理便发现,目前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区域国别学科如何建设;二是区域国别研究如何展开。这两个问题实乃连理同枝,难以分开。在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成果中,谈机遇、唱高调的较多,指出挑战或困难的较少;大而化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较多,具体而微、可操作性的建议或方案较少。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基础研究的界定、研究体系的建构等方面去做一些旨在易于实践的研讨,并结合某些案例分析,来诠释区域国别学以及该学科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某些属性或特征。
一、基础研究的界定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交叉学科,是在一些相关学科基础上交叉出来的。既然是一个在多学科基础上生成的学科,它就一定存在一个基础学科或基础研究的问题。通过比较发现,历史学或历史研究是这一角色的不二之选。
所谓基础研究,是指对一个学科、一个专业门类或一个研究领域的基础知识的系统梳理与认知,对其基本原理的全面和深刻的揭示与阐释。〔1〕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没有基础研究,学科建设如同无源之水。在区域与国别成为学界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领域而未成为一门学科前,学界已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进行过一定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如陈晓律教授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涉及一个庞大的研究对象群,“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单独应对的,它必然要求多学科的合作。但多学科的合作,依然有一个谁来主导,或者说在什么基础上合作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是涉外研究,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所以,研究者的外语能力显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也仅限于此:语言本身并不是区域研究的重点,而是必需的工具,外语不可能成为这项研究的核心和主导的学科。而经济、政治、军事和国际关系等学科本来就有这一块。在这些学科看来,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无非是在自己原有的领地多占一块而已。因此,要以某一学科为主导,似乎也很难服众。这样一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肯定会与他国不同: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科特点考察,只能以现有的世界史学科为主导。”〔2〕也有学者认为是包括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3〕如果仅从本位出发,任何一个相关学科都可以找到使自己成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基础的充分缘由。因为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它们之间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有的是理论或学理上的相通性,有的是知识上的互补性,有的是研究问题的相关性。
如何界定一个交叉学科的基础学科或一个学科的研究基础?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参数就是考察该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与其他学科或其他问题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拟要确认的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与其他学科或其他问题研究之间的关联程度要甚于与之比较的对象,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基础学科或研究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或历史研究就可以被视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这是因为,“一门科学与另一门之不同,在于它要把另一类不同的事物弄明白。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4〕由此可以推导:每一门科学,无论是古典科学,还是近现代科学或未来科学,都存在一个对有关过去“活动事迹”的叩问、当下“活动事迹”的把握以及对未来“活动事迹”的畅想。如果缺少对过去“活动事迹”的追寻,那么何以建立或推动一门科学的发展?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著名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说:“我们决不要忘记,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变化的科学,是要按照物质、政治、道德、宗教、知识存在的一些新条件,进行持续和必要的调整的科学。是在所有时代,在人类的不同但同时存在的生存条件之间进行协调,使和谐持续地和自发地确立起来的科学: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精神条件。历史学就是从这里获得生命。”〔5〕
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进的。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科技等等方面的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既是人的不断进步的历史和物的不断演化的历史,又是各种科学生成和发展的历史。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得益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反过来又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历史就是在研究人类自身,研究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研究科学的前世今生。这也就诠释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真谛和缘由。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诞生前,唯心史观虽触及到了人和人类史,但是从抽象的层面去认识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次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置于一个中心位置,以人的存在及其活动去理解和把握历史。这是唯物史观不同于以往唯心史观的根本所在。因此,历史研究并不是从一个外在于历史的理论或概念出发,而是从历史本身出发,即研究哪个时代的历史,就可去具体地解析那个时代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只要描述出这个现实的社会生活过程,也就能够把握那个时代的历史了。〔6〕人类文明演进的特点及其规律表明: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这些普遍真理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社会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阶段的不竭动力。而这些真理只能通过研究历史才能得以演绎和揭示。〔7〕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每个学科或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也即学科史或学术史,还有必要把历史学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吗?或把历史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吗?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困难,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与学科史或领域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区域国别研究中所提及的历史显然不是指学科史或学术史,也非指某个领域演进的历史,比如经济发展史,而是指一个区域或国家的通史或总体史。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总体史涵盖各个领域的历史,但并不是各个领域历史的拼盘或加总,而是在各种因素合力作用下,一个区域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演进的历史。历史研究考察的对象就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总体史或通史,而其他学科则对应于相关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总体认识基础、认识背景和认识框架。这就是历史学或历史研究被界定为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或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的主要原因。
确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或研究基础不能基于一些人的学科本位主义或受制于传统学科思维,而是要立足本学科的建构原理及其特点,立足于该学科当下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二、研究体系的建构
研究体系的建构是所有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一个规范要求,是一个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客体呈现与主观需求务必实现有机的统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对某个区域或国别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这显然有别于传统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多学科参与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比如,哪些学科理应参与其中,多学科参与是不是意味着参与的学科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具体区域与国别研究来说,虽然区域国别学强调对区域与国别的全方位研究,但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大到民族或国家的文明变迁、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想对此进行穷尽一切的认知或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研究力量来说,由于区域与国别众多,而研究者人数相对有限,分散到某个区域或国别的研究力量就更加薄弱,很难做到对被研究对象的全方位研究。这些主客观因素是不是意味着新学科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又要退回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路?答案是否定的。为避免重蹈覆辙,建构新学科语境下的研究体系就是一条不得不为之举。
(一)学科体系建构
区域国别学科体系的建构层次是较为独特的,它包括基础学科、支撑学科和关联性学科或辅助性学科。
首先,确立支撑学科。
历史学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所谓的支撑学科是指那些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建构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相关学科。这些相关学科有着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研究体系和评价体系,并从各自不同的领域能够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建构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基于这样的认识,历史学也可以视为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之一,准确地说,历史学是一个具有基础意义的支撑学科。为了把支撑学科视为一个有别于基础学科的学科,这里所言的支撑学科是指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根据有关部门的文件精神以及学界已形成的基本共识,文学、经济学和法学被认为是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这里的文学是指外国语言文学。文学之所以成为区域国别学的支撑学科之一,首先是它的外国语言优势。语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沟通的工具,也是学术研究中获取有益文献的重要路径,更是人们认识本土以外世界的一扇窗。此外,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其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一种体验与感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某种情结与共鸣的产物。就此而言,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对象,它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是人们表达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看法的一种方式或载体。因此,研究对象国的文学,透过文学作品来管窥该国的民族心理活动、生活态度、精神风貌以及社会制度变迁,这是区域国别研究舍弃不得的一条独特路径。经济学是探讨人类社会处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经济活动以及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的科学。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看来,“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另一方面,经济学构成了社会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研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8〕如果一门学科既涉及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又关联到创造生产方式和物质财富的人,那么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就自不待言。当各国都把发展民生、提升综合实力当作优先事项时,发展经济就成为各国政府一个聚精会神的目标。发展经济需要统筹规划,需要协调人财物的关系,需要疏通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需要考虑眼前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不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中非常现实的议题吗?法学是以法律及其文本、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这里提及的法学是指一个大的学科门类,与历史学和文学等学科门类一样。与区域国别学有关的一级学科主要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中政治学下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二级学科以及社会学下的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二级学科都可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学科平台。
其次,确立辅助性学科。
做到对区域或国别的全方位研究,如果仅仅依赖于基础学科和支撑学科,那显然是不够的。一个区域或国别的方方面面,都有其相应的学科为其提供认识视角和知识系统。在现代科学注重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技术科学都可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找到一席之地。比如说,研究一个区域或国别的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通常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只能提供一些宏观的认识背景和认识原理,而对于与环境、生态有关的科学知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求之于环境科学。环境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包括生态学、生物学、动物学、海洋学、大气科学、土壤学、地质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它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研究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执行以科学为基础的应对方案的科学。在宏观上,环境科学要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关系,力图发现人类社会活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调的规律;在微观上要研究环境中的物质在有机体内迁移、转化、蓄积的过程以及其运动规律,对生命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等。〔9〕不难看出,一些辅助性学科所提供的所属领域的专业性、科学性知识及其原理,恰恰是人文社会科学所无法给予的。借助于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及其原理,不仅可以拓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视阈,丰富其研究内涵,也可使其经世致用价值得到充分的诠释。
(二)确立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
传统学科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大都处在一个自发的状态。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这是研究者个人的事情。这就出现了一些可以预料的现象:有些领域或议题受到了很多人关注,有些领域或议题则不太受关注,甚至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久而久之就成了所谓的“冷门”“偏门”甚至“绝学”。因此,传统学科背景下对某个区域或国别的认知或研究是不完整的,甚至很片面。区域国别学科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如何实现这一构想?建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就是应然之举;若要建构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对一些概念的模糊认识就有必要得到澄清。
首先,明确区域或国别研究的内涵或要求。
现在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区域或国别研究就是对某一区域或国别的方方面面的研究。〔10〕这一界定可谓切中肯綮。不过,这一界定给人的感觉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就像一个大篮子,什么都可以装进去。但现在的问题是,要装的东西着实太多,这个篮子有可能装不下;或者有些东西没有必要装进去,或者有些东西没有必要装进这个篮子里,可以放进其他篮子里;或者有些东西早已放进其他篮子里,而且那些篮子的空间还很大,没有必要再把它们倒腾出来。这正是目前区域与国别研究较为令人困惑的地方。
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注重区域或国别的“内部”而非“外部”研究。所谓“内部”是指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宗教、环境等,而“外部”主要是指对外关系,也就是外交或国际关系。注重“内部”而非“外部”研究是由区域或国别研究这一概念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特质或属性主要是由“内部”而非“外部”因素决定的,内部的很多因素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民族性或国民性等有关。从研究的范式上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外部”研究习惯性地从概念、理论或模式出发,然后寻找一些案例,最后进行某种前瞻性的预测。因此,“外部”研究通常是务虚的,而“内部”研究恰恰相反。“内部”研究是以资料或事实来说话,以求真为旨归,不信口开河,也不需要预测,因而“内部”研究是“实实在在的”。从实际需求来看,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与我国进行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国家将越来越多,但我们对对方的了解却非常有限,有的是“绝对缺乏”。〔11〕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些对象国“内部”的真情实况是时势所需,容不得虚妄之言。
其次,全方位研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什么都要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的“全方位”研究,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是指对研究对象所有重要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其他方面做力所能及的探讨。这是因为,姑且不说对他国进行所有方面的研究,即便是对本国的研究,这一目标也显得过于理想化。鉴于此,“全方位”研究可以作如下理解:一是不排斥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只要实际需要,都要认真对待,不能持有偏见;二是不能忽视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的研究,只要被认为是重要的,就不能有任何遗漏,要“全单照收”;三是全方位研究也有主次之分,不可能平均用力。若要做到上述几点,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体系的建构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1)确立主要研究领域
何谓主要研究领域?主要研究领域是指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本质性影响的领域。如果这些研究领域缺失,那么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就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出现错误。
就国别研究来说,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包括语言和文学)、宗教、艺术等是认识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域。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具体情况。比如,有的领域对一些国家很重要,但对另外一些国家也许就不那么重要,宗教就属于这一情形。因此,确立国别研究的主要领域,一定要根据对象国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区域研究也是如此。世界上存在很多自然区域、经济区域、政治区域和文化区域,还存在一些跨区域(如亚太、印太)和次区域(如东非共同体、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对这些不同类型或不同属性的区域研究就不可能按照统一的模式。比如欧盟研究与东盟研究就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按照欧盟研究的模式来研究东盟,那么东盟研究就失去其方向和目标。由此可见,确立区域或国别的主要研究领域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研究者对区域或国别研究整体性认识的一种反映。
必须指出的是,确立主要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将非主要研究领域排斥在外,事实上也无法做到,因为很多研究领域之间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没有对相关领域的了解或研究,所谓的主要领域的研究恐怕也难以取得预期目标。
(2)确立主要研究议题
在确立主要研究领域后,每个领域要研究什么,就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每个领域涉及的议题是非常多的,而研究力量又相对不敷,是不是每个议题都要研究?另一方面,并不是每个议题都有研究的显著价值。传统学科背景下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些议题看似有研究价值或意义,其实研究价值或意义并不大,甚至没有研究价值或意义。
确立每个领域的主要研究议题,首先要立足于该领域的主题内涵,即这个领域涉及哪些内容;其次,要立足于主观研究需求,即为什么要去研究,研究的目的或目标又是什么。只要弄清楚上述问题,盲目研究或任性研究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避免或克制。以澳大利亚政治研究(史)为例,除了需要了解澳大利亚联邦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和历史演进外,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了解并且要予以重点关注的?澳大利亚是一个西方政党制国家,这是其政治基础,也是其政治特色。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虽然该国存在多党制,但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工党和自由党,每次联邦大选主要是在这两个党派之间展开角逐。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党是单独组阁,而自由党通常是以执政联盟的方式来行使权力的。自由党为何要组建执政联盟?是不是在联邦众议院的席位达不到组阁的最低要求?作为执政联盟的另一方,国家党〔12〕为何甘当自由党的“助手”?执政联盟很少发生分道扬镳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除了解政党政治外,联邦与州的关系、“联邦主义”以及“新联邦主义”的内涵及其影响、全民公决在澳大利亚政治体制变迁中的重要作用、〔13〕澳大利亚政治文化中的移民因素和原住民因素等,都是澳大利亚政治(史)研究中的主要议题。
在确立主要研究议题时,很多人倾向于运用宏观视角来审视。宏观研究的优势在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它建立在全面和扎实的中观和微观研究基础之上。就国别研究来说,民族的源起与成长、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地缘政治的变迁及其影响等,都可以纳入宏观研究范畴。但是,微观研究也不能忽视。微观研究的优长在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于对一些细节的考察与把握,而这些常常被忽视或轻视的细节可能就是问题之源和真理之门。因此,微观研究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块重要拼图。
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来说,由于国情和区域情况不同,有些比较复杂,有些则相对简单;人们的认知需求也存在差异,这使得研究体系的建构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此外,研究体系的建构只存在现在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因为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它们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就出现了如下的可能性:某些领域或某些议题在过去是不太重要的,因而不会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时过境迁,它们的重要性开始变得显著起来。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基于辩证法的视角对区域国别研究体系的建构进行动态的考察,切不可有一劳永逸的怠惰思维。
三、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统合
传统学科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有其功能方面要求的,但过于笼统与含混,不仅学术功能不突出,其社会应用功能也较隐晦。区域国别学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要注重其多功能性的释放,要处理好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要确立合理的研究范式。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有些人不无这样的担心:区域国别学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性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属性的浅读。首先,学术研究是一切学科立足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走不远的。区域国别学概莫能外。比如,1957年在美国成立的“非洲研究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是“一个对非洲事务有兴趣的所有个人和机构开放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使命就是把对非洲持有学术和专业兴趣的人团结在一起”。〔14〕学术研究在美国的非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一个较受启发的案例;而美国的非洲研究的新范式源于对非洲哲学的讨论,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2002年,波林·豪恩唐迪吉(Paulin Hountondji)的《非洲哲学:神话与现实》(African Philosophy:Myth and Reality)再版。〔15〕阿比奥拉·伊瑞勒(Abiola Irele)为该书出版撰写了新的导言,并抛出了非洲人的哲学是否一定是“非洲哲学”(“African philosophy”)的命题。〔16〕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较易回答的常识性或知识性问题,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术话题,需要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此进行溯源、考辩、论证和推理。
学术研究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全面认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旨在追求真理和理论创新;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在宽度和深度方面推动学科发展的过程。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系统和深入的学术研究,应用研究的问题意识缘何而来?问题意识不是凭空想象来的,而是源于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对真理生成细节的叩问和思考。当然,应用研究对学术研究有反作用。应用研究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案例;没有应用研究,学术研究的理论创新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因此,区域与国别研究应该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统合起来。
首先,学术研究的时代意识。
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很早就有。杨共乐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区域研究不仅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区域研究的历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区域研究方面的杰作。《大宛列传》列在《史记》中,是《史记》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把它抽出来,也是一部完整的区域研究作品:其内容涵盖区域内的国家,涉及区域内的民俗风情、区域内各国的物产,区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区域内国家的人口结构与兵力状况。”〔17〕类似的证据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区域与国别研究渐受重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在高校布局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为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基础。”〔18〕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迎来了一波发展高潮,一些高校或科研院所纷纷建立了国别或区域研究中心。上述事实验明,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并且在传统学科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区域国别研究还是满足不了新时期学科发展以及国家扩大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学科背景下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存在一些弊端,如过分偏重学术,甚至出现“为学术而学术”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学术研究中时代意识的缺乏有关。也许有人会对学术研究中的时代意识提出质疑,甚至不屑一顾。但从学科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应与时代脱节。对于学者个人而言,关起门来搞所谓的纯学术研究无异于作茧自缚。学术研究中的时代意识并不是“短视”或“浅薄”的表现,而是由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和目标所决定的。〔1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20〕
学术研究仍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其他层面或维度的研究就会流于表层,也很难持续下去,即便是应用研究,也需要学术研究思维的加持。同理,如果没有时代意识的牵引和渗透,学术研究就会变得封闭逼仄,甚至枯燥乏味,其价值就难以得到自证,更不消说他证了。
其次,现状研究的历史思维。
当下兴起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把现状研究置于一个显著位置,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这也是这门新学科问世的一个重要背景。传统学科背景下,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分属不同的学科或不同的专业。比如国别史被纳入世界史范畴,现状研究进入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划归政治学,列在法学门类中。这样的学科分类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和传统思维下的产物,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比如学科界限泾渭分明,很少发生交叉。久而久之,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就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领域。更令人不安的是,传统学科背景下,从事现状研究的要远远多于历史研究的。对于其中的原因,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是现状问题更受关注,现状研究性价比高;二是现状研究门槛较低,甚至没有门槛。我们注意到,从事现状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的,什么专业方向的都有,什么层次的人都不乏见。第一个原因是与公众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关;第二个原因也的确是事实。比如在本硕两个阶段或任一阶段,如果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那么博士阶段就很少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但在本硕两个阶段或任一阶段,没有接受过国际关系方向训练而攻读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博士学位的却大有人在。这种学科认识和人才培养模式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从事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同质化研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炒作概念或对某一理论或原理进行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几乎成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甚至衍变成一种学术生态。
鉴于此,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与国别现状研究就要形成自己的特色。第一,要对现状研究的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一些人看来,现状研究就是为现实服务的,为决策者提供相关信息与决策依据,这种认识显然是狭隘和不全面的。现状研究并不只是服务于现实需求,或者说现状研究与现实需求之间并不机械地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其历史演进当中,过往的成功得失就是其前进的基础,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第三,现状研究也是有其门槛要求的。所谓门槛低或没有门槛,那是一些人的认识问题,当然也是学术评价缺乏一个公信标准的问题。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状研究须有历史思维。所谓历史思维,就是把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置于一个历史维度下去思考、观察和分析,不能从现状到现状。就这一点来说,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区域或国别现状研究需要有意识地注入历史思维,要“发挥历史学科从长时段把握时代特征的优势,把现实问题纳入历史纵向发展的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揭示现实问题的本质及其所蕴涵的时代特点,研判问题的走向,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避免研究碎片化。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预测,需要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更需要宏观的历史见识和阅历。史学研究的积累可以为透视现实问题提供长时段的历史洞见”。〔21〕
再次,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智库导向。
传统学科背景下,区域与国别研究更多地属于个人层面的事情。研究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多半是出于个人的偏好,以致“为何研究”就不是一个导向性的问题。在区域国别学背景下,“为何研究”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今后的学科设置、研究方向的确立甚至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等都要围绕“为何研究”这一主线来铺展,避免“无用之学”的出现。侯赛因·库斯罗贾(Hossein Khosrowjah)在谈到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时说:“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不久的区域研究的源头已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区域研究的开启与美国政府的情报和军事动机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这已不是秘密。现在,这段历史得到了参与创造区域研究的那些人的公开承认,并且时而引以为傲。”〔22〕曾经担任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于1964年写道:“这是学术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事实,区域研究的首个重要的中心……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今天,这仍然是正确的,而且我希望这将一贯是正确的,即拥有区域研究项目的大学与政府的情报收集机构之间存在高度的依存关系。”〔23〕
诚然,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动因与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大不相同,在研究理念和目的方面也存在根本差异,但是,美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中的一些做法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区域与国别研究要搞开放式研究,不能封闭在校园里;要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不排除某些“订单”式研究。这是区域国别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和优势所在。正如刘鸿武教授所指出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征使其天然具有特色智库的功能。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实现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专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路径之一。”〔24〕为此,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关注对象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重大或重要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领域的重大或重要问题引领着所在国的政策决策导向。
四、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
研究方法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括研究思路、研究线索、研究手段或研究工具等内容。由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和认知路径,所以,不同的学科很可能就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25〕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包容性特点使得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组合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传统学科背景下,由于学科之间有着较为严格的界限,因此,与本学科有关的研究方法通常被打上了学科的印记,比如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区域与国别研究兴起后,其研究方法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26〕田野考查(在地研究)、母语研究(包括当地方言)、定性与定量分析等,是当下学界提及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
跨学科研究的概念并不新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跨学科研究方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但大多停留在口头上,鲜有落实在具体研究中。既然这是一个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学术创新的一种进路,为何没有付诸实践?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1)学科知识储备不足。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且与传统学科分类和传统教育模式有关。(2)主观能动性不足。一些人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跨学科研究方法不感兴趣,更不愿为此去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以文史交叉为例,常言道:文史不分家或文史是一家。蒋济永在《文学、历史、记忆的话语基础与阐释路径》一文中写道:“新历史主义让我们谈论历史时出现了两种历史观:一是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叙述的历史。根据海登·怀特的观点,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历史,实际上是叙述的历史,或历史话语的历史,事实的历史作为过去的事件是不可能重演的,但是,能留存的历史就是被历史文献记载或叙述的历史,作为过去历史事件的本事已经不存在了。西方模仿或再现文学理论认为,文学就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或再现,而社会生活是由社会众多个体及其相互关联的历史事实构成的,文学是用语言去模仿和再现它的,因此,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是它对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叙述,也即,文学描绘和叙述的社会生活和事件已经不同于社会生活的本身。于是,历史与文学的共同话语基础,就是描绘和叙述的生活(历史),简言之,就是叙述。”〔27〕这就是说,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文学,叙述是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共同方式。就此而论,它们在描绘或再现过去的历史时是有某些共同语言和共同进路的。但在传统学科语境下,文史学科的交叉是很少发生的。这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往往有意无意地给自己贴一个身份标签:研究历史的,或是研究文学的。于是乎,研究历史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与研究文学的那些人区隔开来;反之亦然。这样一来,研究历史的那些人,如果自己的文学功底不好,反倒成了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研究文学的那些人也会找到类似的托辞——自己的历史知识的贫瘠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狭隘意义上的专业分工或广泛意义上社会分工的一种必然。
多学科或跨学科并不是一句空话,也非学术作秀。首先,要具备相应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规范。有些人在行文中提及了一个政治学概念或政治学原理,就自以为运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这显然是自欺欺人。使用某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并非借用或解析一个名词、概念或原理那么简单。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适合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有的议题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路径根本无用武之地。再次,多学科参与并不表明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地位是平等的,而是有重点和辅助之分。一般而言,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会舍近求远去捡拾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现状研究的人也不会把历史研究方法置于首位。最后,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并不一定就能得出确论。如果运用失当,反而会弄巧成拙、多走弯路,离研究的本意就会越来越远,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似是而非或不知所云的结论。正确的做法是,既要立足课题研究本身的实际需求,对症下药;又要根据研究主体的条件,量力而行,不慕虚荣,力争做到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统合。〔28〕
研究方法的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不仅是由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多学科性或跨学科性所决定的,也与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有关,更与时代进步对学科发展的新要求不可分割。因为“跨学科涉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点,而这些元素往往就是新的科学生长点和新的科学前沿,很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使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29〕
五、结束语
区域国别学诞生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以及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语境之下,这使得这一学科的学科价值、学科使命、学科特色有别于传统相关学科。何以体现该学科的上述特色,这就需要学界从其研究基础、研究体系、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探讨。这是本文立意的初衷。确立基础学科是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以及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首要一步,模糊不得;建构由学科、研究领域和研究议题所组成的研究体系,是确保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全面性且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的有效之举;在研究范式上做到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统合,是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彰显区域与国别研究功能的必要前提;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机组合,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应有之义和特色所在。眼下学界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对这一学科抱有很高的期待,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国内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尚处在一个自发甚至被忽视的状态。所以,区域与国别研究一定要脚踏实地,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不急功近利,不盲目追逐热点,少谈“主义”和理论,多作一些具体而微的研究。〔30〕只有这样,区域与国别研究才有可能行稳致远,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1〕汪诗明:《大洋洲研究的新进展、不足及未来展望》,《学术界》2020年第5期。
〔2〕陈晓律:《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几点浅见》,《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3〕王缉思:《浅谈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参见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编委会编:《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页。
〔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7页。
〔5〕〔法〕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高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第33-34页。
〔6〕隽鸿飞:《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个注释谈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30日。
〔7〕杨共乐:《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8〕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9〕“What is Environmental Science?”,January 3,2019,https://easciences.org/what-is-environmental-science/.2023-01-09;“Environmental Science”,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environmental-science.2023-01-09.
〔10〕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 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
〔11〕罗林:《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担当——从“大国之学”到“大学之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6日。
〔12〕澳大利亚国家党成立于1918年,原名乡村党。1972年,该党在昆士兰州改称国家党。1975年在全国范围内更名国家乡村党。1982年改称国家党。
〔13〕汪诗明:《试析1999年澳大利亚共和表决失败之原因》,《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对澳大利亚全民公决意义的几点认识》,《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14〕〔16〕Edward A.Alpers and Allen F.Roberts,“What is African Studies?Some Reflections”,African Studies,2002,Vol.30,No.2,pp.11,12.
〔15〕Paulin Hountondji,African Philosophy:Myth and Realit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2.
〔17〕杨共乐:《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
〔18〕罗林:《着力构建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1
1/t20221109_5562773.shtml.2022-12-20。
〔19〕汪诗明:《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
〔2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22-10-19。
〔21〕梁占军:《构建区域国别学,世界现代史大有可为》,《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
〔22〕Hossein Khosrowjah,“A Brief History of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rab Studies Quarterly,Summer/Fall 2011,Vol.33,No.3/4,p.134.
〔23〕B.Cumings,Parallax Visions: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173.
〔24〕刘鸿武:《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推进路径》,《大学与学科》2022年第3期。
〔25〕这里使用了“很可能”而非“一定”的表述。这是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没有专属于某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谓的某某学科研究方法,无非是下面两种情况:一是某某学科最早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久而久之就被赋予了某某学科的属性;二是某某学科比较多地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而且使用的效果比较好,给人的感觉就是某某学科的研究方法。
〔26〕有学者认为:“如果把单一学科比作苹果(一种水果),那么多学科就是水果沙拉(多种水果),仅仅是不同种类水果的‘大杂烩’,但不同种类水果间并未融合或交叉;跨学科将不同种类的水果相互融合加工成为冰沙;超学科则更进一步,将多个学科融合得更为彻底,制作成由多种水果混合而成的冰淇淋。”参见步一、陈洪侃、许家伟、王延飞:《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解析:理解情报学术中的“范式”》,《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
〔27〕蒋济永、蒋必成:《文学、历史、记忆的话语基础与阐释路径》,《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28〕冯绍雷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29〕步一、陈洪侃、许家伟、王延飞:《跨学科研究的范式解析:理解情报学术中的“范式”》,《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
〔30〕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任晓:《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