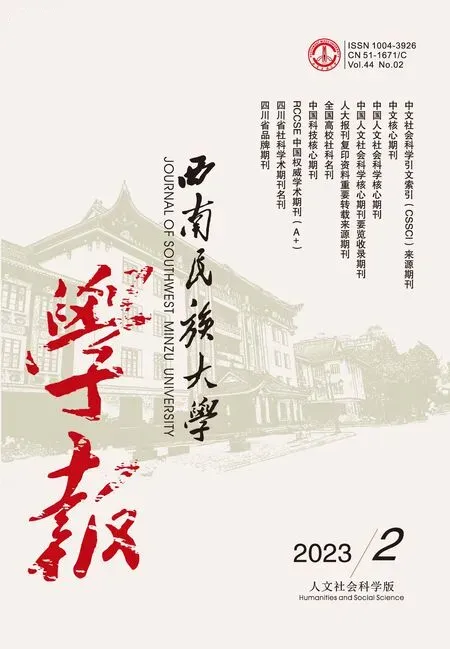“晦暗”在场:地方的构形、隐匿与逃逸
韩 伟 高渊圆
[提要] 地方是具身认知与有关“晦暗”的经验共同构成的情境关系,铭刻着人们独特的情感态度和历史记忆。“晦暗”内在于人与地方的关联之中,其在场深刻地影响着人对地方的感知与理解,关系着此在意义的流动与生成。在现代性及数字的形而上空间中,真实和具身的双重缺席,阻滞了身体和空间深度关系的发生,个体已不复“在地”。此在生命的萎缩,是这一时代个体共同的空间感受。存在的焦虑要求我们正视认知的具身性,通过对“晦暗”的知觉与辨识,寻求在后现代性空间中逃逸的多种可能,并建立起与数字语境相适应的“地方”的经验与想象。
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是空间性的。空间性的哲学问题,关心的是原初场域如何向存在者敞开的问题。“定位”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根本方面,也是我们在世(being-in-the-world)的一种根本状态。在事物之间,我们唯一的存在,在意识中形成了一种空间性焦虑(anxiety of spatiality)。《神曲》开篇便是“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1](P.1)《山海经》的“山”与“海”,也是我们的祖先在混沌中所觅得的空间位置,“在地”的存在观念,于人类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形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科学的进程中,空间这一现成概念,以其成熟的建构和严密的体系,最终远离了现象本身。当相对论物理学确证了绝对客观性只是个虚幻的妄想,量子力学将世界的现象更正为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之时,①正如在物理学科中所发生的那样,文艺批评也意识到空间与颜色一样,乃是我们受限的肉身景象,是在离我们足够近的周围,存在着的有关经验的事件。科学和艺术、哲学及心理学都开始发觉空间是存在于我们之中(space in relationship),而非我们居于空间之内,事件的流动和我们所产生的关联,对空间的构成及其结构至关重要。因此,“我”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央,也即“知觉域”(sensory fields)的中央。换言之,这一知觉域构成了“此在”的前发生境域,“此在”以此为焦点,朝着世界背景逐渐扩散并隐没。于是我们能够始终位于一个极其私人的、特殊的“地方”,且仅有“此在”才具有朝向“地方”发问的特殊性——空间性的问题,就转变为“此在”如何使“地方”显现的问题。
我们和空间的关联并不是一个精神主体与一个遥远的对象间的那种纯粹的关联,而是一个居于空间中的、具身而有限的存在和他所密切相关的环境或场所之间的模糊的关联。而这种模糊,是德勒兹意义上差异(difference)与基底(foundation)之间的模糊,也是“此在”之于地方所被要求的东西。被凸显的“此在”在某种程度上对立于这种不能与它区分开来的基底,后者也始终贴合着它所分离的东西。换言之,“此在”从这地方中被区分出来,同时作为地方的一部分而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人与“地方”的本质关系在于栖居(dwelling),也通过此关系进入到空间中去。于是,在“此在”与地方的深度纠缠之中,我们能够辨识出一种可称为“晦暗”(obscure)的东西,它处于经验的维度,既表示过去在当前的持存,也作为生成过程的支撑物,确保了“此在”的充足条件。保有对“晦暗”的感知能力,乃是“此在”的本质属性。换言之,人正是在地方的“晦暗”中,获得了自身的存在。
一、地方的现象:在“晦暗”中构形
从现象感知到语言表达,思想得以诞生并与之融合交织。这贯穿现象、思想、语言三者的基本节点,人所无法摆脱的出发点——概念,在其积累与建构中走向了背反。“植物学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丛,地理学确定下来的河流‘发源处’不是‘幽谷源头’。”[2](P.83)经典的现象学要求“朝向事情本身”[3](P.42),而这一朝向并非向“前”,而是回返与否思,一种与现成概念相对、与方法崇拜相对的多重意义上的“返魅”——返回思想本身,返回语言前端,返回现象源头之魅。
当我们返回语言的前部,地方的现象就从我们晦暗的周围生发。“当我说某物在桌子上时,我在心理上总是置身于桌子之中或者物体之中,这在理论上符合我的身体与外部物体之间的关系。”[4](P.101)段义孚指出,方位介词必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不同语言中的空间指示词也总和人称代名词紧密地关联,英语中的“this”和“that”就包含着距离的暗示。不仅如此,世界各地的民间往往延续着约定俗成的量度标准,例如“拃”“腕尺”“掌尺”等,即以身体的某一段长度来测定距离。而即便是“一条凶猛的狗”这样没有描述位置和距离的措辞,也暗含着“狗太靠近我”的空间感受。尼奇克(Christian Norberg-Schulz)认为,“个体感知的空间具有一个中心,即一个具有感知的人……随着人的身体移动而发生变化”[5](P.13)。客观的立场和测量的手段无法把握空间与地方的结构,相反,“距离和方向都被体验为切近或遥远的特质,甚至当它们被视为一些路和方法的时候,人们也是通过特定的意义去认识它们的。”[6](P.10)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识是在我们的身体性经验中建立的,我们通过有限的和确定的知觉与世界共同外延。“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给我们的,而这与世界的接触正是知觉给予我们的。”[7](P.20)在梅洛-庞蒂那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身体与世界发生关联,从而建构自身。于是,那种没有身体的、理智的均质空间观念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空间是异质的、是和人的身体紧密联系的,是和我们这样一种被抛在世界中的存在者的处境有着紧密联系的。这种身体性经验是一种整体性经验,人类通过其唯一的存在性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空间图式。一方面,对空间的认识需要放置在整个知觉域来理解。感官感觉不能够单独地使我们置身世界的体验当中,但嗅觉、味觉、听觉等这些对距离不够灵敏的感觉,与视觉和触觉的空间化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于世界的空间特征和几何特征。另一方面,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我们意识的焦点和范围,但存在着比我们选择性关注的那些元素多得多的东西可以去体验。“规律仅仅是对物理事件的近似表达……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澄清其晦暗。”[7](P.9)然而,关于空间和地方的思考常常被局限于分析性的量化、结构或地图,但人从来没有真正抵达过古典思想家所假定的“完成了的人”(un homme accompli),科学家可能已经忘记了人类的简化性只是一个假设,习惯了否定或已忘记我们经验的真实性质。感官对空间质量的估量仅仅是在意识当中构建起的一种几何式的认识,这与对其价值的感知仍相距甚远。波罗的海和柏林如何能够引起无限的感觉?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故乡的地方感如何体现在狼柳散发的气味上?仅仅一个传说如何就能够使克龙贝格城堡环绕着神秘的氛围?因此,尽管地方由我们的外在感知塑造,即通过把我们所见的外在事物进行组织,但也由我们的内在感知塑造——通过连接我们的内在状态。我们要再一次到与我们的思维和感动方式密切相关的事物中、到我们的意识和经验中,去寻找地方的现象源头。
我们所感知并讨论的空间和地方,是存在于共同经验意义上的一种关联。在词汇学中,“空间”与“地方”也是人们熟知的表示共同经验的词语,这已经意味着其概念乃是基于某种共同经验产生。两者相互定义,区别于经验深度上的晦明之分。空间是敞开的、理性的,地方则是有界的、感性的。“地方,将人放置在了一种特定的方式中,既揭示了人自身存在的外部关系,又揭示出他自己所拥有的自由和现实的深度。”[8](P.19)相较于空间,地方更多的是生于经验的、个人历史的层面。充分的经验使地方的具体性从空间中显现,在无差异的风景中得以区分,从而使地方具备可见性。科学思维上的勤奋,可以使人获取一个空间足够的抽象知识或环境的欣赏,但是摄取关于一个地方的“感觉”,则需要对“晦暗”的经验,这些经验难以用具体语汇浇筑,是内生于人的身体中的。这些经验是视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体验的奇特混合,呈现为两种生成路径。其一是重复的经验,它是自然规律与人为规律的独特调和,大多转瞬即逝且平淡无奇,不自觉地随着生活的感知融入了一个人的肌肉与骨骼之中。它们是有界且个性化的,但又非全然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主体间性的缘故,这些经验可以进而构成普遍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突破了狭隘地方观念的经验,体现为一种与世界连接的开放态度,这一体验在杰夫·马尔帕斯(Jeff Malpas)那里得到强调,它往往存在于流动性空间中所产生的“无边界”的地方感,并在现代生活中显著地增强着它的影响力。[9](P.309-310)通过经验,地方成为了存在的第一性,事物在地方中获得它的位置并得到澄明,同时,存在也能超越地方,获得自身位于世界之中的意义。因此,地方的生命在于人,人作为地方的一部分生存于其中,两者在经验的层面上很难区分。地方的实质,就是回到人与空间发生关系之时,感性经验所产生的精神外显——同时也是地方的自显。
身体经验与此在意义,构成了地方的具体内容,它具有尺度上的变化,小到房间一隅,大到整个世界,但是,“在任何尺度上,地方都呈现为一个整体,一个自然事物和人造事物所构成的综合体。”[10](P.141)在此不可分割的整体中,这三者之间交织粘连的东西,便是“晦暗”。经验本质上的含混,有着智性和语言无法涉及的“亲身体验的感性质地”(the sensuous texture of lived experience)[11](P.218),使得人在认识地方的源头就存在着规律不可触及的“晦暗”,存在着认识论所不能统摄和标记的隐蔽沉积。与其说“晦暗”是一种物,不如说是内在于事物间性的一种质素,其内容仍然是一种关联,这便是“此在”与“地方”之间所紧密靠近的那种关联,它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某一存在,而是充满了真实的对象和无止息的行动。空间理性犹如电脑建模般整齐精密,然而地方的“晦暗”,即那些存在于价值维度之外的、犹如积尘般的智性松弛之地——沙发上轻微的凹陷、书桌上烫出的重叠杯印、玛德琳蛋糕的香味等等——引诱着感性经验的相认。这些异质性的褶皱,压制思考与哲学,压制理性和算术,压制永恒和本质,却是在地的有力证据,因其深刻地根植于个体实践本身,促使了人性的自由和解放。而如若我们不是在捕捉这些“晦暗”,便就不是以身心在经验这一切,而是在立义了。立义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把活泼、生动、立体的现实具体的事物坍缩成一个词语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呢?在卡尔维诺那里,“地方”作为“晦暗”的显现样态,始终隐伏于形式逻辑的后场,“虚无”的复杂构成——乌檀和槭木的纹理、节疤、幼虫洞孔以及半圆的凿刻,以及“乌木林、顺流而下的木排、码头和窗口的女人……”[12](P.121-123),这些难以用语言去澄清和归纳的部分,都是“地方”在运算和机制之外顽强的居留形式。高度理性的秩序和权力使之“隐蔽”(invisible)的,正是“地方”的涌现,形式最终还原为棋盘上的一块空方格。[12](P.133-134)当忽必烈汗要求波罗讲述这些描述之外的、未用言语填充过的空间,两者的对谈只能进入沉默。这“不可被描述”的,就是这“晦暗”的在场,这种难以够到语言和标准的“感知”,也是地方的一种重要形态。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在场功能,却又处于德勒兹意义上的逃逸线,它流动并变化于理性的罅隙,似乎无处不在,却又在语言的范畴无影无踪。因此,“在地”的晦暗,不是空间内部的一个物化的坚核,相反,它是经验和情感一种奇特的混合生成,是感性经验面对理性认识的自反,是人的“此在”与世界的交通——此乃晦暗的居间性,也是“此在”的居间性。
二、真实与具身的不在场:“晦暗”的隐匿
“此在”始终携带着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身体场,我们的感知便源自这中心的身体,经由身体,我们获得了感觉并经验当下对象的原始方式,从而与世界相互感知、经验与理解,形成稳定的意义流动。不同的感知和经验方式,显现着“地方”相异的尺度,进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主体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人对“地方”敏锐觉察,将深刻地影响主体与世界的具体关联。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对“晦暗”所失去的“可知性”(knowability)的知觉。
在非现代和前现代性的空间中,传统的整体性的有机生活为其代表,稳固的空间关系保证了这种生活内部的再生性,植物、土地、家宅以及季节的变化富有耐心地编织着每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体——个体生于大地,并与其亲密无间。在现代生活出现之前的普遍的空间记忆中,身体与地方的亲和力是关于这种整体性生活的普遍内容,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并保持自己的语言、风俗、起源和认同。而现代性的分裂,其一就是人和地方的分裂。一方面,现代空间的孳生,就是以消减地方性为前提。这里不再有石块,“桥”就是它作为物所呈现的最小尺度——事物可供描述的最具体的单位就是它本身。地方被约减为单纯的地点(location),难以支持具身经验的生长。这种无法储存“晦暗”的积累、可在其表面任意布局的均质化地理事物——在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那里被称为“非地方”(non-places),加拿大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则命名为“无地方”(placelessness)——“建筑者所具有的任何感同身受,都丧失在了被方法论所局限的视野之中。”[13](P.92)技术之物,将地理空间作为一个他者的对象,强加以粗暴的秩序。另一方面,“此在”与地方关系的紊乱造成了个体严重的单子化。个体被抽离于地理空间的具体现实性,在此类福柯式的空间中被定位、分类、分布、调节和识别,处于此种境况中的个体,其存在性构成便仅剩下他的位置和职能,“现代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成为了自我目的的手段”[14](P.706)。流失了丰富性和内在性的个体,已经丧失了识别和进入地方的能力。总而言之,现代空间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着人身体的一部分。
数字经验的产生与发展乃是对现代性经验接而续之的,其连贯性投射于空间交互界面的媒介谱系,浓缩在“视域”经验的更迭之中。在现代性发生期,随着列斐伏尔“抽象空间”的显现和占据主导,视觉语域逐渐成为日常经验的首要语域,这是空间知觉方式的一个根本改变,个体的感觉方式被削减为“移动的凝视”(mobilized gaze)。于是,作为个体赖以进行观看的必然中介,空间的视域即意味着个体在主观视野中的绝对占有,深刻地影响着这种无需他者承认的自我主体之确立。因此,对于视域话语的争夺,隐现着个体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过程,这不仅是从现代性经验到数字化经验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凸显的关键方面,更是现代空间之于主体的本质要求。借鉴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有关“门窗”的论证,现代性将人与自然的空间关系从“门”引入“窗”内,经过对同一空间的内外分割,人们有关空间的经验便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单一的向度。19世纪的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提出“全景视角”(panoramic perception)概念,揭示了现代技术加速以对空间前所未有的克服,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全景视域(panoramic view),主体在某种意义上被规定了观看的距离。而这一距离的设置,便将个体从原有的、所置身的传统及自然的时空中剥离出来,抛入全景之中,并与所观看之景形成对立。[15](P.52-69)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技术引发的分隔,使得空间的内部和外部一分为二,原先置身地方的个体抽离于地方之外,前景消失,只余下一览无遗却又看不清细节的远景,外部形象原先所具有的认知距离被大幅取消,身体周围的“晦暗”被尽然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算法预设的交互页面。在本雅明那里,主体和所视物之间的视野前景正是使事物在时空中具有独特性的根本保证,认知距离的消除意味着“光晕”(Aura)的消逝。技术加速后的信息密度再度增强,感官难以承载环境的快速涌入,大量外部信息在瞬间体验后便遗失为无意义的感觉碎片,感受和经验的内容深度已经变得稀薄。于是,我们所看的越多,抓住的就越少,视野降为了信息的背景,景观变成了没有细节的画面,就可以被纳入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中——同质性的时空在此成形。从微观上看,这对应着现代主体自诞生之日便具有的宿命式焦虑——“经验的萎缩”(the shrinkage of experience)。
数字时代对现代性经验接而续之的,是对身体可知性的再度降格,“真实”与“身体”的双重不在场,再次降格了主体的经验维度。如果说现代性的技术加速与全景视域是空间压缩对以视觉为主的感知能力的降维,但仍具备以身体感觉、经验和理解世界的可能。而数字化时代,电子装置和信息生物技术进一步展现着重塑知觉的力量,现代性的语境已经不再适用算法预置的“现实”,数字形式阻截了身体与空间之间体验关系的发生,在这一境况中,不啻是视觉性经验,主体的全部感觉方式与经验内容被规定进入被建构的层面。这一时代的空间呈现出数字和现实深入融合的态势,即使那些与现实之连接最为深刻的地方,都无法远离数字平面的捕捉、渗透与架构——电子地图将数字空间接入了物质世界,我们的身体也逐渐接入了信息装置,实现了内外连接的异质性空间互构。在数字地图打造的空间场域中,制图者建立并规范了一套共时性的地图知识和语言来完成空间的转译,空间由此成为具有计算性质的、充满资料的叠加物态,成为时间的参照方向和需被克服的对象。通过高度理性的最优行动逻辑,我们对地方的期待、感受和认知不再构成我们对地方的认识,而是集中于图形、指示符号和对偏离的警觉。除此之外,POI数据机制对商业性的偏好也在悄然改变着地方的性质,图像化的“地方”已经脱离了传统经验所依托的那种地方,POI和实地意义在这里此消彼长。[16](P.74-83)这些“地方”尽管与物理空间有着深刻的经验关联,但其存在仅仅是在物理上的关联,它们与内在经验的连接已经逐渐稀薄与抽象。此类精准再现、即时在场的数字空间,生产了一种统一的生活方式,将个体性的经验让渡为一种同质的集体性的经验。地方经验不再是身体感觉与晦暗经验所构成的情境关系,也不再铭刻着个体独特的情感态度和历史记忆,那些个人的东西被整合为数字工业生产的均质“地方”,原先那种完整的、丰富细腻的感受下沉为一种先在的技术标准。换句话说,数字的即时在场,通过取消身体体验的独特性,削平了生命意义的纵深。
数字虚拟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电子地图的升维与泛化,是对现代空间的一种技术组合进化。虚拟空间设想出一种脱离空间的身体,拆解其惯常的身体知觉,把拟真性(virtuality)带入前场来代替真实性,采用技术化知觉来代替既有经验的感知,分离了体验和事实之间的时空关联,在这里,“真实”成了一种生产物,从根本上关闭了主体进入世界的通道。以AR、VR技术为代表的人机交互方式拆解了视听经验和身体的统一性,全息投影技术(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已经可以成熟地实现人物的虚拟再现。②而“Taste the TV”③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虚拟知觉的范畴,展示着媒介空间的分解和重建能力。VOCALOID、utau以及我国的SV等声音引擎,自2007年就击碎了有关DJ文化重组声音样本的艺术批评,实现声音的直接生产和销售,甚至打破了声音生产主体的悖论。④作为存在论的一个事件,“元宇宙”(Metaverse)力图实现各经验维度的“摹仿”,其勃勃野心在于超越界面、超越身体的边界,无限靠近现实世界结构的孪生。尽管此概念仍具争议,但“元宇宙”的根本确定性仍然在于对某一空间内知觉和经验形式的改变,本质上都是通过电子技术去除物理空间特性,对运动、方向和速度等空间参数进行仿真,实现某一形式的复杂空间的预生产,重建共同体空间。人们对“元宇宙”的警惕并不在于它的“摹仿”,而在于它无情地打破了现代性最初那种天真的渴望——希望能呈现一种绝对的客观真实。我们所目睹的和世界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已经被拟真彻底打破,数字再现的“地方”和现实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指示关系,人的行动和他所身处之地不存在实质的交互。再现机制和虚拟技术以新的生活方式重塑了身体的感知结构,而经验的转移势必造成生活的转移,传统的空间感知与经验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数字时代的语境。直接经验和技术化感知始终存在着无法跨越的觉差,“晦暗”也无法居留于数据和代码,“地方”的不居,便意味着“此在”意义的湮灭,充满了纯粹的感觉体验的虚拟空间,无法支撑深层情感和稳定意义的持久锚定。
“此在”生命的萎缩,是数字时代个体共同的空间感受。“地方”在场,却无处现形。从对地方的视觉性抽离,以图像观看经验取代世界观看经验,扩大到身体场彻底让渡于虚拟的电子界面,数字空间以先在的意义结构,阻滞了具身经验和意义的流动与生成——“此在”不再被实际的身体活动所表达。“抽象的模式决不能完全抓住具身的现实(embodied actuality),除非它像身体本身一样冗长和嘈杂。”[17](P.29-30)因此,“此在”的焦虑要求主体恢复身体场域的活性,重返感性经验的真实现场,重新跳跃在这种具体的、流动的空间之中,以此恢复地方在经验中的位置,重建经验及存在的真实内质——“晦暗”,以再次丰盈“此在”的本然意义。
三、地方的再“魅”:在“晦暗”中逃逸
我们是从内部观察这个空间的,并局限于某个位置。我们是故事,被置于眼睛后方二十厘米的复杂之地,这巨大而混乱的宇宙中一个相当特殊的角落。[18](P.135)并非客观的真理塑造了我们的存在,而是由与这沉重的肉身紧密相关的感知与经验构建了“此在”与生活。纯粹的客观和认识的“零点”都是不可能的,“此在”永远无法脱离经验的维度。感性的身体经验,位于苏格拉底认识之阶的最底层,但肉体并非对立于真理的罪恶,真理最初必然是源于身体的吸引,从此才生发出更高的追求。然而,现代社会中理性和效率至上的原则要我们抛弃这一层面,越级而上,将知识与身体对立起来,将人从大地上剥离,忘却我们出发的起点。事实上,在真实的地方到技术再现的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身体。身体是活的经验结构,虚拟技术的逻辑发生正是以人的感觉现象作为参照,即便是在“人机”对立最为激进的后人类语境中,对具身性(embodiment)的讨论,也恰恰是为了凸显身体的在场。因此,通过恢复身体作为主体的经验途径,回到现象学意义上的感知,能够认识到我们的数字生活与原初的地方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脱节。
世界从不是截然分疏的,地方也并不具有中立的价值,而具有主观性和特定的意义,“每一个身体都占据着特定的地方,身体存在的前提就是地方的存在。”[19](P.10)身体与地方的粘连,是通过经验的或感知的“晦暗”实现的。而“此在”在世界中的观察与吸引,乃是通过一些既揭示又遮蔽的视角进行的。地方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这些总体中,意义所系的符号和细节向“此在”显现了意义——在理性层层叠叠的褶皱中,“晦暗”寻求可见性,它们试图提供关于感性经验、“此在”的能够感觉到的形式。借用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定义,完整明晰的符号和意义来到前场,此为“显义”(sens obvie),而“晦义”(sens obtus)则更深于隐蔽,乃是“理解力所不能吸收的一种多余的东西”[20](P.45)。于是,“晦暗”(Obscure)便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东西——它隐匿于身体与地方之间,也即“此在”与“大地”之间的一种连续的、相互过渡的谱带当中,存在于意识的边缘域,它是经验的,却不位于经验的焦点,它更像身体在世界和意识中持存的一些碎屑,穿梭在理性的罅隙中而完善着“此在”的密度与连续性,与身体一同完成并确立着主体的统一性。它的形式是前反思的,甚至是前语言的,从而呈现为一种对于明确理性的永恒的战斗。正是由于它的不明确、流动和含混,“晦暗”便潜在地包含着逃逸的冲动。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对“此在”与“地方”的考察,就逃逸于规律的刻板和语言的片面性之外——正如“晦暗”不应该被定义所统摄一样,“地方”也不应该被确定的中心性所统摄。萨特认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此在’(Dasein)的本质在于它的存在(existence)”,因而在世的必然特征就是处于“地方”之中。人无法寻求外在的、超验的或永恒的根据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个体必须拥有创造“此在”意义的自由,必须辨识身体场的“晦暗”,即每个个体都应当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精心安排自己生命的各个部分,以建立其所必需的“地方感”和在世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们对数字语境的“矫正”应当具有双重面向,我们也应当反思:在当下,现有世界对于“地方”的想象是否过于狭窄?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怀旧传统牧歌那样的往昔岁月,也总是呈现出一种科技化残障的症状。新语境中的我们和地方的关系近似于跟崭新的义肢不断配套调试的疲惫感,即使最终获得相对理想的平衡,仍时常会有旁逸斜出的错位感,迫使人们以更为开放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的身体和空间之间的关系。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地方”位于特定背景之中,同时也呈现为开放世界里的一部分,我们得以通过一条迂回的路径,返回“地方”的现象。20世纪后期,伴随着福特主义(Fordism)的高歌猛进,大规模的集体性空间意图囊括普遍的人类架构,这种密闭空间对内的生产性体现为对个体有方向的挤压性塑造。从坡到波德莱尔到本雅明,出现了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新审美情感和逃逸想象:了解(know)让位于一种异质性的体验(experience)。他们发现,“地方感”的建立,不在于发现了一个未知的实体,而在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待现实,即“此在”所身处之地并不是一个真正需要“了解”的世界,而是一个要以各种各样、往往令人不安的方式来经验的空间。在波德莱尔那里,“闲逛者”(the flàneur)与其“晦暗”的交织,打通了逃逸的自由。“对于完美的游荡者或热情的旁观者,有一种巨大的快乐是,在人群的中心,在运动的潮起潮落之间,在短暂和无限中,建立起自己的家。远离家宅,却无处不是归家的感觉;看到世界,置于世界的中心,却依然隐藏在世界之外。”[21](P.9)此时的空间域,不再被明确的规划空间所标记,而是被隐晦而流动的踪迹所注释,从而与身体场构成了以“此在”为中心的向外过渡的谱带——“地方”,在身体的延伸场域中现身。在20世纪以来的后现代反思中,街道成为反空间的代表,其对异质性的宽容,吸引了“晦暗”的流动。在这里,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曾称赞过的词语“vago”可以作为这一逃逸线的精巧隐喻,它在拉丁语中的意义是“漫游”,在意大利语中既与不确定、不明确联系在一起,又与美丽、愉快联系在一起。[22](P.59)“游逛……就是对抗理性政治的感官政治,对抗实用政治的耗费政治,对抗官僚政治的娱乐政治。”[23](P.164)作为感官的、松弛的行为,游逛使人从跳出熟悉的语境,紧张和秩序感在这里得到松动,人,正在和地方发生实际意义上的相遇。本雅明深谙“游荡的艺术”[24](P.33-36),“了解一个事物就是了解它的地形,并且学会如何绘制它,从而知道如何迷失。”[25](P.116-117)这种“迷失”,其实质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经验,是人与地方展开的强烈际遇,意味着美学原则对功能主义的短暂压制,是本真性从效率逻辑当中的松动,“人生活于其中,不是在它的确定性之中,而是与想象力的所有片面性一同居于其中。”[26](P.xxxii)无论是“沾有撒马尔罕灰尘的地毯”[27](P.33-38),还是其名“像林中枯枝般清脆响声般”[27](P.90-91)的街道,在本雅明这里,地方感的自足建立在身体场的统摄之中,其与工具性和理性的远离,保证了在地感建立的根本条件。而“游逛”的行动,通过对具体的现实性的有意关切,宕开了后现代性空间的逃逸之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艺术被视作此种逃逸的经典路径,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存在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间接感受的内部性,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它总是最直接地贴近着人的自由精神,这也是文艺产生和生产的本源动力。本质上来说,空间是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理解,或者说是存在的一个层面,即将生命理解成“置身一组流动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中。”[28](P.20)而这些关系需要以某些方式来加以绘制和强调,文学艺术就是其一。经典的“地方”无需文学的帮助就能让人们注意它,而文学艺术能够描述那些不够引人注目的“晦暗”领域,从而引起对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经验的关注。“所有的幻想、所有的梦、所有巫魅性的行为、所有晦暗的现象……在他对自然的认识中留下了种种罅隙——诗正是穿行于此罅隙中。”[7](P.46)文学艺术能够以其独特的形式保护“晦暗”的持存,不仅如此,文学艺术中“地方”通过表达的述行功能获得创造地方感的力量,与地理场所互相补充。“地方必是一种内在的风景,让想象力居住于此……在成为现实的城市之前,巴黎一直是我通过书本想象出来的城市,一座阅读时所占用的城市。”[29](P.167)文学艺术的“内在风景”使地方在美学的模态维度中现身,读者们以此来修正他们自己看待城市本身的方式。在都柏林,读者们沿着布鲁姆和斯蒂芬曾经走过的路,安贝托·艾柯也承认自己是“在都柏林的埃克尔斯街寻找房子的人之一”[30](P.84),布鲁姆日的庆典也在利菲河岸达到了意义的顶峰。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文学艺术在“摹仿”的层面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们与“晦暗”的距离,削弱了前文所说的那种直接经验的即时性。但其特殊性在于,文学艺术具有着双重身份,它既如上文所述,能够作为“晦暗”的持存形式,更重要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同时是经验的对象,在这一层面上,对文学艺术的直接知觉乃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经验世界的方式。但需注意的是,艺术经验的发展或许可以使我们总结出某种逻辑——要素、结构、语法、风格学等等——但这些毋庸置疑的外表仍是为了掩盖它本身的含混,都无法取代我们对文学艺术的直接感知。无论是绘画还是诗歌,都不首先是对某些事物和观念的意指或能指,其目的不是酷肖,它所再现的并非模仿、召回或者指示事物本身,而是制作一幅自为的、自足的景象。其意义不在作品之外,不在所意指的东西那里,而在于系于形形色色的符号和细节的所唤起的直接的感知经验。我们需要做的是还原那个具身而有限的存在与一个复杂神秘的世界之间那种模糊的关联,以极度真诚的方式去直视艺术作品、话语作品以及文学作品本身那自主而原发性的丰盈。[7](P.87)因此,纯粹的艺术经验,也会是一种知觉。但尽管“晦暗”不可言说,在艾柯所说的“清单”(lists),我们能够瞥到它快速流动其间的身影。《伊利亚特》第18卷里以丰富细节和著称的阿喀琉斯之盾,荷马以诗的有限形式赋予其熟谙的世界,以趋近“晦暗”可被描述的边缘。而在阿莱夫中,通过这些流散的星丛般的“晦暗”,我们瞥见了所有地点之最——整个宇宙。“博尔赫斯的清单不仅是对所有逻辑标准的挑战,而且可以利用数学中的集合论悖论……实际上违反了任何合理的判别事物之间和谐性的标准。”[31](P.239)没有一个细节是无关紧要的,无有一物是存在于协调与形式的,清单的长篇累牍里每一个能指都在指涉难以名状的“晦义”,并破碎着每一门科学有关本质和定义的梦想。
尽管现世的我们如此呼唤地方的复魅,但事实上,“晦暗”并不都是舒适的,地方的经验在宏观上展现出不可避免的狭隘性。人类既受限于条纹空间,又无法脱离地方,现代生活便是在智性和感性、功能性和存在性之间的辩证运动——过负的地方经验可能会导致狭隘的理解,完全的平面则会与本真疏离。两者之间的动态张力存在着当前语境下“此在”的多样化与超越的可能性。在雷尔夫晚年的思考中,身体场的结构淡化了地方的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尖锐感,他更倾向于将“地方”与“无地方”放在一种交织的情境中去理解。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皆为存在的必要秩序,不存在高下之分。可以说,文学艺术的创造本质上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艺术作为摹仿的产物,人通过它们的想象去连接被摹仿的自然,从而体验美,体验一种可能。从符号、影像到感知,摹仿的媒介进阶推动了“感知”和想象的不断升级。虚拟空间的“沉浸”,对感知层面上对现实与想象的剥离,这种剥离不是全然放弃感知,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感知的解放。既有经验方式的瘫痪,也恰恰可以是另一种知觉上的站立的起点。拟真所涉及的非本真性问题已是陈词旧调,而数字语境中的本真性蕴含着面对世界的更加敞开的胸怀和以及人类状况的敏锐觉察,“必然存在着属于电子游戏世代的生存哲学,而这种生存哲学从一开始就与我们的身体、自我和世界密切相关,因为在电子游戏的感受中,我们可以打破印刷文字和影像等媒介的藩篱,走向新的身体经验、新的自我同一性、新的可能世界的关系。”[32](P.92-106)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空间,已经超越了技术发明的范畴,力图成为一种世界的合作方式,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已经无法回答新的生活经验所带来的问题。
在虚拟空间中,我们需要更新对身体的想象,这里存在着一种更广义上的地方,意味的是“身体”的彻底更新,人将自身主体化,超越了肉身构成一个“主体”,并与我们内在的主体相对应,这便是现实主体潜在的部分之实体化,即我们原先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部分,在另一个界面中实现,并反作用于现实主体,重建了我们的身体经验。蓝江教授根据阿甘本关于“宁芙”(Ninfe)[33](P.60)的隐喻所提出的“宁芙化身体”阐释了这一经验的形成机制。通过宁芙化身体,感知和体验不同于肉身感知的经历,并因此成为存在的一部分。[32](P.92-106)而当虚拟空间获得可经验性,也就获得了真实性。——这便是虚拟空间原生的反身性(reflexivity),其与现实注定互相迫害的深刻纠缠,催化了自我同一性的解构。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性并存(paradoxical compossibility)的自我形态和经验形式——宁芙化身体经验与肉身经验以悖论式和褶皱式的方式叠加在一起,两者的彼此悬置与复杂纠缠分解了稳定同一的自我,这样一个逃逸的、悖论性分裂的身体,即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无器官的身体”,才具有突破被意识压抑的冲动的可能,通往现实世界的外部,通往德勒兹和加塔利意义上的逃逸的生成。在这里,通过极限的体验,仍然存在着多样的可能性,存在着真实的反思和体验,对“此在”具有着真实的意义。对“此在”的藩篱的突破,凸显了数字时代对“地方”内涵的存续与延展,“地方”本就是同时作为经验性的概念与经验性的现象,理解它们,需要将地方视为无边界的存在,需要我们抛弃偏见,更加开放的心灵。最终而言,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技术工具,而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识别并揭示它们。在数字化的当代,这一知觉的尺度被拓宽,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或许将能够穿越身体的内部和外部边界,建立新空间体验的生物界面,丰富和扩充“此在”的生命体验。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突然的跳跃,从感觉的层面一下子跳跃到抽象与自觉的形而上学中。相反,人类的意识存在着好几个层面,意识里最直接的形态便是身体性的感性经验。“此在”的内质在于此在在此刻对自身存在的确认,这一确认并不为存在的实在性所确保,而为其“晦暗”的自觉辨识和持存而确认。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差别的雪,爱斯基摩人有十二个词语去表达它们,在这十二个词语之间呈现着的细腻的区分,即是“晦暗”。这并不是一种后海德格尔(post-Heideggerian)的论调,而是为确保世界的浪漫化,保持对计算理性及算法哲学的反思。我们的目的在于消除数字的傲慢,退回到认识论的起点,重新跳跃,恢复地方作为“此在”的确认途径,在经验深度上保留着丰富的、包容宽泛的对“晦暗”的知觉,以全身心感官的完整体验,去感受感性具体的、在时间与记忆中流动的、会死亡的那种空间,以建立一种饱满的在世的感觉。
结语
与地方的深度连接对人类来说是必需的,我们每个人都真切地与一些地方亲密相连,我们也都深深地关切着这些地方,一旦被迫远离,人便会产生返归的强烈愿望,正如艺术作品中永恒的地方怀旧书写——罗伯特·塔利使用“处所意识”(Topophrenia)[34](P.17-34)一词来表示这种根本性的“地方关切”(place-mindeness),这种意识构成了我们在所处世界的行为特征,即对“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执着追求。这些地方的意义与本质,不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不在于它的功能,而是我们在其中的联系构建起了我们与世界的认同,构成了我们安全感的来源,让我们在世界中能够找到自身的位置。
在不同的时刻,面向不同的个体,地方表达着不同的意义。这一复杂而含混的关系始终是具体化的,存在于人的身体感知、情感记忆、真实经验等无关理性和逻辑的异质性内容当中,晦暗成为了支撑起地方和此在的内在结构,进而使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可能性,在这一“晦暗”的领域,我们得以建立起了关于地方的意识。因此,对“晦暗”的考察,成为通往理解地方的道路,也是通往理解此在生命的道路。
通过还原地方和人之间这种深刻而隐秘的关联,我们得以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仍然根植于一种具体的现实性,始终为自我的存在定位,并找到出发的坐标——在此处,世界向我们敞开,在彼处,我们可以向之出发。
注释:
①世界的空间由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组成,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世界的现象,是存在最微小的基本形式。而现象唯一的确定性,就在于只在其相互作用时才会存在和实体化。量子理论的基本方程并不描述事物在时空中如何演化,它描述的是事物相对于彼此怎样变化。在这种理论中,时间与空间不再是容器或世界的一般形式,它们不过是量子动力的近似之物,一种人为的创造,其中既不包含时间,也不包含空间,只有事件与之关联。思考世界的最佳方式应该是把世界看作是事件和过程的集合,而非物体、物质或实体,没有物体存在,而是事件发生。参见卡洛·罗韦利:《时间的秩序》,杨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69页;参见Carlo Rovelli:PhysicsNeedsPhilosophy.PhilosophyNeedsPhysics, Foundations of Physics, 48. pp. 481-491. 中文版本参见卡洛·罗韦利:《物理学需要哲学,哲学需要物理学》,朱科夫译,《科学文化评论》2019年第2期,第107-119页。
②2022年江苏卫视采用全息投影技术呈现了“邓丽君”和周深的“跨时空”同台合唱演出,观众们通过电子屏幕观看到的“邓丽君”栩栩如生,甚至在地面投下了影子。而这并非全息投影技术的首次舞台亮相。参见网易网:《和邓丽君在元宇宙的街头走一走》,https://www.163.com/dy/article/GSQQSOLN0552U3GE.html.
③2021年日本明治大学宫下芳明(Homei Miyashita)开发了可舔屏幕品尝味道的电视“Taste the TV”,提出了一种替代的味道再现机制。使用包含由电流控制的凝胶的电解质,过离子电泳通过调味瓶组合装置混合味道,喷洒在屏幕的滚动透明片上就可品尝,再现味道。他更希望可开发一个像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系统,让用户可“下载”世界各地不同味道。参见「味を記錄して再現するという「新体驗」——明治大学の宮下芳明教授、味覚を記録して再現する方法を開発」,https://special.nikkeibp.co.jp/atclh/TS/21/meiji0323/ .
④从2007年Crypton Future Media所塑造的虚拟歌姬初音未来,到2016年同样以雅马哈公司的VOCALOID系列语音合成引擎为基础制作的虚拟偶像洛天依,随着全息投影技术和声音引擎发展,虚拟偶像已经从二维空间走进现实世界。自诞生以来,虚拟形象洛天依以全息形式与杨钰莹、周华健等歌手以及俄罗斯虚拟歌手娜娜(Alena)一同参与了数次大型演出活动,近期曾作为演出嘉宾呈现于2022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