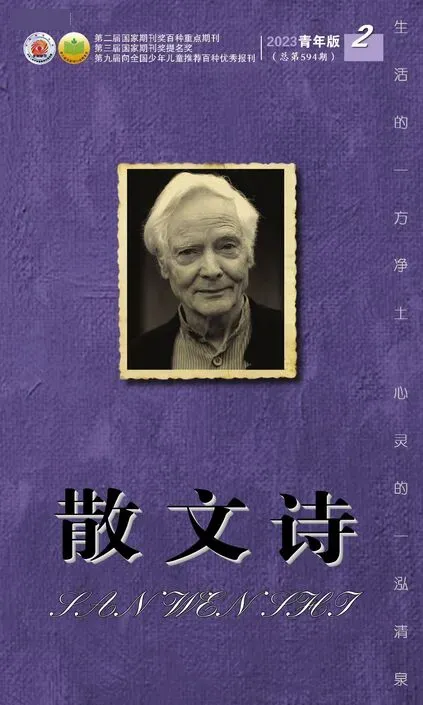油布村的年轻人(外三章)
王唐银
风劈开茂密的樟树林,油布村稀稀落落的房子,就像棋子一样显现出来。
暮色薄凉,月亮的相思,总也走不到波光粼粼的对岸。
阿旺在月光的银质里穿行,他种植的有机油菜、萝卜、玉米,越过黑夜的原野,才能抵达城市的胃。
阿旺站在油布村最高的山梁上,看水,看日落。长江水浩浩荡荡从村庄流过,也从他心中流过。
自从新的长江大桥一只脚踏进油布村,进城的时光就短了一大截。
桥是油布村新的艺术品,这项从春天开始的浩大工程,质地朴素,低旋而又深怀沉静之美。
公元2022 年,油布村的年轻人走在新的长江大桥上。
他跨越了水。
像一艘船,像一只逆风的鹰。
旧 址
这些旧作坊散发的油漆味,有一部分,是从记忆里发出来的。
18 岁那年,他从一列南下的火车上跳下,就再也没有返回到北方。
去川南机械厂,要从罗汉场老码头上岸,一段弯弯曲曲的青石板路,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沿途通向几个院门,门前不见了熟悉的面孔,几棵吐出新芽的黄角树,站在那里,仿佛刚刚认识。
他坐在黄角树下,唱《定军山》,唱《映山红》。
这一天,暮色迟缓,落日红得发黑。
远处,路灯渐渐点亮,灯光照着机械厂的大门。今夜,罗汉场没有机器轰鸣,只有晚风来来往往,吼出漩涡。
他缓缓地走,不知道是该向上还是向下,他感觉这条短短的青石小路,走到尽头,整个罗汉场、机械厂,就再也无法找到。
修鞋的老人
医院旁的小巷子里,他像一颗钉子,被时光牢牢钉在那里。
一架老式穿线机,像他弯曲的脊背,还在嘀嘀嗒嗒忙个不停。那个手动转子太老,黑漆漆的扶手,像燃烧过后的炭,仿佛风一吹,就会断。
每一天,我都从他身旁经过。有十年了,他的头发和他的话一样,越来越少。
两个相差三十年的人,修补着各自的日子,有多少人相逢、相识,又匆匆离开。他永远安静地等在那里。
修鞋的时候,他把头埋得很深,那些密密匝匝的线,在手中穿梭,仿佛稍一疏忽,就会放纵世间所有的风口。
离开小城后,我的鞋一双双地坏,一双双地丢。
在这个拥挤的城市,我找不到这样一个修鞋的老人。
2路公交车
入秋了。
她担着最后两箩筐湿漉漉的油麦菜,在薄雾中等待。
2 路公交车还没有来,小城的街道上,只有几个早起的人,匆匆路过,这个时候,她才感觉自己的存在。
从机械厂退休以后,她在小城边上固守着一亩三分地,种菜,养鱼,看脚下的长江水,缓缓流过。
从双五广场出发,经过酿酒基地、川南机械厂、碱厂,2 路公交车,始终与长江为伴。
寂静的秋天,她用养大的一棵棵蔬菜,和这座小城保持联系,和老去的季节告别。
车窗外,熟悉的长江缓缓流过。
她不知道,这些永远年轻的水,从哪里来,又会去往什么地方。想起离去的亲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越来越老的机械厂,多少年了,想念没有终点。
她害怕有一天,载着整个秋天的2 路公交车,突然就停下,找不到出口。
这一个秋日的早晨,两箩筐新鲜的油麦菜,结了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