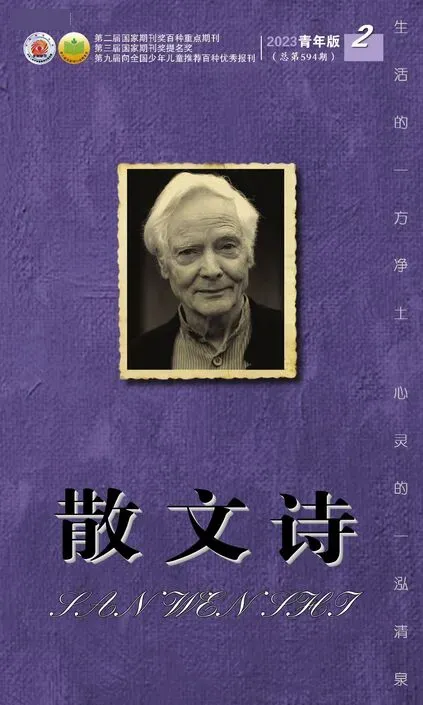诗歌课笔记
容 浩
好诗如初见
朗诵的时候,下面是最安静的:小路于前方浮现,我们经过那栋楼,经过菜地。她种下的爱情已长高半寸,温暖的夕照编织着人世的糖花。
多么好,时间踌躇不前,人间有此一角。春风所至处,都有诗歌的长势。
后面,是一片寂静的林子。
阴影中走出爱你的人。你,刚好看见。
节 制
你们常常让大海以象征的手法成为大海。
少年人,雄心似海。
我以为那太大了,希望看到它变小,比湖泊,比池塘,比胸膛,更小。小小的海,不屈的蔚蓝,置于你胸口。但心中旅程无限,万千的鱼儿啊,一条也不少。你注视着那无穷的奢侈——那游动着的道路、真挚和热望。
写一点无用之诗
我们要有这样的时刻,放弃和巨兽一般粗粝的梦想。我们就这样,说无用的话,爱一只在教室里起飞的孤独的纸飞机。
我教你们眼含泪水,触摸纸张,想到它来自木头,它的种子曾穿破土壤又阔别春天。它的一部分在林中腐朽,一部分化为木浆又被烘干。
它看着年轻的你。
你“沙沙沙” 地写下一些字——光明又灼热的字,坚定又稚嫩的字,它们相识,又分离。
所谓诗的技术
冬日的手势颓然,落叶飘至,湖水以褶皱相迎;你抵达,我以湖水相迎。只不过,所有的褶皱,都将被熨平。朋友们用酒来相互珍惜,酒精,像石子一般留下波纹。
以上这些所谓语言的技术非常老套,并非好东西。但是,好东西恰恰又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敲打着铁器,要把它打制成一把刀。
所以,写下它,磨砺它,留住它,或放弃它。
到处都有窟窿,到处都有雷声
诗歌并不难找——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一个又一个窟窿。完整的,不完整的;高昂的,低垂的。那些不曾想到的窟窿形状各异:比如这时的天空,巨大的深井,它所挥舞的尺度包裹全部的仰望和大地的晚餐。
敬畏那些无处不在的事物,敬畏那些微小的事物,敬畏那些虚无的事物。
它们就是你的诗。你抬头,看到乌云。
乌云深处,藏匿着雷声。
写作的偏执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写作道路上越走越远。孤单如期而至,道路的那头有一个难及的拥抱。
我们不停地写下真挚,渐渐地却又失去真挚。
执著,有时是朋友,但更多时候是敌人。
这很合理,椅子将你挽留,你却成为它思想的钢印。
文学的反对
要的不是你赞成什么,而是改变什么,建立什么。可惜,你渐渐长大,开始像大人们那样,长满正确的枝条。
大人们总是很有道理:这样可以少走弯路,那样比较有面子。很多事情,他们都赞成。
但这时,诗歌慢慢地从一个普通人的身上消失。
坚强的真实
诗歌未必是一些奇滑的句子,未必是思想的芒刺。有时,它只是一粒坚强的真实,沙子一样安详,却成为我们心中之块垒:
比如你展开信纸,复见当初之诺;
比如我们现在虑及这人间事,羞愧地低下头。
远取譬
月亮是你,弯曲是你;
岁月良人,大地银光。
隐喻:诗的暗语
它们就是你的斧头。
但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斧头:半张瓦片遮头,即有屋檐;一句真言入骨,可雕刻一个时代。
双 关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用一句话,可以说出两种现实。
智者已经放下,你还没放下。
那一望无际的棉花,不单单是一望无际的棉花。
陌生化古典吉它
尼龙弦和口吃有同一种愿景:流畅的水滴形弧线来自自己的震动;古典吉它是你的爱人爱你:盐和糖都伏在她的木头上尽情地歌唱。
演奏的人微微颤动。他没有歌词,心中的嘴唇一开一合。
他仿佛看着一个人远去。
旧事重提,月下鸦无啼,泪惊霜。
下课之后
我的心里,也有一间空荡荡的教室。有一本书,我刚刚将它合上。
你们离开,我留在这里。
你们都是独特的一个人,独特的一朵浪花。
你们是雨水从天而降,身体重新聚合,去向远方。
新鲜的河流将要奔腾。
江河里,有亿万朵花。
师 者
给学生们讲起一些事,关于良心,关于远游的学长。
沙哑的石头在心中,在喉咙,露出水面。它仍坚硬,披稀疏的光斑。
事到如今,很多人已不相信师者如父。但今天讲台上坐着的,确是哽咽的父亲。
告别的话
怎么可以忘记羊群,怎么可以点燃水草。
怎么可以长大,怎么可以低垂。
怎么可以渺无音讯,怎么可以不来看我。
祝好。
祝爱。
祝爱抱抱你,添人间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