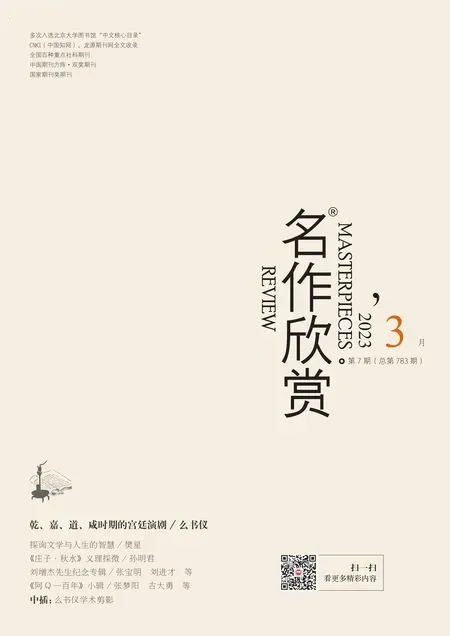安稳的空间、不安的历史与茫然的小说之美
——葛亮《燕食记》讨论
北京 毛晖 林孜 孟睿哲 等
毛晖:我对整部作品(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年7 月版)风格的基本观感就是安稳和恰当。语言方面,从方言持有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小说中的方言非常生动活泼,而且它与标准语结合的度,也拿捏得很恰当;情节方面有一些香港文学的模式痕迹;相应地在人物塑造方面,主要人物形象相对稳定,内在性格特征也没有特别剧烈的变化过程。以上三个方面中的任何一点单独拎出来,相比于葛亮写香港的《浣熊》,或者写工匠的《瓦猫》,都未必更好,但是整合在一起,反而出乎意料得刚刚好,阅读过程非常舒适。当然大家可以认为这种舒适可能是由他的写作对象造成的——小说中出彩的食物描写片段,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个理由实在太过感性,在舌尖抚慰之外,小说“安稳”感的来源,还是值得深入琢磨的。
整部小说是用一种伪回忆录加非虚构的方式来写的。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两个老师傅的回忆和叙述人“我”的文献调查的结合,虚构的成分腾挪在其中,有好处也有难度。在《燕食记》之前,葛亮其实还写了一个匠人系列,也就是构成《瓦猫》这部小说集的三部中篇,这部小说说到底也是关于手艺人的故事,也就是“匠人”的故事。我们不妨从“匠人”这个词开始说起。“工匠精神”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匠艺活动,很多时候都是指一种随着工业社会到来而逐渐消失的生活方式,但它其实也包含了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就是要把事情做好的一种欲望。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我们谈匠人精神,大多会强调其中个人和自主的部分:拥有熟练技艺、个人自主、专心技能和沟通技巧的劳动者,已经为传统劳动和职业注入了新价值和新利益,劳动不再是一种责任重担,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方式,而转化成劳动者共享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成为他们在产业中发挥专长的安身之所。这段话大致出自一本叫《纽约手艺人:精神与品位消费的未来之间》的书,当然这个观点放在中国的手艺人身上,很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譬如《燕食记》中的两位老师傅,之所以对食物认真,很大程度上单纯出于想做好一个东西:他们就只是性格如此,而似乎无关乎自我价值实现。其实关于专心技艺的手艺人,大家应该更熟悉的是《俗世奇人》,那是真正把一种技艺做到极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想就难免怀疑:这些技艺中的大多数放到现代社会,是否还真的需要人去做?即便现在我们推重“工匠精神”,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手艺都是可以用机器替代的,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会被时间吞噬?这样的反思难免会引起对匠人精神的某种担忧。葛亮在“匠人”系列中,也就是之前说的《瓦猫》中,更会强调匠人本身跟他所做的器物之间的联系,但即便如此好像也不让人感到乐观。或许因为这样,有同学跟我说读《燕食记》莫名让人想起王安忆,想起《长恨歌》和《考工记》,二者都是写逐渐跟不上时代的人,在已消逝历史的遗迹所构成的孤独而凝固的空间里面,慢慢变为历史碎片的过程。
但必须承认,这种担忧在《燕食记》里不能说完全消失,但至少被相当程度地冲淡了。《燕食记》里坚持自己的手艺人,跟一个具体的器物(如五举的刀)或者跟他的某种技艺(师徒的厨艺)联系起来,并通过这种方式,联结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来容纳他们整个的生活——这个空间在我看来就是《燕食记》调查人着力挽救的“茶楼”,或更确切一点,是独属于厨师的后厨。厨师当然也是手艺人,我们或许可以将后厨称为他们的“工坊”。
工坊的空间,又为何会给人带来如此强的安全感呢?首先我觉得工坊强调一种绝对的私密性。在第三十五页荣师傅给陈五举传授莲蓉炒法的那个时候,他把谢醒,也就是师兄给排除出去了。这里有师徒相承的规矩,而这种相承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进行的,还是一对一进行的;如果再联系到荣师傅跟养父兼师傅叶凤池,叶师傅传授的技法还是单单少了盐这一味料,需要荣师傅自己去琢磨出来。在这种绝对的私密之下,某种传承的东西就可以一点点地延续下去。
第二点,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两个手艺人很大程度上都被抛除在了现实的历史变迁之外。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重大变迁,这两个人好像没有实际参加到什么大事情里面去,他们的生活是有波折,但是战火基本没有蔓延到他们自身,甚至荣师傅去找叶凤池的师弟学艺的时间,与全面抗战的时间是重合的。但荣师傅被有意地排除在家国大事之外,不管是与他接近的叶凤池所加入的民间武装抗日,还是荣师傅养母的遇难,他都被排除在现场之外。在世事的浮尘当中,由手艺人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单维空间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安身之所。
而书中尤为特异的一点,正是主人公这种随遇而安的安稳感,缺少对一种身份认同追寻的强烈渴望。在第二十八页,五举师傅这么说:“因为没有来历,把他放在哪里,他便落在了哪里,长在哪里。”相比于这种随意而安的心态,我们更熟悉的是文学中的孤儿对于父亲和认同的急切追寻,这两种写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年轻的荣师傅也是如此。而身份与认同焦虑的缺乏,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强烈的对他者的需要,借以凸显主体。这种心态,或许也和葛亮自身已是香港的第二代移民有所关系。《燕食记》开头也说了,调查人来香港的时候,是有同乡会在欢迎他的,他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根基,然后就已经可以以这么一个集群为出发点,融入香港这个社会,而不像第一代南来作家群一般存在生存和融入香港社会的问题。
再回到那个以手艺人为中心的空间。因为其他人需要这门手艺,由此人际关系及其衍生构成一个安稳空间,但这个空间又不完全是封闭的,是向社会敞开的。甚至核心的厨艺共同体本身也不是完全封闭的东西,像十八行里面,在粤菜和沪菜流派泾渭分明的同时,其中还是有粤港点心的踪迹,露露来了十八行之后,又把南洋菜的做法引入,共同体中有着各个地方菜的技艺融合。此外,对于厨师行当来说,戴凤行和露露,就是打破了女子不做厨的行规禁忌。由此观之,这个安稳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有机的空间:这种呼吸吐纳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对当代过量的多样性的应对,同时也可以抚慰现代原子化个人的孤独感。这种多元开放的视野表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参照和拥抱,时代沉浮文化冲撞中人物的归属感,也可以从断裂疏离、犹豫徘徊,到最终与他人和时代的和解。
我虽然对这本书里面所有提到的菜的做法没有太大的惊喜,但是对最后一章,即师徒争艺部分中各种食物的描写,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应该就是一种写法或者说风格的突变。小说最后一章之前,对食物的写法非常沉静,因为所有手艺人即使创新,也都在在遵循、延续一个传统严谨的规矩,但是借助厨艺比赛,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些手艺人,在自由地发挥,展现他们的创造力。虽然他们在竞争,但他们也并不是说要争第一,他们争的从来不是冠军,而是独一份;这种独一份的追求,也是他们在比赛之外的行当经营中所安身立命之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产生一种对工作意义的思考:不是卷生卷死,为了一个东西卷生卷死,也不是固守某个老东西,而是它处在一种始终被需要,然后始终也能够找到一个充满活跃生机的一个社会场域,并在其中扮演一种有机角色;同时从业人也能对自己始终发挥有机角色的目标,保持坚定的信念。
当然这是从手艺人的角度来看的,我们更多人可能扮演的是食客。而对于食客来说,我在《燕食记》中感受到的也是他们和厨师之间基于食物建立起来的切身人际联系,这跟资本主义价值与人之间关系的货币化是不一样的。而由这种关系所构成的,是我们能身处其中、进而得以在各方压力之下获得的安身之所,它是暂时的、来之不易的安身之所。
林孜:接着玥晖的话题,我想就大的空间层面来谈论。我认为只有先理解了大的时空想象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才能把讨论打开,从而更加深入、更加历史化地把握小说多重的空间意蕴。
葛亮将人物的生活史坐落在南粤这个文化空间中,也就是现在“大湾区”的版图,南粤这个空间由于历史原因,内部是有着文化乃至政治的差异性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差异性,为小说处理空间与历史的关系提供前提。《燕食记》的历史背景交叠了“短20 世纪”与“长20 世纪”,小说从饮食文化的流变出发观照历史,勾连起内地的革命史与内地政权更迭后的香港历史,而这种语境的变换是经由大空间从岭南到香港的变化体现出来的。但小说只是在书写人物的迁徙时提及了历史剧变,并没有通过阐发人心,从日常生活中“常”的一面出发,来触碰、质询、反思历史中的“变”,深入触及剧变背后某些“断裂”的经验。或者说,这些历史经验被处理得很隐晦。
“新历史”小说以来,这种“断裂”被反复书写,陈思和先生将这一类讲述“常”与“变”关系的历史叙述统摄到“文化中国”的主题之下,以往的小说,譬如王安忆的小说,往往是在“常”与“变”之间构造张力,用“常”来回应“变”。葛亮以前的两部长篇也是如此,对“文化中国”的营造中隐含了一种对古典价值失落的预感,一种历史的无常感,这在《北鸢》的结尾体现得很鲜明,有着“新历史”小说的余韵。但相较于后者对历史比较虚无的态度,葛亮无疑想借助“常”,为历史赋予一些确定性。他们的相通主要体现在那种虚实相生的暗示与预感上,这种隐喻其实包含了对激进现代性历史及其后果的思考。而在《燕食记》中,葛亮没有在“常”与“变”中制造大的张力,反而让二者有意保持距离,从人物的职业伦理中、从日常生活的安稳感中透示出“常”的一面,淡化了历史中那些更加深重的断裂,来整合南粤这个大时空体中诸多暧昧而参差的历史经验,确实是为当下“文化中国”的历史想象提供了一种路径。我认为这是“文化中国”叙述中的一个新收获,虽然其中不无遗憾。
孟睿哲:林孜抓住了“文化中国”这个主题概念,并指出小说中物与历史相生相克的关系及其限度。我想进一步谈谈小说历史书写的策略以及我的一些困惑。
我将葛亮处理历史的方式概括为“缝合”,我认为作者会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地去封闭一些严峻或幽微的历史经验,把历史转化为人心的某些感触、一些微妙的指涉,进而将其包藏在人物的生活情境中。就《燕食记》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太史第这种封建大家族的没落。小说其实滑过了很多有意味的时刻,比如说戴家跑到香港的原因,60 年代初的大饥荒在书里点到为止了。然后谢醒这个不太正面的角色,参加过香港六七反英抗暴,后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变成了一个金融市场的弄潮儿,虽然书中没有交代,但他的下场未必好,因为1998 年香港就会经历金融危机。再比如像叶凤池的师弟韩世江,还是他教育阿响说你少管闲事,学好手艺就行,但他自己其实管了大事,参与了抗战至关重要的一环。唯独两个自外于时代、依靠食物存身的师徒,他们求得了相对的周全,这种周全可能接近林孜所说的“常”的一面。但关于这种周全,我有两点疑惑:
一是怎么能构建这种周全感。我觉得首先在于葛亮选择了食物这个书写对象,相对于手工艺物件,食物的确是在大历史变迁中相对稳定的东西,因此厨师这个特殊行业让抵抗的成功更加合理化了。另一个问题是,既然要构建出一个小而稳定的共同体,或者像玥晖所说的微观空间的建构,都必须要面对一个潜在的他者,我认为这个“他者”本身可能就是这部书赖以展开的东西,就是时间,具体说是风云动荡的20 世纪历史。他们周围的每个人几乎都被历史的暴力所摧毁,唯独荣贻生和陈五举师徒,就像当初月傅藏在襁褓里的遗书那样,“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金可续命,惟艺全身”,葛亮让他们只凭借手艺在想象的层面实现了自身的保全、共同体的持存。一定意义上,小说借助小人物在大时代中能够自保的身份,更加自然地回避了历史中过于尖锐的部分。
但历史中那些比较尖锐的部分除了本土的现代性历史之外,是否也还包含那些有着东方学症候的历史?对这种历史的处理在小说中似乎也不尽如人意。比如,云重跟一个外国人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在小说里有比较详尽的交代,她把怀孕的母亲推下楼梯,长大成人之后去了法国,之后的故事相当于是被作者给放逐了,连同那段云重和外国人共同生活的历史,也疏离于文本以外了。为什么要放弃掉这段非常具有东方学症候的历史?如果他写出来,我觉得它和香港的命运会产生一种重叠、象征。
二是“外部的”历史到底有没有侵入到师徒的个人空间中,威胁到了这个小共同体?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它“入侵”的形式非常有意思。真正引起改变的是椰汁,露露把椰汁引入了上海菜,引入了五举的厨房。有意思的是,触动了共同体的是一个异族的更加弱小民族的女性,而且是用一种非常温柔,甚至锦上添花的手段,在稳定的共同体里加入新的东西。好像《燕食记》里写的历史要么就特别暴烈,但一定徘徊于共同体之外;进入共同体这一部分,又特别地温和,温和到不能用碰撞来形容,更不用说引起什么质变。我个人觉得这种处理历史的方法是可以商榷的。
最后还留下一个问题,对我来说,一种漂浮在历史之外,以提供慰藉为目的的书写,当然不能说“不好”,但是这样的小说如何面对当前的文化场域?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从流行文化里获得很多慰藉,比如说网文。借用书里的比喻,我们要如何面对莲蓉月饼和莲蓉班戟的差异?
丛治辰:两位同学都企图通过空间,触碰小说与大湾区文化的关系和文化共同体的问题。其实不管是文化空间的历时变迁与内在关系,还是所谓“常”与“变”、物与历史、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这些问题连同小说的“匠”的主题还有美学形式,都是纠缠在一起的。我很认同你们说的,作者试图让人物从置身的小空间中逃离大历史,让人物跟历史保持距离,但问题是,历史真的没有对这对师徒造成影响吗?小说当中其实存在很多关键性的情节变动,恰恰是因为大历史对小空间造成了推动,甚至造成了摧毁。小说也反复在写这种变化,当然它最后总是找到一个方式,让小空间能够延续下去。比如小说中写到了不同的饮食空间,不同的饮食空间对食物精细程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甚至里面写到北方和南方、日本和中国,其实它都是略有差异的。然后葛亮甚至写到人物直接去种荔枝,种种的求生求变的本能恰恰说明,看似一直没有变化的事物,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其实是有变化的。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葛亮回避了历史,至少他是自觉地在处理历史。应该发现,师徒内在的稳定的封闭空间可能没有那么稳定,它是不断地在动摇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常”与“变”,作者也着墨于“变”。他写的“变”可能跟我们一般认为的“变”的关系不大。
我在听你们发言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对小说到底要求什么?以及小说家写出了什么,读者又能够接收到什么?葛亮在小说中表露的思想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有自身的文化情结,而这种情结无疑有暧昧的一面,但是同时他又努力在今天的当代文学秩序当中谋求自身的位置。我绝不认为他是不真诚地去面对历史。他作为一个大陆人在香港,在那样的境遇下,他对家、国的想法必然有一种我们或许无法身临其境体验到的国际感和复杂性,那可能和我们一般的想象有差异,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小说的特异和精彩之处。或许连作者自己都不能够确认,自己潜意识里到底流露出了什么样的情感。因此有趣的恰恰在于小说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很不确定的互动。
我想从睿哲的结尾来开启大家的谈话,就是小孟最后说严肃文学到底跟同题材的游戏、跟通俗小说有什么区别和优点?葛亮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我有一个简单的区分,在严肃文学中可能作者会自觉引导读者去思考,而文化产品似乎欠缺一种自觉具备的、启发性的东西,我们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判断往往是我们脑补出来的,文化产品就其自身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创意。此外,我还想听到大家更加细化地讨论葛亮如何以小说自身的方式建构了文化认同,在小空间和大历史中形成微妙的平衡,我们的讨论或许还要深化,别只是停留在观念的对撞上。
陈绚:我在想如果我们从书中人物出发,可能会更有根据地透视出那些宏大的问题。我非常赞成玥晖说的小说的安稳风格和人物性格的稳定性,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两个主人公,从小到大,性格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且性格比较统一。玥晖的发言其实隐含了对小说的古典性的认识,我认为小说是有古典性的,一定程度体现在脸谱化上。
丛治辰:大家也不妨讨论一下,人物的性格真的统一吗?五举和荣师傅性格像吗?
陈慕雅:我认为在小说里面,荣师傅是最后一个完全地坚守了他们本来的正统性的一个人,到了五举那里,他到后期已经开始接纳,比如说接纳了来自本帮的、南洋的菜色。
张闻昕:我觉得五举在整部小说里面要更驯从一些,荣师傅的自主性还是比五举强。虽然荣师傅把所有的情绪都压抑在心里面,但是你会觉得他的心理活动比起五举来说是更丰富的。至于五举,他有一种非常忠诚的信念。他对这门技艺忠诚、对荣师傅忠诚,所以他后面不再使用莲蓉,从少年到老年,到最后他又回到荣师傅身边,成为一个非常坚定、非常坚守的角色。
丛治辰:我同意闻昕,也认为师徒间的性格并没有那么统一。师徒二人在肯吃苦、知进退、有分寸、厨艺上的才华上都很相似。但是师徒二人其实有相当大的不同,比较起来,荣师傅更持守,更懂那个“熬”字。大家并没有讨论到小说反复提到的“熬”字,“熬”字内涵极其丰富,但至少也包含了一种不得不接受自身命运的意味。荣师傅其实一直在被大的历史所推动。荣师傅和五举差一代人,比五举更保守,刚才是慕雅说的,荣师傅是最后一代手艺人的代表,五举可能并不是。我也不认为最后那一幕是回归,最后那一步其实是传棒。但是手艺已经断了,到师徒打擂的这一地步,还能叫什么传承呢?就已经不是传衣钵了,而是师傅成就徒弟,是旧人成就新人。五举正是那个新人。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荣医生是有父有母的,甚至还有养母养父,家累很重。荣师傅实际上是大时代和传统社会夹缝中的产物。而五举无父无母,它是一个无根的人,这也和人物的性格行动构成关联。
小说结构分上下两阕,各自表述但是又相得益彰,这种结构方式有现代感。分阕的方式可以用来打断这个小说叙述,不断重组和穿插。但在上阕当中其实有非常传统的手法,上阕的主角是荣贻生,但是却让五举先讲故事,这是传统小说常用的手法。他看似讲了一个完全相似的故事,但我觉得不纯然是,一方面荣贻生和五举两个人的命运与性格都有交集,但五举山伯的故事很明确写了一个叛徒的故事,一个逃脱出原来历史逻辑的故事,其实这预示着后来荣贻生的无可奈何。这也隐含在小说的结构和组织中。
而且五举一直都是以退为进的,这一点我觉得跟荣贻生也不是很一样,五举非常知进退,荣贻生则是非常知进取。在关键时候,荣贻生是愿意往前走一步的,五举则选择往后退一步。但他又正因为退了一步才得到了往前走的机会。文中写到阿爷为他谋前程,五举不肯走,眷恋阿爷,要照顾他,这体现了人物性格,但更动人的在于这种人物间的真情,小说的古典性、稳定性,一部分大概也来自这种情义。包括所谓文化中国,更落实在精神层面,那是一种道义,是乱世更格外要坚守的一种立场与尊严。
王思远:谈到葛亮对师徒的刻画,我不太喜欢的地方是作者对那对师徒感情生活的处理,我指的是主人公荣师傅和云重青梅竹马的爱恋,还有他的徒弟和露露的关系,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作者要如此处理这两个人物的感情问题。作者要写荣师傅的外遇,那么妻子秀明就被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因为秀明这个角色的存在,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奇怪。尤其是秀明这个角色处于失语的状态,更处在一个特别可怜的位置上。另一问题是,小说还有五举和露露这一条线。为什么这两个角色会有感情线呢,或者说作者这么处理有什么用意呢?
陈慕雅:是因为他们二人互相都有一种惺惺相惜且志同道合的感情。
张闻昕:但这段三角恋还是有点突兀,作者为什么故意构造这个情节?
丛治辰:或许不妨想一想,从人物性格角度出发,荣师傅和云重能在一起吗?以五举的性格和露露的性格,他们能在一起吗?
孟睿哲:我觉得荣师傅和云重的确很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手艺要传承。
丛治辰:我觉得还不仅仅在于手艺,司徒云重有巾帼气,而且似乎不是古典意义上的穆桂英式的巾帼气,她还有现代的意识和胸襟。荣师傅则是一个深嵌在中国传统性格当中的人物,他遇到这样的女性难免会动心;但是从性格上来讲,他应该和秀明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属于旧人物。荣师傅多少属于那种想要向现代迈步又迈不进去的那种人。
五举和露露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云重和秀明,大概是那一时代从传统女性当中生长出来的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退回去,一种是走出去,然后我们看到了露露这样的人物。到了下阕,敌人似乎不再是动荡的大历史,而是物欲横流中的世俗生活,露露带着这样的色彩进入小说的人物谱系。她是一个有着复杂前史的歌女,如果她要与五举在一起,五举真的有足够勇气接受她吗?这又要回到我们刚才对师徒性格的讨论。师徒二人和云重姐妹俩一样,大概也可以说代表了脱胎于文化传统的性格,他们的柔弱与窥探恰恰说明,这种能在乱世中全身的坚韧性格,面对现代也有着无用和软弱的一面。葛亮写出了师徒两个人宿命般的相似,但这宿命般的相似,其实是不相似,因为上下阕明显处理的是两个时代,这两个人试图面对的压力,明显是两种压力,一种是革命的压力,一种是世俗的压力。
马晓炎:刚刚大家谈论了“文化中国”落实到人物身上所展现的多面性,我还想回到文化本身,观照《燕食记》中处理的文化融合,也就是fusion 这个概念。同时还想谈论葛亮对“文化中国”所投射的情感态度。首先,“fusion”出现在小说下阕,讲“太平馆”这种采用了中体西用的新式菜馆。除了饮食外,《燕食记》里面是存在多重“fusion”的。比如各种语言的融合;葛亮在写作的时候虚构和对非虚构的创作方法的融合。除此之外,“fusion”就很容易让我们从菜式的融合等细微层次,联想到香港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属性。作为香港新移民,葛亮已经没有第一代南来文人的那种中原意识,反倒是积极尝试拥抱香港,融入香港,并坚持了粤港这个共同体本位,形塑的是一种粤港文化的认同。另外,我还想谈“怀旧”这个问题。葛亮很喜欢写“怀旧”,但在阅读《燕食记》的时候,我觉得葛亮也不仅仅是“怀旧”。茶楼也好,各式各样的点心、菜品也好,我认为葛亮在其中想要寻求的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香港近些年一直在提倡保育本土文化,保存集体回忆和历史古迹。我认为葛亮恰恰是通过书写和记录岭南饮食文化的变迁,从而去确认香港,或者说去确认整个大湾区的传统文化身份问题。
丛治辰:就像晓炎说的,如果说葛亮写作的重点是对一个行当的感怀,那么通过怀旧,塑造出的不正是一个固定观念之外的文化中国吗?怀旧包含着一种历史意识,涉及历史滚滚向前的矢量向度,同时也表明了一种不可能的感怀,即过去已经一去不返。小说是要在这种不可能性当中,召唤某种可能性或者召唤某种残影,这个情愫特别值得玩味。
怀旧到底指向什么地方?如何看待这种怀旧?葛亮的怀旧有着《红楼梦》的余韵,感慨老字号的消失,正如红楼中大楼倒塌的意味。但这种传统的怀旧并不过度,葛亮用一个百年食物史把整个世纪包含其中,去静观、品味这种繁华兴衰背后的滋味。包括争霸赛最后的那个场景,这象征了现代的传媒文明对古老技艺的袭击,可是同时匠人以他们的方式保留了某种尊严,也完成了某种蜕变。
毛晖:这种尊严是对环境变化的反拨,也就是把开放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工坊。最后那段厨艺描写,跟前面的基调完全不一样。最后就是一个匠人,在自己的工坊里面专心钻研那种迷人的样子,哪怕是面对一个公开的地方,摄影机在边上,露露作为旁观者也在边上,但他们照样把它当作自己的工坊,极度专注。且除做菜之外,还有人情的解决,就是信义,这指向师徒怎么样解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可能的龃龉,还有一些与大历史相关的人情世态。小说里面感动我的,也经常是那种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和情感方式。
丛治辰:玥晖的感触不来自于理念,而正是因为感知到了小说细节。小说写怀旧、写旧日繁华,用了大量细节,涉及特别详细的菜的做法、食材的来源、风俗、时序,包括庖厨行里的等级差别与传承规制等。细节的妙处还体现在结尾,其实师徒打擂那部分是一个众多眼睛在盯视的情况,但为什么我们的目光还能聚焦在这两个人?因为小说将厨艺的细节呈现得相当充分。
广东菜的特点就在于细节。但据说广东点心的出身并不高贵,只是为了长久保存粮食,所以做成点心。所以所谓旧日繁华,所谓饮食文化,把一些东西做得非常精致,其实是迫于生计,文化是无意间生发出来的。所谓怀旧,怀的不仅仅是旧日繁华,因为旧日不仅是繁华,太史第是繁华,尼姑庵是浮华,到了粤西的小城安浦,已经谈不上什么繁华了,但似乎更令人动情。所以当我们关注小说里的饮食文化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想得多么高尚,首先要看到它平常中见神奇的一面。同样是饭,有太史第吃的饭,也有安浦镇吃的饭,不是要多么昂贵和稀奇,而是把粗茶淡饭也能做得好,在粗朴中锤炼精细,这或许才是《燕食记》要写的“食”。到底什么是好饭呢?我个人觉得,小说当中最动人的一顿饭,还真不是那钟鸣鼎食之家的饭,而是阿响给母亲做的那顿饭,那里面的情感因素,大概才指向所谓的“怀旧”。
胡行舟:小说从一开始的精致、精细到之后香港语境下的批量复制,突显了生产方式的转换。可以说,小说对传统的饮食、烹饪方式的书写指向的是文化研究强调的“日常生活”,与之后的历史转换构成一种否定的关系。历史中那些精致的日常生活,传统日常生活的记忆,构成了对现代性的机械复制和激进大历史的共同抵抗。
王思远:我感觉葛亮所描写的日常生活,就是那种哪怕在艰苦的年代,我们依然能够享有,或者说保存的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不是说有多精细,却有着能让我们跳出艰苦生活的环境,回到平凡的日常中去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就会因此而感觉到内心中有一点安慰,或者说,感受到某种传统与传承的象征,体会到安稳的生活感。比如小说中吃荔枝那一段,葛亮细细描述了荔枝的品种、品类,以及特殊品种所需的那种独特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并且书写了“雾山荔枝”的一系列特殊性,既有着博物学的趣味,也有着民间的智慧感,这是小说中的美学形态的一个代表,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不同寻常的日常生活美学就发生了。
丛治辰:这种安稳当然是一种幻觉,林孜也许会将之视为一种遗憾,或者至少是没有足够正面地回应大历史“变”的一面。但小说家不是负责提供方案的。葛亮自然不能断然提供一种直接有效的回应方式,无论他如何努力去建构历史的可能性,最终也只能提供一种想象。我们在面对这部小说的时候,其实能够读到葛亮自己内心的矛盾,关于传统、现在与未来。而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动人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的不能断然判定。文学的美很多时候就在于茫然,确定的东西是专业读者阐释出来的。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