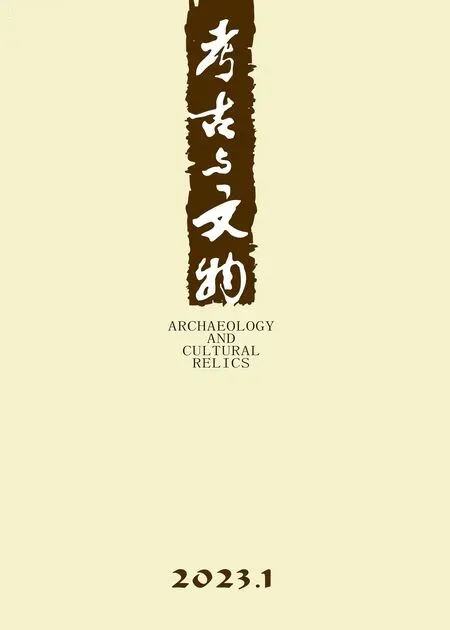秦封泥中苑囿职官结构勘考
——以“御弄”为中心
吴 旦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
古代苑囿,是为帝王豢养奇兽珍禽的地方,也是供帝王宴游射猎的场所。为了苑囿日常的管理维护,以及为帝王提供服务便利,中央朝廷和苑囿内部都设有与苑囿相关的职官。历史文献中关于苑囿职官的记载零散不备,随着新近20、30年秦封泥的大量出土和研究,补充了这一方面资料的缺憾。但同时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研究者对相关出土秦封泥的释读各见仁智。现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上林苑这一秦时较为重要的苑囿为参照对象,对在历史文献中缺如但在出土秦封泥中发现的“御弄”“阳御弄印”“阴御弄印”“御弄尚虎”等封泥进行释读,以期对“御弄”在苑囿职官结构中的职位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脉络梳理,并就与之类似的职官问题的研究提供一隅之见。
一、秦苑囿
苑囿之名,《说文》释为:“苑,所以养禽兽”[1],“囿,苑有垣也”[2],即苑囿最初是砌筑了墙垣在其中豢养禽兽的地方。同时也是为王室贵族提供诸如游猎、宴饮等休闲游乐的场所。苑囿之起,非秦始作,“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鱼跃”[3]。即是描述周代文王时期的灵囿和灵沼。在此之前的殷商时期,纣王亦有鹿台、沙丘苑台的营建,史载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4]。春秋战国时,苑囿大为兴盛,在秦国的昭王、孝文王时,已经有许多关于“苑囿”的文献记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仅在关中地区苑囿众多,在六国原有的苑囿基础之上,又将其加以改造重新利用起来。其时,在秦的诸多苑囿中,形成了以上林苑、宜春苑、云梦苑等为代表的著名苑囿。所以史称“园邑之兴,始自强秦”[5]。此类文献亦不鲜见:“(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6]“秦二世元年十一月,建兔园。”[7]“(始皇三十五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8]
不止统治者有自己的苑囿,位高权重的诸侯大臣也有自己的苑囿,秦始皇时,“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公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9]。到汉代亦是如此,“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10]。有别于王室和诸侯,一些巨贾富民也构筑了自己的私园,《三辅黄图·苑囿》载:“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11]
早期的苑囿,如周文王时的“灵囿”甚至还能做到“与民同其利”。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论是皇家苑囿,还是诸侯大臣的私家苑囿,一般平民百姓都不能入内,所以皇家苑囿一般也称为“禁”或“禁苑”。史载秦二世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12]。汉时,武帝为了自己游猎之便,“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13]。另外,一般人等不能在皇家苑囿之中捕猎动物。“(安丘侯)指坐入上林谋盗鹿,国除。”[14]也不能在苑囿中走马驰猎,不然也会受到处罚,“章坐走马上林下烽驰逐,免官”[15]。这就涉及到苑囿的日常管理、运营和维护,以及相关的职官设置。
在传世文献中虽有不少关于苑囿之中的管理规范和职官结构的记载,但是仅凭这些描述尚不能够了解当时的具体现实,也不能够完全还原其时管理苑囿的职官结构到底如何。随着秦封泥的出土,大大扩充了不见诸文献的许多与当时苑囿相关的职官信息,补充了这方面文献资料的阙如,对秦苑囿尤其对苑囿职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秦封泥
如周晓陆所指出,秦汉的玺印实物多出于庐墓,多为随葬印而非实用物,距实用玺印应有一定距离。而封泥是当时玺印实用的遗蜕,它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玺印的使用方式和实际的职官史地内容[16]。对封泥的关注始于清末,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中秦封泥的不断发现,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渐次展开。考古发现的封泥多见于考古简报,封泥著作以《古封泥集成》[17]《秦封泥集》[18]以及《秦封泥集存》[19]等为代表。
在已公布的秦封泥中,与苑囿相关的封泥,据徐卫民文章所列,不下30例,主要有诸如“宜春禁丞、尚御弄虎、白水苑丞、上林丞印、坼禁丞印”等(图一~三)[20]。另有研究者统计,与禁、苑相关封泥有37例[21],其中苑名有“白水苑、北苑、鼎胡苑、东苑、杜南苑、反苑、萯阳苑、高栎苑、共苑、旱上、南苑、平阳苑、曲桥苑、桑林苑、上□苑、西宫苑、杨台苑、旃郎苑”等18例。以上两种统计各有侧重,但也各有遗漏,随着考古发掘与私人收藏公布于世的封泥来看,苑囿相关封泥还远不止以上统计所列这些。笔者据《秦封泥集存》所著录封泥初步统计,可见的苑名有“白水苑、杨台苑、萯阳苑、鼎湖苑、东苑、段苑、阴苑、高泉苑、高栎苑、共苑、旱上苑、平阳苑、曲桥苑、西宫苑、苑、旃郎苑、北苑、杜南苑、云梦苑”等19例,其中刘瑞书中没有前举王伟统计如“(反)苑、南苑、桑林苑、上□苑”等4例苑名,而王伟统计中亦没有刘瑞书中“段苑、阴苑、高泉苑、苑、云梦苑”等5例苑名,因此综而言之,其实这里就有23例苑名。另有如“霸园、博望蓠园、乐成园、离园、杏园、枳园、中羞阳园、更驾园、高栎园、苇园、永父园、阳寿园、宜春园、柳园、平定园、具园、康园、员里园”等园名18例,还有“宫、禁、台、池、圈”名近40个。它们多与苑囿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统计中所暴露的问题除了统计者能否顾及外,还在于对于封泥印文的识读是否准确以及对苑囿范围的认识和界定是否清楚。譬如,对“尚御弄虎”等封泥的识读之误,也遗漏了一些与苑囿相关封泥的统计;还有一些“园”名,它们究竟是属于苑囿还是属于陵园?这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确定。因此,对苑囿名称的统计,仅可反映苑囿封泥数量之众,但不是最终确数。

图一 “上林丞印”封泥

图二 “白水苑丞”封泥

图三 “宜春禁丞”封泥
在20世纪90年代,西安北郊相家巷出土一批秦封泥,其中发现了本文将要讨论的“御弄”“阳御弄印”“阴御弄印”等封泥。
三、“御弄”与苑囿职官
在皇家众多苑囿里面,管理苑囿的职官也是较为庞大的一支队伍。因此,对职官从属的研究,不仅是对其时官僚制度的一种了解,同时也是了解秦汉苑囿的一个重要面向。现以上林苑为例,以出土“御弄”“阳御弄印”“阴御弄印”“御弄尚虎”等封泥以及相关文献为基础,试对他们的职官从属结构作出考察和梳理。
由于汉承秦制,通过汉代职官等级结构的文献,也有助于理解秦代相关的职官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又上林中十池监……皆属焉”[22],此处虽仅言“上林中十池监”是少府六丞其中之一的属官,却不难知,上林十池监的直接上司即是少府属官六丞之一。又后来在言及武帝时期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时云“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铸钱皆属少府”[23](图四[24]),可知此处之“初”是说在武帝置水衡都尉前的情况。如此,可知皇家苑囿如上林苑是从属于少府管理的。少府是上林苑的上一级机构,这主要是因为上林苑这些苑囿选址本是“山海池泽”之地的缘故,如上林苑、云梦苑即是。同时,上林、御羞、御府等同属少府,应是属同一行政级别。又《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灌、踵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25]这是到了汉武帝时的变化,同时还可以看到,“上林”和“御羞”依然是同一个级别。汉置“水衡都尉”的原因,《史记·平准书》载:“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26]即最初属于少府管理的上林苑,到汉武帝时,由于财物甚富,才改由水衡都尉直接管理。水衡都尉本来是管辖盐、铁等国家极贵重物品的职官,所以由水衡都尉领导管理上林苑是最为适合的。又由《史记·平准书》“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27]可知,汉代新设置的水衡是与原来的少府平行的职官。

图四 “少府”封泥
在上林苑的职官,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管辖苑囿的部门;另一部分则是设在苑囿之中但行政并不归上林苑管辖的部门,在汉代,这其中既有属步兵校尉管辖的“苑门屯兵”[28],也有与上林同属于水衡都尉的“上林三官”[29],由前引文献可知,上林三官最初是属于少府的,后面归水衡都尉管辖,与上林苑是平级单位。上林苑中的职官,文献中亦多有记载,如“上林中十池监”[30],“上林有八丞十二尉”[31],“‘上林有令有尉。’又有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之事,属水衡”[32],“上登虎圈,问上林尉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33],以及出土封泥如“禁苑右监”[34](图五)、瓦当如“上林农官”[35](图六)等等。因此,上林职官可谓队伍庞大、名目繁多,至于其中各职官之从属结构若何,由于具体文献多已散佚,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才有进一步厘清的可能。现仅就出土“御弄”“阳御弄印”“阴御弄印”“御弄尚虎”等职官封泥的从属结构作一简要梳理和分析。

图六 “上林农官”瓦当

图五 “禁苑右监”封泥
出土“御弄”封泥[36](图七),关于“御”之义,《说文》释曰:“御,使马也。”[37]后来由本义还引申有治理、统治之义,也指帝王所用或与之有关的事物,是一种敬称[38]。“弄”之义,《说文》释为“玩也”[39]。文献中,还有“弄田”[40]“弄臣”[41]“弄儿”[42]等。应劭、颜师古皆释“弄”有“戏弄”义[43],当无误。但有研究者指出,我们一般将“弄”字理解为一种比较随意、为了个人的兴趣而进行的娱乐和消遣,而这种含义如果出现在职官的命名用字中,则显得非常的不适宜,但如果将“弄”释为“珍惜”“珍爱”之意,则恰当许多[44]。此说有一定道理,不过也是强调了“弄”之另一层隐含义。实则古注今释,可理解为本义与引申之关系,并无矛盾。如果“弄田”之“弄”释为“戏弄”,而出土的“御弄尚虎”封泥之“弄”释为“珍爱”义,也未尝不可。又,由前面引文材料所示,可推断出“御弄”与“御府”和“御羞”一样,皆属少府。“御弄”即是为帝王保管、提供各种珍爱或贵重之物的职官。

图七 “御弄”封泥
在“御弄”封泥之外,秦封泥中还发现了“阳御弄印”[45]和“阴御弄印”[46](图八、图九)两种封泥。周晓陆初释为“弄陶丞印”[47],后改释为“弄阴御印”“弄阳御印”,又另注说还可读作:御弄阴印、御弄阳印,阴御弄印、阳御弄印[48]。据前文“御弄”封泥,以及结合一般的印文识读顺序,笔者以为识读为“阳御弄印”和“阴御弄印”是准确的。至于这里的“阴”“阳”的含义,周晓陆认为“阴阳或指东周至秦代阴阳家、阴阳术数家之谓”[49]。此释有误,因为若据其对“阴、阳”的解释,和“御弄”并置一起,作为一种职官设置,其义不知所云。其次,其所指的阴阳家和阴阳术家,在秦代该是从属于“奉常”即后来汉代的“太常”属官“太卜”之下[50],不可能像“御弄”一样归属少府管理。再者,后来也发现了“阴阳”的封泥[51](图一〇),此封泥在《秦封泥集存》中也是归在“奉常”的名目之下[52]。因此,不可能为“阴阳家”和“阴阳术数家”中的“阴、阳”。陈治国认为:“‘阴’和‘阳’并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区分二者的符号,如秦官中的左右、上下、大小、东西一样……当御弄一职由一人担任时,称之为御弄,当两人担任时,则分设阴御弄和阳御弄。”[53]此论不确,虽然指出了二者有“左右、上下、大小、东西”的区分,但又说这个区分是没有实际确切的意义的,这是不恰当的;其次,此论也暴露了论者对“御弄”一职认识的模糊性。李超等研究者认为御弄之下分设阴、阳御弄,是因为动物有阴阳之分,设阴、阳御弄是根据动物的类型去分管不同类型珍禽异兽的[54]。此论亦不确,其合理处是指出阴、阳御弄是设置在御弄之下的职官,不确切处是对阴阳意义的推测。在发现的秦封泥中,有“阳都船丞”和“阴都船丞”的封泥,同作为职官名称,其中阴、阳的意义显然与“阳御弄印”和“阴御弄印”具有等同的意义限定。如果阴、阳是对阳性动物和阴性动物的区分,那么对“阳都船丞”和“阴都船丞”的解释将是怪异的。职官中的同一个限定词,不可能有不同的多重意义。刘庆柱与李毓芳在对“阴都船”和“阳都船”作释读时认为,“都船属官或设阴、阳,此犹秦汉之官设左、右”[55]。这一解释是较为合理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秦封泥中出现的类似“阳御弄印”“阴御弄印”中的“阴”“阳”,是为了区分“御弄”之下不同属官的职责范围和权力大小的界定,它们或属平级,或有正、副之别。

图一〇 “阴阳”封泥

图九 “阴御弄印”封泥

图八 “阳御弄印”封泥
此外,还有一种“御弄尚虎”的封泥[56](图一一),周晓陆释读为“御弄尚虚”,依然认为是阴阳家之遗[57]。陈治国释读为“御弄尚虎”,认为“‘御弄’,即‘御弄’封泥中的‘御弄’,在此指的是上一级的官署,‘尚虎’是‘御弄’下的一个机构,指的是具体的职掌”[58]。笔者以为,篆文“虎”与“虚”字形近似,此处应不是“虚”字,更不能和阴阳家者联系起来。参照前文对“御弄”职官的释读,释为“虎”更为确当,虎作为一种珍贵猛兽,是可供帝王观赏珍玩的。另有“华阳尚果”的封泥[59],也可说明职官之中确实存在主管禽兽、蔬果官吏的存在。关于“尚”的释读,又《汉书·惠帝纪》“宦官尚食比郎中”,注引应劭曰:“尚,主也。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又引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书曰尚书。”[60]秦封泥中还有如“尚犬”[61]“尚浴”[62]“尚卧”[63]等的发现(图一二~一四)。综而言之,释读为“御弄尚虎”是更为合理的。

图一一 “御弄尚虎”封泥

图一二 “尚犬”封泥
这样释读,其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即“御弄尚虎”是负责管理帝王苑囿之中猛兽虎的职官。首先应是御弄的属官,而且因为下延至具体的事物,所以也是阴、阳御弄的属官。与其他具体如“尚犬”“尚浴”等职官一样,当是同等级别的小吏。
四、结语
在基本梳理清楚了御弄、阳御弄、阴御弄、御弄尚虎的含义之后,也就不难发现,它们这些职官在苑囿之中的行政位次。可以指出的是,少府之下与上林、御府、御羞等属于同一级别不同支系的御弄职官,其下有阴、阳御弄之别,再下又有具体的御弄尚虎的职官,这其间有无其他职官设置,还有待新的文献或器物证据的支撑。此外,可以推断的是,与御弄尚虎封泥一样,在苑囿之中还可能存在诸如可被称为“御弄尚熊”“御弄尚象”等等管理珍禽异兽的职官,它们和“御弄尚虎”同属于“御弄”领导管辖。所有的皇家苑囿,属中央管辖,只不过其驻所设置在地方。和上林苑职官不同的是,御弄的职权可能还涉及到苑囿之外的其他帝王珍玩的领域,其下可能还有负责管理奇器宝物等等的职官。至于在前引《汉书·张释之传》中出现的“虎圈啬夫”与“御弄尚虎”的关系,笔者以为虎圈啬夫与御弄尚虎分别属于上林与御弄两个不同的职官支系。虎圈啬夫是一个在上林令丞、上林尉等职官之下的一个负责日常管理、饲养具体虎兽的职官,属于末等职位,这也符合张释之传中的具体描述。

图一三 “尚浴”封泥

图一四 “尚卧”封泥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1.
[2]同[1]:278.
[3]高享.诗经今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93-394.
[4]司马迁.史记(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05.
[5]范晔.后汉书(第42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1437.
[6]司马迁.史记(第12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02.
[7]司马迁.史记(第1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758.
[8]司马迁.史记(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6.
[9]同[8]:227.
[10]司马迁.史记(第5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83.
[11]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234.
[12]司马迁.史记(第8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62.
[13]班固.汉书(第6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47.
[14]司马迁.史记(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946.
[15]班固.汉书(第27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36.
[16]周晓陆.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J].考古与文物,1997(1).
[17]孙慰祖.古封泥集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18]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19]刘瑞.秦封泥集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0]徐卫民.秦封泥与宫室苑囿研究[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
[21]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325.
[22]班固.汉书(第19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731.
[23]同[22]:731.
[24]同[18]:128.
[25]同[22]:735.
[26]司马迁.史记(第3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36.
[27]同[26]:1436.
[28]同[22]:737.
[29]a.关于“上林三官”的文献见司马迁.史记(第3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35.b.至于“上林三官”具体指谓为何的讨论,可参见徐龙国.汉长安城地区铸钱遗址与上林铸钱三官[J].考古,2020(10).
[30]同[22]:731.
[31]同[22]:735.
[32]同[11]:237.
[33]班固.汉书(第5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07-2308.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J].考古学报,2001(4).
[35]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瓦当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00-201.
[36]同[19]:364.
[37]同[1]:77.
[38]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95.
[39]同[1]:104.
[40]同[11]:172.
[41]司马迁.史记(第9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2684.
[42]班固.汉书(第6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60.
[43]班固.汉书(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9.
[44]陈治国.“阴御弄印”与“阳御弄印”封泥考释[J].考古与文物,2015(3).
[45]同[34].
[46]同[18]:229.
[47]同[16].
[48]周晓陆.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J].考古与文物,1998(2).
[49]同[48].
[50]同[22]:726.
[51]同[19]:364.
[52]同[19]:47.
[53]同[44].
[54]李超.秦阴阳御弄封泥与苑囿略论[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12).
[55]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J].考古学报,2001(4).
[56]周晓陆.秦封泥再读[J].考古与文物,2002(5).
[57]同[56].
[58]同[44].
[59]陈晓捷,周晓陆.北京文雅堂藏秦封泥选考[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1).
[60]班固.汉书(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85-86.
[61]周晓陆,刘瑞.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J].考古与文物,2005(5).
[62]同[18]:160.
[63]同[18]: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