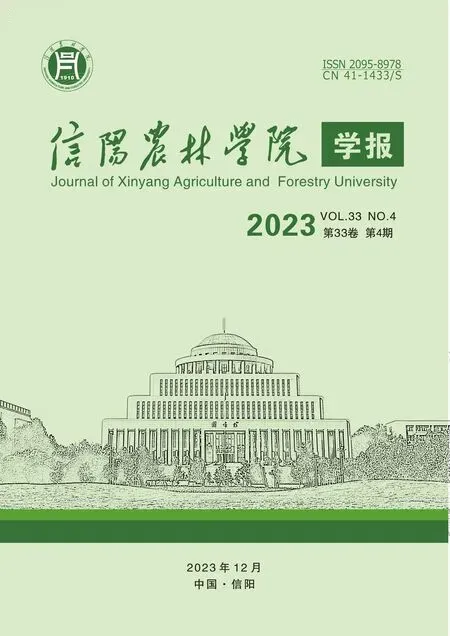书写乡土中国的新气象
——读乔叶《宝水》与付秀莹《野望》
梁玉洁,马腾骧
(1.信阳农林学院 茶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信阳农林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百年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救亡、建设、改革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承担起了书写中国和记录时代的重要责任。在新的社会面貌下,如何对中国式乡土现代化的伟大变革进行有分量的文学赋形,这之于当代作家是个不小的挑战。乔叶的《宝水》和付秀莹的《野望》就直面了这一时代命题,她们从村庄这一基础单位出发,通过个体叙事和乡村新变刻画当代中国沧桑巨变的深刻履痕。本文以这两部新近面世的长篇小说为例,分析作家们如何呈现了当代乡土的新气象,并由此观照新时代乡土的总体样貌和精神气象。
1 返乡:发现新的乡村风景
对于从故土走向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而言,“返乡”常成为反复书写的母题和叙述模式。同为70后女作家,乔叶和付秀莹的人生轨迹极为相似:农村出生,县城读书,在省会乃至首都工作安家,以农村老家为原点,生命轨迹的外延不断扩展。乔叶和付秀莹在创作各自的长篇小说时,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返乡叙述话语,一方面因为人生经历,都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独特的返乡主体,以在场的叙述展现了中国乡村的生命力和包容度。
1.1 转变焦点,发现乡村的包容和阔达
《宝水》中地青萍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失眠症是现代都市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病症,多与生活状态和心理有关,地青萍生活富足、工作轻松,失眠多是心理因素。进入城市生活后,相继面临父亲、奶奶、丈夫的离世,她像无根的浮萍,没有依托,夜夜难寐。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乡下可以治好失眠,于是果断回去,在一年的返乡生活中,她“视觉的焦点和重心发生变化”[1]58,对老家的态度由逃避转变为接纳。
地青萍视觉的焦点和重心发生变化主要见于两组镜像关系。第一对关系是宝水村和福田庄。地青萍返乡了,但没有回老家福田庄,她本能地拒绝福田庄,归根究底是以奶奶和父亲为代表的农村处世观与其本人所持的城市价值观发生了分歧。奶奶的人生信条是“人情似锯,你来我去”“维人”,她也的确以智慧和能力维系住了家族的稳定,待儿子扎根城市,她便将维系家族的绳“套”在了儿子身上,千丝万缕的绳越套越多,终于在父亲借车给同村人结婚的路上车祸身亡而断裂了。奶奶的处世哲学成为地青萍厌恶福田庄的根源,她以为这种恨意会随着奶奶的去世消失,却不想折磨到了她的睡梦中。宝水村的生活,使她不自觉想起福田庄的幸福童年,在宝水村人情往来中的游刃有余,不得不说得益于奶奶身传于她的维人哲学。“宝水如镜”,宝水村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福田庄,也照见了地青萍内心深处对福田庄的依恋。奶奶与九奶是第二对镜像关系,也是触发地青萍真正读懂乡村的重要纽带。在宝水村,她第一次见到九奶,就觉得九奶的脸、做派像极了奶奶;与九奶“扯云话”的时光里,她拼凑出了奶奶少女时的模样,完成了对奶奶的精神画像;与九奶同吃同住,发现九奶的气息也像极了奶奶,她不自觉地把九奶当成自己的奶奶,在她身上倾注了对奶奶未尽的孝心。在九奶的遗言中,她终于知道了让自己无数次梦魇的奶奶的遗言:回来就好。谜团打开,她完成了自我救赎。在两组镜像关系中,地青萍从认为“所谓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1]19到“老家意味的,是亲人”[1]330,而深刻理解了老家的意义。
乡村不会言语,它一直都在那里,对乡村的态度,取决于人的心境。再次返乡,地青萍重新理解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逻辑,内心的矛盾纠缠得到释怀。《宝水》是一场精神返乡之旅,她意外地发现了乡村的包容和阔达。
1.2 全景画卷,呈现乡村的生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书写,较为频繁地流露出对乡土终结命运的忧思,这的确与中国农村溃败、空心化的现实有关,但并不代表乡村就是一派绝望的景观,那些未曾离开的人始终与乡土命运与共。所以,付秀莹是可贵的,她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隐身在主人公翠台的身上,本真地从一个农村妇女的视角全景描绘了热气腾腾的新时代乡村生活画卷。
如果《野望》是一部电影,镜头就是始终围绕着翠台的,“吃罢早饭,翠台到她爹那院里去”[2]1,而后就是一镜到底的长镜头:耀宗家人头攒动的卫生院、卫生院对面秋保超市、超市旁边新盖的村委会大楼、大楼前面建国媳妇的烧饼摊子。翠台脚步和眼睛关涉到的地方几乎涵盖了芳村医疗、经济、政治、社交的全部场所,在这些活动场域,流动着不同的人物和故事,都带有生活的温度和肌理,这是乡村秩序稳固恒常的状态。芳村中的物象也顺应四时的变化,呈现出饱满丰盈的生长姿态。冬日阳光薄金一样淡淡洒下照得人懒洋洋;居连上种着枣树、槐树,杂草茂盛,空气中一股子潮湿的泥土腥味儿和着庄稼地的草木青气……自然物象群不仅装点了故事的自然背景,也凸显了乡土生活的秩序和生气。
芳村的生命力还体现在常态生活中的变态事件,变中涌动着一种寻求出路的迫切需求。翠台的生活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儿子大坡与媳妇爱梨闹矛盾,爱梨连夜回娘家从小寒住到了腊月底,翠台托人请了四回,每请一次内心就愈发焦灼,但在人前,为了维持家庭的体面和安稳,她还是该拉家常拉家常,该办年货办年货。爱梨被接回家,翠台的生活似乎平静了一些,紧接着妹夫投资被骗,厂子快办不下去了,翠台非但帮不上忙,还欠着妹妹家的钱,只能指望丈夫根来养的猪卖了钱才有办法。不料,养的猪一夜之间闹瘟疫死光了,不仅没了经济来源,根来也心事重重。两代人的家庭矛盾、农村传统经济模式的不稳定与低效能带来的生存危机,几乎是芳村家庭都面临的问题,每一家都在平凡琐屑的生活中手忙脚乱地应对。“变动—应变—常态”的过程中,乡村的人和物都在与时代的互动中酝酿新的可能。
2 造境:点亮乡村传统美学的光彩
中国乡村已然步入城镇化的轨道,全球化、现代化的人文风景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大地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乡村中具有地域色彩、民间色彩的民俗文化也正在流逝[3]。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乔叶和付秀莹,将传统文化元素注入小说的血脉和根系,又以鲜活的方言俗语活跃了乡村的表情,点染了中国乡村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2.1 传统的重量
“一部好的长篇必须有一个好的有机结构,以求在相对精小的空间中贮藏起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容量。”[4]《宝水》和《野望》采用了“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结构小说,在始于冬终于冬的四时集序中完成一个井然有序的轮回。《野望》以二十四节气命名章节,形成了以“节气注解语—节气古诗词—生活场景”为固定模式的每章结构:
春分
《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踏莎行·鱼霁风光
[北宋]欧阳修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
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蓦然旧事心上来,无言敛皱眉山翠。
春分了,天气渐渐暖起来。草木万物都生发了,空气里湿漉漉甜丝丝的……算来算去,越算心里越烦恼……闲得人心慌[2]142。
每章古诗词的选择并非简单的对号入座,诗词的基调往往与故事氛围有内在的一致性。春天,自然界万物复苏,但这个家庭却没有生气:翠台家养猪,猪肉价格一直往下掉;村里青壮年都在忙活,儿子儿媳却无业,花钱还不节制,如此种种正是“旧事心上来”。付秀莹深谙节气就是乡村人的生活节奏和精神原点,节气关联着他们的收成、温饱,指导着行为处事和生活秩序。她以节气和传统文化架构小说,打通了进入中国乡村的路径,提供了解开乡村文化的密码,这种精心和耐心正体现了作家还原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乡村面貌的用心良苦。小说的名字“野望”与唐代诗人杜甫、王绩的古诗《野望》题目相同,这种并非刻意的一致,“大约是传统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它早已经渗透到你的文化血脉深处,默默滋养润物无声”[5]。跨越时空的作家们,都在“野”而“望”,看见的风景已是沧海桑田,但对家国民众的深沉情感是相似的,这就是作家对深藏在精神血脉中的传统文化的自觉体味与认同。
《宝水》分为“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每章均匀分布30节,共120节,也时常可见作家对节气、时令相关生活的描写,如惊蛰吃懒龙(菜蟒)、正月挖茵陈、三月三荠菜煮鸡蛋等,都表明了节气对乡村人生活的深刻影响。相比节气,小说中更引人注意的是作家对乡村风俗习惯和口耳相传的念词、唱词等的熟悉。盖房子上梁时要送主家面包或刚出锅的馒头,取一个发字,上梁要选阳气正盛、阴气全无的吉时,请太公、祭梁(浇梁和上梁)、撒梁,每一步都有隆重庄严的念词。这样繁杂的流程反映了土地、房屋之于乡村人的重要意义,传统的自然经济使乡村人依附于土地,土地也带给了他们归属感,人与土地的黏连造就了中国人深刻的乡土观念。小说中舞狮子喊彩的情景也十分热闹,锣鼓班和舞狮兄弟走过村里的每一家,依着家中的情况都有一套唱词,家中有喜就唱得热闹喜庆、有丧就唱得悲恸苍凉,整个队伍配合得行云流水,每一户村人都感受到了社群的亲密团结。小曹结婚时,铺床环节最要紧的还是念词,只有八句,大英还与时俱进,把时兴的词融进去,旧俗新礼竟和谐有趣。九奶是村里行走的典故和风俗集,她被大英逗着唱时令菜名儿曲子,节奏韵律虽完全变形,却让人牵肠挂肚。九奶去世后,吊孝的人络绎不绝,村里安排抬着九奶巡山,选定吉时,由孙子老原摔瓦盆扛幡,徐先儿高喊“八仙各守一方—抬重各在其位—起灵”,巡山正式开始。巡山不走回头路,走过西掌喊四句词,到了中掌又喊四句,下棺前还需至亲躺进墓坑暖房,埋棺前众人撒土……九奶配享巡山,不只是因为年纪和贡献,她仁厚如地母的气质,代表着传统的乡土精神,她是乡村凝聚力的体现。
在乡村,盖房子、结婚、丧葬、农事活动等都有相关的风俗习惯或行事规则,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乡村秩序,人们在共同体中遵守秩序并享受秩序带来的安定,这些传统文化就是乡村赖以存在的根基。需要补充的是,两部小说都描写了乡村迷信现象,《野望》中小别扭媳妇善跳大神,被无助的人们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宝水》中赵先儿铺个卦摊儿,说命看宅相面滔滔不绝。迷信固然是乡村传统文化中蒙昧的一面,但也侧面反映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厚重绵长。
2.2 流淌的语言
两部小说虽都有明确的时间线索,但推动小说的却是一种强大的语言力量,在充满乡野气息的语言流中,细碎的生活、缠绕的人情、绵密的事理全部敞开来,一种久违的生活体验扑面而来。两位作家凭借对地方生活和语言系统的熟悉,唤醒了方言的生命力。
评论家陆梅认为《宝水》是“三成书面语、七成方言土语”,乔叶完全同意这一说法[6]。小说120个标题,有近30个是以方言词条作为标题,如“维”“悠”“扯云话”“里格楞”“得济”等,由此引出对人物、故事以及乡村典故的讲述,颇有周立波《山乡巨变》、韩少功《马桥词典》“词典体”的形式。“悠”是闲庭信步的意思,在放松、无事的情况下,慢悠悠地晃荡在乡村各处,呈现了心境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和谐。“扯云话”是聊天的意思,但又非聊正事,而是无边无际、天马行空般随意聊下去,话头越扯越多、越扯越远,没有目的,也不追求意义。标题之外,小说中还有大量的乡谚、俚语、俗话、童谣,展现了豫北乡村独特的语言样貌,更凸显了地域滋养的人物性格和精神脉络。
《野望》中的语言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细腻的美感,付秀莹善于调配各种感官体验,搭配贴切的语言,打磨小说的细节,使我们感同身受。
“这个季节,天短,黑夜来得就快些。也不知道是雾,还是霾,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慢慢笼罩了整个村庄。路灯却迟迟才亮起来,是那种苍白的灯光,好像是一只一只眼睛,在茫茫的暮色中明明灭灭。田野变得模糊了,天空中那些横七竖八的电线,也没了痕迹。谁家的狗叫起来,懒洋洋的,叫了几声,觉得无趣,也就罢了。有小孩子在放鞭炮,噼啪一声,噼啪又一声,噼啪,又一声,犹犹豫豫的,是试探的意思,也有那么一点不甘心。”[2]39
意象虽稍显低沉,但生活气息丝毫不弱,作家调动了翠台视觉、听觉、触觉、情绪全方位的感知,描绘了大寒傍晚人景交融的场景。翠台本就因爱梨回娘家,三请四请不回来,儿子却没心没肺而恼恨到流泪,此时站在门外见夜色渐渐笼罩,内心更加孤独无助。断断续续的噼啪声,就仿佛爱梨娘家不肯轻易妥协的态度,任她再有心劲,也只能焦虑又期盼。付秀莹这段描写颇有鲁迅遗风,用极其细腻的笔触雕刻出了日常生活的褶皱和人性的共通点。除了极富故事感和情绪力的语言,小说中只要人物互动,方言就无处不在,“叫他们笑话去!都是添言不添钱的。谁家能说一辈子在岗上?谁就没有跌在洼地的时候?”[2]76稠密的方言,不需要解释,就能明白意思,并以此照见人物的脾性,人与话紧密相融,有一种人在话中、话见人心的阅读体验。
一般而言,描写乡土的小说总会有“国骂”“屎尿体”等粗鄙的方言,但在这两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乡村生态纯洁纯真。所以,方言在这里不仅是一种声音、一种语言,更是作家体察当下乡村生活的一种立场和视角。
3 建设:呼之欲出的新乡土想象与乡村变革
在中国村庄的地图上,并不能一比一找到“宝水村”和“芳村”,他们是作家新乡土想象的产物,但也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宝水村是乔叶以焦作的一斗水村的地理形态,融合信阳郝堂村和焦作大南坡村的生活实践创造出来的[7];芳村是付秀莹对故乡的一万种想象和记忆的承载装置,实际上它们彷佛是每一个中国的乡村。《宝水》《野望》用文学想象的方式参与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并试图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方案,也正因如此,乔叶和付秀莹的乡土书写扩大了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格局。
宝水村走美丽乡村道路,除了自然条件成熟,还有赖于国家政策资金扶持、乡建团队的专业指导、领导的重视和乡村基层组织的实干。孟胡子“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乡村干实事、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8],他不是乡村基层干部,也不是农村新人代表,作为宝水村美丽乡村项目的规划师,非体制的灵活身份以及对乡村规则的熟悉使他在与政府、村民的往来中较少局限。孟胡子从不以优越的姿态批判或教育村民,更多是建设性的指导,从乡容乡貌上规划每一家民宿的院墙、瓷砖、指示牌;在垃圾治理、厕所、收费问题上详细解释和引导,以现代管理制度帮助村民摆脱小农意识、顾全大局。孟胡子的乡村规划始终重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就是希望即使自己或闵县长离开,乡村仍能自主运转。孟胡子是乡村外来者,他打造了宝水村人和城里人理想的生活面貌;大英是在村者,她守护和巩固了宝水村的发展和稳定;小曹是返乡者,他享受并参与村庄的建设,他们与村庄都有不同的连接,但都在这里找到了价值并赋予了乡村新的意义。
“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9]。《野望》中芳村是冀北一个平原村,付秀莹没有程式化地将乡村旅游作为乡建的法宝,而是尊重自然生态,让芳村顺势走产业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增强了个体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市场经济时代,这种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小说中大全、增志、团聚等各自经营的皮革厂因为资金、污染等问题面临破产;根来等个人养猪场遭遇猪瘟,全军覆没。独立经营看似自由灵活,一旦风险来袭,对整个家庭就是灭顶之灾。如何解决村民分散经营中的困难,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供了一个有效参考,不同的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包括劳动者的劳动联合,还包括劳动与资本、技术、管理等联合,联合的目的是实现个体的发展”[10]。发达带着根来等人发展公司加农户的新型规模化养殖模式,背靠大公司,把零散的农户养殖联合起来;县里建了产业区,将对增志等的小厂子进行统一管理;香罗经营的超市开启了加盟连锁的模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给了芳村人新的出路,也焕发了乡村新的生机。
宝水村主打旅游致富,芳村依靠产业振兴,在差异化转型的道路上,现代智识资源的注入使乡村旧貌换新颜,而作家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如何激发乡村内部的强韧生命力,真正实现乡村振兴。“村景再美,美的芯儿还是人”[1]483,只有革新乡村人的经济观念、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等,才能使村庄即使没有外在的支持,也能“断了输血自造血,真正做到自力更生且生生不息”[1]162,这也是两部小说进一步关心的问题。乔叶在《宝水》的闪光之一就是塑造了“美的芯儿”——乡村女性雪梅的形象。雪梅同丈夫经营民宿,她善良、有原则、素质高,具有乡村传统女性的美好品行,更重要的是,她具有符合新时代的意识观念。雪梅的审美天分是地青萍和孟胡子认可的,她喜好插花、热爱绘画,民宿的布置具有超出同村人的高级感。食药监管局抽检民宿的食品安全,本村的民宿只有雪梅家过关,因为她不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干货,凭良心、讲原则。《野望》中翠台的孩子大坡和二妞是新时代典型的乡村青年代表,大坡学业无成、工作无着,在父母的操持下娶妻生子,婚后一家三口继续啃老,在经历父亲养猪失利、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后,他意识到家庭责任开始变得勤劳务实。二妞在城里读书,翠台希望她留在城市吃国家饭,二妞却要回来建设乡村,她是属于新时代独有的新人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青年要进城才能改变命运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现在,二妞这样的农村青年选择建设乡村已成为一种趋势:喜针在北京念了博士的外甥回县里工作、镇里新来的博士生张书记、来村里挂职的郝主任、在村里办画画培训班的四川美院毕业生,大批返乡者或下乡的年轻干部投身乡村建设,他们是芳村的一道风景,也是新时代乡村变革跳动的脉搏和翻腾的血液,正是他们,乡土想象才有极大可能成为现实。
“芳村这地方,向来讲究这个。”“芳村这地方有个风俗。”“(宝水)村里就是这”,乡村有自成一套的传统和秩序,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体系,唯其不变,才凝聚人心、涵养情感,才使中国乡土稳固恒常。乔叶和付秀莹在《宝水》和《野望》中,都将乡村作为叙述的主体,活跃传统文化的基因,运用贴近土地的语言,以地方色彩、民俗画卷、乡村新颜展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守常与新变,建构了新乡土小说的文学形态,耐心地完成了当代作家书写乡土中国新故事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