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侄子王老师
“一个人,他姓王,腰里掖着两块糖。”不用问,这是一个老字谜“金”,也是王老师教的第一个字谜。
王老师是多年前我老家村小的老师。这位王老师年龄不小,四十大几了,而辈份却低,教的是一屋子的叔。有一次,这位大侄子王老师就别出心裁地在课堂上搞了个小插曲,跟叔们探讨“王”字。先是写,这“王”字三横一竖谁都会写,难不住叔们,只是叔们写得歪七扭八不太审美而已,王老师就将周正的王字圈出来,讲字形,讲书法,讲做事做人的认真劲。
写出这字当然不算完,接下来,王老师又一个个问:“王字为什么是三横一竖?”面对这个问题,叔们嗫嚅着油嘟嘟的嘴,就无话可答了。有大胆的,就试着说了一句:“老鳖肚子上好像有个王字……”嗨,这个回答显然不是王老师想要的答案。王老师就气不打一处来,噼里啪啦开揍。按当地风俗,再小的叔都可以骂侄子,而再老的侄子也不能骂叔。当然,作为平衡和补偿,侄子既然不能骂叔,是可以揍叔的。王老师就开始逐个揍叔了。当时,老侄子多么“恨叔不成钢”啊。需要说明的是,揍和打是不一样的,揍不是实质性的,主要体现的是象征性、侮辱性、警戒性和教育性。也就是说,侄子揍叔不是非礼行为,而是教育艺术。遗憾的是,揍过之后,王老师最终并没给出什么答案,因为他自己也不知答案。
唉,斗转星移,往事如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直到不久前,我才知道“王”字三横一竖的解释,“天、地、人,三者之贯通也”。这一定是当初王老师最想要的答案,可惜这个答案迟到了这么多年。
回到村里,见到“豆芽”“小乌盆”“吱噜酥”“炸锅”,就浑闹一通。我们这拨五十几岁的人,不太避讳绰号,喊起来就像水浒英雄的雅号一样。
比如我吧,就叫“炉条”。这个绰号得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十一岁,随父亲去了趟县城,午饭时,父亲带我进了饭馆,吃的东西金灿灿的,皮儿酥脆,瓤儿软嫩喷香。父亲对我说:“这是油条。”
回到家,我却将它的名字忘记了。在一次病中,奶奶问我,想吃什么?我想了许久,最后说想吃“炉条”。奶奶一听,懵了,“炉条”是铁的怎能吃?以为我发烧说胡话。我最终没有吃到“炉条”,从此就赚下了这个绰号。
因为经过极端匮乏的年代,伙伴们的绰号基本都与“吃”相关,起因也多巧合。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只因一句“过年好,豆芽菜随便扒”,便叫了“豆芽”;一个伙伴一连几天带饭时煎饼里夹几块“吱噜酥”(炼猪油的肉渣),于是绰号就叫的“吱噜酥”;在中秋节吃下一小乌盆南瓜馅水饺的,因此叫了“小乌盆”。
算起来,“炸锅”是最有故事情节的。那天念完早自习回家吃饭,走在街上就听到了哭声。伙伴们循着哭声找到那户人家,发现这一家的大人们下地,家里的孩子煮了一锅地瓜,最后煮干了锅,又匆忙加了凉水,锅炸了。地瓜煮得真好,个个手指粗细,透亮,是那种紫心的“秧瓜儿”,很香甜。邻居们在解劝哭着的一家人,我们当然知道,这家人哭绝不是心疼地瓜,而是心疼锅,在那时的村里,锅炸了,这几乎是个事件。我们几个小伙伴当时也有些难过,但是那并不妨碍我们伸出小手各自抓了几只透亮的“秧瓜”,在石磨后头旁若无人地吃起来。难以理解,我们当时的心理素质多么好呀!一边替人难过,一边吃人家的东西。那是怎样地没心没肺!从此,这家的孩子就叫了“炸锅”。
绰号与食物息息相关,记载了我们曾经的贫困。后来,终于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绰号——它摆脱了“吃”,这在我们的绰号里极具突破意义。
记得那天上课,大侄子王老师讲了几个生字。待下课时,王老师要验证一下,生字是不是被学生“左耳听、右耳冒”了?便指定一个字叫起一个同学来问:“这个字念什么?”那同学显然已经忘了,吭哧半日说不出。王老师生气了,把那个字拆开,一部分一部分地让他认,同学终于念出了“马”“大”“可”三个音节。从此,这位与“骑”字有着天生缘分的人就叫了“马大可”。这可是伙伴们最早的一个与“文化”有关的“雅号”啊。
后来,我有幸成为教书育人的人。我从大侄子王老师那里学到了一招——“问字”,在与学生的交流中,经常一用,效果很不错。人们常说,教育就像装瓶子,先装石子,再装沙子,最后装水。这冷不丁地问个字,就是装瓶子的那最后一滴水,会让瓶子更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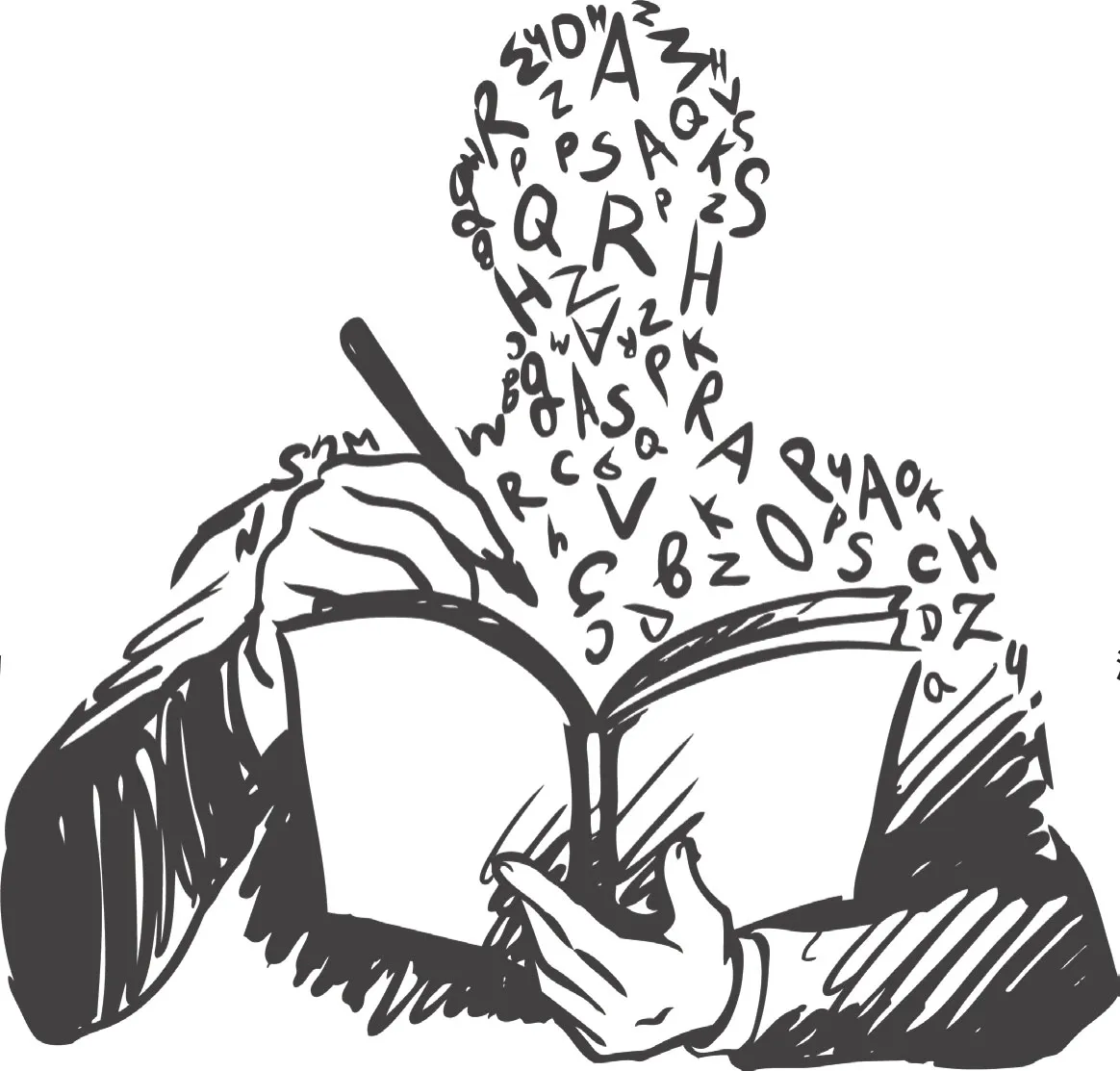
我当然也不敢放松,要时刻提防着学生突然发问。有的学生贼精,他会处心积虑地找一个合适的字,冷不丁地问老师。有鉴于此,我就无法懈怠,尽力博览。我老老实实地读了《史记》,读了《诗经》《论语》《老子》《庄子》,读了四大名著。我从不放过遇到的任何一个生字,不管是书报里的,还是路边招牌上的,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查字典。如此一来,“不见其长,日有所增”,我的字库恰如捡米粒,日渐饱满起来。我认识了“甪直”之“甪”,认识了“水氹”之“氹”,认识了“劬”“亹”“璺”“鼒”“嚚”“旪”“宲”等等。在无声的鞭策下,我成了一只“书虫”。
有一次,回老家过年,去看望大侄子王老师。坐着闲聊了一会,王老师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走到床头,从枕子底下掏出了一本书。他翻到一页,问一句:“你看,这个字念什么?”就把书送到我的眼前。我接过书,一看,愣住了。我不认得那字。我满脸发烧,万分汗颜起来。见我窘住,他说:“真是少见的字哈!”我嗯一声,端着那本书装模做样地看了一会儿,以便从窘态里慢慢挣扎出来。我盯了很久那个让我蒙羞的字:“毐”。又盯住书面,是《东周列国志》。
我知道,这是王老师在试探我。看来,防不胜防。以前,遇到生字只能回家查字典,这次我当然用到了智能手机,我点到网上词典,手写输入“毐”字,一查询,即刻得到完整的解释,是“用于人名,嫪毐,战国时秦国人”。此时,我不由一惊,既然如此,它一定呆在我读过多遍的《史记》里,可是我却屡次漏了它。看来,一个生僻的汉字,只有让你丢尽了丑,你才能牢牢记住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