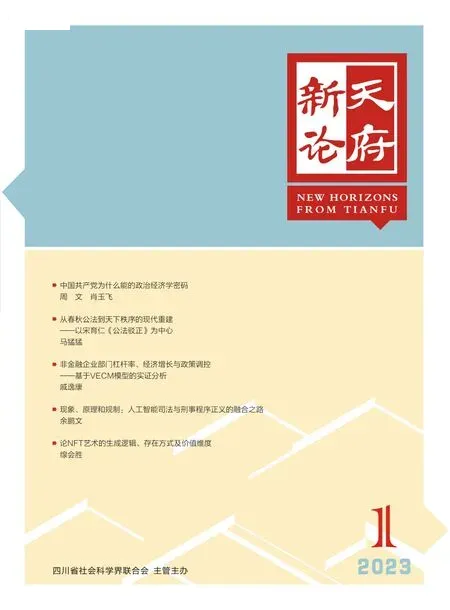从缺失的外部到共-显的姿态:欧美城市文学情感问题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丁鹏飞
进入现代性以来,哲学的“思乡”之情愈益凸显,这种家园意识的潜流,也从现代到后现代欧美作家资本主义的城市背景中被连绵不绝地重新唤起。从自然生态学的牧歌想象,到人类社会学的有机渴望,从记忆伦理学的迫切寻根,再到地理政治学的正义诉求,这种对城市无情感化的批评,已经成为现代思想传统脉络的基本共识。城市“无情”,以致欧文·豪(Irving Howe)在试图理清这一判断所依赖的情感基础时,也陷入了一种不精确(1)Irving Howe, A Voice Still Heard: Selected Essays of Irving Howe,Nina Howe E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61-177.。因此在诸多情感样态流变不居,城市经验也纷繁易逝的事实前,我们又如何才能在两者间建立一种适切的观察距离,从而将问题从失焦带向清晰?
从现代到后现代欧美作家相关城市文学作品来看,正是处身城市的人类的身体姿态,成为将城市经验与情感样态衔接起来的“索引”。因此,要做的就不是在历时性的层面分析城市属性的变迁,也不是浮光掠影地罗列并意图穷尽所有的欧美城市小说。相反,从欧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时段内,在彼此呼应的代表性城市文学作品中,通过姿态现象从共时性的层面见微知著地将其中潜伏的逻辑关联牵拉出来,将能为我们考察城市文学,提供一种清晰可辨的批评视野。从表面上看,虽然这一思路会忽略城市文学与不同历史地理文化背景间互为对应甚至环环相扣的语境意识,如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的分析(2)Richard Lehan, “Urban Signs and Urban Literature: 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Process”, New Literary History, No.1, 1986, pp.99-113.。但它实际上想要抓取的却是在资本主义城市经验固有的离解性与人的情感经验固有的外部性之间所存在的姿态矩阵区。
关于资本城市如何“离解”(Disintegrate)其中的个体及其生活世界,我们在结合城市文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会提拉出从本雅明到列斐伏尔再到哈维分析此问题时的谱系。在具体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这也是城市如何走向“无人区”的过程。关于源于“外部”(Outside)的情感如何能够重新复原流失于城市的人之痕迹,我们会既以福柯的讨论为源点同时又不局限于福柯。(3)“外部”这一哲学概念存在着诸多变体,萨德的欲望、荷尔德林的诸神、尼采的力、巴塔耶的僭越、布朗肖的吸引力等,都是福柯思考这一外部时所罗列的哲学星座。当福柯陈述文学是一个通向外部的问题时,也隐秘地开启了外部即为与他物共在的“可能性”这一维度,而这一点实际也是后来南希思考的主体,即外展中的共-通-体的思想来源。以欧美城市文学为思考对象,本文前两节会分别讨论外部的缺失及其所表现出的症候,第三节则讨论外部如何复归的问题。参见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9页、第159页。简言之,城市文学一方面还原了资本城市作用于人的灾难性离解过程,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不断来临中的难以被离解的外部情感。表征这一离解与外部之关联的则是置身城市的人的姿态。由此,本文最终的论证思路则是:与外部失联的无情感城市,如何作用于人的姿态,而人的姿态又如何昭示源于外部的情感的复归,而在情感的复归中,城市又被复原了什么。
一、丧失:从经验的连续性到情感的连续性
在对英国当代小说的空间研究中,大卫·詹姆斯借助列斐伏尔的理论说道:“小说家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将我们与他们所描述的领域在情感上关联起来是因为文学的场景设置不仅只是传达‘仅有的物质空间,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人们在接触其地域的过程中形成的感知’。”(4)David James,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and the Artistry of Space: Style, Landscape, Perception,London: Continnum, 2008, p.1.作家不仅传达一种具身现象学(Embodiment Phenomenology)上人对城市的体验过程,也传达一种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上城市作用于人的精神影响。对资本主义城市经验(The Urban Experience)(5)正如哈维所言,“经验”一词有着诸多伪装(guises),但它却也为“不眠的分析者”(the restless analyst)提供了探寻城市真相的切口,换言之,城市经验为诱发性而非僵化性的境遇。参见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15.感受到的无常和不安,早在巴尔扎克和海涅的笔下就已出现,在爱伦·坡和波德莱尔那里则构成了其作品的内核,经过狄更斯,成为卡夫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与乔伊斯作品背后隐蔽的经验背景;直至当代,以一种幽灵性的萦绕,渗透在塞巴尔德、麦克尤恩、马丁·艾米斯、贝娄、品钦、罗斯等人涉及纳粹大屠杀的作品中。
作家在城市感受到的四分五裂,可以溯源到本雅明讨论波德莱尔与卡夫卡的城市体验时所折射出的“经验”问题。游荡在城市的波德莱尔,敏锐地察觉到人群所展示出的“梦幻般的一致性”,因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发达”,就在于那种在传送带上决定生产节奏的东西,已经衍化为城市人群的感知结构,一种已被作为感知形式的“震惊”经验被确立了起来(6)参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63页。;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城市,不仅意味着与自身分离,还意味着遭受分离带来的反冲,一种周而复始的不稳定闯入了人的存在中枢。在卡夫卡那里,这种大城市的体验又被置换为层层叠叠难以穷尽的办公建筑意象,行走其中的助手们仿佛“关节通了电”(7)Franz Kafka, The Castle, Anthea Bell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简言之,资本主义城市是一个传统经验分崩离析的场域(8)有别于资本技术塑造的转瞬即逝的城市经验,马尔库塞谈到,前技术世界是“人和自然尚未被作为什物和工具而组织起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山谷和森林、村庄和客栈、贵族和村夫、沙龙和庭院都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前技术文化的诗歌和散文所表现的节奏,是那些信步漫游或驾车逡巡的人的节奏,是那些有时间和雅兴去苦思、冥想、体验和讲述的人的节奏”。传统上持久坚固的人生经验,就诞生在这样的节奏里,而非新兴资本主义城市迫使个体分心的“发达”中。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5页。,而以城市作为构成人物存在所不可或缺的回音区的城市小说的出现,更加凸显了从卢卡奇到本雅明在分析小说时所说到的在生活和意义彼此分离时所产生的飘忽不定的预感意识。
个体在城市丧失的是何种意义上的经验,需要借鉴与小说的知觉方式不同的故事来说明。本雅明认为,缓缓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保藏以待漫长时间后再次苏醒,是因为故事的探针并非如小说那样毕其功于一役般的个人的心理内容。相反,故事关注人与人及人与世界间相互作用与引发,但却不会流于耗尽的神秘节奏(9)对此,约翰·伯格受本雅明的启发写道:“故事证明了可能性那总令人略吃一惊的广度。”参见约翰·伯格:《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故而,本真性的经验,不是可立即返现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在不使个体分心的有节奏的“外部”氛围中,源源不断地维系整体的伦理感觉。福柯用转瞬即逝但却连绵不绝的“间隔”,来表述吸引主体注意力的这一伸展中的外部思想。(10)当福柯在讨论布朗肖的“外部”时写道,它是一种“确定的吸引力本身的无目的的运动”,一种“等待的纯粹性”时,其中将外部作为一种卓越的“可能性”或不可征用的“空闲”提取出来的思想动力也越发显现出来。实际上,从尼采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在自己的周围有一个氛围,一个充满奥秘的气圈”,到德勒兹思考的生命是一种“微分的无意识”,“一个只能作为模糊之物的清楚之物(它越是模糊就越是清楚)”,可以看到,生命是一种分有“外部”的飘忽不定的离散状态,或者生命是一种形散神聚的本源性真相,是推动晚近哲学发展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引线。概而言之,外部揭示了生命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量化存在,是南希思考的坚不可摧的“有”。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0-362页。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页、第151-152页。Jean-Luc Nancy, The Birth to Presence, Brian Holmes and others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4.由外部所维系并滋养的这一经验,使人意识到自身就是一个与他物共存的经验共通体。
“经验是不可分的,它至少在一个甚至可能数个人生里延续……经验先我而行。”(11)伯格:《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然而,在城市文学中,丧失的经验“在个体之外实施”自身(12)Giorgio Agamben, 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and Experience, Liz Heron Trans, New York: Verso, 1993, p.14.。那从人的生命分裂和异化出去的事物,是通过震惊带来的创伤化事后性经验而宣告自身的。相对于从自然孕生并花费其漫长时间所精心培育的身体而言,工业革命后城市的发展对于人类而言,确如战场上的士兵被身边的炮火震慑的时段。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创伤即心理能量分配方式的失衡,也是强迫重复修复时总无功而返的事后性。分配方式与重复修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暗示了一种对一去不返的经验的哀悼。因此,贝克特的人物总遗留着某种灾难过后难以化解的失常感,而乔伊斯、伍尔夫的“城市”看起来就是努力地在复现某个城市的记忆行为,尽管时刻伴随有一种记忆短路现象。现代城市文学中的这一现象,说明了作家都意识到城市人物从背景里被剥离出来而再也无法落脚的存在处境。也是在这里,品钦1966年描述的遗嘱执行人俄迪帕,在看到纳索斯这个城市时,也才会有“一种刚刚溢出她理解限度的轻颤的启示录感觉”(13)Thomas Pynchon,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2, p.13.。因而回到本雅明,城市的这种创伤性经验早已大到了所有坚实的经验储备难以吸收和化解的程度。
在德布林1929年的作品中,刚从监狱出来又被迅即交送给城市的毕伯卡普夫,为何反常地把关禁他的监狱的红墙视作不可分离之物?(14)Alfred Döblin, Berlin Alexanderplatz, Michael Hofmann Tran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18, p.3.而到了罗斯1997年的作品,为了追寻女儿玛丽成为炸弹者以及家庭破碎的原因,作家为何又安排其坚如磐石的父亲利沃弗回忆起纽瓦克的城市发展史,乃至它所代表的整个坚不可摧的美利坚?列斐伏尔在分析城市“地带化”的两重构时认为,空间以分割的方式整合自身与以整合的方式分割自身实际一体两面;处身在城市的人群,在这种“离解性地整合”(Disintegrating Integration)(15)③Henri Lefebvre, Writings on Cities, 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p.144-145, p.143.进程中,时刻面临被抽空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空间的离解性整合,也依然是自波德莱尔以来资本主义传送带生产节奏的一种变相铺展,且早已与政治权力、商业效益捆绑在一起,并以一种均质化的方式,成为让个体、家庭以及共同体自行分解的都市的三位一体。因此,在城市“生活的个人化方面与超出单个个体的方面之间起促进作用的社会结构”(16)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Donald N. Levine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325.,实际就是以分裂的方式进行弥合的恶性循环。而就齐美尔的思路来看,个性面对超出它的这种城市力量所做的适应,并非自我意识的反抗,也不是弗洛伊德所言的防御刺激的过程;相反,它从疲于应付到精疲力竭,再从绝望崩溃到情感涣散,是一种长时间条件反射下的自我规训与无个性化进程。它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列斐伏尔认为的感官的整体性退化③,甚至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它也显示出一种强迫自身回到无机物的驱力意向。这样,随着感官机能的钝化,端赖于与他物共存的感觉活力,这种源自“外部”的情感意识,也就自然熄灭了,而由情感触发的伦理知觉,也进而处在崩解的进程中。
卡夫卡1926年的《城堡》中那个总让K感到挫败的环境,总使K面对既定的失败,那些难以觉察却麻醉K的影响(17)Franz Kafka, The Castle, Anthea Bell Tr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5.,在此可以看作以寓言化的方式对城市的这种有别于故事气氛的异己气氛所做的伟大预言。也由此,麦克尤恩在1992年的《黑犬》里甚至借助叙述者杰瑞米的观察,让丧失了经验连续性的城市卢布林与“事件”纳粹大屠杀间的一种徘徊不定的关系形式凸显了出来,这是一种物质与反物质的转化关系(18)Ian McEwan, Black Dogs, Canada: Vintage Canada, 1993, p.71.。经验的瓦解实际就是情感的瓦解,这就是为什么品钦会将俄迪帕置放进一个寸步难行的蜡像馆般的城市里。人们有的只是弗洛伊德所言的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的诡异情绪,而丧失了与周遭环境、人事物态自然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却又不会耗尽的共存性情感。因此,有待进一步追问的是,情感为何能够担保经验的连续性?
在本雅明的启示下,我们看到,主体之所以能够接纳故事中与他物共存的道德教训,并将其融进自己的生活进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缓缓道来的故事让主体觉知到他是与他物共通的心灵存在,而经验正是心灵在这一从容不迫的醒觉状态中分泌出的指引。更为关键的是,这一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扩散性经验,只有在无意识地调谐主体之注意力节奏的故事力场中产生(19)卡尔维诺曾在分析故事的力场或磁极时写道:“驱策欲望朝着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前进的动力,更多是由故事的节奏而不是由叙述的事件来表达的。”参见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33页。。借鉴本雅明与卡尔维诺的思考,我们可以说,好的故事节奏,施动并导引着主体的心灵速度,展露着主体不为人知的非知领域,揭示着主体实际是一种在分享外部事物的过程中诞生的多元性存在。这种引人入胜的节奏,全然有别于以离解的方式迫使主体分心并使之走向锁闭的传送带上的城市节奏。故事的这种连续不断的推力,最终促成的,实际就是本雅明思考故事时认为的无需理性解释的共通感。故事给出的是主体从未被孤立的共存性经验,而经验本质上说就是生命的一种灵活多变的连接能力(20)约翰·伯格写道,经验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于是,接近一个特定经验时刻的行为同时包括探究(近者)和连接(远者)的能力”。参见伯格:《讲故事的人》,翁海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因而,经验的连续性也就指的是一种与他物共在的连续性。这种并非表象关系的连续性,标画出了主体在存在中的秩序,即主体自为地呈现为一种与他物共存的半透明运动。它之所以不透明,是因为它是先于知识活动的情感性存在, “植物学家的植物不是田畔花丛, 地理学确定下来的河流 ‘发源处’不是‘幽谷源头’”(2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5页。对此还可以参考列斐伏尔对自然在城市中的“虚构存在”(fictive presence)的思考,也即城市被去自然化后的经验写照。See Henri Lefebvre, The Urban Revolution, Robert Bononno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p.27.。它之所以又透明,在于经验在认识论上的确定性是由情感知觉进行担保的,情感让客观性有血有肉了起来,让经验“共通”了起来(22)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情感让经验所具有的外部性“发”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之所以能承传,还在于经验是浸透在情感中的经验。作为主体的存在样式,情感是一种试图与外部建立联系的身心一体的活动,是将自身链接在一个超出自身之外的更大的存在链条中的无意识运动。没有与外部共在的情感的这种先行存在,我们只能静态性地知道事物,而无法动态性地领会事物。与他物共存的这种经验的连续性,在本源上是情感的连续性,情感的连续性担保着与他者共存的伦理的连续性,而伦理的这一连续性,则担保着不会被城市离解以至无地可依的人。
然而,从爱伦·坡到麦尔维尔再到卡夫卡等早期城市文学就已显出的征象来看,城市“无人区”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城市在不断离解通向外部的情感注意力,这一事实尤其随着速度的提举而日益加剧。维利里奥与罗萨都注意到加速城市给个体带来的“注意力裂解”的问题。(23)维利里奥的思考自始至终贯穿着加速如何导致“没有注视的视觉”这一考察。参见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孟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7页。罗萨分析的城市加速让主体处在时间匆匆流过但又力不从心的焦虑状态,也加剧了注意力瓦解的过程。参见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55-173页。也就是说,城市离解个体的速度越快,个体趋向熟视无睹的“非参与”性分裂人格则愈加严重。这一丧失外部注意力的情感异化,及其所带来的生命力枯竭的现象,所导致的就是舍勒认为的不由自主且漫无目的的“怨恨”(24)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在分心中愈益加剧的这种无力感,正是与他物共在的注意力断裂,也即罗萨思考的“去同时性”(Desynchronisation)出现的结果。缺失了外部的情感在变得反复无常,而由情感所维系的来自外部的他者则无地可依。与外部的失联,或者生命被去同时性后的孤立状态,在欧美城市文学中往往就与一种身体性的病理学关联了起来。
二、征兆:从病理化到无法预料的姿态现象
城市文学中经验的丧失,源自通向外部的情感的丧失,但作家又该如何在变幻莫测的城市中呈现这一症候,情感之血肉应该落靠在怎样的骨架上才能显其轮廓?城市文学发端之际即这一问题揭露之时。坡人群中躁动不安的老人,波德莱尔被惊吓的小老太婆,卡夫卡身体形态总不合时宜的助手,城市文学面对情感丧失这一无法挽回的事实,往往借助的是城市人物身体姿态的变形;某种扭变正在城市中发生,而经受这种扭变的是人的肉身。本雅明认为:“情感的丧失,以及作为身体中这些情感源头的生命之潮的退却,将会拉大自我与周遭世界间的距离以至出现身体的异化……在这种病理学状态概念中,最为简单的客体因为和我们缺少了任何自然的、创造的联系,看起来成为了一些谜一样智慧的象征。”(25)Walter Benjamin,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John Osborne Trans, London: Verso, 1998, p.140.这种自然联系即本雅明借瓦莱里所言的心、眼、手的相谐姿态。然而,在城市生活,心、眼、手不仅以分离的方式四分五裂,还会以整合的方式相互同化,两者都是对情感连续性的误认与抑制,其症候性如本雅明所言就是城市文学中身体姿态的病理化现象。
这种在城市中身体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我自己又不知该如何行动的感觉经验,这种挤压着个体的两难,在欧·亨利1908年《城市的声音》“使圆成方”中有着准确无误的再现。欧·亨利讲述了住在坎伯兰山岭的山姆,为了复仇来到城市,但在城市对其一系列的左冲右撞后最终与其敌手握手相和的故事。城市迫使山姆缴械投降的过程,在欧·亨利看来实际是城市的数理空间化进程对生命空间的整饬。空间的数理化对人的扭变有三个维度。一是将人整齐有序封闭快速地安放进以几何直线为特征的交通与建筑的物质现实中,让个体任由一种外在于自身的巨大之物所统摄。二是难以计数又令人猝不及防的直角性转折和密集的依靠暂停与启动运行的诸多城市机关带有一种听口令、齐步走的节奏,借用福柯的思考,这种已经内化进身体姿态中的直角感知方式,借助不断的别出心裁,要求人群遗忘自身并回落到现实中(26)Michel Foucault, History of Madness, Jonathan Murphy and Jean Khalfa Tra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20.,没有了真实意义上的“经过”(27)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97.。简言之,连续不断的直线化意味着齐平化,意味着让生命“发生”的外部性弧度的消失。三是当前两者达到压力阀的顶点,当可有可无感演变为患得患失(28)哈维使用“意识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onsciousness)来分析与描述这种使人“束手无策”和“坐以待毙”的城市经验。See David Harvey,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5, p.276; 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Eleonore Kofman and Elizabeth Lebas Tra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145.,在动荡不安且彼此失去联系的人群中,守住自身的自我,就会逆向发展出一种潜在的无差别反人类倾向。这也是艾米斯在1991年的《时间箭》中呈现一个混迹于城市人群的纳粹党卫军的逃亡心理的隐含之意。当个体无法安分守己地居于前两者,也不能恣睢无忌地施展后者时,那隐而未发的未与外部接通的“残留”,就会以病理化的姿态显露出自身。
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尔维尔1853年的抄写员巴特尔比就是一部情感上“未完成的”城市姿态启示录。虽能每日都毫无偏差地从紊乱的华尔街按时走进工作的办公室,雇员“火鸡”和“镊子”却又间歇性地在每天工作的不同时段,出现姿态失调的怪异现象。从华尔街走向办公室的雇员,虽遭受了城市施加于其身的一系列扭变,却又接着遭遇了办公室也只是城市的内部化这一现实:夜晚的华尔街空无一人,并不说明白日的办公室生命涌动。无声的办公中无法抑制的自我生长在萌发,嘈杂的街道人群中不可遏制的空无一物在扩大,两者相持不下,使得城市文学中的“反刍”性姿态有增无减。巴特尔比就停留于这一区间,一同停留于此的还有那个试图保持城市原状的诉讼代理人。城市这个无所不在的力场,贯穿了所有的内外之界限。看似充满活力的城市,维系自身的东西恰是使姿态丧失的东西。这一考察再次确认了本雅明的洞见——姿态之所以病理化,是因为有一种无法被城市力场的网格所捕获的飘忽不定的残留物,这一应得到“恰逢其时”地安放的外部情感,是巴特尔比感到的“可能之物的寂静之力”(29)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0.,也是他决定停止被城市“抄写”的缘由。
姿态的病理化现象甚至已经延伸到动物园这一隶属于城市地理却不隶属于城市文明的场所,而其中动物们的姿态令人吃惊地有着人的神态。塞巴尔德2001年《奥斯特利茨》中那只在火车站附近被城市颠倒了日夜,反复洗着同一处苹果的浣熊的半人状态,真实地确证了居伊·德波在分析城市时所说的“一种自发性的显现中的分离力量”(30)⑥Guy Debord, The Society of Spectacle,Ken Knabb Trans, Berkeley: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2014, p.9, p.11.,如何最终演变为惰性景观的实质。对于仿佛身处城市水族馆的奥斯特利茨而言,火车站作为微观的城市力场即为一个通过驶向别处去形成自我的始发地意象,也是一个不知会驶向何处却又预感会通向危机的终点站意象;叙述者甚至感到在候车大厅里的旅客与夜间动物园里的动物姿态相差无几,他们与它们仿佛都是某一场浩劫之后的幸存者,也同时因为共同经历过浩劫,人与动物走向了趋同,都呈现出一种因不知名的创伤而遗留下的姿态性症状。在这些不知做何反应的延迟性姿态中,失落的是自然行为的自发性。也是根据这一考察,我们才能理解本雅明为何会在分析波德莱尔时说道,人群的行为模式实际是对“惊颤”的反应,因为“惊颤”是被分离的外部之物总会返回,并作用于姿态的病理化结果;也更能明晓本雅明将卡夫卡的体验与公众濒临大规模灭绝时的体验并置起来的原因,因为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个体的姿态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向他再现动作的另一个人的姿态”⑥。
作为微观城市的火车站,起点成了终点,形成姿态的过程也是丧失姿态的过程。克拉里认为:“正当技术文化内的专注知觉持续不断地获得自动化形式的历史时刻,被认定为‘自动’的人类行为模式却被判定为具有病理性和社会危险性……其中‘心智器官’的最高活动出现缺失……包括‘记忆、情感、推理和自主行为’。”(31)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1, pp.147-148.姿态的丧失与城市日渐从人工化到半军事化的演变不无关系,火车正是技术城市无所不在的自动化缩影。只有在此城市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我们才能领会从波德莱尔对会分身的老人的震惊,到奥斯特利茨对城市的预感之间,时有显露的惴惴不安,也再次看到了麦尔维尔笔下雇员的病理性姿态具有的预言效果,以及为何在品钦与罗斯的作品中城市总有一种“感染”性的原因,后者在《美国牧歌》中有一段利沃弗童年随父亲经过兴起中的城市时体验到的眩晕,“有一种被它拥抱和报之以拥抱它的欲求”(32)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p.220.。
病理化的姿态现象既说明了外部性情感无处安放这一事实,也说明了随着外部性情感的降解,姿态本身会越发丧失控制力的普遍境遇,乃至最终出现“姿态的疏离”(33)④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3,p.53.这种不可控事件。坡笔下那个漫无目的的老人为何带着一把看似无用的短剑,波德莱尔为何总在人群中看到撒旦的踪迹,拉斯克尔尼科夫为何又奇怪地杀死他人,一直到麦克尤恩、艾米斯以及贝娄、罗斯与德里罗的城市小说?阿甘本说道:“对于已经完全丧失自然感知的人类而言,每一单个姿态都成为了一种命数。越多的姿态愈是在不可见权力的施为下丧失其安然,越多的生命则愈是变得不可辨明。”(34)④Giorgio Agamben,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Daniel Heller-Roazen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3,p.53.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出版的《地下室手记》中在涅瓦大街上的叙述者,就为我们展现了在城市中姿态的这种矩阵过程。了无方向而经常游荡于城市的叙述者,因挡了一位军官的道,竟被后者目中无人地挪开,直到多年后叙述者走上涅瓦大街这个城市力场的中心,试图通过坚决不给军官让路的姿态来完成他的复仇计划。事情因为涅瓦大街而进入了更深一层的进退两难:涅瓦大街是城市暴露不同身份之人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收拢所有目光的集结处,这是一处动静难分的区域,是城市力场不同的小漩涡。要么是维持住那永远无法填平的与军官之间仅有的两俄寸距离,要么是不可节制地突然出击,叙述者的姿态无法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能够恰到好处地擦肩而过,而是处在时刻将要四分五裂难以预料的可能性中。(35)See Robert Park,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in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Richard Sennett Ed., New York: Meredith Corporation, 1969, p.126. 此外,列斐伏尔与哈维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如何将地理空间物化为商品从而远离自然、并进而使人与周遭环境发生“争斗”的过程,指出了其中隐藏的必然风险。
作为城市中心的涅瓦大街是加速事件升级的区域,仿佛有一种复魅在那里发生,它成了既吸引又排斥叙述者这只飞蛾的“火焰”,一种在让与不让之间难解难分的距离的冒险:物理上,两俄寸的距离可随时填平;情感上,两俄寸的距离则是一段会自身无限延长的两俄寸。即使如同叙述者那样难以预料地与军官撞到一起,这一距离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越加赤裸地向叙述者投去了它的鬼脸。仿佛被套上了一副看不见的舒适的枷锁,姿态在寸步难行与横冲直撞间裂变着。这一点一直延续到《美国牧歌》中总要确保“万无一失”的运动明星利沃弗的人生故事。他那被定格在叙述者冉克曼心中即使陷于敌方多人包夹而依旧从容不迫的美国田园姿态,很难说没有被他亲眼目睹的纽瓦克撞碎。纽瓦克只是美国城市的一个缩影,人们如同那些在纽瓦克街道上以极快速度不断转圈的盗车贼,其盗车的目的只是为了玩转圈游戏而从不顾及撞死了谁。在这一距离的冒险中,冒险者与犯罪者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
“将威胁性的未来转化为已实现的‘当下’”(36)Walter Benjamin,One-Way Street, Edmund Jephcott Trans,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88.,是城市文学为何频繁周转于情感与姿态的关系形式中的原因,因为确如卡夫卡所言:“作家的任务是把孤立的非永生的东西导入无限的生活,把偶然导入规律。他要完成的是预言性任务。”(37)卡夫卡:《卡夫卡谈话录》,赵登荣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第57页。与外部连通的情感愈是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抑制,身体的姿态则愈是难以预料。索尔·贝娄后现代作品中被城市力场左右的赫索格,为何也如同早期现代作品《地下室手记》里的叙述者写了许多信件而没有发出,这种引而不发的窘迫与赫索格最终要拿起手枪之间,依然是那无法回避的“两俄寸”距离。距离的冒险在此应该被颠倒过来,不再是去填平这一距离,而是把距离从难以预料的欲望假象中解救出来,让其展露出真理所固有的难以被穷尽的外部性。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将要接下来在城市文学中考察的问题。
三、复归:从彼此疏离到作为共-显的情感
根据此前本雅明的启示,情感的血肉终要回落到姿态这一骨架上。在早期现代城市文学中,坡在广场上绕圈子的老人为何要以“绕圈子”的方式回到起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者为何又围绕着神秘莫测的“两俄寸”,K为何围绕着城堡但却无法进入城堡?而在后现代城市文学中,奥斯特利茨为何围绕着城市建筑史,品钦的俄迪帕为何又围绕着城市“地下邮政系统”?实质上,出现在城市文学中的这一带有普遍预兆的姿态,是欧·亨利“使方成圆”的东西。情感的外部连续性的丧失,反过来是姿态的强迫性重复,失落的不是将情感与姿态弥合起来的中间项,也不是不可控事件的出现,而是“被昭示的事物未能实现的征兆”,因为本雅明继续说道:“每种消极都有其价值,它是勾勒生机和积极的因素的背景”(38)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
在城市力场的距离冒险中,姿态与情感彼此分离,各行其是,以至最终出现了从病理化的姿态向难以预料的姿态衍化的过程。然而也是在这一分裂的间隙,文学让一种无法被分离的东西显露了出来,从而复原了真实的距离。因为感到被妻子与情夫所骗,贝娄笔下的赫索格糊里糊涂地到了芝加哥,似是而非地拿起手枪,至于是否真的要杀死前妻马德琳与情夫格斯贝奇从而夺回女儿琼妮,赫索格的姿态依旧仿佛被扣押在了传送带上而左右为难。贝娄在处理赫索格这一神志不清的心理境遇时,是借助公路这一城市力场的微观意象展开的。其巧妙的地方在于,公路既能为赫索格急于杀死前妻与情夫进而救回女儿提供一种乌托邦般的心理能量,也能为赫索格必须学会自制从而减慢车速确立一种法条式威慑。城市公路所引发的心理矩阵,也说明贝娄为何削减叙事情节,且采用大量的心灵私语来呈现赫索格。因为对一个久居城市的匿名者而言,在离解性的整合中是没有人生故事的,有的只是凌乱不堪的独白。也因此,读者会看到,被城市力场不断分层的赫索格,又是一个不断寻找联系的人,他要杀死格斯贝奇的原因,竟然是格斯贝奇“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片碎片,一片从群众中碎裂下来的碎片而已”(39)⑤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第300页。。因此,在既想加速又要减速的城市公路上,作者描述道:“他身上的生命之弦拉得紧紧的,它在疯狂地颤抖。”(40)⑤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05页,第300页。
在终于来到他曾与马德琳和女儿共同居住的地方后,当他时刻绷紧的弦成为时刻瞄准的手枪时,赫索格却看到格斯贝奇正为浴盆里有着闪亮小身体的女儿洗澡,想要瞄准的对象在格斯贝奇细心地为女儿洗澡的姿态中滑落了。这一姿态是试图与即将铸成大错的赫索格沟通的“外部”。这种沟通是通过解除赫索格的自我,把他从欲望的假象中解救出来,并置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的情感过程。为女儿洗澡的姿态,在赫索格心里引发的转折,实际上就是南希所说的“共通体的分享”。这一“让我们每个人都被展露给对我们自身来说的我们之所是的外部”(41)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8页。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本翻译共-显时所用的连字符“-”,仿效了Com-pearance的英文翻译。连字符的使用,是为了更准确地传达南希思考的既非为主体也非为客体所占据的不断位移的“位置”之含义。,使得赫索格“让”出位置。格斯贝奇,女儿以及赫索格三者之间,被这一姿态“间隔起来,这种分享使他们成为他者:彼此相依”(42)③④⑥⑦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79页,第68页,第76页,第66页。,并进而临近到不能被城市力场捕获的“在他者面前并与他者一起不间断发生共-显的边缘位置”(43)③④⑥⑦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79页,第68页,第76页,第66页。。诚如南希所言,“共-显属于更为本原的层次。它并不自我创立,并不自我安置,它并不出现于已经被给予的主体(对象)中间。它包括这样的之间(entre)的问世:你和我(我们之间)——在这个结构式里的‘和’并没有并列之义,而是外展之义。”(44)③④⑥⑦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79页,第68页,第76页,第66页。简言之,本被城市力场左右且即将出现无法预料的姿态的赫索格,被格斯贝奇为女儿洗澡的姿态外展为共-通-体。
时隔三十多年,赫索格对城市的不解,也转移到了《美国牧歌》中那个用炸弹炸死四个人的利沃弗的女儿身上。正如赫索格离开格斯贝奇与女儿之后重新感觉到的那样,在城市芝加哥,他如同那些中西部的街道一样再次陷入了一种“缺乏焦点”的心灵危机,用他的话说是“缺乏一种形成力量”(45)索尔·贝娄:《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同样,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说“寂寞”这个词语且开始结巴的玛丽,后来却只有在制作炸弹的时候才能集中心神,言语流畅。罗斯在让叙述者冉克曼试图重构这一悲剧事件的过程中,将玛丽的成长与利沃弗继承其父亲的手套计件工厂的历史并置在一起,而后者又是整个纽瓦克城市发展史的缩影。手套越是精确计算、越是称手,玛丽的结巴就越严重。手套中隐藏的宽度越是分毫不差,玛丽制作炸弹时的专注力就越是难以动摇。这种安排不是意在建立一种明确可靠的因果关联,而是在玛丽的成长与城市的发展“之间”,让一种飘忽不定的预兆性关系自为地显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利沃弗殚精竭虑要去保全一切的“伟大姿态”,即马克斯·韦伯所分析的含有神学伦理意味的资本主义“天职”的背面,实际上就是竭尽全力把一双小小的手套宽度的误差减至毫厘的姿态。一双制作精良的手套反过来却成为束缚双手乃至制作炸弹的双手。利沃弗的这一姿态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可控事物,成为寓言意义上真正的美国炸弹。
离解性整合进程中的城市越是不可阻挡地发展下去,失控的东西也就会越发不可阻挡地骤然出现,当朋友向利沃弗讲述炸药公司与采矿和铁路的关联时,暗示的也是源于炸弹又结束于炸弹的城市姿态所隐含的恶性循环。如同炸弹的离解性,城市是要炸开阻挡物进而占据被炸后留出的空间,然而直到冉克曼叙述的结尾,女儿玛丽这片哑口的空间,这一如秘密一般的“外部”,依然没有被炸开。相反的是,一如巴特尔比,女儿的哑口到甚至成为耆那教信奉者后不与水接触的整个削减自我的姿态,却是让出空间的寓言性姿态。在这一悲剧性过程中,作为真正意义上无法被炸除的外部,却使得玛丽结巴的心灵冰期出现消融,且自为地流动了起来。原本废弃于城市边缘的幽闭狭小的房间对利沃弗而言,竟也流动着一种恐怖的既难以觉察又无法被占有的崇高。玛丽是让城市力场丧失功效的安提戈涅,而如赫拉克勒斯一般要守住城市的利沃弗,却在错位中“受难”。受难是因为“存在从来都不是单独的我,而总是我和我的同类”(46)③④⑥⑦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79页,第68页,第76页,第66页。,我被我的同类带向界限。利沃弗被玛丽外展为共-通-体的这一“共-显”,正是对无地可依的城市的质询。南希所言的这种“错位和质询,即把自己揭示为在-共通-之中-存在的构成要素”(47)③④⑥⑦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79页,第68页,第76页,第66页。,不仅说明了玛丽后来的姿态已是接通外部的情感,而且也说明了情感的外部性,就是重新匡正“我们是同类”这一无法撼动的姿态。
本雅明认为,如画家克利一样,“卡夫卡生活在一个有待补充的世界。”(48)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 1935—1938,Jephcott, et al. Trans, W. Jennings, et al. Ed,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26.因为两者的作品都显示出孤孑和无处可去的征兆。从巴特尔比到玛丽,为了补充城市造成的这种无人状态,他们悲剧性地都以一种带有自我惩罚性质的“让出”做出应答。在城市文学中,姿态的扭变会有向外部辐射的不可控事物的出现,但与此同时,正如从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到巴特尔比与玛丽,一种向内转的自我暂停的倾向,却在牵制着这种不可控事物的出现。这一倾向到了新千年唐·德里罗的《大都会》形成了一种贯穿始终的谱系现象。将整个世界经济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埃瑞克·帕克,乘坐既防暴又防音的加长版豪华白色轿车穿越市区,但这一看似铜墙铁壁的“穿越”,随着时代广场上一个人的自焚而出现拐点。自焚事件发生后留下了一种难以命名的事后性,所有人仿佛都被这一事件传染,被裹入一种神秘莫测的共-通的停顿,埃瑞克感到,“市场并非全部。市场不能拥有这个自焚者,也不能吸纳他的行为。”(49)Don DeLillo, Cosmopolis, London: Scribner, 2003, p.42.埃瑞克仿佛被唤醒了,随后他的姿态急转直下,直到最终宁愿被他解雇的雇员理查德·施茨杀死。表面上看是埃瑞克急转直下的姿态,实际上却是让某种事物“浮现”的姿态,即通过悲剧性地摧毁他这只藏在轿车里的市场无形之手,而为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他者让出位置。这种力图要自己消失的姿态,实际就是让难以被城市离解的大于自身的外部出场的姿态,诚如福柯所言,“一个人如何被吸引恰恰就是他如何被忽视”(50)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9页,第163页。。这是一种总让埃瑞克失眠,并且总以一种共-显的方式而到时的情感(51)正如南希的分析,小说中埃瑞克的这种难以说清的“知道”“必须以独一性的情感的联系,以‘同类’的检验为前提”。参见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9页。,是真正引他飞蛾扑火的原因。
原初意义上的城市“不是一块属地,而是形成绽出的非实在场域,正如绽出的形式反过来是共通体的形式”(52)⑨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7页,第171页。。南希翻转了海德格尔,“绽出”即如坐针毡。因此,这样一个总在移位中的异城市,就是一个先会哀悼的城市,如弗洛伊德试图从毁灭的庞贝古城,复原格拉迪瓦的步态那样,而不是一个试图将死亡隔离公众世界患了洁癖的城市(53)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Steven Rendall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94.。只有先会哀悼,才会有德里达意义上的“好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欧·亨利《使圆成方》中冰释前嫌的结尾,即山姆之所以有与敌手握手言和的姿态,实际就是被昭示的外部事物,要“实现”自身的意愿(54)See Jacques Derrida,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George Collins Trans, London: Verso, 1997, p.128.,也即情感的血肉终要回落到姿态上这一“使方成圆”的共-显过程。被昭示事物的实现,并不是要去完成一个姿态,仿佛这个姿态在被完成的一刻就耗尽了自身,相反,姿态总处在未完成中,总有一种外部性情感牵引且施演着它,在拥抱中,我拥抱的是多出我的事物;这一总也无法完结的姿态,让一种谁也无法占有的“共存性”情感绽露出来。进一步言之,源于外部的情感已是分享和沟通,“只有因其不能占据最高位置时才会被称为情感”(55)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John Osborne Trans, London: Verso, 1998, p.139.,所以,情感总以退却的方式而让出一片无法被征用的共存性空地。欧美城市文学所表征出的这一源于外部的普遍性潜在姿态,是要把流离失所的人重新扶正的无所不在的情感。如同波德莱尔所认知的“太阳”,它是扶起一切但自身不被扶起的外部。城市文学延续了自波德莱尔以来的这一使命,而波德莱尔的诗作因源于无处可去的城市,就更加深了南希所言的文学的“共产主义”所意指的东西,即“位置的共享”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