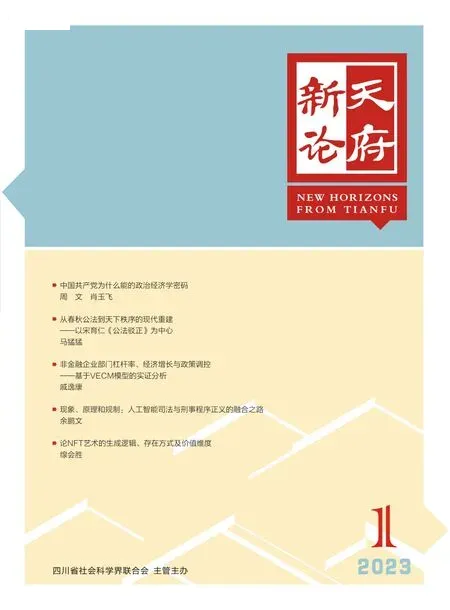论柄谷行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徐晓玲
在学术界,日本马克思主义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理论背景,其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试图通过经典文本的再阐释,还原马克思的“整体像” “原像”,以解决日本所特有的问题,譬如日本为什么存在“天皇制法西斯”(1)丘琦欣、休斯顿·斯莫尔、禚明亮等:《“日本马克思主义”、新左翼运动和历史的辩证法——柄谷行人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4期。。作为当代日本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柄谷行人,在其知名著作《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 《跨越式批判》 《世界史的构造》等文本中,一直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底本,试图勾画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葛兰西等人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柄谷行人认为,日本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日本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基于经济决定论主张推翻帝制是荒谬的,因此他拒绝了此一路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过度强调上层建筑自主性而忽视经济基础地位的倾向,则违背了柄谷行人基于经济学视角研究的旨趣。然而,柄谷行人回到经济基础的研究,不是从马克思经典的生产方式视角而是从交换方式开始的,他透过康德阅读马克思,提出激进的政治纲领,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康德的“目的王国”是一致的,因而“其理论也在西方激进左派这一理论谱系中”(2)王庆丰:《剩余价值理论新释——马克思〈资本论〉的柄谷行人解读》,《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4期。。那么,他是怎样用交换替代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又是如何借助这一概念抵抗资本主义并迈向共产主义呢?回到柄谷行人的文本,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柄谷行人的激进政治理念。
一、从生产到交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曾经分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差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3)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页,第62页。在这里,价值形式被提到核心位置。沿着这一思路,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扎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土壤的新马克思阅读学派。柄谷行人借助宇野弘藏这一中介接续价值形式理论研究并使之激进化,则是又一经典。在柄谷行人看来,引起马克思注意的问题乃是“货币所具有的力量”(4)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0页,第61页。,但是这一点却被斯密与李嘉图给遗忘了,古典经济学家仅仅将货币当作不言自明的前提。对于古典派来讲,货币没有任何秘密,因为货币只是各种商品所具有的劳动价值的表现而已。例如,亚当·斯密认为,商品中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乃是购买其他商品的“力量”。这意味着,每个商品分别也是货币。因而他们嘲笑了特别重视金银货币的重商主义者和重金主义者。
那么,柄谷行人为什么重视价值形式?在柄谷行人看来,人们习惯于从事后的角度来投射商品所具有的价值,但“货币”也只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人们对“货币”这种人的行为的结果的迷恋,忽视了价值为什么表现为货币这一历史过程,这是错误的,因而需要追溯到价值形式的解决路径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5)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页,第62页。。具体来说,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关注源于贝利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说的批判。李嘉图认为,商品中隐含着交换价值,货币则是表现这种交换价值的东西,而这种交换价值是根据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贝利却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存在于与其他商品的关系中,因此,内在于商品的劳动价值乃是幻象。马克思既批判了李嘉图也批判了贝利。依据柄谷行人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他认为,并不存在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古典派站在事后立场思考的。事后性思考的古典派将交换后商品看起来具有的某种价值投射到事前,认为商品早就存在交换价值。譬如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所以,对斯密等古典派来说,既然商品在无形中都被视为货币,那么货币就并不重要,结果抹杀了货币的重要性。因而,对商品的审视必须推进到“事前”。这个时候,商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没有保证,需要看商品有没有实现“惊险一跃”,若商品没有卖出去,不管花费多少劳动都没有价值,甚至连使用价值也没有,只能单纯地废弃掉。由此,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价值形式解决了商品的“价值”难题,一个商品只有被其他商品交换才可能有其价值。(6)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53-158页。换言之,在“价值形态”中才能产生价值。(7)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0页,第61页。
对价值形式的追问,一方面是对货币谜一般特征的“事前”考察。柄谷行人指出:“《资本论》以前的马克思不管怎样具有批判性,我们必须说他依然是在李嘉图的思考范围的。阿尔都塞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存在着一个马克思认识论上的断裂,如果要强调这种断裂存在的话,那也应该是从《导言》到《资本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决定性的‘断裂’,这便是价值形态论。”(8)⑦⑧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 157 页,第253页,第18页。这就是说,不应该以事后言说商品,而要通过事前对商品的思考探寻被隐蔽了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在柄谷行人眼中价值形式是如何展开的。在柄谷行人看来,首先,在简单价值形式上,商品A(相对价值形式)=商品B(等价形式)。商品A的价值表现为商品B的使用价值。此时,商品A是相对价值形式,商品B是等价形式。譬如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等式意味着,20码麻布只有等同于1件上衣后,即与上衣交换时,20码麻布的价值才得以表现出来。而由于上衣处于等价形式上,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交换。等价形式使1件上衣仿佛自身内在着交换价值似的。(9)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第112页,第112页。“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10)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第112页,第112页。。当然,在柄谷行人看来,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商品A与商品B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因为20码麻布也可以处于等价形式上。也即是说,如果观察交换方式的角度不同,所处的位置也就不同。麻布的所有者在交换麻布和上衣时,如果认为是用麻布买了上衣,那么麻布就是等价物。同样,如果上衣的所有者认为自己是用上衣买了麻布,那么上衣就有等价物的可能。其次是“总和的价值形式”。在总和的价值形式中,麻布可以和上衣以外的很多物品交换,但是,这仍然不能决定麻布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上。麻布获得决定地位是在“一般价值形式”的时候。如1件上衣,或者10磅茶叶,或者40磅咖啡=20码麻布。这时,麻布成了一般等价物,才具有了购买力(直接交换的可能性)。而麻布成了一般等价物也就排除了其他物占据等价物位置的可能性。最后是“货币形式”。在货币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位置的只有金银,其他一切物都只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位置上。“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11)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第112页,第112页。柄谷行人再次强调,马克思认为某一物如金成为货币,并不在于金这一物质的性质。金之所以为货币,在于它被置于了一般等价形式上。
对价值形式的追问,另一方面是重新对交换(流通)(12)关于流通和交换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本文中流通与交换在一定意义上相同,即流通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的关照。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肯定了柄谷行人将价值的起源从生产追溯到交换(流通)的“视差”观方面的突破,认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全都丧失了这个“视差”视角,退化到这样的境地:重视生产的地位,排斥交换领域:“正如柄谷行人强调的那样,从青年卢卡奇到阿多诺再到詹明信,这些专门研究物化、商品拜物教的学识渊博的理论家们,全都落入了这个陷阱。”(13)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页。于是,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追问可以视为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流通)领域进行的资本主义分析,“使《资本论》与古典派经济学区别开来的,就是对使用价值以及流通领域的重视。这反映在价值形态论上。”(14)⑦⑧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 157 页,第253页,第18页。这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将马克思经典的生产视角转化为交换(流通)视角,这其实也是柄谷行人阐述其激进政治理念的开端。不过,我们只需要转换一下叙述方式便能够明白。柄谷行人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确是一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但这种思考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阶级关系(资本家和劳动者)作为领主和奴隶的关系之变形来看待。于是,出现了以“主奴辩证法”推导出无产者必将打倒资本主义的逻辑,并认为劳动者一向难以站起来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意识被商品经济“物化”,因此,促使他们觉醒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物化现象来自文化霸权的操作和消费社会的诱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批判工作的焦点应转向“文化批判”,揭示意识形态机制。柄谷行人认为,“既然根本的前提存在谬误,这种批判也不会有结果的”(15)⑦⑧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 157 页,第253页,第18页。,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回到《资本论》中价值形式的逻辑。柄谷行人认为,事实上,价值形式是一个非对称关系,正如上文所揭示的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所具有的力量是因为其处于一般等价形式上,而其他所有物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地位上,因而两端的关系并不对称。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这种非对称性更加突出,一方是劳动力商品(雇佣工人),另一方是货币所有者(资本家)。他们之间的商品交换虽然依据的是协议,却带来了阶级关系。因此,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将其追溯到使其成为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形式。然而,资本的剩余价值通过总体的雇佣劳动者自己买回自己所生产的物品才能实现。柄谷行人将叙述转到流通领域,就是说,在流通领域,资本是站在“卖的立场”,而雇佣劳动者是站在“买的立场”,资本想要把雇佣劳动者生产的物品卖出去,就必须从属于买家(雇佣劳动者)的意志。在此,存在着不同于黑格尔所谓“主人与奴隶辩证法”之辩证法。依柄谷行人之见,传统的劳工运动走向保守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因为它依据的依然只是从生产过程抵抗的逻辑,但是,使劳动者在生产岗位上获得主体性总体来说是困难的。(16)②⑤⑦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第256页,第19页,第194页。由于资本是在流通中实现剩余价值,流通过程也是劳动者有契机让资本从属于其立场的唯一场域,所以,“正是在流通过程中可以发现劳动者对抗资本的根据地”(17)②⑤⑦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第256页,第19页,第194页。。
二、在流通中发现资本停止的契机:阶级斗争新空间
进入丰裕的消费社会,我们能够感受到周围的生活世界被“景观”包围,整个生活都被“景观”统治、规训着。居伊·德波说:“景观就是这个时刻,这时的商品已经成功地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18)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页。让·鲍德里亚也指出,我们自己造出来的物不仅不能为人服务,倒“反过来包围人、围困人”,他甚至断言“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19)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显然,进入丰裕社会前后的统治类型都是商品对人的统治。不过,让·鲍德里亚的兴趣点在于消费社会对主体性的消解,他没有深入到以“交换”来构建起政治学的可能性维度。与之不同,柄谷行人在《资本论》中看到了劳动者作为唯一主体出现的契机。
现在让我们来进一步看柄谷行人是如何在流通领域将主体凸显出来并激进化的。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资本家在生产领域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从而,革命便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抗,譬如英国宪章运动等劳工运动,这里的斗争可以使资本的积累运动停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由于劳动者的意识被商品经济“物化”,这种对抗的消解将依靠“外部灌输”以激活劳动者的革命意识,或者在生产领域进行罢工以达到抵抗资本主义的目的。但这些抵抗基本上都失败了。对此,柄谷行人的设想是另外一条思路。他认为,《资本论》并不是从生产过程开始,而是从交换过程开始的:“如果资本主义经济根本上在于流通过程,那么,与之对抗的运动也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实行。”(20)②⑤⑦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第256页,第19页,第194页。首先,在柄谷行人看来,剩余价值发生的场所不在生产领域而是在流通领域。在资本的一般公式G—W—G′中,马克思指出了剩余价值的二律背反:它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柄谷行人通过引入复数的价值体系消解了这个矛盾,即当交换发生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的时候,货币就会在不同体系之间的交换中转化为得到剩余价值的资本。(22)②⑤⑦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第256页,第19页,第194页。也就是说,同样的商品如果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流通的话,其均衡价格就不同了。剩余价值由此产生。故而货币可以转化为资本。比如商人资本的剩余价值是通过商品在不同空间的价值体系中流通产生的价格差异而获取,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则依靠技术革新在时间上创造的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流通获取。其次,抵抗的契机来自交换领域。柄谷行人认为,在流通领域,资本存在两个危险环节:一个是购买劳动力商品阶段,另一个是向劳动者出卖产品阶段。如果这两个环节中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成功,那么资本运动G—W—G′就失败了,便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前一个环节的抵抗是奈格里所说的“不劳动”,即不出卖资本主义之下的雇佣劳动,后一个环节的抵抗是“不买资本主义生产物”。为了使“不劳动”和“不买”成为可能,就必须同时确保接受劳动和购买的场域,这便是生产—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与靠资本和国家所控制的组织根本不同,它们虽然相互协作,却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在资本主义中培育合作社,为了合作社的联合得以扩大,还需要替代通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支付决算体系和筹措资金体系。最后,抵抗的主体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一方面,在柄谷行人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被卖出的过程中,即“消费”场域,存在劳动者作为唯一主体,这也是劳动者持有货币而得以站到“买入的立场”上的唯一场域。在这一场域,资本从属于劳动者的意志。“在此存在着劳动者作为唯一主体而出现的结构论上的场域。这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产出的生产物被出卖的场域,即‘消费’的场域。”(23)②③④⑤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第257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6页。另一方面,柄谷行人是从总体上看劳动者购买了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不是说个别劳动者买回自己生产的那个东西。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获得不是站在个别资本的角度上来思考,而是站在社会总资本的角度上来考虑。也就是说,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如果商品最终不能实现其价值即没有卖出去,也就不能获得其剩余价值。而购买这些商品的人乃是受其他资本剥削的劳动者。从社会总资本角度来看,消费者正是劳动者。因此,柄谷行人认为,对抗资本的运动既不是单纯的劳动者运动也非单纯的消费者运动,它必须是横向的多国间的“作为消费者之劳动者”的运动。(24)②③④⑤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第257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6页。
进一步来看,当柄谷行人认为生产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是一种主奴关系时,实质上,他反对的是在生产中形成对抗逻辑。这个对抗逻辑就是工人意识到在生产领域被榨取了剩余价值,从而激起工人的革命意识进行劳工运动。不过,“英国的剩余价值乃是从爱尔兰和印度等殖民地获取的,只在生产过程中寻找剩余价值,那是骗人的”(25)②③④⑤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第257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6页。,“从生产过程发现打倒资本主义契机的可能性越来越显得渺茫了。不过,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26)②③④⑤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第257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6页。。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柄谷行人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是通过流通来实现的,生产实质上是劳动力商品实现的现实场所,基于生产的斗争并不是因为工人受到剥削引起的斗争,而是为了提高劳动力商品交换条件的斗争,从而,工会运动将主要是围绕劳动力商品的经济交换层面,对提高薪酬、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时间的缩短很有贡献。所以,柄谷行人认为,恰恰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从社会总资本看,随着工会运动带来的工人经济条件的好转,劳动者的消费也将随之扩大,最终实现了资本剩余价值。这种经济斗争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循环”,也即实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柄谷行人认为,基于生产过程的劳工运动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解,资本的增殖过程,即G—W—G′,不仅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是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工人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商品才最终实现了剩余价值。资本的积累或剩余价值最终只能在流通领域里实现,所以,“正是在流通过程中可以发现劳动者对抗资本的根据地”(27)②③④⑤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第257页,第250页,第251页,第256页。。在这个场域中,有劳动者成为主体的契机存在,这个时刻便是停止资本积累的“裂缝”,裂缝是我们主张的横向的多国间的消费者/劳动者运动,即创造非资本主义经济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不需要货币,而是构筑代替货币的流通和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这意味着,生活是为了围绕一种自由互惠的交换形式重组社会、一种可能的共产主义。温赖特认为,柄谷行人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建立在康德意义上“将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上,即共产主义是一种有尊严的形而上学(28)Kojin Karatani,Joel Wainwright, “Critique is Impossible Without Moves: An Interview of Kojin Karatani by Joel Wainwright,”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p.30.。
那么,他的共产主义是如何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呢?柄谷行人借鉴马塞尔·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提出了交换样式理论,不是“从生产力或生产手段来思考,而是从交换开始思考”(29)柄谷行人、欧阳钰芳:《交换模式论入门》,《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在柄谷行人的世界历史构筑体系中,交换样式有四种类型:A.赠与的互酬,B.服从与保护,C.商品交换,以及超越上述三种形式的D。在任何社会构成体中,这些交换样式都是共生共存的,如果只是其中的一种占统治地位,事态就会变得不同了。(30)④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3页。也就是说,社会形态是由占主导地位的交换样式决定的。交换样式A植根于早期的人类社会,礼物是一种互惠交换的手段,接受了礼物就有义务回报。在氏族社会中,交换样式A占主导地位。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涉及被征服者纳贡的交换保护关系,交换样式B占主导地位。在现代社会形态中,交换样式C占主导地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交换样式A和B,它们仍然存在,但形式有所改变,即交换样式B是以主权国家的形式,交换样式A是以民族的形式。因此,现代社会形态是三种交换模式的组合,即资本—民族—国家,沃勒斯坦称之为“现代世界体系”。最后,交换样式D是一种超越,即一种由自由互惠定义的交换模式。事实上,柄谷行人也承认了基于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考察使他意识到要超越它很困难。譬如靠国家来否定资本主义并不那么困难,但是却强化了国家的功能。在这里,他开始思考康德。康德区分了“建构性理念”和“整合性理念”,能够将理念现实化的称为建构性理念,而整合性理念并不能直接现实化,而只是作为一种目标向前推进。在柄谷行人看来,传统政治路向将共产主义视为建构性理念,结果造成了“理性的暴力”。我们否定建构性理念,但不能也否定了作为整合性理念的共产主义。对柄谷行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整合性理念,而不是建构性理念,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在柄谷行人看来,对共产主义的想法并非来源于我们的愿望和意志,而要基于交换方式的角度结合弗洛伊德“被压抑物的回归”来解释,交换样式D乃是在交换样式B和C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受到其压抑的交换样式A的回归。(32)④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3页。当然,交换样式D也并非交换样式A的简单恢复,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对互酬性的恢复。“被压抑物的回归”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显然是来自未来,而不是来自过去的复兴。在这方面,正如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重建为“未来哲学”,是“尚未意识的”观点。所以,交换样式D本质上是整合性理念,“A、B、C三种交换样式将会顽强地延续下去。正因为如此,交换样式D也会持续地存在。它将作为一个‘整合性理念’而发挥其作用”(33)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7-268页,第267页。。
三、对柄谷行人激进政治理念的反思
柄谷行人说:“抵抗运动是以每个人为出发点的。但那不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置身于社会诸关系中的个人。每个人都生活在性别、性特征上的、民族性、阶级、地域及其他等等各种不同的关怀维度上。”(34)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7-268页,第267页。这样的激进理念无疑有其吸引力。但是,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从流通的契机中进行抵抗,这种思路所依据的交换理论能站得住吗?
首先,柄谷行人强调剩余价值最终在流通中实现,促使人们在流通的契机中走向自为的主体,并论证主体可以通过拒买的方式自觉抵制资本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商品生产就不会有后面的商品流通,通过消费进行抵抗的主体也并不能称得上解放的主体。马克思说:“流通的前提是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从表象上看,在流通领域,从G—W—G′,资本看起来具有增加自身价值的神秘能力,也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在流通中实现剩余价值。然而,马克思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象,要从本质性维度思考流通背后的生产领域,“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7页。一旦我们进入劳动过程,遇到资本对活劳动的依赖,这种表象就会消失。换言之,柄谷行人仅仅将剩余价值阐释为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的价格差异带来的资本增殖,完全无视生产中的劳动者被赤裸裸剥削的事实。正如齐泽克所批判的,“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等概念的解释是极其不当的”,“关键在于,这个商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它创造了新的价值,新的价值又大于它自身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被资本家所占有。”(37)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页。由此可见,柄谷行人将流通作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场所,忽视生产的隐蔽场所,从而未能抓住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真正原因,滑向了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并没有深入资本主义的核心。同样,他所提出的消费者作为主体抵抗,将解放主体从马克思看重的工人阶级转向了消费者,表面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主体的影响,却将在生产领域的对抗看成主奴关系,认为劳动对资本仅具有从属关系,而将消费者在消费领域的抵抗视为主体自我反思的反对资本主义,这注定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个体性的观念。因为,柄谷行人忽视了主体处于普遍的商品化这一现实的“存在论根基”。虽然在经验现象层面,仿佛针对个体来说我们可以不买,从而使得主体拥有抵抗的可能性,但在普遍的商品化世界,个体如何抽离于商品世界?柄谷行人将消费者“抽象”为了可以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个体”。但是,人生存的前提就是“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不可避免地要遭遇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显然,柄谷行人不懂得“现代人”或“现代消费者”正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建构的,我们并不可以自主地选择不买。因此,柄谷行人所谈论的从流通中抵抗注定是只能停留在思想领域中的“概念游戏”。
其次, 柄谷行人倡导在流通领域中取代货币, 并肯定了用来取代货币的支付决算体系, 如迈克尔·林顿提出的LETS(39)马克·林顿于 1982 年提出LETS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地区贸易通商制度)。这个制度是一种记录在账户上的多角的决算系统,参加者有自己的账户,将自己能提供的财产和服务登载于目录中而实行自发的交换。 LETS 的通货与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不同,接受别人提供的财产和服务的人每次要重新发行通货,而所有参加者的黑字与赤字合计起来是零。这个系统今后还有进一步在技术上发展的余地,但在其总体的概念设想中包含着解决货币之二律背反的钥匙。(地区贸易通商制度)。虽然他意指的是实践模式,但他依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柄谷行人复兴了蒲鲁东废除货币、提倡劳动货币或交换银行的思想。他一方面基于价值形态货币具有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沿着《资本论》的考察路径,思考那种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必须有货币’同时又‘不可有货币’。因此,要扬弃货币必须创造出可以满足这两个要求的货币”(40)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第263页。。柄谷行人认为,有了替代货币的决算系统后,将对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斗争,譬如不出卖劳动力、不购买资本主义商品的运动,起到支撑作用。“替代货币”虽然看起来似乎能够如柄谷行人所说的破除货币拜物教,而且LETS中的社会契约与蒲鲁东所谓的“联合”相同,即每个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并且可以从属于复数的LETS,也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行通货的权利,从而每个人都将成为真正的主权者,“联合终归是基于每个人的主体性,而若不是以流通为轴心的话,将不可能实现”(41)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第263页。。但是,就文本而言,柄谷行人的“替代货币”构思并未从资本主义内在运行逻辑去理解“感性世界”为何表现为货币拜物教,其背后的深层历史逻辑又是如何。在今天,激进左翼学者包括柄谷行人几乎都陷入了这种历史现象层面来理解“主体” “抵抗”乃至“解放”的可能性,进而只能将抵抗置于认知的层面来谈论。这是他们拒绝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所付出的代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就说过,“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42)②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第602页,第724页。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的是,“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43)②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第602页,第724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不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生产。马克思的批判力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齐泽克也对LETS提出批评,认为这个经济模型并不能避开货币这个陷阱。(44)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7页。同时,斯洛文尼亚当地知识分子阅读了《跨越性批判》后,立即向政府呼吁并开始LETS,最后失败了。(45)Kojin Karatani,Joel Wainwright, “Critique is Impossible Without Moves: An Interview of Kojin Karatani by Joel Wainwright,”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p.30.很显然,脱离了一定的生产关系,认为仅从流通过程中通过替代货币的手段就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仿佛如苦难之中诗意的想象,只是聊以自慰罢了。
最后,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仅仅号召人们在流通中进行抵抗的策略注定是一种幻象。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6)②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第602页,第724页。柄谷行人所设想的主体在流通领域通过不买的方式抵抗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终,主体只能臣服于资本。因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基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会不断地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1页。显而易见,马克思认为,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劳动者就始终被资本宰制,无法逃离。更进一步讲,正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关系中,工人的主体性地位不断地丧失。原来工人活动的物化结果,现实地成了今天工人的统治者和剥削者,并且是进一步的不平等交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导致人对外化经济力量的依赖性。正是以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分析作为基础,才使得马克思分析了阶级和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与柄谷行人脱离了现实的生产关系分析及其主体在流通中得到契机进行抵抗的激进政治理念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