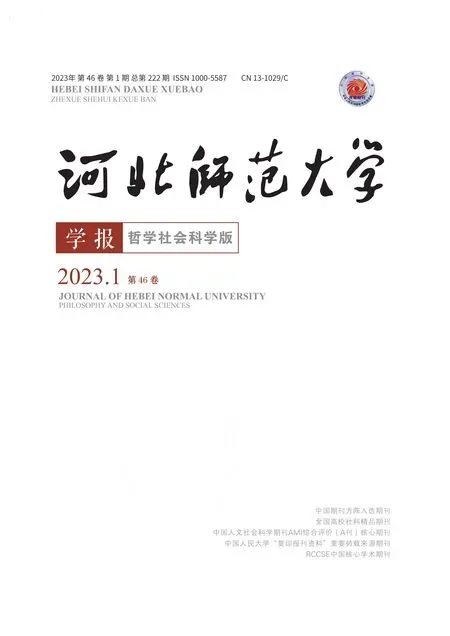“精神生产”与文化领导权问题
——重读考茨基
孙士聪,牛旭阳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尽管经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认为结束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以至于它的“重生”都被提上了议程(1)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然而,它所开创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却一直在蔓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文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扭转充分打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与庸俗马克思主义还原论之间的宽广论域,并由此将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第二国际拖入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视野。一方面,修正主义论争推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趋于稳固,而围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话题,则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得到更深入的阐释(2)陆扬:《论第二国际的文化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另一方面,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中自上而下的“教育论”与自下而上的“启蒙论”两种路径相互交织,并在激烈论争中以及对于第二国际的批判中逐渐趋于复杂化。英国学者哈丁(Neil Harding)曾指出:“第二国际的历史是一种紧张状态持续存在和意见不一的历史。这些紧张状态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表达。首先,以修正主义或改良主义为一方,以革命主义为另一方,存在着这两方的统一体。”(3)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页。也正是如此,第二国际理论家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发多半与具体论争结合在一起,具有明显的论辩色彩,考茨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争议中的考茨基
第二国际理论家卢森堡为考茨基下了“这位马克思主义神殿的官方守护人”(4)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见《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社,2001年版,第7页。此外,一般认为,卢森堡与考茨基的决裂是在1910年,以该年9月9日卢森堡发给考茨基的信件为标志,该信表明了在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辩中,卢森堡对于考茨基“磨擦战略”反批评的明确立场与态度,二人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且公开化了。见罗莎·卢森堡:《致考茨基夫妇》,见《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第235页。这样的定语,梅林则褒扬他“用无情的批评,把具有历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同推挤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垃圾区分开来”(5)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青载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3页。。而与之相反的评价似乎更为广泛。托洛茨基批评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现成体系接受下来,并像一位教师那样把它通俗化”(6)列夫·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柯尔施批评他“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何基本的联系”(7)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卢卡奇批评他“遗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本质”(8)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沈耕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58页。,当然,最著名的批评无疑来自列宁。列宁将考茨基定位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这一判断广为流传。一般认为,列宁对于考茨基的批评出现在1914年之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如《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尤为著名。列宁对于考茨基所使用的定语,从“娼妓”“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一直到“无产阶级的叛徒”“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9)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9、504页;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6页。此外,以1914年为分水岭,列宁对考茨基评价前后迥异乃至截然相反,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在此存而不论。事实上,不仅列宁明确把考茨基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批判考茨基偏离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已经太远,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卢卡奇,也批判考茨基走向“历史宿命论”的思路,主张要重回唯物辩证法;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佩里·安德森断言考茨基的著作“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葛兰西则批判考茨基走向经济决定论。(10)《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48页;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等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上述批判无不根植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中,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考茨基应该被辩证地来看待。事实上,即便是严厉、激烈批判考茨基的列宁,在1914年之前,也曾高度评价考茨基。比如列宁曾将考茨基称为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梅林之后的“社会主义的权威人士”,1909年又称赞《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是最好的反对机会主义的著作;即便在1918年批判考茨基“叛徒”之余,列宁也不忘指出考茨基“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财富”(11)《列宁全集》第35卷,第269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中译本对此的翻译并不完全一致。在《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译本1960年版、1972年版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单行本中,均多出一个定语“可靠的”,该句话为“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而在1985年版的《列宁全集》第35卷、1995年《列宁选集》第3卷以及2012年《列宁选集》第3卷中却并没有这一定语,该句话为分别表述为:“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财富”“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从“可靠的”、“始终是”到“将永远是”,中译本中的细微差别固然有俄文版自身的变化原因,也难免有中译时语境具体性的考量。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75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3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6页。。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本土学界基本继承列宁1914年之后对考茨基的批判,这在20世纪60年代“灰皮书”中尤为典型(12)“灰皮书”主要是作为批判新老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分甲乙丙三种,其中甲种最严。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此外1966年还出版了《考茨基言论》。见苏颖:《卡尔·考茨基的生平与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埃杜阿尔特·伯恩施坦等:《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著作选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卡尔·考茨基:《考茨基言论》,中央编译局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彭树智:《叛徒考茨基》,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开始迅速摆脱既有考茨基的研究程式,出现一些具有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明确提出要重新进一步学理性地审视考茨基思想(13)苏颖:《卡尔·考茨基的生平与思想研究》,第23-28页;张玉宝:《卡尔·考茨基及其中派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页。,而对包括卢森堡、考茨基在内做出相当异类的研究与评价则来自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拉克劳与墨菲两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其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高度评价卢森堡对偶然性的论述:“它最大化地拉开了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的距离(第二国际把阶级统一仅仅看成是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14)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所谓偶然性、自发性或自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统一体,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卢森堡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她并没有着重予以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走向分裂,无产阶级的统一性只有在革命实践中、并且必须通过革命实践才是可能的,但“正是在这里自发主义在发挥作用”(15)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第5页。。质言之,卢森堡意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视野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并非先验地存在着,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并且通过革命实践才自发地生发出无产阶级意识,才成为无产阶级的。后马克思主义动用解构主义理论资源,对此做出解构主义的阐发:每一孤立斗争的真正意义是漂浮不定的能指,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它常常超出表面的意义,不同主体的各种斗争,作为一个意义不完全固定的能指,滑动着、飘摆着、游弋着、绵延着,在一个偶然的遇合之际,它们受多元决定而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象征性统一体,即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意识。在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卢森堡虽然依然穿着阶级统一性以及经济主义的紧身衣,但她提出的工人阶级意识自发性与偶然性已经表明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统一体中的裂隙,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暂时性危机,“那时马克思主义最后失去了它的清白”(16)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等译,第16页。,而他们对考茨基的阐释则力图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拉克劳与墨菲在《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对考茨基1892年的《阶级斗争》文本进行了细致解读,认为该文本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一个德国工人短时期(1873年到1896年)的局部经验,即便在德国,这一经验的典型性也是十分可疑的,比起考茨基的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描述。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更加普遍的情形却是:工人阶级产生离心倾向,工会与政党关系紧张,资本主义组织化复辟,社会愈益不透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主体立场碎片化。考茨基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结构性差异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将个体经验普世化了,结果陷入经济主义决定论和还原论泥淖(17)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其结论就是在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中。
剥离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去魅”这一基本色调(18)“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方面(尤其是政党的控制)、一般总体化理论、对马克思的神化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体系的屈从。他们赞成多元主义、差异、对权威的怀疑、政治自发性以及新社会运动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形象是一个权威主义、极权主义、迷恋控制和虚伪的体系。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再试图弥合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见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卢森堡阐释,也并没有远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普遍性的论述。对于考茨基而言,百年之后第二国际早已是时过境迁,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也仍然不失为第二国际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而他与列宁之间的相互批判,在拉开足够长的历史距离后也完全可以获致更为从容的审视(19)陆扬:《论考茨基的文化思想》,《上海文化》2015年第12期。,也正是如此,有必要重读考茨基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思考。
二、“灌输论”与精神生产
围绕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考茨基有一个有名的判断,此即“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一判断曾受到严厉批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寂于学术史之中。考茨基在其他相关论述中也非常重视精神生产本身的自由性与个体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将他的意识“灌输论”与他关于精神生产的思考结合起来。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曾引述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灌输”的话,并评论这一段话“正确而重要”。后来围绕谁是“灌输论”的首倡者,本土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过争论,90年代以后乃至新世纪依然有学者关注。该争论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谁是首倡者,有观点认为是列宁首先提出,对立观点则认为列宁受到了考茨基的影响(20)早期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柯尔施认为,列宁、考茨基、卢森堡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当时工人运动实际需要出发,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只能由跟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给工人,意即灌输论之谓多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某种程度的共识,非某人独创;此言不虚,因为理论思考不能不植根于彼时无产阶级运动基本现实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但即便如此,列宁也较其他同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此做出了更为具体、完整的阐述;反过来,考察列宁的灌输论,也绝非暗示可以据此否认其他理论家的创造性贡献。参见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第68-69页。;另一个是在考茨基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谁是首倡者,有观点肯定考茨基首先提出,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在考茨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提出过这一范畴。(21)章显培等:《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中央编译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金重:《“灌输论”的首创者不是考茨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王建华:《试析关于“灌输论”首创者的几种观点——兼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形成》,《思想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唐鹏:《思想教育领域灌输概念首先提出者的历史考察——评“灌输”是考茨基首先提出的几种错误说法》,《桂海论丛》2003年第2期;孙来斌:《“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稍加琢磨可以发现,考茨基多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这些批判无不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与其纠缠于谁是“灌输”论的首先提出者,倒不如在一个更宽广的思想史视野中来考察这一命题在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考、论述及其理论启示更有意义。
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言,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没有革命意识将很难会有目标明确的现实革命行动,如何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思想牢牢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所谓“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意即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对于无产阶级的掌握,德国人之所以解放成人,正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个获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思想的过程,也就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过程,因而,“击中”一词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宣传、灌输等内涵。恩格斯在1887年1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在美国无产阶级中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不能强行灌输,而应通过体验、化入心灵(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恩格斯多次谈到思想“灌输”的必要性,这里的思想“灌输”与马克思的理论“说服”基本一致。如何将无产阶级从他所习惯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区分出来、独立建构起自己的阶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重要动机。(24)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列宁自己在引用、评价考茨基的“灌输”论之前,曾经指出,革命政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性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25)《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5页。。他在《怎么办》一文中明确写道:“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2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对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意识与革命学说的“灌输”论述,卢卡奇曾经将其概括为“被赋予”问题,并做出探讨。他认为列宁在“灌输”论中,已经区分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的不同,并且强调,被赋予无产阶级意识并不应该被理解为“纯粹思想的产物”(27)卢卡奇:《卢卡奇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1页。参阅:《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8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基础上,考茨基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的意识灌输问题,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中断言:“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28)《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稍加琢磨考茨基的这段话,可以约略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无产阶级并非自发地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而是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播;其次,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理论也不是无产阶级自发产生的,而是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宣传的结果;再次,被灌输进革命意识的无产阶级将会把这一革命意识贯彻到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概言之,向无产阶级灌输其阶级意识、历史使命与阶级地位,并进而在政治上将具有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在考茨基看来正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反对简单的道德灌输,强调要从无产阶级现实革命愿望出发,灌输才是可能和有效的:“想要用道德说教来向英国工人灌输更高尚的人生观和奔赴崇高理想的观念,这是徒劳无功的。无产阶级的道德只能产生于革命的愿望;有了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就会更加坚强和高尚。正是革命的愿望才使无产阶级从最深沉的屈辱地位中惊人地振奋起来,而成为19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事件。”(29)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无产阶级道德的高尚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从无产阶级现实中生发出来。“最深沉的屈辱地位”是无产阶级生活最坚实的土壤,而对此屈辱生活的意识将产生革命的愿望,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高尚道德与人生观念正是在革命实践中生成的。在考茨基看来,一切意识“都产生于有机体生活的条件,他们是随着这些条件而发生变化的”(30)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社会生活,归根结底不是建立在先验意识之上,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生活条件之中,从特定物质生活来把握意识,正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由此可知,考茨基对于意识灌输的看法,并非简单强调意识灌输的强制性、无视意识接受与精神生产自身的特质与规律,而是突出灌输对象的现实生活基础,意识灌输必须服从与物质生产不同的精神生产自身的规律。
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
考茨基关于“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判断,明确出现于1902年《社会革命》一文(31)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3页。。相关剖析早已汗牛充栋,但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依然不乏启示性。在讨论精神生产中,考茨基认为,物质生产是“最根本的”,物质生产只能为精神生产提供某物质前提,却不能取而代之。精神生产“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而以物质生产方面能提供多余的产品和劳动力为保证的。精神生产只有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时候才会繁荣起来”(32)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2页。。这与强调无产阶级道德意识源自于对“最深沉的屈辱地位”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相对于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同样重要(33)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85页。,这显然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而考茨基试图要做的,是进一步探寻二者结合的可能与路径:一方面,从精神生产的方式来看,无产阶级必须解除资本家和大地主对学校和教育的控制。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缩短了物质劳动时间,从而相对扩大了精神生产时间,而那些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生产,其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产。如此,物质生产才能与精神生产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为了促进二者的结合,考茨基认为必须实行两项措施,一是推动体力劳动成为服务社会的必要劳动,二是推动精神劳动走向摆脱任何强制的自由劳动。(34)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88-189页。
考茨基提出,精神生产有三种具体领导方式,分别是国家、地方以及自由组合的社团。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的前提下,资产阶级对于精神生产的领导权已经丧失了阶级和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国家将在精神生产中处于领导地位。然而,这里依然存在一个问题:如果在无产阶级政权下,精神生产并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所能承担,考茨基质疑道:“这岂不是说,这里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又只是国营企业了么?……国家政权果真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机构,但岂非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机构么?”(35)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0页。的确,这里存在严重问题,但并非不能解决。考茨基提出,可能的解决在于除了将精神生产置于无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下,而且必须在这一领导下,还可以发挥地方在精神生产中的作用,而且“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防止任何千篇一律,防止中央政权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36)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0页。。虽然考茨基并未具体论述地方在精神生产中如何发挥作用、其中具体机制是什么、与中央政府对精神生产的领导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然而单就他对于精神生产千篇一律的提醒以及被操纵的精神生产及其产品未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来说,这一思考就已经值得重视了,而实际上,后来的前苏联在新媒介时代影视艺术以及文化发展方面的僵化与落后,就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考茨基的担忧。
此外,在精神生产中,自由组合的社团将发挥重大作用。在无产阶级精神生产领域,除了无产阶级中央和地方政权之外,自由组合的社团被赋予重任,这些社团将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因为这种社团的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也就取代资产阶级精神生产,成为无产阶级对精神生产领导的一部分,以更为丰富的方式、手段来从事生产,比如“演出戏剧,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等”,从而无论是在精神产品的数量、还是在生产水平、生产者的投入程度等方面,都会有巨大的增长。显然,考茨基认为,以上三种不同的精神生产都是无产阶级精神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体现,而这绝不会给精神文化生产带来更大的束缚,只会带来“更多的自由”(37)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1页。。
考茨基对于精神生产的自由性、个体性高度重视,是与他所谓“精神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考茨基批判了资产阶级在此问题上陷入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也对无产阶级政权对于精神生产的简单化理解可能带来的“千篇一律”保持警惕。在他看来,物质生产上自由竞争的市场发展是有效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规律的调节,而这对于精神生产却是完全无效的;价值论只是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领域。不受影响的原因并不在于其他,而在于精神生产必须遵循自己特有的规律,这绝对不是机械套用、简单遵循物质生产的规律;精神生产并不能够运用物质生产价值规律来指导,精神生产的产品也不能简单运用物质价格来衡量。考茨基断言:“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38)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3页。这一断言有其某种修辞偏执,但对于精神生产领域自由性的理解显而易见。
关于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有过著名的论述,他指出,资本主义与精神生产的规律相违背,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地看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带来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但它同时也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来临奠定了足够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它从根本上使人的存在不得不处于异化状态之中,彻底剥除了人的自由和解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是与它自身相矛盾的。考茨基承认,精神生产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一种职业劳动,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精神劳动则成为一种摆脱了任何社会强制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为比起体力劳动来,精神劳动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得多”。然而,无产阶级必须“解放精神劳动”,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胜利在经济上的必然后果”。(39)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89-190页。也就是说,不论通过体力劳动来为精神劳动获致更多自由时间是否最终实现了原初目的,但精神劳动的自由性根植于无产阶级革命目的之中,即根植于人的自由与解放之中,因为“社会主义将给人类带来安宁、舒适和闲暇,将把人们的思想提高到超凡出俗的境界……使人们都能享有和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并恢复人的天性,使其能从生活的力量和乐趣中得到发展”(40)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96页。。
四、教育者抑或启蒙者
毋庸讳言,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的论述主要集中于1902年的《社会革命》中,该著作整体上反映了考茨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成果,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第二部分是“社会革命之后的日子”,而第二部分作为对于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后的基本设想,考茨基坦言是“到未来国家去的旅行指南”(41)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叶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3页。。考茨基设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必须补上过往资产阶级所没有做的事情,首要之事是清除封建残余以及资产阶级残余,比如要尽快废除一切阶级特权,保证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等等。整体看,《社会革命》是考茨基政治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与修正主义论战的代表作之一(42)张玉宝:《卡尔·考茨基及其中派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然而,无产阶级如何取得政权,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考茨基认为,理论问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实属重要,“理论是促进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因素,因为它教导无产阶级合理地运用这些为经济发展所制约的力量,并且反对对这些力量的无目的消费。而且,理论不仅仅增强无产阶级的实力,它还提高无产阶级做自己的力量的自觉。而这也是同样必要的”。然而问题恰在于,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力量尚缺乏足够的自觉,“只是无产阶级的个别阶层具有这种自觉,而就整个无产阶级来说则缺少这种自觉。社会民主党正在千方百计提高无产阶级的这种自觉。为了这个目的,它不仅从理论方面对群众进行教育,而且也利用其他办法”。(43)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226-227页。那么,对无产阶级进行教育的主体,是哪些人呢?依考茨基所见,传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学说的主体,严格地说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部分反抗资本主义、渴望自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却同情无产阶级:“那些越来越同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中最无战斗力又最缺乏斗志的部分”。(44)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19-120页。在考茨基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首先,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与知识生产的主体,不仅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的使命,而且也负有教育职能,通过教育“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45)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89页。;其次,精神生产与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不同,它更多是完全自由的生产,不仅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不适用于精神生产,甚至连某种意识形态集中控制对于精神生产也是不适用的,而这些恰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契合性。质言之,在无产阶级通向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作为教育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盟友,至于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则“已经成为艺术和科学最可靠的保护人,他们一贯是最坚决地提倡艺术和科学的”,“对艺术和科学最感兴趣,甚至最为尊重”。(46)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第118、185页。
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特殊教育者职能的重视,可以在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中找到辅证。伯恩施坦提出,“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47)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这里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生成视为纯粹自发的过程,实际上误解了革命意识与革命实践的关系,是修正主义的“自发论”论调。对此,考茨基指出,这种自发性的论断是错误的。首先,就无产阶级革命而言,人类科学知识的代表人物,并非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次,社会主义意识也并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出来的,而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再次,无产阶级头脑中的社会主义意识,是先进知识分子“灌输”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的,是从外到内的过程,而不是无产阶级从内到外的生发所致。(48)《列宁全集》第6卷,第37页。应该说,考茨基与伯恩施坦阶级意识“自发论”划清了界限,准确揭示出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对此,列宁给予考茨基以充分肯定。当然,也必须指出,考茨基对于伯恩施坦的批判并不彻底,他“并不能明确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政治任务而同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妥协”(49)贾淑品:《列宁、卢森堡、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413页。。尽管考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着浓厚的实证主义、折中主义、进化主义的色彩(50)姚顺良等:《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但严格地说,考茨基却并不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当然也不是唯意志论者。
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的看法不无片面,甚或带有乌托邦色彩,而革命意识通过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给无产阶级也使他与“马克思的联系遭到了弱化”(51)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中译本序言”》,见《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第1页。,然而他对于精神生产个体性、自由性的强调,值得充分注意。精神生产与意识灌输并非仅仅是简单地从外向内的强制性灌输,而且更主要地属于精神实践,因而也就是一种具有个体性、自由性的实践。正如恩格斯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必须透过无产阶级自身的经验及其反思,宣传才能真正化入心灵,同样,考茨基也认识到,只有在充分发挥精神生产与接受主体的自由性、个体性的基础上,意识灌输与精神生产方能真正发挥意识革命的职能,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结 语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与具体的社会生活,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的思考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而作为佐证,还可以从他对于土地问题的研究中找出相似的致思理路。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中创造性地提出“普鲁士道路”,这是与英国资本主义农业道路不同的发展模式,被视为对马克思、恩格斯生产论的深化,考茨基自言“如果在这本书内我能够发展一些新的有益思想,那首先便应归功于我这两位伟大的先生”(52)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7页。,而列宁称其为“最出色的”、填补了空白的经济学著作(53)《列宁全集》第4卷,第79页。。考茨基关于土地问题的思考表明,他既没有因为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而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没有机械僵化地固守经典批判理论的原有结论,而是坚持创造性地应用这一理论、特别是用其方法论去研究新现象,再以这一研究的新成果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54)姚顺良等:《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见张一兵主编:《资本主义理解史》第2卷,第180页。,应该说,这同样适用于对于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思考的评价。对于第二国际而言,如何看到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经验,是必须面对与思考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在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巨大的争论。比如,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就产生了左、中、右三派,可以约略概括为普世论、否定论、调和论:左派强调俄国革命经验的普世论,主张在西欧国家展开像俄国革命那样的革命;右派的否定论则不认可俄国经验的普适性,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调和派则一方面否定俄国经验的普世性、批判社会改良论,另一方面又在主张充分尊重社会具体性的同时,提倡像俄国革命那样的暴力斗争。整体而言,考茨基持调和论立场,现在看来,这一立场充分体现了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深刻思考与理论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当代阐释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