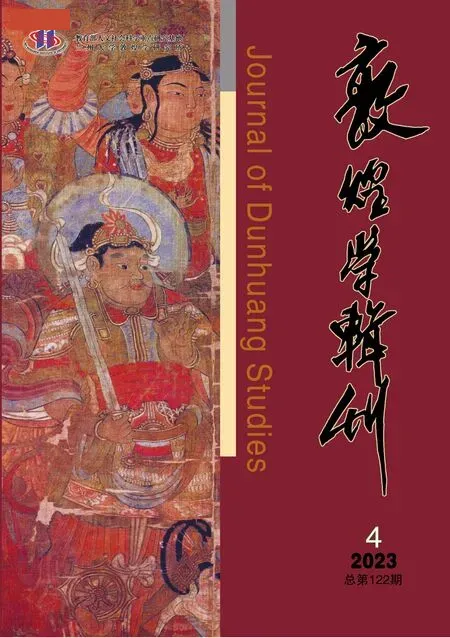不断开启敦煌学研究的新境界
——《敦煌通史(两汉卷)》评介
刘全波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加强敦煌学研究,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全国敦煌学界都在为做大做强敦煌学贡献力量。《敦煌通史》就是响应总书记号召,由甘肃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一套作品,为新时代敦煌学的繁荣发展增光添彩、添砖加瓦。《敦煌通史》由郑炳林教授主编,魏迎春教授、李军教授副主编,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也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分七卷,其中,郑炳林、司豪强承担两汉卷,杜海承担魏晋北朝卷和五代宋初归义军卷,吴炯炯承担隋及唐前期卷,陈继宏承担吐蕃卷,李军承担晚唐归义军卷,陈光文承担西夏元明清卷。《敦煌通史》内容丰富,论证充分,旁征博引,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给读者描绘了一个完整的、详细的、多样的、鲜活的敦煌画卷。
郑炳林、司豪强著《敦煌通史(两汉卷)》于2023年4月出版,(1)郑炳林、司豪强《敦煌通史(两汉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是丛书中最先出版的一部,笔者通读之后,不揣浅陋,写成此文,以作推介。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无垠的戈壁与绿洲交相辉映,大山之外是大漠,点点绿洲连接起来的道路,就是东西交往的孔道,敦煌就矗立在东西要道的关键点上。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38335人,东汉时期敦煌的人口是29170人。其实,敦煌的人口是较少的,在古代,人就是生产力,敦煌这个人口较少的西北边缘之郡,却成为了华戎所交一都会,造就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十分值得我们深思与考察研究。《敦煌通史(两汉卷)》克服了传世文献不足的困境,大量使用敦煌藏经洞文献、简牍碑铭等出土资料,为我们完美展现了两汉时代的敦煌历史与文化,通论中有专精,旧说外有新见,既能立足学术前沿,更具全球思维与世界眼光,着实推进了汉代敦煌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敦煌通史(两汉卷)》共分九章,依次是敦煌的早期历史,西汉敦煌郡、两关的设置与移民实边,西汉经敦煌对匈奴、南羌的经营,西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新莽至东汉初年的敦煌郡,东汉河西战略定位变迁,东汉敦煌郡的职官考察,东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其中,东汉河西战略定位变迁又分为上、下二章。
对于敦煌的早期历史,学术界多有考察,其实也是众说纷纭。《敦煌通史(两汉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早期历史做了更为深入的推进研究,总结、梳理了敦煌的早期发展史,是启迪智慧、点燃新的研究的桥梁与纽带。作者认为“敦煌名称的出现要早于敦煌郡的设置,丝绸之路的开启也远早于张骞出使西域”(第3页)。诚然,丝绸之路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甚至于东西南北之间交往之频繁与深入,超出想象。作者通过对《山海经》《水经注》等文献的考察研究,并结合敦煌文献,对文献所记载的“敦薨”“三危”“黑水”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敦煌附近的山川河流之名,被大量的文献典籍所记载,展现了敦煌之地的重要性与知名度,而这些山川河流几千年来也不断地出现不同的称谓变化,作者通过细致的考察,将他们之间隐秘的联系揭示出来,让读者看到了更加清楚的敦煌早期历史与文化。“焞煌”一词的考察,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敦煌的先民们,《敦煌通史(两汉卷)》也做了详细的考察,即敦煌历史上的乌孙、月氏时代,乌孙与月氏是并处于敦煌、祁连间的,只不过后来乌孙被迫退出这片地区,乌孙的退出与月氏的称霸是紧密相连的时代,这个时间段不会很短,由于史料的缺失,很多真相还有待考古资料来证实。而后是匈奴统治敦煌的时代,匈奴对敦煌以及河西的占有,伴随着对月氏的征服,匈奴对敦煌及河西的丢失,则是汉武帝出击匈奴的成果。不管如何,敦煌以及河西之地的先民们,已经逐渐开发了这片土地,这个时期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被易中天先生称为“青春志”,中华文明虽然还未臻成熟,已经处处散发着勃勃生机,文化、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与状态,而地处中原周边的乌孙、月氏与匈奴,几百年间,绝对也拥有了不俗的业绩与文明。如此,中原的诸多典籍中才可以传承下“敦薨”“三危”“黑水”等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追寻与探索。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以及对河西的占领是众多故事的高潮,其实故事早已经开始。张骞的第一次西行其实是西北行,张骞诸人虽然号称出使月氏,其实此时的月氏早已经被匈奴、乌孙打跑,张骞如果没有被匈奴囚禁,其实也找不到月氏,多次迁徙之后的月氏,已经远遁河中地区。汉武帝之出击匈奴,其实可以分为北向和西北向,卫青是北击匈奴,霍去病则是西北击匈奴,如此,从北到西的大片区域之内,汉朝完成了对匈奴的反击。霍去病之西北击匈奴的结果,就是列四郡、据两关,浑邪王杀休屠王投降汉朝之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这是敦煌设郡以及敦煌城修筑的历史大背景,作者亦强调到“西汉西北边疆面临的周边形势发生了极大改变,此后河西走廊逐渐兼具南防西羌、北阻匈奴、西通西域的作用”(第66页)。《敦煌通史(两汉卷)》大量运用敦煌文献以考察敦煌置郡建城之时间,《沙州城土境》《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等皆记载敦煌城修建于元鼎六年(前111),由此可以确定敦煌郡的设置年代就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命赵破奴主持敦煌的置郡和敦煌城的修筑,赵破奴在置敦煌郡时不仅修筑了敦煌城,而且围绕着敦煌郡城修筑了一系列防御体系。作者指出“随着大量移民进入敦煌郡,为了安置移民发展经济,赵破奴还主持修建了敦煌的水利灌溉系统,马圈口堤堰就是他留下的水利工程项目,而且一直使用至唐五代”(第91页)。如果没有对敦煌文献的熟稔,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仅凭传世文献,绝对得不到这样的结论,敦煌文献的补史功能也再次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与变迁,学界多有讨论,《敦煌通史(两汉卷)》结合典籍记载进行了诸多探讨,着实厘清了诸多混乱。作者认为“西汉政府为通西域,在设置敦煌郡的同时,还修筑玉门关与阳关,形成了拥四郡而据两关的局面。玉门关最初设置于敦煌郡东部,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征大宛得胜后,西汉政府将玉门关移到敦煌郡的西北部,作为经营西域的军事塞城。玉门关设置后,西汉政府为方便与西域通使,又在玉门关以南设置阳关”(第92页)。
对于西汉敦煌郡的移民问题,《敦煌通史(两汉卷)》的研究更是极具创新性。历代王朝对边疆的经营,移民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古代是如此,近现代也不例外,每一次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总是或多或少要涉及一些移民的问题。《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4-1645页。此处《汉书·地理志》所载前半段主要讲为什么移民,以及移民是哪些人,后半段则是讲移民的效果,吏民相亲,有和气之应。前半段《敦煌通史(两汉卷)》亦有引用,后半段其实更加生动,虽有矜夸之嫌,亦可见边郡之其乐融融。对于西汉敦煌移民问题,《敦煌通史(两汉卷)》总结的极其好。“浑邪王降汉后,西汉派遣军队戍守敦煌界进行屯田,形成了第一批西汉敦煌移民;西汉劝说乌孙回迁河西以断匈奴之右臂的计划没有实现,就开始对河西敦煌进行直接管理,置敦煌郡的同时,将中原地区大量的贫民迁徙至敦煌,移民实边;在治理河西敦煌的过程中,移民敦煌不断进行,特别是将犯罪的高级官员和文士谪居敦煌,这些人都是西汉社会的上层,具有很高的文化造诣,他们迁徙敦煌实际上形成了敦煌的文化移民,汉代敦煌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130页)诚然,敦煌自设郡以来,在整个两汉时代,从未受到大范围的破坏,反而由于远离中原而成为世外桃源,迁徙而来的人们聚居在此,独享清平。两汉君臣对于西域之弃守态度多有变化,但从来没有人轻视过敦煌,他们都是极其重视敦煌的经营与开发,源源不断的移民,络绎不绝的军兵,使得本来边远的敦煌竟然慢慢繁荣起来。若再进一步放长眼光来看敦煌,从汉武帝到唐玄宗,从敦煌设郡到安史之乱,将近一千年,敦煌的汉文化从未间断,这一千年,连接起来的是中华文明最繁盛的汉唐时代,汉唐文明的精华聚汇于此,汉唐文明的根深深扎入敦煌大地,才会造就出无比灿烂的敦煌文化,展现出来的就是石窟艺术的巧夺天工,文化文明的博大精深,还有藏经洞的神秘神奇。文化的繁荣使得敦煌有了底蕴、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传承,没有这群有文化的敦煌人的坚守奋斗,敦煌的辉煌灿烂如何创造,没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是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并蓄、辉煌灿烂的文明的。
西汉经敦煌对匈奴、南羌、西域的经营其实是一个整体,恰好是河西走廊的三面,北面主要是匈奴,南面主要是南羌、西面是西域,霍去病出击匈奴的结果就是撕开了一个通道,而通道的门户就是敦煌,敦煌主要是面向西域,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和匈奴、南羌产生联系,地理格局就是如此,所面临的局势亦是如此。从乌孙、月氏到匈奴,从匈奴、汉朝到南羌、西域,彼此实力的此消彼长,淋漓尽致的展现于此地。自汉朝建立,匈奴就是虎踞北方的大敌,对汉朝来说如此,对羌人来说亦是如此,对西域也是一样,匈奴实力之强大,任何一方都难以应对,所以此时此刻匈奴是时代的主宰,更是对所有势力的不可遏止的威胁。汉朝经过多年积累,汉武帝时代终于打破了匈奴的霸权,汉朝占据河西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匈奴传》,第3774页。,此时敦煌、酒泉的压力剧增,所以以河西为中心构筑对匈奴的防线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敦煌通史(两汉卷)》总结道:“西汉政府置敦煌郡之后,修筑了沿边塞城东起高阙塞,往西经鸡鹿塞、眩雷塞、武威塞、居延塞、偃泉障、东部障、西部障、昆仑障、玉门关、阳关,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防御体系。”(第148页)南羌、南山羌其实是一个概而言之的概念,河西南山与西域南山也有不同,故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时,需依据时代、地点等信息判断之。西汉时期,对中原来说,最需要注意的是河西南羌、河西南山羌,因为他们与汉朝的距离更近。其实,在匈奴称霸的时代,其不只是欺辱汉朝,对南羌和西域也是羁縻之,故匈奴占据河西之时,与南羌之间也非平等的关系,即早年匈奴也欺辱过南羌,而随着汉朝的崛起,攻守易势,汉朝逐渐取代匈奴成为霸主,此时的南羌与汉朝之关系也日渐紧张,利益的争夺在所难免。小月氏其实就是月氏迁徙之余,历史上的迁徙多是主力的迁徙,从来不是全部,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迁徙,留在原地或散落在迁徙的路途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小月氏就是如此,小月氏与南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西汉到东汉,皆是如此,故对南羌与小月氏的区别和联系也需多加注意。随着汉朝霸权优势的逐步确立,匈奴与南羌联合起来,或者口头上相互支援一下,就成了必然,河西诸地的防御体系已经建立,羌胡之间直接通过河西走廊进行联络的道路被切断,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借助西域开展联络,西域此时尚属匈奴的势力范围,绕过河西交往的羌胡也多被史书记载了下来,敦煌地接西域,是河西的门户,在阻断羌胡联络中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通史(两汉卷)》中言:“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可知西汉政府在敦煌郡除破羌亭之外还修筑有弱羌亭、安羌亭、羌备城坞垣、南塞等,基本构成了抵御羌人的防御体系。还设置有护羌使者幕府这一经营南羌的机构。”(第178页)
西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是《敦煌通史(两汉卷)》的一个重点,换句话说,敦煌在西汉王朝经营西域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敦煌通史(两汉卷)》中言:“敦煌郡在汉朝经营西域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其扼守汉朝通西域之门户的地理位置。”“敦煌郡还是西汉政府经略西域的军事基地、文化交汇之地及西域都护的重要依仗。”(第180页)西汉出敦煌经鄯善开通西域南道一事,《敦煌通史(两汉卷)》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有学术推进意义。西域南道的开通与张骞亦有关系,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沿着西域南山北边回来的,这条西域南山北边的道路就是西域南道。西域南道距离匈奴较远,匈奴虽然对西域有影响,但是由于距离远,南道诸国受到匈奴的影响相对小,加之汉朝的开拓精神,西域南道得以形成。而对于西域南道的具体道路的考察,《敦煌通史(两汉卷)》大量运用出土简牍资料,尤其是悬泉汉简,完美还原了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故事。西汉经敦煌对鄯善、罗布泊地区的经营问题,亦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关键点、关键地区,是匈奴、汉朝、西域、南羌诸势力皆存在的一个地区,鄯善的后方就是婼羌,罗布泊的附近还有车师,匈奴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是长久的,汉朝则是来势汹汹的新起之秀,故这个地区的争夺,不仅仅是匈奴与汉朝,当然,主要还是匈奴与汉朝,通过悬泉汉简能发现很多被历史湮灭的往事。据《敦煌通史(两汉卷)》考证可知,“伊循都尉是受敦煌太守节制的”(第205页),“西域南道的开通及繁荣与敦煌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191页)。
西汉经敦煌开通北道与经营车师一事,亦是展现了敦煌的门户、窗口、通道意义。匈奴对于西域北道的管辖是要强于南道的,匈奴的僮仆都尉就是在焉耆、危须、尉黎间。但是由于汉朝在东部对匈奴的持久攻势,匈奴已经衰弱下来,其对西域的管辖亦是衰弱下来,但是此时匈奴对西域的影响力还是大于西汉,车师在最初是臣服于匈奴的,匈奴对车师的控制权也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随着汉朝在西域的力量的增强,双方必然发生争夺。最终如作者所言:“西汉与匈奴围绕着车师展开的争夺,最终演变成一场以屯田对屯田、以军队对军队的拉锯战。”(第221页)直到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力完全衰败。居卢訾仓又称居卢仓,学术界研究较多,西汉时期居卢訾仓城修筑与归属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学术问题,《敦煌通史(两汉卷)》做了透彻的分析考证。作者认为:“西汉政府对居卢訾仓的定位开始由过去供应破羌将军及自敦煌出征之汉军的军备仓库转变成为专门供应西域都护府的军备物资储存、转运仓库,其主要职责应是将内地发往西域地区的物资集中于敦煌,然后经水道先转运至居卢訾仓,再经居卢訾仓转运至西域地区。”(第267页)
新莽至东汉初年的敦煌郡一章,首先介绍了王莽辅政时对车师后部、婼羌归降匈奴的处理问题,其次是王莽辅政时对西羌的经略。总之,王莽自辅政时期开始,在边疆治理上采取了一些不合常理、不可理解的做法,使原本友好的汉匈、汉羌关系出现危机。作者直言:“可以说王莽举措的失误把西汉政府百年来在边疆治理上建立的局面全部葬送。于是,王莽辅政至其建立新朝这一时期又成为西北边塞局势由好转坏的转折阶段。”(第271页)对于新朝建立后与匈奴关系的转变,新匈战争对敦煌的影响。作者亦总结道:“新莽时期的敦煌郡大多情况下都在战争、饥荒、逃亡、课税增多、内政混乱等诸多不利因素交织下艰难支撑,摇摇欲坠。而随着新莽在西域统治的瓦解,敦煌郡失去西部的战略纵深,成为直面外敌的军事桥头堡,其战略地位却显得愈发重要。”(第291页)边疆的经营与治理从来不是单一问题,因地制宜、入乡随俗、灵活而不失原则是上策,奈何竟然会有如此“理想主义”者王莽之悖逆常理,盲目自大、目中无人、固执而不知变通中透露着狂妄,实在令人叹息,《敦煌通史(两汉卷)》中作者也发出了令人扼腕的叹息,尽是对历史的感叹,更是对大一统帝国崩溃的惋惜,历代治理边疆之得失研究,无疑就在此叹息之中。如此的新莽政权,其对西域的治理与经营局面,可想而知,战略败势之下的新莽,经过一番无谓的争夺,所有力量最终只能固守于敦煌,敦煌是万不可再丢失的,帝国若没有了门户,后果不堪设想。作者亦总结道:“敦煌郡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增,且因这场战争牵累,敦煌郡需要承受极重的负担,这对其的发展而言可谓雪上加霜。”(第305页)《敦煌通史(两汉卷)》在此部分的论述中大量运用了汉简资料,尤其是敦煌马圈湾汉简,揭示了诸多历史真相,实现了出土简牍资料与正史研究的互补互证。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各地起义不断,天水隗嚣占据河陇,依附更始,更始败亡后,窦融联络河西五郡保境自守,后窦融几经权衡,最终归顺刘秀,这一段时间之内,敦煌以及河西数易其主,但敦煌由于远离中原,反倒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对外征伐的停歇,倒也使得敦煌略有修整。此时的敦煌都尉辛肜,州郡英俊,与窦融善,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则任命辛肜为敦煌太守,保境自守。《敦煌通史(两汉卷)》对隗嚣治理河陇与窦融治理五郡都做了详细的考察,且细致的分析了其中的诸多反复与变化,真实再现了这个时期敦煌以及西北的历史。作者认为:“窦融先后采用过更始、赤眉甚至覆之的西汉平帝的年号后,才跟随陇右隗嚣,尊奉东汉光武帝建武正朔。随着东汉势力扩张,窦融又审时度势劝服五郡太守及豪杰作出了河西归顺东汉的决策。其后双方开始遣使接触,交流渐多,这一过程中双方从最初的怀疑、试探到加强互信,协同作战,关系日益紧密,这也是河西融入东汉统治的过程。”“光武帝恰如其分地处理河西问题的诸多举措也是促使河西归心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河西五郡从更始覆亡后成为一方重要势力到东汉统一战争过程中能够以和平方式实现权力过渡,纳入东汉中央政府管辖,是河西窦融集团与东汉中央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居延新简的一些记载对于补充丰富这一重要历程的诸多细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第360页)
东汉河西战略定位的变迁分为两章,重点阐释了八个问题,即光武帝刘秀对河西的接管及其对凉州的战略定位,汉明帝时代北击匈奴、经营西域与河西战略定位的调整,汉章帝时期河西地区经济、外交功能的凸显,汉和帝至汉安帝初期凉州的边塞形势,弃守凉州争论的始末及其影响,汉安帝至汉灵帝时期河西军事价值的提升,曹操时代东汉对河西的经略。纵观这八个问题,核心是东汉中央政府对凉州当然也包括敦煌的战略定位问题。光武帝刘秀中兴汉朝,使分裂的天下再度一统,其对凉州之收复,奠定了后世经略凉州的基础,但是此时东汉的重心肯定不会放在凉州,与民休息,恢复中原地区的生产力才是最主要的。汉明帝时期北匈奴国力有所恢复,走出低谷,再度骚扰汉朝边地,河西郡县竟然会出现城门昼闭的现象。北匈奴对西域的影响力也逐渐恢复,西域诸国此时也经过了几轮兼并,逐渐出现了多个小的霸主,北匈奴对西域东部的控制力度较大,西域西部则出现了龟兹、莎车、于阗等三霸。面对新的局势,东汉政府必须改变原来的凉州战略定位,经营河西,阻断羌胡,开拓西域,遏止匈奴,再次变成东汉王朝的战略目标。班超在东汉经略西域的过程中贡献巨大,力挽狂澜,扭转了东汉政府对经略西域的消极态度。《敦煌通史(两汉卷)》指出:“班超在西域的攻伐极大牵制了西域敌对势力及北匈奴的精力,大大减轻了敦煌郡乃至河西的边防压力。”(第394页)“随着班超在西域影响愈深,北匈奴日渐衰弱,河西面临的边防威胁愈低,其军事功能相对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外交功能有所展现。”(第398页)班超之后,西域都护任尚性急苛刻,处置不当,致使西域反乱,如作者所言,西域局势一度崩盘。加之西羌叛乱,汉朝公卿认为西域阻远,应罢都护、绝西域。从弃西域发展到弃凉州,则展现了东汉中央政府对西北局势的模糊判断,经过一番讨论,最终东汉政府接受虞诩的进言,着力巩固凉州,“使之不致失陷于叛羌或北匈奴、西域之手”(第441页)。于是“河西四郡成为抵抗叛羌、北匈奴及西域的首要之地,其军事战略地位重新提升”(第444页)。
东汉敦煌郡的职官考察一章重点考察了历任敦煌太守,《敦煌通史(两汉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细致的梳理,并对辛肜、裴遵、王遵、曹宗、张珰、张朗、徐由、裴岑、马达、宋亮、赵袭、赵岐、赵咨、马艾、张恭诸人生平事迹做了一一考索。敦煌太守裴遵建议东汉政府不可假莎车王贤以大权事,可见敦煌太守对西域事务的熟悉,又可见裴遵的远虑,更可见敦煌在处理西域事务中的积极作用与不二权威。敦煌太守张珰从“西域宜弃”到“出据柳中”的转变,则展现了士大夫从空谈到实干的变化,更展现了敦煌之地的重要性,既是门户、窗口,更是前线、后方。西汉时期,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两汉时期,敦煌太守对西域之重要性,虽不能和西域都护比,但其重要性亦是无可比拟。《敦煌通史(两汉卷)》对此类情况亦有总结:“敦煌太守对西域事务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徐由能驱使疏勒王作战,虽应已获得顺帝首肯,但还是能展现出敦煌太守在西域的超然地位。”(第509页)诚然,敦煌太守的确是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敦煌往东,虽然路途亦是遥远,但是敦煌与皇帝的沟通渠道一直是畅通的、有保障的,而西域长史与中央的沟通则会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于是西域长史依赖敦煌太守的局面也就出现了,不是敦煌太守比西域长史级别高,而是有些时候,敦煌太守的决定甚至可以影响西域长史的生命。敦煌设置的西域官员一节,重点考察了中郎将与西域副校尉,是具有突出问题意识的前沿性研究。作者认为“西域副校尉非常设官职,其设置具有临时性。它存在充当西域都护副贰的情况,也不排除充当中郎将副贰的情况,甚至在西域都护、中郎将都不设置时,西域副校尉亦可独当一面,单独设置”(第560页)。
东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再次重点介绍了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东汉与西汉比,对西域的热情已经下降,但是西域在对匈奴作战以及稳定西部局势方面的重要作用,又是不可低估的,所以东汉王朝才会多有弃守西域之争,此时的西域也不是彼时的西域,此时的匈奴也不是彼时的匈奴,而发展最为强劲的西羌,以及鲜卑,又不断侵扰东汉之腹心,所以东汉政府对西域之热情逐渐被消解,或曰,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敦煌的地位从未受到影响,甚至半点动摇,敦煌是战略支点,是补给站,是门户,是通道。东汉经敦煌对西域的经营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与北匈奴争夺伊吾、车师地区及北新道的控制权,第二,经敦煌对鄯善、于阗、莎车等南道诸国的经营,第三,经敦煌对焉耆、龟兹、疏勒等北道诸国的经略。诚然,没有敦煌就没有后方,没有敦煌就没有依靠,离开敦煌,西域与中原就难以沟通,所以敦煌之地位可想而知。其实,那时的敦煌不是后人眼中的边远小城,而是帝国之前哨,更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由此,那时的敦煌人是非常受青睐的,因为他们是开风气之先的一群人,他们身处各种异质文化之中,他们最先接触到从西传来的各种异质文化,他们最先完成了异质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升华,当这些拥有异质文化的人进入中原之时,他们又将早已融合在体内的蛮夷戎狄风气引入中原,而这些所谓的异质文化、蛮夷戎狄之风,恰恰是新鲜空气,恰恰是打破平静湖面的层层涟漪。
总之,《敦煌通史(两汉卷)》一书充分利用传世文献、敦煌文献、简牍碑铭等各类资料,细致考究了两汉时期敦煌的建置沿革、职官体系、军事制度、重要事件等相关问题,厘清了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两汉时期敦煌历史的整体面貌,在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新境界上迈出了稳健的一步。当然,《敦煌通史(两汉卷)》虽然提出并解决了很多新问题,但也仍有很大的继续开拓空间,某些问题甚至可以再次引起新的学术研究热潮。如东汉经略西域、发展敦煌的状况,确有诸多不清楚的地方,而限于史料,很多问题只能猜测,随着出土文物文献的大量涌现,很多问题绝对还可以继续深入考究。此外,古人和现代学者对中国古代西域治理得失的判断都反映了各自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深入分析历史情景下古人的成败认知和现代观念中的得失判断,定能从中发掘出有益于现代中国边疆治理的思想内涵,可以为现代中国边疆治理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