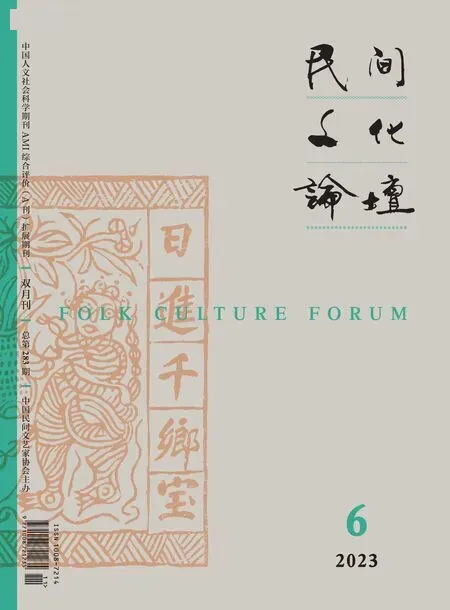蒙古恶魔蟒古思形象的演变
陈岗龙
一、多头一体恶魔蟒古思
蒙古人最熟悉蟒古思(Manggus,Manggas,Manggadhai),蟒古思是蒙古英雄史诗和英雄故事中的可怕敌人,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头一体,头颅从十二颗到九十五颗,甚至几百颗。头越多,蟒古思的力量就越强大,对人类的危害就越大。蟒古思喜欢抢劫人口,占领草场,吃人饮血成性。在史诗《格斯尔》中,抢劫格斯尔的美丽妻子茹格姆高娃的就是长着十二颗头颅的蟒古思;在卫拉特蒙古史诗《江格尔》中,经常来侵犯江格尔故乡北方的宝木巴国的也是各种各样的蟒古思,江格尔和他的勇士们出征作战的对象也基本上都是这些可怕的蟒古思。蒙古英雄史诗的战争主题基本上都是英雄与多头恶魔蟒古思浴血奋战。在很多史诗中,英雄不在家的时候,蟒古思趁机洗劫英雄的家乡,抢劫英雄美丽的妻子,奴役英雄的父母和人民,抢走英雄的牲畜和财产。于是英雄为了拯救人民和财产,备马出征,到蟒古思可怕的国度,通过浴血奋战,最终打败蟒古思,砍尽蟒古思的头,而且最终彻底消灭蟒古思的灵魂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救了自己的亲人,也没收了蟒古思的财产,凯旋回家乡。
关于蟒古思的形象,长久以来学者们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蟒古思是可怕的自然灾害的象征,有学者认为蟒古思的多头是古代北方民族首领戴的头饰,象征其力量和权力。在《蒙古族文学史》等著作中,在起初的时候,蟒古思的形象“接近蟒蛇和几种猛兽的综合,后来愈来愈接近幻想中的魔鬼,比如有十五颗头颅、十八颗头颅……”①荣苏赫、赵永铣、梁一儒、扎拉嘎主编:《蒙古族文学史》(一),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50 页。。著名蒙古史诗专家仁钦道尔吉认为,“蟒古思形象是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起初在传说中蟒古思是自然界凶禽猛兽的象征,后来又有了杀人刽子手和敌对氏族的象征。”②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97 页。而我们从蒙古英雄史诗的内容来看,蟒古思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多头一体”,头越多力量越大,这种形象与其说是自然属性的恶魔,不如说是人文的恶魔。据相关学者研究,原始蒙古史诗中的蟒古思更多的是一种不可抗拒或者难以抗拒的可怕的自然力的象征,和萨满教的自然崇拜有密切联系。到了部落时代和封建时代,蟒古思的形象已经不再只是代表自然力、不再是简单的毒蛇猛兽,而是有了社会属性、人性。蟒古思的社会属性表现在:蟒古思抢夺财富、抢夺美女;蟒古思与英雄较量时也会使用人间的兵器,比如弓箭等;蟒古思也有自己的家庭与社会组织,蟒古思一样有和人类相似的生理需要;蟒古思的思维方式与人类相似。由此可见,蟒古思已经成为某种事物的代名词,而这种事物,应该就是敌对的部落。
我们潜心研究后认为,蟒古思就是对草原上游牧民族中与英雄作战的敌对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妖魔化的形象。也就是说,蟒古思的多头实际上代表着组成部落联盟的许多部落,这些部落的数量越多,形成的部落联盟的力量就越大,他们就四处去吞并其他弱小的部落,而英雄史诗演唱的就是英雄为了维护自己的部落而与可怕的蟒古思战斗的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而且蟒古思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蟒古思的多头中有一个是核心,更多的情况下蟒古思的灵魂还藏在别的地方。因此,如果英雄不消灭蟒古思的灵魂,即使砍掉蟒古思的头还会很快长出新的头来。这实际上就是说英雄如果想摧毁敌人的部落联盟,一定要彻底消灭部落联盟的核心,否则很快会形成新的部落联盟再次威胁英雄的家乡。面对多头恶魔蟒古思,英雄增加力量的方式就是英雄在去往蟒古思住地的途中不断遇到被蟒古思打败的英雄,这些英雄成为史诗主人公的助手,大家一起去打蟒古思。这实际上就是史诗主人公在和蟒古思——敌对部落联盟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团结了被敌人打败的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用共同的力量去对抗敌对的部落联盟。因此,在蒙古英雄史诗中,以史诗主人公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是勇士们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主动投到英雄的旗帜下来的,而蟒古思所代表的部落联盟则是异化的,被妖魔化的部落联盟。这里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身份认同,那就是“我们是正常的人类,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是非人类”,因此侵犯“我们”的敌人就成了可怕的“非人类”的多头恶魔。其实,这种思想和中国古代的“东夷北狄南蛮西羌”的观点是一样的。由此可见,蟒古思就是蒙古英雄史诗中侵犯英雄的家乡,抢劫英雄的人口和牲畜、财产的敌对部落及部落联盟。英雄史诗就是讲这种英雄战胜敌对部落(部落联盟)——蟒古思的战争故事。
史诗的流传,主要借助于口头传承。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比较特殊的流传方式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特殊性。说唱艺人在讲到敌人的时候,往往不会将众多的敌人一个一个的具体描述,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敌人合在一起,整合为一个“个体”进行塑造。比如中国的评书,事实上战争胜负不仅仅只是由将领之间比武决定,而评书却就将其简化为将领之间的较量。这和史诗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蟒古思与萨满教神灵
古代镇压蟒古思的神话和史诗反映了蒙古先民战胜自然灾害和与其他氏族、部落之间进行的战争。这种题材基本上是在阶级出现以前的氏族社会形成的。而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世纪以后的蒙古史诗中的蟒古思形象也有了新的特征和含义。蟒古思除了原始蒙古史诗中描述的多头特征外,还有了骑骡子或毛驴,并在脖子或腰间缠绕毒蛇的形象。同时,蟒古思的社会性加强,有了子女亲属和自己的喇嘛。脖颈或腰间盘缠毒蛇的多头蟒古思骑着一匹骡或驴的描述已成为很多英雄史诗中蟒古思形象的固定描述。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蟒古思的形象和蒙古萨满神歌中的描述具有相似之处。如一首蒙古萨满神歌中将萨满神灵布哈诺颜描述为带着装满人肉的口袋、脖颈和腰间挂着花蛇的形象。另一首萨满神歌中将神灵“达延德尔黑”描述为:“专食人肉,长有石头心的,手持火蛇的鞭子,骑着疯狂的狼”的可怕形象。①[蒙古]呈·达木丁苏伦编:《蒙古古代文学精华一百篇》(蒙古文),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与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年,第128 页。而且蒙古萨满教中的汗古吉尔腾格里被描述为:“你吞食炽热的火焰,你以火蛇作手杖,以疯狼为坐骑,以人肉为美餐。你具有铜石之心,你偷偷地靠近,如同狼潜伏一般,你像狼一样吞噬。”②[意]图齐、[德]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耿昇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429 页。蒙古萨满神话和神歌中对一些山神的描述基本沿袭了上面的这种模式。蟒古思带着装满人肉的皮口袋和脖颈、腰间盘缠毒蛇的形象和萨满教的山神和其他厉神的形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很有可能史诗中的蟒古思形象受到了萨满教山神和其他厉神形象的影响。山神和厉神的装满人肉的皮口袋实际上是萨满教祭山和祭神仪式当中的血肉牺牲的象征,而其身上盘缠的毒蛇和手持火蛇,则与萨满的神鞭和蛇的象征有关。同时,佛教护法神也以毒蛇为标志,并且有更多的象征意义。我们认为,萨满教的神和厉神被贬为蟒古思,可能与佛教和萨满教的斗争有关系。因为,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初期,用其密教的咒术征服了蒙古地区的各种各样的萨满教神灵,其中包括地方保护神——山神。
几乎所有蒙古国和内蒙古流传的短篇史诗中蟒古思的新特征是增加了蟒古思喇嘛。他一手拨着怪石穿成的念珠,一手敲着公牛皮鼓,嘴里恶狠狠地说着诅咒。但是,蟒古思喇嘛在史诗故事中不起重要作用。史诗中蟒古思喇嘛的功能仅仅是为蟒古思祈祷而已。英雄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消灭这个恶魔喇嘛。而在蒙古史诗中,挺着蒙古包一样大肚子的蟒古思母亲也被描述为敲着公牛皮鼓,拨着怪石念珠。挺着大肚子的黄脸妖婆,手里拿着一串怪石念珠,乱拨个不停,并说:“不闻唐古特的语言,不见无用的敌人,不闻蒙古的语言,不见固执的敌人。”史诗专家们认为,蟒古思喇嘛的形象是从萨满演变而来的。英雄往往艰难地战胜蟒古思喇嘛才能最后取得消灭蟒古思斗争的胜利。
蟒古思一般居住在不吉利的东北方,那里有七座“妖都尔(yodur)”山,或者不吉利的三座山旋转不停,或者三棵“妖都尔”树根须相连。“从不吉利的七座山下面,从不吉利的七棵树上腾起蟒古思袭来的烟尘。”这“妖都尔”树就是蒙古地区人死后安葬时插的坟头杆。有的蒙古地区在举行野葬时,在尸体的西北方向插上一根“妖都尔”树,树顶有象征箭头的三角形,两边挂象征日、月的圆形和半圆形。而蟒古思的居住处以此树为标志,无疑蟒古思的住宅与坟墓有关系。而且,蟒古思都住在三座山,更多地是住在七座山底下。据蒙古国神话学家杜拉姆的研究,数字“七”象征死亡和毁灭,数字“三”多与天有联系,而“七”则关系到下界。蟒古思盘居的地方的景色更是令人毛发悚然,长嘴的山直张嘴,长牙的山直龇牙,长尾的山直甩尾,长影子的山直倾斜,狼嚎狐叫直刺耳,是一个不见日月,没有信仰的鬼地方。这里指的“没有信仰”,就是指蟒古思的地方没有信仰佛教。佛教中把佛法比喻为“日月”,信佛的地方就会有日月遍照世界。蟒古思住的地方不信佛,自然就没有象征佛法的日月照耀大地了。而各种怪山奇石无疑是比喻萨满教的精灵鬼怪,因为在萨满教信仰中神山崇拜具有突出的位置。由此可见,蟒古思妖疆景象的描述是象征性的,并与英雄宫殿和家乡的描述互成美和丑的鲜明对照。这里要提到的是,蟒古思往往以“青铜”为自己的象征。蟒古思妖疆的花草是青铜,城堡是青铜,蟒古思母亲或妻子肚子里出来的小蟒古思也具有青铜身躯。这是对古代青铜器时代的一种回忆。随着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的和高贵的金银器具被英雄和佛教所拥有,而落后的和原始的青铜器就留给了蟒古思和萨满教了。
三、蟒古思与佛教护法神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许多民间艺人会演唱蟒古思好来宝《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是晚期东蒙古英雄史诗中典型的蟒古思形象。这个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是从山中自然生成的。钢铁铸成的山裂成了两半,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从山中蹦出来,一跃跳到云端,再从天上落到地上。大地凹陷过膝盖。可见蟒古思的巨大。长着一副彤红的脸,红铜的血盆大嘴扭曲得有些变形,杂乱无章的红头发盘拧在额头上。嘴里喷出魔法火焰,头上长着四支粗大的牛角,长着两只长长的驴耳朵,獠牙歪歪斜斜交叉在一起。头上竖立九缕绿色的鬃毛,额头上戴着用六颗头盖骨做的花环。鼻孔里散发着各种瘟疫,心脏里蕴藏着千病万毒。长着三只眼睛,四只手的指甲是钢铁的,两只脚的指甲是青铜铸成的并向内弯曲。肚脐上挂着青铜宝镜,肩膀上披着人皮做的上衣,四肢节节戴着金银珠宝的手镯和脚镯。披着女人皮做的披风,把两只手像飘带一样在胸前打结,把剥下来的血淋淋的头颅挂在右边的腋下。右手握着飞铁棍仗,下面的右手握着魔法绳索。左手持八节神秘武器,下面的左手中端着盛满鲜血的头盖骨,如果把血喷洒就会下起血雨,引起石头冰雹①笔者1996 年7 月也记录了扎鲁特旗道老都苏木说书艺人扎木萨演唱的《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好来宝。。
以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为代表的晚期蟒古思的特征与护法神的重要特征有了密切关系。我们就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形象和佛教护法神的造像学特征做一简单比较。第一,藏传佛教怒相护法神身体和脸庞的颜色以黑色、红色居多,其中最常见的是黑色和深蓝色,其次就是红色,这种红色被看作是“太阳升起时光芒照到巨大的红铜山上发出的光芒”。其中蒙古人最熟悉的红色护法神就是被称为“红色扎木苏荣”的大红司命主。此外,佛教舞蹈面具中红色面具也是人们比较熟悉的。而传统的蒙古英雄史诗中的蟒古思形象并没有特殊的颜色作为主要特征,这说明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脸庞的颜色主要来自于佛教护法神信仰。第二,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长着碗口大的三只眼睛,这是护法神最突出的形貌特征。护法神造像学文献中经常形容护法神“凸出的、血红的眼睛透出凶猛直视的神情,通常还能在其额头中央看到第三只眼睛”。第三,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头上有九缕绿色鬃毛,而且杂乱无章的红头发盘拧在额头上。有些护法神有九缕铁发,而更多见的则是班丹拉姆和大黑护法等著名护法神的头发都像燃烧的火焰。第四,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额头上戴的用六颗头盖骨做成的花环,实际上就是护法神的五骷髅头冠。佛教护法神造像学文献中,高级怒相护法神经常戴的头饰是用五颗骷髅装饰的王冠;一些地位较低的护法神头戴前面嵌有三颗或仅仅一颗骷髅的王冠。而我们一般看到的藏传佛教唐卡或者羌姆面具上的护法神头饰均为五颗骷髅做成的花环。第五,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鼻孔里散播着瘟疫,嘴角喷出火焰,也是佛教护法神的主要特征之一。许多护法神口中吐出“瘟病之气”。而更多的护法神则都在身上带着“瘟病口袋”。第六,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披在肩膀上的上衣是人皮做的,而且披风也是用女人的皮做的,还把两只手在胸前打结。大黑天神和其他几位著名护法神都用象皮作为背部的护甲;另外一些护法神用人皮做上衣。比如班丹拉姆女神化身之一班丹玛索杰姆的伴神黑色女神查贝拉姆就穿着用人皮制成的飘动的外衣。而且我们在班丹拉姆女神的唐卡上经常见到她身上披着人皮上衣,能够见到刚刚被剥下来的人的手脚。第七,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四肢上都戴着各种珠宝手镯和脚镯。许多护法神都戴手镯,这些手镯是用宝石、绿松石、金、银打制的,一些护法神的下肢上还戴有装饰的脚镯。如班丹拉姆女神手脚都装饰有镯子,脚上戴用铁制作的响脚镯。大黑护法神手上脚上都戴有手镯和脚镯串铃。八、传统蒙古英雄史诗中的蟒古思被形容为多头恶魔,而很少提到他们的多手多臂。嘎剌·达格塔日蟒古思长有四只手,而且每只手中的武器都和护法神的特征相吻合。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两个右手中的武器分别是棍杖和套索。护法神使用的绳索是用来束缚外道徒和伤人邪魔、或用来捕捉他们的“生命之息”和“生命之力”的工具。三叉戟是保护神经常使用的兵器之一,有时用金刚石或各色丝带装饰三叉戟。头盖骨碗主要是作为盛放供奉给怒相护法神的食物饮料等供品的容器。据说这些供品包括人血或“四种魔的血”“湿热的人脑浆和血”“乱伦猥亵之甘露”,还有珍宝、朵玛、刚刚挖出来的人心等。①[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20 页。
从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形貌特征确实与佛教护法神的造像学特征有着渊源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并不能与哪一位具体的护法神对号入座。也就是说,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身上具有佛教护法神的一般特征,但是他并不能等同于班丹拉姆女神或者大黑护法神。
那么,《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原型是如何从护法神造像学传到民间说唱中的呢?我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民间艺人从羌姆舞蹈表演中概括出护法神的主要造像学特征,将其改编演唱,从而创作了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形象。我们的依据是过去在蒙古地区寺庙中举行的一些佛教仪式活动经常被当作说唱艺人的演唱曲目在民间流传。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梭赞》(Sor-un magtagal),其中民间艺人用优美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喇嘛僧人毁灭恶魔的替身——被称为“梭”的面偶的壮观场面。而创作演唱有关寺庙佛教活动题材作品的民间艺人一般都是对寺庙中佛教活动比较深刻了解的人,甚至有的民间艺人本身就是喇嘛。因此,我们认为羌姆舞蹈中护法神和恶魔面具的形象和造型、寺庙中司空见惯的各种护法神唐卡和壁画中的造型可能就是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原型的来源。而且,笔者在民俗学田野调查过程中经常听到老艺人说寺庙中护法神殿里的各种面目狰狞的护法神原来就是蟒古思。
第二,从14 世纪开始蒙古族喇嘛文人翻译和创作了许多护法神仪轨经,在寺庙和民间广泛流传,这也可能给民间艺人的创作提供了蓝本和最基本的素材。如吐鲁番出土的蒙古文文献中就有《大黑护法赞》,是佛教护法神造像学的蒙古文诗歌文献,这种护法神仪轨经诗歌的传统在蒙古地区一直得到保留并发展。下面我们看一看《大黑护法赞》:
一面长出四手臂,三眼圆睁瞳孔红,
天生须发金黄色,锥牙利齿赛钢钉。
张牙舞爪白雄狮,当作耳坠挂右边,
上盘下旋花蟒蛇,当作耳环垂左肩。
嘛哈嘎剌显神通,嘶吼咆哮怒眼睁,
巍巍须弥山震颤,凶神恶煞胆飞魂。
嘛哈嘎剌显神通,威震天地遍宇中,
天龙诸神阿修罗,俯伏地下跪埃尘。①荣苏赫、赵永铣、梁一儒、扎拉嘎主编:《蒙古族文学史》(一),第618 页。
这些优美上口,格律严谨的诗歌作品本身就具有容易口头传承的潜力。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护法神仪轨经诗歌走出佛教寺院,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其片段为蟒古思形象提供了题材和素材。
除此之外,《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演唱曲调和羌姆舞蹈音乐旋律之间有相似的关系。譬如扎木苏演唱的《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的节奏非常短促,和东蒙古说书艺人最常用的战争场面的作战曲调很接近,甚至比它还快,这使人联想到羌姆舞蹈中护法神出场时的情景。在羌姆舞蹈中,每当有一位护法神出场时,音乐的节奏加快,在凶猛的音乐气氛中护法神的扮演者突然闯入场内,给人以护法神从天地的哪一个角落突然蹦出来的印象。而《嘎拉·达格塔日蟒古思》也是描述了蟒古思从山中突然蹦出来,并带着血雨和冰雹来到人间的突发情景。
上文我们提到,史诗中的蟒古思形象受到了萨满教山神和其他厉神形象的影响。山神和厉神的装满人肉的皮口袋实际上就是萨满教祭祀仪式当中血肉牺牲的象征,而其身上盘缠的花蟒蛇和手中的火蛇则与萨满的神鞭和蛇的象征有关系。同时,脖颈和腰间盘缠毒蛇也是佛教护法神的造像学特征之一。因此,萨满神歌中地方神灵的形象绝对不是纯净的原始萨满教神灵,而是萨满教和佛教护法神形象混合而形成的新的神灵形象。而这些萨满神歌则为蒙古英雄史诗提供了蟒古思形象的描述模式和诗歌程式段落。我们认为藏传佛教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不仅影响了萨满教的内容和萨满神歌,而且也影响了蒙古英雄史诗中的蟒古思形象。
结 语
蒙古人中的恶魔蟒古思最初是象征自然灾害和敌对部落的符号化人文恶魔形象,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头一体”。后来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随着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与佛教的斗争和融合,萨满教神灵和佛教护法神的形象特征融入蟒古思形象中,从而使得抽象符号化的蟒古思逐渐形成了具有各种强烈视觉元素的具象特征。
蟒古思(Manggus, Manggas, Manggadhai)是蒙古人最熟悉的恶魔,但是蟒古思与古代日本和古代中国的妖怪不同,其最突出的形象就是“多头一体”,而且具有抽象化和符号化的特征。最初的蟒古思是象征自然灾害和敌对部落的人文恶魔,头越多力量就越大,隐喻和代表了古代蒙古的部落联盟。蟒古思的妻子或者妖婆的形象起源于古老的大母神信仰,保留着明显的生育崇拜特征。后来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并与蒙古原始信仰萨满教的斗争和融合中,萨满教神灵和佛教护法神的形象从不同角度影响了蟒古思的形象,蟒古思形象于是发生了具象化演变,有了强烈的宗教艺术特征和视觉符号象征元素。随着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影响的深入,蟒古思的家族也逐渐发展壮大,不仅有配偶子女,而且还发展出蟒古思喇嘛,庞大的蟒古思王国成为蒙古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中毛骨悚然的恶魔世界。结合口头传统、宗教信仰和图像资料,探讨恶魔蟒古思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