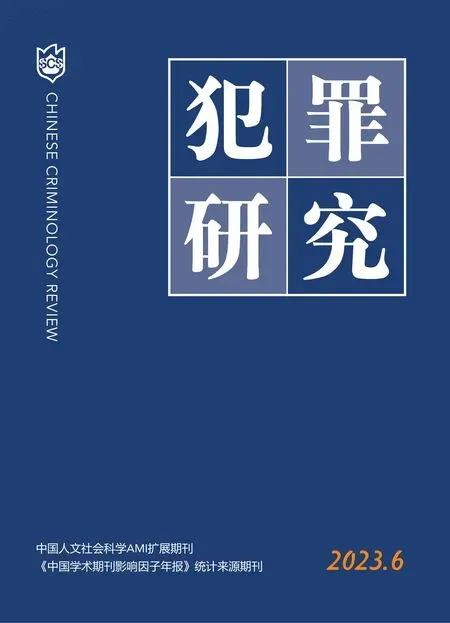袭警罪限缩适用论
张 杰
《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袭警罪迅速成为入罪大户。袭警罪的高发态势,直接导致我国轻罪犯罪圈扩大,袭警罪进而有沦为“口袋罪”之虞。(1)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1期,第28页。在此背景下,更需立足刑法教义学分析,从整体上讨论袭警罪的限缩适用,从而为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出路。为此,笔者试以袭警罪限缩适用为基本立场,论证袭警罪限缩适用的法理依据,并探讨袭警罪限缩适用的具体路径,以为该罪适用取得更好效果提出管见。
一、袭警罪的创设及泛化
(一)袭警罪创设的立法背景
《刑法》在1997年颁布时,并未对袭警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为加强对警察执法行为的保护,自2003年起,有人大代表等不断呼吁增设袭警罪。(2)参见霍志坚、张弘、谢佳:《全国人大代表林文、麦杰俊等建议刑法增设“袭警罪”》,载《人民公安报》2004年3月11日,第1版。在这些呼声的影响下,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77条增设第5款有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暴力袭警行为应当按照妨害公务罪处罚,可谓对袭警行为的提示性规定。2020年8月1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提出刑法修改建议,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单独设立袭警罪,以有力惩办袭警行为,维护警察执法权威。(3)参见赵克志:《国务院关于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2020年8月10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4期,第664页。在这一有力呼吁下,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出来,设立为单独的袭警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增设“袭警罪”的罪名,由此,我国《刑法》中正式设立独立的袭警罪。
相较于原《刑法》第277条第5款附属于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单独设立的袭警罪在内容上,区别于一般性袭警行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将“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严重手段的袭警行为予以单列,并规定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从重处罚规定。可见,《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罪予以单列时,特别关注了一般性袭警行为与严重暴力袭警行为的区别,对两者作出不同的处罚规制。
(二)实证分析显示袭警罪泛化适用状况
《刑法》单设区别于妨害公务罪的袭警罪,是保护警察正常执法秩序的需要,也是基于实践中警察执法过程易受阻挠甚至可能受到人身伤害的现状作出的立法回应。警察执法行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权利,因而对警察执法行为予以法律保护实属必要。但在如何保护的问题上,当然也需要作出分层处理。为此,我国在立法上对袭警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互衔接的规定。对轻微暴力袭警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同时规定了罚款、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对暴力袭警符合入罪标准的,《刑法》分别作出了一般性规定和从重处罚的规定。可见,袭警罪只应当对准行政处罚难以规制的严重危害警察执法、伤害警察人身权利的恶性行为。袭警行为入罪,存在“阶梯状”限制,如果对袭警罪的适用予以泛化甚至过度扩大,对公民与警察之间的轻微冲突动辄予以刑罚介入,则不符合我国法律对袭警行为分层处罚的规定,事实上不利于警察亲民法治形象的树立,最终也不符合警察执法维护权利、服务人民的宗旨。但是,实践中袭警罪恰恰存在泛化适用的状况。《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袭警罪迅速成为入罪大户。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办案数据,袭警罪独立成罪后的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17个罪名中,已提起公诉5568人,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罪名中排第一的即为袭警罪,为4178人,占提起公诉新罪名案件的七成。(4)参见《2021年1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载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2021年10月18日,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10/t20211018_532387.shtml#2。直至今日,袭警罪泛化适用的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仍未得到根本遏制。为进一步说明袭警罪适用情况,本文借助“小包公法律实证软件”,对2021年3月1日至2023年4月24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1210个袭警罪案件涉及的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透析袭警罪泛化适用的问题。
第一,袭警罪的暴力行为没有界限限制,入罪模糊。在1210个袭警案件中,近5成的案件并未说明被告人的暴力行为对警察造成的伤害情况。在有伤情说明的案件中,造成警察轻微伤的案件为大多数,占比达29.8%;造成警察轻伤的案件仅有18件,占比1.47%;另有174个案件明确说明被告人的暴力行为对警察的伤害未达轻微伤的程度,但法院判决仍认定构成袭警罪。由此可见,法院在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袭警罪时,并不对被告人所造成的伤害结果进行要求。可以说,实践中不以被害人伤害结果对暴力行为予以界限。换言之,暴力行为入罪标准存在模糊的问题。
第二,暴力行为的指向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界限不清。从案例上看,暴力行为既包括针对警察人身的暴力,也包括针对警车、警械等警用装备“物”的暴力。而直接指向警察人身的情形中,拳打警察、辱骂和踢踹警察是被告人最常使用的暴力手段,分别占比24.23%、20.11%和19.2%。而暴力指向警车、警械等警用装备的情形中,撕扯警服、破坏警车、驾车冲卡和抢夺警棍为主要方式,占比分别为51.04%、25%、13.54%和10.42%。可见,实践中对暴力行为指向的认定界限不清。
第三,暴力袭警的对象既包括警察,也包括辅警,过于宽泛。在1210个案件中,有632个案件存在被告人暴力袭击辅警人员的情况。其中,有7个案件的辩护人提出,辅警并不具备人民警察身份,被告人暴力袭击辅警不构成袭警罪。然而,此类辩护意见均未被法院采纳,证明司法实践对袭警罪中“警察”这一对象的解释存在扩张宽泛之势。
二、袭警罪限缩适用的根据
袭警罪泛化适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袭警罪的适用没有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而是过于将警察执法权力保护放置于重要位置,对袭警罪适用相对随意。而本文认为,袭警罪适用的基本立场应当是谨慎限缩。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论证:
(一)袭警行为具有应激反应因素
实践中,袭警行为存在暴力分层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所谓袭警行为就是轻微的拳打脚踢和辱骂行为。这些所谓袭警罪的发生情境,大多是社会治安纠纷的发生导致当事人处于情绪激动状态,一方报警后,警察出警予以调停。面对警察的出现,当事人认为事态升级,情绪更加激动,进而实施轻微的拉扯、撕咬、辱骂等行为。还原行为发生场景,这些所谓“暴力”大多属于特殊情境下行为人相对自然的应激反应。在心理学领域,这种应激反应,是指由于应激因子(stressor)对动物体的有害作用所引起的非特异性的一种紧张状态。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或其他高等脊椎动物在压力或紧急情况下(如生命受到威胁时),应激反应会引起血浆的儿茶酚胺类激素(主要是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浓度迅速升高,从而选择“要么攻击,要么逃跑”的行为。(5)参见许铁、张劲松、燕宪亮:《急救医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8页。这些行为的主观恶性明显小于大多数故意行为,与出于恶意蓄意伤害警察人身、恶意阻挠警察执法的行为存在明显区别。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状况以及行为发生时的客观情境,一般情况下袭警罪中的轻微暴力行为,应当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宜简单上升为犯罪予以刑罚处罚。
(二)袭警罪保护对象和处罚对象均显特殊
《刑法》针对特殊职业群体予以专门立法保护的,除军人外,只有警察。警察是和平时期牺牲人数最多的职业,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但是,袭警罪创设的目的是整体性地维护警察执法权威,而不是在个别化的情境下,对轻微袭警行为轻易介入、简单处罚,造成行为人及社会对警察职业的抵触。如果在轻微警民冲突中,对存在轻微滋扰行为的当事人,以批评教育为主,甚至能够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加以处罚的,则不使用刑罚介入,更能从根本上使民众发自内心尊重警察执法行为的正当性,同时也有利于刑罚处罚聚焦对准实质性干扰警察执行公务、蓄意伤害警察人身的严重行为,保证刑罚处罚获得更加普遍的公众认同。
不仅如此,袭警罪针对的对象更多是社会中下层普通民众。这些民众对袭警行为的严重后果往往缺乏更加全面准确的认知和理解,从法律上说,可谓缺乏违法性认识,因此对其予以处罚,更应当注意惩罚与教育相结合,防止矛盾激化。有关学者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在相关袭警罪样本个案中,多数袭警罪被告人的文化程度及收入并不高,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同时收入也相对较低。(6)参见李向玉:《袭警抑或自护:现代警务视角下袭警罪实证研究》,载《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第95页。对这些涉案人员,如果仅因为轻微暴力干扰行为即将其置于刑罚处罚境地,则更易沦入“不教而诛”的刑法适用非理想境地,只会弱化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更可能在特定情境下,煽动警察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甚至有可能累积社会戾气,导致民众与整个警察群体、警察职业的对立。结合两个方面,可以说,由于袭警罪保护对象和处罚对象均极其特殊,对这一犯罪的适用,应当极为谨慎,不可不用,但绝不可滥用。
(三)袭警罪涉及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界分
袭警罪事实上界分着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境域。警察负有侦查、缉捕犯罪嫌疑人等职责,最直接代表着国家公权力。在警察与公民之间,警察毫无疑问属于相对强势的一方。而且,法律还赋予警察在执法时的防卫权,如《人民警察法》第10条赋予警察在遇有严重暴力行为和紧急情况下,可按规定使用武器的权力;第11条赋予警察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可按规定使用警械的权力。与之相对,在涉及袭警罪适用的问题上,“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7)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第52页。,袭警罪适用范围的扩张体现了“警察公务保护和国民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8)张开骏:《公务保护与人权保障平衡下的袭警罪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第1523页。。如果对袭警罪的入罪范围划定过于宽泛,可能意味着警察权的过度扩张,更易对公民权利过于压制,不符合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发生矛盾时适当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的现代国家法治原理。换言之,为避免刑法沦入“强势者刑法”(9)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的误区,不能不对袭警罪的适用持更为限缩谨慎的态度。
(四)袭警罪处罚需贯彻刑法宽容理念
事实问题往往可以从价值角度得到更清晰的审视。“法学研究总是穿梭于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事实视角的法学是狂热的,而没有价值视角的法学是冷冰冰的。”(10)李其瑞:《法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3页。对袭警罪这样涉及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界分的犯罪,如果在刑法价值层面对其予以审视,并对不同行为类型作出分层划分,不仅能有效收缩犯罪圈,促进刑罚适用的谦抑,而且更能渗透体现刑法宽容的价值关怀。刑法宽容,其基本含义便是“刑律的宽免”(11)蒋海怒:《宽容:在人性比较中透析》,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11期,第 17 页。。日本学者大谷实教授认为,即使现实生活中已发生犯罪,但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对犯罪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因而不进行处罚的特性,被称为刑法的宽容性。(12)参见[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陈兴良教授在论述刑法的人道性时,提到了刑法宽容性的问题,并分析了政治宽容、道德宽容、宗教宽容与刑法宽容的关系。(13)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页。张智辉教授则提出,刑法宽和的核心是反对重刑主义,主张刑罚应当和缓,以便减少刑罚施用可能造成的损害。(14)参见张智辉:《刑法理性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邱兴隆教授认为,刑法宽容性是当犯罪人具有某种值得怜悯、同情的原因时,刑法应该对其具有某种宽恕的表示。(15)参见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秉持宽容的理念,对轻微危害行为入罪更需司法理性调节。在刑事司法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办理中,每次刑罚捶楚的落下,伴随的都是当事人及其家属痛苦的磨难。如果这一过程指向的是社会中极少数犯有较大恶行者,当然是社会正常代谢机制的体现。但是,如果频密刑罚处罚针对的是仅实施了轻微危害社会行为的较大群体,则刑罚施加的效果就值得商榷。更何况,网络时代下,刑罚负面效应更易聚焦和放大。在对轻微行为入罪群体性的关注和普遍性的否定中,与之伴随的往往是国家仁慈价值的削弱和社会凝聚力的涣散。故而对暴力相对轻微的袭警行为,国家不能不遏制处罚的冲动,防止刑事手段的轻启,更防止以刑法的简单介入掩盖复杂的社会治理。
三、袭警罪限缩适用的路径考察
袭警罪限缩适用,就是对袭警行为作出界分,将袭警罪的入罪范围予以严格限制,而对其限缩适用的具体途径,可以以法益定位为起点,从客观行为与主观目的等几个方面加以限制。
(一)袭警罪法益定位的聚焦
“构成要件形成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法益”(16)[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法益具有指导具体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的功能。袭警罪位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与妨害公务罪处于同一法条,学界对于该罪保护法益包含警察的公务并无异议。但是,由于袭警罪的行为方式为暴力袭击,往往会对警察的人身权利造成伤害。由此,警察的人身权利是否也应当成为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对此,学界存在“单一法益说”和“双重法益说”两种不同观点。
“单一法益说”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仅为警察公务,而非警察人身权利。这种观点是我国学界主流的观点。如张明楷教授认为:“本罪并不是单纯地对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实施暴力,而是指通过暴力袭警妨碍警察正在执行的职务。”(17)张明楷:《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5页。曲新久教授亦持“单一法益说”观点,认为刑法关于袭警罪的规定,其特殊性既不是由行为指向对象“人民警察”的身份所决定,也不是警察人身需要特别保护,而是由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性质决定。换言之,袭警罪是对于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保护,而不是对警察人身(权)、人身安全予以特别保护和宣示。(18)参见曲新久:《论袭警罪之“暴力袭击”》,载《现代法学》2023年第3期,第201页。李翔教授认为,将警察的人身权利作为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有违平等原则,难以协调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间的关系,会导致本罪的适用范围不当扩大。(19)参见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1期,第107页。刘艳红教授认为,从形式看,设立袭警罪保护的法益是双重的,即警察的人身安全法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法益;但从实质看,设立袭警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只不过行为人对公共秩序法益的侵犯,是通过侵害警察的人身安全进而妨害公务来实现的,(20)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1期,第23—24页。实质上还是贯彻单一法益说。当然,也有学者持双重法益说的观点,认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表现为国家正常管理秩序和人民警察的人身权益。(21)参见胡云腾、熊选国、高憬宏、万春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2版,第856页。还有观点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是“人民警察公务活动与人身安全”的复合。(22)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正案(十一)〉理解与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9页。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的分野,笔者持单一法益说。应当说从袭警罪在刑法中的位置、袭警罪设立的初衷以及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包含关系等,都可以看出袭警罪的法益为单一法益,即使对警察人身安全存在伤害的,也是因为这种伤害具有妨害公务的目的和指向才构成袭警罪,因而人身伤害应当服从于警察公务活动的法益,这是袭警罪与普通人身伤害犯罪的不同之处,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主张“双重法益说”的学者提出,贯彻双重法益说有利于袭警罪的限缩适用,这是因为,“如果对袭警罪采用单一的法益说,便意味着判断‘暴力’的实质内容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无论行为人采取何种行为方式,只要发生了阻碍人民警察执行公务的结果,都能构成‘袭警罪’,而如果根据‘双重法益说’,行为人除了导致人民警察公务活动受阻,对其造成的人身伤害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23)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3期,第96页。。这种观点所提出的通过“双重法益说”限缩袭警罪适用的目的是本文所赞成的。但是,对袭警罪的限缩适用,并不能反推出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为双重法益。这是因为:一是,人身权利与公务行为在袭警罪中具有表象与实质、方式与目的的关系。如果认为二者均是袭警罪的法益,可能导致袭警罪保护对象的偏离和涣散,甚至可能因人身伤害更易鉴定,造成对警察人身伤害的过分重视而对阻止警察执行公务行为本质的忽视,很可能导致实践中避难就易,将“人身伤害标准”予以泛化,只要对警察人身权利造成侵犯的,不论是对警察造成轻伤或轻微伤,还是对警察没有造成人身的实际损害而仅造成侵害威胁的情况,都纳入处罚范畴。如此,不仅不能实现限缩袭警罪适用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袭警罪适用的随意。相反,如果将袭警罪法益界定为警察公务活动秩序,即使对警察人身造成轻微伤害,但是不足以对警察执行公务行为予以阻止或妨害的,即不宜以犯罪论处,这样就对伤害行为及其性质、意义等作出实质判断,更有利于袭警罪的限缩。二是,如果认为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是单一法益,即仅为警察的公务,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是警察不是袭警案件的被害人,不能对法益作出让渡,也就不能接受犯罪人的赔偿。但如果认为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同时包括警察的公务和警察的人身权利,那么,警察的人身权利就是袭警罪的保护法益,警察就能够作为袭警案件的被害人接受侵害人的赔偿。对于袭警罪中警察能否接受侵害人的民事赔偿,这一问题较为复杂,但从袭警罪保护法益的角度,对警察接受侵害人的赔偿应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从实践情况看,袭警罪中,警察接受侵害人民事赔偿的情况较为常见。据笔者开展的调研显示,以北方某省会城市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26日妨害公务、袭警案件显示,全市办理的妨害公务、袭警案件中有约25.1%的案件存在赔偿情况,并且赔偿数额相差较大,大部分案件均在2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但也有造成民警轻微伤的袭警案赔偿金额达20万、10余万元的情况。从相关规定来看,2020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对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不适用刑事和解和治安调解。但是,《意见》同时规定,对于构成犯罪,但具有初犯、偶犯、给予民事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的,在酌情从宽时,应当从严把握从宽幅度。事实上,《意见》是认可袭警罪中民事赔偿的适用的。但是,如果从赔偿原理看,袭警罪侵犯的警察公务属于国家法益,如果将警察接受民事赔偿达成谅解作为从宽处罚的依据,就意味着警察能够代表国家对警察执法相关权益进行处分,对警察个人进行民事赔偿就能消解对警察执法行为体现的国家法益的侵害。这样不但不能维护警察的执法权威,反而会损害公权力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降低民众对警察执法的信任,从袭警罪保护法益的角度来看,似不宜提倡。
对袭警罪法益进行限缩解释后,可以对袭警罪入罪范围作出如下限缩界定:其一,应当区分个案不同情况对警务活动的价值位阶进行判断。不同的警务活动存在不同的价值位阶。在处理暴力袭警案件时,价值位阶的判断凸显重要。按照警务活动的紧急程度,一般可以将警务活动分为处置突发公共卫生、群体性甚至暴恐事件的紧急警务活动和履行行政执法活动、履行日常管理或公共服务职能等的一般警务活动。不同执法环境下发生的暴力袭警行为,秩序和自由价值何者应当优先保护,具有不同的位阶次序。例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或者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环境下的警务活动,维护秩序和安全是首要目标。警察在处理此类警务活动过程中,应当秩序价值优先侧重保护警务活动,即便警务活动履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瑕疵,也应当优先肯定警务活动的合法性。与之相对,在日常警务管理活动中,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与公民个人发生冲突之时,因相对公民个人而言,公权力处于更为强势地位,公民个人权利容易受到公权力的挤压,故更应当强调警察执法行为的程序正当性,优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以“盘查”为例,盘查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警察在开展盘查工作的同时必然会影响不特定公民个人的权利,故法律规定警察在执行盘查时应当坚持依法、文明、确保安全的原则。而依法原则要求警察在盘查过程中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合理怀疑标准”,不可任意为之,且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如果警务行为违反相关规定,随意对公民进行盘查,则应当优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故而在一般性警务活动中,对袭警罪的入罪范围应当持更加谨慎的态度。其二,应当分析警察执法行为是否存在严重瑕疵。如果警察执法行为本身存在瑕疵的,应根据瑕疵的不同程度将瑕疵执法区分为轻微瑕疵执法与严重瑕疵执法。在暴力袭击轻微瑕疵执法警察的情形中,如警察在抓捕嫌疑人时未出示证件、未告知身份、未告知相对人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等,可以导致行为人袭警行为构成犯罪,但应从轻处罚;在暴力袭击严重瑕疵执法警察的情形中,则应当慎重入罪。警察执法行为存在严重瑕疵,是指警察在具体执法程序或者方式上的瑕疵对诱发袭警行为起到支配性或者主导性作用。例如,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执法对象多次使用侮辱性语言,导致执法对象被激怒、失去理智而袭警,此时应当慎重认定暴力袭击行为构成犯罪。这是因为,袭警罪处理的是国家公权力和公民私权利的界分,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应当符合法治文明原则,与公民相比,警察在文明执法上负有更高的法律义务,执法对象对人民警察妥当行使警察权也抱有较高的心理期许。《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3条规定,“公安民警现场采取处置措施,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应当注意方式方法,避免激化矛盾”,即使是现场制止违法犯罪等重大紧急警情时,警察执法也要遵循文明执法原则。如果因为警察执法活动明显违反文明执法原则导致矛盾激化,进而产生暴力抗拒行为的,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应当谨慎。
(二)袭警行为中“暴力”的性质界定
袭警罪中对行为方式的法条表述是“暴力袭击”,实践中导致袭警罪适用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暴力袭击”的理解存在分歧。对袭警罪中“暴力”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界定。
第一,袭警罪中的暴力是否需要具有“主动攻击性”?对此,有学者认为,“袭击”的含义指突然打击,因而暴力袭击应限于积极地、突然地攻击警察的人身,如果对警察的攻击不具有突然性的,不能认定为袭警罪,确实妨害警察执行公务的,也只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24)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页。也有学者认为,袭警罪中的“袭击”是“暴力”的限定语,袭击的特点是突发性、瞬时性和意外性,因而袭警罪的暴力应限于突袭性暴力,不包括和缓及具有预见可能性的非突袭性暴力。(25)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1期,第15页。还有学者认为,暴力袭击具有主动攻击性的特征。(26)参见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79页;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1期,第105页。总体来看,无论立足何种观点,学界大多强调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主动攻击性,这也是笔者所赞成的。正因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需要具有主动攻击性的特征,如果行为人对执法警察的身体行使的有形力不具有主动攻击的性质,则一般不宜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例如,在警察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行为人出于本能实施了摆脱、挣扎的身体动作;又如,为摆脱警察控制、逃避抓捕而实施的甩手、蹬腿等挣脱行为,一般属于消极抵抗,由于不具有主动攻击性,因而不能认定为袭警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为了摆脱警察的控制而向警察的胸口猛击数拳的,行为人的暴力就具有主动攻击性,一般应当认定为袭警罪。
第二,袭警罪中的暴力是否需要达到“轻微伤”以上的限度要求?从限制袭警罪泛化适用的角度,对袭警罪中“暴力”的性质予以界定,更需要对“暴力”的程度予以限定,即袭警罪中的“暴力”是否需要达到“轻微伤”以上的程度。对此,实践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成立袭警罪不要求行为对人民警察人身造成伤害结果;(27)参见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83页。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就《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和适用中相关问题予以解答并提出:“对于实施暴力袭警行为,不能以是否造成民警轻微伤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暴力行为只要足以达到阻碍公务执行的程度即可,不要求造成人身伤害的结果。”(28)《最高检: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的立案标准如何把握等问题的解答》,载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167131,2023年7月28日访问。这一观点产生较大影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要求对警察人身造成轻微伤以上的后果。(29)参见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2年第1期,第110页;陈小彪、邓永凤:《妨害公务罪之袭警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58页。对于以上两种观点,从限缩袭警罪适用并结合考虑实践可行性的角度,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并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原则上应当至少造成警察人身轻微伤的后果,当然,即使造成轻微伤的后果,如果存在其他值得考虑的特殊情形的,也不一定作为犯罪予以处罚。这是因为:一是如果对“暴力”程度不作限度要求,不符合“暴力”的语义本义。一般认为,所谓暴力,是指使用物理性的强制力。由于袭警罪的实行行为是“暴力袭击”,因此对该罪中“暴力”的理解不能脱离“袭击”二字进行,而所谓袭击,则意味着暴力行为能带来一定的伤害后果,具有较为显著的侵害性。实践中,暴力正因为伴随突发袭击,才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对暴力袭击没有后果要求,甚至认为没有任何伤害后果也可以构成袭警罪,则明显不符合暴力袭击的语词本义,无疑会导致袭警罪适用的泛化。二是袭警行为存在不同的入罪阶梯,对于行为没有造成轻微伤的伤害后果,即使存在阻碍警察执行公务的性质的,因为警察相对于公民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也可以由警察在现场予以排除。即使需要施以处罚的,也可以由警察以治安管理处罚的形式予以处分,完全不必要在事后再以繁琐昂贵的司法资源予以定罪量刑,并导致刑罚负面效应的不当放大。
第三,袭警罪中的暴力是直接针对警察人身的暴力还是针对物(警用装备、器械)的暴力,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观点。《意见》第1条明确了下列两种情形属于“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一是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二是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根据《意见》的规定,对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进行打砸、毁坏、抢夺,应当与民警人身攻击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构成袭警罪。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答明确指出:“袭警罪中的暴力是指狭义的暴力,即仅指针对人身的暴力,不包括对物的暴力或者是通过对物的暴力间接伤害人身的情形。”(30)《最高检: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的立案标准如何把握等问题的解答》,载澎湃新闻网,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167131,2023年7月28访问。从前文所述“小包公法律实证软件”实证研究情况看,因对物(警用装备、器械)的暴力而被认定为袭警罪的情形实践中却大量存在。对此,笔者认为,对人的暴力肯定是“暴力袭击”中“暴力”的应有之义,但对物的暴力是否能够认定为暴力袭警,则需进一步探讨。例如,为了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行为人开车直接冲撞警车,其开车撞警车的行为算不算“暴力袭击”?对此,日本刑法理论通说与司法判例均赞同广义的暴力说,认为对人实行有形力和对物实施有形力但强烈的物理影响力影响到了人的身体的,都是暴力。(31)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6期,第9页。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暴力”范围的理解主要分为狭义的暴力说和最狭义的暴力说。狭义的暴力说认为当人民警察人身与物体结合时,对物实施的暴力直接作用于人民警察身体的,可认定为暴力袭击。(32)参见张开骏:《公民保护与人权保障平衡下的袭警罪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6期,第1527页;张永强:《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283页;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83页。最狭义的暴力说仅指积极对警察的身体实施的具有突发性的暴力(直接暴力)。(33)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6期,第11页。我国多数学者赞同狭义暴力说。笔者同样赞成这一观点,“暴力袭击”对象是“人民警察”,但当警察身体和物具有一体性时,直接作用于物就是间接作用于人身,对跟人民警察身体紧密相连的警车、警械实施暴力,其暴力后果可直接归结于人身,这种情况下的暴力就应当视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但是,当警察人身与警用装备分离的情况下,对警车等警用装备的攻击则不宜视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因此,“暴力袭警”包括对物实施有形力但强烈的物理力影响到了人的身体的间接暴力,但不应当包括单纯对警车、警用装备实施暴力的情形。此外,当对人民警察身体的作用力或影响很小时,单纯针对物(如警用装备、器械)的暴力,也应当排除在本罪的暴力之外。例如,打落执法记录仪、掀翻人民警察的帽子等,事实上不可能对警察的人身造成伤害,一般也不宜认定为袭警罪。
(三)袭警对象的限缩界定
人民警察的身份界定是判断是否构成袭警罪的重要标准,认定袭警罪应当准确限定“人民警察”的范围。我国当前由于警力不足及执法办案的现实需要,在处置警情时,很多辅警参与其中,由此导致袭警罪保护的对象是否包括辅警存在争议。
当前公安机关在工作中普遍存在辅警协助人民警察执法的现象,辅警在警务人员总人数中占有比率也不低。但是,《警察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法律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范围,且具有封闭性,无兜底规定,可见依据立法规定,辅警并非人民警察。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依法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主要包括文职、辅警两类从事警务辅助工作的人员。”这更可明确说明,辅警由公安机关管理,履行相关职责,但不具有民警身份,他们本身也不是执法的主体,不能独立执法,只能在民警的指挥下协助开展相应的辅助工作,比如盘问、检查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保护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等。
尽管如此,实践中对暴力袭击辅警是否构成袭警罪,还是存在很多争议,搜索相关案例,有构成妨害公务罪、构成袭警罪和不构成犯罪之争。笔者认为,对此可以分两种情况讨论辅警可否列入袭警罪的保护对象范畴。其一,警察和辅警共同执行职务。这种情况下如果暴力只针对人民警察,那么毫无疑问应认定为袭警罪;如果暴力只针对辅警,如前文所述,辅警没有民警身份,如果在执法过程中,民警在场,因为辅警的工作权限依附于民警的执法权,可以将辅警的执法行为理解为民警执法行为的延伸,此时行为人暴力袭击辅警,其行为针对的对象实际上是警察的执法行为,故以袭警罪评价更恰当。大多数袭警案件中,民警带领辅警出警处置警情时,行为人往往对处理警情的警务人员均有抵抗情绪,实施暴力袭击行为往往带有随意性。因此,我们无法要求行为人能够准确区分人民警察和辅警,对其来说,出警人员均代表国家公权力,所以即使是针对辅警的暴力袭击行为,也应当整体评价为袭警行为。其二,辅警在没有民警带领情况下单独执法。由于辅警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不能单独执法,因而辅警的执法实质上不具有合法性,如果发生纠纷,行为人对辅警袭击造成伤害结果的,不能够以袭警罪或妨害公务罪予以规制;如果构成轻伤以上后果的,则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四)袭警行为人主观状况的全面考察
刑法谦抑宽容理念表现在不是片面依据客观行为予以入罪,而是综合考虑行为人主观状况进行定罪。立足主观状态的考察,袭警罪“暴力袭击”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属于直接故意。袭警罪的法益在于对警察公务的妨害,因而其故意的内容,在于对自身行为具有伤害警察人身性质并通过伤害行为妨害警察依法执行公务行为性质的认知。如果行为人虽然具有阻碍警察执行公务的消极抵抗行为,但不具有直接故意伤害警察人身目的的行为,因不具有袭警性质,也不能认定构成袭警罪。
同样,就主观目的而言,如果行为人动机中不存在卑鄙恶劣的因素,不存在蓄谋伤害警察的故意,则可以对行为人予以适当宽宥。在对醉酒人员采取保护性措施过程中,醉酒人员实施的不针对特定对象的摆臂、挥手等行为,不应当视为暴力袭警。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是出于一时情绪失控、醉酒闹事等激情袭警,冷静或清醒后经批评教育往往能认识到自身错误,能够积极主动认罪认罚,对这种情况下的袭警行为,应当慎重入罪。
(五)袭警行为处罚后果的行刑衔接
为实现袭警罪限缩适用,应当重视发挥行刑衔接的积极效应。作为抗制犯罪的主要法律手段,刑罚兼具积极与消极双重效应。德国刑法学家耶林认为:“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34)转引自林山田:《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7页。对危害性较小的高发类行为慎重入罪,已成为各国共识。日本刑法学家西田典之认为:“对违反法规范行为的制裁范围应当限定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35)[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刑罚这种制裁具有强制力,由于它同药效大的药物一样伴有副作用(资格限制与作为犯罪人的烙印),判断以什么作为刑法的对象时,必须慎重考察对某种行为是否有必要动用刑罚来抑止。即刑罚是为了控制人的违反规范的行为所采取的‘最后的手段’。”(36)同上书,第23页。因而,对轻微的袭警行为,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代替刑事处罚的,不必一律以刑事方式予以处置。
对袭警行为予以分层处理是我国立法精神的体现。除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袭警罪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也规定了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行政处罚方式。按照袭警罪入罪限缩的要求,对于轻微暴力,如明显属于“抓扯、一般肢体冲突”,且未严重阻碍执法的袭警行为,一般不能轻易认定构成犯罪。即使实施了一定的暴力行为,但就伤害后果而言,对于造成民警轻微伤以下伤情的,也应当结合阻碍执行职务程度、民警执法规范性、行为人主观故意等进行综合评判,情节相对较轻的,也可认定不构成犯罪,而是予以行政处罚。对于造成民警轻微伤的,一般可认定构成袭警罪,但仍应当结合案发原因、阻碍执行职务程度,行为人是否为初犯、偶犯,是否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进行综合评断,符合条件且情节轻微的,可不作犯罪处理。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当实施袭警行为的为孕妇、未成年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时,入罪时也应当更加慎重,一般应当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总之,应当从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相结合的角度,根据主观恶性、危害后果、行为强度、行为人具体状况等因素,依照情节轻重对应治安处罚及不同的刑罚处罚措施,谨慎限制刑罚处罚介入,精准执法。在保护警察权威的同时,充分发挥行政处罚对刑罚的衔接、替代功能,注重发挥行刑衔接作用,能够用行政处罚替代的就不以刑事处罚进行处理,防止袭警罪被不当滥用。
四、袭警罪限缩适用的效果提升
(一)袭警罪限缩适用效果的预判
从实践案件发生情况看,袭警罪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并极易引发网络炒作的重点罪名。而受到网络炒作的袭警案件,往往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袭警行为人身份特殊,如妇女、老人、国家公职人员等。二是袭警行为人具有特殊的主观情况,如基于讨债、索要劳动薪酬等目的引发纠纷,在警察出警时实施袭警行为。(37)如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办理的杨某某袭警案中,杨某某从广州至苏州讨要货款,因与人发生争执,警察调解纠纷时,杨某某扇了警察一耳光,检察机关认定杨某某行为不构成袭警罪。参见苏园检刑不诉[2021]97号。三是袭警行为暴力程度极为轻微却被作为犯罪处理。四是袭警行为处罚标准不一,实证研究显示,当前对袭警罪特别是袭警罪中的“暴力行为”,各地区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导致袭警罪入罪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38)参见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3期,第95页。而网络传播中将东中西部不同地区案件对照,易产生行为类似、结论殊异的观感,进而引发网络媒体关注和炒作行为发生。
针对以上情况,为提升袭警罪案件办理效果,避免和减少网络炒作对法治的损害,笔者认为,当前总体上应当对袭警行为入罪采取限缩态度,谦抑谨慎动用刑罚对相对轻微、具有特殊情形的袭警行为予以处分,既能更好体现刑罚宽容理念的要求,又可有效节约司法资源。目前实践中大多数袭警行为主要是轻微暴力行为,通过法益限定及暴力程度、袭警对象等方面的限制,能够使袭警罪的入罪范围大为收缩,有力节省司法资源,防止袭警罪沦为新的入罪大户。以前述“小包公法律实证软件”实证研究选取的1210个样本案例为例,通过袭警罪的限缩适用,至少能够使174个未对警察造成轻微伤以上程度的袭警案件(占比15%)不再作为犯罪处理,从而有效压缩袭警罪入罪范畴。
(二)提升袭警罪案件办理效果的建言
社会转型期,袭警罪的认定具有敏感性,在慎重把握袭警罪入罪标准的同时,还应当多方合力,提升袭警罪案件办理效果。
第一,更加谨慎办理袭警罪案件。对于袭警罪这样高发多发,而发案具体情境、具体行为实施人千差万别的轻罪,如果期待以成文司法解释的形式,划定一条统一而又极为清晰明确的界限,不仅极为困难,而且很可能造成具体案件中适用效果的偏差。为此,对于袭警罪,更需要发挥司法一线智慧,在实践中总体把握限缩适用的案件办理思路。在该类案件办理中,应当务求各方面观点一致,社会充分认可。在具体案件中,更需要结合发案具体情境,贯彻宽严相济原则,准确把握和积极运用各类法定酌定从宽情节予以出罪化处理,尽可能避免刑法适用产生的消极负面影响。
第二,及时明确袭警罪司法适用标准。在谦抑谨慎的基本前提下,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发挥指导、领导司法业务,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功能和作用,积极推进该罪入罪标准的明确。当前在袭警罪的适用上,主要依据有《意见》以及2021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和适用召开专题辅导讲座,并针对相关问题予以解答。此外,各地还出台了一些办理袭警罪的指导性文件,如2022年2月25日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公检法办理袭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这些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或研究意见,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存在不一致之处,且《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袭警罪又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亟待最高司法机关适时总结实践情况,出台更高效力和更具权威的司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袭警罪中的问题予以进一步明确。但是,袭警罪案件发案率高,案件情况千差万别,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应当既具有相对的明确性,又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更多赋予基层司法机关结合具体案件把握实践、相对灵活处理案件的自由裁量权。为此,似更宜以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既发挥成文法条的稳定准确优势,又充分体现案例灵活及时、形象生动的特征,结合两者及时加强对下指导。
第三,结合案件办理发挥司法劝善止恶作用。刑罚的适用,不仅是对恶行的报应,而更应当是对非法行为的制止。“刑罚是预防犯罪的工具。”(39)[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Ι——犯罪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袭警罪刑罚的动用,不仅是对公民不当妨害警察执法行为的制止和惩罚,更是宣示社会,彰显警察执法行为尊严和不容亵渎的生动法治实践。为此,司法应当针对相当部分行为人实施袭警行为缺乏违法性认识的现状,履行司法办案执法普法相统一、治本治标相结合的职责,定期选取典型案例予以宣传公开,借此警示告诫社会,勿要践踏红线,尊重法治权威。
五、结语
人民警察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重要贡献不可磨灭。对暴力袭警、伤害警察人身、严重干扰阻挠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惩。但是,刑法从来都是法治社会不得已而用之的最后手段,刑法被称为“法治社会的吗啡”(40)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上)》(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意指其镇痛的特效和用之的极大负面效应。同样,对于袭警这样极为敏感而又涉及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界分的犯罪,刑法的介入不可不为,但更不可滥为,不能不持极为谨慎谦抑的态度。而司法中更应采取教义学的方法,对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加以限缩解释,防止其泛化适用。由此,以袭警罪的限缩谨慎适用,更能实现警察权的法治正当,更有利于和谐警民关系的建构,应为袭警罪适用基本之理。
——献给为战疫而奉献的人民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