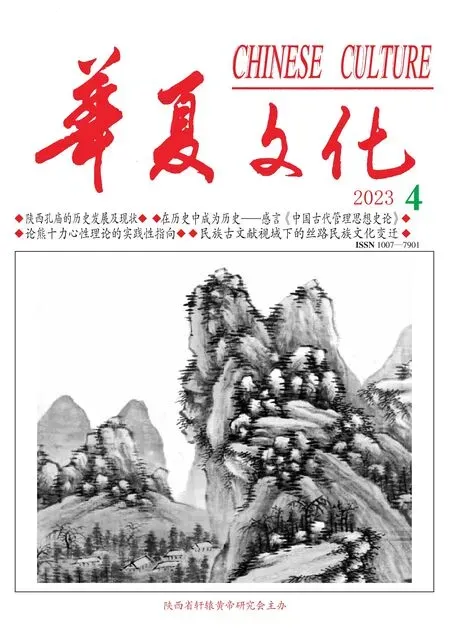《化书》死亡思想探究
□王世超
《化书》是五代时期道教的经典著作,通常被认为是道士谭峭所著。全书共分为六卷,分别是“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化书》中包含着丰富的死亡思想,谭峭一方面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死亡与“食”有直接关系,死亡只是道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死亡不是终结,只是“化化无间”中的一环。此外,还给出了“尚俭”的方法,希望能够契合大道超出生死。
一、认识死亡
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死亡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无数的先贤对此进行了探求与思索。关于死亡问题,谭峭一方面有着与他人相似的观念,同时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谭峭认为人是有着体悟生死的情感与能力。在《化书·仁化·畋渔》中明确指出了人禽之别,“夫禽兽之于人也何异?有巢穴之居,有夫妇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谭峭 著,李似珍、金玉博 译注:《化书》,中华书局2020年,第84页,后文对本书的引用只注明篇目)他认为人和禽兽的区别之一就是人有生死离别之类的情感。我们对于生存和死亡都有着自己的认识,也有着自己的情感,这是人与非人的区别之一。
其次,谭峭认为死亡是一种必然,无可避免。《化书》中有“天地盗太虚生,人虫盗天地生,营虰盗人虫生。营虰者,肠中之虫也,搏我精气,铄我魂魄,盗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见我之必死”(《天地》)的说法,谭峭认为天地是夺得太虚之气而生,人类则是夺得天地之气而生,营虰又是夺取人身中之气而生。营虰就是腹中的寄生虫,它窃取人的元精真气,销融人的魂魄,盗取人的美味食物,然后才有了生命。由此可知,因为营虰的存在,人的死亡是一种必然,无可避免。再者,谭峭还用了蚀木之虫的比喻来进一步阐释,“蠹虫蚀木,木尽虫死”(《天地》),死亡的必然就像是蛀虫蛀蚀木头一样,木头销尽了,蛀虫也就死亡了。除此之外,《化书·道化·死生》中也指出“万物非欲死,不得不死”,万物不是自愿去死亡,而是不得不死亡,死亡就像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恒常,无法避免也无法改变,万物从出生开始就向着死亡迈进。
最后,谭峭独特地阐述了死亡与食的关系。他认为“饮馔,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于亡身”(《天平》),饮食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但是如果吃的不得其法就会死亡。他认为死亡和食直接相关,食不得其法就会导致死亡。在《食迷》篇中他说:“民有嗜食而饱死者,有婪食而鲠死者,有感食而义死者,有辱食而愤死者,有争食而斗死者。”这里列举了嗜食而饱死、婪食而鲠死、感食而义死、辱食而愤死、争食而斗死,种种死亡都是由于食物的缘故。他还列举了“矫佞馋讟而律死”的官吏,“波涛江海而溺死”的商人。他认为官吏矫饰奸巧、馋间诽谤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俸禄,而拿了俸禄也是为了换取食物;同样,商人随货船奔波于江河湖海之间,也是为经营财物,财物积累到最后也是为了换取食物。他认为所有的死亡深究其原因最后都是因为食。再者,在《七夺》篇中更是直接点明“三日不食则死”,指出“不食”与“死”的直接关系。
谭峭关于死亡的认识阐述到此,下一步我们需要去探究的是在谭峭的整个哲学体系里,死亡是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他是如何在自己的体系里来安置死亡的。
二、以“道”论“死亡”
谭峭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他继承了道家老子、庄子的学说,秉承传统的道教理念,同时又依据自己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对“道”做了自己独特的阐释。在笔者看来,谭峭运用了“虚”和“化”两个概念很好地表达了他对“道”的理解。
“虚”在《化书》中有“太虚”“虚空”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虚”并不是虚无,而是有,“虚空非无也”(《龙虎》),“太虚之中无所不有”(《游云》)。在《道化》篇中,谭峭提到“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他认为世界起源于“虚”,然后又复归于“虚”。“道”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虚、神、气、形的相互转化,因为变化的顺序问题,从而形成了由虚到形的“道之委”和由形到虚的“道之用”。从“道之委”与“道之用”的顺序不难看出,“虚”不仅是万物的本源,同时也是万物的归宿,也即是“道”。用“虚”来规定“道”,突出“道”是本体而不是实体,“道”在本质上“虚”的,即是“空”、是“无”,而正是这种性质上的“虚”,才保证了“道”的本体性,才使它能圆融无碍地表现在“用”中,达到体、用一原。(参见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3页)
关于“化”与“道”的关系,明代刘达在为《化书》作序的时候给了很好的解释:“道在天地间不可见,可见者化而。化在天地间不可见,可见者形而已。盖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通过“化”表现出来,它们二者密不可分,“非道无以生化,非化无以显道。道之与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在《道化》篇中谭峭从“道之委”与“道之用”两个方面来说明了“道”与“化”的关系。“道之委”是道顺而产生万物的过程,“道之用”是道借助外化的万物返回自身的过程。也就是说,道是万物产生的本体和内在依据,通过道的变化作用,产生了有形之物,这是道的外在表现。
在谭峭的思想体系里,他运用“化”将“虚”“神”“气”“血”“形”“婴”“童”“少”“壮”“老”“死”串联起来,“虚化神,神化气,气化血,血化形,形化婴,婴化童,童化少,少化壮,壮化老,老化死。死复化为虚,虚复化为神,神复化为气,气复化为物”(《死生》)。生命源于虚,从虚无产生精神,继而产生元气、血液乃至形体,后逐渐演化为婴儿,逐渐成长,经历孩童、少年、壮年、老年,然后死亡。这一连串的演化就是“道”的体现。死亡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只是“道”在不同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就如《龙虎》篇所说的“其生非始,其死非终”,死亡也不意味着终结,死亡后又化为虚无,继而“道”又开始新一轮的演变,整个系统是一个“化化不间,由环之无穷”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生非始”“死非终”。
在《化书》中谭峭还表达了体道而出生死的愿景。在《铅丹》篇中说人只要能够与道达到相一致就能统一生死,就可以超出五行之外,不受三光的制约。《爪发》篇也有同样的说法,“达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在《虚无》篇中也提到了“志于虚无者,可以忘生死”。他希望能通过一定的方法去体悟大道,然后和道达到一致,跳出化化无间的循环过程,超脱于外。
三、出生死之外
谭峭认为要去体悟大道,与大道齐同,需要“忘”。在《道化》篇里,他说:“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忘却有形实体去孕育元气,忘却元气来孕育精神,忘却精神来孕育虚无,虚无与真实互相通畅就叫作与大道融为一体。这里的说法与《庄子·大宗师》中的坐忘较为相似。庄子认为想要做到“坐忘”,就需要“忘仁义”“忘礼乐”“堕肢体,黜聪明”,遗忘肉体的自我,舍弃掉因为欲望而产生的“聪明”,让精神“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谭峭正是对“坐忘”思想的延续,他主张忘却形体,忘却元气,忘却精神,以精神来养道,最终要达到“大同”的境界。
谭峭认为万物的大道都有“一”,“万道皆有‘一’”(《御一》),但现实中因为种种原因而迷惑、困惑,“迷其要”“惑其妙”,导致不能把握它,故而要抱守“一”的大道就只能运用“俭”,“议守‘一’之道,莫过乎俭”。关于俭的具体含义,谭峭在第六卷《俭化》中作了大量说明。在《太平》篇中,他认为俭就是用之得其道、节制不奢淫以及均食。在《礼道》篇中提出“礼贵于盛,俭贵于不盛;礼贵于备,俭贵于不备;礼贵于簪绂,俭贵于布素;礼贵于炳焕,俭贵于寂寞”。俭也就意味着“不盛”“不备”“布素”和“寂寞”。在《雕笼》篇中提出俭就是“不取”的看法。在《礼要》篇中提出俭就是少和小。在《清净》篇中,将俭与静相联系,认为俭就是“静”“易”“简”“恬淡”。在《损益》篇中提出俭就是“损益之道”。谭峭还规定了“俭”的范围,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一方面,他认为“俭”需要从物质入手,像水火、饮馔、礼乐;另一方面在视听言说及心思之类也需要俭。而且他更强调俭的后一部分,在《化柄》中他说:“俭于听可以养虚,俭于视可以养神,俭于言可以养气……俭于心可以出生死。”
谭峭认为要做到“俭”应该要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在《权衡》篇中,他用“服絺绤”和“衣之布帛”、“食藜藿”和“饭之黍稷”、“负石”“负涂”“负蒭”进行对比,提出“饥寒无实状,轻重无必然,皆丰俭相形,彼我相平”,认为饥饿和寒冷没有具体的形状,轻重也没有具体的标准,都是以节俭和丰富进行比较,先改变自己的观念然后评判自己的处境,在俭朴中去追寻“道”。其次,谭峭认为要遵循“俭”的原则需要破除心理上的攀比心态。在《食象》篇中,他提到“观食象者食牛不足,观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正是由于各种攀比与不平衡,才会产生诸多的贪心与不满,进而愈发偏离“道”的路径。最后则提到“俭”需要身体力行。“有宾主之敬,则鸡黍可以为大享,岂在乎箫韶也。有柔淑之态,则荆苎可以行妇道,岂在乎组绣也”,只要践行“俭”的观念,行动到位,哪怕没有外在的形式,也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化书》中,谭峭为了进一步说明“俭”的可行性,给出了两个说明。其一是悭号者的例子,“世有悭号者,人以为大辱,殊不知始得为纯俭之道也。于己无所与,于民无所取。我耕我食,我蚕我衣。妻子不寒,婢仆不饥。人不怨之,神不罪之”,他认为这个悭者正是把握了大道。其二则是认为文饰无用,“乳童拱手,谁敢戏之?岂在乎黼黻也”,乳童只要是拱手行礼了,又有谁在乎是否穿着华美礼服呢,华服无用,何不舍弃从而践行“俭”的观念呢?
最后,回到整个《化书》的篇目结构上来看,全书分为六卷,分别为“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正如明代刘达的序里所说,“道不足,继之以术;术不足,继之以德;德不足,继之以仁;仁不足,继之以食;食不足,继之以俭。其名愈下,其化愈悉。”如要把握“道”还是当从最详细的“俭”入手,从“俭”而知“食”“仁”“德”“术”,进而知“道”。
四、结语
《化书》的重心并不是去探讨生死问题,然而在其中提及的死亡思想也是去呼应他关于“道”的主题的,无论是以“道”论生死,还是最终寄希望于“俭”能超出生死。死亡问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谭峭死亡问题的探寻可以以小见大,从某一方面入手更好地去理解《化书》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