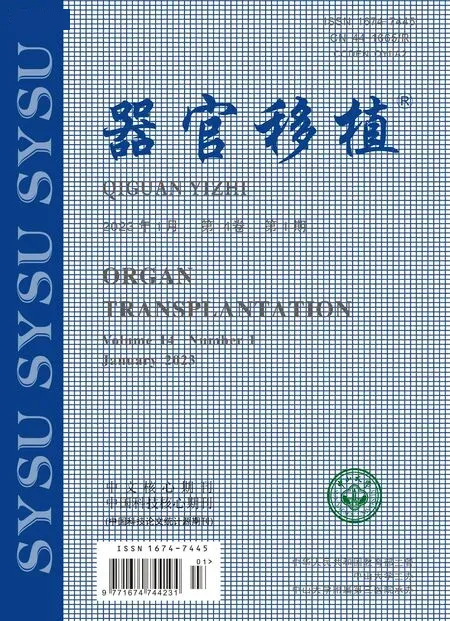心脏移植的发展现状和新挑战
陈良万 李虔桢 戴小福 方冠华 丘智煌
自1967年南非医师Barnard完成了人类首例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手术后,心脏移植逐渐成为终末期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1]。根据2019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ISHLT)的数据,欧美的心脏移植受者的总中位生存期为12.5年,首年存活受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4.8年[2]。心脏移植可以显著提高终末期心衰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目前,全世界每年进行的心脏移植手术超过5 000例。尽管数字令人鼓舞,但挑战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供者数量不足,受者年龄更大、病情更复杂,排斥反应和晚期同种异体心脏移植物血管病变(cardiac allograft vasculopathy,CAV)等。本文将对心脏移植领域面临的这些挑战和其新进展进行集中讨论。
1 心脏移植供者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年龄<45岁、没有合并症(高血压、糖尿病)、无左心室功能障碍、缺血时间<4 h的供者心脏进行移植。然而,供者不足一直以来都是限制心脏移植数量增长的主要问题。虽然器官捐献者的数量在增加,但仍然远远无法满足心脏移植的需求。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引入,供者池被不断扩大,比如使用年龄较大的供者、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的供者、毒品过量致死的供者或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者的心脏等。供者保存技术的改进也有利于提高供心的利用率,恒温储藏和离体心脏灌注技术也被用于远距离供者的运送。
1.1 供者的年龄和合并症
2020年ISHLT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捐献者的中位年龄仍然呈增加趋势,在欧洲更加明显[3]。这一增长很可能是总人口老龄化、捐献器官短缺以及随着时间推移捐献者死亡原因变化的结果。供者年龄的增加与受者死亡风险较高(尤其是30 d内的病死率)相关[4]。供者年龄<35岁的受者,其1年生存率较供者年龄>50岁的受者增加约10%[3]。Jawitz等[5]在对2008年至2015年美国器官资源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UNOS)数据库的分析中发现,当供者年龄>40岁时,死亡风险随着供者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未发现供受者间年龄差异的相互关系。虽然心脏移植的指南指出对高龄供者心脏的应用要谨慎,但指南上并没有提出详细的指导意见。原则上,左心室功能正常、合并症较少的供者来源的心脏可能与较低的围手术期风险相关,缩短供心缺血时间可以降低供者年龄增长所带来的风险[4-5]。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供者疾病谱的改变,合并高血压或糖尿病供者的比例也在增多。患糖尿病的供者比例从1995年的1.1%增加至2018年的4.5%,同一时期患高血压的供者比例从9.3%增加至17.4%[3]。Stehlik等[6]分析了ISHLT的7 322例心脏移植病例后发现,糖尿病和高血压会增加受者的远期病死率(仅限于男性供者,女性供者样本量太小)。Goland等[7]也发现当供者合并左心室肥厚和高血压时,受者的远期生存率会更低。当然,也有些研究者发现[3],当供者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时,受者的1年生存率较低,但是差异较小。当供者合并糖尿病时,受者的1年生存率为87.7%,而供者无糖尿病时受者的1年生存率为88.5%。笔者认为,高血压或糖尿病是否作为排除供者的主要标准存在争议,需要充分权衡供者的危险因素和受者在等待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病情恶化甚至死亡风险之间的矛盾。
1.2 HCV感染供者
受者在接受HCV阳性供者心脏后往往会更早出现CAV且生存率相对更低。随着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出现,通过耐受良好的口服治疗,HCV治愈率高达95%。抗HCV治疗的进展使得以前因HCV感染而常被弃用的供者得以重新被利用。通常有两种主要的治疗策略:一种是泛基因型药物方案,即从围手术期开始应用索非布韦和维帕他韦4周或格列卡韦和吡溴那韦8周进行治疗[8];另一种是受者在确定有HCV感染后开始治疗,应用索非布韦和维帕他韦12周或格列卡韦和吡溴那韦8~12周[9]。相关的文献表明,HCV阳性供者心脏与HCV阴性供者心脏在植入受者后的1年随访结果相似[10],但HCV与免疫激活、排斥反应和CAV长期结果的关系目前仍不确定[11]。从2016年至2019年,HCV阳性供者比例从0.6%上升到11.5%[12],这一差异显示了目前扩大供者库的一个潜在领域。另外,在评估供者HCV感染时,必须区分抗体状态和核酸检测状态。例如,HCV抗体阳性但核酸检测阴性、以前可能接触过病毒但没有活动性感染的供者风险较低,而核酸检测阳性供者有活动性病毒血症,传播给受者的风险最高[13]。
1.3 毒品过量致死的供者
1999年至2017年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OPTN)数据的分析显示,因毒品过量导致死亡的供者比例从1.5%上升到17.6%[14]。由于担心吸毒者之间有HCV、乙型肝炎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传播,术者经常不愿意使用这类供者的器官进行移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供者通常比较年轻,而且很少或没有合并症,对现有的有限供者池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重要补充[15]。ISHLT数据显示,因可卡因死亡的供者心脏植入后受者的1年生存率与未吸毒供者心脏植入后受者相当;同时,因非静脉注射毒品(如大麻或处方药、镇静剂、催眠药或兴奋剂)的供者心脏植入后受者的1年生存率稍高于未吸毒供者心脏植入后受者(90.1%比87.8%)[3],这可能是因为吸毒致死的供者往往年龄更小,合并症更少。Vieira等[15]分析ISHLT数据时也发现,受者接受有吸毒史供者心脏后,10年死亡风险并没有增加。
1.4 循环死亡的供者
首例人体同种异体心脏移植的心脏即是来自与受者相邻手术间的DCD供者。事实上早期几乎所有心脏移植的器官都是来自DCD供者[16-17]。1968年后,美国通过统一死亡判定法,允许不可逆的、完全的和永久性脑损伤患者进行器官捐献,他们被指定为脑死亡器官捐献 (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者。之后人们更倾向于选择DBD供者的心脏进行移植,因为搏动的心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组织缺氧,同时获取前可以对供者心脏进行评估。近年来,由于创伤性脑损伤和颅内出血治疗的进展,符合脑干死亡标准的患者数量有所下降。为了维持和扩大心脏移植的数量,一些术者开始考虑重新利用DCD供心。DCD器官是在循环停止之后进行获取的,其必然会经历一段热缺血时间,因此,DCD器官有可能由于缺血代谢物的积累而产生不可逆性损伤,而且这种损伤的程度往往难以准确评估。这种心肌损伤后存留活性的不确定性使得术者对DCD供心的临床后果充满担忧。因此,使用DCD供心进行移植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心的缺血损伤。
目前针对DCD心脏获取和转运主要有3种模式。第1种是来自澳大利亚的Dhital等[17]提出的直接获取(direct procurement,DP)-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的方法,即当循环停止后立即进行获取,而后将心脏连接至体外灌注装置,应用供者血液和专门灌注液混合后灌注心脏,使心脏复跳,再进行转运,复跳后的心脏可以进行实时的功能监测和评估。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心的缺血损伤,使供心可以进行远距离运送,更为重要的是在供心植入前对其功能进行监测和评估。该方案的缺点是NMP装置昂贵、成本高,同时缺乏适合的机器运输婴幼儿心脏。第2种方案是常温局部灌注(normothermic regional perfusion,NRP)- NMP的方法,即在循环死亡前即行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插管,在宣布循环死亡后开始转机,同时阻断头颈血管以阻止大脑的血供,当心脏复苏并脱离ECMO后,原位评估心功能,确定心脏可用后灌注心肌保护液,取下供心并放置在NMP装置上进行运输。这种方法同样减少了循环停止后的热缺血损伤,但除了高成本问题外,这种方法不能广泛适用的原因是有一些国家禁止对供者进行死前操作(包括使用肝素和ECMO插管)。第3种方法是NRP-静态冷保存(static cold storage,SCS)的方法,供者和受者位于相邻的手术室,在宣布供者循环死亡后进行经胸腹的ECMO插管和随后的心功能原位评估,由于预计的缺血时间很短,使用SCS的方法保存器官,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进行心脏获取前的评估。
欧洲和美国最近的许多项目尚未公布DCD供心植入后的临床结果。然而,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两大中心都发表了使用DCD供心的4年和5年结果,DCD心脏移植目前占其心脏移植总数的1/3,虽然接受DCD心脏(特别是DP-NMP方法获取的心脏)的受者因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需要机械支持的比例增加,但院内生存率和1年生存率与接受DBD供心的受者相当[18]。从多个DCD心脏移植项目积累的临床经验来看,选择DCD供者进行心脏移植似乎是可行和安全的[19]。
1.5 供者的保存和转运
传统的心脏保存方法是SCS,即使用冷的心脏保存液灌停心脏并将其保存在恒温冰箱中。SCS方法简单、廉价、可重复,能够将标准的供者心脏保存长达4~6 h,且移植后有较好的结果。因此,这种器官保存方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改变。尽管如此,由于心肌在静息状态下仍维持着一些基本的代谢活动,SCS保存下的心脏(无论是DBD来源或是DCD来源),在植入前都不可避免存在心肌缺血损伤。较长时间的缺血对于供心(尤其是边缘供心或DCD供心)植入后的预后无疑是不利的。这种缺血时间的限制导致许多供者的心脏因地域或交通的原因而被迫被弃用。全球超过70%的潜在供者心脏被弃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保存技术的局限性[11]。因此,人们也在不断研究新的方法提高供心保存效果。近年来,供心保存的技术进展主要集中在低温氧合机械灌注(hypothermic oxygenated machine perfusion,HOPE)和NMP。
HOPE是通过持续灌注低温、含氧的心脏保存液来保持供心的低代谢和减少心肌细胞的无氧呼吸活动[20]。临床前研究表明,HOPE方法保存的心脏通过有氧代谢产生足够的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因此供心避免了能量应激、组织酸中毒或过度挛缩,再灌注时产生的活性氧也有所减少[21]。因此,HOPE方法保存的心脏收缩功能显著优于SCS方法保存的心脏。尽管这些研究未使用脑干死亡或热缺血损伤的心脏,但它们证明了经过优化灌注方案的HOPE能够维持心脏质量长达48 h。Wicomb等[22]报道了第1个临床HOPE研究,使用便携式HOPE设备保存心脏6~15 h,4例受者中有3例存活3个月以上。Nilsson等[23]进行了另一项比较HOPE与SCS方法的非随机临床试验,所有6例接受HOPE保存的标准DBD供心的受者存活了6个月以上,没有出现严重的PGD、急性排斥反应或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结果明显优于接受SCS保存的心脏的受者。尽管该研究的病例数较少,但该研究表明使用HOPE保存供心是安全、有益的。保存和灌注供心过程中引起的水肿是HOPE方法的主要挑战,可能会阻碍冠状动脉灌注并导致舒张功能较差[23]。使用渗透压相对较高(380 mOsm/L)的灌注液或者高浓度的胶体(例如白蛋白75 g/L),可以预防水肿的形成。
NMP是将获取后的心脏连接至专有的机器,供者的血液和预充液混合后持续灌注心脏,保持心脏处于跳动状态。临床前实验表明,NMP能够安全储存心脏长达12 h,DCD心脏在30 min的热缺血时间后可保存4 h[24]。美国Trans-Medics公司开发的体外器官护理系统(Organ Care System,OCS)是第1个商业化的临床NMP装置。它用混合后的含血灌注液在34 ˚C的恒温条件下持续灌注心脏,并允许心脏在无负荷的状态下持续跳动。搏动的心脏有机会部分逆转热缺血损伤;同时,在保存期间的灌注压、冠状动脉血流流速和血气分析结果会被实时监控,以用来调整灌注条件和评估心脏功能。由于OCS提供了一个可部分逆转热缺血损伤的平台,并可对心室收缩力进行检测,这使得远距离运输供心(尤其是DCD心脏)成为可能。PROCEED-Ⅱ试验(OCS保存心脏的随机临床研究)表明,与标准SCS相比,OCS保存的供心移植后近期疗效不劣于标准SCS的心脏[25]。其他研究进一步证实,在不利的供受者组合中,使用OCS保存供心具有良好的临床结果[17,26]。虽然OCS是否适合远距离(>6 h)运送尚无足够的临床研究,但其未来仍然值得期待。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使用OCS的经济成本并不低。
1.6 异种心脏移植
人类首例异种心脏移植是1964年由James Hardy用黑猩猩的心脏进行的,但受者在2 h内死亡。James Hardy还陆续将不同动物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内,均未获得成功。物种间的排斥反应可能是异种心脏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基因技术为主的一系列科学的新发展,使异种心脏移植不再是天方夜谭。2000年,ISHLT组织了一个关于异种心脏移植的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建议,如果猪器官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存活约60%且至少3个月,同时无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发生时,可以考虑进行临床试验。2018年,科学家们使用转基因的猪心移植到狒狒身上并且存活达195 d。2022年1月7日,1例57岁男性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接受移植了异种心脏移植[27]。供心来源于1只基因编辑猪,科学家对其进行了10次基因操作,其中包括删除3种已知猪异种抗原(人类对其有天然的抗体)的基因,并引入6种人类基因,以提供额外的保护免受人类免疫反应;此外,由于猪器官移植到非人灵长类动物后生长迅速,其编码生长激素受体的基因也被删除。
在抗排斥反应方面,术前分别使用利妥昔单抗和抗胸腺细胞球蛋白以清除B细胞和T细胞,补体C1酯酶抑制剂用于抑制补体。由于传统的免疫抑制疗法(如他克莫司为基础的疗法)在异种移植中已被证实不成功,该患者接受了人源化单克隆抗体(KPL-404)用于阻断CD40-CD154共刺激通路,该药物已被证明可有效防止狒狒的抗猪体液反应。维持免疫抑制药还包括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和快速减量(从每日125 mg减至每日30 mg)的甲泼尼龙。术后早期供心在受者体内工作良好,受者脱离了ECMO,异种移植物功能正常,无明显排斥反应,也无明确的猪病毒感染证据。移植术后49 d,异种移植物突然出现心肌增厚和舒张期功能衰竭。
经过一系列包括ECMO等的积极治疗,受者病情仍然无法恢复,最终于术后60 d死亡。尸检时发现异种移植物明显水肿,重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组织学检查显示散在的肌细胞坏死、间质水肿和红细胞外渗,无微血管血栓形成的证据,这些发现与典型的排斥反应不符。尽管这例供心在受者体内仅工作60 d,但仍有很多创新值得借鉴,比如以基因编辑技术克服物种间的进化距离、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免疫障碍导致的超急性排斥反应和血栓性微血管病导致的异体移植物失功等问题,通过血压控制减缓心脏过度生长,糖皮质激素快速减量治疗等。虽然使用动物器官进行移植将给医学界带来了更多的宗教、伦理和社会问题,但在未来异种心脏移植仍然值得期待。
2 心脏移植受者
随着终末期心衰患者数量的增长,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的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病情也更复杂。高龄、多器官功能不全、机械循环支持及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抗体致敏受者的比例近几年明显增加。受者的复杂性为心脏移植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2.1 受者的年龄与术前状态
在美国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70岁以上患者的比例从200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的11%;2000年至2018年接受的心脏移植受者中,70岁以上的占2.2%[28]。高龄患者往往虚弱指数更高且合并症更多,似乎预示着病死率更高。然而,最近一项研究分析显示年龄较大的受者5年生存率和年龄较小的受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或许因为这组高龄受者及供者经过了高度选择[28]。
心衰的内科治疗在近期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进展,比如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及心肌收缩力调节等。然而我们仍然要对这些内科治疗手段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另外一些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对于一些难以逆转的心肌病(如严重的心肌纤维化),或者因心衰反复发作需要多次住院的患者来说,“勉强的”指南指导下的医学治疗(guideline-directed medical therapy,GDMT )可能无法获益,甚至会延长其它器官低灌注损伤的时间,导致肾或肝出现器官功能不全,或仅维持微弱的平衡[29]。这类情况下,患者心脏移植后往往还要面对年龄和其它器官功能不全的考验,可能会增加术后的治疗费用和风险。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由于部分治疗并不在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且价格不菲,患者经过一系列治疗后可能难以负担心脏移植及之后免疫治疗的昂贵费用。在这里,笔者并不是提倡所有的心衰患者都积极地进行心脏移植,而是建议对每例心衰患者病程的各个阶段做好全面、个体化的病因诊断和病情评估。对于有逆转可能的心衰患者应该积极考虑GDMT,而对于心肌高度纤维化、几乎没有逆转可能的心衰患者,应该尽早主动和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其有潜在的心脏移植或人工心脏植入的必要性,或者建议其去更有经验的中心进行进一步的诊疗。
2.2 多器官联合移植与再次心脏移植
近几年来,多器官联合移植(multiple organ transplantation,MOT)的数量逐渐增加到占所有心脏移植的2%~4%[29]。肝、肾功能障碍常见于晚期心衰患者,MOT可能是其中一些患者的选择;一些晚期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需要心肺移植;还有某些淀粉样变性的患者可能需要心肝移植。MOT在再次移植中的比例明显多于首次移植(12.8%比2.4%)[29]。许多心脏移植受者由于长期使用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治疗而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当需要再次心脏移植,就必须考虑到心肾联合移植的可能性。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可以作为评估是否同时进行心肾联合移植还是序贯性治疗的重要标准[30]。当GFR<30 mL/min且需要透析时,MOT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而当GFR为30~45 mL/min时,两种策略结果相同。MOT显然会增加早期死亡的风险,但有些文献认为,MOT对供心有免疫保护作用[31]。在高度HLA抗体致敏且有心肝联合移植指征的患者中,心肝联合移植术后几乎未见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且极少出现不良免疫反应[32]。心肺移植受者的1年和5年生存率为分别为70%和30%,低于单独心脏移植的受者,其他MOT受者的生存率与单独心脏移植受者相似[29]。
对于PGD、急性排斥反应或CAV的患者,再次心脏移植是较好的选择。由于再次移植的复杂性,其临床结果显然比首次移植更差。一项meta分析发现,再次心脏移植术后1年和10年生存率均低于首次心脏移植[33]。然而,文献也指出,如果再次移植的原因是CAV的发生,且距离首次移植至少5年时,再次移植与首次移植的结果相当。我中心首例心脏移植是在1995年完成,术后第8年因右冠状动脉严重狭窄而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第16年因为弥漫性CAV,受者反复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再次接受心脏移植治疗[34]。目前这例受者仍然健康存活,距再次心脏移植11年,距首次心脏移植已有27年。
2.3 机械循环辅助装置
晚期心衰患者一旦出现急性心源性休克,即使处于高度紧急状态,也很可能最终无法等到供者。还有一些患者可能有暂时的心脏移植禁忌证,如较高的肺血管阻力或可治愈的恶性肿瘤。这些患者往往需要机械循环辅助(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MCS)以维持生命,并在移植术前恢复器官功能和营养状态,或使有暂时心脏移植禁忌证的患者通过治疗达到移植条件。2010年至2018年,在ISHLT登记的心脏移植受者有45%接受过MCS,其中最多的是左心室辅助装 置(left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LVAD)[2]。MCS可以是临时辅助,也可以是长期辅助。
临时MCS包括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心室辅助装置(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VAD)[如Impella(德国)、Centrimag(美国)或TandemHeart(美国)]和静脉-动脉ECMO(veno-arterial ECMO,V-A ECMO)。在我国,IABP和V-A ECMO是桥接心脏移植的主要机械辅助手段[35]。而在欧美国家,LVAD是主要的桥接治疗手段[2]。2018年美国供者心脏分配规则修订后,接受持久LVAD(durable LVAD,dLVAD)的候选者优先级别有所下降,这使得dLVAD植入的比例相对减少,相反临时MCS的使用显著增加。然而临时MCS桥接的患者预后可能较差。在一项西班牙的研究中,V-A ECMO、临时LVAD和临时双心室辅助装置(bi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BiVAD)桥接患者心脏移植术后住院病死率分别为33.3%、11.9%和26.2%,从进入等待名单到出院的总生存率分别为54.4%、78.6%和55.8%,在进入等待名单的1年内,临时LVAD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独立相关[36]。来自ISHLT注册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V-A ECMO支持和经皮的临时VAD支持的患者移植术后病死率增加[37]。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医师应尽力避免使患者处于被动的紧急状态。
dLVAD作为心脏移植的桥接治疗,使晚期心衰患者在等待合适的供者时避免了渐进性的临床恶化,同时也使得一些原来被列为移植禁忌的患者有机会进入等待名单,这其中包括已经循环休克的患者、过度肥胖难以匹配到大供心的患者、肺血管阻力较高的患者和有治愈机会的恶性肿瘤患者。dLVAD作为心脏移植术前的桥接治疗已经被国外大多数医师和患者所接受[38]。以dLVAD桥接治疗的患者比单纯药物治疗的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明显更高。接受HeartMateⅢ的患者1年和2年生存率分别为86.6%和79.0%,与心脏移植的结果相当[39]。dLVAD为那些因肺血管阻力高而无法进行心脏移植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选择,可以通过对左心室的充分卸载使肺血管阻力下降,以适合心脏移植。dLVAD也为过度肥胖患者提供了减重的机会,还为可治愈性的肿瘤患者提供治疗肿瘤的时间。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LVAD不足的另一面。首先,LVAD植入后存在卒中、出血和感染等的风险。一份HeartMateⅡ报告显示,2年随访期内,患者发生设备相关不良事件的概率很高,包括感染(19.0%)、败血症(19.0%)、卒中(11.7%)、血栓形成(3.6%)、出血(54.0%)、需要更换的机械故障(4.0%)和右心衰竭(18.0%)[40]。接受HeartMateⅢ的患者结果有所改善,但这些不良事件仍然存在[41]。其次,在部分国家,LVAD尚未进入医保,患者需要承受较高的经济负担。再者,LVAD的植入增加了心脏移植时开胸分离粘连的难度和出血的风险,还可能增加受者同种异体致敏的发生率。
在我国,自主研发的dLVAD技术近几年才刚刚起步,但是发展迅速。国内已经有3家VAD公司产品上市,包括重庆EvaHeart、苏州CH-VAD、天津Heartcon,还有1家深圳公司的产品Corheart 6也完成了临床试验,相信很快也会面市。目前这几款VAD产品均是LVAD,右心室辅助装置还处在研究阶段。同时,国内能够独立开展LVAD植入的中心也越来越多。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是国内较先开展dLVAD且完成临床植入例数最多的中心,天津泰达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等中心也是国内开展LVAD植入较多的中心。我中心自2019年开展了第1例LVAD植入,现在已经陆续完成了32例LVAD植入手术。
2.4 同种异体致敏
越来越多的受者(如分娩多次的妇女、既往有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或MCS植入史或有输血史的患者)在移植术前检测出抗HLA抗体,这是由于受者暴露于致敏源后的结果。致敏的受者会产生DSA而诱发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为了避免AMR的发生,需要检测受者体内是否存在DSA,这在过去是通过在移植术前进行直接交叉配型来实现。直接交叉配型需要将供者的淋巴结或血清运送到移植中心后与受者的血清混合,以评估互补依赖性的细胞毒性。这必然会受供受者的区域地理位置所限制,导致供者的利用率降低。最近,虚拟交叉配型已经取代直接交叉配型。由于已经知道了受者HLA的特异性,那么只要通过比较供、受者的HLA分型就可以评估其相容性。通过虚拟交叉配型就可以筛除有AMR风险的供者,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另一种方法是在移植术前进行脱敏治疗,或在移植术后去除、减少和(或)中和DSA。脱敏治疗的靶向目标是抗体、B细胞、浆细胞和补体系统,脱敏策略包括联合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利妥昔单抗和硼替佐米治疗。脱敏治疗的目标是使细胞毒性交叉实验为阴性。移植术前未致敏的患者在移植术后仍可产生抗HLA抗体,几乎一半的患者会在移植术后15年内产生抗HLA抗体。中断抗体介导的移植心脏损伤的措施包括大剂量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和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消除血液循环中抗HLA抗体或降低其活性的措施包括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血浆置换、免疫吸附和利妥昔单抗治疗。
3 免疫抑制治疗的精准化
当首例同种异体心脏移植手术完成后,心脏移植数量曾经一度增长非常迅速,但是由于极高的1年内病死率,心脏移植很快进入寒冬,其中排斥反应是最大的“杀手”。直到环孢素的问世才极大地克服了排斥反应这一难题,使心脏移植真正得到飞速发展。但是排斥反应仍然是影响心脏移植术后近、远期生存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宿主对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免疫反应需要终生免疫抑制,如何使免疫抑制与免疫缺陷(感染、恶性肿瘤)和药物毒性(肾毒性、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不良影响之间达到平衡是极大的挑战。
3.1 排斥反应的诊断和评估
精准监测移植物是否发生排斥反应是免疫治疗中重要的环节。传统的检测手段是有创的心内膜心肌活组织检查(endomyocardial biopsy,EMB)。国外心脏移植术后第1年一般实施EMB约12次,其频率为心脏移植术后第1个月每周1次,第2个月每2周1次,以后每个月1次至术后6个月,然后每3个月1次至术后1年。虽然EMB是诊断排斥反应的金标准,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有创检查给患者带来更多的不便及经济负担,许多患者难以接受;多次反复的EMB可能带来其他相应并发症,如静脉血肿、误穿颈动脉、气胸、心律失常、右心室穿孔和三尖瓣损伤;部分EMB未取到淋巴浸润的心肌组织,存在漏诊可能。所以寻找可靠、有效的无创、非侵入性检查手段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血清生物学标志物(高敏肌钙蛋白、B型钠尿肽或N端脑钠肽前体)和成像技术(超声心动图、心脏MRI)在诊断排斥反应方面有一定的意义,但受限于其特异度或灵敏度较低。近十年来,分子诊断技术在急性排斥反应的无创监测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包括基因表达谱检测(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GEP)和供者来源性细胞游离DNA(donor-derived cell-free DNA,dd-cfDNA)。
GEP(AlloMap,CareDx,Inc.)是一种基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11个基因表达水平定量评估的检测手段。GEP用于监测排斥反应的方法已被纳入了ISHLT指南推荐。使用AlloMap进行无创排斥反应监测的临床结果(排斥反应、PGD、死亡和再次移植)并不低于传统的EMB方法。在一项研究中,GEP显示出中度或重度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acute cellular rejection,ACR)诊断的较好辨别能力,尽管阳性预测值较低,但阴性预测值>98%,因此GEP被证明是排除ACR的有效方法[42]。一项观察性、前瞻性和多中心研究纳入1 500多例接受GEP检测的心脏移植受者,发现GEP不仅是ACR的筛查工具,而且可以预测移植后的长期临床结果[43]。然而,但GEP尚未在AMR中得到验证,其次,GEP评分可能会因为如巨细胞病毒感染或服用高剂量糖皮质激素而改变。
移植后dd-cfDNA在总细胞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中比例>5%,在1周内迅速下降至<0.5%。发生排斥反应时,dd-cfDNA进入血液,达到5倍以上的表达,并与EMB确定的排斥反应严重程度和PGD的存在相关[44]。在排斥反应病理学确诊的前5个月甚至可以发现dd-cfDNA的升高。由于dd-cfDNA的释放比其他临床排斥反应生物学标志物发生得更早,可以用于定期监测移植受者,以便早期诊断和治疗急性排斥反应。与GEP不同,dd-cfDNA可以区分ACR和AMR,因为dd-cfDNA在AMR中的升高程度比在ACR中高5倍,发生得更早,而且dd-cfDNA的基因组组成和片段长度在两种排斥反应类型之间都不同。同时,一项回顾性研究发现,dd-cfDNA中位数水平与移植3年后的不良结果(死亡、再次移植、血流动力学受损或PGD)显著相关[45]。
3.2 免疫抑制方案
心脏移植术后大多数患者接受了3种药物联合应用的方案维持免疫抑制,包括CNI、抗代谢物和渐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CNI是一种钙依赖性的丝氨酸/苏氨酸磷酸酶,可激活活化T细胞的核因子,核因子是一种转录因子,可上调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的表达。其经典代表药物环孢素的应用使心脏移植在20世纪80年代重返临床主流。他克莫司因其更低的排斥反应和不良反应发生率而成为CNI的首选。抗代谢药物硫唑嘌呤和MMF或霉酚酸通过干扰细胞生长和分裂参与免疫抑制。一项比较MMF和硫唑嘌呤在心脏移植中的大型临床试验表明,接受MMF治疗的患者生存率提高,排斥反应发生率降低[46]。因此,MMF几乎完全取代了硫唑嘌呤作为首选的抗代谢药物。糖皮质激素是移植中最早使用的免疫抑制药之一,由于其强大而多样的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其仍然是维持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与许多不良反应有关,包括Cushing综合征、葡萄糖耐受不良、感染和骨质疏松。排斥反应风险低的患者通常在移植术后12个月将糖皮质激素剂量减少到低剂量或完全停用。
增殖信号抑制剂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抑制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从而抑制T细胞、B细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西罗莫司或依维莫司替代硫唑嘌呤并与环孢素合用可降低排斥反应和CAV的发生率。西罗莫司与他克莫司合用可降低排斥反应、巨细胞病毒感染和恶性肿瘤的发生率。然而,西罗莫司会加重CNI的肾毒性,延缓胸骨伤口愈合,因此不应在移植术后立即开始使用。移植术后晚期用西罗莫司替代CNI可改善肾损伤患者的肾功能。
贝拉西普(belatacept)是一种高亲和力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免疫球蛋白,与MMF和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可以预防成人肾移植受者排斥反应。一项针对40例心脏移植受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贝拉西普(尤其在移植术后的前3个月内应用)可改善GFR,然而当在移植术后晚期才开始应用时,排斥反应发生率会上升[47]。IL-6是一种促炎因子,可促进急性期反应、诱导B细胞的成熟或抗体生成、引导细胞毒性T细胞的分化,并抑制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动物模型中阻断IL-6/IL-6受体的信号通路可改善移植物排斥反应[48]。在人体CAV研究模型中,IL-6信号通路抑制剂可以减轻血管病变[49]。心脏移植术后早期使用抗IL-6单抗(克拉扎珠单抗)和IL-6信号阻断剂(托珠单抗)的临床研究还正在进行中。
4 同种异体移植物血管病
免疫介导的炎症和内皮损伤最终会导致移植物血管内膜增生和微血管病变,也被称作CAV。心脏移植术后5和10年CAV的发生率分别约为30%和50%[2]。CAV导致的PGD是再次心脏移植的最主要原因[2],也是心脏移植术后晚期死亡的主要原因,占移植术后5~10年死亡原因的32%[2]。由于移植心脏的去神经化,患者不会出现典型的心绞痛,因此发病早期往往难以被发现。因心肌持续缺血,到晚期患者可能出现左心射血分数下降、心衰,甚至猝死。因此,对于CAV的定期监测和早期诊断十分关键。
CAV诊断的传统检测方法是每年进行1次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血管内超声是目前唯一能提供与组织学切片相当的冠状动脉管壁横断面图像的技术,甚至可以检测出早期的斑块负荷。在检测CAV方面,血管内超声比血管造影更敏感,并可以用于评估预后,移植术后1年内冠状动脉内膜增厚>0.5 mm与5年病死率及CAV的发生率增加相关[50]。冠状动脉造影和血管内超声均是有创性的检查,无创成像技术也被应用于CAV的诊断,但准确性相对较低。目前可用的无创性检查包括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检查,单光子发射CT成像和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正常的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对随后的心血管事件有中等的阴性预测值(80%~100%);单光子发射CT成像具有中等的诊断准确性(灵敏度0.63~0.84,特异度0.70~0.78)来检测轻微到严重的狭窄。最近,通过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and computed tomography,PET/CT) 评估心肌血流储备已被证明可以预测心脏移植术后的临床结果,但缺乏长期随访的多中心数据。在治疗方面,霉酚酸、mTOR抑制剂(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他汀类药物可以减缓CAV的进展。但迄今为止,仍未发现完全预防或逆转CAV的治疗方法。
5 小 结
心脏移植是治疗终末期心衰最后的堡垒。供者库的扩大和供心保存技术的提高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供者的利用率,改善供者严重不足的现状。心脏移植等待名单上的受者的情况也较以前发生了改变,人口老龄化使得受者呈现出高龄、复杂化的趋势。机械循环辅助技术的提高为受者提供了更安全的等待期,然而也为后期的心脏移植增加了新的难题。致敏患者的管理、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排斥反应及CAV的诊断和治疗仍然是心脏移植受者管理的重要环节。本文概述了心脏移植领域现今面对的主要挑战,希望有助于改善等待或已经接受心脏移植的终末期心衰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