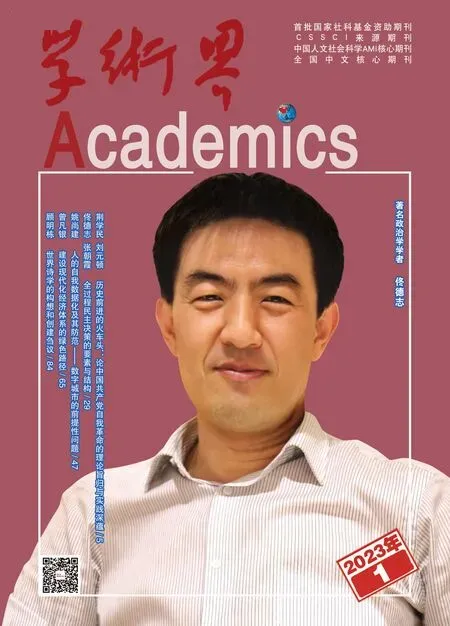人的自我数据化及其防范〔*〕
——数字城市的前提性问题
姚尚建(华东政法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一、研究的缘起
信息技术正深嵌城市化进程,并日益构成城市的数字基座。从政策推动者的角度,数字城市是一种基于技术的城市系统,“数字城市的核心技术是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空间决策支持、管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以及宽带网络等技术,主体是数据、软件、硬件、模型和服务,本质是计算机信息系统。”〔1〕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这一耳熟能详的判断在今天成为现实。
城市运行涉及复杂系统的重构、风险的控制与服务的供给,因此从权力行使者的角度,社会的清晰化与可计算性将带来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城市过程的角度,风险的及时化解构成城市运行的过程性保障;从服务供给的角度,更加精准的服务点位将提升城市运行的质量;从每一个城市个体的角度,更加便捷的城市将带来更加便利的工作与生活。然而,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却是,数字城市建立在日益简化的代码之上,建立在计算机的技术进步之上,在计算机的世界里,由于二进制语汇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信息,如声音和影像,都被数字化了,被简化为同样的1和0。”〔3〕
城市的代码化转向简化了社会问题,同时意味着城市政治的技术性转变,借用杰米·萨斯坎德(Jamie Susskind)的判断,城市政治将被三大发展所转变:日益强大的系统、日益综合的技术和日益量化的社会。〔4〕三大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城市生活,带来了不同的城市治理思路,追求更加透明、更加清晰、更加“科学”的治理方式支配着城市的运行甚至是“全息化”运行,今天城市中的每一个体,“从用户画像、身体、位置、行为到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人的多种维度,都有可能被数据化,甚至思维方式也在受到数据化的影响”,〔5〕均处于自动计算的场景之中。
城市数字化转型给城市治理带来了便利,也让城市社会付出了代价。从思想路线看,城市数字化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Smart Growth)理论的社会学延续。新城市主义者认为街区、街道和建筑是城市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新城市主义的指导原则包括提供可供选择的多个十字路口和可以缓行的交通方式、设置骑车人或行人舒适的街道、建筑物外墙与公共空间保持一致、建筑类型和谐统一、街道和建筑物后面设置停车位、适当的公共与私人空间界限、保护历史建筑等。〔6〕20世纪90年代,精明增长理论沿着新城市主义的路线,主张城乡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开发管理的决定中,以最低的基础设施成本去创造最高的土地开发收益,使城市土地达到最高的使用密度。〔7〕空间的硬约束对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理想形态,数字孪生城市将这些空间、建筑、车位和十字路口投射到城市虚拟系统中,并与城市物理世界双向映射、动态交互;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由于其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却难以被实时映射。
在既有的文献中,数字城市是一个由20世纪末“数字地球”衍生而来的场景应用,是一种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城市变迁。在自然地理学看来,数字城市“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要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展现。‘数字城市’的本质是把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8〕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定会持续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成为人们认识城市的重要工具。
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城市日益清晰化、数据化;智能技术的推出,则进一步深化了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2015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互联网+”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9〕也正是在这一文件中,“互联网+人工智能(AI)”作为重点任务进入经济社会之中,并助推了智慧城市的发展。
“就人工智能的定义来看,它是一门融合了计算机科学、统计学、脑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沿综合性学科,它的目标是希望计算机拥有像人一样的智力,可以替代人类实现识别、认知、分类、预测、决策等多种能力……从技术演进角度看,大数据发展到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迁移过程。”〔10〕如果说数字城市(digital city)建立在城市日常数据之上,重在对城市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的三维展现,那么智慧城市(smart city)则更进一步把城市的日常运行与公共服务结合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借助于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智慧城市建设着力于营建一个基于精致计算的自动化城市秩序。
二、城市“全息”运行的计算强制
在现代城市形成过程中,国家、资本和社会分别构成了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在城市运行中,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城市主体不同程度介入了城市运行,从而构成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对于城市决策者来说,充满复杂性的城市系统加重了城市运行的困难,为了促进城市治理的清晰化,借助于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信息技术及智能计算先后进入城市过程,并日益以“全息”的方式维护城市秩序的数字控制。
(一)城市运行的系统逻辑
基于国家的逻辑,城市仅仅是地方政府单位;但是基于城市形成的市场和社会逻辑,城市依赖空间、产业和人口的互相作用,因此城市必然存在着众多差异性的个体、组织,城市运行也并不存在单一的运行逻辑,而是一个复杂的运行系统。复杂系统的描述必然涉及系统论的理论演变。与经典系统论主要研究系统的整体性问题不同,现代系统论主要研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现代系统论认为,“整体虽然是系统的核心属性,但它并不等于系统自身,系统论也不孤立地考察系统的整体性,而是在其与部分、层次、结构、功能、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其整体性的……人们只是把握了事物的整体性并不能达到把握事物系统的要求,而只有把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认识系统。”〔11〕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催生了类型迥异的城市,截至2020年底,从行政区划上看,今天的中国城市共有685座,〔12〕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一些动辄数十万人口的大镇。行政等级与人口规模在中国城市体系上的差异性也说明了中国城市形成的多样性,而权力、资本和社会力量都将同步影响着城市的运行。从权力分析的角度,在城市这个复杂系统中,作为地方政府的城市事实上已经跨越了省、地、县、乡四个行政等级,并根据行政等级获取不同的国家资源,因此行政权力的运行在城市系统中不可忽视;从资本和社会分析的角度,城市是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集聚,资本和社会的意愿同样影响着城市的运行。
基于关系的角度,权力、资本和社会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市运行,如果说在中国这一国家依附性的经济社会结构中,行政权力意味着高层次的结构,那么这一高层次在约束下层组织的同时,也无法摆脱下层组织的约束,正是在这一逻辑上,整体论者认为,“高层次系统存在的整体性和突现性,不能完全归结为它的组成部分的作用,因为它对于低层级的组分具有一种下向因果作用,也就是说,因果关系对于各层次是开放的。”〔13〕从更加细分的角度,一些研究认为,由于复杂社会建立在不同企业和人群高度分工的基础之上,因此日益增长的需求多样性和服务个性化,以及高度分散的社会的信息,都将增加城市运行的复杂性。〔14〕米勒(Jonny H.Miller)和佩奇(Scott E.Page)进而区分了复合系统(complicated worlds)和复杂系统(complex worlds),他们指出,复合系统的各个要素保持了一定独立性,复杂系统则源于各要素的依赖性,而社会系统天生就容易引起复杂性,无论是蜂群、人类还是机器人,都会陷入彼此联系的网络之中。〔15〕
(二)城市“全息”的技术路线
系统的彼此依赖构成城市运行的基础,也意味着城市问题的弥散。系统论者发现,在具体的问题上,系统论有力所不逮之处,“在系统科学领域,系统论并不能有效解决具体的复杂系统问题,主要原因是未能解决系统悖论——不能针对具体系统给出具体的定量形式描述模型。深入研究发现:复杂系统不存在统一的原理及描述模型,只能针对特定类型的系统,寻求特定的原理及描述模型。”〔16〕约翰·霍兰(John Holland)进一步发现,在世界中普遍存在一种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涌现”现象,“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面临着复杂适应系统中的涌现现象——蚁群、神经网络系统、人体免疫系统、因特网和全球经济系统等。在这些复杂系统中,整体的行为要比其各个部分的行为复杂得多。”〔17〕
因此,城市发展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运作过程,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行政等级的更替、城市空间的变迁、产业与人口的持续流动,这些已知的、未知的、彼此联系的“涌现”现象,给城市运行带来了多重变数。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又融入了全球化进程,超越国家的国际企业、国际市场、国际社会组织以及国际政治机构,都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运行,一个可预测的、甚至透明的城市运行日益成为城市运营者的迫切期待。借助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在20世纪,激光和计算机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生活。激光带来了全息技术,“光学原理可知,光场的频率决定像体的色彩,振幅决定成像的亮暗程度,相位则对应成像的深度信息,就是人们所说的立体感。”〔18〕而全息照相术,正是以物理光学理论为基础,把物体上发出的光信号的全部信息,包括光波的振幅和相位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它反映的是物体的三维空间特性。〔19〕全息技术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启发了社会科学对于精细化、立体化知识的渴望,甚至形成了全息生态学、全息数学、全息医学、全息经济学、全息人类学等交叉学科。
如果说全息技术记录了城市个体的全部信息,那么基于这些信息的政策计算就成为必需。1965年,在IBM工作的罗曼(A.W.Lohmann)用计算机代替激光器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张计算全息图,〔20〕这一借助于计算机技术进行的光学模拟、光学计算以及光信息处理,催生了新的学科——计算全息(computational holography)。计算全息是建立在数字计算与现代光学基础上的,是对光学全息的技术性超越。进入21世纪以来,借助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及智能技术的发展,城市运行日益依赖信息的生产与利用,复杂的信息处理速度支配着城市运行的健康程度。因此对于城市的模糊运行来说,全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对于城市的启发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否能够清晰识别城市运行的每个组织及其行为,甚至精准预测霍兰所谓的涌现现象,通过智能计算、全息识别与系统掌控,来观测城市问题的原点,从而为城市运行提供保障性方案。
(三)城市秩序的计算强制
伴随着信息革命到智能革命的技术变革,城市这一复杂性系统逐渐清晰起来,而“复杂系统研究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是一系列用以探索、开发更加广泛模型的计算技术。利用这些工具,任意数量的异质性主体都能在一个时空受限的动态环境中相互作用”。〔21〕也就是说,一个受控的城市运行系统在计算机技术上日益可行。同时,城市运行过程是一个有限空间众多要素再聚合的过程,是一个空间秩序重塑的过程。随着计算机技术进入城市运行,一个建立在物理空间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转型,一个基于计算的社会形态正在形成,以至于“在算法社会,治理主体既能够通过技术和权力手段追踪具体人群的行为轨迹,也能通过算法模型进行更有效的社会筛查和监控,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数据和计算技术的基础之上”。〔22〕
有研究认为,传统哲学对于实在世界归根到底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所组成的判断存在不足,“当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不仅实体性的物质不是基本的,而且其和能量均可以化归为更基本的要素——信息,即信息和信息变换(即计算)才是构成实在世界的‘本原’。”〔23〕信息对于物质、能量的本原性规定为城市全息运行提供了可能,在城市运行中,计算全息技术致力于经过算法编码,把城市个体、物体、空间绘制成一张清晰的城市全息图。同时,在城市全息运行的时代,计算机必然意味着一种秩序的强制工具,一种对于复杂性的技术性规范,“计算机就像一个自动化的炉子,一旦输入这个菜谱或说明书,它就会按照规定做出美味佳肴来。”〔24〕从整体上看,城市运行是智能计算的过程,这种计算忽视城市间以及城市内部差异性的存在;从个体上看,无差别的计算机分类事实上提供了城市生活的有限选择,并将多样化的个体强制性地塞入一个个程序员编制的城市网络之中。
三、人的量化与城市自动化秩序的演进
城市系统的运行有高低层次之分,层次间的关系互动,推进了城市这一复杂系统的演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揭示,世界是层级结构和突现进化的。层级或层次是突现的结果,是突现形成一个序列的表现。主体之间的局域性相互作用通过自组织和适应性机制,产生了一种全局模式,即一个新的层次,表现出一种突现性质。”〔25〕在城市的模拟运行中,在追求自动化秩序的过程中,全息技术日益被理解为一种代码化的处理工具。为了满足这一处理过程,越来越多的城市个体需要进入一个被编码的过程。
(一)作为机器的城市运行与人的量化
在城市运行中,科学计算的技术前提在于,追求城市运行的透明化,意味着城市各要素必须皆可量化,数据则构成量化的前提。杰米·萨斯坎德认为,四个要素促进了社会现象的数据化转换: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通过数字系统展开、存储数据成本的降低、算力的爆炸式增长、低成本的数据复制。〔26〕随着城市数字化转型,社会现象的数据化转换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平台汇聚了越来越多的数据,为城市的透明运行提供了前提;与此同时,“相关主体可以通过‘逆操作化’,将复杂社会系统中的社会行为、公共事件和潮流现象乃至个体情况,借助算法等技术进行抽象化或符号化处理,变为具体可观察的数据”。〔27〕
数据与城市生活的互相转换,使城市生活以数据流的形态加以展开。社会行为、公共事件以及社会现象的背后是人的多样性活动,技术的抽象化处理建立在人的数据化基础之上。在万物皆可量化的城市中,作为观察主体的人异化为自身凝视的对象。在卢卡奇的物化世界里,这种凝视意味着两种意义上主体的分离:“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致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28〕
城市运行日益体现出机器运行的特征,“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成就,人们有多大意愿上依赖机器,就有多大可能感染机器的负面性,诸如城市环境污染、城市交通、街区停电等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破坏将日益强化,并构成新的城市问题。”〔29〕在新技术革命驱动下,人的异化与共同体的瓦解,构成了城市数字化运行的社会代价。更重要的是,在城市数字机器的运行初期,由于计算手段的有限性,城市对于机器秩序的追求必须简化人的社会角色,从而实现人的“量化”及其可计算性,这种追求“量化”的简单思维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必然给城市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二)代码化与作为变量的人
2003年12月我国第一届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联席会议上确认,将EPC翻译成“产品电子代码”,它的特点是强调适用于对每一件物品都进行编码的通用的编码方案,这种编码方案仅仅涉及对物品的标识,不涉及物品的任何特性。〔30〕事实上从城市运行可计算性的角度,人的量化仅仅构成城市机器运行的前提,是参与信息加工甚至被代码化的基础。因此城市数字运行的过程、城市信息加工的过程都将指向一个结果:城市个体与城市其他要素一样,被无差别地代码化了。有研究乐观地认为,“人类行为被数字表征,进而变为数据和信息之后,就再难以被单一中心所掌握、难以被物理空间所固定,而是变得更为分散、更为多元,也更为流动。”〔31〕但是,只要在数据生产中存在权力的不平等,那么就一定有掌权者在主导着这一数据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在数字城市转型过程中,是城市运行者而非这些城市中的个体掌握着这些代码的密钥。
在人的代码化之后,城市运行自然就成为机器的自在运行,为了即时观察城市运行,一种更为大胆的假设——“数字孪生城市”应运而生。“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是指在信息系统中构建一个虚拟世界,通过信息收集、传输、处理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与物理世界的同生共存,达到社会世界、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作用,并最终形成虚实结合、孪生互动的城市发展新形态。”〔32〕不难看出,数字孪生城市的基本理论框架存在一种技术化的处理过程,人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甚至社会属性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机器行为、技术关系以及工具属性。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里,存在两种类型的技术:一是作为物质人造物的技术,二是作为社会形态的技术;前者主要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33〕国内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前者指科学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应用,后者指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技术。〔34〕这一分类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值得审视,基于什么样的前提,人造的技术最终异化为人类自我束缚的工具?从分化与整合的双重路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解释了机器的力量形成:“机器不同于简单工具,也不同于车间里……被放置在一起的大套工具。机器从自然资源(最早是水,然后是蒸汽,再后来是电)中获取能量,并利用它完成一系列生产任务。现在,工人不再操作工具,而是服务于机器……尽管劳动越发地被分化和隔离,机器却被整合成一种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统一,并且更具生产效益的整体……从一开始,机器就拥有了制造全新东西的潜力,也即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潜力;因此,也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合理性,以及最终的,劳动自身的终结。”〔35〕
(三)被机器切断的城市与人的联系
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的主体,社会是由一个个劳动者组成的关系体。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进一步把社会规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压制性制裁有关的规范,包括分散类型和组织类型;另一种是与恢复性制裁有关的规范。我们已经看到,前者表现出来的是从相似性中产生的团结条件,我们已经将它称作是机械团结;后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否定的团结,我们称之为有机团结。”〔36〕但是涂尔干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日益强大的、自动化的机器不仅终结了劳动,切断了劳动者与社会的联系,也使字面意义的机械团结达到极致;涂尔干更不会想到,他所捍卫的,即分工不会把人们变成不完整的人的判断也会遭遇挑战,他认为,“个人的人格非但没有由于专业化的发展而受到损害,反而随着分工的发展一同发展起来了。”〔37〕但是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以专业的名义,社会分工却出现在了机器与人之间。
在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看来,社会结构不能被看作是物质实体,“在任何的物质意义上,社会有机体是不能形成一个‘连续集结’(continuous mass)。”〔38〕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的重构意味着权力、信任和契约的重组。在涂尔干的阐述中,法律和道德在维系社会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和道德就是能够把我们自身和我们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所有纽带,它能够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39〕但是,日益强大并走向联合的机器进入了城市运行系统,一旦机器的“联合”替代了社会结构,那么机器社会的强制性势必影响着城市社会的系统再造;在这样的城市机器运行中,众多失去主体性的人开始成为分散的信息甚至代码,成为城市机器的原料而非城市的主导者。
四、自我数据化中的自证清白、人的削弱及其纠正
人的量化构成城市自动化秩序的前提,而人的量化也逐渐偏离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原则。“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具体地生活在‘数字状况’(digital condition)下。以指数级速度升级迭代的当代技术已深层次地介入人类共同体之结构,推动其走向数字化——‘数字城市性’(digital urbanity)、‘算法化社会性’(algorithmized sociality)、‘大数据主义’(big-dataism),正在成为共同体的三个构成性要素。”〔40〕在城市运行中,三个要素不同程度地把大量人口驱赶到数字空间之中,并以自我数据化的形式让渡了自由和权利。
(一)代码治理中的自我数据化
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世界遍布生产性的城市,或者说,城市就是一座座巨大的工厂。与此同时,由于人口的彼此交往,城市社会活动充满了复杂性。列斐伏尔以“都市社会”这一概念揭示了都市现象的复杂化(complexification),他强调,“都市社会,连同其自身所独有的秩序与无序,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41〕新技术革命改变了原先的城市形态,日益全息而透明的城市治理需要更加充分的数据,而人,正是城市数据的主要供体。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从无现金支付到打车软件,借助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应用程序(App)被开发出来,这些App与日益普及的智能手机紧密结合,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复杂需求。但是这些App的使用大多存在一个前提,即每一个使用这些程序的居民必须扫码、注册、登陆、允许访问私有空间等,也就是说,这些扫码的过程满足了这些软件窥视个人信息的需求,扫码过程因此成为一个自我数据化的过程。
新技术革命推动着“数字空间”的形成,伴随着数字空间逐渐成为一个新战场,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型权力正在生成。〔42〕自我数据化意味着城市个体收缩甚至部分失去了捍卫自身信息的能力,意味着基于数据的权力对于城市运行的操控。在自我数据化过程中,被称为私权的性别、身份、学历、健康、交往以及行为偏好都被众多数字平台反复搜集并交叉印证,越来越多的数字平台掌握了海量的信息,掌握了基于数据的权力;与此相对,由于失去了私权的捍卫,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日益透明。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中国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场所码等对城市居民进行轨迹追踪的技术工具。以公共管理的名义,这些二维码遍布公共场所,防控人员被授权拒绝那些不扫码的个体进入这些场所;更有甚者,一些城市或社区还推出了“刷脸”等形式,对唯一生物信息进行识别。这些信息识别甚至进入了居民共有的楼道等准公域,从而部分限制了居民回家的权利。
(二)代码治理中的自证清白及其缺陷
在马克思的理想里,未来的社会必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城市的历史中,现代城市的复兴源自权利的解放。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业革命以及汇聚工人阶级的城市的歌颂便不难理解。但是,作为机器的数字技术并非没有社会边界,数字工具归根到底无法具备剥夺自由的道德正当性。沿着马克思的思维路径,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了机器背后的权力,“我们能够为计算机提供某个特定问题的全部数据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机器只能使用以‘是’与‘否’为答案的问题构成的数据,计算机本身也只会对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应。此外,谁能够确保所有数据已经凑齐了呢?谁将保证这个数据大全使用的合法性呢?谁将证明‘城市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语言——是与算法语言(ALGOL)、语言结构(SYNTOL),或公式变换语言(FORTRAN)、机器语言一致,并且这种翻译不是一种背叛呢?这种机器难道没有冒着变成掌握在压迫集团与政治家手中的工具的风险吗?它不是已经成为那些掌权者以及服务于掌权者的人的武器了吗?”〔43〕
“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44〕在城市运行中,当城市主体需要主动扫码才能开启城市生活时,这种生活已经带有强制性的特征。在近年来的疫情防控中,扫码日益成为居民的强制性义务。由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健康码等限制,市民必须通过扫码的方式证明自己没有去过相关疫区,并证明自身的健康状况,这种“自证清白”的扫码过程一旦长期维系,一定给城市政府背上沉重的道德负担。其实从技术本身来看,编码本身并非中立,“软件的编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法律在社会中保证自由和限制行为方面的功能。在市场中,人们使用各种程序或者借由程序存取数据的过程均隐含着权利、限制和补偿等方面的合同或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软件不仅仅在技术层面作为工具而存在,同时也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掌控着信息技术空间的游戏规则”。〔45〕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风险管控,计算机技术在一些城市露出了獠牙,近年来遍布各地的健康码等普遍使用,使人们的行踪更加透明;一些城市有权者甚至出于各种目的,对一些本地甚至外地市民随意赋红码以限制后者出行。
(三)人的削弱与技术纠偏
当城市市民成为编码的对象,当城市管理者成为代码控制者,人便启动了数字世界异化的过程。城市个体通过注册、让渡私权等方式上传信息,助长了技术暴力,也削弱了权利、自由作为人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2022年12月13日零时,疫情防控过程中追踪人员流动轨迹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结束使命,基于公众压力,中国信通院宣布删除所有数据;关于健康码、场所码停用的呼声随之开始成为新的公共舆论。一轮又一轮的针对数字技术的批评,既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由受到限制的不满,更反映了这一技术内在的道德缺陷,即以科学的名义,每一个城市主体需要通过自我数据化的过程实现自我削弱甚至自我否定,却仅仅是为了满足尚不完美的计算机技术的需要:这一过程部分颠覆了人与机器的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主张了机器作为统治者的正当性。
从技术中立的角度,计算机技术无法实现自我纠正;从技术向善的角度,任何削弱人的技术背后都存在缺陷,而这种缺陷只能由人自身才能克服。在计算机程序的背后,是一系列源代码;同样,在城市数字化程序的背后,是一系列社会计算的源代码。这些人类开发的可读的计算机语言指令本身并不具备天然的封闭性,开放源代码因此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兴现象。与传统的科学研究模式相比较,开放源代码科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差别,一是科研成果不是私有产权,而是面对所有人开放的共有产权;二是科学研究不是由某机构(个人)完成,而是通过网络进行开放式合作研究,参与合作的数目不受限制。〔46〕基于这一科学价值立场,在源代码的分类中,向来有自由软件与非自由软件之分。这一分类启发了数字压迫的解决方案,即在城市数字治理中,在涉及居民参与的公共领域部分,合作治理需要建立在必要的源代码开放基础之上。一个数字城市治理应该是在公共领域部分开放源代码的治理,而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因此也是一个共同编写源代码的过程。
五、结 语
今天的中国正在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全力建设数字城市,一系列诸如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涉及数字城市建设的新技术应运而生,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技术垄断与数字门槛的设立,人们参与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知识结构。在技术不对等的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被迫通过自我数据化、自我限制的途径获得正常城市生活的可能。一些地方数字技术的黑箱化运作,技术不对等往往成为数字监控甚至数字奴役的条件,从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套上了数字枷锁,也使城市背离了近千年的自由价值。但是数字城市的建设本身不是要把城市打造成“圆形监狱”,不是要把市民打造成毫无情感的数据,正相反,人归根到底不是数据,人是城市的目的,人的自由始终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性问题。如果说在功利主义的理想里,任何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里,这种自我保存的城市权利意味着参与城市、控制城市的权利,那么在数字城市场景中,这种参与和控制首先是保有不被数字霸权吞噬的权利,必须是共同编制城市运行源代码的权利。
注释:
〔1〕《数字城市导论》编委会:《数字城市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2〕〔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前言”,第61页。
〔3〕〔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5页。
〔4〕〔26〕〔英〕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3、34页。
〔6〕〔美〕雷·哈奇森:《城市研究关键词》,陈恒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539页。
〔7〕〔加〕梁鹤年:《精明增长》,《城市规划》2005年第10期。
〔8〕江绵康:《“数字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经济日报》2015年7月5日。
〔10〕魏真、张伟、聂静欢:《人工智能视角下的智慧城市设计与实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前言”,第2页。
〔11〕常绍舜:《从经典系统论到现代系统论》,《系统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阅读推广服务是一项涉及图书馆多部门的服务,它需要有效对接资源提供部门。比如采访、流通,同时要争取馆办公室的支持、获得其他服务提供部门的资源,比如宣传平台资源、技术部门协作等,所以其品牌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各部门之间进行统一的协调。因而,需要指定专门的负责人来统筹全局,使得各部门在协助阅读推广服务时,能协调一致地实现品牌目标。
〔12〕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1》,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13〕〔25〕范冬萍:《复杂系统的因果观和方法论——一种复杂整体论》,《哲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4〕陆铭:《探求不确定中的确定——复杂社会的危机及应对》,《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15〕〔21〕〔美〕约翰·H.米勒、斯科特·E.佩奇:《复杂适应系统:社会生活计算模型导论》,隆云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12、6页。
〔16〕王迪兴:《准全息系统论与智能计算机》,北京:长征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7〕〔24〕〔美〕约翰·霍兰:《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陈禹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3、19页。
〔18〕韩超:《计算全息与图像加密》,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第3页。
〔19〕龚勇清、何兴道:《激光全息与应用光电技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20〕虞祖良、金国藩:《计算机制全息图》,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序”。
〔22〕〔27〕阙天舒、方彪:《治理中的计算与计算式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技术和艺术》,《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5期。
〔23〕郦全民:《计算社会科学的哲学透视》,《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2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2页。
〔29〕姚尚建:《城市安全:机器空间与人的尺度——一种病理学的视角》,《新视野》2020年第2期。
〔30〕张成海、张铎:《物联网与产品电子代码(EP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31〕〔42〕黄其松:《数字时代的国家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32〕范明月等:《智慧城市运营管控关键技术展望》,《计算机系统应用》2022年第11期。
〔33〕R.Grundmann,Marxism and Ec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139.
〔34〕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
〔35〕〔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07页。
〔36〕〔37〕〔39〕〔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56、360-361、356页。
〔38〕〔英〕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社会结构》,允春喜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40〕吴冠军:《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41〕〔43〕〔法〕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刘怀玉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4、65-66页。
〔44〕〔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
〔45〕杨剑:《数字边疆的权力与财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0页。
〔46〕聂盛:《开放源代码科学研究模式的兴起及思考》,《中国科技论坛》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