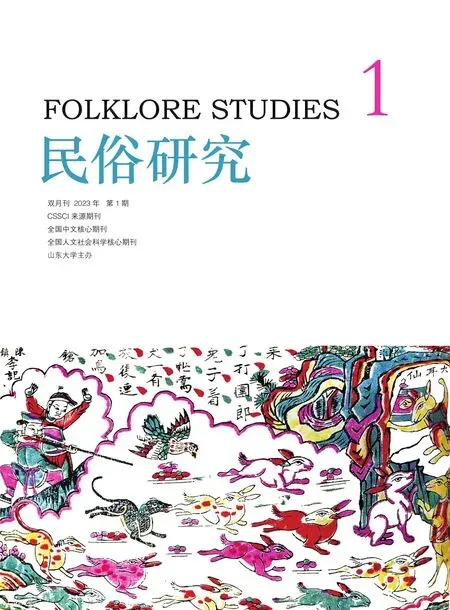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热的冷思考
魏甜甜
中国民俗学朝向生活实践研究的转型过程,恰好是与非遗研究同一时间发生的。十余年来,诸多民俗学者不仅参与到政府主导的非遗普查、申报、评定工作之中,更是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出版了多种学术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学理性支持。与此同时,在民俗学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非遗研究之际,非遗研究和民俗学研究的边界似乎变得模糊不清。就研究对象而言,非遗研究是针对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而展开的;就研究目标而言,非遗研究则是围绕着政府如何更好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而进行的。显然,民俗学研究的视野远大于非遗研究的视野。可是,部分学者将非遗研究视为民俗学的前沿研究、实践研究,过分强调两者的一致性,而对两者研究视野的差异性予以模糊化处理。对于两者研究视野的模糊化判断,可能会将民俗学应有的视野缩小和窄化。其次,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之间关系,尤其是两者的差异性,目前尚缺乏应有的深入讨论。本文基于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关系的研究现状,对于两者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一、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关系的研究现状
自非遗研究开展以来,关于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鲜有人探讨。而相近的问题,即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的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讨论。由于中国的非遗保护本就包含着研究部分,因此,探讨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的关系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讨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
事实上,早有学者注意到非遗与民俗学的相异之处,提醒非遗保护或会损害民俗学学科发展。乌丙安认为非遗与民俗有很大不同,非遗保护是有明确政策指导目标的工作,“与民俗学的本格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1)乌丙安:《21世纪的民俗学开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缘》,《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民俗学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和研究不应该取代主业。陈金文认为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之间的“理想关系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大家加入非遗保护工作之时,“忽略了对民俗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与关注”,“损害了民俗学学科的发展”。(2)陈金文:《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间的理想关系及实际状况》,《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施爱东提出“保护和研究是两个范畴的概念”,目前非遗保护研究的论文“从民俗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非遗研究几乎没有一篇可以有补于民俗学的理论建设”(3)施爱东:《民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尴尬处境》,《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2期。。陈映婕通过对政府运作下的非遗保护工作和理念,认为“国家视野与学术研究对于‘遗产’的观点存在异质的价值悖论”,且非遗研究成果良莠不齐,难以有助于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也无法成为“一个学科本位式的常态科研重心”(4)陈映婕:《超越“遗产观”的中国民俗学发展》,《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显然,在我国非遗研究开展的早期,学者对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本位的反思讨论较多。这类研究传达出一种焦灼之情,认为政府主导的非遗工作与民俗学学术认知或有相悖之处,会伤害民俗学发展和学术独立性。
然而,更多的研究则是关注非遗与民俗学学术发展的相通之处,认为借助非遗保护力量,可以实现民俗学学科的大发展。吴效群从知识论的角度探讨非遗保护工作与民俗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认为二者的意义是“研究、保护人民大众传统的知识创造”。(5)吴效群:《回到原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中国民俗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邢莉从概念、要旨、意义、价值等方面,论证了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相契合,认为非遗保护“必将促进民俗学科的发展”(6)邢莉:《民俗学的研究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民族艺术》2017年第2期。。户晓辉从实践科学的角度强调了非遗保护与民俗学具有实践属性(7)参见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实践范式》,《民族艺术》2017年第4期。,鞠熙从实践的角度提出非遗保护是“民俗学者切身参与的公共文化运动与实践”(8)鞠熙:《实践:民俗学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关键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杨利慧认为非遗保护等因素促进了“公共民俗学实践”(9)杨利慧:《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民俗研究》2021年第1期。,以及与学院派民俗学的融合。这类研究在近些年非遗保护与民俗学研究的讨论中较多,其探讨的不仅是两者的相通之处,更主要的是认为非遗是民俗学应该进行研究的重要领域。
综上可知,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差异性虽然已有学者关注并加以检讨,但主要集中在非遗研究开展的前期,声音比较微弱,缺乏进一步的更加深入的讨论。因此,本文有必要针对二者的差异性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关系的讨论,必须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概念的提出说起。无论是作为学术的还是作为工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其基础皆源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此概念在演化历程中,充分体现了与民俗的密切关系。1982年,教科文组织成立保护民俗专家委员会。198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RecommendationontheSafeguardingofTraditionalCultureandFolklore),其中用“Traditional Culture”(传统文化)和“Folklore”(民俗)来定义所要保护的文化类型。1998年,教科文组织通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以“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来代替之前的“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代替之前的概念。从“folklore”(民俗)到“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北欧、澳大利亚等西方学者对“folklore”中所包含的贬义性的担忧,“folklore”中关于“copyright”(版权)问题的争议,以及日本、韩国的“无形文化财”制度的影响。(10)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术语从“folklore”(民俗)到“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化历程论述,参见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诞生历程,包含了使用“folklore”的阶段,也包含了反思传统民俗术语“folklore”的阶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是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这不仅是“对民俗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境遇中出现的危机的关注和应对”(11)杨利慧:《从“民俗教育”到“非遗教育”——中国非遗教育的本土实践之路》,《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还包含了对文化平等、反文化霸权、反文化普世主义等理念的倡导。这一点与民俗学的文化关怀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
正是因为非遗包含着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以及文化多样性理念,与民俗学的倡导存在相通之处,民俗学者顺理成章地投身到非遗研究和非遗保护工作之中。当前中国的非遗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非遗保护研究与传承人论,政策文件的解读与中国实践的理念,公共民俗学的倡导,非遗运动与实践民俗学的结合。近几年,在遗产保护研究成果和非遗保护工作经验的双重积累下,学界部分同仁将非遗研究视为民俗学的前沿研究,强调非遗研究的实践性、公共性和应用性。他们以美国的公共民俗学实践、日本的在野派与学院派民俗学的区别以及人类学的四种分支等学科建设经验为依据,建构以非遗为学术实践对象的公共民俗学、实践民俗学等重要研究领域,并与所谓“学院民俗学”的研究相区分。
然而,过分强调非遗研究是民俗学的前沿研究或重要领域,是对两者研究差异性的模糊化,也容易导致民俗学研究视野的缩小。非遗研究不应遮蔽民俗学研究应有的视野,对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差异予以检讨,势在必行。
二、研究性质与目的的不同
检讨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根本不同,离不开对二者的研究性质和目的的比较与分析。目前由于缺乏对二者研究性质和目的的明确区分,非遗研究常被认作是民俗学研究。然而,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性质,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尽管在中国加入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前,国内学界已有关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等的研究,但大规模的非遗研究起始于2005年,这与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方针密切相关。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方针里包含“要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注重科研成果和现代技术的应用”(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5/content_63227.htm,发表时间:2005年3月26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18日。。这意味着,非遗研究已经被视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一部分,政府期待非遗研究服务于非遗保护工作。
在此后十余年的研究历程中,“保护”“开发”“策略”“旅游”等词汇确实成了非遗研究的关键词。以CNKI(中国知网)的可视化分析数据为例,检索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与传承”“传承与保护”“非遗保护”“数字化保护”“生产性保护”“法律保护”“保护传承”等关键词,占比分别为13.77%、3.10%、1.66%、1.51%、0.99%、0.96%、0.73%、0.69%,即含“保护”关键词的研究总占比23.41%,仅次于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非遗研究是基于有关非遗保护的国际协定和中国政府政策工作,围绕有关工作实际而开展的学术应用性研究,主要讨论如何进行非遗保护、改进保护方案和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民俗学研究也有文化保护的理念,只不过是从文化研究和学科责任的角度出发的。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进入中国之前,民俗学已经开始了关于文化保护的探讨。钟敬文在1988年谈及民俗学现状时,提出应建立民俗博物馆来保护民俗,将保存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物品加以搜集、陈列、展示,以便人类认识自己。(13)关于钟敬文提出民俗博物馆的想法,参见钟敬文:《钟敬文谈民俗学现状》,《话说民间文化》,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60页。刘锡诚亦曾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文化保护问题,提出以建立民间文化博物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资料、加强中小学的民间文化教育等形式来保存、保护民间文化的传统和记忆。(14)参见刘锡诚:《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文化保护》,《民间文化》1999年第4期。再如刘铁梁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各区县卷本编纂项目,也是从民俗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出发,以普查为基础,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为书写标准,以便更好地把握当地“民俗文化传承的状况和理解民俗文化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并促进对一个地方或群体的民俗文化“想方设法地保留、记住和重新认识民俗文化”。(15)参见刘铁梁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海淀区卷》(总序),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4、1页。不过,保护民俗并不是民俗学研究的本职工作。对于寓含民众文化记忆和身体感受的民俗事象进行记录,只是民俗学研究中极小的一部分。民俗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从民间文化出发认识国家和民族,以真正认知、理解、体认本民族文化为己任。认知人类的文化,是人文社会学科核心的研究目的,而中国民俗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旨在不断地深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认知和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当今世界的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和人类认同。
以年画研究为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年画”为双主题,检索CNKI中被引用量前50名(16)数据截至2022年10月18日。的论文,其关键词主要为“旅游开发”“生产性保护”“品牌传播”“传承人口述史”“传承人保护”“保护研究”等,显示出配合非遗保护工作的学术特色,并主要指向对文化形式的保护及资源性开发利用研究。民俗学研究则与此有别,倾向于将年画置于地方民众的社会分工和社交网络中,从城乡文化交流、工业化进程、劳作模式和交往关系等方面,认知年画对于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建构的作用,并不以保护和开发利用为目的。(17)关于民俗学研究中“年画”研究的论述,详见张杰、张清俐:《重视民间工艺的社会文化建构作用——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14日。
由此可见,已有的非遗研究主要是以检讨、改进、落实文化保护工作为目的的研究,而民俗学研究则是以认知、理解、体认本民族文化为目的的研究。具体说来,是为配合非遗保护工作而进行的研究,还是立足社区生活本位、秉持实践主体观的研究,可能正是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差异性所在。
三、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理论进展的脱节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民俗学,在朝向当下的学术转型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实践的、整体的、主体的研究范式,强调对文明转型和文明交流下地方民众生活实践的关注。然而,非遗研究尽管最初是借助民俗学研究理念而展开的,但由于其研究目的和性质的限制,已经与现阶段民俗学研究的前沿理念相脱节。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早期民俗学“文化遗留物”的理念,即将自然遗产、考古遗产、历史建筑遗产等非生活态的文化保护理念应用于生活态的民间文化保护之中,这是一种脱离社区生活整体、缺乏实践主体观的研究理念。
1.非遗研究的“遗产观”与早期民俗学“文化遗留物”理念的关联
曾长期流行于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文化遗留物”理念,源自于英国进化论人类学派的观点。19世纪中叶,英国古物学者汤姆斯(William Thoms)使用“folklore”一词,指称民间古俗、文化遗留物等。19世纪末,英国人类家泰勒(Edward Tylor)所提出的“遗留物”说,代表了英国民俗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他以“遗留物”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奇风异俗,以文化进化论来解释“民俗事象的社会功能”。(18)参见阎云翔:《欧美民俗学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与赫尔德对民族文化间差异性认知的理念不同,泰勒是从人类文化一致性的角度,认为人类文化是从低等向高等发展的。安德鲁·兰(Andrew Lang)则进一步深化泰勒的“遗留物”说,认为“民俗学,搜集并比较古代种族的非实体的类似遗物:遗留下来的迷信和故事,民族文化那些见之于我们的时代却又不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观念”(19)转引自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他们将遗留下来的民俗事象视为原始文化的碎片,搜集整理这些碎片以拼凑古俗原型。毋庸置疑,英国进化论人类学派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何思敬即主张向英国民俗学学习,以英国民俗学研究为范例来塑造中国民俗学研究。不过,何思敬、杨成志等很快就意识到英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难以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因此杨成志主张借鉴美国民俗学者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术思想。博厄斯提倡“实证主义精神和长期田野调查的方法”(20)施爱东:《民俗学是一门国学——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计划与早期民俗学者对学科的认识》,《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这一思想激发杨成志等深入西南边陲地区进行田野调查。1978年,中国民俗学恢复以后,曾经的“文化遗留物”研究理念卷土重来,闻一多的《端午考》研究被视为民俗学研究的范本,该研究试图证明“现代人无法理解的风俗只有追溯到它们的起源(原型)才能找到它们的本义,这种研究尤其关心‘原型’和‘本义’”(21)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钟敬文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种看待民俗学的范围以及内容项目的见解是比较陈旧的”,“今日世界关于民俗学的范围和内容项目的看法差不多已发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22)钟敬文:《〈民俗学入门〉序》,[日]后藤兴善等著《民俗学入门》,王汝澜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6、7页。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转型,关于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彻底取代了“文化遗留物”理念的研究。
英国进化论派的人类学与民俗学,将民俗看作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认为民俗具有认识古代文化的价值,却不属于现代人生活和文化的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后,部分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会失去的民俗及其价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条例、公约等国际协定指导下,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和研究。如高丙中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留了“遗留物”说的内核,“文化遗留物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遗留物重新成为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机遇”。(23)参见高丙中:《从文化遗留物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日常生活的现代历程》,王文章、张旭主编:《文化认同与国际合作:中国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论坛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高丙中将生活世界理论与遗留物理论相结合,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遗留物在现代社会发生意义的可能性。然而,文化遗留物与民俗文化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在于,英国进化论学派的所谓“遗留物”指的是非生活态的文化,而民俗文化则属于生活态的文化(24)本文中生活态文化指的是当下民众生活中依然鲜活存在、日新月异的文化。非生活态文化指的是历史建筑、考古文物、艺术品等以实体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即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转化、创新的文化。这其实是非遗研究所面临的纠结,即探索如何将一种生活态的文化进行遗产观视角下的非生活态的保护。这种纠结,显然来自于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遗产保护、历史和建筑的遗产保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渡期理念的影响。
1968年以来,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了关于文化财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古迹、建筑群、遗址)、可移动文化财产(考古发掘、古物、艺术品、动物标本、书籍等)等实体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议。这些遗产都是人类历史的遗留物,是非生活态的,不会随着民众生活共同发展,是需要在分类和评估价值后给予保护措施的。1989年以后,教科文组织曾讨论生活态文化的保护,其名词从“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民俗和传统文化)改为“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建立了代表作名录。这种保护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非生活态文化保护的某些举措,即主张文化分类以及强调抢救濒危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非遗研究中,被命名为非遗的民俗文化常以濒危性、传统性、价值性为评估标准,最濒危的文化遗产往往会被采取优先保护原则、静态保护原则,试图以保护为手段保持或恢复其原型。这种将民俗文化视为遗留物的保护举措,是将生活态文化进行文化形式的保护,促成了当前非遗研究“遗产观”的形成。非生活态文化不存在主体的文化传承和创造的问题,其保护的原型是确定的,而生活态文化却是与主体紧密关联的,是随着民众生活实践而发展变化的,无法确定其真正的文化原型。套用非生活态文化保护理念来追求原型、原生态的保持,只会使非遗研究的对象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剥离,正如刘铁梁所言,“忽略了民俗与人不能分开的特质,忽略了民俗只有在当地生活中才能承载的内部意义和功能,因而过早地将民俗文化从生活中分解出来,作为‘遗留物’来展览”(25)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显然,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其实是与早期民俗学的“遗留物”说相关联的。不过,“遗产观”并不等于“遗留物”说,“遗留物”说只强调搜集整理和研究,而“遗产观”则强调对文化形式的保护,并由此强调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民族根性价值、经济价值等,因此会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影响。
2.系统分类的认知与生活整体研究的不同
非遗研究的“遗产观”,将文化事象与生活整体相分离,以分类学的眼光去研究其文化史、存续现状,进行保护对策研究。这种研究范式,首先是受到教科文组织的国际文件和国内文件法规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类的影响。如《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十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26)《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8-03/28/content_5917.htm,发表时间:2008年3月28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18日。。非遗研究作为保护工作的一部分,必然要在遗产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即使有主张整体性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文化生态保护区这一文化空间类型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其次,非遗研究的系统分类观受到早期民俗学分类化、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影响。民俗学者是当代中国非遗研究的主力军,民俗学曾经的学术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遗研究的方法。在中国民俗学奠基时期,分类的方法是当时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深受“逻辑实证主义”(27)赵世瑜:《眼光乡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的影响。周作人曾将歌谣分为“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和儿歌六类”(28)赵世瑜:《眼光乡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9页。,钟敬文也对故事类型进行了分类研究。新时期以来,民俗学学科恢复后,也曾将民俗事象进行分类式的、文化史钩沉式的研究,并视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查阅《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的目录,就将刊载文章分为“卷首篇、论坛、人生礼仪、乡社民俗、饮食民俗、岁时节日、建筑民俗、信仰与禁忌、游艺与竞技、史前民俗、域外民俗、信息”等栏目。20世纪80-90年代,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中国民俗与民俗学》、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等概论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对民俗事象的分类。非遗保护运动兴起后,“现有民俗学概论的概念和分类体系成为了这一工作所直接参考的学术根据”(29)刘铁梁:《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民俗研究》2017年第3期。,而非遗研究对文化事象系统分类的认知和研究就由此被确定下来。
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毕竟具有非常鲜明的历史相对性。文化,很难像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切割分类。当代中国民俗学意识到分类化的观念是对生活的肢解,生活文化并不能以民间美术、民间音乐等任何单一类型进行认知。20世纪90年代起,民俗学者开始从分门别类的民俗事象文化史研究,转向对整体性生活的研究。高丙中受到萨姆纳和胡塞尔的影响,提出“生活世界和民俗生活”的研究理念。所谓“生活世界和民俗生活”的研究,指的是囊括民俗主体和发生情境的整体研究。刘铁梁将村落视作一个民俗传承的有机整体,是民俗学应该调查的基本空间单位,“村落,在民俗学界作为研究单位被发明出来,它的学术意义在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空限定性,以及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整体研究”(30)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此后,许多学者的民俗学研究和民俗学专业博硕士论文都以具体时空中村落生活为基本研究单位,促进了民俗学研究面向生活整体的转向。21世纪后,美国的“表演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发生重要影响,中国学者并不拘泥于鲍曼研究中的民间文学讲述与艺术性交流,而是以表演理论为理论依据,转向面对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时至今日,面对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已成为民俗学朝向当下的重要研究范式。
近些年的非遗研究,也提倡“整体性保护”“语境研究”等,这显然是借鉴了上述民俗学前沿理论探索的影响,如“语境研究是非遗整体性研究范式的重要方法,即在具体的活动情境中研究非遗如何被生产、如何呈现、如何被接受、消费以及传播等过程”(31)汪欣:《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整体论”范式》,《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等等。不过就总体而言,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生活整体理念仍有明显不同。以胶东饽饽研究为例。民俗学研究在探讨胶东荣成市院夼村胶东大饽饽时,首先是将其置于“地方之俗与国家之礼”的社会互构网络之中,从节俗特定食品深描渔村的地方传统、文化记忆、劳作模式与交往行为等,以及民众在人地互动、礼俗互动与人际互动等多元互动关系中的生活意义建构。(32)参见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总序),齐鲁书社,2019年,第10页。也就是说,民俗学研究是在具体生活时空中,关注民俗现象如何发生、传承和再创造的过程,将民俗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表现予以整体观察、体验、理解与阐释。民俗学研究的学术目标,是发挥其特有的田野调查优势,讲好老百姓如何继承发扬自身文化传统的生动故事,并以小见大地深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体认与理解。相形之下,非遗研究受到研究目的和性质(即配合各项非遗保护工作)的限制,很难从社区生活本位、实践主体观出发对具体非遗项目予以深描,从而与如上所述的民俗学生活整体研究视角有别。
3.实践主体观的差异
民俗学转向生活整体的研究,也是转向民俗主体——人的研究。非遗研究也会涉及作为非遗项目主体之一的非遗传承人,但一般不会将非遗项目所涉及的社区生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也缺失了民俗学研究已确立的含括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实践主体观。
文化主体,是与文化权力密切相关的术语。“文化主体性”,是费孝通在探讨关于中华文化如何发展、传承、重建时所提出的概念。事实上,“文化主体性”问题关乎谁拥有文化权力,谁拥有文化自主权、发展权的问题。在非遗研究中,虽然也部分发现了文化主体的问题,但文化主体一再被忽视、被混淆,并未真正触及问题核心。比如,有的非遗研究将主体分为“传承主体”和“保护主体”,即传承主体指的是政府认定的非遗传承人,保护主体则指的是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遗保护主体。(33)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之所以出现非遗“传承人”与“主体”的概念的混淆,是因为非遗本质是“一个关于文化分类和价值判断的概念”(34)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研究,自然就容易忽视真正的主体,忽视民俗文化传统,而过度强调民俗文化外价值,想当然地形成了“只要保护了一些‘传承人’身上的技艺或知识,就可以传承民俗文化的想法”(35)刘铁梁:《民俗文化的内价值与外价值》,《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在此基础上,对“传承人”的保护策略研究,是对传承人的客体化和物化,将“传承人”看作国宝大熊猫、金丝猴并探索如何进行保护性研究,探讨出诸如照顾年老传承人的身体、给予更好的医疗保障、送进养老院等保护策略。这些想法,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无可厚非,但是从文化主体研究的角度,却忽视了文化的生活属性,没有意识到非遗的文化主体是创造、传承、享用这一民俗文化的特定群体。
实践主体观是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性观点,是对民俗学当下转型中对“民”的深化理解。中国民俗学的实践主体观,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把所有的民众都当成民俗的实践主体”(36)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这并不是对主体的泛化理解,而是将普通民众视为实践主体,而不是被认定的传承人或者政府、资本等外在力量。民俗是不同地方、不同群体的生活文化传统,也是个人所参与创造、传承、改造的生活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形成深刻认同的生活文化传统。民俗的传承与变异都具有主体间性,是人们在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个体境遇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所做出的实践活动,并不由单一因素决定。民俗学通过研究生活态文化,进而研究具体的人。如近年来颇为活跃的个人叙事研究,就是将每一个个体都视为民俗的实践主体、给予其充分尊重其话语权的民俗学研究。
第二,民俗学研究的是学者与民众的主体间的交流实践。民俗学者在反思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关于局内与局外、客体与主体等概念之后,提出了民俗学是研究民众主体间交流与对话的学问。如刘铁梁所倡导的交流式民俗志,就是一个“依靠民众和学者来共同生产民俗学成果的过程”(37)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这不仅是如何看待民俗主体性的问题,还涉及与主体相关的学术伦理问题。2019年,北京师范大学与山东大学等接力举办的“有温度的田野”系列学术研讨会,聚焦田野研究中学者与民众的主体间性关系问题,主张“文化共情”。在这种主体间的田野研究中,研究者和访谈对象将同时作为主体而存在(38)参见刁统菊:《感受、入户与个体故事:对民俗学田野伦理的思考》,《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以传达二者之间的“视域融合”为民俗志书写的理想状态。(39)参见张士闪:《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民俗学研究不再是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被攫取资料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而应成为“一种主体之间的协商”(40)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这不仅能够推进学术良性发展,而且可以更好地“将研究成果回馈到生活实践中”(41)李向振:《从民俗事象到生活实践——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的知识社会史》,《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第三,中国民俗学对主体地方性的强调。中国民俗学的民族体认研究,是从地方性认同角度进行的,这与美国等国家对群体性的关注有着明显不同。这源自于中华文明的特性,即主体的文明体认离不开与地方文化的情感链接。陈泳超反思那种将传说当做“超有机体”存在的文本研究,认为应将“地方传说当作是当地民众人际交流的一种话语形式”,这不仅认识到了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传说与地方不同群体的主体性建构的关系,而且意识到了这些地方传说与“地方之外主流社会文化进程的多样联系”(42)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朱鹏对于大禹传说和信仰的研究,不再是从中华文明的国族范围内去谈传说的建构和认同问题,而是立足于登封这一地方社会,从地方精英、普通民众两大实践主体对大禹传说的建构和信仰活动的实践,考察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地方标志性文化生产与民众生活意义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43)参见朱鹏:《地方传说文化的传承实践研究——以登封大禹传说与信仰为中心》,山东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
相形之下,非遗研究倾向于以文化保护的外来力量为非遗保护主体,去审视和判断非遗保护实践中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在客观上很难形成对等的、主体间性的学术伦理关系,以及对整体意义上的社区生活文化传统状况的准确认知。
四、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视野的差异性
民俗学研究应面向当下,业已成为当今民俗学者之共识,他们所讨论的是如何面向当下、面向哪个当下等等。有的学者将非遗研究视为民俗学研究面向当下的前沿研究,这与民俗学研究所理解的面向当下日新月异、常变常新的生活世界的理念其实是有着根本不同的。非遗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文化形式濒危状态下进行文化保护的问题。
目前,对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差异性缺乏应有的探讨,容易导致民俗学研究陷入到学术定位不清的危机之中。就学术视野而论,非遗研究是一种“遗产视野”,是研究文化事象形式如何被保持、如何被改变、如何被开发利用的问题,而民俗学则是一种“民间视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明进程视野”。对此予以辨析,有助于民俗学的学术自觉和本体性认知。
1.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根本动机
在人文社科的研究应用中,“视野”不仅指研究对象的范围,还指对研究对象属性、意义、背景等相关因素的认知方式,如文化视野、空间人类学视野、期待视野、都市民俗学视野等。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研究视野,意味着认知的方式、深度和广度不同,这不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而是由视野决定的。民俗学应有的视野,是以“民间视野”为基础的“文明进程视野”,是在文明类型、文明转型和文明交融背景下,探讨各个地方的日常生活实践内容的研究视野。“遗产视野”与“文明进程视野”,虽然都关注民俗文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本体认知和研究方法却有着根本不同。“文明进程视野”,源自于民俗学建立的根本动机,即真正认知、理解、体认本民族文化。
民俗学研究的根本动机,源自于开端时期赫尔德、格林兄弟等民俗学先驱的思想。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关于民间文学的思想,奠定了德国民俗学的学科基础,而他深受17世纪思想家维柯(Giambattis ta Vico)的影响。维柯认为一个民族的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创作,“可以发掘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习俗”(44)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赫尔德吸收借鉴了维柯的思想,从民歌中探讨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他认为“民歌是民族的档案,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印记,民族活着的声音。从民歌中人们能够了解到民族思想的模式及其情感语言”(45)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赫尔德反思了启蒙主义中人类人性的普遍一致性观点(46)参见王杰文:《反启蒙主义与民俗学——以赛亚·伯林论维柯、赫尔德》,《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6期。,强调了主体性和主体间的差异性,表达出主体对民族文化特有认知的情感和欲望。在维柯、赫尔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雅格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im Grimm)搜集整理德国民间故事时,将民间创作视为民族智慧。格林兄弟的民俗学研究,直接服务于他们重建德国民族文化、抵御当时的法国威胁的政治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们著作中的一条主线。(47)参见阎云翔:《欧美民俗学略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早期德国民俗学深刻地影响了世界范围内民俗学的发展,其传统是“浪漫主义、尚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奇特的结合”(48)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挪威、芬兰等国的学者,纷纷“搜集整理自己民族的古老神话、歌谣,重建正在失去的民族精神”(49)刘晓春:《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法国学者福瑞(Claude Fauriel)出版《现代希腊民歌》,认为这些可以反映希腊的民族精神。英国汤姆斯(William Thoms)也受到德国格林兄弟等人研究的影响,“参考了德语中表述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词语‘Volkskunde’(民众知识)”(50)[日]岛村恭则:《大家的民俗学》,陆薇薇、魏金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1页。,用“folklore”指代民众的知识。“folklore”一词传到亚洲,日本学者将其译为“民俗学”。柳田国男将日本民俗学定位为“一国的民俗学”,即研究日本和日本人的学问。现代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的“亲子心中”等研究,事实上也离不开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
汤姆斯等英国人类学派关于“folklore”的思想传入中国,刺激了20世纪初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但早期民俗学研究活动并未拘于英国人类学派“遗留物”说和文化进化论,而是响应中国社会对重塑民族文化传统的需要。“歌谣运动”、白话文的兴起和学者的调查行动,是一个审视传统精英文化、重建民族文化和发现民族精神的过程。顾颉刚等人在妙峰山香会调查后认为,“在这种民众运动中,看到‘民族中的下级社会的文化保存着一点新鲜气象’,而他们认为这正是拯救民族衰老的‘强壮性的血液’”(51)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129页。。钟敬文在总结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兴起时,认为当时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体现着民族社会生活及其多数成员的思想、感情和创造能力”(52)钟敬文:《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呈献于顾颉刚、董作宾诸故人之灵》,钟敬文著、董晓萍编:《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133页。。钟敬文晚年在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精英文化、民俗文化以及西方外来文化时,倡导建立民俗文化学,他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民俗学与关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这与全球范围内民俗学研究兴起的根本目的紧密相关,即从“民族整体文化”观出发认知本民族文化,正确看待“民俗文化的民族凝聚力”(53)刘铁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的学科性质及方法论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以此更好地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交流。2021年7月26日和9月13日,刘铁梁在山东大学的讲演《文明视野下的民俗观》和《再论文明视野下的民俗观》,明确提出了“文明进程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他认为,中国民俗学如何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与当代进程的研究发生紧密联系,是当下民俗学不可回避的问题意识。(54)刘铁梁:《文明视野下的民俗观》,2021年7月26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1年中华古典学术传承创新暑期学校。这一学术视野的提出,是在国内外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和前沿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深化了赫尔德、钟敬文等前辈学者的学术思想,努力使民俗学研究与当下研究实际相结合,真正与当下生活文化变革相结合。
2.中华文明进程与民俗学的学术使命
文明进程视野,事关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和研究方向。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古文明。关于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类型和进程的问题,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都贡献了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如塞缪尔·亨廷顿将中华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5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页。,认为中华文明并非仅是法律意义或者地理意义上的共同体,而是基于文化、血液、种族等认同的共同体,哪怕远离故土的华裔仍将自己视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汤因比从中国传统儒教治国制度层面解读中华文明,发现在部分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56)[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费孝通认为中华文化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57)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2页。,马戎则认为中华文明的主脉是“中原文化传统”(58)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基本特质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59)马戎:《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凝聚力。然而,中华文明进程不仅是政治、经济意义上的转型进程,更是广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心理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转型进程。再看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思想,是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探讨文明类型和文明进程问题,因而特别关注“社会结构变化和人的行为、心理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60)[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54页。。这启发我们,秉持“文明进程视野”的民俗学研究,应从以民众的心理、行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文化变革出发。
“文明进程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是认知中国社会秩序和中国生活方式的研究。当前民俗学已做出了大量的研究贡献。例如,刘铁梁提出“劳作模式”的概念,以“观察村落集体在进入市场经济过程中日常生产行为模式的变化”(61)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事实上,现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体制带动了大量村落劳作模式变革,山东曹县孙庄村的村落劳作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了“甜秫秸、蔬菜大棚和外出打工的三个阶段”(62)尚小芳:《互联网与新型的村落劳作模式——以鲁西南孙庄村为个案》,山东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近些年随着互联网发展、物流便捷和汉服产业兴起,加工销售演出服和汉服已成为该村新的劳作模式。劳作模式的变化推动了当地民众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和村落认同的改变。购买县城楼房成为民众爱子的新途径。服装加工厂的工作促进了女性家庭地位提高和家庭代际关系变革。“淘宝村”的称号成为该村村落的标签,也是村民文化认同的新标志。张士闪所倡导的“礼俗互动”研究,是对中华文明内部社会交流互动秩序的深刻体察与准确认知,这证明中国是与西方“契约社会”差异明显的“礼俗社会”,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文化传统的坚韧性、能动性、包容性都与此有关。(63)参见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这些研究均体现出民俗学对文明进程和文明类型的研究和理解,而其根本方法则来自于对民众主体实践的长期观察与以文化共情为基础的感悟。
中华文明进程的特性并不仅仅存在于制度、典籍和考古文物之中,更是具体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行为、感受等日常生活中。“文明进程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进行宏大叙事和宏大论证,而是进入大众日常交流领域,采取中华文明独特历史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结合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理解来进行民俗生活文化实践的具体考察和研究。“文明进程视野”下的民俗学研究的学术抱负,是难以通过对某些文化形式的保护研究和政府政策的落实、改进性研究来实现的。这或许就是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根本不同所在。
五、结 语
对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差异性予以辨析,是因为民俗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这一需要并不仅仅是文化形式保护的问题。非遗研究与民俗学研究的不同,不仅表现在研究性质、理论与应用等方面的差异,而根本在于研究视野的不同。民俗学所要着眼的研究,是应该在“文明进程视野”下形成更大更自觉的研究方向,而非遗研究作为工作性质的研究,只能成为这个大方向上的局部。这个局部的存在,并不是要延续“遗产视野”的研究,而应通过非遗研究,理解非遗保护运动对民众文化观念重塑、地方性文化身份认同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民俗学者参与非遗研究,应对此有所承担,而不能以局部替代其整体研究,更不能将两者混同,偏离民俗学研究发展的大方向。
通过“文明进程视野”和“遗产视野”的比较与辨析,我们应对民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和学科作用有更明确的认知。扎根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民俗学,有着关怀国计民生、“学以致用”的本土学术传统,应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