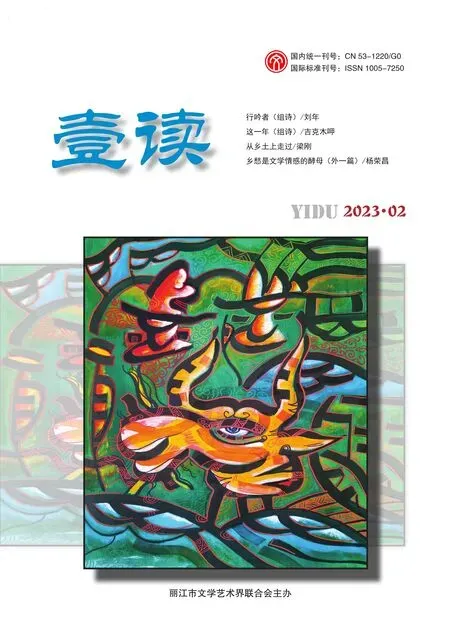桃李芬芳
◆朱弦
一
清晨,天空湛蓝,白云恣意挥洒,呈不规则状晕染开来。在马路上挥动着双臂,在流动着的风景之中寻找一种紧贴大地的平衡,撞见带有生命光泽、寓意着希望的绿。视线越过群山与房屋,思维不断跳跃、扩散,也许相似的记忆之间相联通,开启它们需要在特定的心境下输入岁月的密码,抑或者记忆本身被压抑与埋藏,它们呼唤着,渴望冲破桎梏的牢笼。
我没有读过真正意义上的高中,便直接上了大学,相比之下,初中的那段读书经历更显得弥足珍贵。整理旧物时,朋友手写信纸上的笔迹,笔友精心勾勒的画作,还有那时流行用废纸编织的“菠萝”,都使我的内心掠过一阵欣喜一阵颤动,接着我的眼睛停留在一只水性笔上,那是一只教师专用笔,握住它,只觉得比平常的笔要沉重,涂抹着一种岁月的质感。它本不属于我,在我将要离开初中学校时由老古董递到我手里。
他从三十里外的金兰转到桐梓中学,既是任课老师,也是我所在的163 班的班主任。接手这个班级不久,他才迎来三十岁生日。相对于学校的其他老师来说,他较年轻,但教学中年轻并不占据优势,它意味着经验的缺失,还有因理想与现实的冲撞产生的矛盾。他对我们说,这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班上的同学怀揣的心事各有不同。事实上日后确实如此,这个过程中不仅是一种关系的磨合,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搅动着生活。
照片上的他一脸严肃,而生活中他大多数时候都流露出一种近乎憨厚的笑。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微笑是一种把握分寸的经验之美,有些场合中不适宜用微笑来展示内心情绪,它会吞噬威严,从而演变成为懦弱、好欺负的象征。然而他过了一年以后才逐渐控制住这种笑的行为。我那时认为他太愚,可我未曾想到的是一个人成年后的习惯多么难以改变。他自然流露出的真诚的笑就这样被抑制,退居其后如湖水中隐约可见的倒影,看似真实却又令人捉摸不透。
和班上同学接触不久,他的性格弱点便在我们面前暴露无遗。优柔寡断的性格使一些同学在他面前放肆起来,尽管他老在我们面前唠叨纪律之类的问题,在我们不过是左耳进右耳出。不过这些我还不敢表露出来,我是班长,怎么说也得带个好头。我预感到他这副老好人的形象不适合当班主任,其一学生不听他的,其二很难承受随之而来的反作用力。
没过多久,我们班成为了学校的“有名班级”。上课时班上同学说话,吃东西,甚至一言不合打起架来,也是常有的事,平常的考试成绩也是我们班垫底,为此他应该没少受领导批评和任课老师的投诉,这是我后来猜想到的。但他把这些负面情绪隐藏起来,见了我们依旧一如既往地笑,甚至于开班会时他竟对纪律和成绩一笔带过。
那时的我心高气傲,当他试图用我的例子作为“反面教材”——让班上的第一名证明自己没有作弊,我大光其火。也许在别人看来此事轻若草芥,可孤傲的我无法接受来自众多眼睛的质疑,冲他大声嚷嚷。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异,没想到我的反应竟会如此过激。他露出和平常一样的笑,眼睛在笑的时候便眯成了一条缝。
自此,他的印象大大跌落,班上同学大多也对他流露出抵制的情绪,他就像置放在现代社会的老古董,与我们如此格格不入。古董的价值主要用于收藏,它的本能是适应环境而非试图改变环境。老古董则像是古董中与众不同,顽固不化的一类,坚守旧有的思想与原则,在现代环境中试图占据一席之地。于是,“老古董”便一度成为他的外号。
说教已不起作用,为了应付班上这种混乱的场面,老古董开始坐在教室后面听课,日日如此。一些调皮的男生有所收敛,他们夹着黄鼠狼的尾巴防止在他面前暴露本性。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相安无事时,一次下课时敏却告诉我:“出事了!”教室后面围了一大群人,班上同学伫望着,寂静无声。敏拉着我硬往里面挤。老古董和一个男生正进行着一场搏斗,他们各自出手迅猛,拳脚落在彼此身上,并不像电视里面自带音响效果,由于周围的人屏息静气,那种声音仿佛是通过空气里的紧张情绪传来,无限放大,无限漫展,整个教室的气氛笼罩着一层暴力和反暴力,而我只是作为一个观者,这个过程如同在课堂上等待下课铃声的煎熬过程一样漫长。最后那个男生败下阵来,老古董怒气冲冲地问:“还有谁不服我的?”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去,他的威严如空气里的分子渗透开来,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这和平日里笑着的他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二
乡村的孩子是迎着风长大的,春风轻柔,冬风肆虐,四季轮换,一个个长成了少男少女的模样,那些野性的或者不堪提及的回忆便遗留在了风中。进入青春期后,男生把性格中的野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像黑暗中的豹子,攻击性与防御性共存,身体里跃跃欲试的能量伺机爆发,他们渴望得到一种成熟的身份确认,渴望挑战权威。相对于男生,女生似乎更加早熟,她们各自潜藏着身体的秘密,显得安静、温顺,像惹人怜爱的绵羊。
在六七十人的集体里,矛盾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老古董尝试在关系的磨合中寻找一种平衡,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消耗着年轻,在这个过程中我既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某个清晨,在教师宿舍门口见到他时,他顶着一双熊猫眼,眼里布满了血丝,由于过度操劳他看上去已不像是三十岁。他望见我后微微地笑着,眼睛只剩一条缝,眼袋浮肿。他的这一笑,让我不知所措。班上的各种事务一茬接一茬,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被各种事情包围着,喘不过气来。
学校的冬天是漫长而难熬的,一出门,手与脚都冻得冰凉。这天下午,老古董的课堂上又睡倒了一大片。我听说男生晚上十二点还不睡,吵闹的声音甚至殃及周围的寝室,而一到白天他们大多数人趴在课桌上呼呼大睡。望见老古董那恨铁不成钢的神态中隐隐流露出失望与悲愤,而我和同学们的心过于稚嫩,过于习惯他人的给予和付出,并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长大后我们回想起来,迟来的歉意与愧疚才从心里涌出。
那次老古董特地凌晨披了件衣服,走向男生宿舍。冬天晚上的风裹挟着刺骨的寒冷。一阵风从外面灌进来,呼啸地来回刮着,震得窗户不停地响。一块玻璃上破了个洞,约有半个手掌大,风一刻不停地灌进来,整个寝室不免让人感觉到一丝丝阴冷。他折回教师宿舍,取来锤子和硬纸板,开始修补窗户。男生在睡梦中继续做他们白天没做完的事,锤子敲落在窗框上的声音没能惊醒他们。
“留守儿童”是我们大多数同学常会在电视上听到的一个名词,可我们不情愿接受这个称呼。当十二三岁的表妹在纸上写下“爸爸,我想你了。我多么希望你能回来陪我”诸如此类的话语,然后折成千纸鹤,在日复一日的盼望中染上岁月的尘埃。我的心会在此刻变得柔软起来,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同龄人也大多如此,这份缺失在我们那个偏僻的村庄过于普遍,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但它又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每个人身上。
老古董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他从我们身上看到多年前的自己,因此他懂得我们行为背后隐藏的动因,更多的是给我们以包容。他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并不把成绩差的学生归为不可教的一类,而是给予他们同样的关怀和照顾。后来我没有听到班上任何一个同学说他的坏话,这也让我颇感意外。
夏天来临后男生的胆子也更大了起来,男生厕所里的窗户的钢筋被弄断了两根,他们在夜里轻而易举地爬出去,有的溜出去上网或者偷村民的瓜。男生晚上不睡觉,白天自然精神状态不好,上课老趴在课桌上。
但没过几天男生每天竟精神抖擞,如同受伤的老虎恢复过来。我始终没有料到他们的变化为何如此之快,通过一次偶然的事件我才知道老古董睡在男生寝室。我从敏那里得知,凌晨的时候,老古董6 岁的儿子半夜醒来时发现爸爸不在身边,他走出门外大哭,哭泣声在夜里惊醒了其他老师。于是,这件事便传开。
我这才想起老古董只身一人带着孩子,他的妻子在外打工。一个中年男人独自带孩子,在农村并不常见。洗衣、做饭、陪他做作业,老古董把他对孩子的爱倾注在这些琐碎事务上,加之处理班上的事务,担任三个班的任课老师,在校时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休息时间。由于乡村教师的工资不高,老古董甚至暑假也会去大城市里的工厂里打工。
初二下学期,班上已有一些同学陆续辍学,他们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外出打工。有些人学习一门技术,有些人进入工厂,还有些人从事于服务行业。村庄的贫瘠与落后仿佛映衬着庄稼人一生凉薄的命运,漫长的读书生活使他们感到厌倦和疲乏,于是选择逃离。面对这种情况,老古董常鼓励班上的同学考高中。他开班会,找同学谈话,后来又给班上的同学补习。他教物理和化学,每天在自习课时抽一些同学去他那里背公式、做题。他常常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的手里抓了六七十张扑克牌,这是六七十个学生的命运,因此他常想自己多做一些,每张扑克牌的人生格局也许就会发生改变。
一个周五的下午,放学后老古董拦住我,说想到我家去看看。于是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一路上我心神不定。那时正值破败的冬日,山坡上的草木枯疏,枯黄的树叶无精打采地粘在树梢,略显荒凉。他和我爷爷站在屋前聊天,他有时也接上几句,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倾听者。我站在窗前窥探着他们的背影。这时我突然觉得他的背影多了一份亲切,那些排斥与过失随着时间逐渐淡忘,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未长大的孩子,那些稚嫩不过是树枝上抽出的新芽,在新旧交替的季节里,包容施展它的魔力,那些有意或无意的过错与冒失都可被原谅。
三
面临中考前的体育测试,老古董带领我们在学校外面的马路上跑步,六七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蔚为壮观。由于我体质弱,他常提醒我多加强体育锻炼,我终于下定决心,每天早自习前在乡间的马路上奔跑。天刚蒙蒙亮,出了校门便是稻田,远处连绵起伏的群山互相依偎,整个世界仿佛是睡着的,连空气也是静谧的,野草的芳香沁人心脾,还有那种混合着泥土味道的乡土气息。
新学期意味着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墙壁上倒数的日期由三位数变成两位数,揭示着考试前凝重的氛围。对于班上同学来说,若没有考上高中,不读职业中专,他们的读书生涯也就告一段落。这种压力与紧迫感我与他们感同身受,报考公费师范生后,我感到与他们的心情有相似之处。这个目标像是长跑时遥不可及的终点。我了解到公费师范生在每个县里只分配了不多的名额。中考仅是一道初试的门槛,报考的人多,所划的分数线就很高。
然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我的成绩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其中一个客观因素在于我曾一个学期不听老古董的物理课,上课时唯独我一人埋头在练习书上做题。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学习犹如建一座空中楼阁,即使建得再高,迟早是要塌下来的。加之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关卡,情绪低落,成绩一落千丈。那段日子我只感觉到黑暗如一块巨大的幕布将我紧紧包围,我试图冲出去,没有力量,也没有方向。这时我想起了奔跑,奔跑是无数次回望与眺望的过程,在这种动态的平衡中便可以暂时忘记自我的存在。我盼望在这条乡间的路上无止境地跑下去,跑离痛苦和沮丧的根源,压力与紧迫感便能得到释放。复习后的夜晚我常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潜意识中,把忧虑与恐惧涂抹在设想的未来里,也在现实的迷宫里迈不开步伐。
老古董觉察到我的反常,他主动找机会和我聊天,并询问我的学习情况。那时我已搬出了女生宿舍,和他住在同一层楼。晚自习后,他便让我去他宿舍,给我讲解练习题。他的卧室里只摆放着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在这间窄小的房间里,灯光充盈着四周,透过窗户望去,外面一团漆黑,夜已深,偶尔,一些虫子不厌其烦地叫。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他动笔写下的大号字迹,他讲完一个题后,又担心地询问我是否听懂。那些论证很清晰,步骤说明其依据,想必是为了让我再次看到这个题目时能理清一些思绪。而此刻他的孩子已躺在床上入睡。我的心中陡然升起对他的感激,仿佛一个被迫在水上漂泊的人寻觅到一艘船,也对当初的执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不过是用幼稚与骄傲围成的一层心理屏障罢了。
我逐渐摆脱了焦虑和彷徨的情绪,在他的补习下寻找到以前的自信。一天晚上,一个同学来到我宿舍,说老古董让我去喝粥。我正犹豫着,同桌却已给我端来。后来,老古董几乎每天都会熬上一大锅粥,分给其他老师,叫上班上的同学来他寝室喝粥。中考前的复习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他担心班上同学营养跟不上。而男生一来,一大锅粥往往一扫而光。
紧接着,有消息传出说老古董给我们的任课老师送礼,这让尚未通晓人事的我感到费解。他的生活并不宽裕,在我的印象中,老古董平时穿着朴素,往来学校骑一辆旧式摩托车。他和妻子既要赡养老人,还要供他的儿子读幼儿园。送礼的初衷仅是为了班上同学在中考前更好地复习,就像一个人听说风能使种子长得更快,他便竭尽全力去寻找风的下落。这也许是一种迷信,在另一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信仰。
距中考还有两个月,他精心组织了一次班会。班会的主题是我有话对你说。他娓娓道出这三年的一些经历,面临中考,他说出对我们的希冀,最后袒露心怀:“我相信你们,我爱你们。”在乡村,“爱”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并不高,记忆中他从未用过这个字眼,他习惯用行动表达感情,而不是用话语,就像他习惯久而久之的内敛和含蓄,而不是大胆和奔放。此时他早已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孩子,即使我们犯错,不听劝告。班会上每个同学写下寄语,他一直保存着一份纸稿。
后来,老古董掏出相机,给班上同学拍照,他新买的相机里存下了我们的很多照片。那些日子和记忆被风吹散,连同离别的不舍与往日的眷恋。离别,有时看似很远,有时不可思议的近。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就像遗忘的秘语在耳边再次响起,人是害怕遗忘的,画面定格在某一瞬间,那些秘语相互联结,构成往事经久不散的错觉。我再次来到他宿舍时,他递给我一支教师专用笔,说是给我留个纪念。那一刻,我倏然发现,他男性的外表下隐藏着细腻与温情。我离开了这个熟悉的房间,离别在即,很多感情的表达在说与不说之间选择了沉默,又或者,沉默才是最适合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说与不说、变与不变之间,回忆成为另一个层面美的体验和自我身份的确认。
四
偶然有一次,我在乡村见到初中班上的一个男同学,他初二便辍学,随父母到外地奔波。许久未见,他对我说,以前在班上和男同学打架,受伤后,老古董帮他垫了几十块钱的医药费。说完这话,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准备趁这次回来去看望老古董,顺便补上以前的医药费。这时,话语反而显得苍白和无力。记忆的密码是一种情感的沟通与唤醒,有些事,不说,不是已经忘记,而是为了更深沉的纪念。
五年后,我进入老古董的QQ 空间,里面存留着许多班上同学的照片、由班会记录写成的日志和一些心情随笔。他仍在桐梓中学教书,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为了生计在外打工,为数不多的人继续着学业。人生轨迹从汇聚的一点散开来,铺陈成为各自纷呈的命运。他以前的外号预示着老古董的价值,时间愈久而愈显珍贵。提起老古董,内心深处有一份沉甸甸的重量,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直到记忆也模糊起来,我们仍无法忽视这份情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