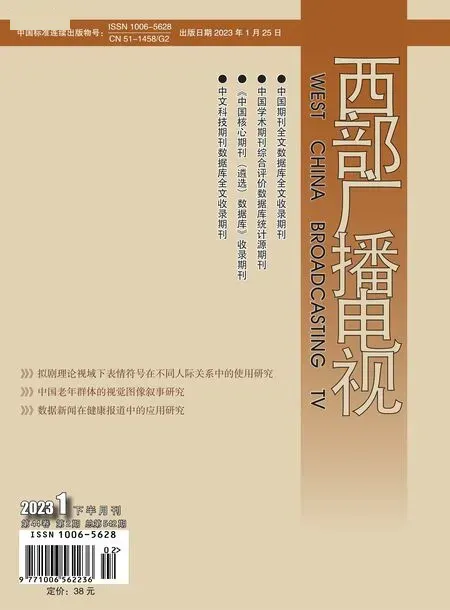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叙事模式
张司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民族发展历史脉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电影也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新起点上[1]。在中国电影史中,“父亲”角色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父亲”不仅代表真实的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也具有能指的象征意义,即“以父之名”[2]。中国家庭伦理关系中,父子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深受历史与时代背景的影响,因此研究新时代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具有现实意义。
电影叙事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论证电影的叙述方式,每个故事因其叙述策略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叙事结构[3]。在故事层面,理论家聚焦于事件和人物的结构;在话语层面,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时间安排、观察故事的角度等成为主要关注对象[4]。叙述体现为叙述者与接受者作斗争的过程,叙述者将事件按照一定的方式和设定展现给接受者,并利用各种可能性控制与影响接受者[5]。因而,概括来讲,叙事模式偏指叙事结构,并兼含或至少影响叙事话语[6]22。本研究梳理2016—2021年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分别为《八月》(2016年)、《乘风破浪》(2017年)、《向阳的日子》(2018年)、《银河补习班》(2019年)、《了不起的老爸》(2021年),对这些电影进行叙事模式分析。
1 人物关系:聚焦小人物父子相融、共同成长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父子关系受到儒家思想与封建王朝礼节的影响,父亲形象多表现为“权父”“慈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大多被树立为政治信仰坚定与道德品行高尚的长者形象[7]。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中,父亲完成了从乌托邦的想象空间向世俗现实空间的转换,在世俗状态下脆弱得有些崩溃的父亲取代了神话般的英雄父亲。第五代导演通过对父亲的精神谋杀实现了对自己脆弱生命的体察[8]150,“弑父”电影诞生。第六代导演的叙事则更进一步,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父亲的缺席或者处于弱势,这种“失父”状态使得找寻自我人格外化的“精神之父”成为一种需要[8]216。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对父权的崇拜再次成为中国影像表达的重要特征[9],“崇父”情结在新生代电影中多有体现[10]。
近年来,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叙事具体表现为“崇父”与“审父”的平衡与交融。“审父”可以看作是父权社会下的传统与反叛的平衡,即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审视“理想之父”的群体形象[6]18。《向阳的日子》中,儿子向阳一直住在乡下,和奶奶相依为命,直到奶奶去世,向阳不得不回到父亲再婚后的新家。尽管父亲张恒远对向阳十分照顾,陪他吃冰棍,为他布置房间,教他骑自行车,准备神秘礼物给他,房子塌后将他护在身下,但是向阳依旧是孤独、无助和困惑的。影片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向阳与新环境的格格不入。向阳虽然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些许温暖,也在父亲教他画画、陪他捉鱼玩耍的过程中产生依赖的情感,但他依旧是警惕的,依旧以审视的态度面对父亲。影片中向阳对父亲一直是直呼其名的,直到最后才在他人面前承认张恒远的父亲身份。
《银河补习班》展现了一种理想的父子关系,影片“崇父”情结浓厚,但“审父”元素依旧存在,并在父子相处的点滴中得以呈现。父亲马浩文是东沛大桥的建筑工程师,因为替整个设计院“背锅”而锒铛入狱,错失了儿子的成长过程,也使马飞被同龄人欺负。面对儿子的质疑,马浩文对儿子说“桥会塌,但爸爸不会塌”,并用实际行动重新赢得马飞的信任,如帮儿子逃学,陪儿子看展览,为了生计去卖血,被人欺负时保护儿子,在生活中教会儿子人生道理等,最终马飞在父亲的鼓励式教育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宇航员。但看似理想的父子关系背后存在现实裂缝,马飞为了自己的事业,阻止父亲继续为自己洗清冤屈,比起父亲的尊严,他更在意自己的名誉与前途。可以看出,马飞崇拜父亲的才华,认可父亲的教育、付出与地位,但就像父亲送他的地球仪已然被他人损坏一样,父亲的形象已经跌落神坛进入世俗社会,难以复原,在“审父”过程中,马飞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比父亲的更加重要。
“崇父”与“审父”的同时存在使得“父权”的重建过程变得隐晦,在“父子相融”的温情脉脉中,脆弱的“父权”得以彰显[10]。近年的父子题材电影中,一方面,影片多为现实主义题材,以平民视角观照常人苦乐生活[11];另一方面,影片多注重代际沟通,强调逐渐淡化父子矛盾,父亲往往作出某种妥协,并在与儿子相处的点滴中与他共同成长。《八月》的故事发生在呼和浩特,北方的工业小城里濒临下岗的人过得压抑而忐忑,小雷的父亲便是其中一员。尽管生活不堪,他仍在八月实现了儿子想要上三中的愿望,让儿子平稳度过燥热又美好的暑假。在相对平凡又舒适的成长环境中,儿子开启下一段旅程,父亲也选择低下高贵的头颅去做场记。《向阳的日子》中,张恒远则褪去传统意义上父亲的威严,他更像是儿子向阳的朋友,父子俩一起吃很多根冰棍造成腹泻;教儿子骑车却不小心使他摔倒;陪儿子一起下水抓鱼、上房藏礼物……这些事情诠释了父辈对子辈的歉意与愧疚,卑微又脆弱的父亲爱子心切,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消除父子间的隔阂。
2 叙事策略:通过身份错位的多样表达实现父子和解
人作为社会关系网格上的节点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个体通过网格中的“角色丛”占有一定地位与身份,由于每个人对角色认知不同,因而自我认知与网格身份认知常常产生矛盾。身份错位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根本上体现为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认同与对他人的认同。身份错位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在影视作品中得到延伸与发展[12]1。魔幻与科幻元素培育了观众的观影认知习惯,也使身份错位叙事策略更易被显性表达。美国电影《雷霆沙赞!》打造了一位在年龄、能力、性格上与观众审美期待有明显身份错位的超级英雄,而这一角色自身也要克服少年与成人、无意识与有能力等身份错位带来的矛盾[13]。身份错位还表现为体验对立角色的身份定位与生活,在此基础上,身份错位延伸出性别、代际、职业的身体互换叙事策略,如德国电影《再生父子》讲述父子之间身体互换的故事,双方在此过程中理解彼此[12]16。
近年来,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包含较多身份错位的设定,并以多样的方式运用在代际关系的叙事中。《乘风破浪》中的阿浪在经历车祸后穿越回20年前父母生活的地方,以兄弟的身份重新和父亲相遇。20世纪90年代末的虚幻情境中,他亲身经历了父母的年轻岁月,亲眼见证了父母的浪漫爱情。发生身份错位后,他感受到了年轻父亲颇具理想主义的青春梦想、和兄弟间的“江湖情谊”以及和妻子之间朴实又热烈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和父亲的矛盾也得到缓解。得知父亲入狱的原因后,他明白了父亲为何在他年幼时缺席家庭生活,间接导致母亲产后抑郁去世,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父亲的所作所为,以之前从未有的视角看到了父亲桀骜不驯背后的斗志昂扬,鲁莽行为背后的赤子之心,冲动之后对妻子的愧疚思念之情,以及从小到大对儿子简单粗暴背后的殷切期盼。此外,身份错位也暗含了父子之间的相似性,曾经的父亲也和阿浪一样希望摆脱束缚,自由自在地实现梦想,而阿浪作为赛车手的野性、固执、追求刺激,也有着父亲年轻时的影子,对阿浪来说,他理解了父亲,就是理解了现实生活中热血的自己。
《了不起的老爸》中的父亲通过“表演”实现身份错位。儿子肖尔东患遗传病,随时可能失明,父亲肖大明为儿子规划好一切,希望他可以学习钢琴,这样即便失明也可以照顾好自己,而儿子只想坚持跑马拉松,完成自己的梦想。父亲与儿子的冲突逐步加深,并在儿子真正失明时达到顶峰,儿子陷入极度低沉的状态并拒绝让父亲照顾自己。于是,父亲只能假扮成无法说话但是会跑马拉松的“赵看护”来照顾儿子起居,这时,父亲完成外部层面的身份转换,从一位管理儿子生活方方面面、限制儿子实现梦想的父亲,变为可以陪儿子一起“做坏事”、帮助并参与儿子实现梦想的同行者,在父子共同努力准备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完成和解。身份错位在其他中国父子关系电影中也有出现,比如《八月》中父亲转换身份的合法性则是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背景下,作为电影剪辑师的小雷爸爸突然失业,失去知识分子优越感的他在周围社会秩序骤然变化后产生身份错位。总体来看,21世纪中国父子题材电影通过“表演”“穿越”等方式,或者是在社会、心理变化过程中产生身份错位,借此叙事策略贯穿故事主线,最终实现父子和解。
3 叙事话语:女性主义下父权的退与守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兴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下的“父本位”文化受到挑战。在当前叙事话语中,父权逻辑正被柔化改写[14],与勇敢的、负责的、内疚的父亲相对应的,是母亲的缺席或“黑化”,《乘风破浪》《银河补习班》《向阳的日子》从不同意义上实践了向父权秩序回归和靠拢的文化立场。
《乘风破浪》中,江湖义气与兄弟情深这种传统男性情谊表达宣示父权文化立场身份,而这一故事中的母亲矢志不渝地爱着父亲,最终因为家庭的重担陷入产后抑郁,乃至丧失生命。与离世母亲相对应的是后期内疚自责的父亲,父亲以弱势的形象回到大众视野中心。出狱之后,父亲独自抚养儿子长大,他不再意气风发,不再抱有幻想。正如主题曲所写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本领的人,我这个家全都靠你”,父亲最终认清现实,心怀愧疚,甚至人生的后几十年都在为年轻时期的鲁莽付出代价,在思念妻子中度过余生。
《银河补习班》则塑造了一位在丈夫困难时提出离婚,在儿子成绩不好时总是责骂、贬低儿子的强势的母亲形象。这部影片从“教育”的话题切入,电影中的父亲在出狱后承担起所有的育儿任务,即使生活艰难也要为儿子创造优越的学习环境。在他的教育理念下,儿子摆脱了“差生”标签,成为优秀的宇航员。反观母亲则不然,她虽然深爱儿子,也能给儿子优越的物质生活,但她的打压式教育让儿子越来越没有自信,也间接破坏了与儿子间的亲密关系。这一对比下,睿智有担当的父亲重新回到叙事中心。
《向阳的日子》中向阳生母早早去世,继母尖酸刻薄,这是向阳痛苦的来源之一,也是父子关系的绊脚石。“父”的存在固然必要,但如若观众从电影中得到“孩子陷入困境源于没有爸爸,强有力的父亲是避免悲剧的根源”这一结论,那么电影就会沦为男权话语的编码[15]。《向阳的日子》的结尾,儿子向阳失去父亲后就失去所有的庇护,他和其他人的世界格格不入,只能蜷缩身体躲到一旁。
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了不起的老爸》呈现出另一种家庭结构,母亲虽然在儿子肖尔东小时候便因病去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在场”的。小时候,肖大明一家幸福美满,妻子是一位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儿子肖尔东和母亲一样拥有运动天赋,从小一家人一起练习奔跑。后来妻子因病去世,儿子常常思念母亲,并励志完成母亲没有实现的梦想,最后比赛时还让父亲肖大明为自己戴上母亲2003年参赛的号码牌。在这一故事中,虽然“父亲”代替“母亲”承担照顾家庭的角色,但是“母亲”并没有完全“退场”,父子是在准备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和解的,父亲、儿子、母亲最终达成梦想的统一。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父子题材电影叙事模式呈现出新的特征,在人物关系方面父子关系不局限于“崇父”的框架,儿子从情感和行为中审视父亲的行为,父子之间相互陪伴、相互成长;在叙事策略方面,父子之间以“表演”“穿越”等方式开展身体错位,强调身份错位前后父子关系的改变,父子间达成和解;在叙事话语方面,近年来父子题材电影在女性主义思潮兴起后转变叙事逻辑,在“退”“守”之间达成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