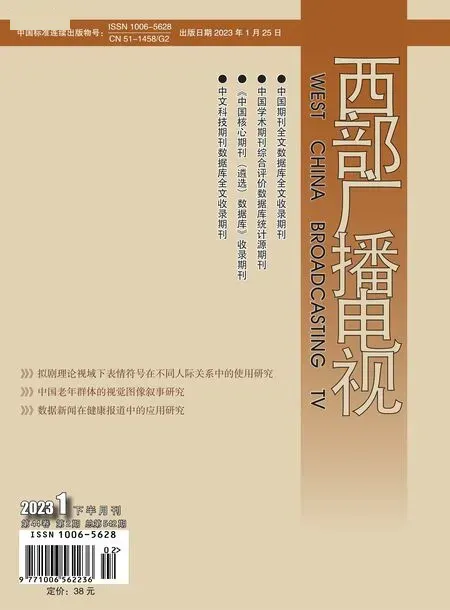大众文化视角下王朔风格城市轻喜剧研究
路永丽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朔热”从最初的文学领域扩展到艺术界、影视界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影响力之深、影响范围之广使其成为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作为大众文化组成形态之一,王朔风格城市轻喜剧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生活的多重面相,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精神缩影。既往很多学者对“王朔热”及“王朔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大多局限于文学领域,影视领域相关研究也多集中在其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方向,较少有学者从剧作家角度出发分析其作品。基于此,本文以王朔风格的城市轻喜剧为个案,探究大众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大众的社会心理。
1 从小说家到剧作家:作为大众文化弄潮儿的王朔
大众文化从早期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发展壮大,其发展史上活跃着一位耀眼的“明星”,那就是作为大众文化弄潮儿的王朔。王朔出现在现代文学的转型期,1984年初,26岁的他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空中小姐》,同年,获得《当代》杂志的文学新人奖。随后又发表了《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动物凶猛》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以鲜明的“痞子”人物形象、机智幽默的口语化语言以及对抗式的故事情节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及作品带来的轰动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促进了当代文学的话语转型,使文学逐渐摆脱“宏大叙事”的单一化表述,变得更加通俗、更加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影视业的繁荣。早期影视剧兼具宣传与教育职能,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转型,影视剧制作逐渐摆脱单一职能的桎梏,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彼时中国影视市场中有政府专项基金扶持的主旋律电影,致力追求彰显电影美学的艺术电影以及强调大众趣味、标榜娱乐本位的商业娱乐片。在艺术电影式微、商业片迅猛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影视剧创作者将目光转向了娱乐,不断摸索寻找艺术电影和娱乐电影结合的新路子,而王朔小说的爆火则为他们提供了灵感、王朔小说剧情循序渐进,语言风格接地气,含有大量人物对白,是天然的剧本原型,且经过市场检验广为大众喜爱。20世纪80年代,对其小说的影视化改编也就成为热潮。1988年,王朔有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这些作品所显现出的市场号召力奠定了王朔在影视界无可争议的影响力,这一年也被称为“王朔年”。1989年初,王朔联合马未都、莫言、魏人、苏雷、海岩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首家民间影视创作机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开始市场化生产,售卖影视剧本,从小说家向剧作家进行转型,《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知名影视剧作品均出自该工作室。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反映城市生活的喜剧电影开始出现,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轮回》(1988年)、《顽主》(1988年)、《大喘气》(1988年)即是这一类电影的代表。这类作品制作成本低廉,以机智幽默的人物对白及针砭时弊的反讽性话语拆解一切看似庄严、实则虚伪的道德和高雅,既不造成现实危害,也使人们在角色的情感投射中获得有关政治或性的自我宣泄,深受大众欢迎。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独特的喜剧风格延伸到了电视剧领域,《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即是这一类电视剧的代表。
2 《编辑部的故事》:直面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
2.1 社会转型与媒介发展:多元召唤下的时代产物
法国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一元决定的,而是多元决定的……任何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有多种多样的复杂原因,而不是由一个简单原因造成的”,进而提出了多元决定的辩证法,认为艺术的起源是多元因素构成的[2]。作为中国第一部电视系列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一经播出便取得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它的流行既源于文本自身的吸引力,同时也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创作团队与受众群体共同“召唤”的产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影视剧创作逐渐摆脱了浓厚的宣传色彩及过于抽象化、哲理化的艺术追求,强调关注大众趣味。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新型职业与组织形态开始出现,形成了市民阶层,其规模的扩大呼唤着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理想与审美趣味作品的出现。有线电视的推广及政策的扶持也使我国电视剧不仅在数量上急剧攀升,而且在题材、内容表现上也更为大胆。在此背景下,王朔等编剧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创作出了《编辑部的故事》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2.2 情节对抗与人物冲突:社会问题的深度把脉
《编辑部的故事》延续了王朔小说的对抗性,透过热点化的故事情节及人物观念的冲突反映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先锋性与贴近性。情节上,它以社会热点话题为切入点,将人们生活中无法回避、令人苦恼、无奈而又严肃的社会议题放在剧中进行讨论,既贴合大众生活又极具前瞻性与抵抗性。如《小保姆》在映射20世纪90年代保姆进城热的同时,也拉近了城乡距离,把社会发展不均衡、城乡差异的问题摆在了大众面前。《吃不消》中,编剧更以犀利的笔触讽刺了社会中的公款吃喝现象,揭露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
《编辑部的故事》一改既往影视剧单面化、崇高化的套路,具有平民化、反传统的特点。在人物塑造上,老陈耐心宽容又有些圆滑世故;老刘善良却又胆小软弱;革命老同志牛大姐热心有正义感却因循守旧、爱上纲上线;中年知识分子余德利口才了得有着生意人的习气;青年知识分子李东宝想法前卫又有些油嘴滑舌,戈玲工作能力虽强却有些高傲。在思想文化聚合的编辑部中,老中青三代人的冲突与差异颠覆了人们对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赞扬、严肃的主流话语被解构成使观众获取“快感”的笑料,既契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自由、平等的心理状态,又展现出社会发展中多元观念的交织与冲击。
2.3 京味儿“侃涮”与深层讽刺:社会问题的“以喜化忧”
《编辑部的故事》延续了王朔一贯的“侃涮”风格,用带有京味儿的台词针砭时弊,极尽辛辣与讽刺意味。该剧的编剧以自己最为熟悉的文字工作者作为全民“开涮”的标靶,充分发挥了北京方言的表现力与冲击力,用通俗的大白话解构时下流行的政治术语与文学话语,使之融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在嬉笑怒骂间将讽刺进行到底,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此外,该剧尽管充斥着大量讽刺,但总体基调是阳光的,它以诙谐幽默的喜剧风格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又在京味儿调侃中消解与淡化社会问题的“问题性”,契合了观众既有的审美经验与心理诉求。
《编辑部的故事》的成功也离不开其背后的创作团队,该剧由郑晓龙任总策划、赵宝刚执导,王朔、马未都、冯小刚任编剧,除了吕齐、侯耀华、葛优、吕丽萍等主演外,连客串演员都是张国立、濮存昕、郭冬临、于谦、英达级别的,可谓大咖云集。作为喜剧,该剧的语言风格虽然是其魅力所在,但也造成了喜剧艺术的缺陷,它淡化了喜剧艺术应有的视觉表现力,完全依靠人物语言营造喜剧化效果,使得人被语言所驾驭,无论是李东宝、戈玲、还是老陈、余德利、牛大姐与老刘,他们只是编剧的传声筒,造成了视听的不和谐性。
3 《海马歌舞厅》:浓缩人间百态的歌舞厅文化
3.1 社会转型与城市化加速:大众文化发展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与城市化加速,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的问题日渐凸显,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焦虑与迷茫。在此背景下,随着欧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流行文化的涌入以及本土流行音乐的发展,集卡拉OK、酒吧、迪厅于一体的歌舞厅逐渐兴起,并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休闲娱乐的前沿阵地。彼时,刚拍完《编辑部的故事》的马未都在朋友的建议下在北京开了一个歌舞厅,然而最终却因多种因素不仅没挣到钱反而亏了43万元,于是王朔提议拍摄一部名为《海马歌舞厅》的电视剧,既可以启迪大众也能挽回些经济损失。
1993年,这部由王朔、马未都、海岩、梁左等“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成员编写的室内情景喜剧《海马歌舞厅》便在万众期待中诞生了,该剧的框架结构脱胎于《编辑部的故事》,一共40集,每一到两集讲述一个故事,在剧情上以北京一隅的海马歌舞厅为故事背景,聚焦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舞厅文化,透过出入海马歌舞厅形形色色的男女及老板(刘斌 饰)、女经理(陈小艺 饰)、领班(梁天 饰)每日的迎来送往中,再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与世间百态,让歌舞厅文化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那个时代极具有代表性的符号。
3.2 黑色幽默与先锋情节:人间百态的深度浓缩
与《编辑部的故事》带有阳光基调的针砭时弊不同,《海马歌舞厅》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讽刺着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带有深刻的抵抗意味。黑色幽默是小说与戏剧中常用的文学手段,它以幽默这种喜剧形式表现生活中的痛苦与绝望,从而带来一种笑中带泪、阴郁苦涩的喜剧效果[3]。《海马歌舞厅》将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富人、穷人、男人、女人、骗子等社会人物囊括剧中,透过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及大胆前卫的故事情节浓缩了人间百态。如在第二集《我是一个兵》中,面对与歌舞厅格格不入进来避雨的军人们,小青年的冷嘲热讽,领班猛子充满市侩气息的抱怨,一掷千金大款“我只抽中华”的优越感,小痞子在军人与老板面前的不屑但在大款面前的唯唯诺诺,再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人们心态的变化,讽刺了社会上的拜金盛行与“有钱就是大爷”的耍酷摆阔风气,剧情虽讽刺但最后通过反转还是回归了温情,表达了对军人的敬意。在那个夜晚,在《我是一个兵》的歌声中,不同身份的人,因为和军队的不同时空交集,获得了相同的身份认同和精神慰藉,用一首普通的兵歌,向军人致敬。
3.3 高开低走:机械复制下艺术“灵韵”的消退
《海马歌舞厅》在播放之初凭借其超强的演员阵容、知名的制作团队以及新闻媒介的有力宣传未播先火,在当时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然而播出之后,尽管该剧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电视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却招致众多批评。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到,商业化所带来的艺术作品的批量复制一方面使艺术更加平民化,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艺术作品“灵韵”的丧失[4]。20世纪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媒介工业的兴起,影视剧的商业价值得以显现,《海马歌舞厅》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艺术灵韵淡化及商业属性凸显的问题。
《海马歌舞厅》内容涉及社会热点、爱情婚姻、家庭伦理等诸多大胆且前卫的议题,但当这些议题强行被安插在歌舞厅这一娱乐场所中就显得有些脱离大众生活了。一方面,海马歌舞厅兼具酒吧、卡拉OK、跳舞以及咖啡餐饮等多种功能,所有消费形式明码标价收费且价格不低,不是一般人可以消费得起的,到这里来的形形色色的人每天都在发生着始料未及的故事,给人一种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冷”范儿,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另一方面,《海马歌舞厅》一人写一集的分工式创作模式,虽然加快了电视剧的制作效率,却也加大了对总体风格把握的难度,不同作家水平风格有较大差异,其对“王朔风格”的理解与学习也各异,这就使得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故事存在水平风格参差不齐的问题,出现了诸如题材、内容立意的重复,不仅未学到王朔风格的精髓,还丢掉了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大众关于《海马歌舞厅》评价的分化与争议并不意味着它的“失败”,恰恰反映了那个时期精英文化趣味在平民化、商品化过程中与大众既有审美经验与趣味不适配的矛盾,割裂了大众审美经验的延续性和继承性,这也是其被诟病的原因所在。学者陈一辉就曾指出,“这些剧作多多少少忽视了当今电视观众审美的期待视野”[5]。《海马歌舞厅》用独具黑色幽默的影像风格再现了社会转型期存在的种种矛盾,具有极强的先锋性与现实意义,但由于该剧统稿环节把关的缺位导致全剧风格的参差,加之大众审美素养的逐渐提高使之出现了口碑的崩坏。尽管如此,该剧依然是我国情景喜剧发展史上的力作,深刻影响了我国情景喜剧的发展。
4 结语
“王朔”的横空出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王朔风格影视作品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影视文化的发展,其开拓的城市轻喜剧制作成本低廉,多以解构的姿态、机智幽默的对白、充满反讽性的语言支撑叙事发展,既针砭时弊、引人深思又不致造成现实危害,在观众获得自我宣泄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主人公的认同实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