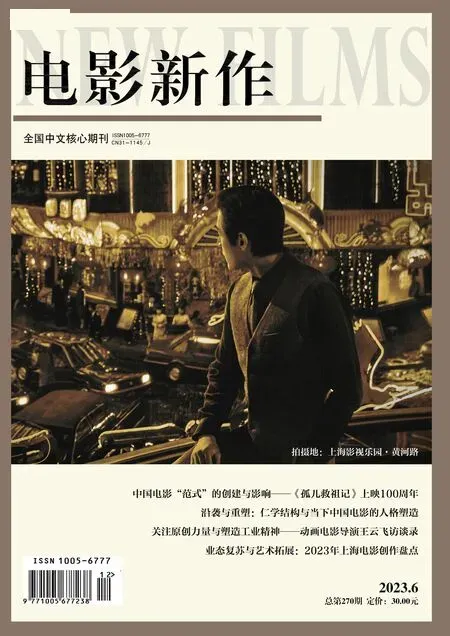跨国电影的叙事机制、转向及潜能
——以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五次“戛纳印记”为考察中心
王宜文 刘璀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跨国电影研究(transnational cinema studies)在国际上形成了一股热潮,其概念的生成基于公民对国家主体身份的认同。尽管蒂姆·贝格菲尔德(Tim Bergfelder)指出,从历史上来说,电影研究在接受文化杂交和使用诸如“全球离散族群”和“跨国主义”等概念方面“有些落后于其他学科”1,但对短暂的跨国电影研究发展史进行梳理,威尔·希格比(Will Higbee)与林松辉仍将目前几种主要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重点指出了不足。在他们看来,虽然“跨国电影”作为一个偏概念性的“符号”被日渐频繁地提及,实际上大多数研究仍将其视为一种常规范式,意指国际性和超越民族性的电影生产模式,这种倾向蕴含了一个潜在的威胁:电影的民族性很容易被忽略。此外,“跨国”这一术语偶尔也被单一地用来指代国际合拍影片或来自全球各地技术和艺术人员的协作形式,未清楚阐释这种合作形式可能产生的美学、政治和经济意义。2
本文所涉及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在叙事文本上提供了足以规避上述两种研究缺陷的可能。其中,前三次“戛纳印记”不仅将“跨国”停留在作为其标签式的个人符号,而且将民族内部离散族群的强烈对话诉求进行编码,形成了一套德勒兹意义上“小语言”的叙事机制,再借助“跨国”视角向这种“对话鸿沟”发出来自时代的叩问。同时,跨国制作的模态从未消解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叙事美学与艺术价值。面对全球化的多方位侵袭,跨国文化协商与国际电影节为其带来了新的关注与考量,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叙事转向出现在后两部入围作品中。
在上述同一个地缘政治范围内生产的五部影片中,表现“跨民族流动中的差异与诉求”成为叙事的强大动力,对时代话题的追问与成全更展现了电影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安德烈·戈德罗曾提出,通过策略性地组合画面、音响、话语、文字、音乐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构建一种所谓“影片话语化的程序”的“叙事体系”3,即影片中存在着由叙事主体能动地创造出的一套“叙事机制”,其组合元素受叙事主体的价值观念、客观世界的持续变迁等多重影响。本文在研究内容上,以勾勒阿基·考里斯马基的跨国电影叙事机制与转向为起点,进一步挖掘其电影叙事对跨国电影的当下实践具有填补性的艺术价值和发展潜能。同时,在研究路径上,试图能够超越目前跨国电影主要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割裂性与不完整性,在哲学视域下探索电影叙事与时代激变之间的互文。
一、作为电影“小语言”的叙事机制:离散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对话实践
(一)电影“小语言”的概念生成及其应用
当代跨国电影研究受到文学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理论范式等的深刻影响。4不仅于此,相当一部分电影理论研究均受惠于广袤的文学研究历史。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在文学研究的滋养中发展出一套语言观,其中包括对结构主义“机械”的语言模式表达反对,强调语言的少数化或者弱势化在其所服务艺术形式中的地位5,并将这些理论运用在了戏剧研究中。随着其语言观的日渐成熟以及电影学在当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代浪潮,自然而然,德勒兹将目光转向了电影和语言的关系,并将其视为“最紧迫的问题”。6
具体来说,“小语言”的概念来自德勒兹对卡夫卡叙事风格的研究。首先他提出卡夫卡的叙事语言“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和非形式的表达,一种质料的内张的表达”。这一语言策略被德勒兹称为“语言的非意指的内张运用”,并进一步从这种“内张”的含义中提炼出了“小语言”(langue mineure) 的概念。要而言之,“小语言”的生成意味着对语言中的变动和异质的要素进行实验,不断释放其颠覆语法和悬置意义的力量,使语言变得质地粗粝以实现自我鸣响。7可以说,电影的“小语言”则包含极为相似的功用,即以作为“少数”的叙事来诠释“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影像的力量发出其作为独特艺术形态的时代轰鸣。
论及电影中对“少数”的叙事,其体量可谓在新世纪初达到了顶峰。这是由于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移民浪潮,一些人口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移民的世纪”。随着个体不断地发生跨境空间位移,在一定范围内聚集的移民及其后代形成了新的离散族群,他们不断冲击并重构着目的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实践。而考里斯马基的跨国电影正是发轫于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采用“小语言”的非“机械”叙事模式,作为当时主流电影之外的“少数”,时刻照拂着同样被归为“少数”的离散族群。
史书美曾借用“小语言”的概念来阐释华语跨国电影是如何“将差异、矛盾和偶然引入‘固化的华人’身份之中”8。在她兼具开创性与奠基性的研究中,“小语言”所具有的“非语法性”为特定区域跨国电影的离散叙事提供了依据。由此,若要为考里斯马基的“跨国电影语言”找到可供参考的理论模型,德勒兹的“小语言”理论不失为一条可靠的路径,因为其“非语法性”恰是为了打破单一的统治地位,使其在各种力的占有中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也是为“少数”而发声的离散叙事之要义所在。
(二)作为电影“小语言”的离散叙事
纵观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五次“戛纳印记”,前三次即涵盖了其著名的“芬兰三部曲”:《浮云世事》《没有过去的男人》(The Man Without a Past, 2002)、《薄暮之光》(Lights in the Dusk,2006)。虽然其作品中对“离散族群”的关照从来就是叙事主题以及被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但关于离散族群的几种明确分类出现在了这三部电影中,分别为失业者、失忆者和失意者,集中塑造起对既定族群的“边缘”叙事范式,反过来也引导了其作为“芬兰三部曲”的主题性指归。
同时,“小语言”意味着语言脱离意义的束缚,进行永无止息的越界运动,是作家在“母语”中创造的“异乡语”。9“芬兰三部曲”即通过离散叙事制造了一种属于“异乡语”的文化,三位代表性的失业者、失忆者和失意者虽然身处家乡,却经常体会着作为“异乡人”的孤独与疏离,失落在公民话语权的边缘,因此他们急需建立一种有效形式来建立起与家乡和时代的共语。
在《浮云世事》中,面对经济大萧条,一对生活本就拮据的夫妻先后失业。他们保有自尊,不愿领取救济金,而是为了生存四处找工作,不断碰壁的过程中彼此扶持,最终在前任老板的帮助下开了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餐厅。“工作”本就是组成芬兰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特征:芬兰民族曾通过不知疲倦的劳作将本属于沼泽的土地和北部森林变成一个理想中的国家。正如芬兰学者塔里娅·莱恩(Tarja L a i n e)所论证的那样,由于国家历史更迭,“民族自我理想”的位置被一个诚实、勤奋的主体特征所定义,而当渴望工作的失业主体在追寻自我理想的同时承认自己属于失业者时,就会产生矛盾心理并滋生一种羞耻感。10矛盾的渴望和羞耻在短暂的时间内将这对失业的夫妻编为了主流从业者之外的离散族群,他们同时在客观事实与心理认同上成为社会的“边缘”。
虽然阿基·考里斯马基给《浮云世事》营造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但新餐厅的未来却仍然不可知。9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影片中这对夫妻实际上也成了一个缩影,无数失去工作的人在深层意义上便淡出了其作为公民的话语圈。影像则为这部分失落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与国家、社会层面沟通的途径,通过具体而微地展示普通人的失业生活,将“羞耻”拉上银幕并将其合理化,从而代替他们寻回本属于自己的公民主体性。
如此一来,在对话的视角下,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也在不断构建我们通常认为属于20世纪离散历史时刻的对象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芬兰社会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一面被再次放大:除了大规模的失业,企业破产、住房紧缺,官僚阶层的腐败和越发富有的银行使得失忆的男主人公M相比《浮云世事》的主角面临更大的危机。他在陌生的城市一下火车便遭遇了抢劫,被殴至昏迷。醒来之后身无分文,也丧失了记忆,只得住进废弃集装箱,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在他周围的几乎都是当地工人、流浪汉等社会底层人员,这些人为了生计从乡村搬到城镇,却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如同M丢失了自己的过往,被迫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土。
M与周围人共同组成的底层阶级所居住的集装箱表面上看是肮脏、阴郁且冷漠的空间,但阿基·考里斯马基所提供的视角是饱含诗意与温情的:众多的集装箱构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居民的生活没有被现实条件所限制,人们下班后聚在一起演奏音乐、烹饪,家中餐桌上永远摆着鲜花。尤其是救济M的一家人,其自制的淋浴区展现了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天赋;手动洗衣区成为这个社区中一个重要的“共享空间”,这些离散在城市化边缘的人物用丰富的设备和装置武装着自己的智慧与尊严。
在这里,M的失忆没有将其打入底谷,相反给他提供了一个重启人生的机会。他成为“新生者”与“外来者”参与了集装箱里的社区生活,从内、外两个视角客观地观察了真实状况。显然,无论是社区大家庭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是他在这里遇到了真正的爱人,考里斯马基透过失忆者的眼睛,将城市化背景下社会离散族群生活的积极一面当作了叙事链条最重要的一环。无关于对国家主题的宏大叙事,“芬兰三部曲”在此已经奠定了一套独特的叙事体系:从边缘人物的日常生活出发,关注普通人由乡村向城市进行空间转向后所形成的“异乡”文化,并试图展现这种文化中积极的一面,使电影语言呈现出希望与温暖的升调,以在社会价值的含义上“实现自我鸣响”。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论述“小语言”的功用时提到:“……它假定从日常统治的语言内精制出一种自治的艺术语言,一种微妙地、难以察觉地与主人的共同语言相区别的语言空间:它带有一种隐蔽的、看不见的胜利姿态。”11阿基·考里斯马基曾在访谈中说:“对伟大人物描写和宏伟浮夸的民族国家主题的展现占满了70年代的银幕。”12而随着芬兰电影基金会(Finnish Film Foundation)对电影发行的控制,这种现象一直延续。《没有过去的男人》已跳脱出了90年代之际芬兰电影“日常统治的语言”,以一种来自新世纪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及民族主义的“小语言”作出了反叛。“看不见的胜利姿态”即表现在其再一次代表更广阔的离散族群完成了逆向主流的对话实践。

图2.电影《薄暮之光》中两处鲜花镜头
在“芬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薄暮之光》中,阿基·考里斯马基却将亲手营造的希冀图景打破:保安考斯蒂南在被心爱的女人欺骗之后,却甘心沦为她的棋子,最后不甘压制对女人的情人大施杀计,生死未卜,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意者。影片不仅在情节上展现了阿基·考里斯马基对于希望的“破坏”,更是在细节处展现了对前两部影片主题的转变。上文提到,《没有过去的男人》中的鲜花是社区居民热爱生活的象征,但本片中对鲜花的意象作出了不同的意指性实践:一是在考斯蒂南家中,为了迎接女人的到来,他特意买了一束鲜花,但花的背后是一睹阴暗的墙,灯光微弱地处在角落,照亮他的背影,此时已显希望渺茫。二是在咖啡店里,鲜花被置于前景,后景仍是一堵更逼仄的墙,加强了空间的局促感,让落魄的主人公更显失意,只剩绝望。
虽然相比前两部影片,《薄暮之光》在主题上对营造“希望”的动力急转直下,主人公所面临的困难也逐步升级,遭受了来自社会多方位的打击,但阿基·考里斯马基并未丧失与国家层面进行“对话”的欲求,只是通过极致的困境,将“小语言”置于更冷静与幽默的现实条件下,展现了个人的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确乎存在一种永恒的冲突。13
二、面向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叙事转向:跨国文化协商与国际电影节的“重塑”价值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后两次“戛纳印记”分别发生于21世纪10年代与20年代。此时全球化的风潮已经深度席卷了整个欧洲,资本循环与增值在各个国家间相互渗透,第一次城市化的进程已步入尾声,甚至在许多欧洲小国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芬兰三部曲”所进行的“小语言”对话实践之上,《勒阿弗尔》(Le Havre,2011)与《枯叶》则凭借“跨国”的优势,将新世纪多形态的跨族群流动模式下所产生的人口、战争、商业等谜题与电影文本进行融合,转向在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叙事。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无意从外部的叙事形式上,对跨国文化协商与国际电影节作为“参与叙事转向的文化与商业工具”作出指涉,而是依旧强调叙事的物质性:考量二者如何作为全球化的产物浸润了电影内部的文本,并对叙事的具体内容与形式产生了“重塑”价值。
(一)跨国文化协商:“他者”叙事的角度与温度
具体来说,“跨国”这一术语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为“全球化”概念的广义性及对其模糊的应用提供了精确的选择。“全球化”被习惯例地应用于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所有过程或关系(政治、社会、文化或经济)中,而“跨国”则更适用于形容这种交互的规模、分布、多样性和它们在地方层面的影响,以及它们可能在民族国家内外产生的影响。14在讨论后现代化进程的议题时,上述两部“跨国”艺术作品即是面向全球化,又不止于讨论全球化,不再满足于将自身作为一种“小语言”参与本土对话的实践形式,而是形成一种跨国/族叙事面向更大的观众群体,使这种影像的轰鸣扩散至远方,继而激起更多的共鸣,用以反哺电影艺术参与后现代化的进程。
若要实现这种愿想,即便是基于“大欧洲”共通的历史,跨国文化协商的重要性是不可被忽略的,尤其是针对政治议题,在本国制作时常显得顾虑重重,但若将其置于超越国家之外,却又与本国息息相关的地域进行讨论,在处理敏感情节时会更加游刃有余。《勒阿弗尔》对于“非法移民”的人物定位和叙事规则即展现了这种跨国文化协商的精明与及时。
故事发生地勒阿弗尔是法国著名海港城市,一个偷渡肆虐的地方。片中的非裔男孩具有双重的“边缘”身份:他既属于儿童这一物理属性的弱势群体,又是社会属性下的一个非法移民。这使得他的境遇同样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欧洲与第三世界,特别是与非洲的关系15:当局时常保有一种尴尬的回避与同情。这一点在法国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调整上显得尤其明显:在2019年欧洲移民危机处于巅峰时,总统马克龙在采访中态度强硬。16但马克龙在2023年初审核的新移民法案时,他转而提出了“严苛”兼具“人性化”的主张。17
《勒阿弗尔》虽仍在法国取景,但其中演员从各个参与制片或发行的国家(芬兰、法国、德国)调度,人物设置为来自各个国家族群的混杂体,事件也不在地域上做任何指涉,以此脱离特定的国家或社会背景,避免了作为当局者极易产生的“尴尬的回避与同情”,尽量客观地对欧洲广泛存在的“非法移民”现象进行真实展现与思考。在这里,阿基·考里斯马基通过在不同国家地域间进行内部文化协商的形式实现了所谓的跨国人文主义——宣扬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边界的团结。18
在《枯叶》里冗长的恋爱约会叙事中,广播里不断地传来关于当今世界战争的报道,却不对主要情节产生任何影响,二人的美好爱情仿佛飘然于世界的动乱之外。阿基·考里斯马基在戛纳电影节的采访中直言:“我认为这个血腥的世界现在需要一些爱情故事。”19在某种意义上,他将爱情视为缓解世界冲突的解药:两个普通人在赫尔辛基街头偶然相遇,尽管自己的善意被视为与权威对抗、所处的平民阶层充满误解与迷茫、世界正面临着分崩离析……诸如此类后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安因素却并不影响他们珍视偶然的机缘,拥抱爱情。这使得《枯叶》不仅彰显了具有普世性的精神、情感价值,更是在一个远离战场却饱受影响的“他国”立场向世界呼唤一份这个时代急需的爱与理解。这样的言说与其说是阿基·考里斯马基再一次的跨国人文主义关怀,不如说是全球化影响下的世界陷入愈发相互依存状态的写实。
通过对新世纪弥散的移民、战争等重要议题进行探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后两次“戛纳印记”做到了在叙事上既不对某一特定区域政治事件表达看法,又履行了“全球公民”的义务,在“世界共同体”的创作意识与表现人文关怀的立场上进行跨文化协商,使得“他者”不再代表对立,而成为一种客观视角的代言。在“小语言”的基础之上,这种转向将全球化议题深度融入电影文本。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反过来在受众与市场层面对其电影叙事转向的即时形态造成了影响。
(二)国际电影节:搭建“重复”叙事的舞台
早在“芬兰三部曲”中,《没有过去的男人》作为在芬兰本土最成功的艺术电影之一,总票房达到了4000万欧元,其中只有9%来自于本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大约分别占35%、18%、15%。尽管法国占据了最多的票房比例,但本片观众人数却只占到了法国人口总数的1%。20由此看来,欧洲国家尤其是大城市的电影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潜力,而抛开商业价值,更是电影作者向观众传递信息与观念、拓宽艺术话语权的绝佳场域。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间资本循环模态日益成熟,欧洲大城市影迷的力量也随之扩大,无论是观影人数的增加,还是对艺术电影审美程度的提高,这批观众的成长与全球化现象之间的交互同样作用于后现代时期的电影创作。
基于以上的论述,国际电影节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对电影作者叙事观念的影响便潜藏在受众价值中:由于媒体的报道对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的影响力起到了“增值”效果,影响了观众的观看议程,因此电影作者反过来不得不重视电影节的平台效应,并在创作中时刻平衡其艺术观念与观众期望之间的关系,尽量彰显独特的时代价值,以便扩大作品话语权。这样的考量对作为“小语言”的叙事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国际电影节提供了将其进行扩散的有效平台。
自9 0 年代以来,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八部电影中有四部在各个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其中《勒阿弗尔》在第5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完成首映。在所有展映中,电影的宣传材料都保持一致:新闻物料以怀旧的字体印刷,海报以视觉艺术家同时也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妻子:宝拉·奥伊诺能(Paula Oinonen)绘制的漫画形象为代表。正如芬兰评论家所言:阿基·考里斯马基在跨国媒体中的知名度建立在他的电影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上取得的艺术评论和商业成功之上。21电影节为其提高了国际知名度,便于与本国之外的观众,尤其是关注国际电影节的观众群体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但阿基·考里斯马基对电影节的探索绝不仅体现在个人知名度的提高上,更在于利用电影节打造了其独具识别性的“品牌”。导演“品牌”即意味着一批观众对其作品保有极高的忠诚度22,这也是艺术电影的品牌价值所在:通过培养一批观众,用相似的叙事内容和方式去影响一批人。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品牌”意识集中体现在了叙事的亲和力和“重复”的主题中。
《勒阿弗尔》是在法国取景、法国首映的电影,展现了一个“人口大杂烩”式的社会,就像真实的法国一样,这里存在着诸多难以言说的人际矛盾和地域冲突。尤其是上映在法国打响利比亚战争的这一年,影片所展现的全球化危机在现实中发展出了更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勒阿弗尔》通过一个警民合作,成功转移非法移民儿童的故事,呼唤“大爱无疆”之精神,使得处于战争国家中的戛纳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同样,《枯叶》片名即取自法国古老香颂《枯叶》(Les Feuilles Mortes),是 1946年法国电影《夜之门》(Portes de la nuit,Les)中的经典绝唱,歌曲内容与影片主题高度相符:歌颂苦难生活中的爱情生机。阿基·考里斯马基将可见可感的视听与影片背后所蕴含的法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一时间为戛纳观众带来了产生于同一地域的先锋艺术与古老文化的双重体验。
在这两部影片中,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重复”的过程:通过无数“法国元素”的叠加与跨国叙事的时代主题完美融合,不仅为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属于本国的观众营造了天然的地域亲和力,也对国际的观众展示了一种固定的叙事取向,即影片主题对时代话题的追问与成全。同时,这样的叙事方式也是将后现代议题融入电影艺术的重要价值之一:质疑权威与中心,但并不回避对当前社会现状的反思以及对社会边缘人群的关怀。
这种“重复”的作用在第7 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得到了印证:在电影节的场刊《银幕》(The Screen)中,国际评审团给予了《枯叶》在主竞赛单元中的最高分3.2。23针对更广泛的观众群体,“重复”有利于引导观众在潜意识中刻画一个固化的品牌形象,并对其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改造。跨国电影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此得以展现:用“冷眼看世界”的方法与态度去讲述,留下余蕴与期盼给观众仔细品味。
三、冲破“二元对立”的叙事潜能:“后民族”批判视角
如本文前言所述,当下跨国电影的叙事及其研究仍有较为明显的缺陷,许多批判性的、带有修正主义的思考也已在学界发声,这同时意味着此领域具有更大的发展潜能。由于民族电影与跨国电影在发展历史上属于交替关系:安德鲁·西格森(Andrew Higson)24、蒂姆·贝格菲尔德(Tim Bergfelder)25等曾专注于民族研究的学者,都提出了“民族”的限制性以支持跨国电影概念的生成,在不可抵抗的全球化之下,对民族电影的探讨便自然地陨落,理论家转身向跨国电影投射了热切目光。在这种情况下,跨国电影中的“民族叙事”往往被抹灭甚至被抵抗,对于其研究中的民族性问题似乎也无人问津,“民族”与“跨国”在此产生了一种二元对立关系。
然而,处在跨国流动中的“身份”或“民族身份”从来就不该是电影艺术所刻意回避的话题。正如电影理论家张英进提倡的,跨国文化“追求多元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倾向于空间中的文化流动,带有融合性、综合性、复合性,甚至可能成为第三种文化”。26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通过关注身份和社会集体性的空间转变,来展示了这种文化的流动性和断裂性,其中议题囊括了:城市化对公民身份及其边界的抹杀、对个人主体性的怀疑,以及全球化在这一切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产生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眩晕感、持续而不确定的转变感。27这种对身份差异的强调要求我们从“后民族”的角度来看待阿基·考里斯马基的跨国电影。基于此角度,阿基·考里斯马基为跨国电影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具有理论缝合性的研究潜能。
“后民族 ”理论集中讨论了民族国家的结构和主权如何受到经济和政治新自由主义、“全球 ”文化的复杂联系、政府间一体化以及人口跨境迁移的挑战等,是政治社会学家对当下世界尤其是欧洲社会变迁的一种价值性考量。1995年,芬兰加入欧盟组织,与整个欧洲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网络中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加上彼时多渠道、多类型的跨国媒体的涌现,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跨境移居风暴,这些新的浪潮对人们所接受的民族文化与身份、民族电影与类型叙事等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对相当一部分“后民族”理论研究者来说,公民身份只是欧盟集体的一部分,或者说社会集体性更多地与民族或宗教归属有关,而非与任何国家称谓相捆绑。28“后民族”的电影则大多关注欧洲跨国移民的叙事,他们的社区身份与其说是由他们在法律上属于哪个国家界定的,不如说是由普遍的人权概念界定的。他们以个人而存在,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结构之中的财产。

图3.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剧照
为此,西格森认为,电影中的“后民族性”绝不能与民族电影中的文化概念及关于身份主体的叙事混为一谈。29他以英国电影为例,分析《我的美丽新娘》(斯蒂芬·弗雷斯,1985)和《火车怪客》(丹尼·博伊尔,1995)等影片如何挑战了英国电影中占主导地位的“英格兰性”:丹尼·博伊尔电影的“苏格兰性 ”和斯蒂芬·弗雷斯的多元文化辩证法似乎暗示了传统意义上,英国民族电影中的文化多元性。然而,将这些电影定义在单一的、伞状的民族电影概念中,实际上会抹灭替代主流英国性的可能,是一种固步自封的行为。而“后民族”的语境则一语击破了“民族”概念中自始至终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提出电影叙事中的“个体身份”话语同样需要打破民族国家的限制。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大部分影片中都有“后民族”元素,但其表现形式却与其他艺术电影叙事大相径庭,展现了跨国的融合视角与复杂的民族身份。在《没有过去的人》和《薄暮之光》中,芬兰被展现为一个不断变化却保有连续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既有先前的传统及其文化遗存(如老旧的木制房屋和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景),也有文化、资本和人口跨国流动的迹象。许多遗产电影(heritage film)使用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对立概念,而阿基·考里斯马基则坚持跨国主义的融合性,同样将这种对立进行解构。在《没有过去的人》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后民族化”的互惠性:影片捕捉到了当前人口迁移对社会身份的影响,即迁徙的动态交流模糊了城乡身份的二元对立,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城市的经济和文化影响逐渐淹没在农业社区的外表之下。

图4.电影《薄暮之光》剧照
无论是展现社会空间的流变模态,还是将民族身份进行融合的叙事方法,正如前文所述,阿基·考里斯马基在此也有意识地将作者和观众纳入了叙事结构中,使处在全球化的身份变动之下的每一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后民族”的精要所在。通过表现作者意识和容纳观众,这种新兴的途径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性和民族身份的复杂性抽离了单纯的电影叙事,使真正的个体参与到当下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交流的全球辩论之中。这些跨国电影叙事的复杂融合很容易给观众一种印象,即全球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甚至相互矛盾的过程,同时鼓励观众思考自己是否在全球视角中保全了心中的自我身份。在这样一个媒介跨国化的世界里,“后民族”的概念也许会使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更为复杂,但它却是打破对“民族”叙事之偏见的核心理论依据。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来自其它地域与本土的角色从来都不像在民族电影的保护主义论述中那样泾渭分明30,因其持续关注后民族状态特征中的流动与融合,在文化、艺术、哲学层面上为地方与全球的复杂性交织效应都提供了更具理论缝合性的批判性视角。
德勒兹曾提出语言的少数化或者弱势地位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基于跨国电影研究对文学研究路径的重要借鉴,对于跨国电影中作为“少数”的影像语言(即“小语言”)进行分析,是讨论“个人导演叙事风格是否在其创作架构内部形成一场变革”这个问题时不可忽视的议程。正如全球化的要义在于流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五次“戛纳印记”从帮助离散族群实现逆向主流的对话实践,到嫁接诸如全球化、城市化等后现代主义元素进入文本,其叙事范式也随着敏锐洞察并反映时代的更高追求实现了一种转向。这不仅展现了跨国电影的优势与底蕴,更是充分利用电影语言经验参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一场精彩实践。在这场与文明对话的实践背后,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影像哲学也通过“后民族”的批判视角,对“跨国电影”这一较为新兴的类型作出了带有反思性与完善性的探索,并为当下的跨国电影研究开辟了更具潜能的理论空间。
【注释】
1 Bergfelder,Tim.National,Transnational or Supranational Cinema?:Rethinking European Film Studies[J].Media,Culture&Socie ty,2005,27(3):321.
2 Will Higbee,Song Hwee Lim.Concepts of Transnational Cinema:Towards a Critical Transnationalism in Film Studies[J].Transnational Cinemas,2010,01(1):7-21.
3[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著.什么是电影叙事学 [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78.
4 Appadurai,Arjun.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J].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90,07(2):295—310.
5 Carmelo Bene,Gilles Deleuze.Superpositions[M].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90:85-131.
6 金虎.试论德勒兹的电影语言观[J].电影文学,2019(05):114.
7 石绘.德勒兹的“小文学”概念探析——以语言论为中心的考察[J].浙江学刊,2021,249(4):207.
8 Shumei Shih.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35.
9 同7,203.
10 Andrew Nestingen.The Cinema of Aki Kaurismaki[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123-159.
1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王逢振,王丽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69.
12[塞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等著.历史悲剧的维度:欧洲电影大师访谈与研究[M].李洋主编.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389.
13江逐浪.《薄暮之光》:欲望与绝望[J].当代电影,2010(6):138.
14同1,321.
15 亨利·贝肯.芬兰电影跨国史——对一个电影小国研究的反思[J].郑睿,赵益译.当代电影,2017(3):61.
16https://www.radiofrance.fr/franceinter/podcasts/la-chroniquede-bruno-donnet/entretien-demmanuel-macron-a-valeursactuelles-extremement-adroitou-extremement-risque-3004895.
17https://www.163.com/dy/article/HNSNE9DT0514BIJT.html.
18同15,65.
19https://deadline.com/2023/05/fallen-leaves-aki-kaurismakipress-conference-cannes-filmfestival-1235376732/.
20同10,156.
21 Näveri,Tuomas.Canneshitistä tuli Kaurismäen uran suurin kassamagneetti[J].Ilta-Sanomat,2002,07(2):12.
22杨晓茹,范玉明.电影导演品牌打造研究[J].电影文学,2017(19):71.
23https://www.screendaily.com/news/aki-kaurismäkis-fallenleaves-tops-screens-final-2023-cannes-jury-grid/5182676.article.
24Higson Andrew ,“The limiting imagination of national cinema”,inMette Hjort and Scott MacKenzie(eds),Cinema and Nation[M].London:Routledge,2000:63—74.
25Bergfelder Tim,National,tran s n a tional or supranational cinema?:Rethinking European film studies[J].Media,Culture &Society,2005:315—331.
26Zhang,Yingjin.Screening China:Critical Interventions,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M].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140.
27 Kaapa,Pietari.The Cinema of Mika Kaurismaki:Transvergent Cinescapes,Emergent Identities[M].Bristol:Intellect,2011:95.
28Ferry Jean-Marc,Pertinence du Postnational[J].Esprit,1991:80-94.
29Higson Andrew.‘The Limiting Concept of the National’,in Mette Hjort and Scott MacKenzie(eds),Cin ema & N ation[M].London:Routledge,2002:63-74.
30同2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