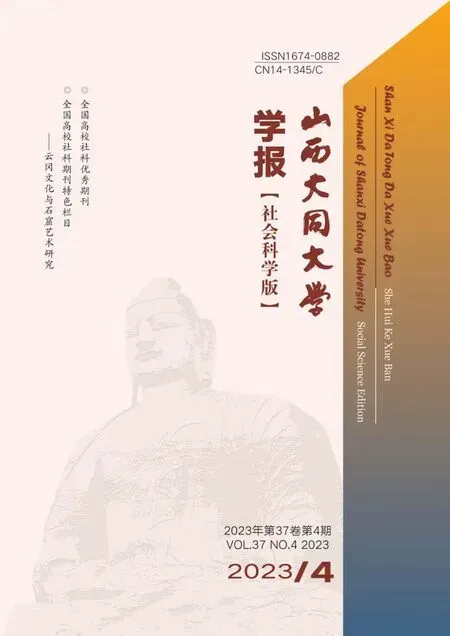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欧德英,侯桂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中长期处于从属位置,并且被不同的因素所压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性主体经历了被集体关注,又被淹没、剥夺话语的过程,女性主体内部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隐微。在“五四”新文化浪潮之后,这种集体的因素,又在寻根文学的书写中复归。伴随着追求内省、寻找定位的历史需要,寻根文学以文化、民族为重要书写对象,以其强大的遮蔽力,掩盖了女性书写的位置,使得女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在寻根文学中无从谈起。通过对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进行分析,可以厘清女性主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书写脉络,更加鲜明地展现女性主体在寻根文学展示民族主体中的不同功能,反思女性书写的未来空间。
一、女性主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沉浮
“主体”原是指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随着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主体”一词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女性主体的自我确证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的主体确认问题不断深化,这不仅是性别关系的博弈,更“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1](P4)
中国历史中的女性被压抑、藏匿、掩盖和抹杀在强大的父系统治秩序之下,在古代社会,女性通过男性“他者”目光来完成自我完形,女性主体按照男性指给自己的理想形象来看自己,完全失去了说话权。伴随着近现代革命潮起、现代文明教育进入,女性力量跳出传统父系秩序内部,成为一支新兴反叛力量,妇女解放也被作为人的解放的中心议题提及,至此,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概念谱系中放有了‘女性’这样一个概念和它标志的女性性别群体。”[1](P27)新文化初期的女性书写作为反叛封建秩序的重要武器,被新文化主体们反复重写,但刚刚获得发声权利的女性声音再次淹没于寻求自我觉醒的集体声音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进入革命文学时代,女性的政治、阶级意识开始对过往的女性书写进行审视与反思,使革命文学时期的女性书写处于混杂的状态,阶级意识与女性意识交织,被掩盖在以民族解放为旗帜的革命文学中。直到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明显淡化,女性书写在文本中失落或潜隐。诚如戴锦华所言:“如今端坐的不是任何一个私有社会的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民族集体的化身。”[1](P31)文学中的父系叙事换了面貌,以民族共同体为载体,以阶级话语为言语方式,设定了一个男女和谐共存、不分性别的文化理想,将女性表达与民族表达同化,使女性自我弱化甚至“消失”。
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新时期文学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性批判精神,大部分作家试图重新反思和建构关于“人”的想象,“试图在抽象层面上建构一种普泛的‘人类’共同的本质”,[2](P14)致使女性主体的发声淹没在对普泛人性的追求之中。新时期的女性书写无法走出文化、政治、民族的裹挟,不能突出对女性角色的深层分析,使女性书写处于尴尬的徘徊之地,对女性问题的审视和书写没有放入女性场域中进行实际的讨论,而是同伦理、阶级、民族、文化等因素融合在一起,压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之下,只能在文化中失去话语权,无言注视自己。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寻根文学:遮蔽女性声音的历史语境与性别立场
新时期文化环境多元开放,“伤痕”“反思”“改革”的文学思潮浪潮迭起,寻根作家历经了饱经创伤的文学时代,在文学解禁的新时期,试图通过文学审美和创作思维的改变,纠偏以往的政治化倾向。同时,他们又尝试与西方话语中心对抗,寻找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之路。因此,寻根文学以“文化寻根”为口号,成为“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3](P220)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创作中,女性书写与国家、种族、阶级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被同质化处理,彻底淹没了声音。寻根文学创作以其鲜明的父系叙事特征遮蔽了文本中的女性声音,与第三世界妇女的境况类似,此时寻根文学文本中的女性书写处于“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被置于寻根文学追求的世界意识之下,处于盲点之中。
(一)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内转的需求:寻根文学作家创作的内在动机 新时期的文学处于全球化语境下,这对处于时代转换时期的作家提出了内外双重的挑战。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语境的开放与包容使民族文学走上世界舞台,其中拉美文学的成功更是直接刺激了中国作家进行民族文化的新时期再书写。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伤痕”“反思”“改革”浪潮已经失去生命力,在“文革”中成长的“知青”作家一直无法很好地融入新时期文学大潮中,他们存在着确证自我的迫切需要,只能开启新的探索。“当作家为文化孤儿的状况而苦恼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慈祥面容及时地浮现了。”[4](P161)寻根作家大部分是知青作家,他们利用知青时期对地方、民间文化的探索和积淀进行创作,在一个短暂时期标新立异,以此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与认同,并将自我的焦虑转为文化的焦虑,形成声势浩大的寻根文学,由此,寻根文学作家踏上文化寻根之路,寻“根”、寻“父”、寻“我”,而寻找女性的声音则被淹没在浩浩荡荡的寻找自我与文化的声音之中。
(二)鲜明的父系叙事特征:寻根、寻父、寻我 寻根作家在形成风格之前,已经形成了寻找意识,这种寻找意识也可以理解为危机意识。在世界文化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寻根作家将内在与外在的焦虑转移到了对“原初中国”的迷恋,这也是学者周蕾提出的“原初的激情”的概念,体现了文化危机的症候。现代中国在全球化的现代时间中不占据优势,明显落后于西方,但追溯文明的古代时间,原初的中国文化却比西方更加古老,存在着极大的挖掘空间,寻根作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转向并挖掘古老、传统的民族文化,从而寻找自我的声音。在寻找的过程中,寻根文学的创作体现了风格鲜明的叙事特征,寻根作家将寻根、寻父、寻我三者的精神向度联系到一起,女性书写则作为父系叙事特征下的某一维度进入寻根文学作品中,被作家的寻找意识所裹挟,成为缺乏女性视域的介入后机械而被高度同化的文化性书写。
首先是将寻根与寻父联系到一起。寻根作品中鲜明地涉及了寻父主题。之所以寻“根”寻“父”,就是因为寻根文学作家处于一种无父、无根的焦虑之中,“无父”使他们深处“一片荒野”“一片意识形态的空白。”[5](P51)从寻根文学的口号来看,“根”“种”“源”这些与原初文化相联系的语汇本身就带有父系叙事色彩。以寻根作家代表莫言为例,他的作品展现了对“父”的追寻。在《红高粱》里,叙述者“我”总是为“种的退化”感到伤怀,由此,他展现了对男性原始生命力和阳刚之气的追求。在意象描写上,可以看到黑土、骡子、人脚獾、红高粱、矢车菊这些体现奇秘色彩的北中国自然风光,关联着莫言对高密东北乡野性原始生命力的描写,体现了莫言早期小说中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莫言如此评价他的文学原乡:“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6](P2)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莫言塑造了混合着匪气与侠气的东北草莽英雄余占鳌。他身上有男性的阳刚之气,在东北乡荒凉与腐烂空气中孕育的余占鳌象征着作者对勇猛刚强的男性力量的赞赏,具有典型的文化意义。孟悦如此评价莫言的写作:“这旅程不是始于写自己,而是始于寻找父亲,重建父亲,或曰,寻找和重建一种缺失了的父子关系——一种主体生成的环境。”[5](P51)莫言选择了充满野性生命力的男性意象,表达寻找父亲的力量和稳定的家族关系的诉求,并通过“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稳定的家族关系来确证男性主体的位置。
其次是寻根作品中鲜明地体现了对父系文化传承的追求。无论是对民族文化的开掘与传承,还是对民族文化的失落与批判,男性都成为寻根文学重续父系谱系、追寻族群文化的主要书写对象。《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是莫言对北中国原始生命力的想象与追寻,承载着他对父系力量与民族文化的向往,凝聚着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小鲍庄》中的捞渣是王安忆对中华民族追求仁义精神品格的形象塑造,凝聚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想象,以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形象传达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棋王》中的王一生亦是传统儒道精神的融合与化身,与捞渣一样,王一生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与典型,代表着作者对现代社会逐渐消失的仁义品格的召唤,也暗藏着将男性作为族群文化传递者的信息。男性不仅是文化框架内民族优根性传扬的典型,也作为高度凝缩的文化形象,被寻根作家批判。《爸爸爸》中的丙崽可以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丙崽处于“无父”状态下,神秘化的生存环境和符号式语言都使得丙崽成为一个“荒野”中寓言化的人物,凝聚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批判。
无论是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还是追寻父系文化的记忆与传承,都与寻根作家寻求自我确证的内在追求紧密相连。新时期文学解禁以来,从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追逐的热潮,再到向内的文化寻根思潮的形成,体现的是部分中国作家对自我意识的逐渐强化,他们从文学新时期的冲动中走出,走向文化的怀抱,寻找向内的深入的自我。这一自我与家族、文化、乡土等传统紧密结合,引领他们走向寻“父”、寻“根”之路,从而获得自我确证、文化自信的原始动力。因此寻根作品展现了浓厚的父系叙事特征,寻根作家力图塑造的文化中国也体现着对男性主体的抽象凝缩。寻根作家们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却没有复原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寻根作家的代表人物王安忆就在她的《纪实与虚构》中对寻根创作的父系叙事特点进行了反思与批评,残雪也在《阳刚之气与文学批评的好时光》中直接提出了寻根文学追寻父系叙事,片面强调创作的阳刚之气的现象。经由后期的反思,可以看见文化寻根思潮、寻根作品对性别问题的忽视甚至是遮掩,希望通过文化、民族等多重因素掩盖性别的特性,回归到父系叙事传统之中,其中女性书写处于自我身份确证与追寻文化记忆的双重焦虑之中,无法发声。
三、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被遮蔽的女性声音
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进行重构,建立有关男性文化相继不绝的民族共同体想象,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图景与构想,个体声音在群体声音中泯灭,女性在个体中边缘化,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
(一)作为结构因素的女性:对男性主体的崇高书写 在寻根作品中,女性常作为促使男性成长,或使其形象在结构上获得改变的因素被书写。在重续父系叙事传统的过程中,女性的位置举重若轻,一方面“她”无法成为民族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但另一方面,男性主体的成长、父系文化的传承却无法失去女性的结构意义。在“子一代”彻底成长与继承父辈文化之前,女性角色至关重要。比如《红高粱》中的“我”与奶奶、《爸爸爸》中丙崽与丙崽娘、《棋王》中的王一生与母亲……王一生走向“棋王”之路不仅出于自身对象棋的热爱,更有对完成母亲临终嘱托的期待,寄托在无字棋中的母性光辉作为主人公一生棋路的感情基底,成为他“孝”的体现,在塑造他传承儒家文化的形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爸爸爸》中,丙崽的父亲是谁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指引着丙崽不断重复着两句宿命式的话语,成为文化象征的隐喻,在丙崽娘说出了父亲的身份后,她便离奇死去,没有人得知她的死因,这仿佛又为寻父的隐喻添加了抽象的神秘感,丙崽娘只是一个女性功能位置的象征,正是她的离去,使丙崽得以进入父系叙事的象征体系,完成男性结构意义上的成长。
《红高粱》中,豆官在遇见父亲之前,与奶奶处于“母子一体”的状态,尚不能认识到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当奶奶牺牲后,豆官自我理想中的他者破灭,父亲的到来补足了缺失的“他者”位置,使豆官正式走向社会文化秩序之中,成为与父亲相当的“男性”,孟悦对此的解读是“奶奶死得既英勇悲壮又恰到好处,恰是时候,她以自己这个性别在故事中的必然命运,成全了一个理想的父子关系式。”[7](P120)父子关系在母亲的献祭后得到延续和升华。最后,奶奶的死如同一首辉煌的民族壮歌,凝结为了中华民族能战胜强大侵略者的原型。
除了促使“子”一辈的结构性成长之外,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还作为父系秩序建立的重要补足性因素。《小鲍庄》被认为是仁义的村庄,主角捞渣作为这套仁义体系的中心人物,是仁义精神的化身。尽管《小鲍庄》是女性作家所写,但其所体现的是浓厚的男性叙事特征,具有高度凝缩的男性文化形象、家族品格与精神追求,体现的都是传统的父系社会精神,其中女性是父系社会秩序破坏与升华的重要因素。二婶是小鲍庄中虽不起眼但不可缺失的一位女性,通过对她的刻画,作者展现了女性在父系叙事传统之下的形象意义和结构意义。因为与二婶的结合,鲍庄人用言论指责拾来违背礼教,挑战秩序,是典型的逾矩行为,拾来与二婶的结合成为违背秩序的行为。殊不知,这一结合发生在特定的时刻——小鲍庄被洪水冲垮的前夜。大水冲垮的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小鲍庄脆弱的“仁义”精神。捞渣用自己的生命彰显了仁义,不仅完成了角色形象意义的升华,更是建立起了小鲍庄的新秩序。在大水过后,捞渣作为典型形象在全省被宣传,拾来与二婶的结合也被视作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典型事件而大肆宣传,自此之后,“二婶要敬着拾来三分了,庄上人都要敬着拾来三分了。”[8](P51)拾来也逐渐掌握了在小鲍庄的话语权,成了小鲍庄新秩序的塑造者之一,而二婶依然是拾来的附庸,并未发生大的改变。与二婶的结合让拾来在旧秩序中被抨击,但也使其在新秩序中获得话语权,这一事迹也成为新秩序的补足性事件,不仅使拾来地位提升,也使得新秩序较之旧秩序显得更加包容、合理。
从母子一体到父子相继,从反叛旧秩序到融入新秩序,男性主体的最后确立需要通过母亲、妻子等女性形象成长、升华成为男人、丈夫和父亲,完成自我主体的确认,进入到父系文化的象征秩序之中。女性书写在寻根文学中有了第一层含义,作为结构性因素帮助男性完成自我确立与精神的崇高化,补充父系秩序尚未进入带来的不足并使其延续和升华。
(二)作为驱逐因素的女性:对民族主体的优化书写 在寻根作品中,对民族优根性的描写占大多数,但亦存在对民族劣根性的描写,与批判丙崽这样高度符号化的男性形象相比,对女性的批判书写则从细节着眼,通过具体的性格描写来进行民族劣根性批判,并以此提出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具体方向,达到重塑民族灵魂的文化目的。除此之外,新女性的反叛声音也被作为驱逐因素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被予以排斥,从而达到对民族主体优化书写的目的。
首先是作为民族劣根性批判典型的寻根作品《爸爸爸》,其中塑造了丙崽娘这样一个自私自利、自轻自贱的女性形象。她爱搬弄是非、在人后闲言碎语,“这婆娘爱好是非,回头就找这个嘀咕几句,找那个嘀咕几句。”[9](P16)她自私自利,为了一己之私将村人公摊的猫粮作为娘俩的食物,除此之外,韩少功还在《女女女》中塑造如幺姑这样存在变态心理、最后疯狂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韩少功曾表示要塑造新时期的东方新人格,显然他批判劣根性,展现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中的某些弊端或丑陋的因素,目的是重塑民族灵魂,优化对民族主体的书写。
为了维持父系族群共同体的秩序与稳定,新女性的声音被视作游离甚至反叛民族文化的不稳定因素,从寻根文学中被驱逐。典型的例子是《老井》中的巧英。老井村的传统是打井,这已成为老井村维系文化共同体与历史记忆的基本“仪式”,并且以父子相继的模式一直传承下来,成为由男性不断传承的族群历史。而巧英面对坚如磐石的男性族群历史有多重身份喻指。首先她出身于城市,并不从属于老井村的文化血脉,自然无法理解并共情老井村的文化记忆。其次,她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现代女性,她并不认同老井村所代表的传统观念,期盼带孙旺泉从老井村一同出走。最后,她不仅在精神上不认同老井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身体上也完成了出走的行动,可以说真正脱离了老井村的族群文化。巧英提出的科学种田方式显然是对老井村打井传统的挑战,不仅是现代科学对传统打井的挑战,也是个人主义对集体化生活的挑战。由此观之,巧英的存在显然威胁到老井村稳定和牢固的族群传统,因此她必须被驱逐出去。文化民族主义叙事中的激情来自寻找历史传统内部的稳定,缺乏对现代性价值的思考,因此这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象征,现代女性退出父系族群文化之根,展开新的寻求自我的旅程。
从女性身上提炼民族劣根性,到驱逐新女性的声音,部分寻根作品在书写中将女性所体现的民族缺陷、现代意识作为被驱逐的因素进行书写,最终是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传承与优化。
(三)作为文化因素的女性:对民族主体的同质书写 寻根文学热潮的出现与世界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好奇与窥视关联紧密,南帆认为,寻根文学显然希望得到世界文化的赞许,许多寻根作家以传统文化应对当下的文化焦虑,有寻根文学作家就明确表示了这种后殖民话语下的焦虑,比如作家阿城:“我的悲观根据是中国文学尚没有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4](P89)而此时的女性书写则作为文化因素被写进对民族文化的开掘中,变成了一种对性别自然化、无差异的抽象人性的书写,最终在对民族主体的书写中被同质化。
在莫言的创作中存在众多类型的女性想象类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母亲的想象。上文提及的无父的焦虑在对母亲的想象中得到了实现,自我的建立必须借助他者的参与,对母亲的想象在建构自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红高粱》中,戴凤莲是一个男人般的女人,一生勇敢不屈,追求自由,身上凝聚着具有原始意味与生命激情的民间气息,她给了豆官以最初的主体想象。在戴凤莲壮烈牺牲后,她生机勃勃的生命与民族文化的不屈不挠融为一体,显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机、勇猛以及面对外来侵略时的不屈不挠。《丰乳肥臀》中,作者对母亲形象的歌颂与对土地的崇拜结合在一起,母亲成长受难、婚后境遇与生殖受苦的血泪史是典型的东方地母受难史。坚韧、无私、善良的母亲默默地承担着生命中的痛苦、灾难、死亡,闪耀着悲悯的神性光辉,她对儿女们一视同仁,付出心血与关爱,不论任何党派、种族,她都给予无限的包容,母亲形象的塑造正如同伤痕累累的中华民族对中华儿女的包容与关爱,因此这一形象成了中华民族的真实象征。由此可以看出莫言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与高密东北乡的土地文化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母亲形象完全被物象化了,成了红高粱的图腾、乳房的图腾、民族的图腾。
作为寻根作品的典型文本,少数民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同样塑造了一个藏族文化的女性化身——次仁吉姆。小说通过塑造四个次仁吉姆,展现了藏文化在经历外来文化侵略时的发展和历史循环的时间观。次仁吉姆的塑造是极具象征意味与魔幻意味的,她一出生便伴随着神迹出现,会跳神秘失传的格鲁金刚舞,体现了藏文化神秘奇异的意味。充满原型意味的次仁吉姆在被外国人亲吻之后,脸上流出了脓液,并且失去了神迹的启示,隐喻着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体现了藏文化保持文化纯粹的坚持与对外来文化的拒斥。第二个次仁吉姆是第一个次仁吉姆出走的灵魂,她追寻扎西尼玛远走高飞,走向新的世界,她身上体现了藏文化巨大的感染力。第三个次仁吉姆对于藏文化极其虔诚,她成为第二个次仁吉姆返回西藏的部分,承担起繁衍族群与传承藏文化的责任。第四个次仁吉姆则彻底结束了藏文化原型“次仁吉姆”的命运,她去加州大学留学,接触了西方现代文明,暗示着民族文化在现代世界文化中融合与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四个次仁吉姆的发展循环、自我封闭和最终走向现代的过程,可以看出藏文化强大的文化感召力、适应力,以及主动走向历史性进步的特点。每一个藏族女子都可在次仁吉姆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这鲜明地体现了次仁吉姆是作者塑造的藏民族母题的象征,代表着藏文化的传承与不断延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寻根文学通过文化原型的塑造、变化与发展,缓解面对世界文化时的焦虑,不断发掘民族文化的岩层,以期获得世界文化的认可。在这样的创作目的导向下,女性书写被同质化,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被共同歌颂,消弭了女性自己独有的声音,作为单一的文化因素被书写进民族主体中。
四、总结
古代妇女在强大的封建伦理道德场域中无法确认自己的位置,尚无觉醒的主体意识,更不消说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到了现代中国,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同新文化运动、革命运动、解放运动等文化、政治、阶级意味浓厚的因素裹挟在一起,虽然已经有自觉意识,但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在具体人性被抽象化,个性被集体化掩盖之后,女性主体的失落伴随着人的主体意志的失落彻底消失在文本之中。当女性书写迎来新时期文学的曙光,当文学解禁带来光明的希望时,女性书写却又被寻根作家急于证明自我、展现自我的文化焦虑所压抑,作为结构性因素、驱逐性因素与文化性因素写进民族文化中,这虽然可以说亦是对女性自我的一种丰富和建构,但却忽视了最真实可感的女性形象书写,出于文化目的的书写并未关注到女性自发自觉的声音,出于融入全球化语境的创作渴求,也未能正视女性书写的真实需求。以至于在此之后出现了私人化、身体化的女性写作,且不论成就与缺陷,20 世纪90 年代的女性书写无疑是对寻根创作一次反思和矫正。
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与地域、民俗、文化等因素紧密结合,展现最原始的文化体征。但同时,寻根文学也对具体鲜活的女性形象进行遮蔽,使其处于强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下,在寻根作家的文本世界中彻底失去说话的权利。如果能够意识到女性在亚文化世界中处于的边缘位置,尊重女性话语内出现的多元化趋向,不将女性问题简单地与阶级、民族、国家、革命等因素相裹挟,而是理清书写女性最初的心理动机,在女性问题与民族、世界、阶级等问题中寻求适度的结合点,或许可以使女性文学书写逐步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