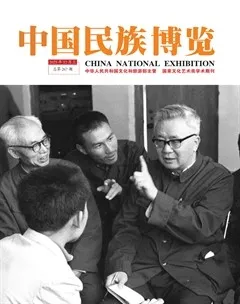论丁衍庸的“戏画”艺术
刘康康


【摘 要】戏曲人物画是戏曲与绘画艺术的集大成。丁衍庸的戏曲人物画是继关良后的又一创造,既是对徐渭、八大山人等人的传统中国画的继承,又是对关良的戏曲人物画的变法。文章通过对丁衍庸戏曲人物画传承与变法的探讨,间以作品的形式分析,以小观大,意在勾出有关“戏画”艺术的完整轮廓,以便对他的创作有更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戏曲人物画;变法;艺术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23—163—03
一、“戏画”概说
戏曲人物画属于人物画中的一类,主要以戏曲中的某一特定情节、人物为表现对象。戏曲人物画最早可追溯至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所刻画的“百戏”图像。继而可在宋元时期的杂剧绘画中得见。据巫鸿《世界是个大舞台——雅、俗艺术中对戏曲的表现》中对宋代杂剧图像的分析可知,宋代杂剧图像可分为两类,一类表现成排站立或者结对行走的人物;一类图像更加具有叙事性。[1]第一类的具体表现可见于南宋画家朱玉的《灯戏图》,13位扮相各异的人物一致排开,给人诙谐幽默之感。第二类可在传为苏汉臣的《五花爨弄》中得见,该图将杂剧图像与婴戏图结合,表现五个孩童穿着大号戏服表演的一个戏剧化瞬间,极具叙事性。亦可见戏曲人物画随着这一时期经济繁荣而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明清时期由于木版印刷戏曲图书的盛行,可谓戏曲人物画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艺术家们不单只刻画人物,而是以文人画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造,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如《西厢记》插图中崔莺莺收到张生来信的一段,陈洪绶通过在屏风上描绘蝴蝶、花朵等来暗示其心理状态。戏画发展至19世纪,题材更加多样化,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白蛇传、打渔杀家等;戏曲角色选择也颇为全面,生、旦、净、丑皆有所涉及,又因创作目的的差异,艺术家在表现角色的选择上又各有喜好;表现手法上诸家取法不同,缤彩纷呈,具体相关分析见于下一章。其中关良率先以文人画的方式表现戏曲人物。随后众多艺术家,诸如林风眠、叶浅予、丁衍庸等人亦开始在中国画中表现戏曲题材。该画种遂逐渐成一潮流,发展至今。
二、丁衍庸与“戏画”
(一)传承
正如丁衍庸本人所言,“不吸收新文化以及外来文化,那能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好似春蚕食叶一样,不把叶子消化了,如何吐得出丝来!”丁氏的“戏画”艺术必然是多方影响下的集大成。为探究丁氏“戏画”的形成原因及成就,笔者从外、内两方面着手进行。20世纪20年代求学期间,丁衍庸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丁氏早期创作以油画为主,如他于1933年创作的《花前》,以线条化的画风表现女人体,可见马蒂斯的影响。倪贻德曾描述丁氏这一时期的画风“笔势飞舞,色彩夺目”,“爱用绚烂鲜艳的色调,但绚烂而不刺激,鲜艳而不庸俗”[2]。1929年他初涉中国传统绘画,对八大山人、石涛、金农等人的作品兴趣渐浓,并将其所学运用于油画创作。1946年他正式步入国画领域,并且将余生的大部分精力放在中国画上。至于丁氏何以如此?陈传席先生归纳总结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丁氏自始至终是一位爱国人士,从他积极参与国画改革及艺术教育就可得知。另一方面,丁氏在《八大山人与现代艺术》中提及,他认为西方艺术“走入了一个死胡同”,东方艺术“注重精神的表现,不斤斤于形式”“具有无限的发挥空间,反而显得更为优越”。[3]以上两方面让丁氏无论从感情、亦或艺术质量上,都必须投身于国画创作。
有关丁衍庸中国画传承的谱系,他曾自述:“基本上,我的画风源自王维、宋米芾、元黄公望、明徐渭和陈道复、明末清初朱耷及晚晴迄今的吴昌硕。”
由此可知,本文所讨论有关丁氏的人物画方面师承应是徐渭、朱耷、吴昌硕一类的明清至近代以来的简笔写意传统。这里笔者需要稍带提及开创简笔写意人物的梁楷,丁衍庸曾于1971年创作过一幅与梁楷同一题材的《太白行吟图》,可见梁楷也是丁氏所师法的对象。相比于梁楷笔下李白的单纯朴拙,丁氏以同样泼墨淋漓的笔法表现李白,但人物形象奇简夸张,更加具有怪诞感。这里涉及他的“变法”问题,具体可见于下一节。丁衍庸也师法徐渭,在《徐文长与现代艺术》中,他指出“文长的画,可說是无可比拟的,严谨处,六法俱备;狂放处,前无古人”。[4]我们可从徐渭的花鸟画作品《墨葡萄图》看出,以洒脱的大写意用笔表现一株自画面右侧探出枝杈的葡萄藤,墨汁淋漓,逸气逼人。丁氏自身画中的狂逸之处即来自徐渭的影响。如《霸王别姬》中“霸王”形象,以淋漓的笔墨表现人物的上半身,正如徐渭的“墨戏”一般,丁氏亦采取一种戏谑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描写世界。此外,他肯定了徐渭对于中国画发展的重要影响,甚至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产生也功不可没。在众多师承之中,丁衍庸最为推崇朱耷,他认为“八大山人的为人和他所创造的艺术是人类最高的表现”“艺术家一定要走在东方色彩的大道上,才有发展的希望”。[5]因此,他取法于所收藏的八大之作,将八大极具创造力的意象表现融于己身。丁衍庸通过符号化处理将线条艺术中的“绘画性”与“书法性”界限模糊,使他的戏曲人物画充满速写感及浓重的书写意味。
(二)变法
上述有关丁氏画风的形成属于外部影响,以下将对内部成因进行探析。我们知道丁氏并不是首位创作戏曲人物画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丁氏要从事于“戏画”创作?相比于关良的戏曲人物画,丁氏“变”在何处?此外,丁氏“戏画”的艺术价值在何处?以上几方面的讨论构成本文的主旨。
通过对丁衍庸、关良二人艺术活动轨迹的考据,二人在活动轨迹上有重合之处。二人作为同事兼好友的关系,二人的艺术理念必然不谋而合。据考关良存世最早的戏曲人物画作品创作于1927年,丁氏则是自1946年开始中国画创作,60年代才开始戏曲人物创作。那么依上诉活动轨迹,丁氏必然亲眼见过关良的戏曲人物画作品。因此在关良的影响下,丁氏进行“戏画”创作也不足为奇。再者,戏曲人物画的创作经关良的倡导下,蔚然成风。与二人同时代诸多国画名家如林风眠、叶浅予、庞薰琹等人也都曾创作过这一题材的作品。
有关丁衍庸创作“戏画”内因,我们有必要先对丁氏的花鸟、山水画进行探讨。丁氏的花鸟画作品通常以青蛙搭配八大的荷花、徐渭的葡萄藤、八怪的芭蕉、吴昌硕的瓜棚以及白石的虾蟹。首先以他于1946年创作《蕉蛙图》为例,画面中芭蕉叶以大笔挥毫而成,芭蕉叶下又以较细的笔画了两只青蛙争跃比高,使整个画面趣味盎然。得见丁氏的花鸟画造型夸张、结构简逸、用笔圆劲内敛、墨色清透明润,是天真、谐趣的文人游戏。丁氏的山水画较花鸟画少,延续传统山水的模式,也有类似速写类作品,结构极其简单,以粗拙枯涩之笔作符号化树石。如《桂林山水》中的山石树木,以浓墨大笔涂刷山体,山顶草草点出树木,又在画面下侧以及山石左侧信笔勾勒三条渔船。最有意趣的是画面下侧渔船上斜向上成排的鱼鹰,颇似孩童涂鸦之作。由上述山水图像可见丁氏不注重如实描绘景物,而以写胸中丘壑,吐胸中块垒为宗旨。丁氏由花鸟、山水题材创作移转人物题材方面,必然也抱同一目的,不过分注重形体的写实,坚持对“天真”“原始”意味的追求,同时也希冀为中国画变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外,纵观二人的“戏画”作品,刘颖在《画中有戏、形神兼备——关良笔下的戏曲人物形象》中总结:“关良笔下的戏曲人物生旦净丑均有所见,老生、武生是他表现的重中之重,如薛仁贵、林冲、武松、孙悟空等”“性别上,男多女少;行当上,生多旦少;具体到各行中的小行当中,武多文少”。[6]而由《丁衍庸艺术回顾展》中所收录的“戏画”人物得见,丁氏所涉也甚广,但更多的是表现以便于他抒心中之所感的题材,其中女人体尤多。由此可见,关良出于对戏曲的喜爱,题材选择上甚为广泛,但他更偏好表现武生,由于其在戏台上动作尤其多,更有助于关良表现人物的“神”。丁氏表现“戏画”的根本目的更多的是借作品进行讽喻,因此他表现裸体女性也合乎情理。

对于丁氏创作“变”在何处的问题,笔者考察了二人一生曾创作过的“戏画”题材,二人都曾创作过四大名著、红楼梦、打渔杀家、牛郎织女、白蛇传、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题材。对于上述如此众多的作品数量,笔者选取其中几种具有典型性的作品对其进行形式分析,以求读者得到更直观的理解。京剧《贵妃醉酒》讲述杨贵妃邀请唐明皇赴宴,明皇爽约未至,贵妃饮酒大醉的故事。戏台上青衣展现的是“贵妃”微醺下,一颦一笑之间舞动扇子的状态。关良于1979年所作《贵妃醉酒》属于对“杨贵妃”的直接描绘,是戏台上的人物表演瞬间的再创造。究其原因,与他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并且以之为爱好密切相关。他追求“戏画”在时空中的“永恒性”,捕捉最传神的人物动态。李苦禅曾评价关良:“良公这种画叫做得意忘形。”相比于关良,丁氏于1978年作的《贵妃醉酒》中的“贵妃”形象一反传统人物画的范式,造型夸张,类似于漫画式造型。画面中人物皆表现为侧脸,瞪大双眼,以如此朴拙的线条表现人物,颇具趣味感。区别于丁氏的写意性线条造型,关良则以墨兼线造型,在色彩选择上,二人亦有不同。关良取材于现实中戏服的颜色,丁氏则在野兽派的影响下色彩运用极为大胆,在画面中使用粉红这类极为鲜艳的颜色。
对于上述人物的表现,可见丁氏“戏画”中西方的影响。同时在《霸王别姬》中更加明显得辨识出来。关良于1983年所作的《霸王别姬》一如上述,是笔墨形式对戏曲人物形神的再创造。丁氏则将“项羽”表现得更为怪诞,怒目圆睁,手举武器;虞姬则以书法性线条表现为形态扭曲的女人体。让人诧异的是丁氏画中的虞姬并不是穿着传统戏曲服装,而是民国旗袍。
上述丁衍庸与关良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结为取法不同,关良在画面中平衡视觉与听觉关系、二维与多维表现之间的关系,给观者展现出戏曲人物画更加传神的表现。丁氏的“戏画”融合东西方文化而自成一格,是现实中理想与失意、荒诞与反讽的缩影,是表达现世生活个人情感与思想诉求的载体。接下来我们要谈丁氏“戏画”中的另一个创新之处。从《贵妃醉酒》谈起,关良注重作品中杨贵妃“神”的艺术化表达,而丁氏更在意画面中的艺术技巧及中西方艺术内在本质的关联。正如丁氏所说:“中国绘画的中心,始终是文字一样代表人类最高的理想和意志的产物。”他那充满速写感以及书法意味的戏曲人物是他对中国现代主义精神理解,亦是他对中国现代绘画交上的一份答卷。
三、丁衍庸“戏画”价值
丁衍庸是继关良后“戏画”创作的重要代表,虽不似好友关良那般出名,但是他亦是绘画史上的一位重要的藝术家。丁氏诗、书、画、印四样皆长,人物、山水、花鸟无一不精。本文所谈论的“戏画”艺术也是他在艺术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维度与可能。丁氏的“戏画”奇简夸张,单纯朴拙,笔墨清狂,稚拙而又高雅,他充满谐趣与戏谑性的表现方式,是他对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探索,也是他对现代社会物欲至上的挖苦与嘲讽。
关于丁衍庸戏曲人物画的艺术价值,第一,丁氏戏曲人物画是中国画现代转型的有效实践。20世纪的中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急速向现代转型,文化艺术方面也出现巨大变革。艺术家对待中国传统绘画也出现不同立场,即激进、保守及折衷三派。丁氏抱着对于中国绘画的热爱而回归中国画创作,他流连于八大、徐渭、石涛、齐白石等大家之间,以期寻求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法。他的“戏画”将东方艺术中含蓄内敛的精神内涵与西方表现主义充分结合,并与诗、书、篆刻相结合,以“墨戏”的方式来表达其人生感受,是“新文人画”的代表。画家谈锡永评价其:“他的画纯粹属于中国,特别是那分特别的‘金石味。”石守谦曾评价他:“尽脱八大山人形骸,全在精神层次发展他的现代水墨。”[7]总之,他的画是向中国画“登堂入室”的回归,也是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再创造。第二,他的“戏画”对关良创作内涵的再丰富。诸如《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与关良相同题材的表现,丁氏以更加变化丰富的笔法表现人物,开拓了戏曲人物画表现的新路径。同时对于后来人的艺术创作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三,丁氏的“戏画”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帮助。他以极拙、极趣、极简的方式重构了戏曲艺术,亦可谓是对戏曲艺术的推广。
参考文献:
[1]巫鸿.陈规再造: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2][4][5][7]倪贻德.南游忆旧[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3]丁衍庸.丁衍庸艺术回顾文集[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6]刘颖.画中有戏、形神兼备——关良笔下的戏曲人物形象[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