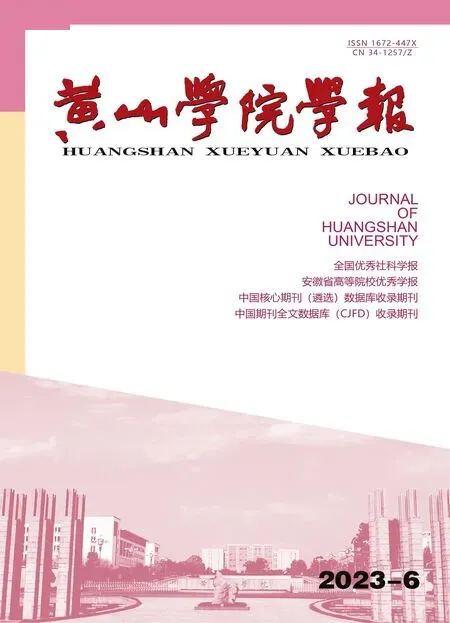论安吉拉·卡特《独角兽》的异质性
——生成机制与文学实验
孔令云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一、引 言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42 年)是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当代英国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在美学、形式、语言、思想等层面皆异于传统和常规,其形态自足、完整和迷人,思想深刻、开放和有建设性,被誉为当代“异质性文学”的典范。梳理已有的卡特研究,发现研究集中于卡特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集,而她的两部诗集——《五个无声的呐喊者》和《独角兽》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少人问津①,正如诗人克里斯托弗·劳格所言:“卡特是一个被低估了的诗人,虽然她的诗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目前有些研究已关注到卡特作品的异质性,但多拘泥于文本内的阐述,重在描述卡特的文体风格和写作技法,而对卡特“异质性书写”的生成逻辑探讨不足。在此研究背景下,以诗歌《独角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异质文化语境、创作主体独异的诗学思想及其独特的经验自我三个层面展开剖析,揭示卡特“异质性书写”的内外动因,并从价值立场和美学形式两个方面,分析卡特诗歌的异质性,最终说明卡特“异质性书写”的美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异质性”本是遗传术语,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异质性”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隐喻,并与文学理论、经济理论、社会政治理论有机融合,形成“文学异质性”“经济异质性”和“社会异质性”等概念。其中,文学异质性是一个强调差异性的文学批评术语,特指那些风格成熟、独具一格且给读者带来强烈陌生化阅读体验的作品特质。它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概念,核心是“作者在人类的基本认知中,发现已知的阴影和未知的深渊,并借助语言、形式、感觉与情绪的异质,提出新知甚至先知”[2]。
二、异质性书写的生成机制
诗歌《独角兽》的思想立场和美学形式皆异于常规和常态,而要理解这种“异质性”就需要追溯其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创作主体的诗学思想和经验自我。
文化异质性通常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特质和文化内涵的两种或多种文化并存于同一个社会空间中,是文化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文化异质性在特定的社会空间里,具有特定的意义内涵。在20世纪60 年代的英国,文化异质性突出地表现为“新观”与“旧思”两者并存。更确切地说,是新兴的“享乐主义”“快乐原则”与传统的“理性精神”“现实法则”在张力中共存。一方面,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快乐至上”原则和“享乐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英国大众社会文化心理中。例如,娱乐场所在主要城市里纷纷建立起来,追求自我宣泄的摇滚音乐开始盛行,崇尚个性表达的服饰成为时尚。正如历史学家史蒂文森所言,1968年“不仅见证了革命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而且见证了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放纵主义的全盛期,一场精神和感官上的另类革命。”[3]另一方面,“现实法则”和“理性精神”依然是英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构成,具有不可撼动的影响力。“理性是英国民族的灵魂。即使处于巨大的变革中,英国人依然对事实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分析,这是他们据以行事的依据,也是这个民族自己极为珍视,几乎带着宗教式的虔诚心情来看待的精神财富。”[4]简言之,“享乐主义”和“现实法则”是20 世纪60 年代英国异质性文化的基因编码。
卡特敏锐地察觉到了20 世纪60 年代英国社会文化的转变,并在不同的场合做出评论。她指出:“在60年代的英国,‘快乐宗旨’遇到了‘现实原则’,就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遇到了一个不可撼动的物体。”[5]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拥有强烈文学意识的年青诗人,她尝试“异质性书写”,以折射异质的文化语境。“卡特是20 世纪60 年代的诗人,她的诗歌携有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基因。”[1]71诗歌《独角兽》充分地体现了20 世纪60 年代特有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双重性。一方面,故事发生地是一家脱衣舞俱乐部里——人们追求快乐、刺激,放纵自我的地方。另一方面,《独角兽》承载了诗人深刻的现实情怀和独特的社会思想。它描述一个脱衣舞女郎在男性为主导的俱乐部中的生存困境,揭示女性群体的生存危机。在诗歌《独角兽》中,“娱乐性”与“现实性”相互交融,完美统一。
一部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形式风格与创作主体的文学观念、资禀、气质、性格、思想、情感、愿望、理想等一切条件直接或间接相关。只有那些对文学创作具有独特观念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作品。20 世纪30 年代,弗·雷·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年)的文化诗学批判思想形成,英国文学批评进入新的时期。利维斯认为文学分崇高文学和低俗文学。“好”的文学秉承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承载文学的教诲功能,具有正统性、严肃性和道德性。利维斯主义自诞生之日起,统治英国大学的英语文学批评课程近30 年,直到结构主义兴起时,他的学术霸权才瓦解。虽然卡特当时就读的布斯特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唯利维斯主义马首是瞻,但是卡特却对其嗤之以鼻,揶揄它是一个“吃掉你的西蓝花”的理论。她喜爱小众的世俗文学和想象文学,认为与“少数的高雅文学”相比,它们更加有趣、刺激,且具有更强的艺术性。此外,卡特广泛阅读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书籍,大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文学,以及布莱克、布德莱尔、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的作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卡特崇尚“想象、刺激和趣味”的异质性诗学思想逐渐形成,与同时代主流的诗学观大相径庭。
20 世纪60 年代的英国文学界受社会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致力于平铺直叙地描述现实生活,缺少活力与新见。卡特的“异质性书写”是对同时代“模式化”和“趋同化”主流文学的一种反向。值得一提的是,卡特在众多独角兽故事的版本中,选择托马斯·布朗爵士(1605—1682 年)的版本进行改编,反映了她独异的诗学思想。布朗爵士是一个游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异类”,他性格古怪,反叛意识强烈,想象力丰富,语言生动。卡特认同布朗爵士的思想观和文学观,且在诗歌创作中承袭了他代表的“异质传统”。诗歌《独角兽》具有同时代作品中罕见的刺激性、趣味感和粗俗感。“在文学的荒地上,卡特超越了利维斯伟大传统的老路。《独角兽》中的裸身胖少女形象与粗鄙、夸张和露骨的描述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情节,这些被利维斯主义边缘化的低俗元素,在卡特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运用,并展现出极大的艺术魅力。”[5]74
《独角兽》的异质性与卡特独特的自我意识和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卡特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叛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新女性,“在她人生中的每个重大场域和每段重要关系里,都有意识地背离传统女性的定义,进行自我发明(self-invention)”[6]。婚前,她与传统女性代表的母亲欧丽芙冲突不断,执意要摆脱母亲对她的女性规训,积极塑造自我形象。她抽烟,说脏话,穿黑色紧身衣(在20 世纪50 年代是堕落青年的记号),听摇滚乐,染头发,看新潮电影……外在的特立独行折射出她与众不同的内心世界。与此同时,她对时下的社会热点问题总是持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她的女性同学杰奎琳·安东尼曾评论说:“卡特舌灿莲花,观点又那么鲜明。她是一个自尊、自信的女孩。”[6]94婚后,卡特继续与女性的传统角色和身份价值相抗争。在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早期,英国女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大男子主义文化盛行。整个社会强调女性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职责,抑制女性外出工作,追求自我价值。然而,卡特坚持她的价值在于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而非料理家务,并且丈夫应该尊重她的抱负。因此,尽管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制,她仍坚持阅读并进行文学创作。
卡特在《独角兽》中有意识地融入她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书写她个人的故事。因此,在卡特的作品中,读者总是能找到诗人自己的影子。她的“自我”以自我叙事和自我指涉等多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诗歌《独角兽》里脱衣舞女郎“生涩和粗壮”,她充满肉感的形象与同时代的主流审美标准大相径庭,却暗合了卡特本人高大的外形;诗歌取材于中世纪的经典故事,显然是受诗人彼时阅读的书籍影响和中世纪文学老师科特尔教授的启发;诗歌中的脱衣舞女郎趋于男性化,具有抗争意识,源于卡特那个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卡特曾在俱乐部里做过服务员,亲身经历了那个场域中的两性权力关系,因此她诗歌中脱衣舞俱乐部带着“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感”。
三、价值立场的新书写
在西方,独角兽的故事流传久远、家喻户晓。它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流行于欧洲中世纪。中世纪的《神兽传》(Bestiary)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独角兽无人能擒、无计可获,除非以一位少女为诱饵。当独角兽发现坐在远处的少女时,就会立刻冲上去,将头温顺地埋在少女的大腿中间,安然入睡。这则故事塑造了独角兽的基本形象,赋予了独角兽故事的经典寓意。此后出现了多个版本的独角兽故事,然而它们的思想立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凸显基督的圣洁与救赎,或歌颂爱情的崇高与伟大。与之不同的是,诗歌《独角兽》的价值立场散发出强烈的“异质性”。
在诗歌主体部分之前,诗人写道:“让我们来切割它(经典独角兽故事),来组成我们自己的诗歌。”[1]3“我们”指代那些与卡特一样不趋同、不盲从、致力于发出自我声音的作家。“切割”和“组成”意指诗歌《独角兽》根植于却不同于传统的独角兽叙事,它不是要对源文本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增加或删减,而是对源文本价值立场进行颠覆性和再生性的改写。“如同莎士比亚,她善用已有的叙事,并且突破它们的局限去创作出伟大的作品。”[7]
诗歌记述了一个男性脱衣舞俱乐部老板为了擒获独角兽,施计安排一个脱衣舞少女去色诱它。它虽然保留了“用处女之身诱捕独角兽”的传统情节,却将其异化成一个性别斗争鲜明的现代故事。首先,从人物关系和象征性来看,《独角兽》中的幕后猎手不再是泛指的“人们”,而是一个男性脱衣舞俱乐部老板。他是脱衣舞俱乐部“权力链条”中的“领导者”,策划、操控和决定脱衣舞女郎的命运,而处女充当“他者”,被视为失去人性的存在,是实现“领导者”计划的“工具”。就人物象征性而言,俱乐部老板指代20 世纪60 年代英国社会中的男权阶级,而脱衣舞女郎则指代英国女性群体。两者之间是“压制与反压制”的关系,指向英国社会中的性别斗争。其次,从叙事结构来看,诗歌《独角兽》的叙事结构更为复杂,它在保留诱捕行动的基础上,新增了脱衣舞女郎反抗男性脱衣舞俱乐部老板这条叙事进程,并将其前置。叙事结构的改变,意味着卡特要对传统独角兽故事的宏大主题和现代意义进行拷问。诗中一句设问“问:独角兽和处女有何共同之处?答:它们都是极好的野兽”[1]3直白地揭示了脱衣舞女郎的生存困境。从存在属性来看,同独角兽一样,她被剥夺了人性,是男权社会的“他者”。就存在价值而言,一方面,她和独角兽都是男性的“猎物”;另一方面,她被“性客体化”,是男性用来捕获独角兽的“诱饵”。即便如此,脱衣舞女郎最终实现了从“受害者”向“歌颂者”和“抗争者”的转变,宣告“我深黑色的嘴唇后面,是尖牙利齿;红色指甲油的下面是我的爪子。我能看到你的武器,你却看不到我的武器。你认为你在占有我,但我可以一口咬住你。”[1]4最后,传统的独角兽故事仅仅描述人物的外部行动,而卡特受精神批评分析和现代主义的影响,《独角兽》更强调人物的语言及其心理。诗歌运用了对话、独白和旁白等人物语言表现形式。例如女郎独自的吟唱:“我喜欢跳舞,……然而是你(俱乐部男老板),将游戏变成了战争。你掏出你的那把长刀要不动神色地拿走我的性命。”[1]4人物的语言展现出背后的心理活动和社会图景,揭示了诗歌的女性主义意蕴。综上,诗歌《独角兽》的价值立场与传统独角兽叙事模式化的主题存在巨大的差异,带给读者强烈的陌生化阅读体验,从而引发他们对女性群体的现实困境进行思考和改变。
四、美学形式的新创造
思维方式的与众不同自然体现在美学形式的与众不同上。尽管卡特熟知英语诗歌的传统形式,然而她要与之背离,创造新颖而独特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实现美学形式和思想立场在异质层面的统一。
首先,从文体与结构上看,《独角兽》与传统诗歌大相径庭。它由三部分构成,小标题分别为:“独角兽”“年轻女郎”以及“灯光和行动”。在第一部分,诗人描写了高贵的独角兽在迟暮中出场,尤其强调了独角兽那只逐渐清晰而高贵的“角”。在第二部分“年轻女郎”中,诗人描述了那个扮作诱饵的处女裸身模样,以及她慌乱和痛苦的心情。在第三部分“灯光和行动”中,诗人描写了独角兽如何被年轻女郎吸引以及她的战斗之歌。三段式的结构有效地突出了每部分的叙事重心,推动了叙事进程,使局部内容和整体叙事相得益彰。整首诗是散文体的叙事诗,没有严格的节奏、韵律和工整的诗行,而是把一段叙述文字切割成若干行。此外,卡特还大胆地加入了一些“画龙点睛”式的个性化和实验性的元素。借助这些独创性的技巧,诗歌要旨被突出,读者可以迅速地进入“深层阅读”。
其次,《独角兽》粗鄙直白的语言进一步加剧了诗歌的异质性。这彻底地颠覆了诗歌传统的审美取向,在极致的“俗”“丑”和赤裸直白的文字表述中,读者感到被冲击、惊叹,甚至恶心,同时领悟出诗歌背后深层次的女性主义诉求和抗争。
最后,极具个人风格化的语言赋予了诗歌独特的气质。卡特摈弃模式化的用词,运用多个细腻、具体、感官性的词汇去描述事物,制造出深刻而有质感的语言效果,体现了诗人对文字运用的敏感性和灵活性。例如,“黑夜”在人类经验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物,但卡特没有简单化或模式化地处理它,而是富有想象力地使用画面感强的描述——撕开隆起的夜幕(ripping the bulging belly of the dark),来描写独角兽在黑夜里奔跑的样子,且预示着如同黑夜笼罩的现实社会将被撕开。
五、结 语
将西方经典作品“异质化”和“当代化”是卡特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它萌芽于她的早期诗歌《独角兽》中。从文化社会语境来看,卡特的异质性书写根源于20 世纪60 年代英国异质性的社会文化;从创作主体的个体性而言,“异质性书写”是卡特社会观和文艺观的创新性实践,也是卡特经验自我的文学性表达。卡特颠覆了经典独角兽故事的主题思想、旧有形式和惯用审美,并在此过程中赋予了诗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一种“异趣”。
值得强调的是,卡特进行异质性书写,并非简单地“为异质而异质”,也并非试图创造卡特式的“文学神话”,而是要借助异质性书写,提出改良英国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的新见。她呼吁文学创作去“虚”就“实”,融合“现实与想象”,兼顾“传统与现代”,从而实现文学的审美价值、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注释:
①卡特的诗歌主要发表于1963—1966 年期间,它们不仅对卡特后期作品有极大的影响,还深刻地揭示了20 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的现状,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独角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首诗,发表在卡特和诗人尼尔·库里(Neil Curry)共同主编的诗册《远见》(Vision)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