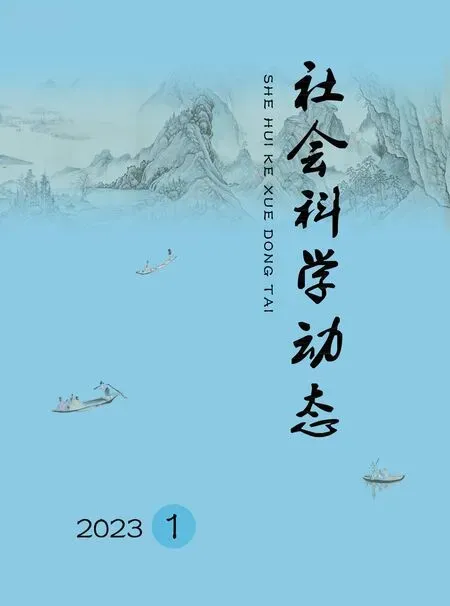中国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研究:基于文献视角
公茂刚 张 云
一、引言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生产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同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粮食安全。事实上,农业对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工业化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自1952年至1997年期间,中国农民以这种 “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形式为国家工业化发展贡献了12641亿元的资本积累①,达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起飞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条件,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人口流动限制逐步取消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产生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农民得到的土地征收补偿款低于土地价值,卖地收益中的大部份被用于城市和工业建设。一言以蔽之,农民在我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当我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时代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时,国家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方针。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 “两个趋向” 的重要论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指出,现在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从2004年开始,国家逐步取消了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在此基础上,还加强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2020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的总额达到1374.28亿元。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临时收储政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救灾资金补助政策等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政府给予农业补贴支持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强其即使没有农业补贴也能内生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实现农业发展的内生化。而过度的农业扶持和保护或者扶持方式不合理均会导致农业发展的惰性和对外依赖性,使其丧失内生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从长远来看,农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可持续内生式发展之路,不仅要摆脱对政府投入的过度依赖,还要形成农业按照价值规律来持续吸引各类要素投入的机制和路径,即实现农业的新内生式发展。要增强农业新内生发展的动力与能力,促进乡村新内生式产业振兴,重点促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逐步实现乡村发展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本文基于文献视角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梳理相关文献,阐明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内涵;其次从发展禀赋、发展理念以及农业体系三方面论述中国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约束条件;随后基于农村地域系统,提出乡村治理和农村社会网络促进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以期有效整合农村地域系统内外力量促进农业发展;最后提出以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中国农业新内生式发展,重点在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地方特色农业和农民主体地位建设。
二、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相关概念
(一)内生式发展内涵及外延
内生式发展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纷纷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各自的现代化之路。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依靠本土资源禀赋,追求生态、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内生发展模式在各国的发展实践中得到推广和应用②。1971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针对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强调居民的参与及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并特别重视环境保护的彻底性。1975年,瑞典Dag Hammar skj ê ld财团在提交给联合国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 “内生式发展” 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式发展的相关理论及实证研究开始延伸至多个学科③。在环境和区域经济学领域,强调解决发展问题需要赋予并保障居民更大的自主权;在社会学领域,强调内生发展需要居民积极参与,并主动寻求和实现本区域发展目标。可见,日益完善的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以人为中心是发展的目的、尺度及条件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内生发展模式得到广泛采用。许多国家重视依托本地的产业、文化和资源来制定发展战略,赋予本地居民对土地和资本的管制权力,体现当地居民意志,重点开发附加值回归本地且主要由当地居民参与的产业⑤。区域内生发展的实质是转换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动能,培育基于本地内部的成长能力,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谋求健全和可持续的地区发展,同时保持和维护本地区生态环境及文化传统,以期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长期效应的结合⑥。
(二)基于农村地域系统的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概念
由于一些乡村长期依靠粗放式投入获取产品来维持生计,使得这些乡村地区陷入 “贫困陷阱” ,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提高农业生产力和保护农村环境的双重目标催生出指导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新理念⑦。农村区域发展强调复原力、地方规划、 “自下而上” 、村民参与等新内生发展理念⑧,重视区域空间系统内要素重组、空间重构、功能提升⑨。基于本国国情,欧洲各国乡村复兴重视区域联网和社会创新,协调整合内力与外力;日本则通过建立 “地域循环共生圈” ,实现城乡共生对流,并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农业农村建设,提升地域循环共生圈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培育农村内源发展动力,实现农村的多功能和可持续发展。
农业空间异质性使得农业转型升级需要着重考虑资源配置、人地关系矛盾、空间地理条件等关键异质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借用地理学的方法将乡村具体化为一个个 “农村地域系统” 空间单元⑩,既保留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内涵,又强调依赖特定区域背景,还能以整体视角应对全球化、市场化等外部力量对乡村发展产生的结构性冲击,进而整合内外资源,强化社会联系,培育根植于农业农村内部的发展动能。农业发展只有脱离小农经济的封闭循环,从 “行政推动” 向 “内源发展” 转型,才能提升农业自我积累与发展能力,实现新内生式发展。基于农业地域系统视角,农业新内生发展根植于本地,以具有社会包容性的社会网络作为农村地域系统与外界联系的桥梁,以本地资源和当地人参与为基础,以本区域与外部空间动态互动为特征,强调权利配置、利益关联机制、地方影响以及农村作为地域系统与外界的互动联系。
三、中国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障碍
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实现一定是多种因素耦合作用的结果,单纯依靠政府资金投入以及社会扶持无法产生农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我国农村的传统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农业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制约因素包括不限于:农业发展缺乏合理的目标规划,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环境滞后、融合程度低下,土地、资金、人才等农业发展要素瓶颈问题严峻,农业主体地位不明确等。同时,农业内部也在发生明显变化,农业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因此,实现农业新内生发展之路障碍重重。
(一)农业新内生式发展资源禀赋匮乏
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必然要依赖经济、文化、资源、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农村地域系统。我国农业粗放式经营造成耕地严重浪费,城市用地挤占农业生产用地现象突出⑪。农村人口基数大,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存在明显的兼业化、副业化趋势,土地均分制使得农业生产经营细碎化,农业劳动力难以选择和使用现代化农业装备和技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阻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致使农业长期囿于传统生产水平。农业特色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开发,依然停留在传统种植业模式,农村水电、道路建设、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由于投入成本过高致使没有得到大范围推广⑫。同时,要素流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偏好以及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不完善的影响,存在从农村净流入城市的问题⑬。农村资源受农村承包地、宅基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产权结构开放性长期滞后的影响,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偏低⑭。
(二)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制度安排不完善
以农地产权制度为代表,近年来推行的 “三权分置” 改革政策提出了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和农地经营权的基本要求,对于放活的方式、范围、幅度等问题仍缺乏具体的制度安排,致使农村土地无法在市场上规范有序地流转⑮,导致空心村面积不断扩大、隐形流转加剧等弊端。城市偏向政策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愈发加剧了农村社会边缘化窘境,长期得不到延伸和扩展的农村社会服务网络限制了农业新内生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获取和整合能力⑯。农村社会保障在居民覆盖面、保障支持水平、缴纳标准设计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顶层设计体系不健全、资金供给能力有待提升、智能化技术应用不佳等现实问题。
(三)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缺乏产业聚集力
由于农业设施投入大、周期长、盈利薄等原因,农业规模性特色产业难以形成,而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网络不足以支撑农业产业集聚⑰,政府引导力度不足,品牌认知度较低,不利于农业内生价值再创造。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供需不匹配现象突出,尤其是农户在资源统筹和市场对接等农业现代化环节存在很大缺陷,以至出现产前、产中、产后价值链断裂的情况⑱,部分涉农企业组织协同能力差,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对小农带动能力弱。分散的小农经营使得机械维护、技术服务等成本过高,农业智慧化、信息化以及数字化建设领域较为滞后,既无法为产业基础薄弱、生产资源分散的农业农村带来规模优势,也无法充分挖掘本区域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
(四)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市场化程度不足
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生产存在 “两张皮” 现象,农业科技创新缺乏激励机制与风险补偿机制,其理念滞后、人才短缺,种种现实困境使得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长期居于低水平状态,阻碍传统农业的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新业态变革进程⑲,进而影响农业新内生发展的生产效率。另外,我国农业要素市场尚在发展初期,滞后于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例如,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成本的土地流转限制了土地的配置效率,无法大规模集中形成规模农业,不利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影响了优质农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由于农业信息不对称,进而促使农业经营主体产生盲目决策行为,影响生产结构,加剧农产品市场波动。农村地域系统社会发展网络还不完善,目前农业生产要素难以与外部的市场体系进行有效的衔接和交换,只能内嵌于村庄社区结构并受其制约⑳,无法延长农业产业链和提升价值链,且缺乏现代组织方式链接外部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市场化改革,不利于农业新内生式发展。
(五)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缺乏韧性,抗风险能力差
由于农业本身无法避免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当自然灾害等不可抗风险到来时,上述农业资源禀赋、内生制度、科技创新能力等约束条件使得现有的农业农村内生发展能力根本就不足以抵御农业风险。长期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合理规划使得城乡一体化、产业园区化、乡村智慧化与智能现代化、高质量农业综合体等有助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改革政策难以落地农村,农村地域系统无法产生强大的农业经济发展韧性,无法保障农业与农村经济系统稳定发展。此外,土地生态韧性不足会减少优质高产粮田的数量,降低粮食生产潜力,不利于 “藏粮于地” 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
四、基于农村地域系统的农业新内生式发展优势
基于农村地域系统的乡村空间治理和社会网络有助于塑造农业新内生发展优势,破除延缓农业新内生发展进程的障碍。完善乡村多层次、非线性空间治理,拓展和强化社会网络联结,既有利于提升农业新内生发展动力,发展多功能农业,也有助于强化农村地域系统稳健性,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及风险应对能力。
(一)乡村空间治理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提供地域支撑力
现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乡村振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㉑。要根植于农村地域系统的资源禀赋,通过乡村空间差异化治理推进制度改革、环境整治和规划创新,搭建乡村空间治理架构,全方位协调地方自然条件与人文属性,形成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新内生发展合力。
1.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了健全的基层组织保障
乡村空间治理的创新和完善,可以提升乡村基层组织效率,推进农村制度、法律、政策的实施㉒,优化城乡格局,加快构建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农业新内生发展组织平台,满足地域农业发展需求。具体来看,乡村空间治理通过创新基层组织机构设置、农村工作方式方法、党员管理和激励机制以及党员干部培养和选拔方式,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功能、致富带动功能等,保障乡村公共领域系统有序、和谐运作,以主动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比起政府和社会资本,乡村集体经济主导的乡村振兴更具有新内生发展能力和韧性,可以作为农村治理改革的重点之一㉓,要充分发挥集体经济在辐射带动、市场导向、要素来源、品牌盈利等方面的组织引领能力,有效地联结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因地制宜地推动农业新内生发展。
2.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了成熟的制度环境保障
乡村空间治理的重心在于拓展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㉔,通过乡村空间治理能够明确界定收益权利、减少信息成本以及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调动农业经济主体积极性,充分发挥农业新内生式发展中制度的激励和信息功能,从而化解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制度约束,进而有效引导资源流转,撬动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投入农业生产。另外,乡村空间治理能有效缓解城乡二元差距,减轻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生产、投资要素配置的阻滞效应,建立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城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构建城乡共享的优质公共服务体系,减轻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农民权利受损的严重程度,优化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制度环境。
3.乡村空间治理提供了旺盛的乡土文化保障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可以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注入乡村文化新内涵,将乡土文化传承置于乡村空间治理的框架体系内,拓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充分利用乡村空间特点和乡土文化资源,重视地方性因素与力量㉕,挖掘农村地域系统承载的多元乡土文化内涵,整合本土的知识、文化传统以及资源要素,形塑农村地域文化价值体系,建设现代乡土文明。具体来说,一方面,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改善农村社会秩序以及农民的精神、生活状态,尤其是文化与认知压力,发展根植于地域内部、利益趋农化的可持续内生农业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克服带有依附和被支配属性的乡村文化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脆弱性,将 “农村地域系统” 作为新内生发展平台,利用地域文化基因形塑地域文化发展属性,改善农民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社会网络提供农业资源整合力
农村社会网络是由农村发展中的各个要素和发展环节构成的,农村区域系统的农业发展资源禀赋匮乏,且与外界存在资本、技术、信息等关键要素的流动障碍。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强调通过社会网络将地方与更广泛的区域甚至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农业市场价值吸引外来资本,形成农村地区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1.社会网络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农村社会网络能充分结合农村地域系统的区位结构和资源禀赋,合理参照最新的农业市场形势,通过农业产业联结、农业生产要素集聚、农业技术渗透、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提供有效的组织结构。同时,在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过程中,农村社会网络利用通畅的交易与合作信息传递渠道,既能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科技含量低等农业产业化基本约束,又能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培育过程中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尺度。
2.社会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从城市主导的空间集聚为特征的城乡区域发展逐步走向城乡互动、空间融合的区域发展,需要农村社会网络的持续推动,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农业新内生式发展要素优化组合。农村社会网络可以有效打通产业、生态、教育、医疗、文化等多维一体的城乡通道,积极发挥社会资本的协作再生产的优势,还可以通过合理调节农产品动态供需平衡,打通农业发展内循环,满足农业的经济、社会环境需求㉖。农村社会网络还具有吸收干扰和冲击的复原能力,通过一个或多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关系节点的交互反馈,确定驱动和障碍因素,通过节点拓展和联结重建来调解矛盾,进而进行再创新和再变革来提高城乡交流发展的能力。
3.社会网络改善农业人力资本
由于我国耕地分布分散化、碎片化的特点,现有以小农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在短期内无法实现根本性变革。借助农村社会网络可以不断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逐步提高农民现代化水平,利用农村社会网络引进高素质人才,构建掌握农业资本、管理、技术、信息等发展要素的人才结构,推动人力资本动态累积。此外,还能搭建良好的协作参与机制,培育农业主体创新能力㉗。
4.社会网络催化农业创新引擎
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农业新内生式发展之路应聚焦农业创新,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搭建农业全产业链创新体系,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提供引擎动力。农村社会网络能加快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扩散农业技术,促进多领域、多行业、多环节协同创新,增加农业产业链的技术优势。基于农村社会网络内生优势的农业创新既能实现农业新内生发展的增值效益,又使得农业创新收益最大程度内化于农村地域系统,促进农业创新目标由生产向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过渡㉘。
五、以产业融合促进农业新内生式发展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既为农业新内生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对农业产业融合提出了新要求。农业产业融合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通过利益联结推动农业产业功能拓展,提升区域农业竞争力,最终实现新内生式发展。
(一)发展高质量的农业经营和服务组织,发挥社会协同优势
农业农村部2020年印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强调,创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农业内生动力。中国农业产业融合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与创新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带动农业全产业链,打造多功能农业。新内生发展模式下的农业经营组织要高度重视农民发展主体权利、构建农企利益共同体,促进农业经营结构与农村地域系统资源禀赋相契合,通过农村社会网络匹配农业消费需求。高质量的农业服务组织能够通过市场化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㉙,在 “产前、产中、产后” 三阶段服务上形成 “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不断加强涉农重点领域政府、社会扶持,探索区域内生式社会化服务模式,助力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㉚,打好防范化解农业重大风险攻坚战,将农业利益最大化趋向 “三农” 。
(二)强化技术要素扩散渗透力,提升融合主体核心竞争力
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产业融合应积极强化农业技术渗透,提升本地农业资源价值和产业融合竞争力。要将农业创新作为 “三农” 工作的重点推进,提升新内生式农业共同创新能力,紧紧围绕 “以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谋篇布局。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强调要因地制宜地激发农业创新动力,参照区域生物自然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区域创新研究,增强技术元素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渗透支持。加快促进农业科技向应用实践转化,通过提供有利的技术环境支持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邻域间产业融合,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政府应该建立新的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推广的创新激励体制和风险补偿机制,搭建长期稳固的技术依托制度,壮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借助信息化、网络化等技术手段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开展科研院校同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合作,提高产业融合主体的核心竞争力㉛。
(三)深化土地流转等机制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在已有的农地流转制度框架下,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强调,在统筹地域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素质、社会保障水平等基础上㉜,继续创造性地开展农地流转模式改革探索,顺应农业市场化、规模化、信息化以及调动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性等方面的发展要求。同时,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在坚持保护耕地的原则下,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集体成员依法平等享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收益㉝。新时期推进农业新内生式发展应着眼于城乡地域系统 “人+地+业” 协同发展,积极引入城乡融合协作机制,创新城乡土地配置与管理制度,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路径。只有从根本上改革农业农村制度,才能产生干预和治理农业农村的内在推力,实现内生于农村的农业自我积累和持续㉞,而非打造 “城市附属品” 或 “城市赝品” 。
(四)重塑农民参与主体地位,推动人才振兴带动农业振兴
产业融合的推进既要坚持扶农、惠农、富农的原则,更要培养农民的自身发展能力。农民获益多少取决于资源支配能力的大小,为农民 “赋能” 可以改善农民的弱质性,增强农民的经济交换力、政治协商力以及文化感召力。以增加农户权益为导向,推进农业经济制度、农村政治制度以及农民保障制度改革,激发农民参与农业发展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外,就地取 “才” ,加强农民教育培训,注重乡村本土人才建设,满足农业产业融合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类型农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促进参与型农业创新,重视 “行动中的知识” ,将农业发展的 “创新者” 和 “受益者” 合二为一,鼓励农民参与农业创新,提高农民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真正发挥农民主体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带动方面的内推力。
(五)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新内生发展要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结合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其内涵和发展道路要根据资源禀赋的客观地域异质性有所差别。当前我们应加强农业供给侧改革,以价格机制、确权改革、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支农扶农机制改革为重要着力点㉟,结合农业市场需求和农业宏观发展趋势,形成高效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挖掘农村地域发展优势,健全农业长效发展机制,从而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激发农业新内生发展动力,有助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保证国家农业安全。
六、总结与展望
通过上文基于文献视角的农业新内生发展研究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于 “重城轻乡” 的农村历史遗留问题,农业农村亟需内生发展动力。鉴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期,应构建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模型,探索中国农业新内生式发展的最优路径。本文通过对农业新内生发展约束和动力机制的剖析,提出探寻实现农业新内生发展的模式,实现区域内外各因素整合联动,缓解农业资源禀赋匮乏等约束条件,挖掘根植于本地的内生发展动力。为了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性,仍然需要基于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资料去完善中国农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解释,进行实证分析。
注释:
① 孔祥智、何安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
② [哥]埃斯科巴:《权力与能见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发明与管理》,载《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③ 王志刚、黄棋:《内生式发展模式的演进过程——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④ 参见[日]守友裕一:《内発的発展の道》,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91年版,第121页。
⑤ 参见[日]宮本憲一:《環境経済学》,岩波書店1989年版,第45页。
⑥ M. Barke, M. Newton,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 in Two Rural Areas of Andalusia, Southern Spain,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997, 13(3),pp.319-341.
⑦ P. Midmore, J. Whittaker, Economics for Sustainable Rural System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35), pp.173-189 ;X. Ji, J. Ren, S. Ulgiati, Towards Urban-Rural Sustainable Cooperation: Model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13,pp.892-898.
⑧ 张丙宣、华逸婕:《激励结构、内生能力与乡村振兴》,《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⑨ 刘彦随、周扬、李玉恒:《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地理学报》2019年第12期。
⑩ Y. Li, P. Fan, Y. Liu, 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 Villages,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83, pp.111-124 ;Y. Li, T.Zhou,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Mechanism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i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of Qingzang Plateau, Geography and Sustainability, 2021, 2(3), pp.139-150.
⑪ 朱启臻、杨汇泉:《谁在种地——对农业劳动力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⑫ 陈雨生、陈志敏、江一帆:《农业科技进步和土地改良对我国耕地质量的影响》,《农业经济问题》2021年第9期。
⑬ 王颂吉、魏后凯:《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背景与内在逻辑》,《农村经济》2019年第1期。
⑭ 魏后凯:《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6期。
⑮ 郭晓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求、困境与发展态势》,《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4期。
⑯ 叶兴庆:《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推进城乡双向开放》,《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1期。
⑰ 张月莉、刘峰:《农业集群品牌提升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经纬》2015年第1期。
⑱ 刘俊显、罗贵榕:《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和路径探究》,《农业经济》2021年第9期。
⑲ 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傅昌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
⑳ 张兆同、周应堂:《论市场化农业的制约因素与解决思路》,《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㉑ 戈大专、龙花楼:《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地理学报》2020年第6期。
㉒ 张建国:《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治理体系优化路径研究》,《农业经济》2021年第9期。
㉓ 方志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㉔ 吕德文:《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㉕ 孙九霞:《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自信的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文化传承与空间治理” 专栏解读》,《地理研究》2019年第6期。
㉖ 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地理研究》2018年第11期。
㉗ 张环宙、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㉘ M. Bogers, The Open Innovation Paradox :Knowledge Sharing and Protection in R&D Collabor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1, 14(1),pp.93-117.
㉙ 潘锦云、汪时珍、李晏墅:《现代服务业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产业耦合的视角》,《经济学家》2011年第12期。
㉚ 秦秀红:《农业产业化与农村金融创新的关联性研究》,《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10期。
㉛ 孔祥智、楼栋:《农业技术推广的国际比较、时态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2012年第1期。
㉜ 包宗顺、徐志明、高珊、周春芳:《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4期。
㉝ 张勇、包婷婷:《农地流转中的农户土地权益保障: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 “三权分置” 视角》,《经济学家》2020年第8期。
㉞ 公茂刚、王学真:《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内生发展的作用机理及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㉟ 梅学书:《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决策与信息》2017年第3期。